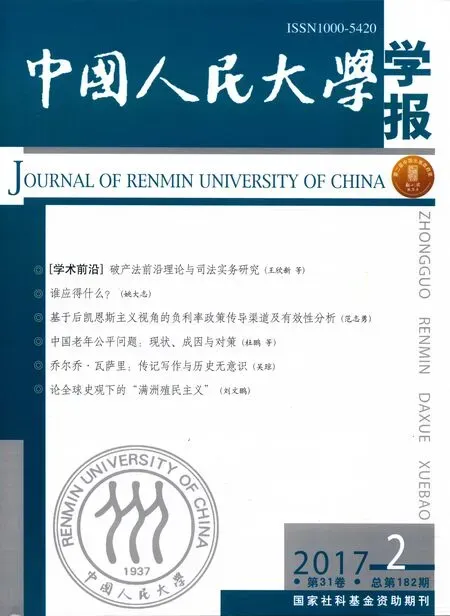女性主義對作者身份的建構
刁克利
女性主義對作者身份的建構
刁克利
女性主義的歷史很大程度上是重新發現和建構女性作者身份的歷史。女性主義既可以看作是生理表征、一種文化現象,也可以看作是意識形態的斗爭。通過對女性主義經典理論著作的解讀,可以發現女性主義與作者理論的密切聯系。探討作者身份對于女性的含義,借以闡明女性主義為建構作者身份而進行的抗爭、局限和貢獻。在文本中心和作者之死的理論潮流中,女性主義對作者身份的建構重申并凸顯了作者的主體性和作者理論的重要意義。
女性主義;作者身份;性別研究;文學理論
20世紀被稱為批評的世紀,文本中心論、讀者中心論和文化研究等構成了文學理論的主潮。傳統的作者中心論被取代,作者的消解與死亡成為壓倒性的理論觀點。如果我們仔細審視女性主義經典理論著作,則不難發現:女性主義的歷史很大程度上是重新發現和建構女性作者身份的歷史。早期的女性作者使用男性筆名代表了身份的藏匿和對男性作者權威的自然認同,雌雄同體的提出意在超越性別的羈絆,對“第二性”的揭示和對女性創造力的挖掘開啟了對女性作者特質的反思。“閣樓上的瘋女人”則以揭示作品背后的女作者為目標,尋找發現和描寫完整的女性作者。
因為要從強大的男性傳統中爭得一席之地,因此女性主義為建構和確立作者身份而進行的論爭就不僅涉及性別的意識形態、經典的界定和文學史的改寫,而且也涉及人類對自身寬容意識的審視。在文本中心論和作者消亡的時代,女性主義重構作品和作者之間的密切聯系,以自身的特殊性重申并凸顯了作者的主體性和作者構建對于文學理論的重要意義。這既是對作者之死的有力反擊,更是對作者的堅定辯護。女性主義經典作家在揭示女性作者的困境,闡釋和建構女性作者身份中所體現出來的性別之惑和性別之爭,對于我們反思現代文學理論,乃至人類思想的狀況都有深刻的啟發。
一、自己的房間為什么重要
《一間自己的房間》(ARoomofOne’sOwn)是女性主義的第一部重要文獻。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強調了物質條件和社會地位對于女性成為作家的必要性。物質條件對于文學創作的重要性在以往的文學研究中很少提到,甚至認為物質條件是最不重要的。而這恰恰是女性主義的獨特視角,也是以往文學研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部分。《一間自己的房間》以女性與小說創作為主題,開宗明義,直接點出女人寫作與物質條件的關系。伍爾夫提出女人要寫小說,必須有年入五百鎊的收入,必須有一間自己的房間。然后她發揮小說家的想象力,以帶聽眾漫步的方式,讓大家隨她體驗女性的歷史。
18世紀前女性默默無聞,女性作家不僅受男性的低看、社會輿論的影響,還難以避免受自己內心的禁錮。到了19世紀,人們仍不鼓勵女性成為藝術家。“藝術家的頭腦必須是明凈的,不能有窒礙,不能有未燃盡的雜質。”[1](P119)這樣才能成就一流的、偉大的、像莎士比亞一樣的藝術家,而女性很難達到這種精神狀態。伍爾夫舉出的幾個例子:科勒·貝爾(Currer Bell)是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的筆名,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喬治·桑(George Sand)都曾用或用了男性筆名試圖掩飾自己的女性身份,結果卻是徒勞。她們無一不是內心沖突的犧牲品。
19世紀幾位著名的女性小說家喬治·艾略特、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簡·奧斯丁(Jane Austen)都沒有子女,寫的都是小說。原因可能是寫小說“不需要格外聚精會神”,她們都沒有自己的書房,都是在全家共用的起居室寫作,在操持家務的間隙寫作。在這種寫作環境中的女作家難免心懷激憤,心境難以達到明凈的止境,即偉大的藝術創作的理想精神狀態。伍爾夫從小說與現實的關系展開論述,道出了女性作者的寫作由于積怨,總不能舒卷自如。女性寫作之缺乏傳統,則是根本的困難。“所謂困難,指的是她們身后缺乏一個傳統,或者這個傳統歷時很短、又不完整,對她們幫助不大。因為我們作為女性,是通過母親來回溯歷史的。求助偉大的男性作家啟示于事無補。”[2](P163)伍爾夫首次提出了關于女性文學的傳統,這一點將得到后來女性主義者的積極響應。
伍爾夫在最后一章提出了雌雄同體的理念,這是伍爾夫留給女性主義的又一大精神遺產。
我們每個人都受兩種力量制約,一種是男性的,一種是女性的;在男性的頭腦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頭腦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的和適意的存在狀態是,兩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中一起……睿智的頭腦是雌雄同體的……在此番交融完成后,頭腦才能充分汲取營養,發揮它的所有功能。[3](P211)
作為女性主義的先驅,伍爾夫論及了女性寫作的方方面面,提出了后來女性主義關注的許多基本問題:女性寫作的物質基礎,獨立意識,去掉自己心中的糾結和戰勝父權社會從輿論和經濟上的壓迫,尋找自己的傳統,堅持自己的特性,追求男性和女性意識的和諧相處,達到雌雄同體的理想等等。對于女性作家面臨的種種問題,她寄希望于社會的改變和女性自身的改變,包括職業的機會均等和社會對女性評價觀念的更新等,時間為一百年。現在,這個時間已經夠了,應該說伍爾夫夢想成真。這些問題很多已經成為女性主義的經典問題。對于探討女性作家必須面對和克服的社會和輿論環境的感受,如何讓女性達到自己理想的創作狀態,成為更好的作家,甚至成為理想的作家,伍爾夫貢獻良多。
二、第二性與創造力
較之于《一間自己的房間》作者的胸有塊壘,西蒙娜·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SecondSexI,II)寫得汪洋大氣。較之于伍爾夫文筆的清澈流暢,波伏瓦寫得厚實而囂張。《第二性》是一部大部頭的著作,兼思想史、女性史、心理史和社會史于一體。
《第二性》分兩部。第一部名為《事實與神話》。波伏瓦從生物學論據、精神分析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解析女性的命運,提出為什么女人是他者?在歷史的過程中,人類把女人變成了什么。她根據存在主義哲學,從人種志和人類史的證據追溯女人的歷史,在對人類歷史進行追溯的過程中,她提出:“這個世界總是屬于男人的”[4](P87)。女人整體上處于附庸地位。她從人類發展史總結出了男人關于女人的神話。男人在她身上尋找整個自我,女人成為非本質事物的世界上的一切。為了證實在普遍看法中存在的女性神話,她分析了五位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角色。結論是:“每個作家在界定女人的時候,也界定了他的一般倫理觀和他對自身的特殊看法:他往往也在她的身上記錄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和自戀的夢想之間存在的距離。”[5](P341-342)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神話是男性心理欲望的表征。有的作家鄙視女人,有的作家崇拜女人,比如勞倫斯就固守必須是男人引領女人。波伏瓦從女性的角度重新評價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看出她們被扭曲被夸張被利用的形象,啟發了后來的女性主義重估文學史、重建女性傳統、重新確立女性形象。
第二部為《實際體驗》,講述和分析女性的成長、處境、辯解和走向解放。波伏瓦在開篇即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6](P9)在最后一部分“走向解放”中,她重點講述了獨立的女人,提出只有工作才能保證女性的具體自由。同時,她也說明,即使女人參加了工作,即使伍爾夫時代女性的大部分問題得以解決,她的獨立仍然是在半路上。
《第二性》是從女人的整個處境研究女人。在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卷尾,波伏瓦分別研究了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角色(男性作家對女人的描寫心理和實質)、從事創造性工作的女演員和想成為作家的女人。像伍爾夫一樣,波伏瓦同樣看到了女性作家的局限,提出了理想的寫作狀態,指出了女性解放的途徑和希冀。波伏瓦提出的創作的理想境界是:“藝術、文學、哲學是在人的自由,即創造者的自由之上重造世界的嘗試,首先必須毫不含糊地成為一種自由,以便擁有這樣的抱負。”[7](P575)對于女性作家,第一要務是生存,是存在。第二要務是自由,獨立。第三才能談得上創造,身心自由、完全放開自我的創造。這種無我之境的創造與伍爾夫所說的明凈狀態相類似。她的這種論述,不但對女性作家和創造性的勞動有啟發,對于了解人類的存在狀況和不同社會階段的人的發展亦有啟發。女人爭取存在的斗爭仍然艱巨。波伏瓦的希望是:
只有當每個人都能將榮譽置于兩性差別之外,置于自己自由的生存難以達到的榮耀中的時候,女人才能將自身的歷史、問題、懷疑、希望與人類的歷史、問題、懷疑和希望等同;只有這時她才能尋求在自身的生活和作品中揭示出全部現實,而不僅僅是她個人。只要她仍然需要為成為人而斗爭,她就不會成為一個創造者。[8](P578)
波伏瓦認為,女性之所以難以成為一流的作家,既有社會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而這自身的原因,究其根源,也來自人類文明占統治地位的男性長期以來對女性的定位,以及女性對這種定位的接受。女人是后天形成的,既是指她自身的發育生長,也說明這個社會輿論環境所助長和引導而刻意為之的結果。所以,一流作家的誕生是作家個人、社會環境、人類文明進程合力的結果,缺一不可。
波伏瓦在《女性與創造力》中更加具體地闡述了女性與創造力的關系。這是她于1966年在日本的演講,與《第二性》相隔近20年,基本觀點不變。她首先強調了女性創造力受制于物質條件,如伍爾夫所強調的一間房子,物質條件與獨立的空間、社會條件和周圍環境等都會制約女性的創造力。其次是女性所獲得的職業機會不均等。再次,藝術家的社會形象與傳統的女性形象不符合,因而會給女性造成極大的心理和社會輿論壓力。這種藝術家的形象也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是以男性意識形態為主導而形成的。第四,傳統女性形象的制約。第五,作家的品質和女性的經歷局限。作家需要標新立異,需要自信和耐心。女作家缺乏這些,咎不在她,而是其經歷所致。
除了剖析女性創造力受制的種種原因,波伏瓦還重點談到了女性作家對世界的抗辯和責任意識不足。創作需要邊緣處境與旁觀角色,這是女性合適的。女性作家與社會同步,認同感高。另一方面這又成為她的局限,使其難以創造出偉大的作品。創作需要旁觀和邊緣,然而,更需要一種深切的責任,這是一種我是主人、舍我其誰的擔當意識。
真正偉大的作品是那些和整個世界抗辯的作品。而婦女卻不會這么做的。她們會批評、駁斥某些細節,但要和整個世界抗辯就需要對世界有一種深切的責任感。這是一個男人的世界,在這個程度上來說婦女是不負責任的。她們不必像偉大的藝術家們那樣去為這個世界承擔責任。[9](P156)
這和她在《第二性》中提到并強調的思想機會毫無二致。可以說,從《第二性》的發表到這次演講的時間段內,波伏瓦并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或者說,她沒有看到女性作家有實質的改觀。也可以說,20年間世界并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
在揭示女性寫作的諸多困境的同時,女性主義論者總會提出自己對理想的文學與理想的作家的向往。伍爾夫和波伏瓦都探討了理想的作家和理想的文學狀態。伍爾夫的文學典范是莎士比亞,波伏瓦推崇的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就所向往的理想的文學狀態而言,對于伍爾夫,是消解了個體存在激憤和超越了個人恩怨的明凈狀態;對于波伏瓦,是超越性的自由和身為世界主人的解釋世界、揭露世界、與世界抗辯的責任感。對于理想作家和理想文學的追求與定義,代表了女性作家的向往和自由寫作的渴望,也是女性主義作者理論的重要特征。
每一代女性主義者都揭示了她們感到親近的時代、階層、種類的女性作家的困境,也都指出了努力和解放的新方向。她們對女性作家困境的揭示,對于理解作家狀況和人類狀況很有意義;她們對文學理想的設定和憧憬,對于理解作家大有啟發。理解女作家,也是理解男作家;理解人類的另一半,理解同樣處境的人類,理解人類性別意識形態的運行和作用機制,也是理解人自身、人的寬容和人的解放,以及人的前途是否可期,人的拯救是否有望。理解女性的文學理想,也是理解文學的特質,理解文學與其他學科的區別,理解人類的智力和情感活動領域,理解文學的獨特作用和魅力,理解人類智力和情感活動的邊界和意義。
三、瘋女人與性別之爭
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庫巴(Sandra M.Gilbert & Susan Gubar)合著的《閣樓上的瘋女人:婦女作家與19世紀的文學想象》(TheMadwomanintheAttic:TheWomanWriterandthe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對19世紀重要女作家進行了視角獨特的透徹研究。著作先檢查了父權文化下作者的概念流變,提出了女性成為作者意味著什么,對女性創造力和男人筆下的女性形象進行了剖析,指出了女性筆下女性形象的雙面性。繼而提出婦女作家的焦慮不是來自于文學傳統的久遠和文學前輩的壓制,而是來自于對女性作者身份的焦慮。接著著作又以洞穴之喻為引子,尋找女性作者的完整性,“最后的這個寓言講述的是一位藝術家的故事”[10](P98)。著作理論構建與文學批評并進,她們以人物是作者的復本為核心觀點和策略,以揭示作品背后的女作者為目標,建立女性主義創作理論。
這部著作對于作者研究至少有三個方面的貢獻:一是她們對作者觀念的溯源大有裨益,其對女性作者身份焦慮的獨特論斷值得借鑒,有助于加深理解作者與文學傳統的關系和文學創新。二是她們所分析的婦女作家多重面具的創作策略,及其所揭示的多重面具背后隱含的作者的憤怒和不平的實質,這有利于解釋女作家的獨特性和創作心理的復雜性。三是她們的女性主義詩學策略構建以所謂的男權文化下的作者為參照,在作者之死風行的年代,她們意圖發現作品背后的作者,這是對作者中心論的認同、對作品是作者內心表現這一信念的堅守。
她們的著作以人物反映作者的觀念,尤其瘋女人為代表的人物作為作者的核心觀點,堅持女性作家和她塑造的某類特殊女性形象的一致性。“正是通過這個復本的暴力行為,女作家才得以實現她自己那種逃離男性住宅和男性文本的瘋狂欲望,而與此同時,也正是通過這個復本的暴力行為,這位焦慮的作者才能為自己表達出以昂貴的代價換來的怒火的毀滅,而那種怒火已郁積良久、再難遏制。”[11](P85)她們試圖通過文本中的這種特殊的(發瘋的)女性形象揭示藏匿在這形象背后的女作家的真實面目,描述女性寫作的特色。在男性文化氛圍中,女作家是性別的囚徒,亦必須是打破這囚籠的戰士。
在她們對男權文化主導下的作者權威批判的前提下,最后恰恰是利用了作者權威界定建立自己的女性詩學。她們視作品中的某些特定的人物形象為作者的復本,甚至將作者等同于人物,乃至于把作者看作是文本唯一的意義源的觀點,是傳統作者中心論的再現。這和她們在著作開始宣稱的作者是男性、上帝是男性的考據是一個循環。以此復興女性作者和女性文學傳統是否可行,值得商榷。這難道說明,女作家要回歸男性傳統,皈依男權文化嗎?這無疑會給批評女性主義的批評家授之以柄,亦讓后結構女性主義者難以認同。
后結構女性主義者認為,作者的概念本身就是男性的或父權的建構——作者的權威本身是父權制的固有方面。像她們倆這樣的批評家面對的危險是在描寫一個女性作者傳統時,她們簡單地重復和加強了父權方式,加強了堅持“把文學看作個人經驗的簡單、直接的表現,這種觀念本身就是把作者當作父權思維的一部分”[12](P286)。在《性別/文本政治》(Sexual/TextualPolitics)中,托麗爾·莫伊(Toril Moi)指出,把作者當作文本的來源、起源和意義,就是把父權制和作者身份聯系在一起。“要解除這一權威的父權實踐”,女性主義批評家需要“和羅蘭·巴爾特一起宣告作者之死”[13](P62-63)。
的確,在作者之死的年代,她們對作者中心論的堅持雖然可貴,但亦飽受質疑。那么,如果換一種思路,這或許說明:作者是文本的創造者,是意義的權威的命題本身就是真理?如果相信后者,則一切矛盾都可化解,并不會引發性別的戰爭。作者可以是男性的,也可以是女性的,無論其是何種性別,但他/她一定是作為創造者現身的。
另一個啟示:她們研究的是女性主義詩學,誠如她們自己所言。更確切地說,她們的研究是女作家創作理論。女作家的創造動力、作家身份、創作資源、創作特點,作家自我與人物形象之間的顯性與隱性關系,作家創作動因與人物塑造、情節設置的策略等。這一切的背后是假定在男權文化中,女作家身份的特殊性、壓抑性、邊緣化,以及女作家對此的抗爭的意圖與應對的策略。這為作者理論和作家創作研究進行了理論探索,提供了例證。核心啟示是:女性作者理論必以作者中心論為基礎,創作理論必須是以作者中心論為依據。舍此,女性作者理論誰與歸,創作理論何去何從,則都會成為疑問。
那么,假如把她們的研究稱之為女作家創作理論研究,則這種研究對于所有的作家,不論男女,皆有益處。如果不把它局限于理論的建構,就不會引起那么激烈的批評。它研究的是創作理論,對于作者如何選擇、利用、構建自己的素材、主題和情節,如何描寫自己的核心意象和人物形象,都有啟發。
女性像男人一樣寫作,還是以女人的身份寫作?這是一個問題。女性批評家一方面拒斥女性身份或女性作者身份,同時卻試圖以之為特色,以一定模式的寫作來表明它。雖然女性主義批評遠不止被局限為以上簡述的兩端,從早期的“雙性同體詩學”(an androgynist poetics)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女性美學”(female aesthetic)、70年代中期開始的“女性作家批評”(gynocritics)以及80年代末期興起的對性別差異進行比較研究的性別理論(gender theory),作者性別和作者身份始終是這些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即使如西蘇強調男人和女人都可以進行女性寫作,以性別界定文本特征也是因循了男性與女性之別的思路,更勿論作者性別這一不可更變的明顯事實而必然與作者身份問題密不可分。
女性主義對性別之爭似乎無以逃遁。女性寫作對于身體的束縛難以擺脫。女性作家是以自己獨特的生理經驗、身體體驗為素材為驕傲,還是以之為恥,掩飾逃避,這是伍爾夫意識到的問題,她從中看到了自身的或者說她所處時代的局限。這是以后的女性作家也必須要面對的。女性主義的寫作是為了強調自己的性別,還是為了超越性別?有沒有一種可以強調性別又超越性別的方法準則?女性主義的性別之惑像極了民族的和世界的關系之爭。如果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那么,能說越是女性的就越是文學所需要的嗎?如何成就女性,如何表達女性?這不僅是女性主義的問題,也是當今世界的問題。
四、反擊與啟示
作者問題是女性文學批評觀念的中心。“幾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女性主義的斗爭基本上就是為作者身份而進行的斗爭。”[14](P145)與作者之死針鋒相對,女性主義著力發掘女性文學傳統,揭示女性作者的身份特征和身份焦慮。她們從整理女性文學傳統出發,構建女性作者身份,既有自身的需要,說明了作者理論的生命力,又是對作者之死的有力反擊。
女性主義反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揭示了作者之死的男性文化背景和歷史特征。南希·米勒(Nancy K.Miller)認為,消除作者可以被看作是對女性主義話語基礎和身份政治的攻擊。作者之死的理論遠不是導致關于作者的新思考,而是對任何寫作身份的壓抑和禁止,因此也是對女性作者的身份、身份認同、壓抑和禁止抑制。因為婦女從來沒有被認為擁有男性作家聲稱的那種作者地位,因而,作者之死并不適合她們。“作者的移除并沒有為修正作者觀念騰出多大空間。”[15](P104)
在女性主義者看來,作者之死是傳統的男性作者權威之死,對作者的解構可以被看作是男性作者的解構,對一定男性思維的解構和父權本身的解構。如果作者之死中的作者是男性,那么,作者之死與女性無關,女性作者需要的不是死亡,而是發現和重生。
事實上,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作者之死的理論,而是一個新的作者觀念,這種新的作者觀念不是天真地強調作家是原創性的天才,創造了歷史之外的美學作品,而是在談到婦女作家對歷史構成的反應時不會抹殺其不同和重要性。[16](P148)
因此,女性主義之作者重建不是在需要解構時建構一個壓抑性的權威,而是要被發現、被肯定,給予女性作者以身份認同。可以說,在一個特殊的時代,作者之死不但對女性主義對作者理論不起作用,反而激發其走向相反的方向,即作者建構的方向,義無反顧地挺進。
女性主義對作者之死的反擊沿用了傳統作家研究的方法,繼承并堅守了作者中心論。女性主義作者理論闡述了女性之所以能夠成為作家,或者妨礙其不能成為作家的各方面因素。這些方面恰恰都是作家中心論的要素。女性主義以為自己爭取權利、表明自己的方式復興了作者中心,復興了作者與作品的密切聯系。文本是有性別的,性別屬于作者。相對于自古希臘文學以來漫長的西方文學史,女作家的歷史的確不長。女性主義批評家重估文學傳統,重新定義文學批評。與其說是恢復,不如說是建立了自己的傳統。女性主義對作者重建具有異乎尋常的特殊意義。
女性主義是一場綿延不斷的運動、行動、實踐,也是一種理論、批評視角和思維方法。女性主義發展先后受到了許多批評理論的影響。女性主義者善于將新的理論運用于理論構建,廣泛吸納,產生了各種女性主義分支,論及亦惠及各種女性階層。其多方面思考女性問題,討論視角不斷累加,從一種女性主義到另一種,從一個階段的女性主義到另一個階段,不斷增添新的概念。女性主義探討過的問題有:對生育的態度,家庭和婦女角色,社會主體生產,種族和男性,女性與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法律權利,教育機會,身體構成,心理構成,性別歧視,文化建構,壓迫與壓抑,帝國主義統治,帝國主義的文化身份,帝國主義的話語場,等等。女性主義始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擴展為對男女地位不均衡的原因探討和背景揭示。女性主義不斷調整批評的矛頭,擴大批評的對象和范圍,使得一切造成種種不平等或不均衡的原因和背景成為批評的對象和開火的靶子,直陳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的潛流和表象下的真實和本質。女性主義幾乎檢查了一切批評理論和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幾乎所有新的理論對女性主義都有啟發,都能為之所用。女性主義的力量也在于此。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考慮女性主義的性別之爭和性別之惑,亦可以對女性主義做如下理解:女性主義是一種思維方式,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方法論。通過女性主義批評,女性主義作者希望達到的目的決不僅僅是性別的。正如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ok)所說:“我期望對帝國主義的深刻批判會引起第一世界讀者的注意,這至少可以擴大閱讀的政治疆界。”[17](P621)同理,女性主義的作者身份的建構也決不僅僅是對女性作者的思考,而是對文學理論,或者是對于世界的思考。因此,在思想層面上,女性主義對作者身份建構帶給我們的更大啟發是:每個作者都是女性。這樣說的意思是,每一個作者都會經歷和女性作者相似的歷程:尋找傳統,發現自己,拓展更新,融入并成為傳統。也可以說,每個人都可能是女人。其意思是,每個人都可能會經歷到女性所經歷過的各種情景和心路歷程:被拒斥、被邊緣化、抗拒力爭、進入主流。這是女性主義作者建構對于文學理論的貢獻,也是女性主義思維方式對于人類的貢獻。
[1][2][3] 弗吉尼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4][5] 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I),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6][7][8] 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II),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9] 西蒙娜·波伏瓦:《女性與創造力》,載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10][11] Sandra M.Gilbert & Susan Gubar.TheMadwomanintheAttic:TheWomanWriterandthe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2] Peggy Kamuf.“Writing Like a Woman”. In Sally Mc Connell-Ginet, Ruth Borker, and Nelly Furman(eds.).WomenandLanguageinLiteratureandSociety.New York: Praeger, 1980.
[13] Toril Moi.Sexual/TextualPolitics:FeministLiteraryTheory.London: Methuen, 1985.
[14] Seán Burke( ed.).Authorship:FromPlatotothePostmodern-AReader.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 Nancy K.Miller.“Changing the Subject: Authorship, Writing, and the Reader”. In Seán Burke (ed.).Authorship:FromPlatotothePostmodern-AReader.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 Cheryl Walker.“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Author”. In Seán Burke(ed.).Authorship:FromPlatotothePostmodern-AReader.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 斯皮瓦克:《三個女性文本和一種帝國主義批評》,載朱立元、李鈞主編:《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責任編輯 張 靜)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thor Identity of Feminism
DIAO Ke-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to a great extent, is a history of rediscover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 author identity.The reading and reflection of theoretical classics of Feminism helps to interpret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s of being a female author, and shed light on the struggles, limits and contributions in forming and constructing female author identity.Against the trend of the text center and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Feminism,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redefines and highlights the author subjectivi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author theory.
Feminism; author identity; gender study; critical theory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作家理論與作家生態研究”(10XNJ026)
刁克利: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