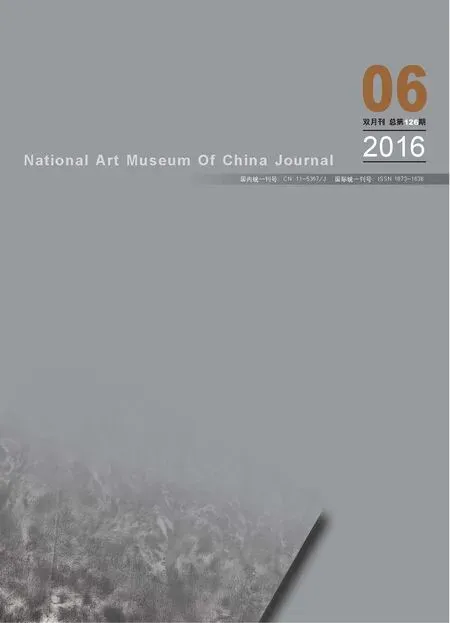以中國美術館為例看“精英”與“大眾”雙重結構的時代特征
□ 蘇典娜(中央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
以中國美術館為例看“精英”與“大眾”雙重結構的時代特征
□ 蘇典娜(中央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
近幾十年來,市場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推動中國的社會轉型,“大眾文化”在大眾消費時代融入公眾生活之中,構成了我們的日常經(jīng)驗與消費行為,對中國的文化建構與研究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也影響了藝術博物館的建設與發(fā)展,藝術博物館紛紛實行免費開放政策,吸引觀眾參觀。作為國家級美術館的中國美術館,在這樣的轉型中如何實現(xiàn)“官方主流精英文化控制下的大眾化”與“精英文化影響下的大眾化”,從而體現(xiàn)出一種博物館結構上的雙重性特征,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一個國內(nèi)藝術博物館案例。
中國美術館1963年正式開館,其定位是收藏、研究、展示以“五四”以來的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為主的國家造型藝術博物館,是唯一的一座由新中國第一代領導親自籌劃的國家級美術館。[1]因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背景的特殊性,該館的發(fā)展過程不同于歐美國家的重要藝術博物館——既不像大都會博物館是由私人捐贈、建立的國家博物館,也不像大英博物館是將私人財產(chǎn)經(jīng)國會議案變?yōu)閲夜藏敭a(chǎn),而是屬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結合的歷史產(chǎn)物。這使得其結構的雙重性特征更為突出,更為復雜,構成了不同于西方的“精英化”與“大眾化”的雙重性關系。
中國美術館作為營造國家藝術形象的重要文化機構,積極響應國家相關政策方針,為人民大眾服務,做百姓喜聞樂見的展覽,構成了新的精英與大眾的歷史沖突與整合。首先,從該館的展覽組織方式分析,可以看到其組織結構和展覽敘事結構具有雙重性的特征。
中國美術館一方面掌握著國家資源和話語權,承擔了每五年一屆的全國美展的重要展覽工作,更多以宣傳官方的文藝政策為己任,成為“官方主流精英文化控制下的大眾化”的重要宣傳機構;另一方面參與到重要的國際藝術交流和當代藝術的推動工作之中,運用了策展人的展覽體制,積極發(fā)揮現(xiàn)代美術館的綜合作用,進行現(xiàn)當代藝術博物館的轉型,從而進一步與知識分子的“精英化”發(fā)生關系,同時實現(xiàn)了當代藝術的“精英文化影響下的大眾化”的訴求。
在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建館初期的中國美術館由“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簡稱“中國美協(xié)”)代管,形成了圍繞“美協(xié)”辦事的管理體制,舉辦展覽主要是通過申報獲得上級領導批示舉辦展覽。“中國美協(xié)”其創(chuàng)立初衷有益于凝聚藝術創(chuàng)作群體的民間力量,組織藝術創(chuàng)作與理論研究,同時該機構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代管,在展覽機制上推行的是由“各地分會—全國美協(xié)”推選、下級單位貫徹上級意圖的工作方式,在新中國特殊時期的藝術創(chuàng)作指導思想上還提出了“領導出主意、群眾出生活、畫家出技術”的“三結合”創(chuàng)作原則。[2]中國美術館作為全國美展的主場地,從官方角度展覽、評獎、收藏全國美展作品,這進一步鞏固了中國美術館的權威機構地位,國內(nèi)的中青年藝術家也紛紛拿出個人創(chuàng)作成果在中國美術館展出。例如1992—2001年(2002年5月中國美術館因進行改造裝修而閉館),每年展覽場次平均為174場,特別是在2001年更是達到了年度展覽205場的高峰,其中以中青年藝術家的展覽為主體[3]。值得注意的是,以2002年為例,在這一年中國美術館閉館前舉行的36場展覽里,中青年藝術家的個人展覽就占據(jù)了14場,其中主要是文化部、中國美協(xié)、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中國書畫聯(lián)誼會,地方美術家協(xié)會、地方宣傳部、地方人民政府主辦的個人展覽[4]。
這些數(shù)據(jù)一方面說明了中國美術館推動了中國美術界的蓬勃發(fā)展,另一方面說明中國美術館在當時的定位更像是一個面向廣大人民群眾的“展覽館”,還未建立公共教育部,缺乏對于藏品的系統(tǒng)研究與學術交流,自主策劃的展覽較少,更多是承接“美協(xié)”以及被動接受其他外來單位的展覽,其展覽存在著說教意味濃厚、展覽形式單一等問題。這一方面刺激了前衛(wèi)藝術家對于中國美術館的官方展覽的批判,另一方面也促使前衛(wèi)藝術不斷試圖進入中國美術館,打破當時的僵化體制,形成了“精英”與“大眾”在中國美術館的組織結構上的博弈。

中國美術館
作為一個處于經(jīng)濟轉型期的國家美術機構,中國美術館舉辦展覽的主流思維留有計劃經(jīng)濟時期的尾巴,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并不是以策展人作為主要的展覽策劃模式,但是中國美術館的工作者和相關人士也認識到了策展人的獨立性和重要性。這在90年代體制改革以前亦有體現(xiàn),以1989年2月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現(xiàn)代藝術大展為例,這個展覽是由批評家集體策劃的重要現(xiàn)代藝術展覽,最后因不可控制的偶發(fā)事件而被迫關閉,中國美術館也一度禁止行為藝術和裝置藝術的展出。1989年3月文化部還下達了對中國美術館加強管理的文件,指出中國美術館一樓大廳相對可固定展出“代表中國美術創(chuàng)作最高水平的藏品”[5]。該文件確立了該館的一樓圓廳、東西廳為館藏陳列廳的布局,可想而知前衛(wèi)藝術在當時的邊緣性,這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美術館的空間結構的“精英化”。直到2008年借助北京奧運會提供的開放平臺,蔡國強在中國美術館的個人展覽“蔡國強:我想要相信”,該館才恢復了大型裝置藝術的展出。這個展覽在一樓入口大廳展出了大型裝置作品《草舟借箭》,還在一樓圓廳展出了大型的火藥草圖和藝術家自己制作的大事記,并且在其他展廳展覽了《撞墻》《不合時宜:舞臺一》等裝置作品,實現(xiàn)了當代藝術所推崇的“大眾化”。
全國美展和當代藝術展覽為中國美術館帶來了博物館組織結構和展覽結構的雙重性愈發(fā)凸顯,甚至在當代藝術影響下的全國美展本身的發(fā)展變化上得以體現(xiàn)。回顧1980—1981年由文化部、中國美協(xié)主辦的“第五屆全國美展”以及“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該展覽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從獲獎作品上看,一方面《人民和總理》《沒有共產(chǎn)黨就沒有新中國》《紅燭頌》等這樣喜聞樂見的政治題材作品依然是獲獎主體,但是全國美展和全國青年美展改變了單一的政治題材模式,題材更為豐富,涌現(xiàn)了《父親》《一九六八年×月×日雪》《再見吧,小路》等重要的“傷痕美術”作品,開辟了中國現(xiàn)代藝術的先河,也開創(chuàng)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在中國美術館大展上的新局面。另外,2014年全國美展首次設立了實驗藝術展區(qū),雖然沒有在中國美術館展出,而是選擇在一座更為前衛(wèi)的私立美術館——今日美術館展出,但是可以看到當代藝術的雙重性對于博物館空間結構的雙重性進一步影響。
其次,我們從中國美術館的觀眾定位和公共教育的發(fā)展,來看其主體結構和傳播結構的雙重性,這種雙重性也集中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中國美術館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引下要求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與其現(xiàn)當代藝術藏品自身以及相關藏品研究所具有的“精英化”的整合與沖突的關系。
國內(nèi)學者西川曾指出,中國的大眾在網(wǎng)絡自媒體時代擁有一種評判藝術的權力,即所有的藝術應該能看懂,看不懂的藝術會被認為是糟糕的,除非開始賣錢[6]。而筆者認為,大眾所擁有的這種權力,其實在“官方主流精英文化”占據(jù)主導文化地位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
這種現(xiàn)象在1979年7月鄧小平發(fā)言后,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指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藝術成就,應當由人民來評定……在文藝家與廣大讀者之間,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討論,提倡擺事實、講道理”[7],同時指出“衙門作風必須拋棄,在文藝創(chuàng)作、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8],這有益于人民大眾對藝術作品做出自己的選擇和評判。
在1979年11月,出現(xiàn)了時任中國美協(xié)主席的江豐在全國美協(xié)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批評的現(xiàn)象——主要供給人民大眾閱讀的美術作品越來越不被重視了。江豐在提到藝術民主的問題時,引用了周恩來1962年文藝創(chuàng)作座談會上的發(fā)言,“妨礙藝術創(chuàng)作的各種框框一定要打破,但藝術為人民大眾服務的這個大框框決不能跑掉,因為這是個立場問題,也就是社會主義藝術的核心問題”[9]。江豐談及國內(nèi)的美術學院不像歐美和日本一樣教抽象畫的原因是,“人民看不懂,也不愛看”[10],并認為對待人民大眾的態(tài)度的不同,正是社會主義藝術與資本主義藝術的性質根本不同點。之后,江豐在1981年的講話中明確表示抽象派藝術之類的美術流派不會受到人民群眾的喜愛,在社會主義中國是沒有發(fā)展前途的。[11]
1986年,文化部制定了《美術館工作暫行條例》,規(guī)定“美術館是造型藝術的博物館”,并且強調“美術館在各級政府文化部門的領導下,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的方針,努力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做出貢獻”[12],再次強化了藝術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問題。1993年,當時的國家領導人為中國美術館題詞“努力建設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xiàn)代美術博物館”[13],等等。
自改革開放以來,貫徹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成為國內(nèi)美術界的工作重點,中國美術館作為國家級美術館更是首當其沖,賦予了人民大眾評判藝術的權力。受到國內(nèi)相關方針、政策的影響,藝術如何為人民大眾服務?如何展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如何讓人民大眾看得懂藝術作品?展示之后對人民大眾有何益處?這些問題亦成為中國美術館長期以來致力于探索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初,轉型期的中國美術館依舊保留了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tǒng),將精力集中于舉辦讓“人民大眾”看得懂、喜歡看的展覽的工作上。這使得中國美術館不同于歐美藝術博物館相對平行對待展示與研究的情況。
另一方面,進入市場經(jīng)濟時代的中國美術館,兼具了有中國特色的雙重性結構的另一種特征,即“精英文化影響下的大眾化”。
2006年,政府印發(fā)了《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將中國美術館的二期改擴建工程納入塑造國家文化形象的重大項目和工程建設計劃里,并提出國有博物館、美術館等公共文化設施對特殊人群免費或優(yōu)惠開放制度,以及健全文化市場,鼓勵引導文化消費。2011年,這一年中國美術館作為國家級美術館積極響應國家的免費開放政策,這一舉措被認為是從精英性質真正轉向了大眾性,拆除了“高雅藝術殿堂”的圍墻,使得更多的人走進美術館。而免費開放政策帶來的影響、意義,在2011年的《中國美術館年鑒》里得到了重點的宣傳介紹和較為細致的研究[14],這就進一步體現(xiàn)了中國美術館在“官方主流精英文化”控制下和“精英文化”影響下的“大眾化”特征。
在這個時期,盡管中國美術館開始成為人民群眾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美育場所,但是中國美術館對觀眾卻缺乏廣泛接納的態(tài)度,更不鼓勵對公眾全面免費開放。在2002年的《中國美術館年鑒》里,我們能看到研究人員論述提高中國美術館的場租和門票合理性、重要性的文章,例如:
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下的展覽運作方式的確立,也促進了我們思想觀念的轉變。我們現(xiàn)在的認識是:當一個展覽被認定可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后,它必須交付展覽所用展廳的使用費和展覽必須的其他費用。而不必謀求或許美術館的減免場租,因為美術館的展廳是一種國家資源,在市場經(jīng)濟下,誰也不能無償?shù)卣加泻褪褂谩C佬g館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擔有對國家資產(chǎn)保值和增值的責任。[15]
盡管中國美術館在將社會教育作為美術博物館的最終價值體現(xiàn),但是其工作人員的態(tài)度是門票和場租應該適當提高,與“大眾化”的取向存在著矛盾,其實質也是一種機構內(nèi)在的精英主義價值觀。這樣的認識與當時人們對于市場經(jīng)濟和文化產(chǎn)業(yè)關系的認識的不完善有關,特別是未形成健全的、活躍的藝術市場。民營美術館的發(fā)展還不成氣候(例如今日美術館、上海龍美術館、昊美術館等一批頗具影響力的民營美術館還未開館或處于建館初期),也缺乏國家對于民營美術館的政策支持,地方性的美術館基礎設施不完整,因而缺乏民營美術館、藝術區(qū)、畫廊對于國家藝術博物館的競爭力,當時北京地區(qū)的藝術展覽機構的格局仍處于少數(shù)藝術博物館(如故宮博物院、中國美術館、中華世紀壇等)占主導地位的局面。
雖然20世紀90年代我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改革以來,計劃經(jīng)濟體制淡出了歷史舞臺,但是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mào)易組織,文化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國內(nèi)藝術博物館的展覽才趨向于多元化。隨著更多的國際藝術博物館的工作交流,以及相關理論研究被介紹到中國,使得國內(nèi)涌現(xiàn)了一大批民營美術館、畫廊、拍賣公司等,形成了相對完善的藝術市場。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美術館才逐漸在擺脫單一的傳統(tǒng)理念,逐漸改變對于門票和場租收入的依賴,豐富博物館的功能,并于2005年設立了公共教育部,以實現(xiàn)藝術博物館“公共性”的轉型。
隨著由“精英文化”分裂形成的“前衛(wèi)文化”(以現(xiàn)當代藝術為主體)從地下走向殿堂,從邊緣走向主流,加之美術館對于“公共性”的訴求,中國美術館在一定范圍內(nèi)進行自我調節(jié),以適應現(xiàn)當代藝術的發(fā)展,并警惕市場和金錢支配的力量,努力實現(xiàn)文化精英提出的“公共性”。由西方精英知識分子提出的“公共性”概念本身,體現(xiàn)了“公共領域”的自由、民主原則和批判性。[16]這個概念對于新時期的中國美術館的影響,正體現(xiàn)了“精英化”對中國美術館的“大眾化”傾向的影響,以及兩者重新整合的關系。
在中國的博物館學界,人們長期以來對“精英化”與“大眾化”問題的爭論不止,其問題的實質是博物館如何選擇和平衡精英文化受眾與基礎文化受眾的問題,換句話說,是一個藝術博物館承擔雙重責任的問題。只要我們把“精英”“大眾”這兩個層面作為文化概念問題來考究,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精英對象和民主對象都是相對的,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是可以交互轉換角色的,這就是互補結構的關系。在中國的藝術博物館中,仍有不少的管理者還在困惑于服務大眾還是精英的問題,甚至還在按照“傳統(tǒng)”習慣地把“觀眾”的概念等同于“群眾”的概念,把藝術博物館更多地當作了青少年、幼兒教育的場所,企圖對觀眾只進行單向的說教式的教育。其實更值得關心的問題應該是更新對于觀眾的認識。這是因為,當今國內(nèi)的藝術博物館面對的受眾實際上早已是知識多樣化、視野國際化、興趣個性化、審美多元化的觀眾“聚合體”[17],而不是需要進行常識教育的單一團體。
在我國的藝術博物館和美術館的服務結構轉型的時候,上海、廣州、深圳、成都已有不少私人美術館、博物館走在了時代的前列,相對而言,中國美術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都為中國的公立和學院美術館的改革做出了表率。
我們同時清晰地認識到,雖然國內(nèi)的官方藝術博物館界近年來也進行了理念的革新,開始積極面對“大眾化”的轉向與“精英化”的知識結構平衡的問題,但在實踐中,目前的管理機制還不能完全適應一個大國藝術博物館事業(yè)發(fā)展的時代要求。國內(nèi)藝術博物館普遍傾向于“大眾化”的發(fā)展趨勢,紛紛實施免費對公眾開放政,注重參觀人數(shù),但在收藏、展示、學術研究、教育的研究還不夠深入,業(yè)務管理不夠國際水準,一方面忽略精英文化和經(jīng)典藝術對現(xiàn)代文明的啟示作用,另一方面對前衛(wèi)作品價值缺乏及時的預判和收藏,致使許多優(yōu)秀的作品流失,被過度炒作的商業(yè)作品卻泛濫于市。很多地方的官方藝術博物館依舊還停留在“展覽館”,甚至展覽租借地的業(yè)務水準上,而非真正的美術館和藝術博物館,容易被市場左右,缺乏美術館、博物館自己的專業(yè)價值判斷和審美批評。
回顧藝術博物館的演變歷史,正是博物館的知識權力所代表的“精英化”與博物館的知識傳播所代表的“大眾化”交織在其歷史之中讓其生機勃勃地發(fā)展。我們慶幸已經(jīng)走出了單純讓藝術成為說教公教的時代,到了現(xiàn)代圖像信息爆炸時代和商品消費社會,既要避免“娛樂至死”的局面,又要避免讓藝術的歷史走向“廢墟”或“陵墓”的境遇。未來的藝術博物館會如何發(fā)展?其結構雙重性的悖論特征是否會繼續(xù)存在?會呈現(xiàn)怎樣的新面貌?又是否會給“后博物館”時代帶來新的機遇和變化?這都是博物館學界亟待思考的問題。
關于“精英化”和“大眾化”的雙重結構問題,是一個“精英”與“大眾”誰創(chuàng)造了歷史的問題和為誰服務的問題。事實上,這兩個問題于理論上,早在海德格爾的煩神的故事中就得到了解決[18],只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誰的博物館”有了更加豐富的內(nèi)涵。現(xiàn)代主義之后的藝術博物館將受到更多的挑戰(zhàn),我們需要下更多的功夫研究藝術博物館結構的悖論問題,本文只是拋磚引玉,嘗試借中國美術館的案列,梳理出一條相對清晰的歷史脈絡,為實現(xiàn)當下公立的藝術博物館的結構轉型,提供一種基礎的理論依據(jù)。
注釋:
[1]楊力舟《歷時性的飛躍——中國美術館改造裝修工程巡禮》,載《中國美術館年鑒(2002年)》,第13頁。
[2]賈方舟《21世紀:中國的美術館時代——兼論美術館在當代美術發(fā)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載于中國美術館編《社會轉型與美術演進——紀念中國美術館建館4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頁。
[3]原始數(shù)據(jù)參見裴建國《十年展覽回顧》,《中國美術館年鑒(2002年)》,第124頁。筆者對數(shù)據(jù)進行了重新統(tǒng)計。
[4]展覽數(shù)據(jù)來源于裴建國《十年展覽回顧》,《中國美術館年鑒(2002年)》,第124頁;羅萍《中國美術館2002年展覽一覽》,《中國美術館年鑒(2002年)》,第31-33頁。
[5]楊力舟《開拓創(chuàng)新,辦出特色》,載《藝苑摭言——楊力舟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頁。
[6]根據(jù)中央美術美術學院美術館“場域,空間,展呈與博物館”研討會現(xiàn)場視頻整理。視頻網(wǎng)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4NjE3Njg0.html
[7]《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載于《中國文藝年鑒(1981年)》,文化藝術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頁。
[8]同上,第30頁。
[9]江豐《藝術為人民大眾服務——1979年11月21日在美協(xié)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的發(fā)言》,載《中國文藝年鑒(1981年)》,第625頁。
[10]同上注。
[11]江豐《在青年油畫作者創(chuàng)作座談會開幕會議上的講話(摘要)(1981年8月10日)》,載《中國文藝年鑒(1981年)》,第440頁。
[12]文化部《美術館工作暫行條例》,1986年11月10日,引自http://www.law-lib.com/ lawhtm/1986/3958.htm
[13]馬鴻增《美術館的學術定位與個性特色》,載于中國美術館編《社會轉型與美術演進——紀念中國美術館建館4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1頁。
[14]相關文章如《年度工作總結》(第13-15頁)、《中國美術館迎來了全面的“免費時代”》(第66-67頁)、《在中國美術館免費開放啟動儀式上的講話》(第68-69頁)、《中國美術館免費開放成效觀察》(第70-75頁)、《從媒體傳播看社會對美術館的期待與要求》(第81-83頁)等。
[15]裴建國《十年展覽回顧》,載《中國美術館年鑒(2002年)》,第124頁。
[16][德]哈貝馬斯著,曹衛(wèi)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頁。
[17]參見[德]弗德利希·瓦達荷西著,曾于珍、林資杰等譯《博物館學—德語系世界觀點(理論篇)》,臺北:五觀藝術管理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81頁。
[18]參見[德]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jié)合譯《存在與時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版,第2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