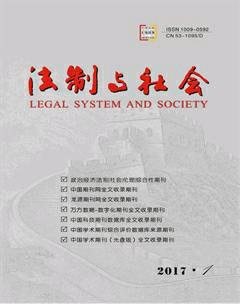暴恐犯罪行為的對策思考
摘 要 本文立足于我國暴恐犯罪實際狀況,從暴恐犯罪概念的界定、特征和我國暴恐犯罪的現狀、策略以及相關優秀經驗等多個方面分析國內暴恐犯罪發生的原因,同時結合我國與暴恐犯罪斗爭的經驗及實際情況,并從偵查部門的視角,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反暴恐犯罪對策與措施。
關鍵詞 暴恐犯罪 偵查 情報
作者簡介:侯曉翔,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1.115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得到迅猛發展,綜合國力也不斷提高,但我國國情特殊,一些歷史遺留問題與復雜的國際情勢相結合,導致我國也難免遭受暴恐犯罪行為的侵害。目前針對暴恐犯罪方面的研究也頗多,筆者通過對暴恐犯罪的概念和我國暴恐犯罪的現狀以及應對暴恐犯罪行為對策的角度進行了探討。
一、暴恐犯罪的界定
當界定暴恐犯罪時,大多學者首先就對恐怖主義進行定義,暴力恐怖犯罪概念源于國際上的恐怖主義概念,但又與恐怖主義概念有區別。在2014 年昆明火車站“3·01”事件發生后,國內媒體在進行與暴力恐怖犯罪活動有關的報道中,開始逐漸在標題和報道正文中大量使用“暴恐犯罪”一詞。暴恐犯罪即暴力恐怖犯罪。有國內學者認為暴力恐怖犯罪(有時稱“暴恐活動”),主要是當前反恐怖斗爭的專業術語,它是刑事犯罪的一種,是特指刑法規定的,以極端恐怖的方式,使用暴力手段實施的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且應受刑罰處罰的具有特定意義的犯罪行為 。也有國外學者荷蘭政治家P·施密特從暴力恐怖犯罪的百余種定義中總結歸納出五個要素:暴力或武力、政治目的、恐懼或者不安、威脅以及可以預料到心理作用或者作出的反映 。當前針對我國的暴力恐怖事件呈多發頻發態勢,我國針對暴恐犯罪立法方面有了新的成果,2016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反恐怖主義法》對“恐怖主義”、“恐怖活動”、恐怖活動組織及其人員和“暴恐犯罪”等概念進行了界定,其中列舉了“恐怖活動”包括的情形,主要是指恐怖主義性質的下列行為:“(一)組織、策劃、準備實施、實施造成或者意圖造成人員傷亡、重大財產損失、公共設施損壞、社會秩序混亂等嚴重社會危害的活動的;(二)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或者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的物品,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戴宣揚恐怖主義的服飾、標志的;(三)組織、領導、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的;(四)為恐怖活動組織、恐怖活動人員、實施恐怖活動或者恐怖活動培訓提供信息、資金、物資、勞務、技術、場所等支持、協助、便利的;(五)其他恐怖活動。”根據多方觀點和法律法規的規定,筆者認為暴恐犯罪是指個人或組織采取爆炸、破壞等暴力手段,以政治、宗教等訴求為主,造成或者意圖造成人員傷亡、重大財產損失、公共設施損壞、社會秩序混亂等,制造恐怖氣氛,宣揚極端主義或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行為。
二、暴恐犯罪的特征和現狀
(一)犯罪目的多樣性
暴恐犯罪的目的,就是引發恐怖活動的緣由或背景因素。暴恐犯罪的目的遠非一般的奪命傷財等普通刑事犯罪,暴恐犯罪最重要的是通過制造對社會造成極具負面性的事端,以達到政治恐嚇、要挾社會、政府的目的,這是區別暴恐犯罪與其他犯罪活動尤其是嚴重暴力犯罪活動的重要特征。實施暴恐犯罪行為的個人或者組織在社會和公眾中制造恐怖氣氛,產生蝴蝶效應,給一些乃至世界大多數國家的主流社會和民眾帶來揮之不去的巨大精神壓力和心理恐懼,直接引發社會混亂,對國家的政局穩定、經濟發展等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二)犯罪對象的不確定性和犯罪活動的突發性
暴恐犯罪的對象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國家重要的領導機關、影響國計民生的要害單位或者具有意義的特殊場所。還會經常濫殺無辜殃及平民百姓。在某一項具體的暴恐犯罪活動中,除非有可靠情報,犯罪對象是誰,以及具體實施的時間、地點、方式等一般不為人們所知曉。因此,暴恐犯罪活動亦具有突發性的特點。
(三)暴恐犯罪的破壞性
從我國以及全球已發生的暴恐犯罪活動看,暴恐犯罪活動往往對一個國家、地區的政治、經濟諸多方面造成不可估量、難以挽回的損失和極為惡劣的影響。同時,還會造成大量的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損失,更為嚴重的是暴恐犯罪活動所引發的人們心理產生的恐慌,是短期內無法彌補或平息的。一旦發生恐怖活動,就會嚴重影響社會安定和政治穩定,人們心理的緊張和恐懼情緒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平復。
(四)高度的組織性
當前暴恐犯罪大多由恐怖組織實施的,這些恐怖組織具有內部層級分明,組織結構嚴密,紀律約束嚴酷,經濟實力雄厚和巨額資金易于籌集等特點。因此,這些恐怖組織實施的暴恐犯罪活動,往往使得國家有關部門和民眾難以預料。
(五)政治企圖十分明確
境內外“三股勢力”相互勾結,大肆宣揚“雙泛主義”,鼓吹新疆獨立,妄圖通過暴恐犯罪活動分裂國家政權,在新疆建立所謂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新疆分裂勢力所進行的暴恐活動不僅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而且還顯露出大國博弈的痕跡。21世紀以來各大國之間逐漸轉化為無硝煙的非武裝較量,比較常規的方式便是對他國進行思想文化滲透以及意識形態的攻擊,傳播分裂主義、極端主義,挑撥民族仇恨,制造和蔓延社會恐慌,破壞我國穩定大局,掣肘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西方敵對勢力大打“疆獨”、“藏獨”、“臺獨”牌,通過一些NGO組織以慈善資助等幌子向“三股勢力”提供資金,并在境外網歪曲事實,企圖制造國際輿論對我國進行戰略訛詐,阻礙中國和平崛起。
三、我國暴恐犯罪活動的對策
(一)完善反恐立法機制
應對暴恐犯罪一定要依法進行。2016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反恐怖主義法》,彌補了我國對于反恐怖主義犯罪這一塊的法律空白,特別是對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增加和規定了財產刑,這使我國對參與暴恐犯罪活動的行為人在財產方面的打擊有法可依。同時,《反恐怖主義法》將資助恐怖活動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的個人的,或者資助恐怖活動培訓的,以及為恐怖活動組織、實施恐怖活動或者恐怖活動培訓招募、運送人員的行為;為實施恐怖 活動而準備兇器或危險品,組織或者積極參加恐怖 活動培訓,與境外恐怖活動組織、人員聯系,以及為實施恐怖活動進行策劃或者其他準備的行為;以制作資料、散發資料、發布信息、當面講授等方式或者通過音頻視頻、信息網絡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或者煽動實施恐怖暴力活動的行為;利用極端主義煽動、脅迫群眾破壞國家法律確立的婚姻、司法、教育、社會管理等制度的行為;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物品、圖書、音頻視頻資料的行為;拒不提供恐怖、極端主義犯罪證據的行為;以暴力、脅迫等方式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志的行為增加規定為犯罪,使我國打擊恐怖活動犯罪的刑事法律依據更加嚴密。進一步對暴恐犯罪各種現象進行立法機制方面的完善,同時也講賦予偵查主體更全面的偵查權,對于犯罪活動的預防和有效精準打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二)加強情報信息工作
暴恐犯罪活動一般情況都是有預謀的,從組織策劃實施犯罪開始,到資金的募集,到后面有針的對犯罪實施者的系列培訓以及具體犯罪活動的實施都是環環相扣的,掌握到每一環節的情報,對于打擊犯罪都十分重要。情報部門又屬中樞部門,基于情報信息所作的研判材料,不僅能給領導層提供決策依據,也能有效控制和打擊暴恐犯罪活動。
一是情報機構的優化。結合國內反恐工作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立足于暴恐犯罪的特點和趨勢建立專門的情報機構。國內針對反恐的機構有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軍隊的相關情報機關,在某些方面特別是情報工作方面重合,誠然各個機關對于暴恐情報的收集有利于通過競爭關系提高大家工作的積極性,但是對于情報信息的收集和處理方面由于之間分處不同機構,所占有資源也不相同,導致重復工作或者進行無用的工作,例如某公安機關也在對涉嫌暴恐活動的人員進行調查,由于相關人員的特殊和敏感性,一部分人員已被國家安全機關抓獲,但公安機關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繼續對相關人員抓捕,這無疑造成了偵查資源的浪費。建議不同的情報機構和反恐部門設立聯絡員,對指定和獨辦案件之外的情報采取共享機制,或者在特殊情況下共同執行偵查權;
二是加強情報研判工作。情報研判工作就是對所收集的情報進行分析和研判并給出主觀或者客觀的看法和意見,情報信息如“食材”一樣,首先要挑選好的“食材”篩選有價值的情報,并將這些情報加工成美味的“佳肴”也就是做好研判工作。在進行情報信息工作時,首先,要有針對的收集和篩選具有價值的涉及暴恐犯罪方面的情報,其次,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對相關情報進行核實,并根據核實情況采取初步行動,要在情報研判分析作出之前,充分完成情報的處置工作。同時要對暴恐犯罪活動的情報信息進行整理和歸檔,可能一些情況暫時沒有很大用處,但對于之后的反恐工作將會有指導意義,形成某一情勢的情報信息網,一定條件下各情報的關聯性才會凸顯,這將大大提高反恐工作的效率。
三是提高情報工作人員的素質。如果說對情報信息的研判分析比喻成“做菜”的話,那么“菜”做的好不好吃,情報研判做的好不好,就取決于情報工作人員這個“廚師”的水平好不好。情報工作人員不應局限于本單位本部門的情報人員,應當把各部門工作人員都發展成情報員,并遴選情報工作好的人員到情報部門進行輪訓,讓所有工作人員都熟知情報工作的流程,每個人都參與情報工作,人人都是情報員、戰斗員。同時,應當定期對情報人員進行培訓,或者引進特殊人才充實反恐情報工作。此外,也應當做好反恐工作的宣傳,讓全民參與反恐,建立與完善群眾反恐情報信息系統。這個系統是十分必要的,可以獲得到所有與暴恐活動相關聯的民生動態情報,也與我黨的群眾路線相符。總之,以情報工作為立足點,結合各種方式和途徑,全面掌握暴恐組織結構、資金流向及人員情況等各類信息。
(三)完善技術偵查措施獲得證據的轉換程序
根據最新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公安機關在立案后,根據辦案需要,經過批準,可以對恐怖活動犯罪案件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所收集的材料可在刑事訴訟中作為證據使用。這使公安機關的技術偵查部門在偵辦暴恐案件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但是由于恐怖活動犯罪的特殊性、復雜性,很多證據都是通過技術偵查手段或者“特情”取得的,這類證據在取證、庭審質證和證據轉換等方面存在一定難度,并且在實際工作中技偵工作人員可能獲得到能確切證實暴恐活動的線索和證據,但是在證據轉化方面由于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而不能夠用作法律意義上的證據,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強調法無授權即禁止,在這方面可能存在明知有犯罪行為卻無法有效打擊犯罪行為的情況出現。建議對相關立法條目進行細化、優化,特別是對于技術手段所獲取的線索和材料轉換為刑事訴訟中的證據方面的簡化和優化應當給予法律授權的支持。
(四)加強國際合作
全球日趨一體化,各國之間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暴恐犯罪活動不僅僅對一國造成了危害,往往會波及到其它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因此,我國應當順應當下反恐工作的國際形勢,充分利用我國日益上升的國際影響力,積極開展反恐工作的國際合作,在打擊我國暴恐犯罪組織的同時,通過雙邊或多邊合作震懾境外“三種勢力”,嚴防其與我國暴恐犯罪組織進行勾聯活動,增加暴恐犯罪的犯罪成本,強化國內外打擊力度,樹立起反恐大國的標桿。
注釋:
任克勤.當前暴力恐怖活動犯罪的內涵、特點與偵查防控對策.專論·爭鳴.2015年1月10日.
葉高峰、劉純法.集團犯罪對策.中國監察出版社.200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