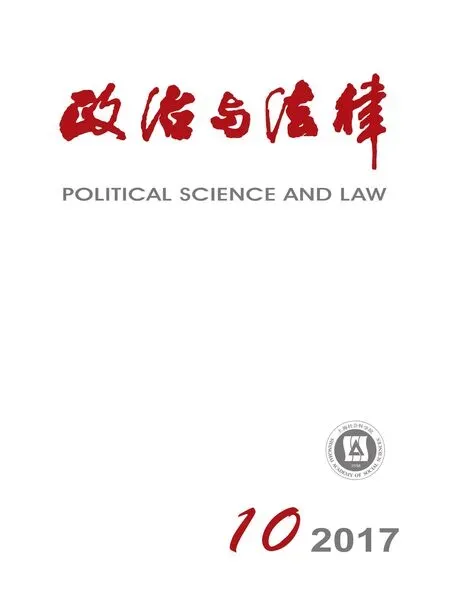被害人教義學在德國:源流、發展與局限
(北京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871)
被害人教義學在德國:源流、發展與局限
車浩
(北京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871)
德國的被害人教義學肇始于刑法分論若干具體罪名的研究,從被害人自我保護和刑法輔助性原則的視角研究個罪,主要集中于詐騙罪中的被害人因素。之后被害人教義學持續發展,從最初涉及的詐騙罪和侵害私人秘密罪出發,不斷地向越來越多的構成要件擴展和蔓延,并試圖在分則體系與總則體系之間架起橋梁。與此同時,被害人教義學也面臨著各種爭議,比較基礎性的爭議集中于對刑法輔助性原則的不同理解及這種思想在刑事政策的導向上是否正確。目前德國的刑法教義學仍處于不斷深化、滲透、傳播及爭取共識的進程中。從被害人視角切入刑法問題,將傳統的行為人單維視角的理解模式,改變為“行為人-被害人”雙維視角的理解模式,這才是被害人教義學的概念應當承載的使命和理論目標。被害人教義學能夠在規范層面上理解并規范化地處理被害人的行為對行為人的影響,通過一般性的理論構建回應被害人的規范需求。一個更具包容性和解釋力的被害人教義學理論體系將給未來的刑法理論革新帶來深刻的影響。
被害人教義學; 刑事輔助性; 刑事政策;“行為人-被害人”雙維視角
筆者于本文中所稱的被害人教義學,是從被害人角度展開的刑法教義學。它以被害人作為思考的出發點,落腳點是合理有效地回應被害人的規范需求。傳統的刑法理論都是從行為人出發,單向度地沿著行為人的行為這一方向去思考刑法問題,展開不法與責任的判斷。被害人教義學試圖打破這一傳統的理解模式,構建一種“行為人-被害人”雙維視角下理解刑法的思考模式。它的最初靈感來自于犯罪學領域中的被害人學研究,特別是在一些犯罪人與被害人有互動關系的場合,被害人的行為在事實上也不同程度地影響到行為人的行為。如何在規范層面上理解這種事實性的影響?如何在法教義學的領域中規范化地處理這種影響?如何通過一般性的理論構建,回應被害人的規范需求?這些就是被害人教義學的問題意識和價值追求。
筆者于本文中將要完成的工作,是對于德國的刑法學同行們所界定的“被害人教義學”的源流、發展和局限,做一個盡量簡明的梳理和評價,這樣也有利于分析、回應上述問題。被害人教義學在德國的狀況(或者說)德國版的被害人教義學(既對筆者以往的思考構成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和借鑒,也讓筆者感到不能滿意,由此推動筆者以此為基礎,努力構建一個更具有包容性和解釋力的被害人教義學理論。
一、首次亮相:“錯誤”的登場
當德國學者阿梅隆于1977年發表論文,討論詐騙罪中受騙者的錯誤與懷疑這個問題時,他并不會想到,由此引發的,不僅是在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中熱衷于從被害人角度展開討論的傾向,而且激發了一種被德國同行中的批判者稱之為“被害人教義學”的一般性理論的風潮。這種理論將行為不法的判斷與被害人聯系在一起,野心勃勃地想要在眾多構成要件的限縮性解釋中發揮作用,并在刑法總論領域中占有一席之地。不過,在阿梅隆最初的論文中,他只是把目光盯在詐騙罪客觀構成要件幾個行為特征中的“錯誤”這個要素上。*Amelung, Irrtum und Zweifel des Getaeuschten beim Betrug, GA, 1977, S.在他看來,只有那種不包含任何具體懷疑的認識偏差,才能認定為錯誤。如果一個人已經對他人言行的真偽產生了具體懷疑而仍然處分財物,此時,這就不再是陷入錯誤的財產處分,而是一種帶有冒險性質的投機行為。對于這種自冒風險的投機行為,刑法沒有保護的必要性。
這就涉及如何理解和評價現代社會中的交往行為。在一個匿名化的、高度復雜化的經濟交往的環境中,整個社會交往充滿了不確定性。人們應當對自己與他人的財產交易安全抱著謹慎小心的態度。換言之,帶著審慎甚至懷疑的眼光去從事交易,是一個交易者必備的品質。例如,通過各種渠道去驗證交易條件是否屬實,要求對方提供相應的擔保,發現有不確定、不安全的或者其他值得懷疑的因素時停止交易等等。在阿梅隆眼中,這些都是一個正常的交易者可以采取的自我保護措施,只有在這些措施無效之后,交易者才可以去尋求國家的保護。然而,如果交易者已經對交易產生了具體的懷疑,卻仍然置這些本可以輕易采取的自我保護措施于不顧,而在投機未遂的情況下,完全依賴國家的救濟,這樣只會催生一群懶惰的投機者。因為這相當于是把消除交易風險的任務一股腦地交給了國家,只想著利用刑罰的強制力來威懾潛在的欺詐者,卻不肯在自己能夠消除風險的情況下去自我保護。對此,阿梅隆表達了明確的反對意見,他認為刑法不應當承擔對所有的受騙者進行全面保護的任務,那些已經產生具體懷疑卻仍然交易的人并沒有陷入錯誤,而僅僅是在投機,對此,應當將其排除出刑法保護范圍。*Amelung, Irrtum und Zweifel des Getaeuschten beim Betrug, GA, 1977, S. 7f.
為了準確理解阿梅隆的觀點,這里用另一種從被害人本身特點入手研究詐騙罪的觀點進行對比。比阿梅隆更早,瑙克在1974年提出,對于簡單、拙劣、易于識破的欺詐行為,應當排除出詐騙罪的構成要件范圍。在這些騙局中上當受騙者,往往都是一些沒有經驗的無助者,但是這樣一來,刑法就要承擔著全面培訓公民交往能力的任務,這對于刑法而言,是過于奢侈的工作。因此,刑法不應當給愚笨者或缺乏經驗者提供幫助,而是應該讓他們有機會去自我訓練自己的決斷能力。一言以蔽之,刑法并不是用來訓練智力和彌補安全感的工具。*Naucke, Die kausalzusammenhang zwischen Taeuschung und Irttm beim Betrug, FS Peter, 1974, S.117f.按照這種觀點,如果人們去信任那些明顯拙劣和虛假的騙術,刑法就不應當保護這種信任;相反,只有那些復雜的、不易被識破的騙術,才具有刑事可罰性。只是,由此必然會引出的爭議是,輕信的受騙者不受刑法保護是否符合詐騙罪的立法價值。與此相聯系的結論是,面對一個拙劣的騙術而輕信上當者,可能是愚蠢和智力缺陷者,但是,對這種社會意義上的不保護弱者的歧視性立場是有爭議的,這涉及非常復雜的價值判斷的問題。
與瑙克的觀點不同,阿梅隆自認為,他的觀點并沒有陷入上述價值判斷的泥潭中。在他看來,對存有具體懷疑者不予保護,不是一個是否值得保護的價值判斷的問題,而是一個是否需要保護的問題。因為輕信的人未必就是愚蠢的人,他們之所以受騙上當,往往不是由于愚蠢或智力缺陷,而是由于不積極運用自己的智力進行審慎的判斷。因此,對已經有了具體懷疑但仍然不進行自我保護的被害人而言,不提供刑法保護,排除的不是被害人的應保護性或者說值得保護性,而是需保護性或者說保護必要性。排除的根據,也不是根據被害人的愚蠢或道德方面的價值判斷的理由,而是根據他在處分財產的心理事實。*Amelung, Irrtum und Zweifel des Getaeuschten beim Betrug, GA, 1977, S. 9f.那就是,交易在客觀上存在足以令人懷疑的事實,被害人主觀上也對交易的真實性產生了具體懷疑,但仍然處分了財產,這就是放棄了本來可以實施的自我保護。從構成要件特征上講,此處排除了德國《刑法》第263條中“錯誤”的要素,行為人不構成詐騙罪。于是,為后來那些支持或反對“被害人教義學”的德國學者們共同認可的該理論的核心原則,在阿梅隆的這篇文章中就雛形出現了:如果被害人有適當的手段可以自我保護卻不使用,那么以輔助性保護為原則的刑法就沒有必要介入。
阿梅隆的文章是被害人教義學正式亮相的開山之作。從一開始,被害人教義學就從刑法分論而非總論的舞臺上登場,奠定了從被害人自我保護和刑法輔助性原則的視角研究個罪的基調。在此文發表之后的幾十年中,德國刑法學界涌現了大量從被害人的角度分析詐騙罪構成要件各個特征的文獻。詐騙罪中的被害人因素,成為一股學術潮流,當然也引發了此起彼伏的激烈爭論。
二、縱深發展:鏖戰于詐騙罪的主戰場
詐騙罪,向來被認為是驗證和演練被害人教義學的最佳場所,是“一個深入檢驗被害人教義學效能和極限的例子”,因為“迄今為止被害人教義學在德國刑法第263條的構成要件上面被說明得最詳盡”。*[德]許乃曼:《刑事不法之體系:以法益概念與被害者學作為總則體系與分則體系間的橋梁》,載許玉秀、陳志輝等編譯:《不移不惑獻身法與正義——許迺曼教授刑事法論文選輯》,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臺北)2006年版,第221頁。可以說,在詐騙罪構成要件的各個要素上面,都集中了大量的從被害人角度展開的討論。
首先,是關于“錯誤”的研究。在阿梅隆前后,哈賽默、赫茨伯格、庫恩、弗里希等學者都曾經對“錯誤”展開過研究。例如,赫茨伯格主張用被害人同意的意思瑕疵理論來解決詐騙罪中的錯誤問題。通過與德國刑法中的侵占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進行對比,赫茨伯格認為,詐騙罪中的錯誤范圍,與在侵占罪或毀壞財物罪中,認定那些足以影響被害人同意效力的瑕疵標準是一樣的。*Herzberg, Funktion und Bedeutung des Merkmals “Irrtums” im § 263 StGB, GA, 1977.按照這種觀點,詐騙罪中的處分行為,是一種有瑕疵的被害人同意,同意的內容就是財產損失。如果這種同意是在沒有意思瑕疵的情況下做出的,那么,被害人就沒有陷入錯誤,就應當排除詐騙罪的既遂。詐騙罪的解釋能夠與其他財產中的同意瑕疵的解釋在體系上保持協調一致,這是赫茨伯格自認為他的理論的一個重要優點。至于錯誤這一要素的功能,赫茨伯格認為并不像阿梅隆所說的那樣,是有助于刑法輔助性原則的實現,而是將那些被害人沒有意思瑕疵的情況下處分財產而造成財產損失的情形,從詐騙罪的既遂中排除出去。*在赫茨伯格1977年發表這篇論文的時候,阿茨特已經在1970年的著作中提出了“法益錯誤說”的理論。他將被害人同意中的錯誤分為兩類,一類是法益(相關性)錯誤, 另一類是與法益無關的錯誤,主要是指動機錯誤。 前者會使同意無效,后者并不影響同意效力。Arzt, Willensmaengel bei der Einwilligung, 1970.其后,等到這種理論成為德日刑法學界的通說之日,就被有心的日本學者如山口厚拿去,用在了對詐騙罪的錯誤的解釋上面,成為山口厚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實際上,將被害人同意瑕疵理論與詐騙罪中的錯誤聯系在一起,這個思路的始作俑者是赫茨伯格,他當時在文中也提到了法益相關的認知缺陷(rechtsgutsbezogene Fehlvorstellung)。只是,山口厚對法益錯誤說在詐騙罪中的引入更為徹底,那些與法益無關的錯誤,都不屬于詐騙罪的“錯誤”,由此,實現了這一要素的排除功能。參見[日]山口厚:《刑法各論》,王昭武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頁。赫茨伯格對阿梅隆的批評遭到了哈賽默的反駁。在哈賽默看來,在德國刑法規定的侵占罪和毀壞財物罪中,立法者并沒有要求以“錯誤”為構成要件特征。詐騙罪中被立法者明確規定的“錯誤”與同意是兩回事,不應該扯在一起。這樣反而會使得“錯誤”這個要素的功能變得模糊不清。*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s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Irrtumsmerkmals in § 263 StGB, 1981, S.124.
又如,盡管弗里希贊成阿梅隆從被害人角度探討錯誤要素,因為“目前德國刑法理論對被害人行為的價值和意義關注太少,沒有清晰的說明”,*Frisch, Funktion und Inhalt des “Irrtums” im Betrugtatbestand, FS Bockelmann, 1978, S. 657.但是,其對于阿梅隆由此與刑法輔助性原則相聯系的做法卻大不以為然。刑法輔助性原則是一個普遍性原則,為什么它僅僅在阿梅隆所說的詐騙罪這種關系型犯罪中凸顯出來,卻在其他犯罪的構成要件中沉默?在弗里希看來,這種“在一個獨特的、個別的概念(錯誤)身上賦予普遍性原則的功能”的思考方式是錯誤的,因為個別的法律概念的功能僅在于指向和確定特定的事實,而類似于刑法輔助性這樣的普遍性原則,正好是在這一過程中起到限制的作用。*Frisch, Funktion und Inhalt des “Irrtums” im Betrugtatbestand, FS Bockelmann, 1978, S. 656.在批評阿梅隆將錯誤概念的功能與刑法輔助性不當關聯之后,弗里希提出了他所理解的錯誤的功能。作為自我損害型的財產犯罪,被害人的財產處分處在詐騙罪構成要件的中心。弗里希眼中的錯誤,實際上是一種財產處分行為的預備狀態。處分財產的預備行為范圍寬泛,而錯誤的功能,就是標志著一種會導致被害人財產損失后果的特定的、危險的預備形態。*Frisch, Funktion und Inhalt des “Irrtums” im Betrugtatbestand, FS Bockelmann, 1978, S. 660f.這就為詐騙罪的處罰限定了范圍。
與阿梅隆的觀點相呼應,這個領域中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哈賽默,進一步把德國《刑法》第263條規定“錯誤”的立法任務與自我保護可能性聯結起來。哈賽默在著作中通過“危險強度”的概念來引入被害人的作用。立法者規定構成詐騙罪需具備“錯誤”的特征,就是在描述一種典型的被害人缺乏保護可能性的狀況,它與立法者規定的另一個構成要件特征“欺詐”一起,在法律上共同設定了詐騙罪的危險強度。按照哈賽默的劃定,詐騙罪屬于一種關系型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具有互動關系,犯罪的成立需要一方對另一方行為的配合,對詐騙罪而言就是處分財產。這同時也意味著,被害人在這種侵害模式中發揮著共同作用,他對于阻止這種侵害完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s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Irrtumsmerkmals in § 263 StGB, 1981, S.54, 55.簡單地說,在詐騙罪的結構中,一方面是來自于行為人的危險行為,另一方面是來自于被害人的自我保護,只有當前者的強度達到了足以讓后者無效的情況下,詐騙罪的刑法保護才是必要的。
可以看出,哈賽默嘗試在詐騙罪的欺詐行為的特征與錯誤特征之間,建立起一種功能性的關聯。正是由于危險強度足夠狡猾和欺騙性的欺詐行為,讓被害人陷入到無法進行自我保護的錯誤狀態之中,才處分了財產遭受了損失。相反,如果行為人的騙術沒有對被害人產生那么強的效果,卻讓被害人產生了具體懷疑,*哈賽默把被害人的主觀狀況區分為三種形態:主觀確信、模糊懷疑和具體懷疑。主觀確信是指被害人確信自己得到的信息完全是真實完整的;模糊懷疑是指被害人對于交易的不安全性有模糊的感覺;具體懷疑是指被害人的懷疑程度超過了模糊的感覺,而是對特定相關事實的真實性產生疑問。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s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Irrtumsmerkmals in § 263 StGB, 1981, S.132ff.此時,被害人就有充分的能力并且也被期待去進行自我保護,因為他并沒有陷入一個錯誤,從而也不需要刑法的保護。*對于產生具體懷疑卻不自保的情形,哈賽默列舉了兩種類型加以說明。一種是懶惰的被害人,另一種是投機的被害人。這兩種被害人在有具體懷疑的情況下都有自保的可能性,但是基于自身原因而仍然處分財產,這就屬于未陷入錯誤。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s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Irrtumsmerkmals in § 263 StGB, 1981, S.162.由此,哈賽默就把詐騙罪構成要件中的“錯誤”特征,功能化地詮釋為刑法輔助性原則的實現。這在思路和結論上與阿梅隆保持了一致性。不過,與阿梅隆一樣,哈賽默的觀點也遭受了不少批評。麥瓦德認為,按照哈賽默的理論,恰恰會把那些需要保護的弱勢群體排除在詐騙罪的保護范圍之外,這有違社會倫理的基本底線。*Maiwald, Literatur Bericht zur R.Hassemer, ZStW96(1984), S.70ff. 按照哈賽默的表述,處于愚笨、缺乏考慮和經驗而處于確信或模糊懷疑的人群,應當保留其應保護性。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s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Irrtumsmerkmals in § 263 StGB, 1981, S.165. 所以,麥瓦德的批評有對哈賽默的觀點曲解之處。這些人,而不是哈賽默所說的懶惰者或投機者,可能更符合麥瓦德所說的弱勢人群。
其次,關于“欺詐行為”的要素,也有不少學者從被害人角度展開研究,如前述瑙克的觀點。根據理性的、有正常生活經驗的一般人的標準,那些通常情況下根本不會上當受騙的低級、拙劣、易于識破的騙術,應當被排除在詐騙罪的欺詐行為之外。*瑙克認為,下面案例中的被害人就不應當受到詐騙罪的保護:一個廚師做廣告,謊稱自己是一個性工作者,只要有人按照指定的地址付款,就會上門提供服務。瑙克認為如此拙劣的騙術,根本沒有達到欺詐行為所要求的狡猾的標準,被害人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Naucke, Die kausalzusammenhang zwischen Taeuschung und Irttm beim Betrug, FS Peter, 1974, S.112.當然,瑙克也為精神病人和兒童的保護留下了余地。這些人雖然可以被歸入愚笨或缺乏生活經驗之列,但是這種狀態的出現,并非他們自身不努力去學習和適應,而是由于不可改變的原因,因此,這些人也應當受到刑法的保護。只是在瑙克看來,這種欺詐行為已經不屬于詐騙而是盜竊或者侵占。*Naucke, Die kausalzusammenhang zwischen Taeuschung und Irttm beim Betrug, FS Peter, 1974, S.116.埃爾默贊成瑙克在詐騙罪構成要件層面考慮被害人共同責任的想法,同時認為,應當在個案中仔細考察欺詐行為是否屬于一般人眼中的簡單、拙劣的低級騙術。*Ellmer, Betrug und Opfermitverantwortung, 1986, S. 148f.
還有一些學者從被害人角度討論詐騙罪各個要素之間的因果關系。例如,瑙克認為,通過改變欺詐與認識錯誤之間的因果關系法則,使用相當因果關系說而非條件說,可以對詐騙罪的構成要件進行限縮解釋。相當性的因果關系意味著進行規范的判斷,由此可以評價欺騙行為的強度以及對騙術無力抵抗的被害人。在瑙克看來,在詐騙罪中運用相當因果關系說,就是將被害人共同責任的思想融入詐騙罪教義學的表現,由此可以限制刑法適用,讓交易者增強財產安全意識。*Naucke,Die kausalzusammenhang zwischen Taeuschung und Irttm beim Betrug, FS Peter, 1974, S.118f.又如,布萊認為,在被害人對行為人所說情況產生懷疑的場合,并不是像阿梅隆那樣從否定“錯誤”的角度來排除可罰性,而是因為,這種懷疑與財產處分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不過,布萊在原則上也同意阿梅隆關于被害人自我保護的想法。他之所以否定錯誤與財產處分之間的因果關系,就是因為產生了懷疑的被害人原本能夠自我保護,或者說,本來有機會避免自己的財產遭受損失。*Blei, Strafrecht BT, 1978, S. 199.不過,布萊的觀點也受到了希倫坎普的批評。被害人在產生懷疑時仍然處分財產,恰恰說明騙術的高明。懷疑并不能直接否定錯誤,而只是說明,這個錯誤因為可避免而危險性較小而已。Hillenkamp, Der Einfluss des Opferverhaltens auf die dogmatische Beurteilung der Tat, 1983, S. 25f.
比這種因果關系的討論進一步規范化,也更加具有總論色彩的分析,是庫爾特將客觀歸責理論引入到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的分析之中。構成要件的保護范圍是客觀歸責的下位規則之一,它意味著,如果風險實現的類型并沒有包含在構成要件的效力范圍或者規范保護目的的范圍之內,就不能將此歸責給行為人。庫爾特將此一般原理引入到詐騙罪中。*Kurth, Das Mitverschulden des Opfers beim Betrug, 1984, S. 171ff.按照他的觀點,在被害人共同負責的情況下,雖然行為人通過實施騙術創設了一個法所不允許的風險,但最終的結果并不是這個風險的具體實現,而是由于被害人自己的疏忽所導致的,因而不能輕易地將此結果歸責給行為人。還需要進一步判斷的是,在共同負責的場合,究竟是行為人的欺詐還是被害人的過失對整個風險實現有支配地位。如果是后者,即被害人在共同責任中占統治地位,就不能再把結果歸責給行為人,而只能由被害人自己承擔。
綜上所述,在詐騙罪的領域,從被害人角度展開研究可謂是應者云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國刑法學的語境中,“被害人教義學”這頂帽子,只戴在了其中部分學者的頭上。換言之,并非上文評述的與被害人相關的詐騙罪研究,都被德國學界稱之為“被害人教義學”。這個被部分德國學者搶注“商標”的一般認定的理論符號,包含了特定的內涵,因而也只有部分德國學者愿意用在自己身上。
三、開疆拓土:向其他構成要件延展
“被害人教義學”的說法,幾乎是在一面世,就遭遇了“新瓶裝舊酒”的指責,認為這個概念只不過是把早在它出現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工作,歸入這個名目之下而已。*S/S/Lenckner, vor 13 Rdnr. 70b.令人尷尬的是,就連被許乃曼引為同道的埃爾默,*在許乃曼的劃分中,自己和阿梅隆以及哈賽默屬于一派,埃爾默、庫爾特屬于另外一派,但都屬于被害人教義學的陣營,只是路徑不同而已。Schuenemann, Die Schwindel in der Dogmatik und die doppelte Weisheit der Viktimo-Dogmatik, FS Beulk, 2015, S. 543.也并不愿意被歸入“被害人教義學”的陣營中,他不無譏諷地指出:“被害人教義學只是一個蓋上印戳的‘流行詞’,古老的認識被貼上了新的標簽就作為新產品出售了。”*Ellmer, Betrug und Opfermitverantwortung, 1986, S. 268.與之相似,研究主題多與被害人相關的阿茨特,則把“被害人教義學”的觀點,淡化成是“理所當然之事的重新發現”,*Arzt, Rezension Raimund 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 und Strafrechtdogmatik, GA 1982, 522. 觀點類似的,還有米特胥,他也質疑所謂的被害人教義學究竟是新發現還是重新發現?“就像帶有欺騙性的波特金村莊一樣,在用涂料粉刷上了一層新的語詞外表之下,是被塵埃遮蓋的古老的思想建筑。”Mitsch, Rechtfertigung und Opferverhalten, 2004, S.13.并且不同意羅克辛把他稱之為“被害人教義學之父”。*Roxin, Anm. Zu BGHSt 31, 915, JR 1983, 335, Fn.12. 阿茨特的反對意見,Arzt, Viktimologie und Strafrecht, MschrKrim 1984, 113.
與上述質疑聲相反,在被害人教義學這個概念正當化的過程中,許乃曼以一種當仁不讓的姿態出現,“他把重要的角色分配給了自己”。*Mitsch, Rechtfertigung und Opferverhalten, 2004, S.14.從許乃曼自己的角度來說,標志性的文獻是他在1986年發表的《被害人在刑法保護中的地位》。*Schuenemann, Zur Stellung des Opfers im System der Strafrechtspflege, NStZ 1986, 439.然而,實際情況是,就被害人教義學這個名稱而言,既不是來自于許乃曼,也不是來自于他的追隨者,而是來自于最重要的反對者希倫坎普,他在自己1981年的著作中創造了這個名稱。“被害人學(Viktimologie)和教義學(Dogmatik)的融合產生了被害人教義學(Viktimodogmatik)。”*Hillenkamp, Vorsatztat und Opferverhalten, 1981.這個概念一經問世,立刻成為一面旗幟,而在這面旗幟下努力證明其價值,并且始終站在回擊反對意見的第一線的,是許乃曼。在整個刑法教義學與刑事政策的評價體系中,許乃曼以持續的熱情積極評價被害人教義學的地位和作用,例如像“教義學的新發展”、“最重要的立法者格言”、“刑事政策的指針”、“刑事政策的格言”、“功能主義刑法體系的成熟果實”等等。*這些評價來自于許乃曼不同時期的一些文章。Schuenemann, Einige vorlaeufige Bemerkungen, S. 413.; Schuenemann, Der strafrechtliche Schutz von Privatgeheimnissen, ZStW 90(1978), 11ff.; Schuenemann, GA 1985,352 Fn.32.; Schuenemann, FS Faller, S.362.;Schuenemann, FS R. Schmitt, S.129.總之,這些來自于許乃曼的表述,一直在提供關于被害人教義學價值的論證。*Mitsch, Rechtfertigung und Opferverhalten, 2004, S.14.
作為被害人教義學的旗手,許乃曼在這個領域中的開端性文獻,是其于1978年發表的《刑法對于私人秘密的保護》一文。*Schuenemann, Der strafrechtliche Schutz von Privatgeheimnissen, ZStW 90(1978), 11ff.該文是許乃曼1977年向德國刑法學會提交的報告。在這篇討論私人秘密的刑法保護的報告中,許乃曼顯示出了與同年發表的阿梅隆的論文討論詐騙罪相似的思路。德國《刑法》第203條規定了侵犯他人秘密罪。根據該條,醫師、藥劑師、心理師、律師、婚姻家庭咨詢人員等人士,無故泄露因該身份而受托付或以其他方法而知悉的他人秘密,特別是屬于私人生活領域的秘密或經營業務秘密的,構成侵害他人秘密罪。許乃曼認為,泄密行為人的主體身份應當限定在特定的受托人范圍之內。因為只有特定的負有義務保守秘密的人泄露了秘密,才屬于刑罰的對象。第三人可因他人泄露秘密而免于處罰,因為只有針對那些秘密所有人無法避免,必須吐露個人秘密且必須信賴的特定人而言,秘密所有人才是需要保護的。第三人也能夠經由他所委托的人來泄露秘密而免于處罰。因而也免除聽第三人泄露秘密之人的保守該秘密的人。同樣的,秘密所有人保守特定秘密也是如此,因為需要或期待特定利害關系人的保守秘密的意愿,也屬于秘密概念的一部分。
這篇文章中舉了一個如何看待患者秘密的例子。一個患者在治療期間主動向醫生透露自己與某官員夫人有曖昧關系。許乃曼認為,由于這一信息與治療行為毫無聯系,醫生沒有保守這一隱私的義務。如果醫生向其他人透露了這一信息,不違反德國《刑法》第203條的規定。因為這里法益主體能夠保護自己的秘密,具有自我保護的可能性,卻放棄了對自己秘密的保護。德國《刑法》第203條保護的不是法益主體在非緊急狀況下泄露的信息,而是保護那些有價值的、如果不告訴他人就無法實現巨大利益的秘密。只有那些在面對特定的信賴對象不得不吐露的秘密,秘密所有人才是需要保護的,所以說,那些聽第三人泄漏秘密的人,也應當免除其保守該秘密的義務。而且,期待特定的利害關系人為自己保守秘密的意愿,也屬于秘密概念的一部分。總之,在許乃曼看來,只有個人無法也沒有能力進行自我保護的秘密,才受刑法保護,泄密行為才能犯罪化。*Schuenemann, Der strafrechtliche Schutz von Privatgeheimnissen, ZStW 90(1978), 34ff.顯然,許乃曼通過對非法侵害他人秘密罪中的“秘密”進行了限縮解釋,而限縮是通過評價被害人有無自我保護可能性來完成的。
在詐騙罪的問題上,許乃曼贊成和堅持阿梅隆的觀點,認為“只有具體的懷疑才能阻卻構成要件,這個具體懷疑正好使被害人的錯誤不能滿足構成要件,并因此基于被害人教義學的詮釋,適當限縮欺詐的可罰性”。此外,在許乃曼最新的于2015年發表的論文中,其專門討論了神秘的、超自然的騙術。在他那憤青般的筆觸下,德國社會已經進入“一個充斥神秘主義的、集體癡呆癥烙印其上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Schuenemann, Die Schwindel in der Dogmatik und die doppelte Weisheit der Viktimo-Dogmatik, FS Beulk, 2015, S. 543.從占星術到足球比賽預言再到超自然的精神治療,存在著一個非常廣泛的神秘主義的、超自然的市場。然而,在許乃曼看來,今天的人們已經過啟蒙洗禮,其對于可能的超自然的神秘主義愛好或興趣,刑法不需要再介入其中。那些信任神秘主義的、超自然的騙術的被害人,不應該得到刑法的保護。在構成要件層面的處理方式是,那些神秘主義的、超自然的陳述或情狀并不屬于作為欺詐行為對象的事實,因此,詐騙罪構成要件中的欺詐行為的特征就沒有得到滿足。
被害人教義學的持續發展,一個重要的指標是,它從最開始涉及的詐騙罪和侵害私人秘密罪出發,不斷地向越來越多的構成要件擴展和蔓延。
例如,在性犯罪領域,德國《刑法》第177條第1款第3項規定了行為人利用被害人所處的一種無助的、無保護的(schutzlos)的狀態。許乃曼認為,要比較理性地限縮這個構成要件,只有排除那些行為人只有一點點優勢或者被害人只有一點點無助的情況才能辦到。因為在那些情況下,可以期待被害人采取絕對能夠采取的抵制行為,那么,行為人為了壓制這種反抗,就必須使用明顯符合構成要件的暴力手段。*同前注⑤,許乃曼文,載同前注⑤,許玉秀、陳志輝等編譯書,第211-212頁。又如,在財產犯罪領域,在德國刑法針對盜竊行為規定了不同程度的可罰性的問題上,許乃曼認為,這也反映了被害人教義學的思想。德國《刑法》第246條、第242條、第243條,規定了從侵占到普通盜竊到加重盜竊由輕到重的等級,其中的區別始終在于被害人保護自己的財產的程度不同。這種情況直至德國《刑法》第243條的規定出現時達到頂峰,因為行為人必須要侵入被害人受到特別周全保護的領域中,此時被害人的自我保護力度是最強的。此外,德國《刑法》第242條規定了盜竊罪,在對“取走”這一構成要件要素展開解釋時所使用的“占有”的概念,德國多數意見主張要考慮社會意義的歸屬。對此,許乃曼認為,在考慮是否因為社會生活的類型、類型的必要性以及普遍性等因素以后,會導致要大為放松支配地位,并且因此無論如何還要留下一個所有人都要尊重的權利人的支配這些問題的時候,明顯是在使用一個被害人教義學的標準。對于這一點,應當適用德國《刑法》第243條規定的通常情形,在那些情形中,刑法之所以加強對被害人的保護,是因為被害人自己采取了特別的保護措施。*同前注⑤,許乃曼文,載同前注⑤,許玉秀、陳志輝等編譯書,第214頁。 類似的觀點,即在從盜竊罪到搶劫罪之間體現出一個被害人需保護性逐漸升級的狀況,布萊也在他的論文中明確表達過。Blei, Strafschutzbeduerfnis und Auslegung, FS Henkel, 1974, S. 122.
以專著形式將被害人教義學的理念縱深推廣的,是哈賽默。他的著作深入闡釋了被害人自我保護可能性及需保護性等被害人教義學的基本概念,并嘗試將這些理論適用于包括詐騙罪在內的多個構成要件。哈賽默認為,刑法規定的構成要件包括對稱與非對稱的兩類。前者對法益實行全方面的防御,后者的規定體現出特殊的、具體的保護。在非對稱的構成要件中,有一部分屬于關系犯,例如詐騙罪,就要求行為人與法益主體之間存在互動關系,一方需要另一方的配合,才能完成犯罪。相反,不以這種互動關系為前提的,例如殺人罪,就是單方的干預犯。在哈賽默看來,被害人教義學的主要場域是在關系犯中。*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s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Irrtumsmerkmals in § 263 StGB, 1981, S.52ff.由此,他討論了德國刑法中的計算機詐騙罪、信貸詐騙罪以及救助金詐騙等。
阿梅隆在1977年從詐騙罪著手啟動被害人教義學研究之后,也將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構成要件。在他看來,被害人教義學的思想,至少可以適用于各種輕微犯罪領域。*Amelung, Kommentar zur Hillenkamp, GA 1984, S. 582f.例如,以被害人的心理影響為前提的犯罪,立法者對于被害人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反抗有一個預期的設定。以強迫罪為例,既然要求達到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程度,那么在被害人放棄反抗的情況下,就可以運用被害人教義學的觀點限縮構成要件的解釋。又如,涉及個人秘密的犯罪,包括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侵害言論秘密罪、泄露個人秘密罪等,這些犯罪成立的前提,是被害人首先自己要把所謂的秘密或者隱私當回事兒,此時受害的就是以自我保護為基礎的人際信賴。相反,如果被害人自己都無所謂,不保護自己的隱私或秘密,那刑法就更沒有保護的必要。
盡管涉及刑法分則中不同的構成要件,但是,在討論問題的分析思路和結論上,上述這些學者文章相互呼應,形成了一定的聲勢。在評價行為人的行為不法時,他們都把被害人的自我保護放在了一個重要的位置:自我保護的可能性對于刑法是否保護被害人,進而是否懲罰行為人具有直接的影響。而且,發揮影響力的根據,被追溯到刑法的輔助性原則之上。這些思想,成為他們討論分則問題的概念工具,構成了所謂“被害人教義學”的核心內容,使得它與其他從被害人角度切入的研究區別開來,這也是它引起眾多爭議甚至成為批判的靶心的原因之所在。
四、遭遇阻擊:法理基礎的質疑
被害人教義學發展的一個標志,是一直在努力把在刑法分則中發展起來的被害人自我保護的概念,與刑法總則層面的刑法輔助性原則或者說最后手段性原則鏈接起來。
作為一種解釋準則,被害人教義學自我設定的功能,是將被害人不應當也不必要受到刑法保護的行為方式,排除在刑事可罰性范圍之外。它的主張者們堅稱,被害人教義學是從刑法輔助性原則推導而出的,或者說,是最后手段性原則的具體化。*Schuenemann, Das Verbrechensopfer in der Strafrechtspflege, 1982, S. 407.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法益主體也要承擔自我保護的任務。相對于刑法保護而言,被害人的可期待的自我保護,就屬于其他前置于刑法的手段。一個具有自我保護可能性也被期待去自我保護的被害人,卻放棄了自我保護的措施,此時,他就喪失了應保護性與需保護性。與之相應,行為人的刑罰也欠缺刑事可罰性,由此,顯示出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則的實現。*Schuenemann, Zukunft der Viktimodogmatik, FS Faller, 1984, S. 357ff.于是,從分論研究出發的被害人教義學,按照許乃曼的表述,是要“在分則體系與總則體系之間架起橋梁”。*同前注⑤,許乃曼文,載同前注⑤,同許玉秀、陳志輝等編譯書,第207頁。
然而,這個理論雄心遭到了各種形式的阻擊。也正是在與各種批評意見不知疲倦的論戰中,許乃曼的觀點成為在被害人教義學領域中具有代表性的聲音。
比較基礎性的爭議,首先來自于對刑法輔助性原則的不同理解。批評者認為,從輔助性思想中,并不能直接地引導出與其所支持的認識相違背的被害人教義學原則。刑法是社會政策的最后手段,這僅僅是在說,在國家能夠使用較輕微的手段解決社會沖突時,就不允許處以刑事懲罰,而不是意味著,在公民能夠自我保護時,就必須放棄刑法保護。把輔助性原則擴展到公民的自我保護可能性上面,會與歷史事實相悖。因為公民正是為了解除自我保護的責任,而將刑罰權賦予國家行使。*Roxin, Strafrecht AT, 2006, §14, Rn.20.在被害人的法益受到損害的時候,刑法不予保護,意味著一種刑事法網的回撤。因此,批評意見認為,被害人教義學所主張的刑事法網應當在被害人能夠自我保護之處回撤的觀點,是對刑法輔助性的誤解。刑法的輔助性,是認定刑法作為最后手段,是與其他的公權力救濟渠道相比較,而不是與公民自我保護的手段相比。*Hillenkamp, Vorsatztat und Opferverhalten, 1981, S.177ff.在希倫坎普看來,輔助性原則的正確指向,是用來反對那種極度壓縮個人自由的國家主權行為,而不是用來反對釋放個體力量的行為。*Hillenkamp, Der Einfluss des Opferverhaltens auf die dogmatische Beurteilung der Tat, 1983, S. 13f.國家之所以承擔保護公民的義務,正是因為公民不能夠進行有效的自我保護。*Hillenkamp, Der Einfluss des Opferverhaltens auf die dogmatische Beurteilung der Tat, 1983, S. 12f.在被害人法益受到損害的地方,恰恰說明不存在有效的自我保護,此時最需要國家的保護。
筆者認為,關于刑法輔助性原則的爭議,實際上關聯著一個法哲學層面的疑問,即公民訂立社會契約,向國家交出部分權利,形成刑罰,這究竟是為了要減輕自我保護的負擔而由國家來承擔,還是由于個人的力量不足以自保因而才求助于國家?
在被害人教義學的批評者看來,答案是前者,“公民接受國家行使刑罰權,真是為了將自我保護的責任委托給刑法,從而能夠更好發展自己的人格”。*Roxin, Strafrecht AT, 2006, §14, Rn.20.然而,在主張被害人教義學的學者看來,答案是后者。因為根據國家哲學和憲法學的一般理論,當社會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時,國家就不必介入;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的公民,當他可以自我保護自己的法益時,就是在社會層面有效地發揮作用,此時,并不需要國家通過刑法進行保護。相反,只有當他的力量不足以或者難以期待去自我保護時,國家的力量才有必要出場。“輔助性原則終究植根于社會契約論,人民只想在保護彼此自由的必要限度內放棄自由,這倒是早已由貝卡利亞幾乎逐字地寫在刑法上。最初市民本身也必須保留他對于法益的支配,并且當他的力量不是完全足夠自保時,他才需要國家。”*同前注⑤,許乃曼文,載同前注⑤,許玉秀、陳志輝等編譯書,第210頁。因此,在被害人教義學的主張者看來,批評被害人教義學的學者才是誤解了刑法輔助性原則。按照許乃曼的說法,這種基礎原則與概念或歷史上的問題無關,而是與所謂的實踐理性相關。“反映在國家最后原則上面,就是在社會本身不愿也無法支配自己的自由時,才托付給國家。”*同前注⑤,許乃曼文,載同前注⑤,許玉秀、陳志輝等編譯書,第211頁。
由此可見,被害人教義學所理解的最后手段性包括兩個層面:一是與其他較為輕微和溫和的國家手段相比,二是與法益主體能夠且可期待采取的自我保護手段相比。當這兩方面手段均不具備時,才應當將刑法作為最后手段予以啟用。顯然,傳統刑法觀念對刑法最后手段性的理解,是堅守在第一個層面,被害人教義學則想要開拓出第二個層面的內容。從被害人教義學的角度看來,可能且可期待的自我保護,是在刑法上相比較民法而言更為有效的選擇。民法的強制機制是在事后才啟動的,嚴格來說已經太晚,因為法益損害已經形成,相反,被害人的自我保護卻可以在法益損害發生之前就有效地避免這種損害。這樣看來,最后手段性的雙重含義,有助于加強法益的保障。
除了刑法輔助性原則和最后手段性原則之外,關于被害人教義學的另一個基礎性爭議,是這種思想在刑事政策的導向上是否正確。
批評的聲音認為,從刑事政策的角度來看,被害人教義學導向的后果是不可欲的。因為它將會取消對輕信人的刑法保護。這樣一來,不信任、懷疑和謹小慎微的自我保護思想會成為社會共同生活的法則。由此導致的,是公民基于對法律的信賴而充分展開的自由,相反,那些想要非法干涉他人專屬領域的人的行動自由,卻得到了擴大。羅克辛認為,這在刑事政策上是不正確的。國家在利益衡量時,應當站在支持被害人一邊而不是犯罪人一邊。*Roxin, Strafrecht AT, 2006, §14, Rn.21.即使按照被害人教義學的說法,可以期待被害人在能夠自我保護的時候去自我保護,這點要求并不過分,但是,在被害人不進行自我保護的時候,國家就置之不理,這種不作為是過分的。在刑事政策的導向上,這實際上變成了“一種通過懲罰被害人來打擊犯罪人的斗爭”。*Ebert, Verbrechensbekaempfung durch Opferstrafung, JZ 1983, S. 633ff.進一步而言,批評者認為,被害人教義學對構成要件的限縮性解釋,會導致一個面對犯罪不斷退縮而暴力盛行的社會。因為隨著國家對被害人保護的整體性收縮,被害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自我保護,于是,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出現一個以暴制暴、私力解決的“拳頭法”社會。
針對不合理的刑事政策導向的批評,被害人教義學的回應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拳頭法”的想象,只是出現在暴力犯罪的場合,但是,在這個領域,本來也不是被害人教義學深入展開的地方。僅僅是在那些涉及非暴力的強制性行為的問題時,被害人教義學的思想才會提供一種新的解釋資源。“在暴力犯罪領域中,目前沒有任何人曾經主張過,由于被害人不進行自我保護而對構成要件進行限縮性解釋。”*Schuenemann, Zukunft der Viktimodogmatik, FS Faller, 1984, S. 368f.; Schuenemann, Zur Stellung des Opfers im System der Strafrechtspflege, NStZ 1986, 440.因此,在被害人教義學的辯護者看來,這是批評者對于被害人教義學適用場域的誤解或扭曲。既然被害人教義學并不適用于暴力犯罪,那所謂的退縮性保護和“拳頭法”社會就不會出現。另一方面,被害人教義學的主張者聲稱,被害人教義學導致的限縮性解釋,是應對刑法“肥大癥”和“通貨膨脹”的良藥。許乃曼認為,刑法犯罪圈的不斷擴大,導致實體法膨脹和司法效率的低下,而當前刑法教義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要設定一個有意義的標準來解決“刑事可罰性的肥大癥”,進而實現最后手段性原則。*Schuenemann, Zukunft der Viktimodogmatik, FS Faller, 1984, S. 368f.而被害人教義學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標準,在那些被害人欠缺需保護性的地方,也正好取消了行為人的需罰性,由此形成了對構成要件的限制性解釋和國家刑罰權的克制性適用。
此外,在形成針對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雙面激勵這一點上,被害人教義學也能找到為自己辯解的理由。因為如果損害是由被害人自我放棄保護造成的,那么他對于自己利益的否認,就不會再得到刑法的保護。換言之,如果法益主體不認真對待和積極保護自己的利益,那么,在出現法益損害的場合,也可能得不到國家的保護。由此一來,這里就出現了一種反向激勵的效果,激勵每一個公民認真審慎地對待自己的法益,面對風險積極預防,采取可能的自我保護手段去回避危害結果的發生。
以上筆者只是簡單地勾勒了被害人教義學的核心思想所遭受的爭議。直至今日,這些批評與反批評也未能真正地達成和解。因為,被害人教義學的理論,觸及如何看待被害人,如何理解刑法的手段和任務,如何為刑法在社會治理體系中準確定位等基礎性問題。圍繞著這樣一些基礎性觀念的爭論,注定難以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見。可以預見,由被害人教義學引發的觀念沖突,還將長久地持續下去。
五、休養生息:論戰之后的滲透與傳播
盡管曾經遭受過猛烈的批評,也在各種爭論無果后淡出了學界的聚焦范圍,不過,在以許乃曼為代表的部分辯護者的持續論述下,被害人教義學的思想還是在德國刑法學界頑強地存活下來,逐漸從闡述性的專著和論戰性的論文,走進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教科書和注釋書中,以被承認或被批判的形象占據了一席之地。
在那本影響廣泛的刑法教科書中,羅克辛賦予了被害人教義學一個值得專門討論的章節地位。一方面,羅克辛承認,被害人教義學的觀點不僅對于討論分則中的詐騙罪、侵害個人秘密罪、偽造貨幣罪以及強制罪等構成要件時提供了符合目的論的解釋方法,而且對于處理總論的構成要件理論和不法理論中的一些問題,也能夠提供說服力資源。例如,在被害人同意、被害人自陷風險以及挑唆防衛等問題上,被害人教義學還是可以說得比較清楚的。另一方面,羅克辛又認為,被害人教義學的理論基礎,即因為具有自我保護可能性而排除刑法保護,特別是與刑法輔助性原則的鏈接這一點,則是難以被接受的。最后,羅克辛“和稀泥”,表示被害人教義學不能作為一般性和絕對性的原則,但是可以提供一種角度,使得由此在各種特定利益的權衡中綜合性地考慮刑法的保護范圍。
在2006年的第四版教科書中,羅克辛在保留先前各種批評的基礎上,最后增加了一段(相對于1997年的第三版),算是比之前更為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承認許乃曼這么多年堅持不懈地為被害人教義學辯護和論戰的不易。然而,針對許乃曼表示和羅克辛之間沒有本質區別的說法,羅克辛靈活地回應,他認可被害人教義學是一種解釋準則,針對構成要件進行目的限縮的解釋,將那些被害人不具有應保護性也沒有需保護性的情形排除出可罰性的范圍。簡言之,“是一個關于個別構成要件的解釋問題”。*Roxin, Strafrecht AT, 2006, §14, Rn.25.按照羅克辛的這種表述,他把自己對于“被害人教義學”的支持劃定在了一個非常狹窄的范圍。在這個范圍內,他僅僅是贊成在考慮被害人的應保護性與需保護性的情況下去解釋構成要件,但是,在最后這段總結性的表態中,羅克辛完全沒有提及對于所謂“被害人教義學”至關重要的核心論點即自我保護可能性與最后手段性原則。在這個意義上,羅克辛的立場是清楚的:他僅僅是同意在構成要件的目的性限縮中考慮被害人因素這個解釋方向意義上的“被害人教義學”而已,但是對于被阿梅隆、哈塞默、許乃曼等人所主張的“被害人教義學”,他根本不像許乃曼所說的本質上觀點相近,而幾乎是完全回避了。
在德國最權威的刑法注釋書之一,由舍恩克和施羅德主編的注釋書中,在討論法益概念的部分,艾希爾(Eisele)提到了被害人教義學的原則,將其定位在一種選擇性概念,功能在于對于法益保護原則的“非決定性的調節”。*Eisele, in: Sch?nke/Schr?der, Kommentar StGB, 2014, vor §13, Rn.10b.對被害人教義學更具體的展開出現在該注釋書的不法論部分。被害人教義學被承認為一種限制構成要件解釋的原則。“如果被害人有可能并且被期待在損害出現之前,自己采取保護措施去避免其發生,被害人就不具有應保護性和需保護性,那么就可以在構成要件解釋允許的范圍之內消除可罰性。……這種被害人教義學,并不是重新制造一個獨立的修正的構成要件,……是對解釋空間的一種限制,是一種一般性的調節性原則。”*Eisele, in: Sch?nke/Schr?der, Kommentar StGB,, StGB Kommentar, 2014, vor §13, Rn.70b.應當說,“調節性原則而非一般性的推演前提”這個理論定位對被害人教義學而言,已經是得來不易了。而且,這個評價離被害人教義學主張者自己的描述,也相去不遠。
此外,在其他注釋書中,被害人教義學的觀點也開始在刑法總則或刑法分則部分出現,篇幅上或多或少,態度上或贊成或批評。作為萊比錫注釋書的作者之一,許乃曼自然是在萊比錫注釋書中不遺余力地鼓吹被害人教義學,此處不再贅述。在另一部重要的注釋書(慕尼黑刑法注釋書)中,弗羅因德(Freund)明確表達了對被害人教義學的反對意見。在他看來,被害人教義學的辯護者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想要作為一種特定的構成要件的限制準則的觀點,即“損害可能性的形成單獨地以被害人是否有自我保護可行性為基礎,因此缺少了國家的特別是刑法保護的必要性”,是不可接受的。弗羅因德認為這首先是源于對必要性原則的誤解。作為比例原則的要素之一,刑法上的必要性原則意味著,“當國家有數個同樣適合的手段去達到目標時,應當使用其中最溫和的手段。至于說公民個人是否能夠達到這一目標,在所不問”。*Freund, in: MK StGB, 2017,vor § 13, Rn. 426.相反,也是在慕尼黑注釋書中,黑芬德爾(Hefendehl)則對被害人教義學表達了肯定的態度。他從詐騙罪作為一種被害人共同負責的犯罪的角度,評介了被害人教義學的觀點。“當法益主體明明有行為選擇可能性,卻在明知的情況下提升了危險強度,此時,就有必要對構成要件做出限縮性解釋。此時,不存在歧視那些有特殊保護需求者的問題,而是把那些能夠獨立負責的有意識進行風險決定的法益主體,從刑法的適用范圍中排除出去。因此,進一步地出現了這樣的建議,即那些輕信或者有重大過失的被害人,不再受到詐騙罪構成要件的保護。”*Hefendehl, in: MK StGB, 2014, § 263, Rn. 28.從黑芬德爾的論述來看,盡管他主要還是從他所說的支配原則出發,認為被害人教義學不過就是支配原則的具體化表現形式而已,但是,在基本觀念的層面上,他還是站在了被害人教義學的這一方。在黑芬德爾看來,關于被害人教義學會違背社會契約論和不當地解脫國家保護功能的擔憂,是不能自我證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教義學在德國學界的影響甚至超出了核心刑法的領域,例如,在最新的著作權法的注釋書中,斯滕伯格-里本(Sternberg-Lieben)在介紹了被害人教義學的論點(在有可能且可期待自我保護的情況下,缺乏需保護性與應保護性)之后,將其作為討論下列情形的基礎:著作權的權利人長期對某些侵權活動不提出訴訟請求,這使得侵權人信任權利人將繼續容忍他的相應行為,從這種容忍中可以推導出一個合理的(隱含的)同意。*Sternberg-Lieben, in: BeckOK Urheberrecht, 2017, § 106.
近年來,被害人教義學的理論也漂洋過海,傳入了中國學界。在論文方面,筆者于2008年在《法學》上發表的《從華南虎照案看詐騙罪中的受害者責任》一文,是國內學界第一次正式地使用“被害人教義學”的名稱并運用該理論討論詐騙罪的個案問題。這篇論文簡要地介紹了德國刑法學界從被害人在量刑階段發揮作用到在不法判斷中發揮作用的觀念轉變和理論爭議。特別是在詐騙罪的構成要件限縮性解釋中,對于有具體懷疑的被害人是否陷入錯誤,以及簡單、拙劣的騙術是否構成詐騙罪中的欺詐行為這兩個被害人教義學的代表性問題,此文分別介紹了阿梅隆和瑙克這兩位德國學者的觀點,并在此基礎上,從兩個方面用被害人教義學的理論分析了當年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華南虎照案。作為結論,筆者在該文中認為:“如果能夠證明受騙者已經對照片的真假產生懷疑,但是最終還是舍棄本可以充分使用的自我保護手段,而基于投機心理貿然投身風險,從而遭受損失的,國家就沒有必要再大費周折對其保護了。這種投機的心理不宜再被看做是‘陷入錯誤’。”*一方面,從欺詐行為的要素來看,基于當時社會上對虎照真假的討論之廣泛與對抗之激烈,很難將周正龍的行為評價為一種對普通人而言是“特別簡單、拙劣、易于識破”的騙術,也不能由此來否定本案中存在欺詐行為。另一方面,從作為被害人的陜西省林業廳官員的情況來看,承認虎照為真又會為其帶來獲批國家自然保護區資源的巨大利益。在客觀上完全具備嚴格審查的時間和條件下的情況下并沒有仔細審查。車浩:《從華南虎照案看詐騙罪中的受害者責任》,《法學》2008年第9期。
盡管筆者最早在學術論文中引入并運用了德國學者表述的被害人教義學理論,但是,現在看來,當時筆者還沒有對這種理論本身進行全面的審視和分析,而僅僅是作為一種舶來品引入到國內,然后將其運用于國內司法實踐中的具體問題的解決。簡言之,對于德國版的被害人教義學,筆者當時的態度是“拿來主義”,主要是引介并應用到個案中,但對理論本身的展開和批判都不夠充分。一年之后,緱澤昆在《清華法學》上發表的《詐騙罪中被害人的懷疑與錯誤》一文,對被害人教義學在詐騙罪中的理論空間,進行了更為詳盡的闡述。此文主要是引用了許乃曼的理論資源,為被害人教義學的理論優勢辯護。*緱澤昆:《詐騙罪中被害人的懷疑與錯誤》,《清華法學》2009年第5期。如果說筆者之前的論文是直接將被害人教義學應用于國內個案分析,那么,緱澤昆的論文則是針對理論本身,更加詳細和全面地介紹德國學者特別是許乃曼眼中的被害人教義學,增進了國內學界對于被害人教義學的了解。然而,這篇論文與之后的很多一樣,基本上對被害人教義學采取全盤接受的態度,也同樣缺乏足夠的反思。此后,國內學界中又有多篇關于被害人教義學的學術論文陸續面世。于小川的《被害人對于欺騙行為不法的作用》一文,明確指出“被害人的謹慎義務落實在被害人教義學原理上,即為對被害人的自我保護可能性和需保護性的評價和判斷。”*于小川:《被害人對于欺騙行為不法的作用》,《中國刑事法雜志》2012年第5期。黎宏和劉軍強在《被害人懷疑對詐騙罪認定影響研究》一文中,仔細探討了被害人教義學在詐騙罪認定中的作用。他們在該文中認為,當根據被害人有具體懷疑而限縮詐騙罪成立范圍的基礎上,再根據謹慎注意義務的有無,將詐騙發生領域劃分為無需謹慎注意義務的一般生活領域與應當具有謹慎注意義務的市場、投資、投機和違法領域。“對前者實行無差別的、嚴格的保護,對后者適用被害人自我答責,從而在限縮的基礎上適當擴大詐騙罪的處罰范圍。”*黎宏、劉軍強:《被害人懷疑對詐騙罪認定影響研究》,《中國刑事法雜志》2015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王駿在《論被害人的自陷風險——以詐騙罪為中心》一文中認為,對于被害人自陷風險時行為人是否需要對結果負責的問題,被害人教義學不能給予妥適的解答。*王駿:《論害人的自陷風險——以詐騙罪為中心》,《中國法學》2014年第5期。此文從幾個方面對被害人教義學的觀點進行了批評。
在文獻翻譯方面,許乃曼的一篇關于被害人角色的論文,最早于2001年被王秀梅和杜澎翻譯發表在《中國刑事法雜志》上。*[德]許乃曼:《刑事制度中的被害人角色研究》,王秀梅、杜澎譯,《中國刑事法雜志》2001年第2期。此外,羅克辛的刑法教科書(1997年第三版)由王世洲翻譯,于2005年在我國出版,該書中也有專門的章節討論了所謂“被害人信條學”對于實質不法的影響。真正全面地引介德國學者的被害人教義學觀點的,是2011年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申柳華博士的《德國被害人信條學研究》。這本出版于2011年的博士論文,是迄今為止我國學者對德國被害人教義學理論研究最為深入和廣泛的一本專著。這本書較為全面地介紹了德國被害人教義學的發展脈絡和基本內容,并對圍繞這些理論產生的廣泛爭議,進行了批評和反批評的理性思考。不過,申柳華基本站在了重述許乃曼觀點的立場上。針對一些關于被害人教義學的批評,用許乃曼的觀點回應之后,就很少有申柳華本人的反思或進一步的展開了。此外,這本著作也存在著選擇性論述甚至夸大己方陣營影響力的疑問。有些德國學者雖然是從被害人角度展開的研究,或者討論被害人行為對行為人不法的影響,但是其核心思路與許乃曼等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例如,米特胥關于正當化領域中的被害人行為的著作,就是以對許乃曼等人的“被害人教義學”的批評作為研究的出發點,*Mitsch, Rechtfertigung und Opferverhalten, 2004.但是,申柳華的著作也把他歸入到所謂“被害人教義學”的名目之下,用來說明這一理論的研究規模的擴大,*參見申柳華:《德國被害人信條學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頁。這就有誤導之嫌了。不過,瑕不掩瑜,該書仍然是一本難得的學術前沿之作,對于德國版的被害人教義學思想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六、結語:被害人教義學的重新出發
本文的主題,是被害人教義學在德國的源流和發展。這就意味著,在筆者看來,目前在德國被部分學者主張的所謂“被害人教義學”,僅僅是被害人教義學發展的一個支流,或者說形態之一。部分德國學者將“被害人教義學”限定在一個狹窄的范圍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這個概念在德國的發展。被害人教義學的理論疆域,應當得到更加寬廣的定義。
筆者認為,從被害人視角切入刑法問題,將傳統的行為人單維視角的理解模式,改變為“行為人-被害人”雙維視角的理解模式,才是“被害人教義學”的概念應當承載的使命和理論目標。由德國學者許乃曼等人主張的所謂“被害人教義學”,顯示出追求這一目標的雄心,但是,這種從被害人自我保護可能性以及最后手段性原則出發的理論,其法理基礎、所遭遇的各種批評以及發展現狀足以說明,它無法單獨地實現這一任務。它的確是從被害人角度理解刑法的一個重要進路,但遠遠不是全部。很多從被害人角度對刑法問題展開過深入研究的德國學者,包括阿茨特、米特胥、庫爾特等等,他們的研究與許乃曼、哈賽默等人的主張完全不同,甚至對后者持激烈批評的態度。為了與后者相區別,他們也只能與已經和后者捆綁在一起的“被害人教義學”劃清界限。被害人教義學在德國遇到的這種”注冊商標“式的瓶頸,是一種畫地為牢、自我設限的悲哀。
然而,對具有理論后發優勢的中國刑法學界來說,這些人為設定的限制都不存在。筆者在2013年的《自我決定權與刑法家長主義》一文中,對被害人教義學做出了一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定義。德國學者主要在詐騙罪中主張的那種被害人教義學,與被害人自陷風險以及被害人同意,都屬于一個以自我決定權為共同基礎的、廣義的被害人教義學的下位理論。“德國學者所發展的被害人教義學,其思考原點必然要追溯到自我決定權和自我答責的思想。……德國刑法學語境中的所謂‘被害人教義學’,與被害人同意中的自我決定權以及被害人自陷風險中的自我答責原則,在強調被害人的自由意志這一點上殊途同歸。三者之間在教義學理論模型上的差異,既是德國刑法理論精細化的產物,也是學者試圖從新的視角去創設新的概念表述,進而樹立自身學術個性和標簽的結果,但是不能因為這種教義學層面的差異而遮蔽或忽視了它們共通共享的思想基礎。”*車浩:《自我決定權與刑法家長主義》,《中國法學》2012年第1期。被害人教義學在中國的發展,有可能構建出更寬廣的理論基礎,挖掘出更豐富的可能性,也會給未來的刑法理論革新帶來更深刻的影響。
(責任編輯:杜小麗)
DF61
A
1005-9512-(2017)10-0002-13
車浩,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