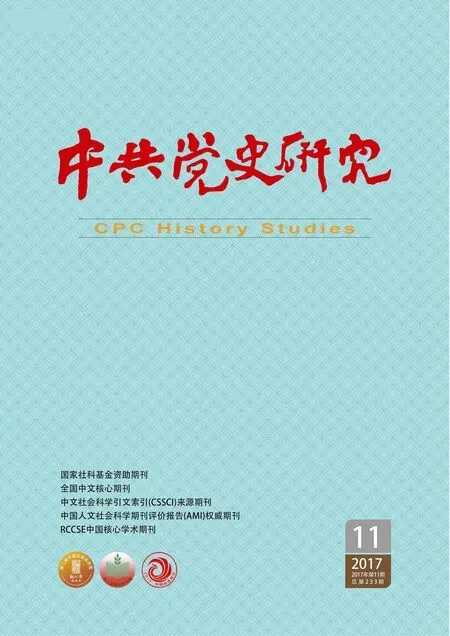實踐限度:中共概念史研究的技藝認知*
郭 若 平
Guo Ruoping
(本文作者 中共福建省委黨校教授 福州 350001)
·理論與方法·
實踐限度:中共概念史研究的技藝認知*
郭 若 平
以中共歷史概念為主體對象的中共概念史研究,是中共歷史學的一個研究分支或類型。由于中共歷史學作為整體性的學科,面對的是不同的實踐史事研究對象,這就導致了在方法(技藝)上,既存在整體性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具體性的研究方法。中共概念史研究具有自身的具體研究方法,亦即研究技藝——技術性方法。討論中共概念史的研究技藝,不僅僅是一種方法論的問題,更涉及對這種方法論認知的理論問題。因此,對中共概念史的研究技藝進行分析,不能不建立在相關的理論認知基礎上。要避免研究技藝的誤用,不能不首先對研究對象的性質作出判斷。在這個意義上講,理論認知決定研究技藝的運用。
中共概念史;實踐歷史;研究技藝
Guo Ruoping
中共歷史學作為有別于其他歷史學門類的一門研究學科,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具備自足性的整體研究理論和方法。在整體性研究的時空結構中,中共黨史研究不能不面對各種不同的具體史事,這又使得研究過程不能不考慮具體的研究類型,而中共概念史就是其中的研究類型之一。既然是一種研究類型,中共概念史研究也就應當具備適合這種類型研究的分析技藝。所謂的概念史研究技藝*法國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馬克·布洛赫的《歷史學家的技藝》(張和聲等譯,另有譯名《為歷史學辯護》)一書,針對的是“歷史有什么用”這樣一個問題而作。書中對歷史研究中“技藝”(只是譯名)問題的討論,不僅涉及如何認知歷史學的存在意義,而且涉及歷史研究中的技術性方法(技藝)問題。而研究上的技術性方法,恰恰是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得以成立的基礎。不同學科都有自身的技藝問題,即便是同一學科內部不同類型的研究,也有相應的技藝問題。,實際上就是既指研究概念歷史變遷的方式或手段,又指這種方式或手段的特征。就研究方法論而言,任何分析技藝都不具備普適性,因為不同學科的特點與差異,決定了不同學科存在符合本學科的分析技藝。概念史屬于歷史研究的范疇,但概念史研究對象的歷史主體是“概念”,而不是以其他歷史主體為對象,因而概念史研究的分析技藝,當然不同于其他歷史類型研究的分析技藝。中共歷史中存在著大量的理論概念,這些概念之于理解中共歷史具有雙重功能,它既承載并顯示著中共歷史發展的特征和性質,也為認知中共歷史發展軌跡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分析技藝,是以歷史主體的“概念”起源和演變為考察對象,其中必然涉及概念的內涵、功能和意義甚至歷史文本的敘事方式。但是,就已有的中共概念史研究現狀來看,對這些方面的研究還存在一定的缺陷,這既有學科認知上的原因,也有具體的分析技藝上的原因。鑒于此,在此以一孔之見略作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實踐史與概念史的張力
雖然中共概念史研究是通過概念的起源與變遷,解釋、認知、分析中共歷史變遷的一種研究方式,具有鉤稽中共歷史實踐軌跡的功能。但是,這種研究潛藏著一種誤導性的陷阱,最主要地表現在“如何”去研究概念的起源與形成及其變遷,以什么方式將概念史研究置于中共歷史研究之中。概念史試圖表明,某種特定概念既是構成人們解讀、認知社會歷史變遷的語言表征,又是構成蘊含或承載社會歷史實踐的因素。這樣一來,概念就意味著具有雙重符號的身份,它既是一種表征社會歷史的語言符號,又是一種包含社會歷史實踐因素的語言符號。所以,概念史作為一種歷史形式,既作為歷史的存在形式,也作為歷史分析的形式,這使得概念史既具有歷史實踐因素的承載功能,又具有歷史解釋的表征功能。在這個意義上,概念史研究既要分析語言符號的概念歷史,也要分析社會實踐的概念歷史。
德國概念史家考斯萊克在題為《“社會史”和“概念史”》的文章中強調:“歷史要成為可能,它必須預設‘社會’和‘語言’的存在,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歷史都不可能脫離‘社會’和‘語言’而存在。”*〔英〕伊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5頁。在這里,“語言”主要是指以文字符號體現出來的概念,盡管文字符號不是“語言”的唯一體現,而“社會”當然就是包括概念在內的“語言”所蘊藉、所承載的社會實踐,概念則是人們用抽象化后的語言進行表達社會實踐的用語或詞匯,它集中地反映社會實踐的本質特征。概念史研究肩負著語言意義的解釋和語言承載的社會實踐意義的解釋,是這兩種解釋的歷史統一體。為此,有研究者認為:“只有在對語言作為表征和因素的雙重把握中,概念史方法才會生成其特有的研究領域。”*方維規主編:《思想與方法——近代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知識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6頁。表征社會實踐的概念和概念蘊含的社會實踐,共同處在特定的歷史發展軌跡中,雙重張力構成了概念歷史的存在形態。
但是,在這種雙重張力的概念歷史存在方式中,表征社會實踐的概念和概念蘊含的社會實踐,并不是一種絕對的對應關系,雙方恰恰是處在既互為條件又無法絕對對應的關系之中。這種概念與實踐的非完全對應性關系,對于中共概念史研究而言,正是需要著力解決的技藝性問題。
對于概念與實踐存在的非完全對應性關系這種歷史現象,恩格斯在1895年3月12日給康施米特的信中就說:“一個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現實,就像兩條漸近線一樣,一齊向前延伸, 彼此不斷接近,但是永遠不會相交。兩者的這種差別正好是這樣一種差別,由于這種差別,概念并不無條件地直接就是現實,而現實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征,就是說,它不是直接地、明顯地符合于它只有從那里才能抽象出來的現實”,“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這種統一無論在這個場合還是在其他一切場合都是如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4、746頁。。那么,既然“概念并不無條件地直接就是現實,而現實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并且通常(不是絕對)還是概念的形成遠遠滯后于社會實踐(現實)的歷史過程,這種現象在中共概念史領域存在著諸多實例*本文研究在其后列舉出的具體概念并對其展開討論,就是這種實例的典型形式。。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分析技藝,就是要研究這些概念實例中存在的概念與實踐的關系,研究這種關系在歷史變遷中是為何“不是直接地、明顯地符合于它只有從那里才能抽象出來的現實”,又是如何“一齊向前延伸,彼此不斷接近”,以及如何從中共思想理論儲存的概念變遷中,透視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實踐變遷的歷史面相,反過來也從這種變遷出發,揭示中共概念史內涵演變的歷史邏輯。
概念史研究不是語義學意義上的歷史研究,而是社會實踐史意義上的歷史研究。中共概念史是與中共實踐史相關聯的歷史,因此,考察中共思想理論領域某些特定概念的歷史發展,就不能僅僅將其當成一種滿足理論上需要的詞匯來考察,也不應僅僅將其當作考索語義變化來分析。中共概念史研究所當做的,應當是考察中共特定歷史概念與特定時代變遷的關系,亦即考察特定概念如何在特定時代社會實踐中的生成與變化,考察概念史與實踐史到底處于何種關系之中。就此而言,中共概念史就存在兩條歷史發展的線索:其一是作為概念生成的社會存在實踐史,其二是作為概念構成的語言形式概念史。譬如中共政治理論中的“革命”概念,這是一個對政治行為高度抽象的表述用語或命名概念,也是學術理論領域、政治政策領域乃至日常生活領域使用頻率極高的政治概念,在不同時期被不同的語言組合所使用,其內涵由于指涉對象的差異而存在巨大歧義。在中共政治思想或政治理論領域,“革命”這個概念的內涵界定并非固定不變,它會隨著中共歷史實踐過程的性質變化而變化。中共在不同時期的實踐過程所表現的不同特征,主導著“革命”概念的定義或再定義。以此類推,中共概念史研究應當對某種特定概念的定義或再定義的實踐依據作出解釋和分析,而不是僅僅停留于語言層面上的語義內涵分析。
盡管概念史中的“概念”是對構成這個概念的社會實踐本質特征的語言抽象,但是,這種社會實踐并不等同于人們直觀到的那種具體社會實踐。因此,概念只是面對生成該概念的社會實踐本質屬性的一般性描述與定性。概念的這種一般性描述與定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與社會實踐相吻合,恐怕是概念史研究的最大難題。社會實踐作為一種客觀現象的存在,人們在使用某一概念對其進行抽象命名或展開意涵解釋時,必然要依據社會實踐的一些具體特征所形成的共性進行內涵概括。這個過程的完成,實際上就使概念成為獨立于直觀的社會實踐之外的語言形式。這時以語言形式表現出來的概念,不但成為社會實踐的表達方式,而且成為社會實踐之所以能夠被認知的前提。以語言形式獨立出來的概念,在其被使用的過程中,也構成了自身的歷史,并且是一種有別于其他歷史類型的歷史。概念自身歷史如何變遷以及為何變遷,構成了概念史研究試圖解釋或還原的對象。
棘手的問題是,在中共概念史研究中,要解釋某特定概念如何變遷以及為何如此變遷,就不得不進入概念史與實踐史互為關聯的歷史解釋空間,而這種關聯又應該如何得到恰當的歷史解釋,這就不能不調動構成概念史分析技藝的歷史意識的介入。譬如,對發生在江西和福建部分地域范圍、史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命名,在事后的特定時期被稱為“中央蘇區”。這是一個在中共黨史研究領域極其重要的歷史概念,如何解釋它的內涵生成與變遷呢?其中包含的中共革命實踐史又是如何呢?這種實踐史與這個概念的相互關聯是如何構成的呢?要解釋這些與“中央蘇區”概念歷史構成的因素,就不能僅僅停留于對“蘇區”字面語義的解釋,而必須將“中央蘇區”概念的歷史構成,置于形成這個概念歷史時期的中共革命實踐史的過程之中,才能夠得到有效的歷史說明。這種歷史說明就是對歷史實踐的敘事性重建,盡管任何重建都不可能就是原本的那種歷史實踐*之所以存在這樣的“不可能”,那是“由于事實并不表明它們自己的意義,而只具有歷史學家賦予他們的意義,由于一位歷史學家對過去的一個特定事件的意義賦予,無法通過考察這個事件在變化的條件下反復出現的‘規定性’來加以檢驗,因此,不可排除的個人因素或主觀因素就進入了每一個歷史重建之中”。參見〔美〕歐內斯特·內格爾著,徐向東譯:《科學的結構》,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656—657頁。。但是,沒有這種歷史實踐的敘事性重建,“中央蘇區”概念構成的歷史因果關系,終將得不到最起碼的歷史邏輯性分析。
對“中央蘇區”概念的生成及其變遷的歷史說明,最基本的是要意識到,這種歷史說明必須涉及兩個方面的中國革命政治實踐史。第一,“中央蘇區”首先是一個政治性的概念,而不僅僅是一個標識區域特征的地理學概念。因此,應當從中共政治革命實踐史角度出發,去考察中共領導的蘇維埃運動史的實踐過程。這種考察,實際上就是重建中共建構革命政權實踐的“蘇區”敘事。“中央蘇區”概念中的“蘇區”,其意涵具有一段較長的政治實踐過程,對于特定時期的中共來說,“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是一種革命的政權形式,即是保證工農民權獨裁制直接進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獨裁制;這種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從民權革命生長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而且是保證中國之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唯一方式”*《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337—338頁。。這種對政權建構認知的程度,或者政治行為運作的程度,無論存在何種局限,都是一種政治實踐具體化的表現,都構成“中央蘇區”概念形成的歷史“前結構”。蘇維埃運動的政治實踐史是“中央蘇區”概念生成的歷史語境。第二,“中央蘇區”又是一個地理性的概念,是地理性與政治性相結合的意義指涉。因此,應當從地理維度出發,去考察“中央蘇區”概念形成的區域構成。當然,地理維度并非僅僅是地理學意義上的指涉,它是政治化的“地理學”,因為政治運動和軍事斗爭的實踐程度決定了“中央蘇區”地理疆域的形成與變化。“中央蘇區”區域空間的構成與延展過程,是中共政治革命實踐歷史發展的結果。因此,如果沒有結合政治革命實踐去考察地理上的構成過程,那么對于“中央蘇區”概念的分析,就無法顯示這個概念的地域空間特征,“如果要真實地確定‘中央蘇區’這個概念的完整內涵,就必須首先考察這個概念存在時期所指涉的地域范圍及其界限”*郭若平、袁超乘:《“中央蘇區”概念的地域指涉變遷考》,《東南學術》2017年第1期。。不厘清這種范圍或界限,就可能導致對這個政治歷史概念的誤解,也可能導致對這個概念的實用主義濫用*這種隨意性地使用“中央蘇區”概念,導致在某些地方自我命名,在區域空間上附會“中央蘇區”。這種現象在現實中常常誤導歷史理解,在理論上構成曲解歷史,在史觀上攪亂對中共歷史的科學認知。。
顯然,在中共概念史研究中,概念史與實踐史的邏輯銜接,只能回到中共歷史實踐史的敘事層面,才可能構成歷史事實面相的展開。也就是說,這種銜接當由中共歷史實踐過程的歷史情節作為橋梁所搭建。這種“搭建”的分析技藝,不是一般性的政論式分析,而是應當從歷史思維出發,以歷史敘事的方式重建實踐史的過程。實踐史作為一種史事存在,經由敘事化的描述程序,實現與概念史的交匯,共同構成概念對實踐的意涵對接。在此基礎上,由特定概念延伸而來的“概念叢”,其相關性概念的內涵變遷與意義建構,同樣由實踐史的多重史事所提供。中共概念史研究不是單向度的意義闡釋,盡管概念史能夠重現實踐史的歷史面相,但這種重現的闡釋技藝不得不從實踐史開始。實踐史有多少復雜層面的展現,概念史就有多大的意義闡釋空間,二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意義張力,任何時候都會顯示語言與實踐的歷史互文關系。
二、以“革命”概念為例的解釋
在中共概念史研究范疇中,中共實踐史是一個與理解概念意涵形影相隨的分析單位。中共實踐史是中共概念史的分析基礎,反之,中共概念史又是中共實踐歷史語言的抽象表意,雙方在共享歷史語境中互為支撐、互為解釋。由此觀之,中共概念史研究決然不能局限于對概念進行單方面的論證,對中共歷史概念內涵構成及意義變遷的解釋,必須融匯在實踐的歷史語境之中,才有可能印證這種解釋具有史事基礎,并由這種事實推演出概念意義指向與增減的變化軌跡。即便像“革命”這種高度抽象化的政治概念,同樣恰如恩格斯所提示的那種情況,其內涵及其意義的生成與變化,也是由概念與實踐在歷史的延伸軌跡上所構成。對中共的“革命”概念展開概念史研究,已有的研究技藝顯示,這一用詞在中共革命年代具有兩條延伸的歷史軌跡,亦即它既是“革命”的實踐史,又是“革命”的概念史。作為歷史研究的行為主體,“革命”概念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研究單位。但是,不能因為“革命”概念是一個研究單位,就將這種研究僅僅局限于單位范圍,而應當將“革命”概念這種歷史研究單位,置于生成這個單位行為的實踐史層面來進行分析。
從中共革命歷史實踐角度來看,“革命”概念的政治內涵并非一成不變,這是因為中共革命實踐存在不同的政治目標指向、不同的發展階段特征、不同的未來期待意識。面對這些不同的政治因素和歷史意識,中共革命歷史實踐的任務、目標及其推進與實施的實踐方式也就不同。對革命年代的政治目的而言,“革命”概念顯然可能成為革命行為者對其政治實踐的符號賦予,但這種符號賦予又受制于其所依據的政治實踐過程。中共政治實踐史事在歷史文獻的記錄中隨處可鑒,人們就此依據將其劃分出不同革命實踐的年代形態,以證實中共革命歷史實踐的不同政治特征。但是,對中共革命歷史實踐的政治特征的認知差異,將導致對“革命”概念史解讀的差異,概念史研究中的“革命”這一政治詞匯,也就不能不被嵌入革命的政治實踐語境之中而被觀照。
假如中共的“革命”概念史要被恰當地得到解釋,那么其中的概念研究技藝,就必須面對如下革命實踐過程的年代史差異*原本是為了研究方便,而后卻形成一種歷史年代觀。中共黨史學界通常對中共1949年之前的整體歷史作出階段性劃分,并由以下四個命名階段組成,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這樣的劃分無疑便于中共歷史研究的展開,但不能說明以“革命”為中心對象的中共革命實踐的主要政治特征。本文此處的概括未必完全準確,但要義不離其中。。
以1921年至1927年為中共早期革命歷史實踐的年代,它所要反映的中共政治實踐特征,可以從這個時期中共所發布的一系列有關時局的“主張”或“通告”中看出,其中典型的表征,就是中共的政治革命實踐主要以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政治勢力為主要目標,這個政治目標的歷史形式是以國民革命運動為基本特征。因此,這個年代中共革命歷史實踐的政治目的、政治力量、政治策略等都烙上了符合這個年代特征的政治印記與色彩。這個年代中共的“革命”概念如何被定義,就要以這個年代的革命實踐特征為概念構成的基礎,并且是以國民革命運動歷史敘事的形式——復線式的史事敘事——來完成這種基礎的建構。
以1927年至1937年為中共推動中國蘇維埃運動革命實踐的年代,它所反映的中共革命歷史實踐特征體現在兩種政治行為上:一是顯示以武裝斗爭反抗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政治行為,二是顯示嘗試建立中共革命政權的政治行為。這兩種政治行為凸顯的革命實踐特征,則表現為以土地革命為核心的中國蘇維埃運動。蘇維埃運動式的政治革命是這個年代中共革命實踐的基本特色,土地革命只不過是這場運動的核心內容。因此,對這個年代中共的“革命”概念解釋,應當將“革命”置于這樣的歷史語境中加以分析,這就是中共推動蘇維埃運動的政治意圖在于試圖建構中國蘇維埃政權,其中許多重大的政治關系如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系、中共黨內不同政治路線的關系、中共與蘇維埃政府的關系、中共與軍隊的關系、中共與中國革命道路的關系、中共與革命根據地的關系、中共與中國革命理論的關系等等,都是在蘇維埃運動這樣的政治框架中展開的。無論中國蘇維埃運動存在什么缺陷,乃至“蘇維埃”概念的使用以及這個概念在新民主主義理論形成后的最終舍棄,都不能抹去中國蘇維埃運動在這個時期的政治年代學意義。中共這個時期的“革命”概念史研究,不能不回歸到這個年代的蘇維埃運動歷史語境之中。
以1937年至1945年為歷史年代的時期,對于中共來說是一個較為特殊的階段。因為這個階段的中共革命歷史實踐,在時空層面上既可以納入八年全面抗戰的范疇,也可以納入十四年抗戰的特定時期范疇。由此,中共革命歷史實踐一方面體現在繼續承載著國共之間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另一方面又體現在承載著全民族全面抗戰的歷史內容,并且在歷史銜接的時段上,中共革命實踐的歷史軌跡又可以往前延伸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后的中外政治時局。但是,無論其中交錯重疊如何,在世界與中國的歷史總體形態上,這個歷史年代的中共革命歷史實踐,最主要的是體現在參與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之中,并具體落實到中國救亡圖存的民族革命和探索建立民主政權的政治革命層面上。因此,由這兩個層面所構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意義上的中國民族的、民主的革命,是這個時期定義中共“革命”概念的實踐基礎。
以1945年至1949年為歷史年代的中共革命實踐特征,具有內外兩個層面的整體性歷史要素。在外層要素方面,歷史整體性意義表現為因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共的政治力量日益壯大,未來的國家建構成為中共革命歷史實踐的關鍵目標,革命性的國家建構實踐構成了中共革命歷史實踐的整體性政治方向。在內層要素方面,中共的政治能量在經歷延安時期的思想建構后得到了巨大積蓄,延安時期所開展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革命性理論成為中共革命歷史實踐持續發展的內在能量。政治革命的推動是一種實踐行為,革命理論的創建也是一種實踐行為。在這種二重實踐行為的主導下,中共革命歷史實踐的政治性開始上升為對人民民主國家建構的預期。在這個歷史年代的“革命”概念內涵的生成與變化,不應當脫離這個年代中共革命歷史實踐的特征而被定義。
由此可見,不同年代中共的革命歷史實踐具有不同的政治指向。因此,分析中共的“革命”概念內涵及其意義變遷,只能回到中共革命實踐史的具體年代范疇中加以分析,才能夠使概念與實踐在歷史變遷中獲得鏈接。中共歷史年代的革命實踐差異,為中共黨史研究在認識論上提供了歷史時期劃分的基礎,盡管對這種時期劃分的命名,因取舍內容的差異而可能出現不同的歷史敘事*黨史敘事是中共歷史學理論與方法中的一個被忽視的問題,幾近于空白,其中應當涉及的問題頗為復雜,當另文討論。。對中共歷史不同年代的劃分及其指稱,雖然并不能完全左右中共概念史對“革命”概念的意義分析,但不同歷史年代中共的革命實踐史事,卻對“革命”概念內涵的界定及其意義變化,發揮著范圍和性質等方面的分析作用。
顯然,“革命”的實踐史為“革命”的概念史成為可能提供了史事基礎,也就是說,“革命”的概念史是在“革命”的實踐史過程中生成的。因此,只有“革命”實踐史的存在,“革命”概念史才有可能拉開它的歷史軌跡,才能成為歷史類型中的一種歷史形式。同樣,只有當“革命”的實踐史成為認知和反思的對象時,“革命”的概念史才有可能上升為一種歷史認識的形式。
當然,就像業已提及的分析原則那樣,概念歷史與實踐歷史不可能完全在同一歷史軌道上延伸,“革命”的概念史也不能等同于“革命”的實踐史,二者之間并非完全無條件吻合,在某種情形之下還可能存在裂隙甚至背離。為此,在展開“革命”的概念史研究過程中,就不能不分析“革命”實踐史與“革命”概念史鏈接關系背后的沖突因素。任何概念都有自己的歷史,“革命”這個政治概念同樣有自己的歷史,這種歷史在多大程度上與“革命”實踐史相對應,就要看對“革命”概念史的構成是如何分析的,這有賴于歷史認知的技藝方式的介入。
如果暫且不考慮“革命”概念內涵的具體特定指涉,那么,這個概念是否存在本質性的規定?也就是說,“革命”概念是否具有本質主義的特征?有的政治學家這樣認為:“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對‘革命’(revolution)這一概念進行專門研究并沒有多大的價值,因為他們感興趣的主要是一系列特定事件的不同甚至獨特之處。而對政治分析家來說,對‘革命’這一概念的研究不只是必要的,它簡直就是使政治研究得以進行的恰切步驟。”*〔英〕安德魯·海伍德著,吳勇譯:《政治學核心概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頁。這里把歷史學意義上的“革命”概念研究同政治學意義上的“革命”概念研究對立了起來,顯然存在認知上的誤解。即便歷史學家對某個“革命”的“特定事件”進行研究,也同樣需要對“革命”概念的一般意義作專門研究,這是因為“革命”概念本身有自己的一般性概念變遷史,盡管在研究目的性方面,這種一般性概念變遷的歷史首先針對的應當是“特定事件”如何使用“革命”概念,在使用這個概念的過程中,顯示因不同“特定事件”而導致概念內涵發生變化。
“革命”概念研究之于歷史研究的必要性,在諸如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中國革命等“特定事件”中被經典地表現出來。從人類革命史的角度看,中共的政治革命歷史實踐,顯然不同于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實踐,也不同于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實踐。這三種革命歷史實踐,都稱得上具有世界性的意義,盡管其中革命的起因、過程、方式、目的、結果等都存在不少差異,但“革命”是一個共同的特征。因此,如果在這三種“特定事件”的革命實踐基礎上,對其共同特征的“革命”概念歷史展開研究,那么就有助于理解這三種革命歷史實踐的發生過程與特征。
就像不能將特定概念誤認為就是特定事實本身那樣,同樣也不能將概念史本身視為實踐史。概念是對實踐在語言層面上的抽象,但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語境、不同的對象等條件下,即便是同樣的概念,其抽象的內涵指涉也可能發生變易。尤其是在不同的時代,同一個概念的使用,它所試圖涵蓋的對象及其意義也不能不有所區別。正是這種變易或區別,使得概念史研究成為歷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概念辨析技藝。法國年鑒學派奠基者布洛赫就極其敏銳地意識到這種技藝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曾經如此強調:“每一個重要的術語,每一次獨具特色的文風轉變,都有助于加深人們對歷史真相的認識,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將語言現象與一定的時代、社會或作者的習慣用法聯系起來進行考察。”*〔法〕馬克·布洛赫著,張和聲等譯:《歷史學家的技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122頁。
既然如此,人們在表達某種不同的對象時,又為何會使用同一種概念對其進行描述,就如“革命”概念之于法國大革命、蘇俄十月革命或中國革命那樣?這其中必有某種內在緣由,而這種緣由就在于概念都有其一般性的內涵與意義。對法國革命、俄國革命或中國革命的政治性質的定位,一般性“革命”概念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它使這些革命實踐的合法性得到確認,并且與“反革命”的政治行為區別開來。因此,作為一種政治意義上的概念,“革命”一詞具有它的內涵一致性與共通性。正因為如此,學術界對這個概念作出了諸多定義,盡管界定的內容涵蓋面并非完全統一,但都是對這個概念的一般性特征進行規約。
盡管眾多政治學或歷史學的術語辭典或學術專著對“革命”概念的內涵界定存在不同的取舍性選擇,但這并不妨礙從不同角度解釋這個概念的本質特征。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學家雷蒙·威廉斯意識到:“在這個發生一連串重要革命的世紀里,最重要的是去區分revolution這個詞的用法與語意,以厘清它的政治意涵。”*〔英〕雷蒙·威廉斯著,劉建基譯:《關鍵詞》,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417頁。由于針對的對象差異,“革命”概念可能涵蓋“必要的更新”“創建新秩序”“顛覆舊秩序”等含義,也可能涵蓋“暴力顛覆”“和平改革”等含義。因此,“革命”概念的“兩個重要意涵——恢復(restorative)或革新(innovative),都帶有‘根本的重要變革’之意”*〔英〕雷蒙·威廉斯著,劉建基譯:《關鍵詞》,第416頁。。“革命”概念在西學意義上,存在著一個內涵不斷轉換的過程,只是到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概念,才意指著“從崩潰到重建的歷史發展軌跡,把20世紀革命置于現代世界史的中心”*〔美〕特倫斯·鮑爾等編,朱進東譯:《政治創新與概念變革》,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370頁。。實際上,“革命”這個符號所涵蓋的歷史事件或歷史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歷史過程或歷史軌跡的存在,這個存在并不是一夜之間的產物,也就是說,“革命是一個破壞與取代舊秩序的戲劇性與深遠性的變化過程”*〔英〕安德魯·海伍德著,吳勇譯:《政治學核心概念》,第226頁。。
任何一場具有實質意義的革命過程,都是通過發動、組織、動員、推進等行為力量的驅動而出現的,它由群體行為能量的聚集所構成,盡管個體行為作用并非無關緊要。因此,在“革命”這個概念中,蘊含著以復數形式出現的革命行為主體的能動作用,它既包含行為性質上的“更新”“變革”“破壞”“暴力”等意涵,又包含行為特征上的“恢復”“取代”“重建”“創建”等意涵,同時還包含行為過程上的“發展”“變化”“更替”等意涵。所有的這些意涵所顯示的行為方式,都不是單方面在起作用,但每一種意涵指涉的行為方式,都構成“革命”概念在歷史實踐上的基本要素。“革命”概念無非是對這些復雜的、多重的、變化的基本要素在語言上的綜合抽象。某種行為過程是否具備這些基本要素及其綜合特征,往往就被判定為是否屬于“革命”的范疇。因此,“革命”概念就成為描述或理解具備這些要素或綜合特征所構成的特定行為的用語。在現代政治學或現代歷史學的分析領域,如果沒有這個高度抽象化的“革命”概念,與之相關的特定行為——可能還是一種相當個性化的行為,就變得無法描述或理解。
中國傳統經典文獻中的“革命”概念,其內涵暫且擱置不表。就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概念而言,作為一個綜合性的抽象概念,它能夠賦予任何一種革命行為在語言上的特質,但并不能具體地說明這種行為現象如何構成以及為何如此。因此,不同的革命實踐可能導致人們對“革命”概念認知的差異,可能導致人們對其進行描述和判斷出現矛盾,因而導致對“革命”概念作出不同定義。就此而言,對“革命”概念的歷史解釋,必須在具體的革命實踐史過程中才能得到說明。不同的革命實踐無論如何都會具備“革命”的共性,但不能因此而將共性視為判斷某種具體革命實踐的唯一依據。就如同近代以來中國革命所顯示的那樣,清王朝的政治崩潰與辛亥革命及至共產主義革命的興起,導致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推動以人民為主體的新社會制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革命”所賜,但不能因此就斷定辛亥革命的政治實踐與中共的革命實踐是同一類型的革命,或者其他革命實踐也同樣具有這樣的性質和過程。各式各樣的革命實踐,因國情政情的不同,無疑會導致人們對“革命”概念理解的不同,其中的時代差異、地域差異、起源差異、事件差異、人物差異等都可能對“革命”概念的內涵及其演變造成認識差異。因此,對“革命”一詞進行概念史研究,就必須對構成這種差異性的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的因素進行具體分析。也就是說,導致“革命”概念內涵差異的原因,恰恰就存在于具體革命實踐史的復雜性之中。在某種意義上說,分析實踐差異而不是分析概念語義差異,正是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分析技藝。甚至在中共概念史研究中,區分相同概念在不同年代或時期的實踐意義差異,應當是正確解釋中共概念史與實踐史關系的條件,盡管可能不是充分條件。只有在中共概念史研究中識別概念差異性,才能使得中共歷史研究更具科學性,而不至于陷入概念誤置的泥沼,導致對不同歷史現象的誤讀與誤解。
三、概念意圖與詞頻分析的局限
概念史研究所要達到的目的,并不是純粹的從概念解釋概念,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解釋沒有意義。僅僅從概念本身的內涵分析,只能滿足于定義性的解釋期待,并不能提供概念史背后的社會實踐史的意圖,這從以上“革命”概念實例的分析中可以獲得歷史說明。從這種歷史說明中,還可以概括出中共概念史研究應當關注的分析技藝。
其一,對影響現代中國歷史進程的中共重要概念進行概念史分析,目的是為了獲取這個概念所蘊含的雙重意義:第一層意義是針對某個特定概念的歷史分析,揭示在該概念發生作用的歷史時刻是如何支撐中共政治歷程的解釋,這種概念是如何隨著中共歷史實踐的發展而發生意涵的變化,這種變化又說明了概念蘊含了什么歷史問題;第二層意義是通過某個特定概念的歷史分析,揭示出概念背后所能提供的中共歷史變遷中的史事實踐軌跡,解釋中共概念史研究的路徑是如何顯示中共實踐史的面相。這兩個方面之所以能夠構成中共概念史研究的目的性意義,是因為中共是一個現代型政黨,作為政黨行為的任何史事在某種意義上都屬于政治性范疇,因此包括史事的起源、發生、變化、發展、結果等變遷要素,都不能不保存于記錄這種要素的政治思想系統之中,而相應的一系列政治概念正是支撐這種政治思想系統的政治語言基礎。中共概念史所要作的就是要通過中共政治思想中存在的特定概念內涵的變遷,既審視概念支撐中共政治思想史的表意功能,又審視概念承載的中共政治實踐史的變化特征。概念史研究的這種意圖,正如有論者所強調的那樣:“‘概念史’關注的焦點之一在于政治和社會思想中所展現出來的主要概念在涵義上的延續、轉變和革新。”*〔英〕梅爾文·里克特著,張智譯:《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頁。因此,在中共概念史研究的歷史意識中,首當明確的是,對任何一個特定政治概念的解釋,只能將其置于中共政治實踐史之中才有被解釋的意義,而不是這種政治概念的出現與使用天然就有被解釋的必要,盡管這種解釋在政治思想史疆域僅具有相對的價值。
其二,在中共概念史的分析技藝上,應當意識到任何一個中共歷史概念都可以將其視為意義顯示的能指,而其所指并不具有一致性或確定性。也就是說,概念符號相同的中共歷史概念,在表征不同時期的中共歷史實踐現象時,并非能夠完全而恰當地解釋概念蘊含的全部實踐意義,實踐的限度與語言的限度都是同時存在的。字符相同的概念能指并非一定與這個概念所指涉的實踐對象相吻合,因為所指是在社會實踐的變化過程中被確定的,而變化著的實踐在任何時候都存在被認知的限度。某個特定概念存在于不同歷史年代、不同史事過程、不同使用意圖等之中,但并不意味著它因概念符號的相同,其內涵就可以作出相同的解釋。如“封建”這個政治化的歷史概念*“封建”一詞近來頗受爭議,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內涵所指引發的,其中涉及這個概念的原始含義與后出的“約定俗成”含義之間的糾紛,尤為意識形態所制約。相關的歷史因緣頗為復雜,須有另文討論。,在中共政治理論中,并不是在任何時候的內涵解釋都是相同的。至于其他的同質性概念,也應當如此看待。顯然,在解釋一個相同的中共歷史概念時,必須考慮這個概念與中共政治實踐史的具體語境的相關性,只能依據不同的實踐史去定義相同概念的意義所指。既然觸及實踐史所牽涉的具體語境,那么,研究相同性或同質性的概念內涵變化,無論這個概念出現的頻率達到何種程度,在分析技藝上并不能局限于這種概念之間的互證關系,而必須同時利用構成“概念史”的來源史料與構成“實踐史”的來源史料的分析作用。在兩方面的史料來源中,追蹤“概念史”與“實踐史”相互關聯的變遷軌跡,才能使中共概念史中的概念構成更接近歷史實踐史的真相。真相意圖永遠都是概念史研究的追求目標,盡管這種追求永遠只能獲得相對的意義。
其三,展開中共概念史研究,不能不考慮特定概念所處的中共實踐史語境對概念形成、定型、變化等方面的影響,這是中共概念史研究必備的分析技藝。德國政治思想家卡爾·施米特強調:“所有概念,包括精神概念,均具有多樣含義,只能在具體的政治語境中方能理解。”*〔德〕卡爾·施米特著,劉宗坤等譯:《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7頁。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語境,對特定概念內涵的意義構成甚至對理解其內涵來說,都會造成實質性影響。實際上,也只有在相應的實踐史語境中,特定概念才能被解釋為曾經發生過作用,并且因此而具有意義。中共的歷史實踐史語境從理論上說具有兩個可分析的層面:一個是特定概念所處的歷史文獻的文本語境,它屬于概念的語言存在方式的語境;另一個是特定概念所對應的中共實踐史的語境,它屬于概念史的史事經驗存在方式的語境。前一方面強調的是概念史研究應當分析特定概念與文獻意圖的語境關系、特定概念與其他概念或概念叢的語境關系、特定概念與文本及其文本生產者的語境關系等;后一方面強調的是概念史研究應當分析特定概念變化與社會實踐所構成的實踐語境關系、特定概念與社會實踐行為方式的語境關系、特定概念與社會實踐主體目的性意圖的語境關系等*這兩個方面實際上就是概念史研究領域內英國劍橋學派與德國海德堡學派各自追求的學術方向。。但是,這兩個方面最終都要借助文獻文本的承載才有可能被記錄、保留,并且可能被識別、獲取、認知和研究。因此,所謂的概念史分析語境,只有從這個層面去理解才是有意義的。
顯然,中共概念史研究并不是就概念內涵的考證而研究概念,它所要研究的面相要寬廣得多,它既關注概念內涵變化與社會實踐史的變遷關系,也關注概念內涵與概念形成語境的變遷關系,又關注概念內涵與不同概念或概念叢的變遷關系。就此而言,某個特定概念在中共歷史中的存在和使用,無論使用頻率達到何種程度,都不能顯示這個概念內涵歷史變遷的復雜關系。也就是說,概念使用在量上的出現頻率,并不能證明該概念內涵的變遷意義。因此,詞頻現象并不能驗證概念史研究的意義,詞頻現象也不是概念史研究所要著重解決的問題。
詞頻分析具有一定的遮蔽性。在無特別提示的前提下,它往往是誤導概念史研究的一個陷阱。在中共概念史研究領域,往往會出現一種研究現象,這就是單純從中共歷史文獻中追溯某個特定概念在特定時期出現的次數頻率高低,以此來確認這個概念的發展變遷軌跡,并以這種被追溯的次數作為驗證概念重要性的尺度。可是,概念使用的詞頻現象,只能說明某個特定概念被人們使用的程度,并不能說明這個概念內涵意義的變化程度,更不能說明概念使用次數與社會實踐關系的內在意義關聯。因此,中共歷史文獻詞頻現象的存在以及對它的分析,并不能解決中共概念史研究所要解決的問題。
但是,指出中共概念史研究上存在依賴詞頻分析的局限性,并不等于說詞頻分析對概念史研究就毫無價值,相反,在一定范圍內,詞頻分析能夠顯示某種特定概念的存在狀態。實際上,詞頻分析是一種量化研究方法,它在社會科學領域被廣泛運用,是一種具有相對排除主觀性的科學計量方法,“詞頻分析法是利用能夠揭示或表達文獻核心內容的關鍵詞或主題詞在某一研究領域文獻中出現的頻次高低來確定該領域研究熱點和發展動向的文獻計量方法”,“詞頻分析法作為一種透過現象看本質的科學研究方法,克服了傳統文獻綜述方法過于依賴定性的總結描述、難以擺脫個人經驗和主觀偏見、無法深入揭示文獻隱含的深層次內容等弊端,具有客觀性、準確性、系統性、實用性等特點”*安興茹:《我國詞頻分析法的方法論研究(1)》,《情報雜志》2016年第2期。。無論如何定位詞頻分析特點的科學性,它能夠在兩方面顯示影響概念歷史變遷的過程:一方面是特定時期概念在文獻中出現頻率的高低,可以顯示該概念在特定時期被關注的程度,或者顯示該概念在特定時期被人們接受的廣度;另一方面則顯示特定時期的政治局勢變化導致特定概念出現頻率高低升降的狀態。很顯然,這只是統計學意義上的功能,盡管它可能具有一定的精確性,但對中共概念史研究而言,這只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出場頻率體現,并不涉及概念與容納其存在的社會實踐關系,因而不能真正實現概念史研究所要達到的目的。
對于中共概念史研究而言,詞頻分析的局限性主要源于這種分析不能夠揭示概念史作為中共歷史研究的意圖。中共概念史是一種歷史研究的方式,其目的在于利用概念歷史的變遷分析,用以解釋概念中蘊含的中共理論思想變化的歷史形式,用以解釋概念所承載的中共政治實踐史的特征。概念之所以具備這樣的解釋功能,是因為中共的一系列歷史實踐,在其具體的變遷過程中,不能不通過社會性的語言方式而被表達,哪怕是一項細微的工作,也不能不通過相應的工作語言來推動,更不用說構成中共歷史運動的一系列政治會議、政治動員、政治路線、政治方案、政治宣傳等,都離不開基本的表意語言尤其是政治用語的運用。概念史的研究技藝提示,語言就是一種行動,而就中共政治活動而言,政治語言既是政治實踐行為本身,也是政治實踐的思想承載物。在所有的政治語言中,政治概念是最典型、最集中、最根本反映政治實踐行為的語言。無論什么政治概念,它的內涵指涉與意義界定都與相應的政治實踐密切相關;同一個概念在不同發展階段,內涵指涉與意義界定可能發生變化,概念史研究就是要分析概念這種變化背后與客觀實踐的歷史關聯。所以,無論同一個概念在同一時期或不同時期的歷史文獻中出現多少次,這種數量頻率多寡現象都與概念的內涵指涉與意義界定沒有必然關系。因此,中共概念史的詞頻分析,并不能有效地反映概念內涵的變遷,也不能反映概念使用意圖的變化。
與此同時,中共歷史無論作為整體性的存在,還是作為具象性的存在,這種存在之所以被認為是一種客觀性的事實,一方面取決于這種歷史本身的發生過程,另一方面則取決于這種歷史能夠被人們所認知。不能被認知的歷史,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導致確認客觀性存在的困難,以至于完全不可能。但是,在人們的歷史意識中,歷史的存在及其意義的構成,需要由語言特別是概念作為中介來完成。這種語言特別是概念構成的時空關系、情節關系、因果關系、心態關系等歷史要素,可以從歷史認知語言層面得到說明。一般的認知語言學強調:“語言知識只不過是關于世界的知識固化于語言符號而已。”*趙艷芳:《認知語言學概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頁。人們認知歷史及其發展過程,是通過語言符號對歷史事實進行概念化的,歷史中形成的各種概念只不過是人們認知歷史而形成的語言知識。在中共歷史的知識世界里,特別是蘊含著中共發展變遷的史事,最終不得不固化為有關政黨歷史知識的各種語言符號,尤其是概念這種政治符號。沒有這種因認知需要而構成相應的概念符號,中共歷史的種種復雜史事,實際上就無法被命名、無法被認知、無法被辨析、無法被分析,那么它的歷史存在及其在認知上的客觀性也就無法得到承認。但是,如同上面分析的那樣,人們使用某個特定概念,對中共歷史進行分析和解釋,由于認知主體受到主客觀條件的制約,在使用概念過程中可能存在意圖差異,這種情況使得所使用的概念具有內涵的不確定性,即便使用同一個概念也是如此。因此,中共歷史概念的出現頻率,即便是處于高頻率狀態,也并不代表概念意涵具有同質性,對其進行詞頻分析并不能揭示歷史蘊含的復雜性,這顯然是詞頻分析存在的局限性。
總之,對中共歷史概念進行詞頻分析,只能對中共概念史研究起到輔助性的作用,這種分析技藝并不能解決中共概念史研究試圖解決的問題。雖然任何一種理解和解釋中共歷史概念的方式,都必須經由感知、思考、記憶等歷史語言形式來完成,但這種完成過程并不能由概念的純粹語言解釋來完成。因此,中共歷史中存在的某個特定概念在相應文獻中出現頻率的高低,并不能證明這個概念在特定時期對中共歷史的解釋具有關鍵性作用——能夠起關鍵性作用的要素是實踐行為而不是概念使用,它只能證明這個特定概念在特定時期被使用的程度,也可以顯示這個概念所反映的特定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一般狀態。顯而易見,中共概念史研究中的詞頻分析無法滿足中共概念史與實踐史之間實質性關系的論述,因而不能將詞頻分析當作中共概念史研究的主要技藝。
四、概念考索與意義限制
在中共歷史文獻中,諸如“階級”“革命”“唯物史觀”“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許多業已形成特定所指的概念,既是中共歷史特別是思想理論史的記述符號,也是這種歷史的語言承載者,已經成為中共實踐史在政治語言范疇領域的構成部分。這些特定概念不但蘊含著中共歷史的意義,而且成為中共歷史解釋的理論表達,是中共歷史認知語言的符號化形式。中共在特定年代所使用的各種特定概念,在中共概念史的分析范疇內,具有雙重身份的解釋功能:其一,任何一個特定概念,實際上都直接參與了中共實踐史過程,并且具有解釋這個過程的文化功能;其二,任何一個特定概念,都是中共實踐史的語言轉換,并且承擔著這種歷史的表意功能。因此,對中共歷史概念進行概念內涵及意義變遷的考釋,是對概念史分析技藝的功能性兌現。
前已論及,中共概念史研究不能不建立在中共實踐史解釋的基礎上。但是,某個概念一旦生成,并被社會群體或政治勢力普遍認同和廣泛使用之后,就必然獨自構成自己的歷史,并開始進入內涵調整、定型、變化直至消亡的歷史周期過程。當然,也存在那種相當時期已舍棄不用的概念,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再度出現而被不同程度使用的現象。中共歷史概念在這種存在歷史過程中的環流現象,不可能不使概念內涵發生代謝與變異。況且,人們對概念歷史解釋的事后觀察,也會因歷史語境的變化而產生歧義,概念內涵的界定也就會因針對的具象不同而出現差異。概念歷史的這種存在狀況因時空的積淀,使得對概念的準確性理解出現了困難。因此,考索概念內涵的起源與變化,就成為中共概念史研究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在概念史研究領域,通常的共識認為,概念是由語言詞匯來構成,并且具有自己的歷史,“概念借助于語言而具形,概念可以用一個說明性或比喻性的詞組、短語或一句話來表達,也可以用一個詞來表達”*沈國威:《近代關鍵詞與近代觀念史》,《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后的東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24頁。。在一般情況下,概念史研究主要根據研究對象在某個特定時期具有高度詞化的概念進行研究,而詞化是“由不同的語義要素(semantic elements)構成不同的詞”*蔣紹愚:《漢語歷史詞匯學概要》,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28頁。。通常是以現成的單詞來表示原本語義較為復雜的短語或語句的內涵,“詞化是對概念的命名”,但并不是所有的概念都能實現詞化,“一般來說,在容受社會出現頻率高的概念比較容易詞化,否則將停留在詞組和短語等說明性(非命名性)表達的層面上”*沈國威:《近代關鍵詞與近代觀念史》,《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后的東亞》,第424頁。。詞化了的概念意味著該概念所使用的詞已經高度濃縮了表達對象的意義。可是,任何一種詞義都不可能簡單地對應所指的事物,因為詞義是人們對外在世界的能動認知,而詞化了的概念同樣具有這種特征。因此,某個概念的內涵表達,并不是某個事物的等價品,它只是對這種事物的理解。外在的復雜因素會影響人們對事物的理解,以至于由理解而構成的概念意涵也就可能出現差異,中共概念史研究因此有必要對概念的差異性意涵作出考索。
對中共歷史概念含義進行歷時考證,當屬于中共歷史研究中的一種常規方法。作為一般性的歷史考證方法,在中外歷史學領域早已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即考據學。中國傳統考據學發展到清代的乾嘉學派,已具極高水平。乾嘉學派所謂的學問,大抵不出于義理、辭章和考證之外,其中考證方法被看成是一種專門的學問。現代史學家陳垣強調:“考證為史學方法之一,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陳垣:《通鑒胡注表微》,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6頁。國外史學界對考據學的重視程度也是相當高的,如法國年鑒學派的布洛赫就認為:“‘考據’并沒有使人們過于謹小慎微,它標志著新方法的誕生,這種方法放之四海而皆準。”*〔法〕馬克·布洛赫著,張和聲等譯:《歷史學家的技藝》,第64頁。顯然,歷史考證是歷史研究求真求實的要求。但是,概念考索之于中共概念史研究而言,往往出現一種誤導性的研究,認為這種研究可以滿足于對某個特定概念內涵的歷時考證。殊不知,這種考證只不過是語言范疇內的詞義考證,它并不能考索出概念變遷的內在社會實踐關系。
在中共概念史研究中,對某個特定概念的歷史考索,常常出現這樣一種研究狀態,即對概念內涵作定義式的考證。考證概念的內涵,追溯概念內涵的起源,分析不同時期概念內涵的定義變化,這些本來都是概念史研究應當觸及的方面,但并不是說這樣做就是概念史研究了。概念史研究并不是僅僅要處理概念的考證問題。
首先,概念史研究不是詞源考證研究。任何一個概念都要在語言上表現為一個詞或詞組,但概念并不是詞本身,并不是任何一個詞或詞組都能構成概念。即便是針對一個已經構成概念的詞,在沒有特殊需要的情況下,概念史研究也不必對其進行詞源考證。詞源研究作為一門語言學學問,主要探討詞的語源及其發展變化,重點在于考察詞的構成理據和詞的音義關系,在方法上相當于中國傳統訓詁學、音韻學和文字學的綜合研究。因此,詞源研究在對詞的來源進行探討過程中,主要關注詞的同源與派生關系,而不必對“該詞語的傳播尋找理由和根據”*埃里克·P·漢普著,榕培譯:《關于詞源學》,《外語與外語教學》1994年第1期。。既然一個概念不等同于一個詞,因此對概念內涵歷史變遷的考察,并不能像對詞的語源構成或音義關系等方面的考察那樣,只局限于語言學范疇之內。對概念進行詞源考究,對揭示概念內涵的政治社會文化意義變遷來說,并沒有多大實質性的幫助。
其次,概念史研究不是對概念進行詞義考證研究。詞義解釋與概念解釋具有許多內在性關聯,以至于有論者就直接將概念史研究稱為“歷史語義學”或者“歷史文化語義學”*有學者強調,作為一種研究范式,歷史文化語義學的主旨是“在古今轉換、東西交會的時空坐標上展開研究,不僅對諸多漢字新語的生成、演變尋流討源,而且透過語義的窗口,觀照語義變遷中所蘊藏的歷史文化意涵”。參見馮天瑜:《我為何倡導研究“歷史文化語義學”》,《北京日報》2012年12月10日。。就語言學范疇而言*語義學從研究角度或研究范疇來看,至少可分為語言學的語義學、邏輯學的語義學和哲學的語義學三種。,語義學研究的是“語言的意義”*李福印:《語義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5頁。。那么,“歷史語義學”或者“歷史文化語義學”就是由歷時性出發,在歷史文化層面對語言意義作出系統解釋,考察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詞匯、術語、概念的涵義,探索由詞匯、術語、概念所傳遞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方面的語義變化。雖然詞匯并不完全等同于概念,但在語義學視角下,無論是詞匯還是概念,都存在語義解釋的問題。盡管如此,即便是在語義學領域,研究詞義內涵及其變遷同樣不能等同于研究概念內涵及其變遷,畢竟二者存在一定差異*關于概念與詞的異同關系,英國概念史家昆廷·斯金納曾提示:“概念和詞語究竟有何關系呢?我們很難采用單一的公式去獲取答案,但是至少可以做出下述判斷。某一團體或社會已然達成對某個新概念之自覺持有的最可靠標志,乃是發展出一套相應的語匯(vocabulary),人們可以利用這套語匯,對此概念進行具有一致性的擇取或討論。”參見許紀霖主編:《知識分子論叢》第9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0頁。。據相關研究提示,詞匯與概念存在如下差異:兩種屬于不同的范疇,詞匯屬于語言學范疇,概念屬于邏輯學和認知科學范疇;詞匯內容包括詞匯意義、語法意義、附加意義,而只有詞匯意義可以納入概念之中;詞匯與概念不存在絕對的對應關系,同一個概念可以用多個詞匯表示,不同概念也可以用同一個詞匯表示*束定芳編:《什么是語義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27頁。。因此,雖然詞匯與概念存在不可割裂的關系,但不能因此認為詞義考證就是概念史研究,更不能認為概念史研究就等同于對形成概念的詞匯進行考證。
在中共概念史研究中,對概念展開語源考索和詞義考證,在一定程度上對理解概念的形成源流和涵義變化有所幫助,但在分析技藝上的意義則極其有限,至多起輔助性的作用,因此在概念史研究中的分析比重較低,不能主導概念史研究的整體方式,更不能構成概念史研究的學理范式。中共概念史研究試圖考察概念本身的歷史,這種考察具有兩方面的分析視點:一方面的分析視點,主要針對的是中共歷史過程中所生成的主導性概念的變化歷史;另一方面的分析視點,主要針對的是主導性概念所構成的中共實踐史,尤其是政治實踐史。兩方面互為關系、互為作用、互為解釋,共同構成中共概念史研究的主要內容。
第一方面,中共概念史研究面對的是在中共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并被廣泛使用的主導性概念的歷史變遷。這個研究視點將概念看成是一種生成、發展、定型、變化甚至消亡的過程,其中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分析某個主導性概念是如何適應中共實踐史發展的需要而出現,研究這個概念出現后如何被使用,其內涵是如何隨著時局的變化而變化,在歷史的轉捩點上是如何地發揮作用,舊概念是在何種條件下被新概念所取代,在何種條件下被再定義或再概念化,在社會轉型和政治導向發生變化之中如何被廢棄,等等。譬如,“階級斗爭”這個概念是中共思想理論史上極其重要和關鍵的一個政治概念,它長期主導著中共政治行為的存在狀態,左右著社會集體性的思維方式。那么,這個概念是如何因中共政治實踐的需要而產生,在理論上又是如何被精致地闡釋,在中共政治話語中是如何地占主導地位并被廣泛使用,其內涵因政治時局的變化又有何種變化,這個主導性政治概念在政治路線和政治思想發生變化后是如何地消歇,如此等等都不是對“階級斗爭”的詞義考證就能夠了結完事的。顯然,以“階級斗爭”這個概念為例所延伸出來的概念史研究問題,與之相類似的提問,在中共概念史研究中都需要作出合理的回答和展開系統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影響中共歷史進程的主導性概念的生成與使用,在歷史變化的范圍內與中共政治實踐史互為作用的關系,應當是中共概念史研究的重點部分。
第二方面,中共概念史研究是將概念視為歷史存在形式的演進過程,也就是說,概念歷史本身就是中共歷史構成方式的類型。這種研究視點與第一方面略有不同,其中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概念在歷史時空變遷過程中如何成為一個中共歷史的研究單元,也就是概念如何構成中共的政治歷史和思想歷史,亦即中共政治實踐史和思想發展史的概念史構成。中共歷史之所以能夠被轉換為中共概念史,原因在于中共政治實踐史過程要能夠被表達并且能夠被認知和理解,就必須通過相應的政治性概念來實現。在表面上,這樣的思考似乎是將實踐史當成由概念史來構成,但換個思考方式,就可以發現“大量的政治行為在語言(只能在語言)中且通過語言得以完成”,并且“政治的信仰、行為和實踐部分地由某些概念所構成,這些涉及政治信仰、行為和實踐的概念為政治行為人所秉持”*〔美〕特倫斯·鮑爾等編,朱進東譯:《政治創新與概念變革》,第22頁。。就此而言,中共概念史表達的就是中共政治實踐史。在此層面,中共概念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試圖從概念的移動、轉換、擴散、接受等變遷特征出發,從主導性概念的分析入手,揭示某種特定概念如何構成中共政治實踐的歷史,如何上升為表達中共政治實踐史的核心用語,如何隨著中共政治實踐史的變化而變化。在這個前提下,開掘概念內涵語義變化背后所蘊藏的中共政治實踐史的面相,通過考察中共歷史概念在不同用例中反映的內涵變化,探析其中所傳遞的中共歷史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意義。簡要地說,中共概念史研究是從概念的變遷中“發現”中共的政治實踐史,而概念史的語義或意涵考證并不能實現這種“發現”。
由以上兩方面分析視點來考察中共概念史變遷的要義,在于顯示中共概念史研究不但涉及概念與中共政治實踐過程的多方關系,而且涉及在中共政治實踐史基礎上形成的主導性概念的多重關系,目的在于“發現”中共政治實踐史的復雜發展歷程。因此,中共概念史研究并不是概念詞義或詞源考證所能夠完全擔當的,它的研究視閾要遠遠廣于概念考證。但是,并不能因此簡單地排斥考證技藝在中共概念史研究中的必要性,盡管這是意義有限的必要性。在中共概念史研究中對某個特定概念的考證,至少需要涉及如下幾個問題:其一,概念史解釋的史實來源的可靠性,需要對史料遺存的真實性進行必要的甄別、審查、辨訂等文獻性的考證;其二,在概念史與實踐史的相關性中,實踐史所顯示的史事是否具備相應的客觀性,直接左右著概念史研究的可信度,因此必須考證實踐史的真實情況,用以驗證與概念史在史事上的符合程度;其三,概念史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是考察概念的使用歷史,一個特定概念為何使用、如何使用、使用意圖等都涉及使用者在一定歷史位置上的情況,因此要解釋一個特定概念的歷史,不能不對概念使用者所處的歷史位置進行考證,尤其要對概念使用者的社會身份或政治身份進行厘清,以避免在概念與史事對應關系上的張冠李戴;其四,概念變遷涉及概念存在的歷史語境,而對歷史語境的分析可能觸及種種復雜的社會歷史因素,對于這些社會歷史因素是否與概念史研究具有相關性需要作出必要考證;其五,概念史研究不得不涉及概念的語言范疇,構成概念的字詞具有原生義、延伸義、轉換義等特質,對這些字詞特質在何種程度上符合概念內涵的定義,也應當作出相應考證。總而言之,在中共概念史研究中,考證這項技藝只是一種輔助性的研究程序,它的存在必要性只能置于概念史整體研究原則的基礎上才有意義。
五、結語:概念折射的實踐史限度
中共概念史研究總體上是一種闡釋性的歷史分析,概念及其歷史變遷構成了這種闡釋的歷史行為主體。由于任何一種概念的生成與變化都與相應的社會實踐存在不可脫節的關系,因而研究中共概念史就不能不同時關注中共實踐史的分析。可是,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實踐史的分析可能遭遇不可避免的困難。史料的不足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更為致命的是,實踐史總是已經發生過的史事,事后無論采用何種方式進行史實“提取”,都不可避免會導致一定程度的“走樣”。這樣一來,實踐史的可靠性就不可能是周全的。與此同時,實踐史的闡釋必然只是闡釋者的闡釋,而闡釋者的見識、學識以及其他種種主觀因素的局限性,無疑會對所闡釋的實踐史客觀性造成限制,以至于概念史賴以建構的實踐史作用就存在一定限度。
盡管實踐史無法被精確地把握,其歷史實證功能也存在有限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實踐史無法為概念史提供事實支持。實際上,就像歷史理論家們業已取得大致共識那樣,歷史研究的人文性使得這項研究被鎖定在“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目標上*實證與解釋的關系,歷來是歷史理論中爭論不休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的態度,在一般意義上可以說,是識別傳統史學與現代史學不同研究進路的標識。。因此,“在歷史學中,史實和對史實的理解以及對這種理解的反思,在歷史學家的思想意識里是交互為一體的,它統一于歷史學家的人文價值觀”*何兆武:《可能與現實: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4頁。。作為歷史學科的人文性研究類型,實踐史之于中共概念史而言,困難的并不是一個精確性的問題,而是一個史事窮盡程度的問題。換個角度說,在中共概念史研究中,支撐概念史構成的實踐史被揭示到何種程度,在相對意義上,概念史研究的可靠性就達到何種程度。
中共概念史所面對的實踐史,無論是政治行為實踐史還是思想行為實踐史,其中的人事、制度、組織、運動、語言等行為性實踐要素,都可能集聚為一種歷史合力,推動某個或某些特定概念的生成與變遷。正因如此,在概念史研究的視野下,考究概念生成與變遷的歷史過程,當然就不是語言學或考據學的分析技藝所能擔當,即便是實踐史闡釋在認知上的限度羈絆無處不在,情況也是這樣。概念史追問的不是或不僅僅是語言上或考據上的詞義或語義,“概念史追問的是,被理解了的是何種體驗和事實,它們如何獲得理解,以及就概念和事實的關系而言,歷史進程中出現了哪些融匯、轉變和差異”*石坤森著,羅宇維譯:《萊因哈特·科塞雷克:〈概念史〉與理解史》,張鳳陽、孫江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3輯,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第297頁。。對于中共概念史研究來說,這種研究具有更為寬廣的歷史意圖,它從概念歷史變遷中“發現”自身過往面相,由此去“洞察處于變遷中的社會信息和理論;洞察處于變遷中的社會認知與意識;洞察處于變遷中的社會價值和態度”*〔英〕昆廷·斯金納著,康子興譯:《文化詞典之觀念》,許紀霖主編:《啟蒙的遺產與反思》,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1頁。,歸根結底是去洞察中共漫長歷史的曲折發展歷程。
TheLimitationsofPractice:TheTechnicalResearchSkillsRequiredforaConceptualHistory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nceptual history, whose central subject is the historical concept of the CPC, is a branch or type of research on CPC history. Because CPC history is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involving research subjects derived from various practical historical events, it involves both comprehensive research methods as well as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on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CPC has its own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namely specific research skills and technical methods. Discussions on the research skills required for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CPC focus not only methodological issues but also on theoretical questions related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thodological issues. Therefore, an analysis of the techniques involved in research on CPC conceptual history requires a basic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In order to avoid misusing the technical research skills, one must first evaluate the nature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In this sense, a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determines the correct utilization of the research techniques.
K01;K061
A
1003-3815(2017)-11-0039-15
*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共黨史研究科學化中的概念史問題研究”(14BDJ024)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 中共福建省委黨校教授 福州 350001)
(責任編輯 吳志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