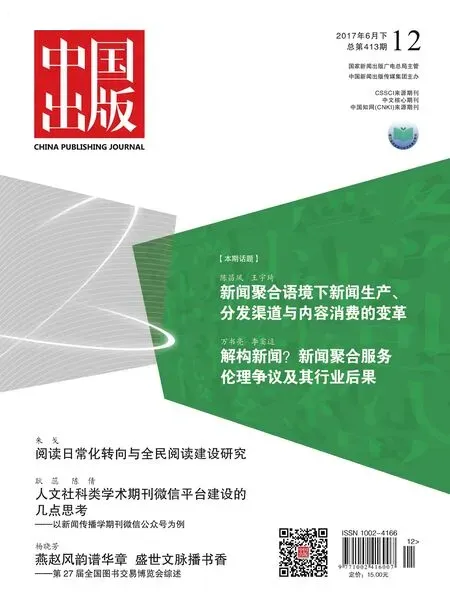清末民初貴州報刊業轉型研究*
□文│史經霞
(作者單位:信陽師范學院)
報刊業與近代中國社會輿論轉型是學者們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只是很多已有相關研究成果往往聚焦沿海開埠城市或地區,對受外來思想影響較弱的內陸地區較少涉及。就公共輿論的近代轉型而言,沿海開埠城市的確走在全國前列,但近代中國區域社會發展不平衡,近代西部內陸地區受經濟、社會發展、民眾思想狀況等因素影響,公共輿論的發育程度與沿海開埠城市存在一定差異。
一、清末民初貴州報刊業的發展
19世紀末20世紀初,維新思想和民主思想先后傳入貴州。宣傳新思想的報刊逐漸在貴陽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秘密傳閱。清末至民國初期,貴州的報紙業有了較快的發展。
1.報刊種類逐漸增多
清末,貴州報紙種類有限。1906年,在遵義知府袁玉錫倡導下,遵義學務局創辦了貴州最早的報紙《白話報》。同一年,貴州學務所創辦了《貴州教育官報》。1908年,貴州咨議局籌辦處發行了《貴州自治白話報》,次年官報局發行了《貴州官報》。以上四種官辦的冊報多為月刊,發行面窄,僅在官府中間傳閱,對民眾的影響不大。[1]除官辦報刊外,清末貴州民間社團也參與創辦報紙。1907年成立的自治學社和1909年成立的憲政預備會對民間報紙的影響重大。這兩個團體成立后都興辦報紙,作為本團體宣傳政治主張、發表言論的陣地。
民國初期,貴州出版過的報紙有20余種。其中,日報種類最多,如《黔風》《群報》《黔鋒報》等。晚報種類較少,如《貴陽晚報》,一周刊行兩次的有《安順三日刊》《新銅仁報》等。在上述報紙中,出版時間長短不一,出版時間最長的能達15年,如《鐸報》,也有出版僅數月即夭折的如《教育日報》。
2.報刊發行量有限
清朝末年,貴州出版的報紙發行量均不大,如《黔報》最初額定銷數為700余份,發行最高峰時期也未能超過1000份。《西南日報》銷數400份左右,《貴州公報》銷數900余份,《商報》僅有百余份,《黔風》的銷量最高達700余份,《群報》日銷量300余份,《黔鐸報》銷量最高為700余份。其他各種類報紙銷數不過千余份,少則二三百份。[2]
報刊出版和發行有賴于兩個基本條件,一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二是印行報紙需要的物質技術條件。其時,貴州軍閥勢力強大,地方市場經濟發展不足,民眾參政議政意識較為缺乏,報刊不易在民眾間流轉。如《黔報》出版之初,貴陽許多士紳拒絕閱讀。據士紳的解釋,他們拒絕參與到報紙的政治論爭中。[3]
3.報刊內容豐富多樣
清末民初,貴州報紙的政治新聞明顯增多。例如開辦之初的《黔報》注重國內外新聞和新聞評論,鼓吹革命思想,宣傳革命精神。《鐸報》和《貴州公報》自貴州宣布獨立后,每日詳載護國反袁的文告、通電、戰報、社論、評論和消息等,并將袁世凱的帝制活動密電刊載報上,加以抨擊。《黔報》《黔風》《貴州公報》等報紙均辟有《外國新聞》專欄,介紹國外政治新聞。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貴州公報》以《俄國第二次大革命要聞種種》為題,第一次報道了俄國革命的相關信息,這些新信息,立即引起貴州知識界的極大興趣。[4]
除政治新聞外,清末民初貴州的各家報紙還刊載一些文藝欄目。如《黔報》辟有《雜俎》《諧談》《短篇小說》《廣告》欄,《黔風》日報有《談叢》《小說》《插畫》《文苑》等文化休閑專欄。[5]這一時期的報紙沒有專門的副刊,報上雖也登載文藝方面稿件,但只是在稿件前加上“文苑”“小說”“諧文”等字樣。后來逐步發展為固定的欄目及專版式的文藝、社會、知識副刊。
清末民初,報紙雖也刊登商業性廣告,但數量不多,篇幅較小。報紙創辦之初,多數人并不了解報紙這一新式的傳播媒介,以致“預算的廣告收入,始終沒有人上門”。[6]這些報紙的出版,使落后閉塞的貴州大開眼界,有傳播新思想、新知識,啟迪民智的積極作用。
二、報刊讀者及其身份
從新聞媒介選擇與受眾人口特征關系來看,年齡、職業和受教育程度三要素是影響受眾新聞媒介選擇的關鍵因素。[7]受條件的制約,清末民初貴州報刊讀者群體有限。
清末民初,貴州的識字群體首先包含已經取得功名的科舉士子和由舊式官員轉化而成的第一代知識分子。近代報紙“研究憲政之預備,贊助教育之發達,調查商務之狀況,鼓吹實業之組織”。[8]這些問題恰是這類人群關注的主題,有官紳權貴家庭子弟,如李叔元、雙清等;有城市望族或鄉紳地主,其中后者尤以興義地區群體最為典型,如王文化、王伯群、袁祖鉻、何應欽等;有稍有田產者家庭、或城市工商業者家庭,而更多的是城鄉貧民家庭。盡管其身份各有不同,但對于新式的傳播媒介,如報紙,這一代知識分子將可能成為最早的讀者和受眾。其次,舊式書院、新式學堂及留學歸國的學生是清末民初貴州新式知識分子,接受新鮮事物能力強,是報刊的主要受眾。1905年,林紹年在貴州先后創辦了蠶桑學堂、師范傳習所、貴陽府中學堂等新式學堂。據不完全統計,法政學堂第一期有60人,1909年全省公立中學有學生近300人,1901年至1907年在貴州大學堂就讀的學生也有近300人,而在政法學堂學習者近1000人。[9]與此同時,歸國的留學生也為這一群體增加了力量。[10]與同期其他省份相比,雖人數較少,但畢竟開了學習西方之風。1905年,在中央政府的大力倡導和維新思潮的推動下,貴州巡撫林紹年選派151名留學人員赴日留學。[11]林紹年認為,本省出國留學人員應主要學習師范,歸國后派往各學校任職。留學生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成長為貴州新型的知識分子。
除識字群體的規模制約報紙發行傳播外,貴州經濟發展水平滯后也制約或限制了報紙受眾和讀者。
三、清末民初貴州報刊發展的特點
清末民初,貴州擁有經濟實力的士紳和新興階層,逐漸從“文學公共領域”(對文學、藝術等文化形式的品評)轉移到“政治公共領域”,與哈貝馬斯建立的理想公共領域不同,貴州的公共領域發展并沒有完全超然于政治權力之外。
其一,各種報刊在創立之初都曾受到政治團體不同程度控制或影響。如《黔風》,該報在出版廣告中自稱:“本報以啟發國民知識,鑄造健全的輿論,促進完美共和政治為宗旨。”[12]清末民初,貴州各時期的主政者操縱報紙,作為自己派系和所主持的政府的宣傳工具,如憲政預備會控制的《貴州公報》和《商報》,自治學社控制的《西南日報》。民間辦的報紙也受到新舊執政者更迭的影響,稍有不合當政者意,就可能被停刊。如《黔靈》日報,1925年2月創刊,屬于民間性質的報紙,因其“報以平民名,以民為資料,惡民之所惡,好民之所好。”[13]1926年周西成主政時被勒令停刊。《平民》日報,雖創刊時宣稱辦“為人民說話”的報紙,同時也為創辦者參加政治活動奠定基礎,但在操作過程中,對于滇軍的擾民行徑,只有少數有保留的揭露。
其二,清末民初,貴陽民間辦報的風氣雖已形成,但多數報刊發行時間短,影響有限。貴州雖地處偏遠,在維新思想影響下,稍晚于相鄰的湖南、四川、廣西等省區,1907年開創了貴州民間辦報的風氣。此后,民間報人投資創辦《黔報》《西南日報》《貴州公報》《商報》在貴陽陸續發行。民國初年,民主及言論自由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各式報刊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創立。但受經費和主政者影響,多數報刊發行時間較短,如《商報》1911年創刊,次年便停刊;《平民》1923年4月在貴陽創刊,1926年周西成執掌貴州后被勒令停刊。而《覺報》創刊后數月,因經費無著,被迫停刊。
其三,貴州報刊業建構其社會批判功能所需的民眾基礎逐漸建立。真正的公共機制,不僅要將讀者、觀眾和聽眾塑造成文學藝術和政治思潮的接受者和消費者,更要將他們塑造成議論者和批評者。《黔報》曾遭到士紳們的拒絕,理由并不是經濟上的問題,而是他們懼怕報紙上的言論和觀點。人們的言論得到法律保障后,全國范圍內辦報高潮迭起,報刊出版事業蓬勃發展。貴州青年們在給周素園(時任貴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來信中表示:“你說的都是我們想說的話,貴州本是一個盲啞的社會,你給我們帶來光明和喉舌了。你要維護你的報,發展你的報,不要令我們甫嘗生趣,又陷入黑暗和苦悶的深淵里!”[14]這些青年熱情洋溢,甚至主動擔任報社通訊員,引領民眾把對政治的關注付諸實踐,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貴州公共輿論空間。
四、結語
發端于清末的貴州近代報刊業呈現躍進式發展,報刊的編輯、發行經營及傳播等體制建設還處于模仿和學習西方的階段,其過程明顯是政論發展史。交流是關系建立的最基本方式,通過交流信息,聽眾自身也開始發展起自己的社交關系。[15]民國初年,報刊業的印刷技術和發行經營在相互交流的基礎上都有所提高。在新聞自主性方面,貴州報刊業也體現了輿論傳播機制自身的發展軌跡。但囿于貴州區域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此一時期人們在建構公共輿論空間時并未超出政治范疇,帶有明顯的論政史特征,并且其公共輿論的影響有限。一是因為經濟發展滯后,制約了新式媒介的傳播。經濟枯竭,民眾日惟汲衣食,無余力以謀智識之享受,讀書閱報只為少數精英階層關注。二是因交通阻隔,對外交流困難。三是評論時局,針砭時弊還不能成為普通民眾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