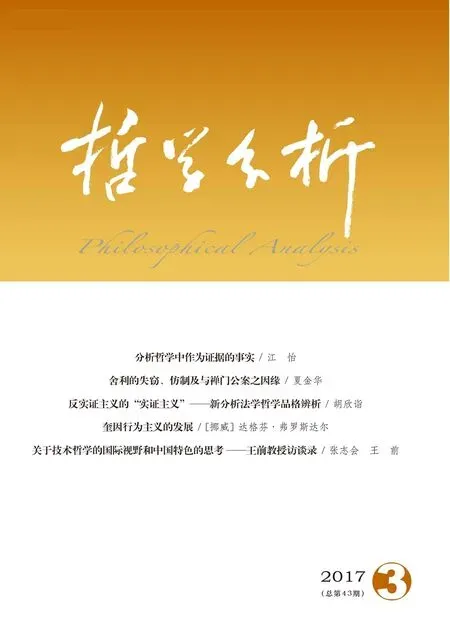法律與認識論:判斷的一個說明
米建國 [美]沙恩·瑞安 /文
薛 平/譯
法律與認識論:判斷的一個說明
米建國 [美]沙恩·瑞安 /文
薛 平/譯
借助索薩(Sosa)關于信念的實施模型,我們提供了法律情形中的優異判斷的一個模型。在提供模型的過程中,當代認識論文獻對法律,尤其是對法律情形中優異判斷的相關性是值得關注的。一個好的審判取決于證據的合適處理,還是實體判決如何構成,二者是不同的。分別由法官和陪審團做出的適切判決之不同也需要討論。
法律;認識論;優異判斷
一、導 論
一個法律案例的三種關鍵要素是證據、事實與判斷。在一個十分周全的判斷中,存在著這三個要素之間的一種適當的關系。研究知識本性的認識論學者注意到與之相類似的三種要素之間的關系。更具體地說,認識論學者關注辯護、真實性和信念這三種要素,以及如果知識得以成立,這三個要素應當如何關聯。給定這一類似性,人們有理由認為認識論學者的研究將會為法律理論家提供洞見。事實上,如我們將會看到的,認識論能夠為法律理論提供的也超出了這一點。與此同時,認識論學者也能由于介入法律理論研究而受益。法律理論提供了關于證據的不同例子和觀念,這將使關于證據這一關鍵的認識論概念的研究受益匪淺。
認識論學者關注對于認知的辯護。事實上,辯護是認識論的一個核心概念,也許是唯一的核心概念。辯護這一概念已經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被理論化。根據一種觀點,辯護源于可靠性。某些持這一立場的學者認為,基于簡單可靠的過程的信念產生辯護,而持同一立場的其他學者則認為,基于構成能力的可靠過程的信念產生辯護。不過,另一種觀點是,正是基于證據的信念才產生辯護。①Richard Feldman and Earl Conee,“Evidentialism”,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48, No.1, 1985, pp.15—34.如我們將會看到的,按照兩種觀點中的任何一種,由于相關主體的本性,對于證據的有效和適當的處理將會有所不同。
認識論由于介入法律理論而受益的另一種方式是由于后者而注意到集體性主體,不論該主體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公司或陪審團。再者,這一介入推動認識論學者接觸到重要的現實生活場景。正是陪審團的主體性成為本文的關注對象之一。傳統的認識論被表征為具有個體本位傾向。長期以來,其唯一的模型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個體的知識擁有者,其知識被認為源于其自身的機能。這一模型,盡管仍然有影響力,但在最近的20年里發生了某些改變。現在的認識論學者更多地關注集體性知識擁有者,以及作為知識源泉的其他人,也就是褒獎性知識。在本文中,當我們考察作為主體的陪審團時,我們對陪審團的集體屬性如何模塑那些使得一個陪審團成為有效的陪審團的屬性這一問題給予特殊關注。
二、應用于法律情形中的判斷的實施模型
認識論的核心關注是分析知識。按照對于知識的前蓋梯爾(pre-Gettier)式標準分析,知識是受到辯護的真信念。換句話說,對于知識之成立,辯護、真實性和信念三者都是必要的,它們是共有充分條件。這表明,標準分析主張,得不到辯護人們就不能擁有知識,不具備真實性就不能得到知識,不擁有信念也不能獲得知識。不過,當這三種要素都具備,人們就擁有了知識。讓我們通過一個例子看看其中的講究如何。假定約翰知道戶外在下雨,按照對于知識的傳統說明,如果關于約翰的前述假定為真,則約翰相信戶外在下雨,他關于戶外在下雨的信念受到了辯護,而且戶外真的在下雨。埃德蒙德·蓋梯爾向知識的標準分析的這一簡單性發起了著名的挑戰。說得更具體些,盡管他并沒有觸及必要性主張,但他挑戰了知識的標準說明(或JTB說明,即知識是受到辯護的真信念)的充分性主張。①Edmund Gettier,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 Vol.23, No.6, 1963, pp.121—123.他舉例說明,主體受到辯護的信念純粹是由于幸運而成為真的。著名的蓋梯爾案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一主張。在田野中的羊的例子中,主人公獲得了他關于田野里有一只羊的信念。②主人公的這一信念受到了辯護,因為這一信念是在知覺的基礎上獲得的。的確,田野里有一只羊。但出人意料之處在于,當主人公獲得他關于田野中有一只羊的信念時,他所看到的實際上是一個具有羊的形體的對象,而非真的羊。結果表明,有一只羊藏在羊形對象之后。認識論學者對這一例子的反應是將它視為關于知識的標準說明的反例。
對于蓋梯爾案例的一個有代表性的反應來自恩斯特·索薩(Ernest Sosa)。他的反應基于把信念視為某種類型的表現。③換句話說,相信是某種主體可以做得好或做得不好的事情,就像主體可以把鋼琴彈好,或彈得不好。按照索薩的觀點,一種好的表現包含三種要素:精確性、敏捷性和才具。一種好的表現要求同時具備這三種要素。就好的鋼琴演奏而言,這種演奏必須是準確的,它是對于曲譜要求的確切再現;演奏還必須是靈巧的,以顯示演奏者能夠駕馭其演奏。但這些還不是全部,一種好的演奏應當是有才情的。借助良好表現的三要素的觀點,索薩想要主張的是,由于其敏捷性,一種好的表現應當是精確的。信念具有類似的結構。一個信念是準確的,當且僅當,它是真的。信念的形成可能具備敏捷性—— 信念可以由知覺、演繹或其他方式形成。關鍵在于,一個信念顯示其持有者具有形成適當信念的能力,當且僅當,該信念由于其形成上的敏捷性而成為準確的。索薩認為,如果一個信念顯示其持有者具有形成適當信念的能力,它就是知識。回顧田野中羊的例子,它表明,使得該例子成為反例的關鍵在于,主人公關于田野里有一只羊的信念盡管是真的,其形成卻不能令人滿意,也就是說,其準確性并非由于其形成上的敏捷性。④關于我們重構索薩的工作的努力,參見Chienkuo Mi,“What Is Knowledge? When Confucius Meets Ernest Sosa”,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Vol.14, No.3, 2015, pp.355—367;Chienkuo Mi and Shane Ryan,“Skilful Reflection as an Epistemic Virtu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Virtues in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edited by Mi,Slote,Sosa, New York:Routledge,2016,pp.34—48。
法律理論中的核心概念與諸如辯護、真實性和信念之類的概念很相似,甚至可以說有結構上的雷同。認識論學者們關注優異的信念,而法律理論學者的主要關注對象是優異的判斷。判斷在法律過程達到高潮時給出。例如,一次審判就是告知一種判斷的機會。如果所提供的判斷是蹩腳的,那么提供這一判斷的審判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浪費。用另一種說法表達這一點,如果一個判斷是蹩腳的,那么,表明目擊者并不可靠就沒有意義。
為了看清楚我們之所思所想,讓我們進一步推究,所謂的優異判斷究竟是什么。把索薩的模型應用于法律情形中的判斷將把判斷作為某種類型的表現來對待,并由此為我們提供一種關于優異判斷的說明。這樣一種判斷最終將關注數量非常有限的事實。這些事實中最為核心的那些,關系到被告是否應為某種罪行承擔責任。一種優異判斷將是精確的。換句話說,在法律過程的高潮,它將正確地確定被告有罪與否的事實。事實上,判決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使這一目標得以達成而設置
的。
不過,一種優異判斷并不僅僅是一個恰好成為正確答案的判斷。當我們思考法律情形中的優異判斷時,我們當然是在思考以正確的方式達致的判斷。換句話說,我們正在思考具備敏捷性或勝任性的判斷。在法律情形中,這樣一種判斷是一種以適當方式對待證據的判斷。證據是法律情形中的流動性。正是它們要被納入考慮,并在最后的判斷中加以權衡。審判中構成抗辯體制的是控辯雙方提供它們所主張的證據,并挑戰對方的證據主張。法律情形中的優異判斷是對證據的適當反應。
于是如何在一個案例中對證據作出適當反應就成為一個問題。一個案例中的一種顯而易見的證據類型是正式證言—— 目擊者、專家等的陳述。認識論學者對于一個主體如何能夠在他人證言的基礎上獲得合理信念頗為關注。這一話題上的諸多立場已經在文獻中得到呈示。一種十分寬容的立場認為,證言性信念享有默認的認知合理性。換句話說,一個證言接受者可以有合理信念正是因為他相信證言。按照這一立場,在某些情形中信念可能不是合理的,這一事實正是認知合理性的默認性的一部分。人們知道證言提供者撒謊,或者注意到他自相矛盾是證言可能喪失其默認的合理性的事例。另一種包含更多限定的立場認為,為了在證言的基礎上獲得合理信念,人們必須在證言的基礎上作出推理或判斷。換句話說,證言本身不足以提供直接的辯護。根據這一立場,簡單地相信證言提供者并不足以獲得合理信念。①Jonathan Adler,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Testimony”,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5 Edition), edited by Edward N. Zalta, URL =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5/entries/testimonyepisprob/〉.使用與我們這里的討論相關聯的措辭,我們可以說,按照第二種觀點,簡單地相信目擊者并不是對證據的適當處理。我們并不試圖在這里解決有關的爭論,不如說,我們的討論旨在顯示,認識論中進一步的爭論如何能夠幫助人們理解我們試圖提出的優異判斷模型。
最后,精確與敏捷并不足以使一個判斷成為優異的—— 如果一個判斷由于其敏捷而不精確,我們不認為它是優異的。在法律情形中,一種可能導致,比方說,長期監禁判決的判斷能夠被認為優異如果它只是由于幸運而成為精確的。類似地,如果一個判斷是精確的,但并不是由于適當地處理了證據,則在審判的首要目的在于呈示與考察證據的情況下,它不能被認為是優異的。
到此為止,我們借助索薩的實施模型為法律情形中的優異判斷提供了一種說明。我們發現,優異判斷是由于適當地處理證據而作出的精確判斷。確立了什么是法律情形中的判斷,我們可以對這一類判斷的認識論做更為精細的考察。不同的司法制度共同地關切被告是否有罪的問題。類似地,種類廣泛的各司法體系均設定審判過程來呈示與考察一個案例中的證據,以促成關于該案例的被告是否有罪的優異判斷。不過,關于種類廣泛的各司法體系間的差別的一個核心點是,適當地處理證據,以提供關于被告是否有罪的判斷究竟是相關各方中的哪一方的職責。在許多司法制度中,這是法官的職責,而在其他的司法制度中,在許多情形下,這是陪審團的職責。正如我們求助于認識論以提供關于優異判斷的說明,在一種裁決為法官的判斷所達致以及在該裁決由陪審團的判斷所達致的情況下,認識論也能夠提供資源以便更為精細地說明一種優異判斷究竟是什么。
三、認知優異主體
如我們將在下文中更為詳細地看到的,兩個主體可以就他們各自所參與的認知活動表現出認知上的優異程度的差異,二者中的每一個也可以表現出所謂的職業美德上的差異。職業美德與角色職能完成有關,在這一情形中它提供裁斷的依據。角色職能完成并不僅僅是個認知問題,正如成為一個好的法官或陪審團并不僅僅依賴相關的認知優異性。在每一種情形之下,各種職業美德涉及對于相關方面的法律的敏感性,以便適當地完成法律提供的職位所承擔的義務。
在認識論的限度內,存在著基于性格的理智價值與基于機能的認知價值的區別。前者依賴于,相關的主體是否公平待人,是否在理智上有勇氣,等等。另一方面,后者涉及相關主體的能力或才具是否有助于探究真實性。例如,知覺上的才具或能力就是一種基于機能的認知優點。雖然在價值認識論(virtue epistemology)的范圍內,這一區別被認為推動了兩種對立的研究,但二者都對理解法官與陪審團的價值發揮了顯著的作用,盡管是以不同的方式。
在法官與陪審團之間存在一種顯而易見的差別。一個法官是一個單個的主體,我們期待其在給出裁決之前參與推敲一個案例中呈示的證據。另一方面,一個陪審團是一個由多個陪審員組成的集體性主體,他們被期待在作出裁決之前一同進行評議,以確定裁決。由于作為主體的法官與陪審團有顯著差異,可以預料,就二者各自而言,好的判斷涉及何種因素也有所不同。
一個法官對達致優異判斷負有完全責任。這意味著,是否考察提供給他的全部證據,以及對各種證據的評價都取決于他本人。此外,管控他自己達致判斷的方式,以確保他以適當的方式完成此事同樣取決于他本人。避免以有偏頗的方式處理證據,避免在達致判斷的過程中陷入謬誤都是他的責任。他的理智價值能夠引導他管理自己的一階機能。
他的任務經常是頗為繁重的,呈示給他的證據也時常是復雜而又相互沖突的,他的道德責任十分沉重,但他具備接受多年訓練,以及擁有處理難以勝數的先例判決的經驗的優勢。這一訓練與經驗有助于發展其優異的理智優長,以及他基于機能的認知優長,這將有助于使他的判斷具備認知上的價值。
但是,對于一個陪審團而言,情形卻十分不同。事實上,傳統的認識論更關注個體法官達致其判斷的模型,而社會認識論,除了關注其他問題,也關注集體性判斷。陪審團對他們的判斷,以及他們如何達致判斷負有集體責任。陪審員們被要求在他們各自的判斷基礎上就被告是否有罪達成一致。他們通過參與相互評議來實現這一目標。在評議過程中,一個陪審員可以質疑證據是否以一種無偏頗的方式被處理,或者,其他陪審員是否在申述中陷于謬誤。達致判斷,以及管控判斷達致過程的責任由一同工作的各個主體共同分擔。這將有助于確保令個人煩惱的簡單錯誤和輕微誤判得以避免。此時,認知上的負擔是被分擔的。
不過,在通常情況下,陪審員在此前并沒有擔任陪審員的經驗。這意味著,就他們所參與的過程而言,他們是新手。他們也沒有就達致判斷接受過任何特殊培訓。盡管認知負擔由于多人介入裁決達致過程而可望減輕,這一事實也有助于改善判斷的認知品質,缺乏訓練與經驗則將損害判斷的認知品質。陪審團是一個由公民組成的團體,是一個適合于達致法律裁決的實體。這一團體已經具備得到長足發展的理智水準,足以在案例中提供一種集體性判斷。陪審團成員是導致案例產生的事件在其中發生的國家的公民,為陪審團提供認知上的支持。
不過,陪審團制度的意義在于,從其中挑選陪審員的備用人員的群體,也就是全體公民,必須具備適當的素養以保證這一制度獲得認知支持。這意味著,存在運用陪審團制度的司法體制有一種管治義務,以保證其公民有必不可少的認知素養,這些素養包括慎思明辨的美德—— 能夠表達真實主張,并予以支持,同時具備適當能力能夠發現他人的類似表達。對于一個陪審團來說,另一個重要因素—— 該因素在個體法官的情形中并不以一種顯而易見的方式存在—— 是,一個陪審團必須能夠對不同意見作出適當反應,這一要求源于陪審團的集體屬性。同行分歧,以及人們應當如何對此作出反應以獲得合理信念也是一個在當下的認識論中受到注意的話題。
我們已經在索薩的實施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了一個法律情形中的優異判斷的模型。我們也討論了作出判斷的實體的不同本性對于與他們之作出優異判斷有關的優異性的影響。在論文中我們已經表明一種認識論的研究如何能夠就法律情形中的優異判斷的話題為法律理論帶來教益。
(責任編輯:肖志珂)
B80
A
2095-0047(2017)03-0010-07
米建國,南開大學哲學院講座教授,臺灣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沙恩·瑞安(Shane Ryan),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大學歷史、哲學與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譯者簡介:薛平,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