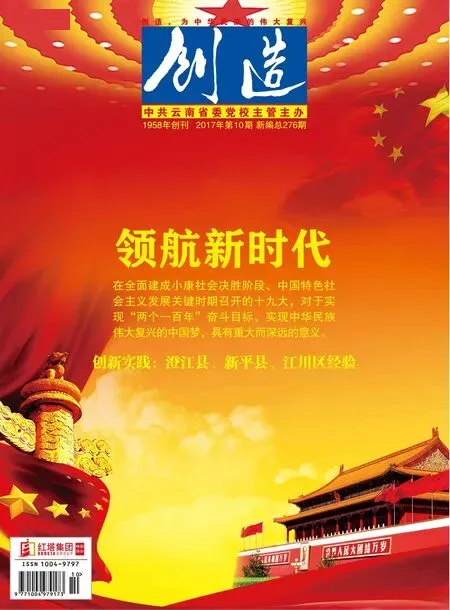閃現(xiàn)著頑強(qiáng)生命光輝的《古詩十九首》
鄒華 云南民族大學(xué)文學(xué)與傳媒學(xué)院副教授
閃現(xiàn)著頑強(qiáng)生命光輝的《古詩十九首》
鄒華 云南民族大學(xué)文學(xué)與傳媒學(xué)院副教授
生命意識(shí)是躍動(dòng)在《古詩十九首》中的不安分的靈魂,正是由于它的觀照,無論是表現(xiàn)人生短暫和死亡終至的“死之慨嘆”,還是表現(xiàn)仕途坎坷和相思離別的“生之悲怨”,或者是企圖超越生命痛苦和追求生命自由的“及時(shí)行樂”,都閃現(xiàn)出頑強(qiáng)生命的光輝。正是因?yàn)樵姼枵蔑@了對(duì)生命問題的理性思考,才使《古詩十九首》實(shí)現(xiàn)了由世俗生活境界到生命境界的提升,從美學(xué)的層面升華了詩歌的審美意蘊(yùn),使詩歌達(dá)到了較高的審美境界。
一、“死之慨嘆”——《古詩十九首》對(duì)生命本體的關(guān)注
東漢末年的文人們,在生的困境中開始了對(duì)生命本體的關(guān)注與思考,他們的詩歌表現(xiàn)了人生短暫之嘆和死亡終至之慨,在“死之慨嘆”中關(guān)涉到了生死這一生命主題。文人們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生命所能穿越的時(shí)空是有限的,對(duì)于生與死抱著一種理性的態(tài)度。雖然生命有限早已是詩經(jīng)時(shí)代的人們就已體認(rèn)到的人類最顯豁的事實(shí),但是,人類強(qiáng)烈的求生欲望及種種超越生命的意圖,使生命短暫的必然性成為需要反復(fù)論證的問題,《古詩十九首》便反復(fù)觸及到了這個(gè)問題。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yuǎn)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今日良宴會(huì)》),“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回車駕言邁》),“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驅(qū)車上東門》),“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生年不滿百》)等詩句直接道出了人生短暫之慮與生命有限之感。在《古詩十九首》中,生命之短暫與脆弱竟是如此地讓人觸目驚心!“人生”不但是“遠(yuǎn)行客”,而且只是“寄一世”,無法長久于世,亦不能堅(jiān)如金石。“萬歲更相送,圣賢莫能度。”(《驅(qū)車上東門》)
人的一生,無論如何絢爛與成功,終將只能在生與死的兩極中展開,無論能力如何強(qiáng)大,終將無法掌控生命之必然。面對(duì)這樣一種生命過程與生命特征,有著理性意識(shí)的文士們,不能不對(duì)生命充滿敬畏,不能不思考人生應(yīng)有的選擇。
還有一些詩作,雖沒有直接談及人生,但依然表達(dá)著相同的主題。“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在女子相思離別的情感抒發(fā)中,感嘆年華易逝,人生有限,時(shí)間之迅疾讓人充滿一種緊迫感。“玉衡指孟冬,眾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shí)節(jié)忽復(fù)易”,《明月皎夜光》雖是怨朋友不相援引,但其中也隱含著季節(jié)更替、時(shí)不我待的感嘆。“四時(shí)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東城高且長》中同樣是由時(shí)物變遷,引起年華易逝的感慨。
由此可見,人生短暫之慮,已經(jīng)成為東漢文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陰霾,成為他們普遍和共同的人生喟嘆,是其生命意識(sh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這種憂慮和喟嘆的背后,凸顯出他們對(duì)死亡的思考與體認(rèn)。
人生如此短暫,死亡終將如期而至。不管身處什么樣的環(huán)境中,死亡都將作為一種恒常既定的狀態(tài)存在著。對(duì)死亡事實(shí)的直接面對(duì),也是《古詩十九首》表現(xiàn)的主要內(nèi)容。在《驅(qū)車上東門》和《去者日已疏》兩首詩歌中,都涉及到了“墓”“白楊”“松柏”“死人”“黃泉”“陰陽”“年命”等與死亡密切相關(guān)的意象,鮮明地顯現(xiàn)著詩人對(duì)死亡的思考與體認(rèn)。
人生短暫之嘆和死亡終至之慮,共同構(gòu)成了《古詩十九首》的生命詠嘆,文人們或憂慮或悲苦,在對(duì)生命的認(rèn)識(shí)和感悟中,走向了自己的心靈深處,揭示了對(duì)生命性質(zhì)的認(rèn)識(shí)。東漢文人們對(duì)生與死的思考,不僅是他們觀念上的問題,更是殘酷現(xiàn)實(shí)帶給他們的真切拷問。如果說對(duì)生的憂慮是他們生命意識(shí)的開始,那么對(duì)死的理性體認(rèn)和直面,便是他們生命意識(shí)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正因?yàn)槿绱耍麄儾虐炎晕掖嬖诘膬r(jià)值擺放到了一個(gè)重要的位置,審視著自身存在的意義。
二、“生之悲怨”——《古詩十九首》對(duì)生命價(jià)值的叩問
《古詩十九首》中內(nèi)容最為豐富的,就是抒寫游子思婦仕途坎坷之悲和相思離別之苦的詩作,它把文人們深藏于內(nèi)心的希翼與無望、思念與孤寂等生命的苦難與不幸,都幻化為種種悲情訴說。“生之悲怨”是一種渴望建功立業(yè)卻求而不得的無望,是一種親人分離且相見無期的悲苦。文士們上不可建功立業(yè),下不可安享人生的悲怨之中隱含的正是對(duì)生命價(jià)值和意義的叩問與探尋。
東漢末年桓靈之世,正常的社會(huì)秩序被打亂,文人們建功立業(yè)的美好理想只能化為烏有,仕途之路也變得渺茫虛無,他們的美好理想只能湮沒在現(xiàn)實(shí)的洪流里,《回車駕言邁》中勾畫的孤獨(dú)求索者的形象就是這類文人的代表與象征。
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fēng)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shí),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今日良宴會(huì)》歌詠的重點(diǎn)也是那種特有的感懷,即對(duì)建功立業(yè)的渴望和功業(yè)無成的嘆息。詩中道出了主人公痛快淋漓的呼喊“何不策高足,先據(jù)要路津?無為守貧賤,坎坷常苦辛”,表達(dá)了想要追求高位,享受榮華富貴的人生理想。在渴望建功立業(yè)的亢奮和“無為守貧賤,坎坷常苦辛”的希望中掩藏的恰恰是理想無法實(shí)現(xiàn)的哀嘆,表達(dá)出了當(dāng)時(shí)大多數(shù)文士共同的心聲。
應(yīng)該說,正是文士們的社會(huì)價(jià)值無法實(shí)現(xiàn),使得他們在痛苦中開始慢慢地轉(zhuǎn)向自我的內(nèi)心世界,在建功立業(yè)的失落中更加關(guān)注個(gè)體生命的存在方式,并以生命的本真狀態(tài)去體驗(yàn)生之悲苦。他們似乎只能企圖借助愛情的幻想撫慰內(nèi)心郁結(jié)的哀傷,然而,由此帶來的卻是更多的相思離別的悲怨。《古詩十九首》中表達(dá)此類情感的詩歌有《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迢迢牽牛星》《凜凜歲云暮》《明月何皎皎》等十首,占據(jù)了半壁江山還多,其中多數(shù)又是從思婦的角度寫的,這實(shí)質(zhì)上可以看作是借思婦之口表達(dá)游子的生離之悲。游子思婦的忠貞不渝之情與相思離別之苦相互映襯,使得這種生離之凄楚悲痛更甚一籌。可見,東漢末年文人的一己之漂泊,釀成了多少人間悲劇。
詩歌中的游子思婦都是孤苦無依的人,跨越時(shí)空的濃郁愁苦相思把他們緊緊連在了一起,一塊素綺,一朵芙蓉,一札書信,都寄托著他們彼此牽掛之情誼,記錄著他們彼此分離之凄苦。《客從遠(yuǎn)方來》在此類詩歌固有的黯淡色調(diào)中一反常態(tài)地注入了明麗的色彩,卻產(chǎn)生了更為聲淚俱下的藝術(shù)效果。詩歌借一位女子的內(nèi)心獨(dú)白,從遠(yuǎn)離久別入手,在由“客來遺綺”和“故人心尚爾”所驀然激起的情感漣漪中,表現(xiàn)了誠摯深厚的伉儷之情。所贈(zèng)之物“綺”上的文彩又是“雙鴛鴦”,引發(fā)了女子裁綺制為“合歡被”,并裝入自己綿長相思的快樂懸想。短暫驚喜之后,女子面對(duì)的卻是她精神世界的無垠黑暗,故人與自己之間依然是“相去萬余里”“誰能別離此”的冷酷現(xiàn)實(shí)。整首詩歌頓時(shí)籠罩在濃重的落寞與孤寂中,使那份夫婦間的篤誠情好和離別后的執(zhí)著相思動(dòng)人心魄。
《涉江采芙蓉》寫的是行者望鄉(xiāng)之情,是游子思婦相見無期之苦。采芳既不能贈(zèng)遠(yuǎn),望鄉(xiāng)又茫無所見,所以,只能“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庭中有奇樹》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它的主人公是一位思婦,眼見庭中奇樹葉綠花繁,而“攀條”,而“折其榮”以“遺所思”,雖“馨香盈懷袖”,卻“路遠(yuǎn)莫致”“但感別經(jīng)時(shí)”,幾番無可奈何更添一層失望。《孟冬寒氣至》中的妻子,只能以丈夫的書札寄托一片深情和相思之意,繾綣的情懷隱約地顯露在字里行間,詩歌敘寫了一對(duì)分別已久的夫婦間專一堅(jiān)貞的愛情。如果說《孟冬寒氣至》表現(xiàn)的是一個(gè)愛得真切而內(nèi)斂的思婦之情,那么《青青河畔草》表現(xiàn)的卻是另一種閨中人——昔日“倡家女”、今日“蕩子?jì)D”的離別之感。詩歌以明艷的色彩與寂寥的內(nèi)心世界的強(qiáng)烈對(duì)照,揭示了詩中少婦對(duì)美好生活的渴望與其實(shí)際的不能實(shí)現(xiàn)之間的矛盾。她守著空房等待良人,是需要以如火如荼的青春的寸寸消磨作為代價(jià)的,盛顏如花而年華似水,因此,她發(fā)出了直白而深切的吶喊“蕩子行不歸,空房難獨(dú)守”。離別相思之苦成為橫亙在游子思婦間繞不開的阻礙,這種折磨時(shí)時(shí)縈繞在他們心頭,揮之不去。在對(duì)不幸生活、苦難生命的悲情訴說和體悟中,文士們表現(xiàn)出了對(duì)自身精神境遇的關(guān)注和對(duì)個(gè)體生命價(jià)值的觀照,在不經(jīng)意間觸及到了對(duì)生命意義的深層思考。
三、生命意識(shí)——《古詩十九首》審美意蘊(yùn)的升華
漢一代,詩歌似乎并非文人創(chuàng)作的主流,但東漢末年的《古詩十九首》,卻獨(dú)領(lǐng)風(fēng)騷,成為中國早期抒情詩的典范之一,它的價(jià)值不僅在于它的藝術(shù)形式,而且更重要的還在于其中隱含的濃郁生命意識(shí)提升了詩歌的審美意蘊(yùn)。它通過對(duì)游子思婦世俗生活中的羈旅情懷和閨愁怨艾的抒寫,表現(xiàn)了人生短暫和死亡終至的慨嘆,這實(shí)質(zhì)上是文人們對(duì)生命本體的關(guān)注與思考,也表現(xiàn)了仕途坎坷和相思離別的悲怨,其中凸顯的是文人們對(duì)生命價(jià)值的叩問與追尋,更表現(xiàn)出了及時(shí)行樂的生命觀,彰顯了文人們對(duì)生命痛苦的超越和對(duì)生命自由的追求。正是諸多生命意識(shí)的滲透,才使得詩歌實(shí)現(xiàn)了由世俗生活境界到生命境界的飛躍,從美學(xué)的層面升華了詩歌的審美意蘊(yùn),是詩歌美之真正所在。
《古詩十九首》把筆墨置于世俗化的視野之下,在世俗生活中體味著生命存在的悲苦或喜悅,自覺或不自覺地融入了對(duì)生命的感知與體悟,抒發(fā)了真切的生命體驗(yàn),最終把對(duì)人生痛苦的超越定位為及時(shí)行樂。在詩人們看似頹廢和悲觀的選擇之下,恰恰隱含著他們對(duì)生命的悲憫和珍愛,因此使《古詩十九首》成為不僅僅是對(duì)形而下的世俗生活的簡單詠嘆,更是對(duì)形而上的生命問題所作的哲理性思考。
文學(xué)作品只要是源于內(nèi)在的生命意識(shí),就會(huì)有持久的生命力,其中投入的生命意識(shí)越強(qiáng)越深厚,就越有可能震撼人心,也就越可能具有更高和更為普遍的價(jià)值與意義。《古詩十九首》之所以動(dòng)人情懷,具有永久的魅力,其中涌動(dòng)著的生命意識(shí)當(dāng)是首要原因,或許正如尼采曾經(jīng)指出的,藝術(shù)原本就是人類“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來的形而上活動(dò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