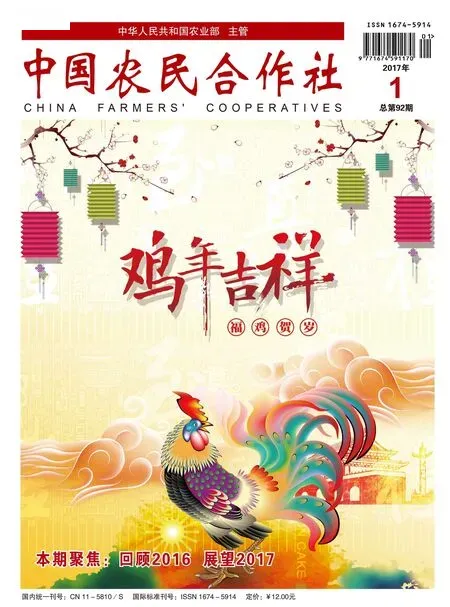談談合作社治理:信任
■ 文/本刊特約評論員 徐旭初
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
談談合作社治理:信任
■ 文/本刊特約評論員 徐旭初
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

一般而言,合作社治理的要素大約包括機構、規則、信任和認同幾方面。今天,我們談談信任。
可以確認,盡管信任不能取代必要的制度安排,但是合作經常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自由的行動主體之間如果充滿不信任,就不會出現合作;而且,信任若是單方面的,也不太可能出現合作。在此意義上,信任是合作的必要條件。不過,信任并非合作的充分條件,也就是說信任并不必然導致合作,因為合作除了信任還有其他的影響因素。
無疑,信任是影響合作社組建、治理、發展以及績效的重要因素。在合作社組建初期,往往是一種傳統的非制度信任,主要包括親緣信任、私人信任、聲望信任、宗教道德信任等。隨著合作社規模發展,成員之間的信任程度可能加深(當然也可能減弱),逐漸形成一種更為廣闊、深入的超越血緣、親緣的信任關系,從而為合作社進一步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條件。所以說,“在某種意義上,合作社是被良好組織的信任機構。”
當面對中國鄉土背景下農民合作社治理行為時,我們必然會想及信任問題。農民們選定某一組織形式(治理結構),他們考慮的就是該組織形式如何能實現他們最具體的切身利益,而親緣關系及其信任首先在組織內部治理過程中充當了一種“潤滑劑”,功不可沒。通過親緣關系并由此為基礎“層層外推”而發展起來的社會關系,給合作社帶來了資金、市場、技術、信息以及更寬廣的社會關系,同時,通過這些關系而獲取的資金、市場、技術、信息又往往成為合作社組建與經營的直接動因。特別是,合作社的內部治理和運營也遵循了親緣關系規則,具體表現在勞動分工的差序格局和組織管理的親信原則與家長權威上。而這種親信原則有別于一味地任人唯親的親情原則,它所依據是一種親緣、忠信和能力相結合的原則。實際上,合作社這種發育成長和內部治理過程,勢必帶有某些傳統社會關系的特征,同時也就呈現出了一種親緣關系與市場規則相交織的新的農村社會關系。現實中,這些基于關系的合作社治理結構,通常表現在核心成員的家族化或泛家族化、合作社核算單位的班組化、成員投機主義行為防范的聯坐化等方面。不難發現,相當部分農民合作社的發展正是在這種新的社會關系及其信任中尋找到一種有效率的均衡。
成員對領導人、核心成員的信任也是合作社治理結構的重要支撐。合作社組建、治理、發展以及績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領導人、核心成員,而成員的信任則可以有效降低合作社內部的交易成本,促使內部資源更合理運用,進而產生組織績效;此外,尤為重要的是,信任也可以促成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助合作,提升凝聚力,有助于組織生存和發展。
當然,在中國農村長期社會關系實踐中形成的以親緣和擬親緣關系為基礎的“特殊信任”,是中國農民走向合作的行動邏輯,但同時這種信任也規定了合作對象及范圍的“規模界限”,從而制約了合作社向更大規模、地域地拓展。究其原因,主要是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是需要以契約、產權等現代制度為基礎的“普遍信任”來做支柱,而不能僅以親緣、地緣關系為紐帶的“個人信用”來維系。因此,從合作社持續健康發展來看,關鍵還在于信任能否實現由傳統社會資本向現代社會資本的變遷。
〔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373063)與農村改革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