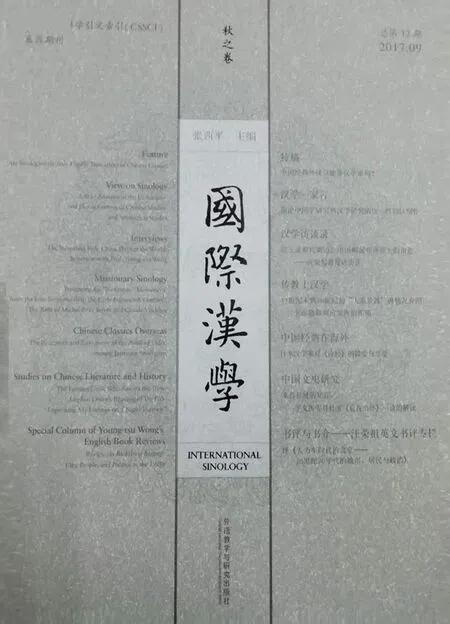傅蘭雅的漢語語言觀及其當代價值*
□
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是晚清西學東漸過程中的一位標志性人物。他是英國傳教士,但畢生獻給中國:他在中國譯書、創刊、辦學,在美國教授中國文化。他在華共35年,其中在江南制造局從事翻譯工作28年,共譯書129種,涉及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軍事科學和社會科學,對晚清社會發展與學術界都影響深遠。他西學譯介內容之豐,范圍之廣,影響之大,同時代人幾乎無可匹敵。熊月之①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53頁。、馬敏②戴吉禮:《傅蘭雅檔案》,第一卷,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V頁。等學者都曾倡導學界要深入研究傅蘭雅。專門史和科技史領域的諸多學者如阿德里安·貝內特(Adrian A.Bennett)③Adrian A.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王揚宗④王揚宗:《傅蘭雅與中國近代的科學啟蒙》,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2000年。、熊月之⑤《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孫邦華⑥孫邦華:《論傅蘭雅在西學漢譯中的杰出貢獻》,《南京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第133—139頁。、王紅霞⑦王紅霞:《傅蘭雅的西書中譯事業》,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06年。、夏晶⑧夏晶:《晚清科技術語的翻譯—以傅蘭雅為中心》,博士學位論文,武漢大學,2012年。等都展開了對傅蘭雅的研究,但往往集中于對其譯作或西學傳播事件的整理與羅列,對其科技譯名策略與統一策略的歸納。《傅蘭雅檔案》(1—3卷)2010年在國內出版,給傅蘭雅研究提供了翔實的一手資料,有助于傅蘭雅研究進一步深化。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傅蘭雅漢語語言觀,將主要基于《傅蘭雅檔案》(1—3卷),探討傅蘭雅漢語語言觀的內容與成因,并揭示其當代價值。
一、傅蘭雅漢語語言觀的歷史語境
每一種思想和觀點都有其產生的深厚歷史背景,因為思想者思考的對象往往就是特定歷史語境下的問題。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天朝上國”的迷夢,開始出現李鴻章所稱的“三千余年一大變局”,①李鴻章:《復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轉引自梁啟超著,何恩超評注《李鴻章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4頁。或梁啟超感嘆的“中國四千年大夢之醒悟”,②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13頁。中國由此開始了近代社會的轉型。“自強”“求富”“救亡”“圖存”成為晚清中國社會的主旋律。飽受戰亂之后,中國政府意識到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以維護封建統治的重要性,開辦江南制造局,并設翻譯館。在這種背景下,傅蘭雅入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從事西學翻譯。由于西方近代科學飛速發展,而中國科學停滯不前,中國缺乏西方相應的學科與術語,因此晚清的西學譯介就面臨嚴峻的科技譯名問題:“名目為難”與“混名之事”。③傅蘭雅:《江南制造局翻譯西書事略》,載羅新璋,陳應年編《翻譯論集》(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285—286頁。正是面對晚清科技譯名問題,傅蘭雅開始思考中國語言與翻譯問題。
二、傅蘭雅漢語語言觀的內涵
經過多年的翻譯實踐和中文學習,傅蘭雅的漢語語言觀在19世紀90年代漸趨成熟。1890年5月,傅蘭雅在新教傳教士會議上發表了《科學術語:當前的差異和尋求一致的方法》的長篇講話;1896年5月,傅蘭雅在中華教育會第二次會議上宣讀了《中文科學術語》。1899年傅蘭雅在太平洋語言學會年會宣讀了《漢語語言學》(后在《加州大學年刊》發表)。三篇講話各有側重,前兩篇主要側重科學術語翻譯,后一篇則聚焦于中國語言文字,但前者與后者都涉及中國語言文字問題,內容上出現一定的重合,呈現出一種繼承與發展關系。傅蘭雅在翻譯實踐中深化他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理解,他的漢語語言觀的主要內容如下:
1.“漢語”概念
傅蘭雅在《漢語語言學》中探討“作為獨立語言的漢語”時界定了一般意義上的“漢語”(Chinese language)。他指出中國存在兩種語言:口語和書面語。口語只用于交談,書面語只用于書寫。口語分外來語和本地語。外來語包括印支語系、邊遠山區部落使用的土著語、土耳其語、蒙古語、滿洲話。本地語是指中國的方言,主要包括四大類:官話、吳語、閩語和廣東方言(粵語和客家話)。④《傅蘭雅檔案》,第3卷,第213頁。而且每一個方言大類都還有若干小類,因為幾乎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傅蘭雅也指出:漢語書寫語類型各不相同,包括古體、近體、官方體、文獻體、商業體、書信體等。⑤同上,第203頁。因此,“漢語”是個統稱而不特指某一種。
2.漢語的特點
傅蘭雅把漢語與世界上其他語言進行比較,總結出漢語獨特的優點和特點。⑥同上,第202—213頁。(1)中文漢字具有圖示、表意特性,把原始的漢字進行組合仍能表意,這為漢語所獨有。(2)漢語基本詞形有限,但漢語的組合使中文書寫有著其他語言所缺乏的表達能力。漢語字形簡潔合理,遠比歐洲其他語言更能有效地交流意念、表達思想。(3)漢語有很多量詞。(4)漢語擁有完備的數字體系。(5)漢語沒有變形、變格、規則、不規則、助動詞等特性,通過行文、漢字的位置與搭配來表達不同意思。人們只需要掌握四五千個漢字,就能準確閱讀,表達任意一個思想觀念。總而言之,傅蘭雅認為:中國語言歷史悠久,中國漢字獨特而古老,經過數千百年的持續發展,積累了龐大的詞匯。此外,中國語言使用者人數幾乎占全球一半,具備做“世界通用語”的潛力。
3.中國語言文字的發展性
針對西人“中國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⑦《江南制造局翻譯西書事略》(修訂版),第284頁。和“中文很難再發展”⑧《傅蘭雅檔案》,第2卷,第593頁。的論調,傅蘭雅予以駁斥,他認為中國語言文字與其他國家文字一樣具有發展性。他說,“然中國文字與他國略同,俱為隨時逐漸生新,非一旦而忽然俱有。故前時能生新者,則日后亦可生新者,以至無窮”。①《江南制造局翻譯西書事略》,第284頁。他分析了中國語言文字發展的兩個向度:內部發展與外部發展。在內部發展向度,中國文字的發展來自原住民。他從中國漢字的構詞體系說起,用象形字、形聲字證明中國漢字的發展規則。此外,他以《康熙字典》中漢字詞義轉變以及新增漢字為例,證明漢字發展的表現。在外部發展向度,他指出歷史上中國文字的發展與佛教徒、阿拉伯人、波斯人、滿人、蒙古人的交往有關。毋庸置疑,佛經的傳入給中國語言增添了不少新成員,如“般若” “宗旨”“凈土”“蕓蕓眾生”“有口皆碑”等詞語都源于佛經。同樣,晚清西學術語的引進,也豐富了漢語詞匯。傅蘭雅就科技術語翻譯提出了三種新創譯名方式:一是創字譯名,采取“形旁表類屬、聲旁表讀音”來新創漢字,或賦予《康熙字典》里的生僻字以新含義;二是復合術語譯名應采用意譯法;三是音譯。這些措施極大豐富了漢語的詞匯量。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所言的“余前與傅蘭雅先生同譯書于制造局,計為中國新添之字與名詞,已不啻一萬有奇矣”,②盧明玉:《譯與異—林樂知譯述與西學傳播》,北京: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9頁。便是明證。
4.用中文譯介西方科學
“西方知識能夠用中文來完整描述嗎?一種與歐洲語言毫不相干的古老語言能適應先進的科學、藝術和制造業嗎?近200年來產生的中國人毫無所知的無數個現代術語能用中文表述并使中國學者明白嗎?”③《傅蘭雅檔案》,第2卷,第592頁。針對這樣的問題,傅蘭雅堅定地認為,中國語言有足夠的能力來解決這些問題。他從自身多年的中文學習和翻譯實踐出發,闡明“中文書面語言靈活、簡潔,善于表達”,④同上,第421頁。不僅可以命名西方科技術語,而且還能保持科學的精確性和術語的特性。其次,他從中國歷史上的翻譯事實出發,指出中文不僅已經成功翻譯出了佛教、伊斯蘭教等典籍,也成功譯出了《圣經》和一些科學譯著。此外,用中文翻譯近代科學知識,“上可供官紳閱讀,下可教育青年”。⑤王樹槐:《清末翻譯名詞的統一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第47頁。因此,他極力倡導用中文譯介西方科學。
5.保護中國語言文字
在傅蘭雅看來,中國語言具有強大生命力,“中國的圖示性文字直到今天仍堅守著自己的立場” 而“未被表音符號或字母取代”;⑥《傅蘭雅檔案》,第3卷,第202頁。中國語言也具有獨特性,“漢字簡潔有力,形美感目,音美感耳”⑦同上。,能夠輕松表達任何抽象的概念。傅蘭雅說:“語言和文字是這個國家緊密團結在一起的支柱,是幫助全民族度過災難的力量,也是中國在歷史上稱雄鄰國的力量源泉,將與國家共存。”⑧《傅蘭雅檔案》,第2卷,第591—592頁。因此他認為中國語言文字應該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在西學譯介中,他也提出了保護中國民族語言的方法與策略。比如,針對晚清譯者采取音譯的方法譯介西方科學術語,他指出音譯法應該只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使用,因為音譯不顧原意,所用字數繁多,給漢語造成了無用的負擔,“損害了中文的歷史和表意功能的魅力”。⑨同上,第387頁。此外,他辯證地看待中國語言文字的發展路徑,一方面他認為可以靠吸收外來語發展中國語言文字,另一方面他堅持,不要讓不相關聯的語言借用成為漢語發展的“沉重包袱”,“比例適當,才有益處”。⑩同上,第388頁。
三、傅蘭雅漢語語言觀成因探析
傅蘭雅的漢語語言觀源于特定歷史語境中對西學翻譯的關注,但他與同時代眾傳教士不同的語言觀也是受其自身諸多因素影響的產物。傅蘭雅漢語語言觀受其日常生活、工作經歷與宗教信仰因素的影響。
1.日常生活因素:傅蘭雅的成長環境
家庭對于個人成長的影響毋庸置疑。有學者說,家庭環境的性質與特點直接或間接影響著兒童早期認知能力、社會性情感以及各種人格品質的發展。①谷傳華等:《中國近現代社會創造性人物早期的家庭環境與父母教養方式》,《心理發展與教育》2003年第4期,第17頁。傅蘭雅出生于一個傳教士家庭,其父是一位對中國深懷好奇心的傳教士,受他影響,他們全家對中國都有濃厚興趣,他母親甚至常煮米飯吃以備適應將來前往中國之需。就傅蘭雅個人而言,他嬰兒期就與中國結緣。據傅蘭雅的《中國生活回憶錄》,他嬰兒期曾受到一中國人探訪,并被贈以一枚中國銀元。這枚銀元也是傅蘭雅孩童時期非常珍視的物品。②《傅蘭雅檔案》,第1卷,第4頁。身處濃厚中國情結的傳教士家庭氛圍,傅蘭雅耳濡目染,從小就向往中國。少年時代,他竭盡所能閱讀有關中國的書籍,也常以中國為作文題材,因此他被昵稱“傅親中”。青少年時期正是個人價值觀形成期,傅蘭雅少年時期對中國的這份熱情、了解與憧憬,讓他對中國語言文化有著一種“同情之理解”。這份“同情之理解”隨著他在中國的工作與學習而與日俱增。
2.工作經歷因素:傅蘭雅的中文學習與翻譯實踐
傅蘭雅在中國的英文教學與翻譯工作都加深了他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理解。他1861年啟航從英格蘭前往中國,在航船上他都抓緊時間和機會學習中文。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最近花了大量時間學習”,③同上,第46頁。“我的中文有了一些進步,我可以慢慢閱讀中文版《馬太福音》了”。④同上,第40頁。他甚至能用筆頭與同船的一個廣東人交流。在他到達中國后的六年里,傅蘭雅在香港圣保羅書院、京師同文館、英華書館從事管理與英文教學。他的教學工作讓他明白了中國人學習外語的意愿與難度,認識到“要讓英語成為中國的學術語言需要很長時間”,⑤《傅蘭雅檔案》,第2卷,第361頁。因此要讓西學傳入中國,必須讓科學說中國話。另一方面,他的中文學習在教學中得到發展。在1865年12月《給圣公會的信:關于英華書館的第一份報告》中,他寫道,“廣東教師教中文典籍和唐詩”,“我也在學習中文課程,……自己受益”。⑥同上,第232頁。
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傅蘭雅不僅譯介了大量西學著作,而且翻閱了中國諸多經典之作,這都加深了他對中國語言文字和文化的理解。比如,他在《科學術語:當前的差異和尋求一致的方法》報告中說:無論是遠古時代佛教傳入,還是近世早期耶穌會士,他們傳下來的著作中引進的新詞或新觀念都是易于用中文表達的。中國宋代成書的《本草綱目》⑦此點有誤。《本草綱目》成書于明代,最初由劉應翻譯介紹到西方,1735年在《中華帝國全志》發表。之后多有傳教士對《本草綱目》加以關注。參見曹增友:《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386—387頁。和《洗冤錄》應該要成為這兩種科目引入新術語的基礎⑧《傅蘭雅檔案》,第2卷,第381頁。。再如,他后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開設中國文化課程,講授內容涵蓋中國概況、語言文字、歷史、地理、宗教、政治、文學、藝術、商業等。⑨《傅蘭雅檔案》,第1卷,第4—5頁。在西學譯介方面,他總結了科技術語翻譯三法:描述法、音譯法、描述與音譯結合法,并用中文譯出129種著作。他的翻譯實踐告訴他,中國語言可以應對翻譯問題。總之,傅蘭雅“漢語學習能力異常出眾”,⑩同上,第215頁。來中國六年后,不僅掌握了通用的書面語言,對粵語、官話、上海話也能運用自如。“傅君深通中國語言文字”?? (清)華蘅芳:《防海序》,載傅蘭雅、華蘅芳譯《防海新論》,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1874年,序言頁。是對傅蘭雅多年中文學習成果的高度總結。3.宗教因素:基督精神的影響
“基督精神即為耶穌基督的人格所表現的精神,或耶教《圣經》中所含的精義”。①賀麟:《基督教與政治》,載《文化與人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38頁。基督教充滿民主與博愛精神,民主,即“在上帝面前人人一律平等”,“己之所欲,則施于人”。②顧紅亮:《基督教精神如何進入賀麟心學之思》,《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第51頁。博愛則指廣泛地愛一切人與生命,“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的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③《馬太福音》,第22章,第25節。作為傳教士,他深受基督精神的熏陶,心懷“廣傳上帝福音”的愿望來到中國,堅信“只有依照上帝的旨意方能成功”。④《傅蘭雅檔案》,第1卷,第II頁。基督教的博愛、平等精神在傅蘭雅身上得到具體體現。他認為知識無國界,“學術一道,不在一國一邦”。⑤《江南制造局翻譯西書事略》(修訂版),第289頁。他認為,現代科學是人類共同財富,沒有中西之分,更無夷夏之別,因此他把“譯書啟發中國民智”當作“神圣責任”,⑥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3頁。“全心全意熱愛這份事業”,⑦《傅蘭雅檔案》,第2卷,第579頁。希望中國能步入科技發展的行列。他希望能確保把“這些科學成果……帶給西方國家的恩惠,同樣帶給居住在這片絢麗土地上的人民。”⑧同上,第378頁。他希望中國能享受上帝的福音,走上科技發展的道路。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對中國語言文字的態度。
四、傅蘭雅漢語語言觀的當代價值
作為一個英國傳教士,在晚清中國深受西方列強侵略、“國將不國”的情況下,傅蘭雅拋棄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偏見,站在中國的立場上,表達了其具有鮮明系統性、批判性和前瞻性的漢語語言觀。他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中國語言文字,系統總結了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批判了當時西方文化殖民主義的語言觀,堅信中國語言文字的歷史優越性和發展性,提出要保護中國語言,并堅信中國語言有理由成為世界通用語。他的這些觀點不僅對晚清中國的西學譯介和文字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當今中國的翻譯實踐、語言政策制定,維護中國語言的純潔性,增強中國語言文字自信也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1.翻譯與漢語的規范性
傅蘭雅在晚清缺乏西方科技術語的對應中文詞匯的情況下,主張用中文進行譯介,即使沒有合適的字眼,他都主張根據中國漢字的特點創造新字來譯介。這對于今天譯介紛繁復雜的外來術語仍有借鑒價值。如今,諸多外來術語如OpenedX、iphone、ipad都直接出現在中文里,直接影響中文句子的流暢和美感。要保護漢語的純潔性與規范性,就必須把好翻譯關,加強翻譯的“轉換器”和“過濾器”功能,盡可能地減少“零翻譯”。2014年4月11日,《人民日報》刊發《外來語濫用,不行》。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外語中文譯寫規范部暨聯席會議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黃友義也反對把外來語直接“塞”進中文中,他認為這種做法不代表開放程度,也不代表國際意識,只能說明我們不負責任,對漢語不尊重。⑨董洪亮:《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黃友義:要預防外語詞“捷足先登”》,《人民日報》2014年4月11日,第12版。因此,中國譯者在面對外來術語時,一定要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態度,注意“首譯”的重要性和影響,盡可能地根據情況采取意譯和音譯方式進行譯介,一方面化“外來語”為漢語,豐富漢語的詞匯,另一方面維護漢語的規范性。
2.中國文化自信與語言文化推廣
早在晚清,傅蘭雅從一個西方人的視角對漢語進行了系統總結,多方面肯定了漢語的優越性和普及性;他預言,漢語的“精煉與無語法變化使其易于掌握并很容易為每個國家所使用”,“足以成為世界通用語”。⑩《傅蘭雅檔案》,第3卷,第213頁。他這種對中國語言文字的信心給當今中國實施語言文字推廣和“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歷史依據。增強中國語言文字自信,可以從兩方面展開:一是增強中國人自身對漢字的文化自尊心和認同感;二是提升漢字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已有一些組織和機構采取相應措施。如2009年成立的中國文字博物館,“以字為體,傳承民族自信”,“以字為媒,讓中華文明走出去”①劉先琴:《為漢字插上翅膀—中國文字博物館建館五周年回首》,《光明日報》2014 年11月24日,第9版。為建館宗旨,傳承與弘揚中國文字和文化。該機構舉辦“中國文字藝術國際展”,在海外舉辦“漢字巡展”,以促進中國文字和文化的推廣。“文字是中華民族的脊梁骨”,②何苗苗,王剛:《在文字中尋找中華文化根脈》,《河北畫報》2014年第5期,第26頁。所以,作為中國人,我們一方面要增強中國文化自信,學好漢字,傳承中國文化,另一方面要宣傳中國漢字和文化,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國專家指出,目前世界對中國的了解還遠非全面,我們要“從古到今、從東到西、從表里到內核,全方位地表達和推廣”。③同上,第27頁。
結語
傅蘭雅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之下,形成了與眾傳教士迥異的漢語語言觀,其語言觀充分體現了他對中國語言文字的認識,對中國語言文字發展的關切與信心。他的語言觀為當今中國外譯漢實踐、維護中國語言文字的純潔性,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都提供了歷史依據和理論基礎。這就是歷史研究的現實教益價值。
法籍華人漢學家程艾藍
程艾藍(Anne Cheng),法籍華人。1955年生于巴黎的中國家庭,接受了完整的法國教育,深受古典與歐洲人文思想的熏陶。其父程抱一是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de France)首位亞裔院士。1975年她畢業于巴黎高等師范學校,曾留學復旦大學。三十余年來,她先后在法國國家研究中心(CNRS)和法國東方語言學院(INALCO)從事中國思想史的教育與研究工作,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儒學、新儒學和當代哲學問題。1981年用法文翻譯了《論語》。1997年出版了《中國思想史》,得到漢學界高度評價。她的著作,以既歷史又主題的方法來敘述一個長達數千年的精神歷程,重點凸顯了復雜整體中幾個驚人的時刻。2007年主編了法文版論文集《中國當代思想》。2008年在法蘭西學院發表就職演講《中國有沒有思想?》。2010年主講《法國當代漢學概覽》講座。
她曾在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等機構任教,是法國大學科學院高級院士、法蘭西學院中國思想史講席教授、歐洲漢學會副主席。2008年被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選中為中國哲學文化課教授。她還管理法國文學出版社(Edition des belles lettres)于2010年3月成立的“中國書房”。她深受歐洲古典人文思想影響,同時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直致力于漢學研究,自稱歸屬于中國與歐洲兩種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