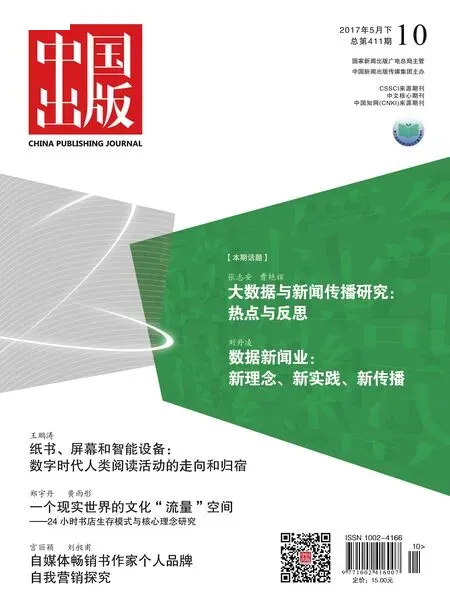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文學期刊發展策略*
□文│朱卉平
進入新的世紀以來,隨著新媒體的強勢來襲,文學期刊不僅要抵制大眾文化對其文學藝術傳統地位的顛覆,還要面對來勢兇猛的新生力量新媒體所發起的挑戰。文學期刊需要積極尋求與探索新媒體的支持和契合,并樹立其在人們精神世界中不可取代的權威性。
一、文學期刊發展狀況調查分析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網絡信息技術與電子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節奏與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改變,在業余生活中更加熱衷于選擇文化快餐,文學期刊逐漸喪失其精神場的主導地位,并被文化市場邊緣化,生態環境逐步惡化。大量調查數據表明,文學期刊的受眾大量減少,發行量也銳減,其發展舉步維艱。
文學期刊的受眾與發行量是其發展狀況的主要指標,為了直觀地審視文學期刊發展的真實狀況,可以通過從文學期刊的受眾與發行狀況兩個方面來對其進行調查與分析。
文學期刊主要以知識精英中的文學愛好者、從事文學創作和研究的從業者以及普通市民中接受能力較強的文學愛好者為受眾目標。而當前隨著生活方式的娛樂化,一些受眾尤其是青年讀者轉向輕松淺層次的新媒體閱讀,文學期刊的受眾正在快速流失。據《天津日報》2014年4月30日調查報道,當地絕大多數大學生課余愛好上網、看電影、外出游玩,也有部分學生喜歡做兼職工作而賺取一些生活費,而相比之下,愛好文學閱讀的學生少之又少,其中38.68%以上的大學生對文學閱讀根本就沒有興趣,還有10.71%的大學生幾乎從來就不看書,大部分學生每天上網時間超過3個小時,而其中59%的時間用來聊天、打游戲,或者看綜藝節目與影視劇等,網絡在大學生的日常生活中變得愈來愈重要,大學生閱讀文學期刊的人數也愈來愈少。這種現象頗能反映新媒體對青少年讀者的閱讀影響。
另外,文學期刊發行量也在急劇萎縮。業界人士認為,文學期刊實現自負盈虧“生存線”的發行量為每期 5 萬份,但是相關數據顯示,我國文學類期刊共有600多種,發行量能達到“生存線”的雜志卻只有《收獲》《當代》《十月》與《人民文學》等七八份雜志。目前《收獲》的發行量是13.5 萬冊,《當代》與《十月》發行量為8萬~10萬冊,《人民文學》則為5萬~6 萬冊。
二、新媒體時代背景下的發展機遇
在新媒體時代背景下,新媒介的快速發展與融合對于文學期刊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文學期刊該如何借助新媒體的信息傳播技術優勢來提升自身發展空間與影響力,其對策的研究與制定是當務之急。對于傳統文學期刊來說,應該充分利用新媒體信息傳播的優勢,不斷加大新媒體建設的力度,從而利用更加高效而廣泛的電子技術手段傳播出去。所以,新媒體的強勢來襲,對于文學期刊的發展來說,是挑戰,更是機遇。新媒體及其技術的發展與融合對其發展可能產生的機遇包括:在文學期刊的銷售與傳播方面,新媒體的網絡平臺及其異常龐大的移動客戶端可以為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銷售與傳播渠道,并大大提高其市場競爭力,從而為文學期刊提供長期、持續發展的機會。在文學期刊的受眾量的維護方面,微博與微信等新媒體的后臺數據搜集功能不僅可以幫助其輕而易舉地完成對用戶數據的調查與分析,而且還可以增強其與受眾的良性互動,并大力提升其業務空間。
三、與不同媒介合作探索發展路徑
當前,在新媒體時代所帶來的發展機遇中,各種文學期刊不斷嘗試與各種媒介及其網絡信息傳播平臺進行合作,并試圖探索與尋找在新媒體時代的各種發展對策。
1.建立長期有效的新媒體傳播渠道
《十月》雜志副主編寧肯認為:“如果把紙質期刊看作是一只鳥的身軀,那么新媒體就像是翅膀,帶著讀者飛得更高、更遠。”[1]要擴大文學期刊的傳播途徑及其影響力,必須與時俱進,建立起微博、微信公眾號與客戶端等長期有效的新媒體傳播渠道。
當前,各種文學期刊在試圖尋求發展機遇的過程中,也都在不斷嘗試與各種新媒體網絡平臺的合作,并尋找文學期刊更加多元而有效的發行與傳播途徑。《人民文學》《當代》等一些傳統的文學期刊都先后開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以及手機客戶端等,不斷加大文學期刊的新媒體建設,進一步拓展了文學期刊的傳播途徑及其影響力。如作為我國傳統文學期刊一面旗幟的《人民文學》,在文學期刊的新媒體建設中,不斷探索,積極創新,在引導文學期刊尋求長期有效的新媒體傳播渠道與擴大文學期刊的傳播途徑及其影響力上,都做出了貢獻。《人民文學》官網與官方微博已開通近10年,官方微博愈來愈有特色,自主開發了手機客戶端應用程序APP平臺“人民文學醒客”,并開設微信公眾號等,其關注度與閱讀受眾人數不斷攀升。在微信公眾號上,《人民文學》每期發送卷首語、目錄及其重點篇目內容片斷等,為期刊開發造勢宣傳;設置微店鋪、消息樹、小助手等工具,開發多種文學信息的閱讀功能;專門開辟作家小輯、創作談與評論等欄目,在其內容上不斷創新,并逐步形成其常規化的運作與管理;在醒客APP上,《人民文學》以“盒子”為組合方式,為文學受眾提供了“五四”以來所有的中短篇小說及其文論,使其傳播渠道更加便捷而高效。同時,我國傳統文學期刊《當代》自1999年開啟其新媒體之路之后,現在也基本建立了文學期刊電子媒介的新常態,官方微博與微信公眾號日日更新,在閱讀受眾中已經產生了廣泛而良好的影響。我國這些極有影響力的文學期刊發展的實踐經驗證明,在當前新媒體時代的背景下,雖然各種文學期刊的品牌定位與經營理念各不相同,但是,為了擴大其傳播途徑及其影響力而建立起自己的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與客戶端等長期有效的新媒體傳播渠道已經是必然選擇。
2.打造IP孵化合作平臺,開展線上線下活動
在互聯網技術發展變化日新月異、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市場不斷升級的時代,文學作品的IP孵化已經成為文化商業市場爭相關注的一個經濟熱點。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不斷沖破新媒體的圍困與擠壓,探索各種文學期刊交流平臺的可能性,建立編輯、作家與讀者新的溝通機制與方式,延伸其發展空間,文學期刊應該積極嘗試打造IP孵化合作平臺,大力開展線上線下的文學創作與交流活動。例如2016年5月《收獲》雜志聯手“贊賞”IP平臺共同開發寫作出版社區“行距”APP。“行距”是一個為作者與包括文學編輯、出版及其經紀人在內的專業出版人而搭建的主流文學創作與IP孵化、交易的平臺。作為一個文學IP孵化的平臺,“行距”APP不僅可以接受在線投稿,得到以《收獲》雜志編輯為主的國內一流編輯的在線寫作輔導,而且還可以把一些優秀的文學作品集成再進一步延伸出去。《收獲》主編程永新對此稱,“我們想改變現有的作家、編輯、讀者的溝通方式和體制,通過這個平臺探索各種可能性。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在原創為王、IP為王、內容為王的時代,開拓一條通往劇本工廠的道路”。[2]如今,經過近一年經營與運作,“行距”APP已經逐步成長為一個新的文學生態系統,其中自由投稿多達幾千部,且保持了一定質量水平。《收獲》雜志與“贊賞”IP平臺的合作,不僅解決了文學期刊新媒體建設的技術問題,消除了文學期刊遭遇的轉型困境,而且將通過文學作品的IP孵化,大大提高文學期刊的市場經營效益,為整個華語文學圈文學期刊的發展帶來新的生機與希望。
3.精心打造期刊品牌,全面實施文學期刊媒體品牌戰略
期刊品牌是文學期刊的無形資產,是文學期刊的核心競爭力。因此,在新媒體時代,文學期刊要參與市場競爭,既要不斷加強與新媒體的合作與融合,又要堅持自己的特色與風格,樹立品牌意識,精心經營與營銷文學期刊品牌,創辦名牌欄目,推出名牌作家,努力塑造優質化和品牌化的文學期刊形象,全面實施文學期刊媒體品牌戰略,大力提升其社會影響力。
當前,在品牌經營與營銷做得比較成功的文學期刊有《萌芽》《青年作家》與《北京文學》等。1998年12月文學期刊《萌芽》走上文化創意產業化與品牌化之路,經過精心策劃與設計,率先發起旨在為新世紀“培養新人才”的新概念作文比賽,并由此展開了以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為載體的品牌經營與營銷活動。而隨著“新概念作文”品牌的成功宣傳與營銷,《萌芽》不僅培養了韓寒、郭敬明與張悅然等一批新銳暢銷小說作家,其銷量與影響力也隨著其品牌效應節節攀升,而且還不斷進行品牌延伸,出版“萌芽書系”,推出青春讀物品牌,創立教育品牌“上海市萌芽實驗中學”等。在當前各種媒體競爭異常激烈的背景下,《萌芽》成功的期刊品牌營銷經驗給全面實施文學期刊媒體品牌戰略提供了參考與借鑒意義。成都本土文學期刊《青年作家》一直以時尚、文藝與市場化為辦刊理念,始終堅持雜志的文學性、思想性與青年性方向,致力打造品位、有力度而新銳的文學期刊品牌,其借助“品牌中國行”活動,打造全國性品牌文化工程,明確期刊的青年目標,精益求精的期刊作品風格、形象設計及其整個工藝流程等,從而使其成為2016年 “中國最美期刊”,成功塑造了自己的品牌,大大提升了其影響力。這些期刊成功的經驗說明,只有精心經營與營銷期刊品牌,才能全面實施文學期刊媒體品牌戰略。
四、結語
文學作為一種影響人們的意識形態與引導社會主流價值觀的精神產品,“在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有著其他載體無法比擬的重要地位”。[3]因此,在新媒體時代背景下,文學期刊既要與時俱進,不斷加大與新媒體的合作與融合,尋找新的生長點,同時也要始終堅持文學的質的規定性,堅持自身應有的文學精神及其審美價值取向,從而在新興媒體和傳統紙質媒體的激烈博弈中尋求新的發展平衡點。
注釋:
[1]孫宗鶴.新媒體是文學報刊的翅膀[N].光明日報,2016-07-31
[2]徐穎.《收獲》聯手“贊賞”IP平臺重新出發[N].新聞晨報,2016-05-20
[3]李娟.新媒體時代文學期刊應有的文學品格[J].安徽文學,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