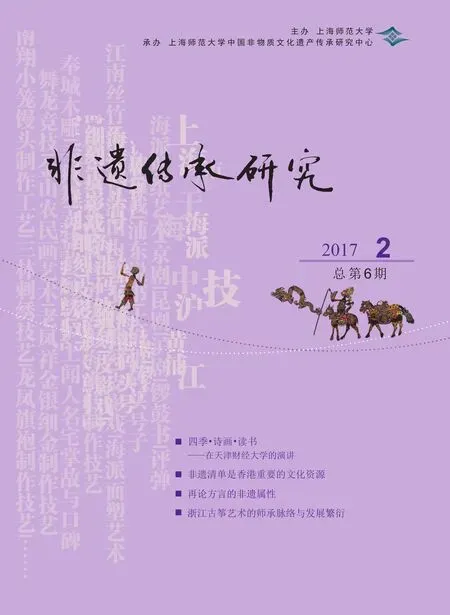非遺傳承機制的文化研究
——論傳承人口述史的人文訴求
祝昇慧
洛特曼把文化定義為“群體的不可遺傳的記憶”[1](P22),卡西爾也認為,“在人的‘符號形式’中——它們構(gòu)成了人的存在和天賦中的非遺傳的部分——人仿佛已經(jīng)找到了解決他的有機自然所不能解決的那個問題的方法。過去‘生命’概念所沒有涵括的,現(xiàn)在由‘精神’概念全面地給予涵括了。在這里,個體的變化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更加深刻的方式與類的變化相聯(lián)系。”[2](P194)正是在充滿符號的文化世界中,人區(qū)別于其他有賴于遺傳的生物,得以突破生死的局限,在更寬廣的關(guān)聯(lián)中將一種精神的生活延續(xù),這也印證了“人類的文化根性就是一種傳承的機制”。[3]
事實上,民間文化的傳承往往是自發(fā)性的,很多傳承人對于自身的傳承行為及其價值并沒有自覺清醒的認識,如何把這種自發(fā)狀態(tài)激活為自覺的表達,正是口述史有所作為的地方。口述史不只是被動的記錄,更是能動的實踐,它能夠通過研究者與傳承人之間的對話,深入到人本、歷史、文化等價值層面,把握非遺傳承機制中的人文訴求,達至文化自覺。
一、傳承人的生命情感與主體意識
在非遺熱潮中,傳承人逐漸從日常生活世界和熟悉的鄉(xiāng)土社會中脫離出來,并面臨著文化身份轉(zhuǎn)換的問題,正是在這一轉(zhuǎn)型過程中,他們身上最大程度地體現(xiàn)出由傳統(tǒng)藝人的自發(fā)性向非遺傳承人的主體自覺性的過渡與變化。相應(yīng)地,學者也“從過去主要注重對民俗事象的文本研究轉(zhuǎn)向重點對民俗文化的人本研究”。[4]正如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中指出的那樣,“民間史詩是匿名的這一觀點,是一種謬誤,因為歌手擁有一個名字”,[5](P146)這種觀點改變了以往傳承人被淹沒在群體和傳統(tǒng)背后的“無名”或“匿名”狀態(tài),由此帶來了對傳承人個性、風格、生命情感、創(chuàng)造力的關(guān)注。
1.傳承人生命情感的表達
傳承人所傳承的不僅是智慧、技藝和審美,更重要的是一代代先人們的生命情感,它讓我們直接、真切和活生生地感知到古老而未泯的靈魂。這是一種用生命相傳的文化,一種生命文化,它的意義是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不能替代的。在傳承人身上充分展現(xiàn)了民間文化的審美之維,它包括三方面:首先是直接來自生命本身的“自發(fā)性”,具有生命的本質(zhì)與生命之美;第二是非理性的、純感性的民間情感;第三是鮮明的地域性與審美語言的方言化。[6](P350)這三點渾然一體地反映在傳承人及其傳承的民間文化上。
如何“有可能使歷史展現(xiàn)出有血有肉的‘人’的個性特征”[7](P1)是我們在做傳承人口述史時的首要追求。馮驥才先生曾經(jīng)總結(jié)他的田野經(jīng)驗,談到“把握傳承人的個性,就像音樂家在鋼琴上隨性彈奏,忽然有了靈感,從中找到幾個音,然后鋪就成樂章一樣,是一種文學的手法。對于人的理解,不同于記者訪談的誘導,也許傳承人說的并不是你問的,或者是說出你也許根本不知道的。”在此,文學家對于人物的觀察手法可以運用到口述史中,以捕捉傳承人的生命情感與生活細節(jié)。
生活在西北高原的庫淑蘭是一位經(jīng)歷坎坷的剪花娘子,在李小江主編的《讓女人說話:文化尋蹤》[8](P299-331)中,采訪者從女性的視角、從庫淑蘭身為女人的獨特生命體驗出發(fā)來理解她的藝術(shù)與人生。口述中,庫淑蘭在回顧自己一生時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恓惶哩很”(恓惶是當?shù)胤窖裕锌蓱z、傷心、憐惜的意思)。她和任何一名普通的農(nóng)村婦女一樣,從小就做農(nóng)活、纏腳、定親,15歲就嫁人,受婆家的辱罵,挨丈夫的毒打,從凌晨到深夜不停地勞作,她生過13個孩子,又看著10個孩子死去。她也相信神鬼靈怪,也會燒香、禱告,時不時用農(nóng)村人“送病”的法術(shù),給小孩治個頭疼腦熱。過年時,也會剪個紙花,貼窯里,貼窗上,求個喜慶,祈求多點幸運。如果不理解她和她身后億萬名中國農(nóng)村婦女的命運,也許就無法理解她何以在剪紙中寄托和表現(xiàn)出那么強烈的理想、情感、自由和歡樂。她在一次意外中從山崖上跌下,被救醒后就說自己是“剪花娘子”,這段類似于史詩傳承中“托夢”或“神授”的經(jīng)歷,更是為她的人生增添了傳奇的色彩。
因此,對傳承人生命情感的理解首先需要我們打破長期在書面文化訓練下養(yǎng)就的邏輯思維的束縛,從傳承人的日常生活和他們的生命情感中去理解他們的世界與觀念。前蘇聯(lián)心理學家盧利亞針對許多不識字和半文盲的人做了大量田野調(diào)查工作,發(fā)現(xiàn)“口語文化根本就不能對付幾何圖形、抽象分類、形式邏輯推理、下定義之類的東西,更不用說詳細描繪、自我分析之類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并不僅僅是思維本身的產(chǎn)物,而是文本形成的思維的產(chǎn)物。”[9](P42)
曾經(jīng)做過土匪、淘金、伐木、放排、狩獵、吹鼓、皮匠、木匠、鐵匠等多個文化系列口述史的曹保明,發(fā)現(xiàn)在東北這片地表文化遺存匱乏的土地上,口述文化卻極為發(fā)達,所以他較早開始進入傳承人口述史的領(lǐng)域。在筆者對他的一次訪談中,他講了一個親身經(jīng)歷的案例來說明口述史對于人的關(guān)注的重要性。他說,“一個唱二人傳的老頭要死了,他死之前跟老伴說:‘老婆,你把門推開,我唱兩句再走’。你看多好,他一輩子要死了的時候,唱了才咽的氣。過去我們只注意記載二人傳藝人所唱的詞,錯了,我們現(xiàn)在應(yīng)該關(guān)心的是這個人,他為什么要唱一段再走,他唱的是什么,他唱的這一段故事當中,或者是大西廂、或者是白蛇傳,和他有什么關(guān)系。”之所以要關(guān)注人,是因為“文化的生動性不是傳統(tǒng)文化記下來的東西,更多地體現(xiàn)在人的生命史上”。對于生命情感的關(guān)懷和理解帶給傳承人口述史不一樣的追求,“每一個口述史都是非常細膩的,你得有他遺產(chǎn)傳承的氣息。……口述史不是復述文化的本身,是復述文化形成的過程,如何保留這個文化的情感。”
因此,我們需要摒棄來自書面文化的思維定式,到民間去,走進傳承人的生活世界,從他們自發(fā)的情感中,從他們的日常勞作中,從他們的生命記憶中,以人文的情懷去貼近、理解、捕捉他們身上保留的傳統(tǒng)的生動。
2.傳承人主體意識的覺醒
作為口述采訪者(研究者)一方,我們做“民間”的學問,在心中要有“民”,有積極行動的個人。當我們在泛指的意義上使用“民間”的時候,清楚地意識到民間是主體的集合;當我們在談?wù)撎囟ㄎ幕臏Y源而使用“folk”的時候,認真地把他們當作具有政治、社會、文化的公民身份的成員來對待,這是今天在“民間”做關(guān)于文化的調(diào)查研究要具備的學術(shù)倫理。[9](P4)
作為被采訪的另一方,傳承人也表現(xiàn)出主體意識覺醒過程中的種種尷尬與調(diào)適、選擇與建構(gòu)。筆者所在的學院于2010年10月份曾舉辦過一次“把國家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請進校園”的活動,全國各地身懷絕技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到此進行現(xiàn)場表演,期間還舉辦了“民藝大師與大學生面對面”系列座談會。當時的媒體報道出現(xiàn)筆誤,將“民間藝術(shù)大師”寫成“民間藝人”,馬上就有傳承人拿著報紙找到我們指出錯誤,他們十分在意自己“大師”的頭銜,不滿于傳統(tǒng)的“藝人”稱謂,這恰恰折射出他們在新時期對于自身變化了的文化身份的敏感與認同。
當然,也有的傳承人依然保持著對自我與傳統(tǒng)、個體與群體關(guān)系的清醒認識,并能較為順利地完成身份的轉(zhuǎn)換。如陜西鳳翔年畫傳承人邰立平,現(xiàn)今搬到寶雞市,離開了世代居住的南肖里村,“地氣”的改變,使他“只能關(guān)起門來搞恢復工作,即使創(chuàng)作,也不會有原汁原味的作品”。在口述采訪中,他談到跟祖輩們相比,自己“已經(jīng)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年畫藝人了”。他將成功歸于自己趕上了好時代,“祖輩做年畫的深度我沒能達到,但是大大拓寬了廣度。借助各種力量,尤其是新聞媒體,把鳳翔年畫推了好遠,這是過去沒法想象的事兒。”在傳統(tǒng)面前,他覺得自己“與過去那些人,差距太大。不要說去超越他。”難能可貴的是,他始終不忘自己身后那些默默無聞的藝人們,“其實民間藝術(shù)里邊,真正做事兒的人,好多還沒被發(fā)現(xiàn),很多很多的。正是這些人,把我們這些人都托起來,要沒有這些人,中國民間美術(shù)這一塊就不會興旺,就不會再繼承和發(fā)展。”
事實上,正是在面對傳統(tǒng)的問題上,最能體現(xiàn)出傳承人是如何對待傳承并自我定位的,最能反映其主體意識的覺醒程度,這也是口述史應(yīng)當著力之處。
對于傳統(tǒng)的問題,首先可以從社會知識分層的角度來考察:社區(qū)中傳承人的身份是如何確定的?一個人是如何成為或被培養(yǎng)為所在社區(qū)的傳承人的?傳承人是在怎樣的知識語境或情境化語境下來完成其特殊的責任的?不同社區(qū)中的傳承人具有什么樣的文化經(jīng)歷?[10](P213)
此外,傳承人身上表現(xiàn)出來的傳統(tǒng)與創(chuàng)造性之間的關(guān)系也可以作為考察的方面,創(chuàng)造性也可以理解為在新的情境下、以新的方式對傳統(tǒng)形式的一種應(yīng)用。傳承人會表現(xiàn)出不同的取向:有的恪守祖制,膜拜傳統(tǒng);有的力求擺脫匠氣,表現(xiàn)出向精英文化的靠攏;有的吸取其它藝術(shù)門類的精華,或者借鑒其它地方同類作品的風格等等。
再有就是從“傳統(tǒng)化實踐”的角度來考察社會的互動關(guān)系。人們要把自己的現(xiàn)在與過去相結(jié)合,可以把自己的話語傳統(tǒng)化,為自己賦予傳統(tǒng)的權(quán)威。這種策略性操作,體現(xiàn)于個人或集體層面,同時針對社會內(nèi)部成員和外部他者。[10](P218)
當前,與傳承人相關(guān)的一個新的特殊領(lǐng)域就是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我們從非遺熱潮中不斷傳來的各類民間文化遺產(chǎn)的著作權(quán)、版權(quán)、商標權(quán)等糾紛案中既可以看到傳承人維權(quán)意識的增強,也可以感受到市場化商品化帶來的價值失范。在此,鮑曼提供了一種批判的視角,他認為,“當把某種東西說成是傳統(tǒng)的,其實也是在表示:‘我沒有制造它’、‘我沒有創(chuàng)造它’、‘它是過去早就創(chuàng)造出來的東西。’而關(guān)于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許多理解,則力圖要確定個體的作者,聲明各種不同的所有權(quán)。傳統(tǒng)就是與創(chuàng)造有關(guān),與所有權(quán)有關(guān):說什么是傳統(tǒng),就是在強調(diào)它不僅僅同我自己有關(guān),而且同所有人相關(guān)。”[10](P221)這也表明,傳承人應(yīng)當既能從復數(shù)的、匿名的民眾中走出來,又能容納厚重的文化傳統(tǒng)與身后的地域群體。
綜上所述,非遺帶給傳承人身份的轉(zhuǎn)換、利益的博弈、傳承的挑戰(zhàn)等諸多現(xiàn)實問題,傳承人如何應(yīng)對并完成自我定位與轉(zhuǎn)型是一個主體文化自覺的過程。所謂主體文化自覺,是指主體在現(xiàn)實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自覺地認識到自我的文化存在,自覺形成和持有一種文化準則和文化價值追求,自覺地反思自我的文化存在,自覺的實現(xiàn)文化的內(nèi)化,并通過主體意識的強化和實踐活動的深入自覺地實現(xiàn)新文化生成的動態(tài)過程。[11]而口述史將有助于傳承人從非遺研究的“客體”轉(zhuǎn)化為非遺實踐的“主體”,并最終走向文化自覺。
二、歷史建構(gòu)中的再現(xiàn)與敘事
口述史能夠“把歷史引入共同體,又從共同體中引出了歷史”[12](P24),傳承人因其攜帶著密集的群體歷史文化訊息發(fā)揮著核心的凝聚作用,能將分散孤立的個體聚攏起來,將日常生活領(lǐng)域與宏大事件連接起來,書寫屬于共同體的歷史。由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過去在當前的呈現(xiàn),因而傳承人作為歷史的闡釋者,在“如何同過去對話,怎樣透過時間的距離來理解過去要說些什么”的問題上,將以現(xiàn)在為中心,同時朝向過去與未來展開對話,即“我們試圖理解某一事件在它發(fā)生的時代里意味著什么,同時也要理解這件事對于我們今天具有什么意義”,“再現(xiàn)”歷史的同時,闡釋者必須顯露出自己的聲音和價值觀,也就在此處,闡釋者試圖參與和建構(gòu)關(guān)于未來(而不只是關(guān)于過去)的對話。[13](P7)雙重時間之維指向的對話,既是自發(fā)的、無意識的對于歷史的回憶,也是自覺的、有意識的對于歷史的生產(chǎn)。
1.歷史的再現(xiàn)與還原
在人類尚沒有“文化遺產(chǎn)”的概念之時,廣大民間的世代相傳的文化中,唱主角的就是傳承人。他們就是數(shù)千年來一直活躍在民間的歌手、樂師、畫工、舞者、戲人、武師、繡娘、說書人、各類高明的工匠以及各種民俗的主持者與祭師。這是一群智慧超群者,才華在身,技藝高超。黃土地上燦爛的文明集萃般地表現(xiàn)在他們身上,并靠著他們代代相傳。特別是這些傳承人自覺而嚴格地恪守著文化傳統(tǒng)的種種規(guī)范與程式,所以往往他們的一個姿態(tài)、一種腔調(diào)、一些手法直通著遠古。常常使我們穿越時光,置身于這一文化古樸的源頭里。所以我們稱民間文化為歷史的“活化石”。
傳承人的記憶就住藏在他的身體認知當中,口述采訪者如何能夠通過訪談發(fā)現(xiàn)、挖掘并還原出歷史鮮活的生命整體呢?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海登·懷特首先致力于恢復歷史學在文學想象力中的起源,他認為事實上,歷史——隨著時間而進展的真正的世界——是按照詩人或小說家所描寫的那樣使人理解的,歷史把原來看起來似乎是成問題和神秘的東西變成可以理解和令人熟悉的模式。不管我們把世界看成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解釋世界的方式都是一樣的。[13](P178)
全國年畫大普查時豫北古畫鄉(xiāng)——滑縣木版年畫產(chǎn)地的田野發(fā)現(xiàn)也是這樣一個對歷史索影追蹤的過程。馮驥才在對年畫傳承人韓建峰的口述采訪中,緊緊盯住當?shù)匾恍┠戤嬂习妫憩F(xiàn)出對以下幾個關(guān)鍵線索的追問:一是神農(nóng)像,人面牛首、身披樹葉的老者,被敬奉于年畫正中,當?shù)厝朔Q為“田祖”,對于神農(nóng)氏的崇拜,在其它產(chǎn)地較為罕見,它說明農(nóng)耕文明在中原大地上的長流不斷,具有活化石的意義;二是很多年畫的上端印著“神之格思”四個字,出自《詩經(jīng)·大雅·抑》,這四個字從未出現(xiàn)于任何地方的木版年畫中,而且當?shù)乩先艘膊唤馄湟猓炊堰@四個字從左到右念成“思格之神”,顯然這歷史已經(jīng)十分古老了;三是組字對聯(lián),即民間用圖案化的奇異文字來書寫的一種詩句或?qū)β?lián),藏字于其中,憑觀者來猜解,目前只知道橫批是“自求多福”,下聯(lián)是“日出富貴花開一品紅”,上聯(lián)無人曉得,猶如“失落的文明”;四是有的年畫上出現(xiàn)滿文的文字,經(jīng)采訪,了解到當?shù)啬戤嬙跉v史上曾遠銷東北、內(nèi)蒙一帶,供那邊的滿人使用,可以想見曾經(jīng)的生產(chǎn)規(guī)模之大與銷售區(qū)域之廣;五是《老虎》年畫,酷似山東楊家埠的《深山猛虎》,據(jù)傳承人口述,此地年畫也曾遠銷山東,他們還專門為山東人印制一種那里喜歡的《搖錢樹》,類似于為外地“照樣加工”的活路。因此,從這個年畫產(chǎn)地的田野發(fā)現(xiàn)和傳承人的口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它歷史的輝煌,直通遠古的氣息,流布四方的影響力。難怪馮驥才感慨道,滑縣曾經(jīng)并不是一個封閉的地方,只不過被遺忘罷了。而歷史,只要被遺忘就是一片空白,只要中斷就會失去。[14]這正是我們在做傳承人口述史時要特別追蹤歷史的源頭,捕捉歷史的細節(jié),把歷史的上限不斷推進的原因,同時也需要有一種建構(gòu)性的文學想象力去填補歷史的空白與罅隙。
我們和傳承人面對面的口述交流是一種歷史的拾遺;然而,較之物質(zhì)的見證更為優(yōu)越的是,傳承人身上承載著非遺活態(tài)的生命與傳統(tǒng)的生動。正是通過他們,我們得以與往昔的文化晤面。
2.歷史的敘事與生產(chǎn)
歷史建構(gòu)是在構(gòu)造一個由事件與敘述構(gòu)成的富有意義的世界。因為建構(gòu)過程的動機來自于居住在特定社會世界的主體,我們可以說,歷史是現(xiàn)在對過去的銘刻。
臺灣學者王明珂也指出“當代口述歷史學者常藉由當事人的親身經(jīng)歷記憶,來補充歷史文獻記載之不足”。這對于追求“歷史事實”的歷史學者而言,不失為一種歷史研究的新工具。然而研究者若只滿足于追求如此的歷史事實,則忽略了口述資料的價值。這樣的口述歷史只是為“典范歷史”增些枝節(jié)之末的知識而已。甚至它更進一步強化了反映男性、統(tǒng)治者、優(yōu)勢族群觀點與其偏見下的“典范歷史”,而使得“歷史”成為階級權(quán)力下的工具。由社會記憶角度來說,每一個口述中的“過去”都是一種“述事”。它反映口述者的社會認同與文化價值,以及對自身社會角色之體認。[15](P8)
民眾在對待文化傳承的問題上,表現(xiàn)出民間智慧特有的靈活與變通,他們有意識地通過對歷史的“改寫”和“敘事”,重建中斷的歷史的連續(xù)性,并使民間文化得以再生和復興。
“5·12”汶川地震之后,隨著羌族文化遺產(chǎn)搶救和保護的升溫,汶川和北川兩地爭報羌區(qū)大禹傳說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并非偶然。從歷史上看,“禹興于西羌”在《史記》與其它漢代文獻中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蜀地知識分子“在邊緣人群的認同危機感之下”,藉著說“古華夏圣人大禹出生在本地”,以強調(diào)本地的非邊陲地位,表達對華夏文明的認同心態(tài)。[15](P8)此后,逐漸由知識分子的言說層面進入和積淀在民間信仰與族群心理層面,廣泛地表現(xiàn)在羌族的史詩、民間傳說、戲劇表演以及名勝古跡當中,成為一種不斷強化的社會記憶。這種社會記憶在當下現(xiàn)實中因其承載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所具有的資源價值而被重新挖掘和建構(gòu),以服務(wù)于旅游開發(fā)的需要。因此,從歷史敘事的視角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歷史時期,社會記憶是如何被不同的族群用來進行“我族”與“他族”的劃分,發(fā)揮建構(gòu)歷史事實與文化身份的功能,并影響社會現(xiàn)實的動態(tài)過程。
由此可見,歷史存在的真正理由并不在于它為某些古老的事物賦予了永恒。歷史是人們理解其在這個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某種方式。[12](P327)
三、作為生活哲學的文化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在全球化語境下應(yīng)對民間文化的危機而借用的外來概念,因而,需要一個本土化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又是與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相同步的。在此背景下,我們面臨著如何進行文化定位,并“從價值層面上維持和組織好我們的生活世界,使其成為一個整體”[16](P5)的問題。
在此,傳統(tǒng)再一次成為文化反思的出發(fā)點。所謂的傳統(tǒng)并不等于歷史,傳統(tǒng)是文化。傳統(tǒng)并不在我們的過去,更應(yīng)該在我們的未來。相應(yīng)地,傳承人“不是作為歷史的見證者,而是作為文化的承載者”,[17](P306)攜帶著“文化不可化約的特性”。[17](P308)將傳統(tǒng)由昨天的歷史帶入當下的生活,正是文化由自發(fā)到自覺的過程。文化并不只是自發(fā)的對傳統(tǒng)的傳承延續(xù),它還是應(yīng)對變遷、應(yīng)對現(xiàn)實的自覺創(chuàng)造與發(fā)明。我們不如將文化理解為“一種生活哲學”,理解為“一種對世界的挑戰(zhàn)作出反應(yīng)的無窮無盡的寶藏”,[18]從而在非遺的活態(tài)傳承中進一步去理解并發(fā)現(xiàn)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無限生機和活力。
1.文化生態(tài)的土壤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實際上是一種生活文化或者說文化的生活,這種生活是精神性的,文化性的,但它是一種生活,一種跟老百姓生活吃喝拉撒婚喪嫁娶融契在一起不可分離的生活,有感情的生活。民間文化渾然一體的形態(tài)特點,需要我們在進行非遺傳承研究時要注意返回生活世界,在整體關(guān)聯(lián)中予以把握。如果用非遺項目化思維和分類體系來肢解民間文化,勢必損害其鮮活的生命。
湖北呂家河民歌村的人們在地里干活時要打“薅草鑼鼓”,放牛娃在山野互相逗樂唱“仗歌”,舉辦紅白喜事時更要唱歌,辦婚事唱喜歌“鬧房”,辦喪事唱陰歌“鬧夜”,逢年過節(jié)時要唱歌“鬧年”,建新房要唱歌“暖房”。而這一帶從明代集聚幾十萬民工興建武當山道教宮觀起,就有著南北方民歌的豐厚積淀,加上武當山作為道教圣地長期營造的文化氛圍,于是唱民歌的風氣就融進民眾日常生活而構(gòu)成地方特色了。因此,民間文化生態(tài)的構(gòu)成有兩項基本特征:第一,它是圍繞某項民間文化活動,由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各個方面構(gòu)成的互動體系。不論何種民間文藝樣式,它都不可能脫離相關(guān)的社會人文條件而孤立存活。第二,它以活態(tài)呈現(xiàn),楔入民眾日常生產(chǎn)生活中間,發(fā)揮著自己的特殊功能。其運動變化既是自發(fā)的,又有著一種內(nèi)在動力使它世代傳承不息,具有持續(xù)穩(wěn)固的生命力。[19]
我們在做傳承人口述史時,需要把傳承人及其傳承的非遺事象背后的文化生態(tài)盡可能全面而生動地挖掘和還原出來。對此,馮驥才有一個形象的比喻——“把一棵花從地上挖起來,如果讓它活著的話,必須帶著它的原土,越大越多越好。因此它(普查)必須是一個全方位的立體的調(diào)查,區(qū)別于以往學者做的個人化的民藝調(diào)查。”[20](P117)
這種文化普查的理念在中國民協(xié)2005年編寫的《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調(diào)查·認定·命名工作手冊》中得到很好的體現(xiàn),其中明示了傳承人口述采訪應(yīng)包括如下幾項主要內(nèi)容:(1)傳承人人文自然背景:傳承人所在地區(qū)行政區(qū)劃及其相關(guān)建制;傳承人所在地區(qū)地理環(huán)境、生態(tài)環(huán)境、民族構(gòu)成情況、歷史發(fā)展沿革;傳承人所在地區(qū)和社區(qū)(村寨等)文化整體狀況概述。(2)家族史及傳承人成長歷程。(3)杰出技藝內(nèi)容與其文化內(nèi)涵:主要代表作品介紹;傳承技藝特征及其描述;傳承活動時間和場所的說明;技藝、工藝、表演、說唱、演示活動全過程的逐個環(huán)節(jié)(包括其功能、意義)的詳細描述;傳承技藝使用的工具、道具、樂器、服裝等的說明;傳承人技藝的民俗功能、民俗內(nèi)容、民俗意義等。(4)杰出技藝傳承方式及過程:拜師、授徒、出師、祭祖師的過程描述;傳承人師傳譜系圖;與傳承技藝相關(guān)的傳說、故事、歌謠、口訣、諺語的記錄;技藝活動的班/會、行會、組織等情況及傳承人在其中的角色。(5)杰出技藝的傳播:技藝表演、展示過程描述;技藝產(chǎn)品銷售情況;傳承人目前生存狀況及傳承狀況,由技藝獲得的榮譽及收益情況。 這里只是列出了主要的采訪內(nèi)容,還需要根據(jù)不同的非遺事象進行有針對性的提綱設(shè)計,但是已經(jīng)能反映出文化視域的整體觀照。
日常生活世界是滋養(yǎng)非遺傳承人的深厚土壤,一方水土的地域文化,傳承人背后的父老鄉(xiāng)親,百態(tài)叢生的民間藝術(shù),與生產(chǎn)生活實踐密切相關(guān)的民俗等等,都構(gòu)成了不可分割的民間文化生態(tài)。
2.變遷中的文化述行
隨著全球化、現(xiàn)代化、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民間文化場域內(nèi)發(fā)生了巨大的變遷,一方面是曾經(jīng)超越世代存續(xù)的傳承母體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存在,如村落的拆除并村,城市社區(qū)的拆遷改造;另一方面是傳承人身份的改變,有的棄農(nóng)經(jīng)商,有的進城打工,有的到旅游景點表演。因而,有必要將原本相對封閉靜態(tài)的文化傳承納入到開放動態(tài)的過程中,關(guān)注以往“很少被注意到的表演、參與、經(jīng)歷、相互作用、妥協(xié)、交換”等過程,以“文化的述行性”(即研究重心在于對過程、行為、表達方式的關(guān)注)[28]為視角,來考察文化傳承的活力所在。[20](P119)
事實上,這種活力恰恰體現(xiàn)在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上,它能夠不斷地把“他者”包容進來,不斷地讓“他者”來挑戰(zhàn)自己,從而在同“異”和“變”的纏斗中不斷地把“同”和“不變”闡釋或生產(chǎn)出來。由此,打破了傳統(tǒng)文化傳承中相對靜態(tài)封閉的狀態(tài),通過他者文化的引入,使自身文化得以相對化和客觀化,而文化的自覺意識正是在此過程中生成。傳承人在傳承母體之外接觸到異文化,或者異文化從外部傳播進入到傳承母體中,都會使得傳承人在兩種或多種文化的比較中形成判斷與評價,從而有意識地對本族群進行文化定位與文化構(gòu)想。
天津津南區(qū)葛沽鎮(zhèn)的寶輦花會雖然與天津皇會同源于對天后的崇信,但二者之間卻存在著諸多差異,追溯其成因與演變,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民間智慧是如何應(yīng)對文化變遷,借鑒他者文化,進行自我調(diào)適并建構(gòu)“地方性知識”的。
歷史上,葛沽鎮(zhèn)輦會格局的形成最早緣于明代萬歷年間,當?shù)馗簧逃窈裉脧埣以谝淮纬龃ジ=ǖ耐局杏龊ky而得救,故從福建媽祖廟分靈天后娘娘泥塑一座,回來后供奉于自家佛龕中。后隨香客的增加,張家又出資興建東茶棚,將天后娘娘從家中請出供眾多信徒燒香膜拜,由是衍生了沿街抬娘娘的習俗,并依照官轎,將乘載娘娘的八仙桌、佛龕加以整合,創(chuàng)建了第一代鳳輦。此后到民國時期,東茶棚天后娘娘祭禮文化被晚出的其它茶棚爭相模仿和復制,他們在吸收和融合既有的文化模式的過程中,依托地方鄉(xiāng)紳富甲的財力與權(quán)力,也在創(chuàng)造著各自的信仰體系,于是形成了現(xiàn)今葛沽花會八輦二亭的局面。
現(xiàn)實中,經(jīng)歷了文革慘遭破壞的葛沽寶輦花會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恢復,最初在當?shù)卣桶傩盏呐ο拢亟说谝患茌偅耖g私塑娘娘神像,后被官方作為迷信活動下令禁止。可村民們頂著壓力,自發(fā)集資,在熱衷于地方文化人士的帶領(lǐng)下,重建了剩余的七架輦和兩架亭。在隨后的寶輦花會表演中,酬神的要素被弱化,體現(xiàn)出更多民間文藝表演的成份。然而,復建后的花會沒有可依附的廟宇,由于娘娘信仰在國家政策規(guī)范中缺乏正當性,于是,花會協(xié)會提出了以建造媽祖廟來代替娘娘廟的方案并付諸實施。一方面因為天津市內(nèi)有始建于元代的天后宮(媽祖廟),媽祖經(jīng)過歷代的晉封列入國家祀典,并在九十年代恢復皇會等民俗表演活動;另一方面,在過去葛沽鎮(zhèn)的娘娘廟中也供奉有天后娘娘(媽祖),而且祭祀天后娘娘的模式是葛沽寶輦花會體系形成的契機。
由此,民間通過對內(nèi)部有效因素的最大化操作來掩蓋被官方認為“迷信”的部分,以此達到與外部條件相一致,來取得國家的認同。從娘娘廟到天后宮,是傳統(tǒng)社會與現(xiàn)代社會相互碰撞成形的產(chǎn)物。這就是現(xiàn)今葛沽寶輦花會表演儀式中呈現(xiàn)出的八尊娘娘與信仰載體(天后宮)不相一致的原因,也正是這種差異使雙方達成默契,地方政府規(guī)避了政策、法規(guī)層面的風險,村民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心理上與精神上的訴求,從而得以“會”與“廟”共存。通過這種變通方式,求得地方傳統(tǒng)文化的生存和發(fā)展。
當傳統(tǒng)生活步入當代社會中時,非遺熱潮中的民間文化不可避免地會遭遇來自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宰制和市場經(jīng)濟的沖擊,難脫被“異化”或“涵化”的命運。然而,文化作為一種生活哲學,自身就包含了解決危機與延續(xù)傳統(tǒng)的應(yīng)對能力。因而,經(jīng)常是“文化在我們探詢?nèi)绾稳ダ斫馑鼤r隨之消失,接著又會以我們從未想象過的方式重現(xiàn)出來了。”[21]文化就在民間,希望也在民間。
注釋:
①此處參考了中國民協(xié)編寫的《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調(diào)查·認定·命名工作手冊》(內(nèi)部資料)P57-59,局部做了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