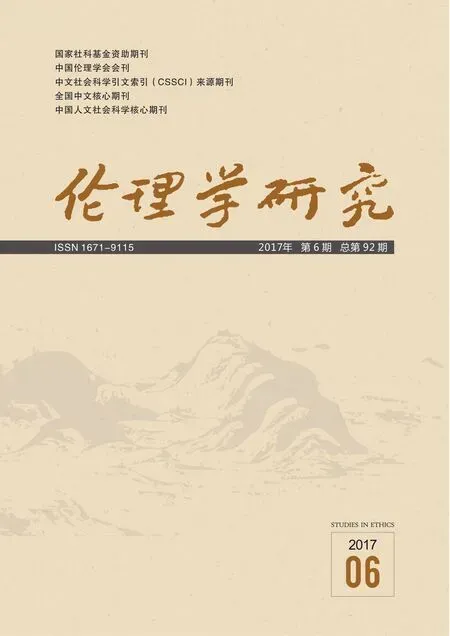斯多亞倫理學(xué)受到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的影響嗎?
——從二者對(幸福)的界定來看
田書峰
斯多亞倫理學(xué)受到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的影響嗎?
田書峰
斯多亞倫理學(xué)是否受到了亞里士多德或漫步學(xué)派倫理學(xué)的影響?這是一個直到今天都仍具有爭議的問題。爭議的焦點主要表現(xiàn)在朗(A.A.Long)與桑德巴赫(F.H.Sandbach)所持的對立的觀點上,朗認(rèn)為斯多亞倫理學(xué)是對隱含在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內(nèi)部未解的矛盾和張力的一種回應(yīng)和解決的嘗試;而桑德巴赫則認(rèn)為斯多亞倫理學(xué)并沒有受到亞里士多德或漫步學(xué)派倫理學(xué)的影響,而二者的術(shù)語重合不能作為有力證據(jù),因為柏拉圖哲學(xué)也同樣使用過相同術(shù)語。本文意在借助斯多亞學(xué)派的創(chuàng)立者芝諾對幸福和德性的看法而重新審視這個難題,通過比較和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朗和桑德巴赫的觀點并非完全對立,因為朗所列舉的斯多亞倫理學(xué)與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相重合或?qū)?yīng)的三個方面并不能完全窮盡二者的關(guān)系,而桑德巴赫在缺乏對具體的斯多亞主義者的倫理思想探析的前提下對上述三個方面進(jìn)行反駁的依據(jù)本身也不能作為充足的理由。事實上,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的影響可以通過芝諾對德性與幸福的關(guān)系的分析可見一斑。
倫理學(xué);幸福;德性;斯多亞;亞里士多德
一、引 言
毋庸置疑,斯多亞倫理學(xué)仍然是古希臘德性倫理學(xué)傳統(tǒng)的一種延續(xù),因為斯多亞主義者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一樣都是將幸福(εδαιμονα)作為人的所有行動的最后目的(λο,幸福是人生的終極目的,一切別的都是為了它才被做,而它不再是為了任何別的東西。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并不清楚斯多亞倫理學(xué)或幸福論與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究竟是怎樣的。只是將斯多亞幸福論看作是古希臘幸福論傳統(tǒng)的一種延續(xù)并不能解釋它是否是在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論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來的一種幸福論,如此它對于后者就有一種依賴性;抑或是它根本沒有受到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的影響,而是獨立地發(fā)展出自己的幸福論,也就是說斯多亞倫理學(xué)具有原創(chuàng)性或獨立性,將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沒有解決的內(nèi)部問題或矛盾進(jìn)行了清楚的闡釋,因此對后者并沒有依賴性。按照第一種觀點,斯多亞倫理學(xué)只是借用了很多亞里士多德或其漫步學(xué)派的倫理觀點,如果沒有后者的影響,斯多亞倫理學(xué)是無法被理解的,因此斯多亞倫理學(xué)對于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xué)有一種依賴性①。另外一些學(xué)者則堅持認(rèn)為斯多亞倫理學(xué)的陳述讓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xué)變得更加清晰易懂,并不是用一些生澀艱深的術(shù)語來詮釋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xué)②。也就是說,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xué)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我的觀點是,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是否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產(chǎn)生過影響這個問題只能從對斯多亞主義者的具體倫理思想分析中來看,尤其是從二者對于幸福和德性的觀點入手,通過對比更能把握二者的關(guān)系的真實脈絡(luò)。但是,如果想要弄清楚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是否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產(chǎn)生過不可替代的影響,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楚斯多亞主義者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接觸到了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因為按照一些學(xué)述史家(doxographer)的看法,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曾經(jīng)在地窖里被掩埋200年左右的時間,如此,斯多亞學(xué)派根本無法直接接觸到這些著作的。接下來,筆者試著主要從塞浦路斯的芝諾(Zenon:前336年-前264年)、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 103-前 43)、狄杜牧斯(Arius Didymus:公元前1世紀(jì)中葉)對于 εδαιμον α(幸福)的觀點來看他們與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xué)的關(guān)系。
二、亞里士多德著作的歷史失傳問題
那些支持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對斯多亞學(xué)派并沒有產(chǎn)生什么影響的學(xué)者通常訴諸亞里士多德著作的失傳論證來為自己的立場進(jìn)行辯護(hù)。眾所周知,亞里士多德的作品歷史上通常分為兩種,一種是為學(xué)園內(nèi)部的秘傳作品(esoteric),另一種是為公眾而寫的外傳作品(exoteric),這些外傳作品大部分是一些對話,但是,這些作品全部失傳;只有所謂的秘傳作品流傳下來③。這也就是我們今日看到的亞里士多德全集(Corpus Aristotelicum)。但是,如果我們想到亞里士多德的這些內(nèi)部的學(xué)園作品在歷史中的流傳曾經(jīng)有過將近200年的失傳,那么,緊接著我們就可以提出一個疑難,那些斯多亞學(xué)主義者又是通過什么方式來了解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思想的呢?斯特拉波(Strabo,64/63 BC–c.?24 AD),普魯塔克(Plutarch,c.AD 46–AD 120)與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200-250)都曾經(jīng)記載過特奧弗拉斯特(Theophrastus:前371-前287年)死后亞里士多德的圖書館的命運和所藏書籍的去向。根據(jù)拉爾修的記載,特奧弗拉斯特在去世時并沒有將亞里士多德和他的藏書及手稿交給學(xué)園的繼承者斯特拉托(Strato of Lampsacus,335–c.269 BC),而是交給了他的同事斯凱珀西斯的涅琉斯(Neleus of Scepsis),他便把這些藏書和手稿帶到了自己的家鄉(xiāng)-斯凱珀西斯。他的后人為了躲避當(dāng)時皇家對擴(kuò)建帕加馬圖書館(Pergamon Library)而發(fā)動的收繳私人藏書運動,就把這些書籍儲藏在一個地窖中,直到公元前1世紀(jì)初才被特奧斯的阿佩里孔(Appelicon of Teos)從涅琉斯的后人手中買下了亞里士多德和特奧弗拉斯特的藏書和手稿④,這些藏書后來又被羅馬的蘇拉將軍當(dāng)作戰(zhàn)利品的一部分從雅典帶回羅馬,而蘇拉將軍的圖書館管理員泰讓尼奧(Tyrannio)將這些藏書匆忙加以整理,很快就公之于眾,流傳開來。后來,羅德島的安德羅尼科斯(Andronicus of Rhodes)又重新對這些作品進(jìn)行整理編撰,這就是我們今日看到的Corpus Aristotelicum(亞里士多德全集)⑤。從斯特拉波的描述來看,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從特奧弗拉斯特在公元前287年過世一直到蘇拉將軍在公元前86年將這些著作重新公之于眾的200年間,漫步學(xué)派內(nèi)部除了亞里士多德的一些對外的公眾作品外就沒有什么內(nèi)部的學(xué)園秘傳作品可讀。對于這個觀點,很多學(xué)者提出了反駁意見,他們認(rèn)為,盡管我們承認(rèn)這個地窖的故事是真實的,并且涅琉斯帶著亞里士多德的大部分學(xué)園秘傳作品而離開了雅典,但這并不足以證明亞里士多德的這些著作在伊壁鳩魯學(xué)派和斯多亞學(xué)派初立伊始時并不被人所知。一個理由就是,如果我們相信安德羅尼科斯編輯的版本只有一個資料來源,那就是阿佩里孔買下的被蟲蛀而受損的并在錯漏百出的情況下就被出版的版本(Edition A1),那么,安德羅尼科斯的版本(Edition A2)又有什么優(yōu)越之處和權(quán)威之處呢?因為,如果安德羅尼科斯沒有其他的版本來源與阿佩里孔的版本進(jìn)行核對的話,那么,他的版本至多也只能算是依據(jù)受損的不完整的Edition A1而進(jìn)行的個人遐想或明顯書寫錯誤的糾正而已,也就是Edition A2與Edition A1沒有什么太大的區(qū)別。所以一個可能性就是,漫步學(xué)派內(nèi)部不可能對亞里士多德的每個著作只有一個手抄本⑥。尼爾森(Nielsen)認(rèn)為,亞里士多德的學(xué)友羅德島的歐德慕斯(Eudemus of Rhodes)在亞里士多德死后帶著很多不少的學(xué)園作品離開雅典返回羅德島。歐德慕斯不僅向特奧弗拉斯特就《物理學(xué)》第五卷中的一段正確讀法討教過,而且他還藏有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xué)》,并編輯了《歐德謨倫理學(xué)》(Eudemian Ethics)。另外,羅德島在公元接下來的幾個世紀(jì)曾是亞里士多德哲學(xué)研習(xí)的重鎮(zhèn)之一,從這幾點來看,亞里士多德的學(xué)園作品不可能在特奧弗拉斯特死后便在雅典銷聲匿跡了,斯特拉波和普魯塔克的記載不足以能證明亞里士多德著作或至少是倫理著作失傳200年的說法⑦。
事實上,在斯多白烏斯(Stobaeus:生活公元5世紀(jì))編撰的有關(guān)古典哲學(xué)流派概略或綱要《物理學(xué)與倫理學(xué)摘錄》(Eclogae)第II卷第116-152節(jié)中,我們可以找到這樣一個有關(guān)亞里士多德和其他漫步學(xué)派的倫理學(xué)的概覽(summary),這個總覽的作者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紀(jì)中期的一位名叫狄杜牧斯(Arius Didymus:生活于公元前1世紀(jì))的斯多亞主義者。他更多地用斯多亞學(xué)派的倫理語言來描述亞里士多德或漫步學(xué)派的倫理思想。我們?nèi)绾谓忉尩叶拍了沟倪@種作法呢?對這一現(xiàn)象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解釋:要么狄杜牧斯對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xué)并不十分了解,而只是隨意地選用了斯多亞學(xué)派慣用的語詞來解釋漫步學(xué)派的倫理學(xué)(mindless eclecticism);要么他其實對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諳熟于心,只是為了適應(yīng)當(dāng)時更為流行的哲學(xué)語詞來描述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xué)而已⑧。問題是,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xué)在公元前1世紀(jì)左右已經(jīng)熟被人知了么?根據(jù)歷史記載,最早的有關(guān)《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nicomachean ethics)的引用是在西塞羅的《論善惡的目的》(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的第五卷第12章中,背景是討論漫步學(xué)派對于至善(supreme good)的觀點。西塞羅對于《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的引用說明斯多亞學(xué)派對于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早有了解,他認(rèn)為斯多亞學(xué)派只不過是用自己的術(shù)語重新解釋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xué),給他披上一層新的衣服而已,基本觀點是一致的,沖突只是在于論證方式。西塞羅的這種調(diào)和論主要來源于一位叫做安提奧胡斯(Antiochus of Ascalon:前125-前68年)的柏拉圖學(xué)園派主義者。他反對中期柏拉圖學(xué)園的創(chuàng)立者阿爾則西勞斯(Arcesilaus:前315-前240年)的懷疑論立場⑨,而認(rèn)為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與斯多亞倫理學(xué)在有關(guān)幸福與德性的關(guān)系問題上并沒有嚴(yán)格的分歧。他認(rèn)為特奧弗拉斯特作為亞里士多德漫步學(xué)園的第一任繼承者雖然反對幸福完全在智者的能力掌控之下,強調(diào)外在的厄運或好運可以毀壞或提升幸福,但是這并不表示,斯多亞學(xué)派倫理學(xué)就與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完全相悖。相反,西塞羅與安提奧胡斯在公元前79年同時在雅典留學(xué),西塞羅將他視為“統(tǒng)一派或調(diào)和派”(unitarianism)的代表。無論如何,西塞羅和狄蒂姆斯的敘述證實了斯多亞學(xué)派在其早期就對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xué)有所涉獵和研究。
三、芝諾與亞里士多德論幸福
1.桑德巴赫(Sandbach)對朗(Long)的批判
那么,亞里士多德的這種幸福觀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產(chǎn)生過影響么?斯多亞主義的幸福觀是源自上述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觀么?按照桑德巴赫(F.H.Sandbach)與安東尼(Kenny Anthony)的看法,任何嘗試證明亞里士多德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的想法都是個人的憑空想象,并且注定會失敗。與之相反的是,朗(A.A.Long)在“亞里士多德對斯多亞學(xué)派的遺產(chǎn)”一文中列舉了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至少在下述三個方面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產(chǎn)生過深遠(yuǎn)影響?。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產(chǎn)生影響的第一個方面是有關(guān)外在的善事物與德性以及幸福之間的關(guān)系。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幸福雖然不能與外在的善等同(比如,財富、出身優(yōu)越、名聲或榮譽等),而是幸福更在于人的內(nèi)在德性,但是,人需要具有一些外在的善來完成某些德性行動(比如慷慨的行動需要具備一定的財富),具備外在的善可以成就更為完滿的幸福,完滿的幸福需要具有外在的善?。而斯多亞學(xué)派則認(rèn)為,外在的善根本不是真正的善,而是只有那些倫理上的善,即德性,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善。幸福與德性具有絕對性,幸福并不直接與外在的善相關(guān),而只是與使我們在外在的善事物中做出選擇的德性相關(guān)。盡管外在的善對于某些德性來說提供了一個使其運作的條件,但是,擁有外在的善并不必然是德性的條件,因為在倫理之外并沒有什么善。那些自然的善對于一個志在度高尚的道德生活的人來說是無足輕重的,理由是,只有美德或德性才具有真正的價值。倫理選擇的善(the good of the ethical choice)之所以是善的是因為我們的倫理選擇是符合理性的,它的價值是源自于建基在神性的存在秩序(divine order of the being)之上的善?。朗(A.A.Long)認(rèn)為,在有關(guān)外在的善與幸福的關(guān)系問題,斯多亞倫理學(xué)提供了一個超越了亞里士多德的解決方案。但是,桑德巴赫(Sandbach)強調(diào)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并沒有產(chǎn)生什么影響,因為早在亞里士多德之前,就有很多關(guān)于什么才是構(gòu)成幸福生活的主要因素的討論?。而且色諾克拉底(Xenocrates,前396-前314)就認(rèn)為,幸福生活雖然主要取決于德性,但是如若沒有外在的善,人也很難達(dá)到完滿的幸福。所以,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中有關(guān)幸福的觀點是對前人的觀點的改進(jìn),而斯多亞倫理學(xué)則開始于一個完全不同的論點,即唯有德性才與幸福相關(guān),而外在的善并不會增加或減少幸福。根據(jù)朗(Long)的看法,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產(chǎn)生影響的第二個方面是有關(guān)什么是德性行動的條件以及一個人如何成為具有德性的。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看法,一個符合德性的行動必須滿足如下三個條件:(1)知道自己所做的;(2)選擇這個行動,且為了行動自身的原因而選擇;(3)出于一種堅固而不會改變的習(xí)性。Long認(rèn)為,斯多亞倫理學(xué)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上述三個條件。Sandbach對上述三個方面逐一進(jìn)行分析后認(rèn)為,斯多亞倫理學(xué)對于這三個條件的理解并不與亞里士多德的相一致。首先芝諾認(rèn)為,擁有(明知性)就是擁有 φρóνησι(實踐知識或?qū)嵺`智慧),而擁有φρóνησι就是擁有諸種德性。但是,這明顯不是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因為一個人具有語法的知識,就能夠進(jìn)行拼寫,但一個人知道如何慷慨,但并不等于他就一定具有慷慨的德性。而對于προαιρομενο(選擇)來說,單從其詞源學(xué)上(προ:在…之前,αιρομενο,決定,擇取)就能看出這是指在不同的可能性面前擇取自己想要的,即這是一種明辨后的行動,而不需要單獨而特別地從亞里士多德那里學(xué)到。而第三種德性習(xí)性的非變易性則更是源自柏拉圖,而非亞里士多德之獨創(chuàng)?。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產(chǎn)生影響的第三個方面是對快樂的看法。亞里士多德在EN X中將快樂定義為“使實現(xiàn)活動變?yōu)橥暾缘臇|西,不是作為一種內(nèi)在的倫理品性,而是作為一種隨附的目的來起作用的,就像美麗完善著青春年華”?。但是,桑德巴赫(Sandbach)認(rèn)為,斯多亞倫理學(xué)并未將快樂視為目的,而是達(dá)到了目的之后的結(jié)果。雖然二者具有某種相似性,但這并不表示斯多亞倫理學(xué)有關(guān)快樂的思想來源于亞里士多德的哲學(xué)。
桑德巴赫(Sandbach)雖然也接受朗(A.A.Long)提出的斯多亞倫理學(xué)在上述三個方面與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相吻合或相對應(yīng),但是桑德巴赫卻否認(rèn)這種吻合就證明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產(chǎn)生過實質(zhì)性的深遠(yuǎn)影響。桑德巴赫對朗的反駁主要是依據(jù)在二者之間的三種吻合早在亞里士多德之前就早已有過相關(guān)的討論,比如很多吻合的術(shù)語早在柏拉圖的對話中就出現(xiàn)過,或者早在亞里士多德之前就有過關(guān)于什么才是組成幸福的本質(zhì)性要素的討論(ENI 9.1098b23)。但是,只是通過一些與柏拉圖對話錄中的哲學(xué)術(shù)語之吻合是否就能充分地證明這些術(shù)語就是源自柏拉圖傳統(tǒng)?如果這種表面術(shù)語吻合所表達(dá)的概念在實際的問題框架中并不是一樣的,那么這種吻合也并不能作為一個充足的證據(jù)來證明這些術(shù)語背后的倫理學(xué)源自亞里士多德之前的柏拉圖傳統(tǒng)。
2.芝諾論幸福與德性
雖然桑德巴赫(Sanbach)對朗(Long)所主張的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產(chǎn)生影響的三個方面一一加以駁斥,但是,他的駁斥并非完全中肯適宜,我的觀點是,雖然我們并不具有直接的文本證據(jù)來證明斯多亞倫理學(xué)與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早期的確實產(chǎn)生過一定的影響,而且只是依靠一些漫步學(xué)派倫理學(xué)與斯多亞倫理學(xué)之間的術(shù)語重合或本質(zhì)性的命題對應(yīng)很難證明前者對后者的影響,但是,我們可以找到另外一種哲學(xué)傳統(tǒng)影響另一種的方式,即把早期斯多亞學(xué)派的某些倫理觀點視作是對漫步學(xué)派倫理學(xué)內(nèi)部所包含的一些未解問題或張力的回應(yīng)?。這隱含在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中的張力就是有關(guān)幸福作為自足而完整的至善與外在的和身體的善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和對于德性行動與幸福的本質(zhì)性理解方面。在EN I 7.1097b20-21,幸福被界定為“完善而自足的,因為它是人們在實踐活動中可以達(dá)到的最后目的。”幸福是完滿的,因為人所選擇的一切都是為了幸福這個最后目的,而幸福自身不再為任何其他目的。它又是自足的,因為它足以使整個生活變得有價值?。這種張力就表現(xiàn)在亞里士多德試圖保全如下兩種觀點:一方面他認(rèn)為德性才是幸福的主要組成因素;另一方面又強調(diào)外在的不幸會損毀幸福,或缺乏外在的善會減少幸福(EN 1099b2-5),而擁有外在的或身體的善會增加幸福。芝諾否定任何外在的或身體的善是真正的善,而只有倫理上的善或德性才是真正的善,芝諾試圖通過確立德性的不可取代的地位來解決這個兩難問題。如果亞里士多德或漫步學(xué)派倫理學(xué)仍然在德性的至高地位與外在的和身體的善之間有所徘徊不定,那么芝諾就是斬釘截鐵地“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即外在的善(財富、名譽、權(quán)利、朋友等)并不是真正意義上幸福的本質(zhì)性組成部分,它們只是具有某種價值的東西,而只有德性才是構(gòu)成幸福的本質(zhì)性要素。顯然,芝諾對幸福的這種解讀是最小化的解讀(見注釋20),但是,問題是,斯多亞倫理學(xué)如何來解釋這種絕對而突兀的主張?如果我們理解了芝諾對人的幸福和德性的本質(zhì)定義,也許這種最小化的解讀就不會顯得那么突兀,那么決絕或不近乎人情了。
雖然根據(jù)拉爾修的記載,芝諾曾經(jīng)寫過很多著作,但是,不幸的是,無一作品被保留下來。我們只能通過拉爾修,西塞羅等人的記載而重構(gòu)他的倫理思想。芝諾將幸福界定為“符合自然地生活”?,并按此原則而將人的行為或行動分為符合自然的適宜行動和德性的完美行動。按照芝諾的看法,那些符合自然的事物值得人們欲求或選擇,相反那些不符合自然的東西就應(yīng)該被舍棄。如果一個人能夠按照符合自然的原則而對事物進(jìn)行選擇或舍棄的時候,他也就具有了能夠進(jìn)行符合自然的適宜行動了,但是,這仍然還沒有達(dá)到德性的完美行動,因為符合德性的完美行動需要行動者具備幾個條件:為了正確的理性、出于不可變易的習(xí)性、向著一個固定的自為目的,就像一個有智慧的人計劃他的生活一樣。一個有智慧的人的行動并不是因為他們這樣做可以獲得一定的外在的善而值得稱道,而是因為這些行動本身就是具有德性的,是自為的目的。所以一個符合自然的適宜行動在外表上與德性的完美行動并沒有什么不同,但是,前者在本質(zhì)上并不能與后者等同,因為后者需要滿足上述三個條件,這三個條件正好與亞里士多德在EN II 4.1105a31-35所列舉的三個條件吻合。而朗(Long)也注意到,斯多亞學(xué)派在符合自然的適宜行動與德性的完美行動之間所做出的區(qū)分與亞里士多德在與德性行動相合的行動(acts in accord with the virtues)與源自德性的行動(acts that flow from the virtues)之間的區(qū)分相對應(yīng)?,朗就將這種對應(yīng)理解為早期斯多亞倫理學(xué)對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的回應(yīng)。盡管桑德巴赫反對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產(chǎn)生過真正意義上的影響,但是朗始終堅持早期斯多亞倫理學(xué)不可能在對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完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進(jìn)行的。桑德巴赫的觀點主要是基于亞里士多德哲學(xué)尤其倫理學(xué)在希臘化時期并不被人所知,而有關(guān)亞里士多德全集在地窖被掩埋幾乎200年的文本流傳故事則更加幫助桑德巴赫取消這最后的斯多亞倫理學(xué)與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的聯(lián)系。
四、結(jié) 語
對于亞里士多德或漫步學(xué)派倫理學(xué)是對斯多亞倫理學(xué)產(chǎn)生過深遠(yuǎn)的影響這個問題,桑德巴赫和朗的觀點代表了兩種截然相對的立場,前者基于亞里士多德作品集的流傳斷裂和存在于亞里士多德之前的倫理學(xué)傳統(tǒng)而堅持認(rèn)為斯多亞倫理學(xué)并未受到過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的影響,盡管有些時候在二者之間存在著不同的術(shù)語吻合或者主題呼應(yīng)的現(xiàn)象;而后者則認(rèn)為這種術(shù)語吻合和主題呼應(yīng)的現(xiàn)象并不能通過比亞里士多德更早的倫理學(xué)傳統(tǒng)的存在而輕易地被否定,雖然我們并不具有任何直接的文本證據(jù)或歷史記錄來證明二者之間有過怎樣的聯(lián)系和碰撞,但是,至少可以通過一些核心的倫理命題而推論出斯多亞倫理學(xué)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內(nèi)部所蘊含著的未解矛盾的一種回應(yīng)或者解決的嘗試。本人通過具體分析芝諾對德性和幸福的觀點而發(fā)現(xiàn)朗和桑德巴赫的觀點并非完全對立,因為朗所列舉的斯多亞倫理學(xué)與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相重合或?qū)?yīng)的三個方面并不能完全窮盡二者的關(guān)系,而桑德巴赫在缺乏對具體的斯多亞主義者的倫理思想探析的前提下對上述三個方面進(jìn)行反駁的依據(jù)本身也不能作為充足的理由。實際上,芝諾在一定程度上發(fā)現(xiàn)了隱含在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內(nèi)部的問題或張力,并嘗試回應(yīng)或解決。這個問題或張力就是德性和外在的善對幸福的作用或意義,如果說,因為亞里士多德在保全德性對于幸福的主導(dǎo)地位的同時又想保全外在的或身體的善會增加或破壞幸福而不得不陷入一種模棱兩可的處境,那么芝諾通過否定外在的善根本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或目的論意義上的善解決了這種模棱兩可,因為真正的善只限于倫理上的善,即德性。但是,這并不否認(rèn)外在的善具有一定的工具價值,外在的或身體的善始終是為終極價值——幸福服務(wù)的,而構(gòu)成幸福的本質(zhì)性或建構(gòu)性要素只能是德性。
[注 釋]
① Long,A.A.(1968),“Aristotle’s Legacy to Stoic Ethics”,in:Boulletin of the Insititute of Classical Study,15,pp. 75-85. See also:Long,A.A.,Stoic Studies,Oxford Univ.Press 1996.
②Irwin,T.(1999),“Virtue,Praise and Success:Stoic Response to Aristotle”,Monist I,59-79.Sandbach,F(xiàn). H.,Aristotle and the Stoics,Cambridge Univ.Press 1985.
③4See:Bobonich,Chris,Aristotle’s Ethical Treatises,in:The Blackwell Guide to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ed. by Richard Kraut,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p.12-29.
④阿佩里孔是一位富商,后成為希臘公民,是公元前1世紀(jì)有名的圖書收藏家,他主要搜集那些稀少的重要的圖書。
⑤斯特拉波在自己的《地理學(xué)》中這樣寫道:“涅琉斯不僅聽亞里士多德和特奧弗拉斯特的課,而且還繼承了特奧弗拉斯特的圖書館,其中也包括亞里士多德的圖書館,因為亞里士多德不僅將自己的圖書館,也將自己的學(xué)園托付給了特奧弗拉斯特(亞里士多德是我們所認(rèn)識的第一位收集書籍的人,他還教埃及國王如何組建圖書館),特奧弗拉斯特將圖書館交給了涅琉斯,他將這些書帶到了斯凱普西斯(Scepsis),并傳給自己的繼承者。因為他們并不是哲學(xué)家,只是隨便堆放起來,沒有好好管理。當(dāng)他們聽說統(tǒng)治該城的阿塔里克國王正在為建立帕加馬圖書館而急切地四處尋找書籍,他們就將圖書藏到地窖里,這些圖書就被地窖的潮濕和蛀蟲所損毀,后來,涅琉斯家人就將這些圖書高價賣給了特奧斯的阿佩里孔。但是,阿佩里孔更是一個圖書愛好者,而不是智慧愛好者。因此,他試圖制造新的抄本以修復(fù)那些受損的書籍,但是,他還沒有填補缺漏,就出版了錯誤百出的版本。如此,那些特奧弗拉斯特之后的早期漫步學(xué)派除了少數(shù)公開作品之外,并沒有什么文本可讀,因此不能真正地從事哲學(xué),只是泛泛而談一些普遍性的東西。相反,自從那些書籍出現(xiàn)之后,他們的繼承者算得上更好的哲學(xué)家和亞里士多德主義者;但由于手抄本中錯漏百出,所以顯得大部分在似是而非地談?wù)撜軐W(xué)。羅馬對此貢獻(xiàn)很多。因為阿佩里孔一死,攻陷雅典的蘇拉就立即將他的藏書運往羅馬。文法家泰讓尼奧(Tyrannio)——一位熱愛亞里士多德的人,通過討好圖書館長而有機(jī)會接觸到這批書籍。一些書商雇用了糟糕的抄寫員,他們并沒有校對抄本,在羅馬和亞歷山大里亞類似的事情也發(fā)生在其他那些為了出售而被抄寫的書籍上。”參:溥林:亞里士多德《范疇篇》箋釋,以晚期希臘評注為線索,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09年。第24-30頁。斯特拉波:《地理學(xué)》(Geographica),第13卷第1章第54節(jié)。
另外,普魯塔克也記載了同樣的故事:“蘇拉(Sulla)將軍將藏有亞里士多德與特奧弗拉斯特的大部分作品的特奧斯的阿佩里孔(Appelicon of Teos)的圖書館據(jù)為己有。圖書館的藏書被運到羅馬后,泰讓尼奧(Tyrannio)著手整理這些藏書,而羅德島的安德若尼庫斯(Andronicus of Rhodes)從他那里獲得了手稿,并公之于眾,他制作的亞里士多德作品目錄也流行起來。漫步學(xué)派的長者都是卓有成就的學(xué)問家,但是,他們所發(fā)現(xiàn)的亞里士多德與特奧夫拉斯特的作品既不是在數(shù)量上那么多,也沒有被正確地抄寫下來,因為內(nèi)琉斯的所有藏書都被轉(zhuǎn)交給了那些平庸無奇的人,他們并不是哲學(xué)家(普魯塔克,《平行傳記》中的《蘇拉傳》第26節(jié)。Sulla 26)”。同樣,拉爾修也記載了特奧弗拉斯特的遺囑:“我把全部書卷遺贈給涅琉斯。我把花園,散步長廊以及連接花園的房屋全都遺贈給我下面提及的這些朋友,只要他們愿意總在那里共同研究文學(xué)和哲學(xué),既然不可能所有人老是住在一起。當(dāng)然,任何人都不得轉(zhuǎn)讓這些財產(chǎn)和據(jù)為己有,而只是方便使用,就像公共廟宇一樣,并親密友好地住在一起,只要恰當(dāng)公正就行。”見:第歐根尼·拉爾修:《名哲言行錄》(希漢對照本),徐開來、溥林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第463頁。
⑥Nielsen,Karen Margreth,The Nicomachean Ethics in Hellenistic Philosophy,in:The Reception of Aristotle’s Ethics,ed. By Jon Miller,Cambridge 2012.pp.15-18.
⑦Nielsen(2012),pp.17.
⑧ See:Annas,J.,“The Hellenistic Version of Aristotle’s Ethics,”Monist,I,pp.80-97.1990.
⑨根據(jù)萊爾修(Diogenes La?rtius)的分法,柏拉圖學(xué)園總共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以柏拉圖為首的早期學(xué)園(387BC-266BC):柏拉圖離世后由斯彪西(Speusippus,347–339 BC)接管,然后是塞諾克拉特斯(Xenocrates,339–314 BC)接著是珀來莫( Polemo,314–269 BC)和克拉特斯(Crates,c.269–266 BC)。(2)以阿爾采西勞斯(Arcesilaus)為首的中期柏拉圖學(xué)園(266BC-160BC);(3) 以呂西德斯(Lacydes) 為首的第三時期(160BC-84BC)。
⑩亞里士多德用了四個有名的論證來證明最好的或最完美的生活就是靈魂的符合理智德性—智慧的沉思生活,這四個論證是:標(biāo)準(zhǔn)論證(Criteria-argument,EN X 7.1177a19-b26);本有論證 (oikeion-argument,X 7.1178a4-8);神性論證(argument from divinity,X 8.1178b7-32);與神具有最大的友誼論證(theophilestatos argument X 9.1179a22-32)。這四個論證足以證明沉思智慧的生活才是最完美的首要幸福(primary Eudaimonia)。
?對于次好的幸福也有兩種解讀,排他性的解讀認(rèn)為政治的德性生活只是在一種引申的(derivative sense)意義上是幸福,因為它缺乏沉思;而包容性的解讀則認(rèn)為政治的德性生活在其自身也具有幸福特性,只不過是在一種比沉思較弱的意義上來說。
? Long,A.A.,“Aristotle’s Legacy to Stoic Ethics”,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y,15,pp.72-85.
? EN X 9.1178b33-1179a33;EN I 9,1099a31-1099b8.
?EN I 9.1098b23. 見:Sandbach,F(xiàn).H.,Aristotle and the Stoics,Cambriadge 1985.pp.24-31.
?《理想國》444c;503c;537c.
?EN X 4.1174b31.
? 參 :Irwin,T.,“Virtue,Praise and Success:Stoic Response to Aristotle,”Monist,I,pp.59-79.
?對于這種幸福的界定可以有不同的解讀:(1)最大化解讀:幸福不需要任何其他額外的善,因為它已經(jīng)包含了外在的善(比如財富、朋友、社會地位)、身體的善(健康、力量)和靈魂的善(德性)。(2)最小化解讀:幸福與非倫理的善(外在的善和身體的善)并沒有什么直接相關(guān)性,真正的善僅僅限于德性。(3)有限性解讀:亞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只要我們具備了一定的外在和身體的善,我們就可以過一種自足的完善的幸福生活,任何其他的善并不會增加幸福。因為幸福并不在于擁有這些善,而是在于以適宜的方式或德性的方式尋找并利用這些善。參:Nielsen(2012),pp.21f.
? 拉 爾 修 (2010 年),VII 87;Cicero,On Moral Ends,trans. R. Woolf,commentary J. Anna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Long (1968),pp.77.
田書峰,北京師范大學(xué)哲學(xué)學(xué)院教師。
北京師范大學(xué)青年教師基金項目(SKXJS2015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