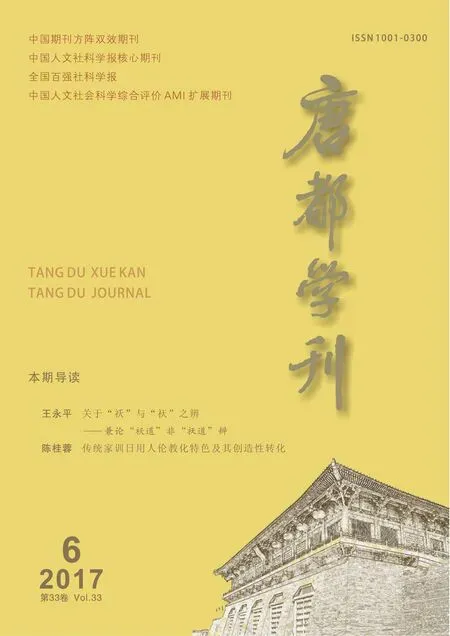政治關系親屬化才是“和親”的真正內涵與實質
劉興成
(云南大學 歷史與檔案學院,昆明 650091;貴州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貴陽 550025)
【歷史文化研究】
政治關系親屬化才是“和親”的真正內涵與實質
劉興成
(云南大學 歷史與檔案學院,昆明 650091;貴州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貴陽 550025)
國內外學界都將我國古代的“和親”政策理解為政治聯姻,從而形成了“和親”即政治聯姻的傳統“和親”觀念。然而,這一觀念卻與歷史事實并不相符。從文獻記載來看,在我國古代雖然有不少“和親”事件確實包含有不同民族或政權之間聯姻的內容,具有政治聯姻的性質,但同時也有不少沒有包含不同民族或政權之間聯姻內容,而與政治聯姻完全無關的歷史事件也被稱為“和親”。也就是說,在我國古代既有政治聯姻型“和親”,也有非政治聯姻型“和親”。顯然,“和親”即政治聯姻這一論斷無法涵蓋我國歷史上所有“和親”史實。因此,政治聯姻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和親”的真正內涵與實質。在我國古代絕大部分“和親”都有一共同現象,即在“和親”過程中,當事雙方都要確立某種或某幾種親屬或親屬化關系,將雙方政治關系親屬化、親情化。“和親”的核心內容是當事雙方在“和親”過程中所確立的親屬或親屬化關系以及以此為基礎而確立的相應的責任與義務。由此可見,政治關系親屬化、親情化才是“和親”的真正內涵與實質。
和親;政治聯姻型和親;非政治聯姻型和親;政治關系親屬化;和親的實質
長期以來,學界研究者都將我國古代民族“和親”理解為政治聯姻,從而形成了“和親”即政治聯姻的傳統“和親”觀念。然而,從文獻記載來看,在我國古代,雖然有很多“和親”事件確實包含有不同民族或政權之間聯姻內容,具有政治聯姻的性質,但同時也有不少沒有包含不同民族或政權之間聯姻內容,而與政治聯姻完全無關的歷史事件也被稱為“和親”,也就是說,在我國古代既有政治聯姻型“和親”,也有非政治聯姻型“和親”。顯然,傳統的“和親”觀無法涵蓋我國歷史上所有“和親”史實,也就是說政治聯姻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和親”政策的真正內涵與實質。既然如此,那么“和親”政策的真正內涵與實質究竟是什么呢?本文將就這一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一、“和親”即政治聯姻未能涵蓋所有“和親”史實
1929年王桐齡在《漢唐之和親政策》中明確將“和親”政策解釋為政治聯姻,他說:“和親政策者,漢族皇帝以本國公主嫁與外國君主,與之講求婚媾之謂。”[1]此后,這一論斷不斷得到修正與補充,如崔明德說:“‘和親’是兩個不同的民族政權或同一民族的兩個不同政權的首領之間,出于‘為我所用’的目的所進行的聯姻。”[2]510他將“和親”政策適用對象由漢族皇帝與外國君主,擴大到“兩個不同的民族政權或同一民族的兩個不同政權的首領之間”,于是,“和親”即政治聯姻的論斷顯得更加合理與完善,并逐漸形成了“和親”即政治聯姻的“和親”觀念。目前,我國學界幾乎所有相關研究都以這一“和親”觀為前提。這種“和親”觀不僅深深影響了我國史學工作者,而且就連海外漢學家也都深受其影響,如《劍橋中國秦漢史》就將漢代“和親”政策稱為“婚姻協議制度”[3]415。顯然,“‘和親’即政治聯姻”已經成了中外研究者共同信守的“和親”觀念。
然而,事實上“和親”即政治聯姻這一論斷無法涵蓋歷史上所有“和親”史實。因為,從文獻記載來看,在我國古代雖然有不少“和親”事件確實包含有不同民族或政權之間聯姻內容,具有政治聯姻的性質,但同時也有不少沒有包含不同民族或政權之間聯姻內容,而與政治聯姻完全無關的歷史事件,也被稱為“和親”。也就是說,在我國古代既有政治聯姻型“和親”,也有非政治聯姻型“和親”。
政治聯姻型“和親”,在我國歷史上有很多,而且大家都很熟悉,比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親”等,無需細說。非政治聯姻型“和親”,在我國歷史上,實際上也很多,可以說是歷代皆有,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卻一直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眾所周知,東漢、宋、明等朝代始終未與周邊民族或政權政治聯姻,故以往研究者大多根據“和親”即政治聯姻這一“和親”觀念斷言或相信這些朝代無“和親”。然而事實上,不管是東漢,還是宋、明都曾與周邊民族或政權建立過“和親”關系。只不過這些朝代的“和親”沒有包含不同民族或政權之間聯姻內容,而與政治聯姻完全無關,是非政治聯姻型“和親”。對此,拙文《東漢、宋、明三代無“和親”說質疑》[4]已有詳細論述,茲不贅述。
其實,在我國古代,不僅東漢、宋、明等朝代的“和親”是非政治聯姻型“和親”,而且就連漢、唐等朝代的很多“和親”也同樣是非政治聯姻型“和親”,如唐與東突厥的多次“和親”即屬此類。眾所周知,在唐與東突厥十多年的交往過程中,二者之間雖然多次討論政治聯姻,但始終沒有實現政治聯姻。因此,學界有些研究者根據“和親”即政治聯姻這一論斷,推斷或相信唐與東突厥之間沒有“和親”*關于這一問題,拙文《試論判定政治聯姻的標準問題——以唐與突厥“和親”研究為例》(《中國邊疆學》第四輯)、《論唐與突厥“和親”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未刊)均有論述。。然而事實上,唐與東突厥之間曾多次“和親”。據《資治通鑒》等文獻記載,早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淵就采納劉文靜與東突厥“和親”的建議,并親自寫信給東突厥始畢可汗,說:“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可汗得到信當即表示:“茍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5]5737-5738。從這段記載來看,李淵為了得到東突厥的支持,承諾“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而且還提出東突厥可以“與我俱南”,也可以“但和親,坐受寶貨”兩種建議。從始畢可汗回信內容以及后來東突厥派兵隨李淵進軍關中的歷史事實來看,東突厥顯然同意了李淵的“和親”請求。雖然當時唐朝尚未正式建立,但這仍可看作唐與東突厥的第一次“和親”。
此后,唐與東突厥又多次“和親”。如武德元年(618)九月,唐高祖派襄武王李琛“與太常卿鄭元赍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6]2347又武德五年八月東突厥寇廉州,陷大震關,唐高祖“遣鄭元詣頡利……元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擄掠所得,皆入國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如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5]5955這里的“復”字,說明在此之前唐與東突厥之間曾有過“和親”。而“頡利悅,引兵還”一語也說明,東突厥可汗采納了鄭元的建議,恢復了與唐王朝的“和親”。又武德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頡利)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5]5992-5993又武德九年,“頡利可汗入涇陽,靖率兵倍道趨豳州,邀賊歸路,既而與虜和親而罷。”[6]2478從相關記載來看,唐與東突厥的這次“和親”實際上就是指便橋會盟。在相關文獻中,類似記載還很多,限于篇幅,不便一一列舉。
從上文所列舉的材料來看,唐與東突厥之間確實有過多次“和親”,但是,由于這些“和親”事件都沒有聯姻的內容,不具有政治聯姻的性質,是非政治聯姻型“和親”,所以研究者;依據“和親”即政治聯姻的傳統“和親”觀,將其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從而得出了唐與東突厥沒有“和親”的結論。
當然,也有個別研究者將唐高祖遣使“赍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理解為政治聯姻*如崔明德、龔蔭等人在其相關論著中都將此次“和親”理解為政治聯姻。,這是值得商榷的。所謂政治聯姻,一般指不同政治實體通過個別成員(一般是核心領導者或其家庭成員)的婚姻而結成的政治聯盟。政治聯姻的核心內容是不同政治實體通過婚姻關系而確立的姻親名分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因此,并非凡有女性參與的外交事件都是政治聯姻,只有既有女性參與,又確實確立了相應的姻親名分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相應的責任與義務的外交事件才是真正的政治聯姻,否則,即便有再多的女性參與,也不是政治聯姻。唐高祖送“女妓”于東突厥可汗,雙方并未確立相應的姻親名分,更沒有確立以姻親名分為基礎的責任與義務,所以,這次“和親”雖有女性參與,但是并不是政治聯姻。其實,所謂“女妓”就是舞女、歌女之類。我國古代社會是典型的男權社會,在人們的觀念中,女人是男人的財產或附屬物,男人有權將其作為特殊的禮物贈送他人。唐高祖送“女妓”于突厥可汗就屬于這種情況,這最多可算美人計或性賄賂,與政治聯姻性質完全不同。
可見,在我國古代雖然有不少“和親”事件確實包含有不同民族或政權之間聯姻內容,具有政治聯姻的性質,但同時也有不少沒有包含不同民族或政權之間聯姻內容,而與政治聯姻完全無關的歷史事件也被稱為“和親”,也就是說,在我國古代既有政治聯姻型“和親”,也有非政治聯姻型“和親”。顯然,“和親”即政治聯姻這一論斷無法涵蓋我國歷史上所有“和親”史實,它只能涵蓋政治聯姻型“和親”,而無法涵蓋非政治聯姻性“和親”。因此,政治聯姻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和親”的真正內涵與實質。也正因此,長期以來,學界研究者在研究“和親”問題時,往往只考察前者,而將后者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
二、“和親”一詞的含義
既然“和親”政策的真正內涵和實質不是政治聯姻,那是什么呢?
目前,學界一般都認為“和親”政策始于西漢初年,但“和親”一詞卻并非漢高祖或劉敬所創,它至少在春秋戰國時期即已存在,而且被廣泛運用于包含民族或國家關系在內的幾乎所有社會關系之中。因此,要想弄清楚“和親”政策的真正內涵和實質,首先要對先秦時期“和親”一詞的用法和含義做全面考察。下面根據不同使用對象,將先秦時期“和親”一詞的含義和用法分為以下幾個層次:
1.父子兄弟“和親”
《禮記》在論述音樂的社會功能時說:“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7]140從語法來看,“和敬”“和順”“和親”結構一致,“敬”“順”“親”都對“和”起補充與限定作用,分別與“和”構成補充式合成詞;從內容來看,君臣有別,長幼有序,父子兄弟有情,“敬”與“順”分別是君臣尊卑、長幼秩序之體現,而“親”則是父子兄弟親情之流露。“和敬”“和順”“和親”三個詞,雖然本質上都是“和”的意思,但因對象不同,“和”的方式或內容亦有所不同,君臣之“和”需要“敬”,即在臣子對君主的畢恭畢敬的基礎上實現君臣之“和”,長幼之“和”需要“順”,即在晚輩對長輩的絕對順從的基礎上實現長幼之“和”,而父子兄弟之“和”則需要“親”,這個“親”字則表示具有血緣關系的親人之間的天然親情,也就是說,父子兄弟之“和”需要以天然的血緣親情為基礎和底色。顯然,這里的“和親”具有以血緣親屬關系為基礎的親情底色,特指父子兄弟等有血緣關系的親人之間和睦相處、相親相愛。
2.鄰里“和親”
《周禮·秋官司寇》在記載“比長”這一職官的職責時說:“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邪,則相及。”[8]82“比”是基層組織單位,相鄰五家為“比”,官長稱“比長”。這段話闡明了“比長”的職責,使“五家相受相和親”乃是比長職責之所在。所謂“五家相受相和親”實際上就是鄰里“和親”。《周禮注疏》注釋言:“云‘相和親’者,案《尚書》云:‘爾室不睦,爾唯和哉。’五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9]卷12,第20頁可見,在這里“和親”實際上就是“睦”“和”的意思,所謂鄰里“和親”,就是鄰里之間和睦相處。
3.萬民“和親”
《周禮》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兇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8]243又《大戴禮記·禮察》*《大戴禮記》最后成書雖非在先秦,但其內容當有所本。漢初賈誼也有“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等語,這里還要考察《大戴禮記》的成書時間以及賈誼說此話的背景。云:“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10]410“萬民”與“民”皆為泛指。在前一材料中“和親”與“康樂”“安平”并列,意義雖有不同,但性質相近。“康樂”指物質豐富,幸福快樂;“安平”指社會安定,人們生活穩定;而“和親”則指人們相互之間和睦親近。而在后一材料中“和親”還與“怨”相對,這也說明“和親”實質上就是“和”的意思。可見,萬民“和親”就是泛指人們之間和睦相處而無怨恨。
4.君臣“和親”
《禮記·燕義》云:“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于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后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7]233“上”和“下”分別指君王和大臣,“上下和親”,指君臣“和親”。“上下和親”與“不相怨”行文表明“和親”與“怨”詞義相反。《禮記正義》云:“‘上下和親’,是和也。”[11]1936可見,君臣“和親”指君臣之間和睦相處而無怨恨。
5.家族或宗族“和親”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云:“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12]131。趙氏、欒氏、魏氏、中行氏以及韓、趙都是當時晉國極有影響的家族或宗族。《左傳》這一段話主要交代了當時這六大家族或宗族的相互關系,欒氏與魏氏“私”,韓氏與趙氏“睦”,中行氏與范氏“和親”,顯然,“和親”與“私”“睦”的意思相近。據杜預注釋,“私”為“私相親愛”,“睦”為“和睦”。[12]131由此可見,家族或宗族“和親”指家族或宗族之間的“私相親愛”與“和睦”。
6.諸侯“和親”
《子夏易傳》云:“故先王建萬國、和親諸侯,然后天下安也。”[13]17從語義來看,“先王建萬國、和親諸侯”與“天下安”具有因果關系,顯然,“和親諸侯”大概就是諸侯之間和睦相處而無征戰,否則不可能出現“天下安”的結果。又《越絕書》云:“當時無天子,強者為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眾道,范蠡善偽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于楚?”[14]128這段材料先談論了“時無天子,強者為右”的情況,然后又設想了與此相反的情形,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貢珍,屈膝請臣”。“時無天子,強者為右”,諸侯之間紛爭四起,而“諸侯和親,四夷樂德”,則天下太平。顯然,諸侯和親主要指諸侯之間和平相處而無征戰。由此可見,無論是和親諸侯還是諸侯和親,都主要指諸侯之間和睦相處而無征戰。
7.民族或國家“和親”
《周禮·秋官司寇》記載:“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8]248鄭玄認為蕃國之臣來眺聘者[9]21。賈公彥進一步解釋道:“蕃國之君世一見,其臣得有眺聘者,彼雖無聘使法,有國事來,小行人受其幣,聽其辭,以中國眺聘況之耳,其實無眺聘也。”[9]卷38,第21頁從鄭玄、賈公彥的解釋來看,《周禮》所記“象胥”這一官職的職責就是負責接待周邊民族或國家使臣,并將周王意旨傳達到這些民族或國家,而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和親”周邊民族或國家。顯然,這里的“和親”實際上就是與周邊民族或國家處理好關系,和睦相處。
以上即先秦時期“和親”一詞的使用情況及意義。“和親”一詞的這一含義,在秦漢至清末民國兩千多年中,一直沿用不息,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變化。如蘇東坡說:“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于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15]743梁啟超也說:“今我國所號稱識時俊杰,莫不艷羨乎彼諸國者。其群治之光華美滿也如彼,其人民之和親、康樂也如彼,其政府之安富尊榮也如彼。”[16]84此類材料不勝枚舉,限于篇幅,不便遍舉。
自先秦時期開始,我國古代社會就表現出比較濃厚的宗法化的特點。許倬云曾說:“西周分封,用親緣關系維持封建網絡,宗統與君統相疊,血緣與政治結合,這雙層結構,為中國文化傳統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7]12考慮到我國古代社會這一宗法化的特點,不難判斷,在上述七層意義中,第一層當為“和親”一詞的初始含義,其余各層皆由其引申、擴展而來,意為像父子兄弟等具有血緣關系的親人一樣和睦相處、相親相愛。顯然,在先秦時期“和親”一詞雖然總體上是“和”或“和睦”的意思,但又不是一般的“和”或“和睦”,除了“和”或“和睦”這一層意思之外,還有“親”,而“親”在這里是親人的“親”、親情的“親”,所以“和親”一詞具有親情色彩,表示親人或像親人一樣和睦相處、相親相愛之意。這顯然與政治聯姻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系。
三、政治關系親屬化才是“和親”政策的真正內涵與實質
既然“和親”一詞在先秦時期就已經被廣泛運用于包含民族或國家關系在內的幾乎所有社會關系之中,表示親人或像親人一樣和睦相處、相親相愛的意思,而與政治聯姻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系。所以,從理論上來講,自漢代以來“和親”政策的“和親”也應當是先秦“和親”一詞的繼承與沿用,其含義也應當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
從文獻記載來看,我國古代絕大部分“和親”事件都存在這樣一個共同的現象,即當事雙方要在“和親”過程中確立某種或某幾種親屬或親屬化關系,將政治關系親屬化、親情化。如西漢初年,漢與匈奴“和親”就是“約為兄弟”。據《漢書·匈奴傳》記載:“匈奴以漢將數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于是高祖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18]3754此后,漢與匈奴還曾多次“和親”。由于大家對這些“和親”史實都比較清楚,故無需一一詳述。
在目前學界,研究者一般都認為西漢初年漢匈“和親”是政治聯姻,其依據就是劉敬向漢高祖所進“和親”之策的主要內容就是嫁長公主于冒頓單于,而且此后“和親”,漢朝雖未嫁長公主,卻多次遣宗室女“為單于閼氏”。我們認為,劉敬建議嫁長公主以及在“和親”過程中漢朝多次遣宗室女“為單于閼氏”,都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但這并不說明漢匈“和親”的內涵與實質就是政治聯姻。
首先,根據政治聯姻的定義,政治聯姻關系的確立不僅要有女性參與,而且還要以婚姻為基礎確立相應的姻親名分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相應的責任與義務,而在漢與匈奴“和親”中,盡管漢朝多次送翁主“為單于閼氏”,但雙方始終都沒有確立相應的姻親名分,更未確立以姻親名分為基礎的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劉敬對漢高祖說:“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余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風喻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18]2122顯然,在劉敬的設想中,如果能夠嫁長公主,則不僅可以在漢與匈奴之間確立翁婿甚至外祖與外孫等姻親關系,而且還能夠確立一些以這些姻親關系為基礎的對匈奴有所約束的責任與義務。盡管劉敬在其政治聯姻政策構建中也提到了物質饋贈,但是這在他整個政策構想中只是起到輔助作用,而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以婚姻為基礎的姻親名分以及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因此,從劉敬建議的內容來看,嫁長公主于匈奴單于確實是政治聯姻。但是,在真實的歷史中,劉敬政治聯姻建議,由于呂后的堅決反對而未能實行,漢高祖不得已用家人子翁主冒充長公主嫁與匈奴單于。我們暫時不討論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使真能將長公主嫁于匈奴單于,漢匈雙方是否真能確立像劉敬所設想的那種姻親關系,但是用家人子翁主冒充長公主的欺騙行為肯定不可能達到政治聯姻的目的。對于這一點,劉敬當時也說得非常明白,他說:“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18]2122在漢與匈奴的多次“和親”中,漢朝都送過翁主,但從文獻記載來看,雙方之間始終都沒有確立相應的姻親名分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相應的責任與義務。顯然,從政治聯姻概念來看,將漢匈“和親”解釋為政治聯姻,與歷史事實并不符合。
其次,從文獻記載來看,漢匈“和親”過程中,雖然沒有確立姻親名分,但是雙方始終以兄弟相稱,確立兄弟關系。《漢書·劉敬傳》就明確記載劉敬奉漢高祖之命“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與匈奴“約為兄弟以和親”。從內容上來看,似乎比較矛盾。因為,既然“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那么漢匈之間就應該建立政治聯姻關系,但結果雙方卻“約為兄弟以和親”。我們知道,劉敬在向漢高祖建議“和親”時是希望嫁長公主于匈奴單于,并且明確指出不能用其他女子冒充長公主,而最后漢高祖在不能嫁長公主的情況下還是用家人子假冒長公主參與“和親”,這說明漢高祖確實希望與匈奴建立政治聯姻關系,但結果正如劉敬所料,匈奴識破了漢高祖“令宗室及后宮詐稱公主”之騙局,不愿意承認雙方是政治聯姻關系,所以,最后雙方只能“約為兄弟以和親”。因此,我們說文獻中“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的記載,實際上只是體現的是漢朝當時的愿望,至于翁主到了匈奴是否真能被立為“單于閼氏”,是否能夠得到“單于閼氏”名號,則是另外一回事情;而“約為兄弟以和親”才是當時雙方“和親”的真實內涵。從文獻記載來看,雙方這種兄弟關系還維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如漢文帝時期,匈奴單于在給漢文帝的信中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后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18]3756漢文帝在回信中也說:“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18]3758顯然,漢匈“和親”以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雙方一直維持著兄弟關系。
又如宋遼澶淵之盟也是兄弟“和親”。對于澶淵之盟,文獻記載中一般都用“議和”等詞,但也有不少時人及后世學者用“和親”,如司馬光在《涑水記聞》卷6稱:“虜兵既退,來求和親,詔劉仁范往議之,仁范以疾辭,乃命曹利用代之。”[19]115又同卷:“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修河北城隍,允則欲殿雄州城,乃置銀器五百兩于城北神祠中。”[19]107《三朝北盟會篇》記載許翰曾說:“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來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與虜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功效異者,何也?”[20]332此外,將澶淵之盟稱為“和親”的人還有很多,如李沆、王旦、陳亮等。顯然,在這些人的觀念中澶淵之盟也是“和親”。
其實,澶淵之盟不僅是“和親”,而且還與漢匈“和親”一樣,也是“約為兄弟以和親”。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嘉祐六年九月丙子司馬光上書說:“切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場日駭,乘輿暴露于澶淵,敵騎憑陵于齊、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為兄弟。”[21]4721嘉祐八年四月庚辰他又說:“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遭此大喪,立當訃告……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六年,生民樂業。”[21]4796顯然,澶淵之盟與漢匈“和親”一樣也是“約為兄弟以和親”。
在我國歷史上,這種“約為兄弟以和親”的例子還有很多,如唐與突厥“大唐初有天下,即與可汗結為兄弟”[6]2380,唐與回紇“自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5]7505,宋金“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22]11522-11523等等。對此拙文《中國古代“和親”類型新論》[23]《中國古代“和親”類型及其相關問題新論》[24]均有比較詳細的討論,故不贅述。
在我國古代,由于親屬關系劃分較細,種類很多,因此,通過確立親屬關系而實現的“和親”的種類相應的也很多。除了兄弟和親之外,還有父子(母子)和親、伯侄和親、叔侄和親,等等。由于姻親關系也是親屬關系的一種,因此,政治聯姻也是實現“和親”的有效途徑,是“和親”的典型類型。另外,在我國古代文化觀念中,一些非親屬關系的社會關系被固定親屬化為某種親屬關系,如君臣、師生、官民等關系固定親屬化為父子(或母子)關系,因此,這些社會關系也可被用來實現“和親”關系。或許是因為君臣關系符合我國古代“天無二日,人無二主”的政治邏輯,故君臣“和親”一直都是我國古代“和親”的主要類型,不論是中原王朝占優勢,還是周邊民族或政權占優勢,他們都熱衷于爭取確立這種類型的“和親”。因此,我國古代“和親”,按照在“和親”過程中所確立的親屬或親屬化關系,可以劃分為兄弟和親、父子(母子)和親、伯侄和親、叔侄和親、政治聯姻和親、君臣和親等多種類型。其中政治聯姻和親還可以細分為翁婿和親、甥舅和親等。對此拙文《中國古代“和親”類型新論》《中國古代“和親”類型及其相關問題新論》均有論述。
四、結論
在我國古代雖然有不少“和親”事件確實包含有不同民族或政權之間聯姻內容,具有政治聯姻的性質,但同時也有不少沒有包含不同民族或政權之間聯姻內容,而與政治聯姻完全無關的歷史事件也被稱為“和親”,也就是說,在我國古代既有政治聯姻型“和親”,也有非政治聯姻型“和親”。顯然,傳統的“和親”觀無法涵蓋歷史上所有的“和親”史實,也就是說政治聯姻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和親”政策的真實內涵與實質。事實上,絕大部分“和親”都存在這樣一個共同的特征,即當事雙方在“和親”過程中要確立某種或某幾種親屬或親屬化關系。因此,所謂“和親”政策就是不同政治實體之間通過建立某種或某幾種親屬或親屬化關系,將政治關系親屬化、親情化,“和親”政策的核心內容就是當事雙方所確立的親屬或親屬化關系以及以此為基礎而確立的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因此,“和親”的真正內涵與實質是政治關系親屬化、親情化。
[1] 王桐齡.漢唐之和親政策[J].史學年報,1929(1):9-14.
[2] 崔明德.中國古代和親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4] 劉興成.東漢、宋、明三代無“和親”說質疑[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4):162-168.
[5] 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
[6] 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7] 鄭玄注.禮記[M].四部備要本.
[8] 鄭玄注.周禮[M].四部備要本.
[9]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M].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
[10] 戴德撰,盧辯注.大戴禮記[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四庫全書》本,第128冊.
[11]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12] 左丘明撰,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四庫全書》本.
[13] 卜子夏.子夏易傳[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四庫全書》本,第007冊.
[14] 袁康.越絕書[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四庫全書》本,第463冊.
[15] 蘇軾.蘇東坡全集[M].北京:中國書店,1986.
[16] 梁啟超.新民說[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17] 許倬云.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18] 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9] 司馬光.涑水記聞[M].北京:中華書局,1989.
[20]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四庫全書》本,第350冊.
[21]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5.
[22] 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23] 劉興成.中國古代“和親”類型新論[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3(3):10-15.
[24] 劉興成.中國古代“和親”類型及其相關問題新論[J].西北民族論叢,第十輯:220-238.
[責任編輯朱偉東]
ConnotationandEssenceofPeace-makingMarriagePolicy:KinshipofPoliticalRelations
LIU Xing-cheng
(YunnanUniversity,SchoolofHistoryandArchives,Kunming650091,China;Guizhou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Guiyang550025,China)
The ancient Chinese peace-making marriage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political marriag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us formed the idea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eace-making marriage. However, this idea i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s. Based on the documentary records, some ancient peace-making marriages are connected with other nationalities and politics, others are absolutely not. In other words, there are political and non-political peace-making marriages in the ancient China. It is evident that the assumption of political peace-making marriages cannot cover all the facts of marriages. Therefore, political marriages are not and possibly cannot be the real connotation of peace-making marriage. In fact, most peace-making marriages have it in common that in the process of peace-making marriage, both sides have established certain or several kinds of relatives or kinships and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have followed. The main points of peace-making marriage include: the established relatives and kinships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Accordingly, kinship and family affection of political relations are the real connotations.
peace-making marriage; political peace-making marriage; non-political peace-making marriage; kinship of political relations; essence of peace-making marriage
K205
A
1001-0300(2017)06-0085-07
2017-05-27
劉興成,男,湖南桃源人,貴州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博士后,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民族史、經濟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