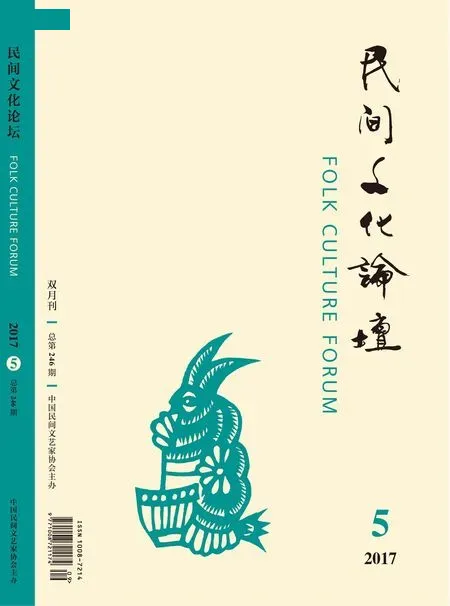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民俗的調適與發展*—以廣東佛山“行通濟”為例
陳恩維
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民俗的調適與發展*—以廣東佛山“行通濟”為例
陳恩維
近代以來,佛山社會經歷了從工商古鎮到現代化都市的變化,其“行通濟”民俗在此進程中由一種古老的社區民俗蛻變為現代都市民俗。其發生時間,因佛山城市化進程帶來的參與主體的變化而發生了微調;其儀式細節,因環境和文化觀念的變化而出現了諸如部分消亡、補償、適應、強化等諸多變化;其巡游路線,與佛山城市空間的擴展同步擴張,通過城市邊界確認構建新的城市記憶與地方認同。“行通濟”民俗的調適,是一種發展中的實踐,具有典型的樣本意義,當代民俗研究和保護應當予以正視和重視。
城鎮化;行通濟;調適
城鎮化(Urbanization,又譯成“城市化”)的過程,是世界各國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的社會變遷的一種反映。城鎮化是一個歷史范疇,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實踐。在此背景下,許多富有責任感的學者對城鎮化進程中包括傳統民俗在內的非遺的蛻變表達了充滿人文和人道情懷的“鄉愁”①岳永逸:《城鎮化的鄉愁》,《民間文化論壇》,2015年第2期,第11—14頁。,但是,僅有“情懷”和“鄉愁”,還是難以有效地解決現實的問題。有鑒于此,本文以廣東省佛山市的“行通濟”民俗為例,試圖通過對它較長歷史時段的一些富有意義的變化的描述,揭示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民俗的自我調適和發展,并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對民俗生活與當代社會生活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從而為當代民俗傳承發展提供鏡鑒。
“行通濟”,是廣東省佛山市一項傳統深厚、影響巨大的民俗。1936年2月9日《越華報》星期日特刊所載《猶言舊習“行通濟”,鄭擲肥鵝取兆頭》一文詳細介紹了其儀式:“每年正月十六日,佛山男女例有游‘行通濟’之舉。八日屆期,自晨至暮,迷信男女攜兒帶女過橋者甚眾,俱繞道于尾竇方面轉入廟前,再折返菜市返回橋頭。跋涉長途,不以為苦。蓋傳言不如此則是年命運必多阻滯也。附近鄉人為點綴圣地計,在橋尾一帶至行運社,及通濟橋亭菜市方面,擺賣生菜、筷子等物者,觸目皆是。且有擲鵝骰、雞蛋骰、三軍等玩意賭局,有蟠龍癡者如蟻附膻,侯六侯六之聲不絕于耳。又有手持香燭往橋頭南泉觀音廟膜拜者,或則領取圣水、或則爭扯燈帶,怪狀百百。而橋尾行運社葵棚所奉之金花、送生司馬等木偶,香火亦盛。其熱鬧情形,不亞于臨海廟云。”②《猶言舊習“行通濟”,鄭擲肥鵝取兆頭》,《越華報》,1936年2月9日星期日特刊。“行通濟”民俗原本是存在于佛山古鎮城鄉接合的一種社區性民俗,它來源于中原地區的“走百病”(過橋),在清代中葉完成了地方化定型,但是近代以來又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那么,這些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在當代的民俗研究和保護實踐中,我們應如何對待這一發展中的實踐?
一、社會生活轉型與 “行通濟”的時間變化
通濟橋為佛山古鎮的西南門戶。傳統“行通濟”的時間,是農歷正月十六日自晨至暮。這樣的時間安排,與佛山鎮和周邊四鄉群眾的日常生活相關。“這里四鄉民眾一般都是過了正月十五才出外工作,種田的正月十六開始耕作,出外找生活的也是過了正月十五以后才出去的。正月十六呢,大家就聚會在這里慶祝一下,慶祝完以后,就可以出去了。”①被訪談人:吳蝦。訪談人:陳恩維,黃曉敏。訪談時間:2012年2月26日。訪談地點:佛山市禪城區通濟橋畔。吳蝦(1937——)長期生活于佛山古鎮垂虹村,少年時曾在通濟橋頭的南濟觀音廟當過廟祝,也親自見證過通濟橋自1945年以來的數次重修。此外,佛山工、商業者有造祃祭慰勞員工習俗②區瑞芝:《佛山新語》,1992年內部印刷本,第292頁。,每月初二、十六兩天還會祭祀土地公,稱作“做迓”“迓福”(迎接福運之意)③[美]龔天民:《中國民間宗教信仰與基佛問題》,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2年,第17頁。。20世紀70年代末,佛山城區的上班族為了方便上班把“行通濟”時間從正月十六日白天提前到了正月十五晚上十一時。2002年以來,政府全面主導的“行通濟”巡游定在正月十五日,而大量涌入的城市移民將“行通濟”習俗當成了元宵習俗,于是形成了外來人正月十五日“行通濟”,本地人正月十六“行通濟”的現象。
其實,“行通濟”民俗與元宵節俗在時間上的混淆,也是事出有因。佛山地區傳統春節有“開燈”的習俗,時間從正月十一持續到正月十六日。所謂“開燈”,是指鄉民到祠堂或者寺廟掛燈,以酬謝祖先或者神靈。如頭年生兒子的家庭要開燈,稱為“開新丁燈”。建造或購買房子要“開新居燈”。娶新婦要開“乘龍燈”。還有一種叫“發財燈”,就是去年發了財或希望來年發財,都要從初二到初五這幾天中選定一天開燈。正月十五要請燈,因為“燈”和“丁”諧音,向廟里請燈,寓意添丁。因此,春節期間,佛山各廟掛了許多燈,各自編有吉祥名目,又分為幾種價錢。人們根據自己的愿望向司祝說明需要哪一盞,并用紅箋寫上“某宅敬請”字樣,稱為“請燈”。完燈的日子多在正月十六晚上,當晚用冥鏹等焚拜神明,以后不再點燈了,稱為完燈。元宵節后三天,司祝還邀請許多人拿著花燈,敲鑼打鼓挨戶分送,稱為“送燈”。到次年開燈時,受燈之家要買一盞同樣的花燈,連其定價、香油和鼓樂金等一起送到廟里,稱為“還燈”。④史仲文主編:《中國全史》百卷本第096卷《民國習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清人孫錫慧《佛山四時雜記》云:“燭花火萼綴瓊枝,一派笙歌徹夜遲。通濟橋邊燈市好,年年歡賞起頭時。”此詩反映的正是佛山“完燈”和“行通濟”民俗由于時間、地點的重疊而出現交叉混合的情景。“燭花火萼綴瓊枝”說的是元宵之夜人們用各色燈籠掛在樹上、裝點街道的情景。佛山人把正月十五元宵看作是一年的結束,而正月十六為一年的開始。所以,“年年歡賞起頭時”,是指正月十六“完燈”時人們在通濟橋頭賞燈,時間、地點都與正月十六“行通濟”混合。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十詳細記載了佛山元宵燈市的盛況以及人們在通濟橋、城門頭賞燈的情景:
上元開燈宴,普君墟為燈市。燈之名狀不一,其最多者曰茶燈,以極白紙為之,剔鏤玲瓏,光洩于外。生子者以酬各廟及社,兼獻茶果,因名茶燈。曰樹燈,伐樹之枝稠而杪平者為燈干,綴蓮花于枝頭,多至百余朵,燃之如繹樹瓊葩。曰八角燈,中作大蓮花,下綴花籃,八面環以瓔珞。曰魚燈,曰蝦燈,曰蟾蜍燈,曰香瓜燈,則象形為之。曰折燈,可折而藏者。曰傘燈,可持而行者。自元旦為始,他鄉皆來買燈,挈燈者魚貫于道。通濟橋邊,勝門溪畔,彌望率燈客矣。⑤(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十五《藝文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81、683頁。
《越華報》提到行通濟時橋尾行運社有葵棚,奉金花、送生司馬等神像,這里的“葵棚”,其實就是“捐燈棚”。由于上元燈節“張燈五夜”,造成正月十六日“行通濟”與正月十六的“完燈”“送燈”習俗相疊合。
至遲在民國期間,佛山正月十六日“行通濟”與正月十五元宵節(上元誕)的節俗也已經大致趨同了。1936年2月9日《越華報》星期日特刊所載《三官廟上元誕之熱鬧》一文記載:
佛山涌邊三官廟,七日為上元誕。禪市及附近各鄉往拜者絡繹不絕,廟內尤擁擠。取圣水、領燈籠、添香油、索寶燭費及簽筒之聲不絕于耳。而香煙彌漫,中人欲淚。司祝事先在廟前搭葵棚,張燈結彩唱八音,投機小販在此擺賣生菜、快子、紅雞蛋等物,婦女購者甚眾。賭徒亦在廟前及橋旁擺設擲鵝骰、三軍等賭博。是午燒丁財花炮,夜放煙花,并延僧道尼在橋畔葵棚內放三寶、水陸超幽,往觀者甚眾。①《越華報》,1936年2月9日星期日特刊。
佛山三官廟,距離通濟橋不過幾里路程;七日,指1936年2月7日,農歷即正月十五元宵節,又稱上元誕。這里記載的上元誕擺賣生菜、快(筷)子、取圣水、廟前及橋旁搭葵棚、擺設擲鵝骰、三軍等賭博等細節,與《越華報》同日所載“行通濟”舊俗的細節也基本一致。這說明上元誕與“行通濟”雖然在時間上相差一天,但節俗上已經區別不大。這種時間和節俗的混合在佛山古鎮周邊鄉村地區也很明顯。佛山順德龍山鄉“元夕張燈,燒起火,放花筒,笙歌歡飲。自初八、九以后,廟社開燈,人家亦然,恒以蔗酒享神,曰‘慶燈’,或設宴延客,曰‘燈酌’。凡前一歲生兒或娶婦之家,以姜酒、雞蛋往祭廟社,謂之‘燈頭’,亦有鳴鑼擊鼓,送燈與人,以為生男之兆者,至十五而止。十六日散燈,并迎灶神。是夕,婦女偷摘人家蔬菜,謂可宜男,名曰‘采青’。”②丁世良:《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801—802頁。這里所說的“采青”,其實就是“行通濟”中的一種變形。顯然,在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影響下,佛山地區元宵節俗和“行通濟”節俗逐漸融合。
20世紀30年代以來,佛山由傳統工商古鎮逐漸向現代城市轉變,“行通濟”逐漸由白天行走轉向白天夜間并行。20世紀30年代以前,佛山人“行通濟”一般不在夜晚走,因為通濟橋一帶原是河涌和山岡,沒有路燈,夜晚行走不夠安全,故而“行通濟”白天一早開始,到傍晚就結束了。但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佛山開始填埋河道,開辟馬路,逐漸由鄉鎮向城市發展。佛山第一條馬路——升平路在1930年通行,以后相繼建成中山路、福賢路、福寧路、慶寧路、市東路、普君路等。由于“大光燈”的應用,傍晚開始有人“行通濟”。吳蝦老人回憶幼時“行通濟”時的情景時說:“到了晚間,商販們點起大光燈(汽油燈)、大蠟燭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晝,吸引“行通濟”的人們購物娛樂。”③據采訪吳蝦老人所得。1956年以來,佛山的城市化進程加快,通濟橋一帶開辟了馬路,裝上了路燈,于是開始出現正月十六日夜間“行通濟”。大概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部分人把“行通濟”時間提前到正月十五晚上十一時(按傳統歷法,是十六的“子時”),但仍以正月十六白天“行通濟”為主。
20世紀80年代末,佛山發達的制造業吸引了大量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外來務工人員。外來人口不斷涌入,帶來了各地走百病的時間習慣,再加之一部分人把“行通濟”誤作“鬧元宵”,所以正月十五“行通濟”的人數越來越多。2007年以來,地方政府開始出面組織在元宵之夜“行通濟”大巡游。于是,從正月十五日下午六七點鐘開始,通濟橋上就已經開始形成人流,但在12時以前來的一般都是外來人員或者是從順德南海等較遠的地方來的。過去“行通濟”最熱鬧的時間是正月十六的上午10時到下午3時;現在最擁擠的時間是正月十五日晚7時至9時和晚12時前后。本地人、特別是中老年人仍然堅持正月十六日子時后才開始“行通濟”。于是,“行通濟”便出現了官方十五行、民間十六行,外地人十五夜行、本地人十六白天行的現象。
2002年以來,隨著參與主體的顯著變化,人們更強調國家與社會在人們生活中的影響與地位,對自然時間日漸淡漠,歲時節日逐漸成了社會性與政治性的時間表達。時任禪城區文廣新局局長張遠征認為:“我們把時間定在元宵節,是為了順應民意,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參加。正月十五,花前月下,許多年輕人都喜歡吃完晚飯出來散步,他們一直走到正月十六凌晨。正月十五晚12點左右達到人流的最高峰,算起來,也進入正月十六了,所以既順應民意,也能聚集更多的市民參與。”①楊怡、章利平、李紅:《佛山人挑燈漏夜“行通濟”》,《羊城晚報》,2006年2月13日。其實,這種變遷多帶來的糾結與沖突是毋庸諱言的。傳統“行通濟”選擇正月十六日進行,主要表現為人對自然和社會的時間順應,以及對神靈的祭祀。多數佛山本地人(特別是中老年人)認為正月十五“行通濟”“唔正宗”。有本地網友表示:“剛看了佛山年俗節,感覺很悲哀,這是佛山人的年俗節么?佛山人是正月十六“行通濟”的!”還有人表示:“我都系十六先‘行通濟’,有機會我都同人講以前是十六‘行通濟’,盡自己所能去留下一些傳統記憶。”不過,也有網友認為,“行通濟”時間已經不再重要,更重視的是參與。“難道十五去‘行通濟’的就沒有本地的?那些賣風車、賣生菜的大部分是本地人吧,‘行通濟’辦得越來越有影響力,不就是因為大家積極參與么?”②廖銀潔、龍樂樂:《正月十五“行通濟”唔正宗?》,《廣州日報》,2010年1月26日。“行通濟”的時間的變化以及帶來的沖突,看似發生的只是一個物理時間的置換,但實質是佛山城市化進程中參與主體的變化所帶來的社會生活轉型的反映。
二、環境變遷與“行通濟”民俗的細節變化
除了時間發生變化之外,“行通濟”民俗的儀式細節也隨著城市空間的變化和經濟社會轉型而變遷。其變化表現為儀式細節的消失、補償、適應和強化。
首先,一些儀式細節因環境的改變而消失。20世紀30年代,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導致佛山外河內涌日漸淤塞,河涌被大量掩埋,橋梁被拆毀。新中國成立后,佛山市政府對通濟橋進行了多次拆建。1958年改建為水泥混凝土單孔拱橋,拆去了牌樓和對聯,原有的紅砂石被用來修建位于中山公園秀麗湖的岸邊石。1964年又改建成公路橋。20世紀70年代通濟橋下河涌被填埋,橋干被徹底拆毀。1982年通濟橋被重建為鋼筋混凝土橋梁。③佛山市交通局編:《佛山市交通志》第二章《公路運輸?橋梁?通濟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8頁。1958-1982年期間,通濟橋的三次重建,通濟橋一直沒有被當作文物看待,通濟橋及其附屬設施構成的文化空間遭到徹底破壞,其形制、材質和規模均發生了徹底的改變。由于通濟橋及周邊環境提供的線索發生了改變,人們“行通濟”的民俗行為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1958年,南濟觀音廟和通運社的拆毀,以往行通濟中所出現的膜拜南濟觀音廟,領取圣水、爭扯燈帶以及橋尾行運社葵棚供奉金花、送生司馬等木偶的民俗現象,因失去了存在的空間和文化上的合法性而逐漸消失。“行通濟”中曾經熱鬧非凡的賭博現象也因遭受嚴厲打擊而銷聲匿跡。
其次,“行通濟”民俗的一些傳統儀式, 出現了替代性補償。比如,舊時“行通濟”的人們,喜歡站在橋上用銅錢擲向鎮橋的赑屃(螭龜),以求好運,這是一種常見“投物度厄”的民俗的儀式化表達,即通過砸“閉翳”來表達遠離不幸(閉翳)儀式。20世紀末以來,“行通濟”中一度出現過有人往橋下扔硬幣的現象,這其實是“行通濟”中民俗儀式以某種變通的方式被保留下來。 但是,由于丟硬幣引發了一些人到橋下水中撈取硬幣,且丟擲錢幣的行為被認為是浪費,所以在公安干警的勸阻和專家和媒體的批評引導下,此俗逐漸減少。但是,丟生菜作為一種替代性的民俗細節出現了。過去“行通濟”的生菜,是作為祭品敬奉觀音或社公的民俗物品,拜過觀音、社公后,生菜拿回家后一般用于敬神敬祖先,然后將其與其他配料煮成齋菜吃,是并不丟棄的。由于南濟觀音廟和通運社已被拆毀,再加之20世紀90年代以來佛山人家里供奉神位的人越來越少,很多年輕人或外地人不明白生菜的寓意和用途,過橋之時隨手將生菜拋在河中,大家相互效仿,扔生菜遂相沿成俗。市民朱先生回憶80年代的情景:“過橋的時候就往當時通濟橋下的河涌扔,不一會兒河面就飄滿了生菜,像條生菜河。”①麥鳳莊、劉海波:《那些年,我們一起行過的“通濟”》,《佛山日報》,2012年2月6日A04版。2001年通濟橋重建時,政府在通濟廣場修建了生菜池,池的中央豎起生菜雕塑,無意中成了“行通濟”的人們拋生菜的最佳場所。市民相信,把手中的生菜準確地扔到生菜池中的生菜雕塑上可以帶來一年的好運。近年來盡管政府和民俗專家一再呼吁“引財歸家”,提倡把生菜帶回家,但是這一現象仍然愈演愈烈,禁而不止,每年節后清理的生菜垃圾多達數十噸。丟生菜已經成了“行通濟”民俗的一大新景觀。個中原因,我認為主要有三點:一是因為“行通濟”本來就有以硬幣投擲鎮橋石龜的習俗,丟生菜其實是傳統儀式消失之后的替代性補償;二是“行通濟”與元宵出現時間混合后,“行通濟”其實承接了元宵節的狂歡功能。
第三,傳統民俗用品出現了適應性變化。早期“行通濟”時,人們因拜神需要,必備生菜、元寶以及蠟燭三件東西,被稱為行通濟“三寶”。其中生菜用于求子,元寶用于求財,蠟燭用于拜神。“祭祀物品作為一種消費中介,連接現實和過去,使人們在儀式過程中,深刻地體會到祖先和神靈的‘存在’,并極大地縮短了時間和空間,激活人的想象力。物品使祭祀場面更為隆重,物品的符號化意義使祭祀活動更具社會張力。”②蔣建國著,《廣州消費文化與社會變遷(1800-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7頁。舊的“通濟三寶”作為民俗祭祀物品,通過祭神活動而具有一定的文化意義。但是,由于破除四舊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市區禁燃鞭炮③20世紀80年代末, 全國各大城市因燃放煙花爆竹而造成財產損失和人身傷害的事件逐年上升。1988年春節后,反思之聲漸為高漲。當年,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即提出,要加強煙花爆竹的生產和燃放安全。北京市分別在1987年和1993年, 開始實施了煙花爆竹安全的有關管理方針和禁令。此后,一場“禁放”潮波及全國,包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在內的282個城市頒布了類似法令,禁放煙花爆竹。,元寶、蠟燭因失去用途而逐漸退出了民俗舞臺,舊“三寶”中僅有生菜得以保留。與此同時,“風車、風鈴、生菜”作為替代物應運而生。本來,在廣東的節日習俗中,風車是以“轉運”為意頭的節慶用品,象征著“時來運轉”或者是“一帆風順”。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行通濟”民俗中開始零星出現舉著風車出游的現象。大概從1993、1994年開始,有嗅覺靈敏的小販聞到了商機,開始販賣風車,方便人們“行通濟”時購買。市民在“行通濟”時手持風車,走在橋上,輪葉呼呼轉動,頓覺神清氣爽,心曠神怡,也填補了由于禁放鞭炮帶來的遺憾和郁悶。更重要的是,風車蘊涵轉運的寓意,也正好印證了傳統“行通濟”行大運的民俗信仰,于是“行通濟”買風車逐漸風靡起來,相沿成俗。后來,風車又相繼出現了小燈、風鈴等飾物,于是形成了“風車、風鈴、生菜”為新的“通濟三寶”的說法:風車象征時來運轉、風鈴象征迎來福音、生菜象征祈求生財。新的“通濟三寶”,既部分保留了傳統的民俗物品,又根據民俗的傳統內涵與時代發展衍生出了新的民俗物品,適應了時代的變化。
第四,一些符合當代需要的儀式細節得到了恢復和強化。2001年,佛山市政府斥資1700萬元重建通濟橋,同時整治美化周邊環境,擴充建成通濟廣場。①鄭力鵬、郭祥:《佛山通濟橋民俗景區再造設計》,《中國園林》,2002年第5期,第54—55頁。通濟橋的這一次修復,在已被掩埋的原有河涌上,營造水體,走向仿照原有河涌,與主軸線垂直,兩岸作水澳、水院、水榭、埠頭等,使通濟橋的傳統風貌得到了部分恢復。此次修復,不僅恢復了“通濟橋”的屬性,而且也喚起了民眾對水鄉和“橋”的記憶,避免了“過橋”習俗特性消失的可能,對于“行通濟”民俗橋俗性質的恢復和保護十分重要。尤其值得贊揚的是,在橋的形制方面,保留了通濟古橋原有特點:北坡 9 道防滑線,南坡13道防滑線。這就是所謂的“九出十三歸”。“九出十三歸”,原本是清代佛山當鋪的利率,即當票寫的足十元,先扣利息10%,實付給物主九元,利息則照十元計算。即實借九元,半年期滿,取贖時要還本息十一元八角。②佛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佛山史話》,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33頁。這種利率是佛山工商社會的一種金融保障,因此也是佛山經濟繁榮的一個象征符號,因而被佛山市民所廣泛接受。事實上,此前關于“行通濟”民俗介紹的文字資料中都沒有提及“九出十三歸”的細節,這次重修時“九出十三歸”的臺階設計,是根據通濟橋附近居民的口頭記憶而恢復的。顯然,這個傳統儀式細節的恢復或者強化,對于保護“行通濟”民俗的地方特色具有重要意義,有利于對其進行整體性保護。
“環境是通過向人們提供線索作用于人們的行為,并使人們理解一定的社會情境和社會脈絡。這種提供線索的方式可作為一種記憶方法,提醒人們采取其預期的行為。”③[美]阿摩斯?拉普卜特:《建成環境的意義——非言語表達方法》,黃蘭谷等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2年,第32頁。“行通濟”儀式細節的消失、補償、適應和強化,是因應城市化進程中空間的變化所致,是一種提醒人們采取預期行為的記憶方法,歸根到底則是由于社會轉型中人們文化觀念變遷的產物。傳統“行通濟”的文化內涵主要是求子、求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佛山的城市化進程以及生育觀念的變化,“行通濟”的求子功能不斷淡化,而求財功能日益突出,因而其相關儀式也發生了適應性變化。
三、城市記憶認同與“行通濟”的路線調整
據《越華報》所載,行通濟的傳統路線是“繞道于尾竇方面轉入廟前,再折返菜市返回橋頭。”④《猶言舊習“行通濟”,鄭擲肥鵝取兆頭》,《越華報》,1936年2月9日星期日特刊。隨著佛山城市建設的加快和人口不斷增多,“行通濟”的路線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余婉韶老人曾回憶50年代“行通濟”的路線:“以前‘行通濟’從普君圩、存院圍那邊上橋,過通濟橋牌坊,之后下橋,向左轉,兜一個圈,再上橋過橋,之后才算行完通濟的。兜一個圈,寓意行大運的意思。”①被訪談人:余婉韶。訪談人:陳恩維,黃曉敏。訪談時間:2012年2月16日。余婉韶(1936——),初中文化,長期在佛山文化戰線工作,曾任佛山市文化局社文科科長,佛山著名民俗專家。這一個人性的回憶,僅提及了存院圍、通濟橋兩個關鍵節點。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于橋亭鋪之南濟觀音廟、通運社等文化景觀相繼被拆毀,蜘蛛山淪為平地,存院圍尾竇等因為河涌的掩埋而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繼而又因開辟道路而被移除,“行通濟”作為城市記憶的一種儀式性、象征性表達,因城市景觀的變化也出現了變化。
20世紀80年代,“行通濟”路線增加了兩個新的節點——同濟路和同濟新村,這與同濟路的開辟以及佛山市第一批商品房——同濟新村的建設有關。據市民孫韋林說:“1982年同濟路開通,人們除了從金魚街匯集,還從同濟路匯集,一同走向通濟橋,一過橋后馬上就拐右,沿著河涌走,向同濟新村的方向疏散。”同濟路的開辟以及同濟新村的建設,使通濟橋右側的郊區村落開始形成現代化城市面貌。相比之下,通濟橋的左側一帶,“還很荒蕪,成片的菜地,魚塘和樹林,村居都很稀疏。”②麥風莊、劉海波:《那些年,我們一起行過的“通濟”》,《佛山日報》,2012年2月6日A04版。一個住宅區或商業區的建立,把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聚集在一起,逐漸結成新型的人際關系。這種新型關系,完全是由空間生產所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變化,突破了原有的血緣和地緣結構。另外,在空間進行大范圍生產以前,城市居民的身份通常比較單一,一般只有職業身份( 由單位決定) 和戶籍身份( 由行政屬性決定) 。但是,隨著空間生產范圍的增大,越來越多的居民成為房產所有者,從而變成了業主以及小區( 社區) 的物業公司的雇主。由此,在戶籍身份、工作身份、階級身份之外,他們的身份屬性中又添加了民間社會特征、個體產業特征以及市場經濟特征等。城市居民身份的復雜化和多元化,使人們迫切需要集體記憶來建構地方認同。同濟東路的開辟以及同濟新村的開辟,是佛山新型社區建立的開始,是佛山城市建設和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歷史事件,是佛山人自主擁有商品房的集體記憶的一部分。“行通濟”路線加入同濟路和同濟新村,實質上是以民俗儀式的形式對新的城市景觀和集體記憶加以確認,從而不斷強化地方認同,并具有見證城市發展歷史的意義。
20世紀90年代開始,交通部門開始介入“行通濟”的路線規劃,實行人流單向行進,路線逐漸走向規范。90年代初,基本形成了以佛山樂園為起點,經過普瀾路,再入大福路(現嶺南大道),最后過“通濟橋”的新路線。這一路線使“行通濟”的范圍較原來的路線擴大了數倍。其中,佛山樂園的納入,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件。佛山樂園創建于1984年,是佛山市金馬旅游集團與香港商人合作興辦,樂園集玩、食、娛于一體,成為80、90年代人們玩樂、鍛煉、憩息、休閑首選之地。網友“虎仔的主人”回憶說:“最中意過黎呢邊,睇睇海盜船、旋轉木馬同摩天輪,雖然五玩(不玩),但系睇住,就覺得好似玩緊甘。”網友Majicaby說:“佛山樂園系我細細個就有了,我外公年輕時工作的地方,是好多人的童年。”2000年以來,隨著時代改變和經營不善,佛山樂園逐漸失去了舊日的風采。網友Rigna Tam說:“變化好大好大的一個小公園。小時候這里有一個可以釣蝌蚪的大魚塘,后來被填平了。以前有小火車,2011年的時候被拆除了。園內的設施普遍幼稚,但是是佛山長大的80后的童年回憶。”①見佛山大眾點評網:http://www.dianping.com/shop/1581538。“個體重復回憶的一切過程與社會習俗化過程具有精確的相似性。”②[英]弗雷德里克?C?巴特萊特,李煒譯:《記憶:一個實驗的和社會的心理學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01頁。表面上,每個個體對于佛山樂園的記憶是帶有強烈的個人自我色彩,但是個體的記憶受到其所屬的社會群體的習俗、信仰、制度、思維模式等社會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響,這些社會因素會不斷被同化為個體內在的行為標準,并以一個完全習俗化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固定下來,從而成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佛山人關于佛山樂園的記憶,其實也是一種具有群體特征的集體文化記憶。佛山人“行通濟”以佛山樂園為起點,似乎是一個集體的無意識行為,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此慣性行為熟視無睹,但實際上人們在“行通濟”時,就會反過身來仔細審視其共同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這時人們就會發現,那些原來看似是集體無意識的東西恰恰是生長在骨子里的一種“集體有意識”。這樣看來,佛山樂園承載著佛山人的家庭情感和童年記憶,將其納入“行通濟”的路線范圍,也是對佛山人童年記憶和城市記憶的一種文化確認。
2002年,隨著通濟橋景區的重建,“行通濟”路線的調整完全由政府主導,對“行通濟”的文化記憶功能的確認由民間走向了官方。為滿足“行通濟”大量人流集散的需要,政府結合通濟橋的重修在通濟橋兩頭設置廣場,組織形成“行通濟”的主軸線上的如下空間序列:北面城市道路(金魚街)——北入口廣場——閘門樓(通濟門)——北引橋——通濟橋——南引橋——南廣場——生菜臺——城市道路(普瀾二路)。這一主軸線的設計,規范了“行通濟”的核心路線,大大增加了“行通濟”的方便,“行通濟”民俗越來越受到廣大市民的歡迎,參與人數劇增。為適應參與“行通濟”人數不斷增長的現實,2005年以來,“行通濟”的外圍路線進入了一個頻繁調整期。2005年,禪城區人民政府首次在媒體公布了“行通濟”的規定路線,采取了封閉路口的措施。③鄧德勛:《元宵節“行通濟”路線確定》,《珠江時報》,2005年1月11日。2006年路線的最大特點是,增加了“季華路”作為重要節點。季華路“誕生”于1993年,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開始發展,從2003年至2013年間,它利用10年的高速發展期,成長為禪城唯一一條東西貫穿城市核心的“主動脈”,迅速帶動禪西的產業升級和城市升級,引領禪城走向“強中心”。④楊漢坤、郭美歡:《季華路:見證佛山21年變遷》,《珠江時報》,2014年4月17日C02版。季華路進入“行通濟”的范圍,是對佛山城市空間不斷南拓的一種確認。2007年,南北走向的嶺南大道,被納入了“行通濟”的路線范圍。嶺南大道原名大福路,在改革開放前只是很短的一條小路。隨著城市的發展,原處于郊區的大福路逐漸成為禪城區的南北主干道,2006年擴建更名為“嶺南大道”,作為中心城區南北向交通動脈和重要景觀路,被佛山市政府和人民賦予中軸線功能,希望借此凝聚佛山精氣神。⑤李文波、安小慶等:《嶺南大道成為中軸線能否撐起佛山精氣神》,《南方都市報》,2012年2月15日。嶺南大道被納入“行通濟”路線節點,反映了人們對于“大佛山”的記憶與夢想。2010年11月開通的廣佛地鐵線,是中國第一條城際地鐵,承載著佛山人“廣佛同城”的夢想。廣佛地鐵的開通,大大方便了廣州和港澳地區以及珠三角等地群眾前來“行通濟”。2011年“行通濟”時,地鐵站也被納入“行通濟”指引范圍,廣佛線發車間隔時間已縮短至7分鐘一班車,以方便廣佛地區乘客“行通濟”時搭乘。⑥趙西東、鐘紅梅:《今年“行通濟”乘地鐵最方便》,《信息時報》,2011年2月16日。這無疑也增強了“行通濟”民俗的文化輻射力,“行通濟”參與人群來源不斷擴大,開始由佛山城市民俗一變而為廣府地區的標志性民俗。 2012年,“嶺南大道以東的另一條南北向的交通干道——文華路被納入了“行通濟”的范圍。文華路是聯系佛山市南海區和禪城區的南北向的交通干道,同時這條路上也串聯了李廣海醫館、佛山民間藝術社新址、忠義路、平政橋等人文景觀。文華路納入“行通濟”范圍,說明“行通濟”的參與人群已不局限于禪城區,業已成為佛山中心城區的最為重要的民俗活動,從而由社區民俗一躍成為佛山全市性的都市民俗。
2013、2014年“行通濟”路線基本按照2012年的范圍穩定下來。至此,佛山“行通濟”的路線經歷了向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兩輪擴張,其涉及的范圍不斷擴大,這與“行通濟”的人數不斷增多與疏散稀釋人流的安全考量有關,更與“行通濟”的文化認同功能不斷提升有關。“行通濟”民俗以路線調整的方式,把歷史事物、歷史事件、歷史傳統和習俗延續下來,儀式化地建構著佛山的城市記憶,并對佛山的現在和未來施加影響。2005年,少數專家出于做大“行通濟”的考慮,曾提出通濟橋遷址,徹底改變“行通濟”的路線。①《佛山學者大膽提出“行通濟”遷址東平河大橋辦嶺南文化“狂歡節”》,《佛山日報》,2005年4月21日。2010年,佛山市禪城區有關部門規劃在汾江河上修一條新通濟橋,將“行通濟”整體平移到汾江河畔。上述建議與規劃,遭到了絕大部分市民和民俗專家的反對。本地“天天新論壇”,對通濟橋遷址一事展開了討論,網友們對遷址事件強烈反對,甚至對提出建議的有關方面進行了情緒性的謾罵。②環保人生:行通濟前扯扯通濟橋遷址一事,http://bbs.ttx.cn/read-htm-tid-547257.html,2011-02-11。為什么佛山人可以接受“行通濟”外圍路線的頻繁調整,卻無法接受易地舉行呢?因為,通濟橋的遷址將徹底破壞佛山人對“行通濟”原有的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人們對某種文化在觀念上和心理上持認可和接受的態度,它可以使人們形成共同的信念、理想、價值觀,從而在價值取向、思維模式、行為模式等方面達成一致,從而形成一股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文化層面上來看,自我認同實際上就是“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到哪里去”的問題。有了這個自我確認和自我定位的標準,人們在世界中的活動就具有了相對確定的方向和目標,因此文化認同必然包含著一種深刻的自我主體意識。佛山人接受“行通濟”路線的部分調整,但卻拒絕“行通濟”橋整體搬遷和“行通濟”易地舉行,原因就在這里。其次,“行通濟”行走路線的調整,其實是傳統民俗適應城市空間的變化來實現地方認同的重構。城市記憶實際上就是城市的歷史與文化在城市空間中的存在與延續,而記憶是一種保持身份認同感的有力工具。“行通濟”民俗巡游路線既保持核心線路不變,又不斷擴展巡游的范圍,把佛山市民的日常生活、市民風尚、城市風情和城市精神,借助巡游路線的不斷擴展連綴成章,從而不僅使地方記憶保持了發展的活力,而且使城市記憶和文化認同在這一過程中得以生成或拓展,地方文化認同因此而得以建構。
綜上所述,在近代百余年的城鎮化進程中,“行通濟”民俗面對自然和社會環境變遷所帶來的沖擊,不斷適應、調整、發展,最終由一種古老的社區民俗蛻變為現代的都市民俗。我們當代的民俗研究和保護,必須正視和重視這一日益發展的實踐,而不能一味抱殘守缺,固守傳統。
K890
A
1008-7214(2017)05-0084-09
陳恩維,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
* 本文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人才引進項目“行通濟民俗與佛山社會變遷(299-X5217109)”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王素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