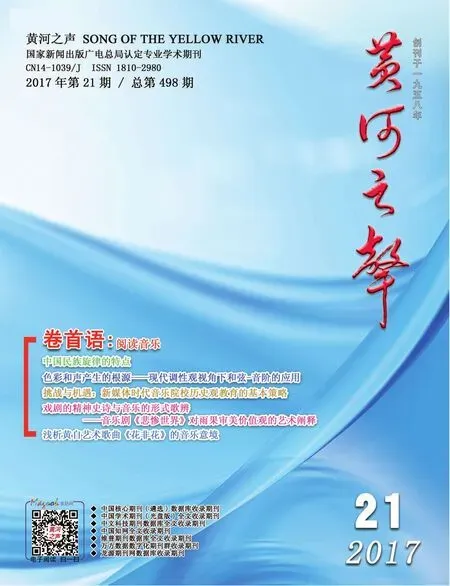“陰陽”與音樂
丁佳楠
(哈爾濱音樂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8)
“陰陽”與音樂
丁佳楠
(哈爾濱音樂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8)
將音樂按地理區域劃分,可以將整個世界劃分為九大音樂區,在各區之中的音樂具有一定的共性。然而這九大風格迥異的音樂區之間真的就是劃分的極致?本文以一種僅次于“太一”的觀點——“太極”,來對世界性的音樂進行探索與假設。
音、人本思想、陰陽、假設
沒有人知曉音樂真正的誕生時間,但是我們可以猜想。沒有人能確定什么是音樂,但是我可以假設。有一位美學家說過“得到音樂的瞬間,就是失去音樂的瞬間。”當我們以旋律為界定音樂的標準的時候,我們就失去了沒有旋律的音樂;當我們以節奏為界定音樂的標準的時候,我們就失去沒有節奏的音樂……著名鋼琴家趙曉生老師以“太極”為靈感,創造出了“太極音樂”。筆者也從相互對立又相互交融的“陰陽”之中尋得靈感,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中的次級存在——“陰陽”為音樂的共性,對音樂進行探索與假設。
一、“陰陽”與音樂
太極生兩儀,兩儀分陰陽。“陰陽”是我國道家的一門重要哲學思想,講究:陰陽互體,陰陽化育,陰陽對立,陰陽同根。“陰陽”一般是一個整體,以相互轉化,相互孕育,相互對比,卻本為同根的形式闡述“陰陽”。音樂也是一般以一個整體的形式出現,闡述屬于音樂的本質——一種人創造出來,表達人類情感的聲音或形式。“陰陽”可以分化為“陰”與“陽”,“音樂”也可以分為“音”與“樂”。由“陰生陽,陰生陰,陽生陰,陽生陽”可推“音生音,音生樂,樂生音,樂生樂”。
中國古代“音樂”和“陰陽”一樣都是拆分的——《禮記·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形象一點,可將音謂之自然之聲,樂謂之人心之聲。“音”與“樂”本為不同之物,卻如同“陰”與“陽”,雖然不同卻同生,同根,同育,同立。
音生音。將自然之聲順其自然,自然將演化自然之聲。“風聲”演“鶴唳”、“微風”化“柳動”…自然之音包羅萬象,無音也為音。寂靜的山谷是自然之聲,沉默的黑夜也屬自然。微風拂過河、流、湖、泊、海所得之音皆為自然之聲。而引動自然之聲者,皆為自然。可謂以自然生自然、以音生音。
音生樂。音乃自然之聲,樂乃人心之聲。《禮記·樂記》記載:“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即“心物感應說”,人心之聲皆感于自然之聲而生。《高山流水》是感于高山流水之聲而生成的人心之聲;《百鳥朝鳳》是感于百鳥之鳴而所作之聲……自然之樂皆因人心感于自然而作。樂皆為人心之音,卻源于自然,可謂自然生人心、以音生樂。
樂生樂。樂乃人心之聲,而以樂生樂則是思想之聲。樂不光是可為音,亦可以為樂——以人心定人心。孔子主倡樂、墨子主非樂、老子主至樂;嵇康有《聲無哀樂論》,劉勰有“心物感應說”……音樂不止有外在之音方為音樂,內心思想的聲音亦可以為音樂,即思想上的音樂也是音樂。以人心創思想之上的音樂,可謂以樂生樂。
樂生音。樂可以理解為思想,而以樂生音則是思想創造自然之音。思想如何創造自然,認同即可。何為自然、何為音樂、何為思想…都是人心內定之產物,如此人心之思想為何不能創造自然之聲。水之聲、雨之聲、風之聲、火之聲……皆為自然之聲,卻皆為人心所定。所以思想可定自然之聲,可謂以樂生音。
“音生音,音生樂,樂生樂,樂生音”。此乃循環,由此及彼,循環往復,亦與“陰陽”相通——“陽生陽,陽生陰,陰生陰,陰生陽”。可見音樂和“陰陽”一樣都屬于高深的哲學范疇,只不過音樂因為有了體現的形式——音樂,才不被更多的哲學家所關注,然而卻無法忽視音樂的哲學性。“陰陽”之中的“陰”與“陽”可以作為一種世界萬物的共性條件,那么“音樂”之中的“音”和“樂”是否也是所有音樂的共性。
二、音樂之“音”
音樂遍布全世界的各個角落,然而音樂的形式卻各不相同。中國的京劇、美國的流行音樂、法國的歌劇、德奧的交響曲、非洲的節奏音樂……這些音樂千奇百怪,各不相同,有的只有節奏沒有旋律,有的只有旋律無節奏,有的純人聲,有的純器樂……但是,卻無法逃脫一個重要的因素,或者說一個狹義上的音樂無法逃脫的因素——音。
從時間上看,無論是中國的音樂之祖——傳說之中的女媧、伏羲、神農氏;還是西方音樂之祖——亞當的第八代子孫猶八。他們所創造的音樂都是有音的,或許他們創造出來過人所無法聽到或者表現出來的音樂,但是我們卻不認為它是音樂。時間繼續,古希臘古羅馬的音樂有音,中世紀時期有,文藝復興時期有,巴洛克時期有,古典主義時期有,浪漫主義時期有,20世紀有,現在也有。音是音樂的一大界限,在沒打破這個界限之前,音樂都會有音。
從空間上看,世界各地的音樂都有音。亞洲的祭祀音樂有,美國的流行音樂有,非洲的打擊音樂有,歐洲的宗教音樂有,文萊人的土著音樂有,日本的的歌舞伎音樂有,德奧的歌劇、交響曲有……將整個世界囊括,各個地區能被承認是音樂的音樂都有音,或許其中有些只要動作,但是那已經無法被人們認同為音樂了,所以目前在空間之上,音依舊是音樂的共性之一。
從形式上看,從人類誕生到現在的的所有音樂種類之中都有音。中國的京劇、黃梅戲、梆子腔、中國式搖滾有;歐洲的歌劇、清唱劇、安魂曲、交響詩畫、交響套曲、奏鳴曲也有;黑人的打擊樂、藍調、POP、爵士有;現在的20世紀音樂、水樂、紙樂、電子音樂、在線音樂、運用AR技術的音樂游戲、網上虛擬合唱團等等,或許人類從最開始的敲打石頭,演變成了彈奏樂器,更變成了虛擬音樂,然而這些統統都沒有辦法離開音,他們都被音限制在一個大圈子里,不突破圈子,音就是音樂的必須。
面對全世界的音樂去推演共性無疑是困難的,但是反過來從音樂的源頭去確定音樂的共性無疑是準確且便捷的。相信音對于音樂的重要性也是無法忽視的,音樂之“音”是音樂的根基。
三、音樂之“樂”
音是音樂的根基是肯定的,但是卻不可忽視音樂之中僅次于音的樂。在古代音是單指聲音,樂才是令人感覺享受的音樂,并且無論從時間、空間、形式上看,音樂必須要有音才可行,然而真的沒有不是音的樂嗎?如果是狹義的音樂概念自然沒有,不過廣義的音樂概念上,卻是存在的。
樂可以是由音拼湊而成的集合體,或許可以將其他物件加入其中。如:人聲可為樂,絲竹可為樂,天地萬物皆可為樂;然而必須有音,并且音必須占主要地位,不然就不再是樂。如:重意境的行為藝術,重思想的辯論,重劇情的電影。他們都存在音,然而卻因不再以音為主,不在是樂。可見樂需要以音為主,或者說專注于音,研究于音。
約翰·凱奇的《四分三十三秒》沒有音,在很多人眼中可能為行為藝術,然而《四分三十三秒》不是音,卻不一定不是樂。因為《四分三十三秒》符合樂的一個主旨,以音為主。雖然形式上沒有音,但是《四分三十三秒》的思想與意識形態之中全是音。狹隘的音樂會不認同《四分三十三秒》,但是廣義的音樂卻能將其包納。
何者為樂,定者為人。音樂思想就是思想上的音樂,而思想上的音樂可以進而投射到實質的音上面形成被廣泛認知的音樂。莊子提倡的“天籟、地籟、人籟”將音樂分為三個級別,也將聲樂與器樂的等級以他的音樂思想來界定,為當時的音樂發展提供了他的一份力量。而老子的“大音希聲”也為當時打開了一條,化繁為簡的新道路,更為約翰·凱奇的《四分三十三秒》提供思路與理念支撐。
我國的三分損益法、五度相生律、純律都是十分重要的律制思想。我國的音樂也都隨著這些思想的影響,衍生為中國的五聲音階、六聲音階、七聲音階。西方的音樂思想受基督教影響,追求上帝與極致的單純形成了圣詠;追求莊重與華麗形成了多人唱詩班與巴洛克式繁華的和聲。
樂不光可以理解為思想上的音樂,還可以理解為人認同。音樂起于人,發于人,終于人。好似行為藝術的《四分三十三秒》如果被人認同為樂,那么它不是也是。
四、結語
本文探討的是世界范圍內,音樂的共性問題。而得到的假設認為,音與樂猶如“陰陽”——由兩部分組成,雖然可以獨立存在,卻只有在合二為一時方為本真。
目前認同的音樂必須含有“音”,而身為“樂”,必須為人所定義并認同。所以“音”為自然之聲,“樂”為人心之聲。“音”與“樂”猶如“陰”與“陽”必須合二為一方為“音樂”和“陰陽”。
音樂與陰陽的相似之處究竟是巧合還是必然,學生本次嘗試將音樂與陰陽的共性相關聯,并以“音”和“樂”兩點作為音樂的共性去驗證世界性音樂的共同。“音”與“樂”作為音樂的關鍵,筆者相信目前的音樂之中不會有超出者。■
[1]《禮記·樂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2]梅梅.嵇康與《聲無哀樂論》研究[D].內蒙古師范大學,2011,04.
[3]約翰·布萊金.人的音樂性[M].人民音樂,2007,05.
[4]鄭祖襄.中國古代音樂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5]孫繼南,周柱銓.中國音樂通史簡編[M].山東教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