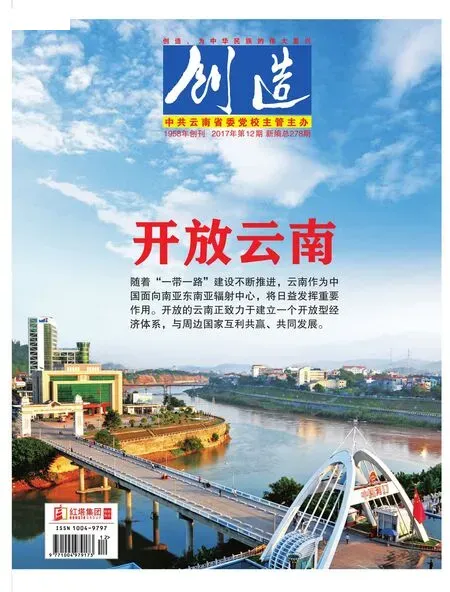西南聯(lián)大軼事
梁思成的茅草房
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來到昆明后,聯(lián)大校長、清華大學原校長梅貽琦就請梁思成夫婦為西南聯(lián)大設計校舍。兩人欣然受命,花了一個月時間,拿出了第一套設計方案:一個中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赫然紙上。
然而,設計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聯(lián)大不可能拿出這么多經費。此后兩個月,梁思成夫婦把設計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樓變成了矮樓,矮樓變成了平房,磚墻變成了土墻。當梁思成夫婦交出最后一稿設計方案時,建設長黃鈺生很無奈地告訴他:經校委會研究,除了圖書館的屋頂可以使用青瓦外,其他建筑一律覆蓋茅草,土坯墻改為用粘土打壘,磚頭和木料使用再削減二分之一,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調整。
此時的梁思成已經忍無可忍,他沖進梅貽琦的辦公室,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還要我怎么改?我……已經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們知不知道農民蓋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梅貽琦嘆了口氣說:“正因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師們對木材的用量嚴格計算啊。”
梁思成聽著,流下了眼淚,哭得像一個受傷的孩子……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滿了原來空蕩蕩的校園空間。
華羅庚的“特殊屏帳”
數學系教授華羅庚一家住在黃土坡上一處簡陋的房屋中,可是即便這樣的陋室還是遭到了敵機的轟炸而倒塌,所幸一家人當時外出,躲過了一劫。失去了住的地方,華羅庚一家只好在野外當“山大王”。
聞一多得知后,熱情地邀請華羅庚一家到自己家中共居。當時,聞一多租住的房屋是昆明地區(qū)典型的“一顆印”民居。所謂“一顆印”,是當時昆明人形容一般平民百姓的住房像印章那樣狹小的代名詞。這套住房兩層樓,樓下為炊房,堆放雜物;樓上住人。
華家搬來后,聞一多騰出稍大一點的一間給華羅庚。由于中間沒隔墻,生活上總有些不方便。聞一多只好掛幾條花花綠綠的床單隔開。華羅庚幽默地對聞一多說:“聞兄,你在室內掛屏風,我們兩家人好似住進賓館了。”一席話,逗得兩家人圍在一起捧腹大笑。
后來,華羅庚回到北京,當他得知聞一多、李公樸在昆明遭特務暗殺的消息后,悲傷地翻出當年的照片,痛哭不已。
幽默風趣金岳霖
金岳霖先生在學生面前,總是認真而又謙遜、風趣而又天真。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他給新生上課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
老師對學生的尊重,細致至此,似不多見。金先生班上有一個很愛提問的同學叫林國達,一次在課堂上又提了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林國達君垂直于黑板’,這什么意思?”林國達傻了,林國達自然無法垂直于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成立。金先生就是這么風趣地對學生的問題進行解釋,而且十分形象。
金先生有一門選修課“符號邏輯”,特別深奧,選修者少,一個叫王浩的學生卻例外,頗懂個中奧妙。金先生經常會在講授過程中停下來,問道:“王浩,你以為如何?”于是,接下來的課堂便成了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后來赴美留學,又曾任教牛津大學,成了國際一流的邏輯學家。
狂人劉文典
劉文典在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當教授時,不把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對講授語體文寫作的作家教師沈從文甚有偏見。當他獲悉聯(lián)大當局要提升沈為教授時,勃然大怒,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在昆明時,某日空襲警報響起,師生們爭先恐后到處跑,劉跑警報時,忽然想起陳寅恪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