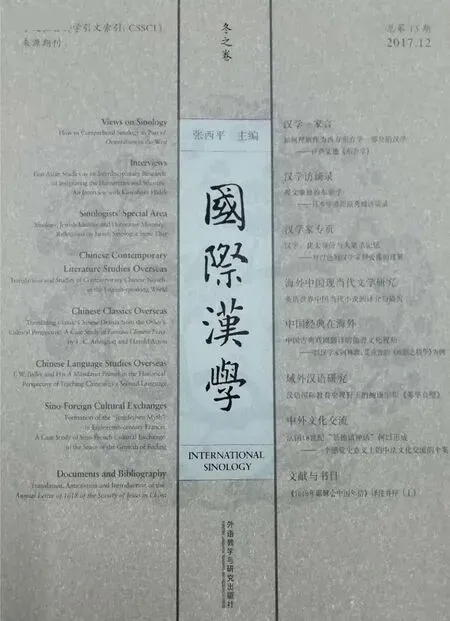中國古典戲劇翻譯的他者文化視角
——以漢學家阿林敦、艾克敦的《戲劇之精華》為例*
□
中國元代雜劇《趙氏孤兒》走進18世紀的西方文化一直為我國學界關注,視之為中國戲劇藝術普遍價值存在的象征。然而,這部戲的“走出去”也伴隨著不解。該劇并非中國古典戲劇的代表作,即以同一時期的《西廂記》而論,其思想價值、藝術成就,可能都在其上。西人漠視“一流”,青睞“二流”,其對中國戲劇藝術的認知水平令人生疑。不過這種疑慮應該歸咎于考察問題的單一文化視角的局限。如果跨出中國文化邊界,從西方文化視角審視中國戲劇,又將得出何種結論,這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我國國家機構推動的古典戲劇外譯實踐中,中國的一元文化視角特征比較明顯。從20世紀50年代國家外文局主導的幾部戲劇的翻譯,至20世紀80年代后北京大學等高校教師的翻譯,及至近幾年中國人民大學的翻譯,從原文文本選擇到文本翻譯策略都具有這種特征。原文本都是當今中國文化認同的經典文本,翻譯文本與原文本高度相似。這一做法,似乎理所當然。可是,這些外譯文本對目標文化的影響,對弘揚中國文化的價值大小或有無,換言之,中國文學(文化)外譯行為的目標達到與否,目前還不能確定。對這些問題做出結論,還需要他者文化,或跨文化視角,中國文化的單一視角有局限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對中國文學(文化)外譯是跨文化行為這一命題的認同。僅以一種視角考察文本跨文化轉換與這種行為的跨文化屬性不相匹配,這種行為的分析需要超越單一的自我文化視角。20世紀30年代兩位西方漢學家出版的《戲劇之精華》(Famous Chinese Plays)①該譯本的大部分皮黃戲原文出自《戲典》(伶音館主編,上海中央書店印行,1936年出版);昆曲基于韓世昌的文本譯出,散見于《六十種古曲》(汲古閣,1935年出版)。參見管興忠、馬會娟:《胡同貴族中國夢—艾克敦對中國文學的譯介研究》,《外語學刊》2016年第2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他者文化視角,對認識單一文化視角的局限性應有啟迪。
一、《戲劇之精華》的原文本選擇
《戲劇之精華》是中國古典戲劇的譯文集,譯者為阿林敦(L.C.Arlington,1859—1942)和艾克敦(Harold Acton,1904—1994),1937年由羅素和羅素(Russell & Russell)公司在當時的北平第一次發行。阿林敦為中國政府雇員,也是中國戲劇的研究者,1879年始居北京,至該書第一次發行時他在中國已生活了近60年,此前獨自出版過專著《中國戲劇》(TheChinese Drama: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ntil today,Shanghai:Benjamin Blom,1930),較全面地論述了中國戲劇的起源、角色、服裝、化妝、舞臺特征等。另一位譯者艾克敦是一位年輕詩人,1932年來北京居住,受聘于北京大學講授文學、詩歌,與北京的學術圈多有交往。他的另一部重要譯作是《現代中國詩歌》(Modern Chinese Poetry)。與阿林敦一樣,他對中國戲劇同樣入迷,程度不亞于任何一位北京戲迷。兩人對中國戲劇都經歷了從接觸到入迷進而到研究的過程,最終均成為頗有成就的中國戲劇研究者。
《戲劇之精華》收錄了33部中國古典戲曲譯文,選譯的原文之多是其翻譯文本選擇的第一個特點。當時北京地區的常演劇目有50多部,這33部是其中較為常見的。譯者表示,譯作所選的劇目達到了當時中國全國常演劇目的50%。這在其他中國古典戲劇譯者包括西方的漢學家中都是獨一無二的。其他的譯者往往根據自己的喜好選譯一兩部,從未像他倆這樣選擇了如此之多的文本加以翻譯。按上述數據推算,當時全國常演劇目應為60多部。基于何種考慮,《戲劇之精華》譯者從中選擇了這33部,這是有待分析的問題。
該譯作的文本選擇體現于文本主題與藝術水平兩個維度。從文本主題維度上看,忠孝節義、道德教化類劇目占了《戲劇之精華》的一大部分。《九更天》講述仆人犧牲親生女兒救贖主人,是忠義觀念的化身;《一捧雪》主人逢冤,仆人舍命以救,異曲同工。《玉碑亭》男女主人公恪守道德規范,終得報償,是節婦義男的經典。
《戲劇之精華》文本主題的選擇與20世紀50年代之后中國譯者包括西方漢學家的做法存在顯著區別。阿林敦、艾克敦選擇了較多的忠孝節義、道德教化劇目,這是當時中國古典戲劇舞臺的主流劇目。而中國的翻譯家以及其他的西方漢學家更為傾心的卻是愛情題材的作品,昆曲《牡丹亭》《梁山伯與祝英臺》、京劇《白蛇傳》《霸王別姬》等是這些譯者的首選文本。2014年中國人民大學發行的十一部中國古典戲劇英譯本中這些劇目也占了大部分。《戲劇之精華》中此類題材卻不被待見,相反則是戰爭題材戲較多,如《長坂坡》《群英會》《戰宛城》等取材三國故事的戲就有7部。戰爭題材的戲大多通過文臣武將的心機計謀、剛毅勇猛表現他們的忠肝義膽。就文本題材而言,這更接近當時中國古典戲劇的舞臺現實。其他譯者鐘情的愛情題材并沒有進入兩位譯者的法眼。《戲劇之精華》譯者放棄愛情題材而選其他題材彰顯了其獨特的翻譯動機,客觀公允地向西方觀眾反映中國的戲曲舞臺現實,按照中國戲劇舞臺的本來面目選擇翻譯文本可能是他們的主要關切。
從與其他譯者的比較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戲劇之精華》文本選擇視角的不同,而其具體文本的翻譯策略也再次證實了這一特征。《戲劇之精華》33部劇目的翻譯及相關的介紹與評介差別很大,一些劇目的主要角色簡介、道白、唱詞等都全部譯出;另一些僅僅翻譯了劇情概要、部分唱段及主要角色姓名。這種差別化的翻譯策略表明不同劇目受譯者關注的程度存在差別。這與通常的中國戲劇文本統一的翻譯策略明顯不同。《戰宛城》《群英會》《慶頂珠》《九更天》《一捧雪》《奇雙會》《翠屏山》《汾河灣》都給予了詳細翻譯;而《尼姑思凡》《打城隍》《天河配》《銅網陣》《王華賣父》《五花洞》等卻屬于簡要的翻譯。兩相比較,譯者對中國戲劇的所謂代表性劇目厚此薄彼的態度一目了然。顯然,這種差別化的翻譯與譯者的文化視角緊密相關。
在《戲劇之精華》入選劇目的另一維度—藝術維度上他們主要考慮的是舞臺演出和戲劇音樂兩方面的價值。該書中,有些三國題材的劇目入選不僅因為文本主題屬于當時舞臺演出的主流劇目,而演員表演的精湛超群可能是更為重要的標準。譯者的相關評介中也說明了這點。如關于《戰宛城》,譯者寫道“該戲的演員精英薈萃,他們中的任一位演員都足以使整個演出精彩奪目,……演員的服裝別出心裁,意味深長—曹操著女人服裝,滿是喜感;張繡著孝服刺殺嬸母。……武生演員的刀槍劍戟,身手拳腳,模仿搏斗,動作迅捷,身段柔軟,無以復加。”①L.C.Arlington and Harold Acton, Famous Chinese Plays.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Inc., 1937, p.24.關于《長坂坡》,譯者對舞臺展示的戰爭場面叫絕,“……演出節奏鮮明;場面千變萬化,令人目不暇接,陶醉其中。”②Ibid., p.37.這些描述表明一點,演員的表演是中國戲劇藝術精華的集中體現,這些劇目反映了中國戲劇的這種特征,因而入選的理由是該劇目演員的知名度及其表演的藝術水準。這反映了譯者對中國戲劇藝術的準確把握及原文本選擇的獨到思考。
《捉放曹》的表演對人物性格的刻畫最為深刻,曹操的殘忍暴虐、冷酷無情被演員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樣的表演打動了觀眾,因此成了入選的理由。《玉堂春》則因為其現實主義價值而被選中。由于中國的古典戲劇大多具有超現實的意蘊,該劇屬于少數的現實主義題材,其入選是因其題材的獨特,它展示了中國傳統戲曲題材的多樣性。譯者表示,外國觀眾應該喜歡這部戲,可能就是因為它是現實主義題材。中國傳統戲曲中,它最接近生活的真實。③Ibid., p.419.所以盡管該戲屬于少數題材,但對上了西方觀眾的口味,還是被譯者選中,這是譯者文本選擇的目標文化取向特征的表現。
代表性的戲劇音樂是原文本藝術維度的另一方面,《尼姑思凡》屬于這種類型。該劇的音樂以譯者看來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代表了中國戲劇音樂的最高水準,因此而入選。《尼姑思凡》可能兼具文本主題與藝術,即音樂兩方面之長,而另一些劇本音樂的藝術水準自身可能就打動了挑剔的譯者。
該譯本給出了9部戲的主要音樂唱段。譯者認為,中國戲劇以綜合藝術形式見長,相對西方戲劇的單一藝術形式,這是其精彩之處,所以戲劇音樂應該得到表現。這些音樂以五線譜記譜,附加在相應劇目的譯文上,有的是一個完整的唱段,有的只有幾行曲譜。這些曲譜與譯文自身的簡繁不一致,簡要翻譯的給了曲譜,詳細翻譯的卻不一定有曲譜。音樂被看成了相對獨立的藝術表現形式。音樂與譯文的匹配在其他的中國戲曲翻譯中多被忽略。這里《戲劇之精華》刻意表現的是中國戲劇區別于西方戲劇的綜合性藝術形態。
音樂是中國戲劇藝術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譯文如果放棄了音樂,目標語觀眾看到的就是殘缺的藝術表現形式,中國戲劇的藝術特征因而將大打折扣。這對于志在使西方觀眾見識中國戲劇藝術全貌的譯者而言,可能是難以容忍的缺憾。譯者附加的9部戲曲的音樂片段很難說就能彌補外譯中國戲劇藝術的不足,但這種管中窺豹的方式至少為西方觀眾提供了領略中國戲劇音樂的機會,至少在一定意義上表現了中國戲劇藝術的完整性。這也是譯者“將外國讀者放在心上” 這種目標語翻譯取向的再次體現。
譯者給出了部分唱段的曲譜并不代表他們服膺中國戲劇音樂,相反他們認為中國戲劇音樂過于喧鬧,而且盡管節奏鮮明,但易使人昏睡,中國最好的音樂完全不是這樣。這不僅是譯者的個人評價,更是西方文化比較普遍的看法。之所以收入這些曲譜,是為了客觀地展示真實的中國戲劇藝術,并不擔心因此而有悖自己的初衷,因為中國戲劇藝術的精彩之處在于其各種表演藝術的完整統一。這應該是基于不同文化視角才能得到的印象。
阿林敦、艾克敦兩位譯者長時間生活在北京,親身體驗了舞臺上的中國古典戲劇,他們對中國戲劇藝術的理解是直接的、全面的,也是深刻的,這在西方文化中少有人及。完整地介紹中國戲劇藝術的真實面目,使西方文化能正確地體會與己不同的藝術形式,獲得異域文化的藝術體驗,可能是兩位譯者的文化訴求,這一訴求的產生源于其觀察問題的文化立場與視角。
二、《戲劇之精華》的文本翻譯過程
譯者的翻譯過程是其西方文化視角的具體表現。《戲劇之精華》譯文多有刪節、添加、結構調整等特點。這樣做的目的是“剔除一些平淡乏味的,甚至是重復的敘述”。④Ibid., preface, p.xii.“剔除”的依據當然是目標文化的美學觀;另一方面這種調整更是為了最大程度地吻合西方觀眾的欣賞習慣。根據西方的戲劇觀念,中國戲劇往往不合邏輯,這在習慣上看重戲劇情節的邏輯關系的西方觀眾看來有怪異之感,有時無法容忍。不過中國觀眾對此仿佛視而不見,他們認為戲劇的魅力在于名角的知名度、演唱水平。中國北方,尤以北京地區為代表,戲曲欣賞稱為“聽戲”,在劇場里閉目傾聽名角的演唱,就是中國觀眾欣賞習慣的形象表述,而演員的表演、化妝、服裝、布景、燈光等方面相對而言不那么受關注。
中國觀眾欣賞習慣的這些特點構成了中國戲劇演出的文化語境,當翻譯為英文時,這種語境就發生了變化,觀眾的美學觀念、欣賞習慣發生了變化。如何適應新的文化語境,翻譯文本做出何種調整,譯者的文化視角就顯出了作用。
對原文的相關部分進行刪除或添加在《戲劇之精華》文本翻譯中比較常見,《奇雙會》的譯文中,不止一處出現這類情形。原文本的第一場講述了金星神仙與鶚神在上天安排主人公李奇在人間的運數。金星神仙講述李奇獄中受難期限已滿,今日是他父女相見之日,因此命鶚神降落縣衙引導他們,鶚神領命。這場戲旨在申明,人間運數皆為天定。這樣的場面符合中國文化的宿命心理,觀眾往往欣然接受,并不感覺有何不妥。而兩位譯者則跳出了中國文化視角,從西方的美學觀念對這一場演出的價值加以解讀。他們認為這場戲與全劇的劇情關聯不大。假使在譯文中留保這一場,譯文文本的完整性、連貫性可能受損。更有甚者這種刻意添加的神仙戲看上去荒誕滑稽,不符合西方觀眾的欣賞預期。因此兩位譯者的譯文中這一場僅僅給出了概述,劇情直接由第二場開始。他們的這種解讀與該劇的另一譯本,二者的差別更為明顯。這部戲的另一英譯文本是1935年《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上姚莘農的譯文,這一場被完整譯出。姚譯劇名為“Madame Cassia (桂枝夫人)”,以劇中女主角名字命名。①Yao Hsin-nung, “Madame Cassia,” T’ien Hsia Monthly, 1935, Vol.1, No.4, pp.540—584.阿、艾譯為“Chi Shuang-Hui, An Extraordinary Twin Meeting”。原文第六場,李奇的兒子、時為八府巡按的李保童處置了冤案制造者后,家人團聚,父親李奇與兒子、女兒、女婿細敘家常,其中的多行對話涉及生活、官場現狀,以及父親的感慨等。這一段阿、艾譯文里沒有出現,姚譯文卻悉數保留。另一處明顯刪節出現在第二場開始。鶚神再次出現在李奇監房,告知受金星神之命查詢冤情,李奇哭訴,女兒桂枝遂聽到有人深夜哭泣。阿、艾的譯文直接由桂枝在縣衙家中聽到李奇哭聲開始。李奇向鶚神哭冤的部分刪除后,情節的發展更為直截了當。李奇這場戲的譯文還有譯者的添加。第二場獄卒進入監室向李奇索錢,原文寫道:
禁子:自你進入監門以來從沒見你花過一個小錢,今天把你叫來,或是有錢有鈔的,拿出些來也好給我使用使用嚇。
李奇:哎呀大哥嚇,想老犯人遭此不白之冤枉,所有家產被楊氏霸占去了,哪有銀錢送與大哥使用,望大哥行個方便罷。
禁子:好嚇來一個行事方便,來兩個行事方便,那我也方便不了那么多嚇。告訴你說,有銀子趁早拿出來,要是沒有,今兒我就活活地打死你。②《曲譜選刊·奇雙會》,北京:中華書局,1922年,第1731—1732頁。
譯文:
Warder There is no oil for the lamps,money is needed.If you have any,it is high time to hand it over.
Li Chi In such dire straits how can I produce money?
Warder Just listen to this: Those who dwell on mountains depend on timber for living;those who dwell by a river depend upon waters.Never mind how much it is, you have got to pay up; otherwise, look out yourself! I’ll give you a taste of ankle squeezers, and even worse.③Yao, op.cit., p.543.
可以看出譯文為獄卒增加了索錢的借口,no oil for the lamps,盡管說的人和聽的人心知肚明屬于無稽之談,但這比起原文直來直去的強索聽上去至少婉轉了一些。添加的這一句,豐富了獄卒的心理活動,其形象個性得到增強。隨后譯文添加的內容使這一效果更為顯著,即, those who dwell on mountains depend upon timber for living;those who dwell by a river depend upon waters(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這一句聽上去像監犯索錢是監牢的慣例,并非我獄卒獨出心裁。犯人不給獄卒銀錢倒有些不合規矩了。獄卒貪婪、強詞奪理的形象躍然紙上。中國的古典戲曲中,獄卒已被定型為卑賤下作、不擇手段的一類人,他們的形象已被臉譜化。顯然譯者以不同的視角看到了中國戲劇人物模式化的不足,為了克服這點,他們有意添加了譯文,以增強人物的個性。
原劇中李奇敘述楊氏攫取家產的部分先后出現兩次,《戲劇之精華》刪去一次。而在姚譯文中,兩段內容都被譯出。姚譯文更看重譯文與原文的一致性,而《戲劇之精華》則看重目標語觀眾的戲劇體驗。兩種取向形成了兩種翻譯策略,反映了兩種文化視角。阿、艾的文化視角在“譯者前言”中談到姚氏譯文時有過明確表述:姚譯文細膩入微,有學術翻譯的味道(sensitive and scholarly translation),是否收入他的譯文我們有所猶豫,但還是堅持了自己的理念—以外國戲劇觀眾為取向(with foreign playgoers in our mind)。①Arlington and Acton, op.cit., p.xxx.
類似的增刪操本在該譯本的另一些劇目中也經常出現,如《打魚殺家》《九更天》等都有類似情形。
對原文進行結構次序的調整是兩位譯者的又一翻譯特點。《群英會》全劇結構就做了這種調整。《群英會》原文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大致順序是,周瑜設局(為謀害孔明讓他去截取曹操軍糧),蔣干盜書,誅殺大將(曹操誅殺水軍都督蔡瑁、張允),周、孔定計,打黃蓋,草船借箭,借東風,曹軍大敗。阿林敦、艾克敦的譯文結構是,以孔明草船借箭開始,隨后是打黃蓋,之后是蔣干盜書,最后是借東風曹軍大敗。刪掉幾個場次并調整次序后,譯文的情節簡化明晰,統帥的文韜武略,謀臣的神機妙算,武將的忠義赤誠等得以凸顯,全劇的英雄群像被顯著拔高。很明顯這是西方文化對《群英會》的解讀,而中國文化的解讀則褒貶互見,全面褒獎了心機近乎神仙的孔明,部分貶抑了雄才大略卻心胸狹小的周瑜。
譯文對原文的增刪、結構調整處處表現了譯者的他者文化視角,但這類操作在其他的翻譯中也經常出現,不能說是《戲劇之精華》譯者他者文化視角的獨特表現。而最能體現這兩位譯者解讀視角的要首推他們對中國戲劇人物與西方歷史人物的比較。這種比較本質上是譯者建構了兩種文化經驗的連接通道,為西方觀眾理解中國文化確立了文化心理基礎,這是譯者創立的最為有效的文化障礙克服手段。這些被比較的西方文化人物早已內化于西方觀眾的頭腦,沉淀為西方文化經驗的組成部分。譯者訴諸這種文化經驗,中國戲劇和西方文化就形成了心靈溝通,目標語接受者進入中國戲曲的文化世界就具備了文化心理基礎。《玉堂春》中的女主角蘇三對愛的執著,仿佛就是巴黎的曼農·萊斯科(Manon Lescaut,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1858—1924]歌劇《曼農·萊斯科》中的女主角)的中國版,因而撥動了觀眾的心弦(the figure that stirs the heart)。②Ibid., p.419.兩部劇中的女主角都是各自文化中摯愛情感的化身,最終都實現了自己的追求。在譯著成書的年代,由于文化的隔閡,西方文化對中國戲劇存在偏見。與這種偏見不同,譯者對《玉堂春》給出了自己的解讀,顯然這是西方式的解讀,否則,《玉堂春》這部中國戲的藝術價值不會是現實主義,而仍然是一部道德劇。譯者認為,這部戲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浪漫愛情故事,但與其他中國戲相比,它的人物不落俗套,鮮活生動。賣花的金哥、獄卒崇公道心地善良、古道熱腸,難得一見,如果遇上優秀的演員,他們就是我們身邊的熟人。③Ibid.接下來譯者表示:該劇超越了那種刻板的儒家倫理道德劇(above the strait-jacket Confucian moralityplays),因此,西方文化關于中國戲劇往往單調重復的看法在《玉堂春》這部戲中是站不住腳的。④Ibid.
在《捉放曹》的評介中,對曹操的個性,譯者用了狡詐、殘忍、喪失人倫、自負等九個形容詞。為使西方觀眾更深入地理解這個人物,譯者再次借用西方觀眾熟悉的歷史人物,18世紀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與曹操的個性相比。這為西方觀眾確立了一個理解人物的參照點,使他們自身的文化經驗能夠得以參與到異域文化人物理解的過程中去。對該劇另一人物陳宮的評價,西方話語特征一目了然,“公正地講,陳宮性格懦弱,他人的巧言令色使其背叛了自己的朝廷,這是個機會主義者。”①Ibid., p.151.譯者認為《群英會》處處體現了心機計謀,即使《普林西比島》(del Principe)的作者面對此劇中比比皆是的口是心非之人也要自愧不如。②Ibid., p.210.這種解讀是譯者他者文化視角的客觀印證,也是譯者無法擺脫的文化立場的體現。他們的他者文化解讀被用于兩種文化的連接溝通,克服中西戲劇的文化隔膜,這是《戲劇之精華》對中國戲劇外譯的重要啟示。
結論
文學(文化)翻譯是跨文化交際行為,它一方面聯結原文文本,另一方面聯結譯文文本。不同于單一文化邊界內的行為,通常主要受單一文化的影響,兩種文化都對這種翻譯行為有直接影響。相對于單一文化內的行為它具有跨文化特征,這就要求采用多元文化視角分析問題。目前中國戲劇,或者文學(文化)翻譯存在不少疑惑,主要原因是對這種行為的跨文化本質缺乏深入的認識,“走出去”的翻譯依然沒有擺脫原文本與譯文本一致性關系的羈絆,從自我文化出發選擇自我喜愛的文本,忽視了目標文化的感受,沒能走出單一的自我文化視角的局限,因此對基于他者文化視角的翻譯行為不解大于理解。當下“走出去”的翻譯實踐中這類情形不乏其例。20世紀中期,我國文學史上并無大名的唐代詩人寒山在美國頗受青睞,成為美國社會所知不多的中國詩人中較受關注的一位。中美文化對中國詩人的接受不同,很明顯,這與兩種文化的不同視角有關。
跨文化交流的要義是兩種文化的相互理解,他者文化如何理解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有何感受,翻譯時必須清楚。這就需要進入他者文化視角,以他者視角審視中國文化,從他者視角理解中國文學(文化)的“走出去”,這是文學外譯行為能否實現其行為目標的前提。
《戲劇之精華》深化了我們對他者文化視角之于中國文學(文化)翻譯“走出去”的認識,有助于我們擺脫自我文化視角的局限。同時譯者對中國戲劇藝術的他者文化解讀,使我們能夠得到先前單一視角無法得到的東西,這又促使我們對原文本進行反思,對原文本的認識也由此得以深入。
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翻譯轉向他者文化視角并不意味著放棄自我文化,當然我們也難以放棄,而是要堅持多元文化立場,在自我文化基礎上觀照他者文化,在兩種文化間不斷切換,用兩種文化視角不斷比較分析,由此獲得不同的文化體驗。中國文化將這種認識過程概括為“和實生物”,兩種不同的事物接觸,不是一種化掉另一種,也不是兩種的單純融合,而是“和”之后生成新的事物,事物由此不斷發展,這是中國文化對事物發展普遍規律的認識。“和實生物”是跨文化交流應有的情懷,也可視作中國文化“走出去”轉向他者文化視角,或跨文化視角的中國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