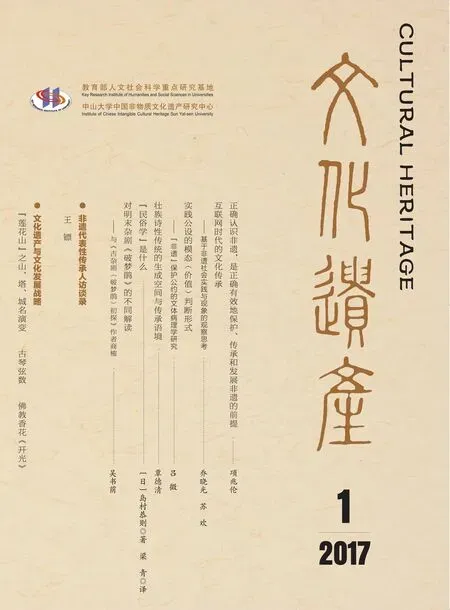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入高校課程的現狀和影響*
——以黔東南凱里學院為例
張光紅
?
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入高校課程的現狀和影響*
——以黔東南凱里學院為例
張光紅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現代化建設迅猛發展。無論城市或鄉村,在現代化潮流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都遭到了巨大的流變。隨著市場經濟的觸角延伸至鄉村的每個角落,同質性的擴張,異質性的收縮,許多地方性、區域性文化正在消失,文化多樣性正處于破損之中。在此狀況下,傳統文化所寄存的文化生境正遭受強烈的沖擊,非物質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正面臨新的挑戰,它是否能適應在新時期下的生存和發展,是關系到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否有效地得到保護、并能繼續傳承下去的關鍵所在。為了保護非物質文化許多地方把它納入高校之中,企圖借助高校的優勢資源,更高層面地、系統地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本文以黔東南侗族苗族自治州凱里學院為例,探究凱里學院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所采取的舉措,以及學校主體對非物質文化的態度。
少數民族 非物質文化遺產 傳承 保護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極速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已經引起了社會主體的普遍關注。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產”,在2003年10月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將其定義界定為:“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持續的認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約中,只考慮符合現有的國際人權文件,各社區、群體和個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順應可持續發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從定義中可知非物質文化遺產涉及社會主體的各個方面,力圖構建文化多元性社會。隨著市場經濟觸角延伸至鄉村社會的各個角落,新興的市場經濟以及隨之而來的消費主義迅速占領了農村的生活空間。①王華:《農村“高音喇叭”的權力隱喻》,《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民族地區文化的發展與保護備受關注。而民族教育在傳承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的作用日益明顯。教育是人類社會文化傳承的主要途徑和手段,是培養人的社會活動;為興國之本的教育,同樣也是傳承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最為有效的途徑和方法。教育的本質就是文化傳承,而學校是這種文化傳遞和延續的最主要場所和方式。*特木爾巴根:《民族教育在保護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作用——以北京郵電大學民族教育學院為例》,《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8年第7期。
因此,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入高校課堂是當前形勢下實現民族文化傳承與保護的主要方式之一。
為探究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高校的發展狀況及產生的社會影響,2015年10月筆者運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深入黔東南凱里學院,訪問學院領導、教師和學生。通過對非物質文化在高校課程中的現狀及其連帶的社會文化動態的分析,可窺見這一措施對民族非物質遺產文化產生的影響。
一、引入課堂的非物質文化內容及教授特點
凱里學院坐落于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凱里,學院建筑和校園生活充斥著濃郁的民族文化特色。通過訪談和調查得知,音樂學院、藝術學院、體育學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最為集中展現的地方。三個分院都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入課堂之中,然具體實施各有特點。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于音樂學院中傳承方式和特點
在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課程設置中,音樂學院主要以民族音樂為特色。所教授的班級是五年制民族文化傳承班,就地域而言生源皆來自黔東南境內各縣、鄉(鎮)、村和寨子。苗族和侗族占班級成員的90%以上,輔之少量的其它民族,如布依族、水族等。他們皆是初中畢業,許多學生因家中經濟拮據或成績太差致使中考失敗才選擇進入凱里學院學習。民族文化傳承班主旨是傳承和弘揚少數民族(由于受其地域影響這里主要指苗族和侗族)文化,特別是歌曲和舞蹈。
從2003年起,音樂學院(當時凱里學院仍是是大專院校,所以嚴格上講音樂學院在當時是音樂系)首次面向全州中學招生,當年一共招進63名。此后每年皆在州內招收五年制大專生,但招生人數呈緩慢地逐年下滑趨勢,據統計可知從2003級至2006級一共招有145人。這些五年制學生大多來自苗鄉侗寨的少數民族子女,且年齡小、可塑性強,對少數民族民間文化理解深、接受快。*張雪梅:《民族地區高校民族民間文化傳承人培養模式探討——以凱里學院民族民間文化傳承班為個案》,《凱里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每年中考之前,音樂學院將在全州內招收學生,學院老師通過面試的方式,確定學生對本民族文化的掌握程度,以此決定學生的擇取。如果學生在某一方面極為突出,學校也會把他招入民族文化傳承班。通過學院領導處得知,五年制大專班生源主要來自偏遠的山村地區。2015年10月20日于凱里學院做調查,音樂學院34歲的侗族女老師楊莉在招生科辦公室講道:“學院每年招生時,其實也有很多縣城里的學生來面試,雖然他們都是少數民族,但當問及是否了解本民族習俗、音樂、服飾時,許多人一無所知。由于長期離開祖先生存的母土,他們甚至不會講本民族的語言。與之相反的是,常年生活在鄉村的學生,當問及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時,他們能侃侃而談,并能現場唱歌跳舞。因此,在招生時我們對民族地區偏遠山村的學生總是滿懷期望。”*本文訪談資料皆為筆者調查所得,由于凱里學院是筆者本科所讀院校,這為資料的獲取提供了極大地便利,調查期間獲得學院老師和同學的極力幫助。訪談人:張光紅,男,貴州大學民族學研究生,云南昭通人;被訪談人:楊莉,女,侗族,碩士生,主講西方音樂理論兼招生科科長一職;訪談時間:2015年10月20日早上9點半;訪談地點:凱里學院音樂學院招生辦公室。黔東南由于受地勢和經濟發展狀況的限制,加強山村地區與外界溝通仍困難重重,致使鄉村社會具有濃厚的地方性特色。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費孝通:《鄉土社會與鄉土重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頁。鄉村社會的內閉性,減緩了原生文化流動變遷。而從小在村莊長大的孩子,在村莊老人和家庭生活的熏陶下,很好地傳承了自我民族的特色文化。
例1:安慧,女,苗族,17歲,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劍河縣南加鎮展留村人。截至2015年10月,安慧已在凱里學院民族文化傳承班求學三年。據其講述,初中時期由于學習成績太差且家庭經濟困難,中考基本無望。在家庭經濟拮據的狀況下,父母在其很小的時候就已出去務工,每年只有春節在家待上一段時間。由于那時安慧年齡太小,父母讓她常年與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爺爺是村里的歌師,曾參加過多次由縣里主辦的苗族歌唱大賽,并多次獲獎,而且還被評定為民間文化傳承人。安慧自小在爺爺的培育下成長,因受爺爺的影響,所唱苗族飛歌是村里最好的。對苗族許多神話故事、風俗習慣、服飾等如數家珍。
父母長期在外務工,爺爺奶奶年齡已大,作為家中的長女安慧主動承擔了沉重的勞務。繁重的勞務占去了她許多學習時間,因此,上初中后她的成績一直排在班級末尾。正如她說:“我也想過要好好學習,把成績提升上去,可是每當想到家里還有這么多勞務要我去做,我整天想著的都是怎么把當下的農活干完,哪還有心情學習啊!”*訪談人:張光紅,男,貴州大學民族學研究生,云南昭通人;被訪談人:安慧,女,苗族,17歲,五年制大三學生,凱里劍河縣南加鎮展留村人;訪談時間:2015年10月20日14時;訪談地點:凱里學院音樂學院練琴室。在初中時安慧唱苗族歌曲極好,因此她的老師建議她去凱里學院讀五年制民族文化傳承班,該班不收任何學費,所以比較適合她。在父母的同意之下,父親帶著安慧到凱里學院參加了面試,并唱了多首苗族歌曲,其中還包括難度較高的飛歌。安慧的歌唱水平使她成功的成為民族文化傳承班的一員,由于對自我民族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表演能力,她進一步的成為學院重點培養對象,并時常出去參加節目表演。
從凱里學院文化傳承班可知,非物質民族文化傳承和保護的比較好的地方往往是本民族原生文化保存地最好的地區。一方面文化受其主流社會沖擊相對較少,社會相對穩定,文化保存比較完整;其次村莊主體從小于原生文化的土壤之中成長,具有極強的文化可塑性,成長的生活經驗形成其特有的歷史記憶,這促進了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因此,鄉村社會往往是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較為原生的集中體現。
當這些具有民族文化烙印的中學生進入學院后,為使其得到全面性和正規性的培養,音樂學院請著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到高校進行授課。招生科楊科長講道:“我們學院請民間文化傳承人到學校授課,只看其民族文化技能,而不看文憑。”*訪談人:張光紅,男,貴州大學民族學研究生,云南昭通人;被訪談人:楊莉,女,侗族,碩士生,主講西方音樂理論兼招生科科長一職;訪談時間:2015年10月20日11點20分;訪談地點:凱里學院后勤服務樓。所請文化傳承人各有特點,皆是在各自領域的代表人。如楊振平老人以吹蘆笙而聞名,吳培煥老人以高亢嘹亮的侗歌而被人熟記。民間文化傳承人是學院通過正規的文書而聘請到學校執教,學院經過探究并與其商討,進行課程和教學內容安排。這些課程最大的特點是注重實踐,在課堂上老人家會手把手的教學生唱歌和吹蘆笙等技能,并講述其歷史經歷和從祖先、長輩處傳承而來的社會知識。這些老人由于早年艱苦的社會生活和經濟條件,都沒有受過長時間的學校教育。因此,他們講課時側重自身的生活體驗,并是自己多年生活經驗所得。這樣的講課效果,往往能讓學生少走彎路,并常常觸類旁通。上課期間通過現場的反復嘗試,學生遇到問題時可以馬上請老人進行詳解。每當講完關鍵的藝術技能時,文化傳承人會讓學生不斷地練習,于下次課堂上進行表演,然后進行點評,并指出問題。民間文化傳承人開設的課程,主旨是教學生如何做、怎樣做,由于老師的生活經歷和學識背景,在這樣的課堂上主要強調實踐性。
民族文化傳承班在開設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課之時,學校也為其開設了音樂和舞蹈課程。近年來,學院從其它高校引進一批擁有高學歷的人才,為了民族歌曲擁有更廣的發展空間,許多音樂學院的老師對民族歌曲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使其音調和旋律更加的和諧,民族歌曲的聲調更加的優美,句與句的銜接更加自然和順暢。從高校而來的這批老師,更注重于理論的教導,他們會把普適性的音樂引入民族音樂之中。每當凱里學院到省會或其它地方參加比賽或演出時,如果有民族歌曲大合唱,進行理論教導的音樂老師會使用鋼琴進行配樂,使其更加的協調和通暢。把大眾的、普適性的音樂引入民族音樂之中,在不改變其本質特征的基礎之上進行相應的調整和改變,使其在適應社會需求的同時也承載了非物質文化傳承和發展的功能,這是凱里學院在民族音樂保護和發展方面取得成功的最集中體現。
(二)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于藝術學院中的調適和整合
藝術學院是凱里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主要場所之一。主要傳承的對象是蠟染和刺繡以及繪畫。蠟染古稱“蠟纈”,是我國古老的一種傳統印花方法。“纈”是染彩的意思,“蠟纈”與“絞纈”“夾纈”一起被稱為中國古代的三大防染工藝。貴州的蠟染主要流行于苗族、布依族、水族等少數民族地區,是千百年來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它歷史悠久、紋樣優美、色彩素雅、工藝考究、內涵豐富,有著較高的藝術審美價值。*龍惠敏:《貴州民間蠟染藝術特征解析》,《大舞臺》2014年第4期。凱里學院不但收集了一批蠟染珍藏于圖書館,同時也從民族地區聘請蠟染技術師到學院傳授蠟染制作技術。蠟染師通過實踐操作的方式教學生學習蠟染,在施教的過程中前者將把蠟染所蘊含的習俗、神話、生計方式等向學生一一解釋,并傳授蠟染的制作技術。當然,在傳統的蠟染中發現美麗只是蠟染藝術化和文化特征的一部分,與此伴生的另一個部分就是傳統文化的創新。*邱澤奇:《衍生于傳統的文化:以蠟染為例》,《文藝研究》2005年第4期。藝術學院學生在接受蠟染技術時,早已接受主流文化下的藝術熏陶。他們將在少數民族原有的蠟染工藝技術之上,運用現代化潮流下普適性的藝術觀對民族地區蠟染進行革新,使其具有現代性的時代特點。一位從事蠟染藝術創作的人士就曾經這樣說道:“從民間蠟染到現代藝術的轉換,不能只把蠟當作防染的掩護物質,而要拓展蠟畫的不同用蠟手法如蠟裂、蠟封、蠟點,造成畫面的力度、厚重、豐滿,缺少這些特點就失去了蠟染的藝術意義”*周世英:《從民間蠟染到現代文藝轉化中的體驗》,未刊搞。轉引自邱澤奇:《衍生于傳統的文化:以蠟染為例》,《文藝研究》2005年第4期。。當傳統的蠟染品和技術引入凱里學院,學院老師及同學在原有的特點上,把當下時代的技術和審美與蠟染融為一體,使蠟染在承擔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功能之上同時兼具有藝術價值。刺繡在凱里學院的傳承和發展狀況與蠟染具有極大的相似之處。藝術學院繪畫不僅具有現代化的普適性特點,而且必須根據民族地區的文化和生境特點,對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況、生計方式、神話故事等進行繪畫。有關民族題材的繪畫,不僅流行于課堂之上,同時遍及校園的每個角落。在凱里學院的宣傳欄、藝術學院的墻壁之處、五四廣場表演臺的墻壁上等地方繪制了大量涉及少數民族題材的繪畫,這些內容與神話、農業生產技術、農作物、生計模式、風俗習慣、民族價值觀等密切相關。就凱里學院而言,非物質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經歷了從民族地區到學院課堂再到課堂之外,其中發生的變化是依據當前社會具體生境之下而做的調適和整合。
(三)民族體育與主流體育于體育學院中的整合
民族體育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凱里學院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體育學院無疑是民族體育的主要踐行者。與全國許多地方高校相同的是,現代化潮流下大眾體育的理論知識和實踐項目仍占據著凱里學院體育學院較高課程比重,這在不同年級均有所體現,具體情況為:2015-2016年體育學院第一學期大一新生每星期課程約為30節(每節課為50分鐘),其中約十二節為體育課;大二每星期約26節,體育課約14節;大三每周約26節,至少有20節是體育課,大四每周約26節課程,體育課達20節以上。體育課主要劃分為課堂理論教學和戶外體育實踐兩大類,與其它地方高校不同的是,凱里學院體育學院在每學期的課程安排中,規定學生的選課中應有四節民族體育,這一現象持續到到大學畢業為止。*文中信息是筆者于2015年10月20日18時在大一學生張成成學弟的幫助下獲得。張成成是凱里學院體育學院學生,男,19歲,苗族,家住施秉縣,田野期間與筆者偶然相識。在他的幫助下筆者從各個年級的學生處獲得課程表,為了確保準確性,又將其與每間教室中所貼的課程表一一對照。
從體育學院每個年級的體育課程安排可知,大眾體育為主、民族體育為輔是凱里學院體育學院最為鮮明的教學特色。改革開放以來,西方體育的沖擊、社會轉型、經濟利益的驅使等因素對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許多民族地區民族體育文化逐漸失真,體育項目日漸被人忘卻。而凱里學院依托高校教育設施,將地方民族體育引入課堂,并在各個年級將民族體育作為選修課,體育項目有獨腳架、打雞毛毽、苗拳、踢草球、踢腳架、蘆笙舞、板凳舞等,可將之歸為競技、表演、歌舞、游戲四大類別,從項目內容可知引入高校的民族傳統體育日漸增多,凱里學院力圖將主流體育與民族體育于體育學院實現兩者的耦合。另外,凱里學院把部分民族體育列入選修課的課表中,這從一定的程度推廣了民族體育在學院的普及,增加學校主體對民族體育的認知和體驗,利于民族體育的進一步傳承、延續和發展。不同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反映著各個少數民族獨特的生活習慣、文化特征、道德風尚和宗教觀念。*國偉、田維華:《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和發展》,《體育學刊》2009年第9期。傳統民族體育映射著民族的傳統文化特質,民族體育的保護與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
學院在積極推動少數民族傳統體育于校內發展和延續的同時,也鼓勵學生參加各高校、各地區有關民族體育的表演和競賽等活動,一方面可促進參與者對民族傳統體育的體驗、認知,另一方面也推動了民族體育的傳播和發展,體育學院學生是民族體育活動的主要參與者。
例2:吳芮,男,22歲,苗族,貴州施秉人。現為凱里學院體育學院大三學生,因體育成績突出,熱心公眾活動,遂被班主任指定主管班級相關體育事項。在校期間因頻繁參加籃球、田徑、乒乓球等體育活動,多次獲得獎勵。與此同時,在學校的組織下他多次參與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活動,曾到劍河縣參加蘆笙舞、凱里市參與獨腳架、施秉縣參與龍舟大賽。訪談得知,2016年端午節將有一場大型龍舟比賽于施秉開展,屆時他將參與。他坦言,親身參與少數民族體育活動,有利于從大眾體育的視野下加強民族傳統體育的認識。*訪談人:張光紅,男,貴州大學民族學研究生,云南昭通人;被訪談人:吳芮,男,苗族,貴州施秉人,體育學院大三學生;訪談時間:2015年10月20日18點30分;訪談地點:凱里學院六棟宿舍樓314室。
從案例可知,凱里學院民族體育的傳承不僅于校內開展,而且還鼓勵學生于民族地區參與民族活動。在校側重于學生理論認知的培養,以西方體育為主、民族體育為輔;校外注重學生對民族體育的實踐培養,力圖以經驗獲得感知,通過此方式實現作為非遺組成部分的民族體育的傳承。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開設對學生發展和就業的影響
正如上文所言,在凱里學院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入課堂的主要踐行者有音樂學院、藝術學院和體育學院,其中音樂學院執行力度最強,體育學院相對較弱。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入課堂,一方面促進了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學生的就業選擇。
接受民族文化傳承教育的同學,只有極少部分可以繼續深造。民族文化傳承班的生源來自初中,有極少部分在高中學習一段時間后,由于學習太苦或成績太差等原因,轉而到凱里學院接受民族文化傳承的教育。這一類學生和學校其他學生最大的區別在于他們跳過高中的教育階段,依靠民族文化和時間的積累獲取大專學歷。部分學生因為擔心學位太低或想要為下一步深造做準備,將會在本校繼續讀書,以便拿取本科畢業證書。凱里學院五年制文化傳承班采取“2+2+1”的培養模式,即一、二年級以公共基礎必修課、專業基礎課、民族文化基礎課的學習為主,三、四年級以專業主修課和民族民間特色課程的學習為主。并將兩個月的教育實習改為1年的專業實習,以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就業競爭力。*張雪梅:《民族地區高校民族民間文化傳承人培養模式探討——以凱里學院民族民間文化傳承班為個案》。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學生因錯失高中而未接受的知識,但這是遠遠不夠的。當成績優異,并具有深厚民族文化知識和較強專業技能的學生想要考取研究生進行深造時,英語對他們來說無疑是一道天塹。許多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中表現突出的同學,為了獲得進一步深造的機會從而參與研究生考試,但結果往往令人遺憾且感嘆,從凱里學院得知從2012年到2015年整個音樂學院只要寥寥三人考上研究生,這三人中沒有一名來自民族文化傳承班,即使專業水平極其突出的同學也不例外。
例3:熊X,女,苗族。因在招生面試時表現出優異的苗族歌唱能力,初中畢業后被納入凱里學院民族文化傳承班。在校期間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并在學生會中鍛煉自己,成績在班上名利前茅,多次獲得國家獎學金和學院獎學金。熊X主修歌唱,多次隨同學參加大型比賽和表演,曾參加十三屆CCTV全國青年歌手大賽,并取得優異成績。大專畢業后,熊X參加專升本考試,兩年后獲得了凱里學院本科畢業證書。學院老師和領導認為她是唱歌的好苗子,鼓勵她考其它高校的研究生,學校領導承諾只要她通過筆試,面試將由學校出面,并幫她找相應的導師。然而,由于英語成績太差,致使與高校研究生失之交臂。畢業后的熊X想加入省歌舞團,但由于學歷和專業限制而不得不放棄。尋找工作期間,她發現想找到符合自己專業并讓其滿意的工作極其困難,因此最后只有在家人的安排之下進入縣城的某事業單位工作,然這份工作與自己的專業相差甚遠。
從例子可知,民族文化傳承班和民族文化引入高校課程客觀上培養了一批民族文化傳承者和弘揚者,但由于自身的缺陷限制了繼續深造的機會,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民族文化發展。當然,由于民族文化引入課堂,這使許多同學更具民族特質。部分同學畢業后,由于競爭力薄弱的緣故,往往與待遇較好、比較熱門的事業單位無緣,從而選擇崗位較多、競爭力較小的教師特崗。當這些即將成為老師的同學進入鄉鎮從事執教,由于在大學所受的專業訓練影響著他們的教學方式。并把自己所學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授給學生,這在一定的程度上促進了民族文化的發展。從中可發現,民間非物質文化傳承人進入民族地區高校傳授民族文化,接受教育的學生畢業后很多選擇回到鄉村執教,他們在高校期間所接受的民族文化將會通過課堂的平臺教授給學生。客觀上講,民族文化傳承班限制了學生的就業選擇,但從另一個角度講,這同時也是保障了學生的就業。就黔東南當下狀況而言,由于經濟狀況和交通條件的限制,許多鄉村和城鎮仍缺乏教師,而具備民族文化特性的老師進入這一地區后,不但促進了當地教育的發展,同時也能很好的融入當地社會。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入高校課程的反思及未來傳承保護路徑
在凱里學院調查期間,有幸就“少數民族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現狀”為主題對該校羅老師進行了相應訪談。在訪談期間主要涉及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引進高校的發展前景”、“怎樣實現非物質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高校和民族文化承載區域在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傳承與保護中所起作用如何”等問題。由于訪談時間有限,羅老師集中于對主要內容和問題做分析和解釋,他講到:“近些年來,許多高校紛紛參與到非物質文化傳承與保護的活動中去,不可否認的是效果是極其明顯的,就拿我們凱里學院來講,在這方面算是做的挺不錯的,可是問題也是挺多的。高校教師常常聲稱自己的研究成果將會成為政府施政的理論指導,同時也有利于推動民族文化的弘揚,總覺得這種想法有點一廂情愿嫌疑。因為我們很難確定理論在多大程度上對實踐進行指導,具體實施程度又有多大?在進行非物質文化研究時許多人強調高校所起的作用,而往往忽視了許多其它問題。如保護什么?為誰保護?誰來保護?為什么保護等?”
羅老師進一步指出:
把非物質文化引入高校中進行傳承與保護是有一定的效果,但這不是最好的方式。文化傳承與保護的最佳方式是從文化植根的土壤著手,因為在這個地方有文化的最好傳承者——文化持有主體。在高校中傳承非物質文化,有著先天的劣勢——文化與其持有主體產生了分裂。所以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要著眼點還是文化原生區。但我們必須明白,不能只談文化傳承,而不談物質,飯都吃不飽誰有心思去承擔文化傳承的義務。所以文化保護要談利益,沒有利益誰來保護,同時在發展過程中造成了生態破壞,必須進行補償。地方生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造成的生態破壞怎樣進行補償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很多時候,只有個人受益,集體才能受益,補償也是如此。*訪談人:張光紅,男,貴州大學民族學研究生,云南昭通人;被訪談人:羅康智,男,苗族,41歲,凱里學院副教授,博士,貴州天柱縣人;訪談時間:2015年10月20日16時;訪談地點:凱里學院“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編輯部副主編辦公室。
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于村落,傳承的最佳地點也在村落,所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保護傳統村落。在村落保護中可以從三個層面著手:一、組織層面。鄉村最大的困境是沒人,文化持有主體都沒了誰來保護文化,因此必須促進村落的經濟發展,使地方主體有經濟盼頭,同時地方精英應當組織群體保護固有文化。二、精神層面。非遺主要集中點在精神層面,但這有賴于物質層面的建構。三、實物層面。通過實物看文化,與非遺有關的東西必須進行保護,同時可進行展覽。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之中,我們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堅信文化創新。只有文化創新,才能延續。但不用擔心文化的普適化,因為文化因生境不同而產生差異。
[責任編輯]王霄冰
張光紅(1990-),男,云南昭通人,貴州大學人文學院民族學2014級碩士研究生。(貴州貴陽,550025)
* 本文系貴州省優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長專項資金項目“非物質文化傳承的高校實踐研究”(合同編號:黔省專合字[2011]76號);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項課題“貴州古驛道走廊民間故事流變透視多民族融合和諧之路研究”(項目編號:13BMZ038);貴州大學文科重點學科及特色學科重大科研項目:貴州的生態環境與社會發展研究(項目編號:GDZT2012005);認同與傳承:貴州施秉縣漢族山歌文化研究(項目編號:研人文2016018)的階段性成果。
G122
A
1674-0890(2017)01-0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