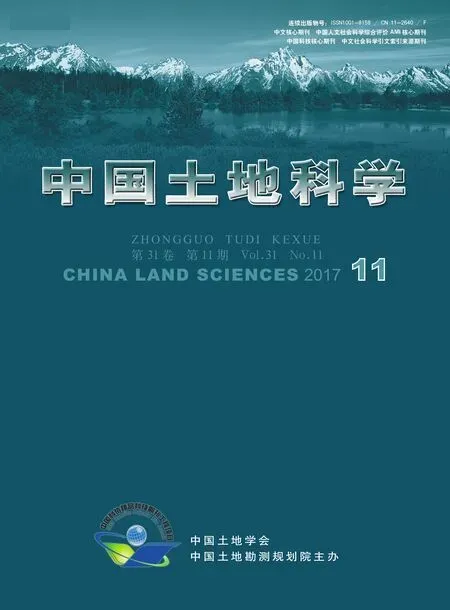基于土地發展權和合作博弈的農村土地增值收益量化分配比例研究
——來自川渝地區的樣本分析
韓 冬,韓立達,何 理,王 靜,王艷西
(1.成都理工大學管理科學學院,四川 成都 610059;2.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5)
1 問題的提出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2016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了“適當提高農民集體和個人分享的增值收益,抓緊出臺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征管辦法。”關于增值收益分配提法的變化反映了中央希望通過賦予集體和農民較完整的土地權能,使農村地區能夠參與到快速城鎮化中以解決“三農”問題的同時,還必須保障國家履行公共產品提供職責下的財政收支平衡。這種權衡極為艱難,學界關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詳細研究較少且存在激烈爭論:在分配原則上,朱一中將土地發展權分為歸屬于集體和農民、以“平均地價”衡量農地發展權和歸屬政府所有、以宗地最終市場價格與“平均地價”之差衡量的市地發展權[1];劉英博認為完整的收益權應歸屬于農地所有者,政府依據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各項投入參與分享土地增值收益[2];楊紅朝認為“公私兼顧”的增值收益分配應是農民以“小康市民”生產生活標準獲得補償,剩余歸政府用于全國“三農”事業發展與建設[3];徐美銀基于共享發展理念提出了“漲價歸民、地利共享”[4]。在分配方法上,武立永認為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使其私人成本及收益率與社會一致以防止社會階層固化和制度僵化[5];鄭雄飛對地租進行了時空解構,認為應該通過“權利再造”修復并確保農民的地租收益權[6];部分學者還通過定量方法對當前中國土地征收、增減掛鉤等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進行了實證研究[7-9]。這些研究結果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探討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依據,為未來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鋪墊了基礎,但并未提出一個較可行的量化分配方法。
通過大量的實踐調查和分析比較后,本文認為,農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是由國家與農民集體、集體內部兩層基于不同機理的關系構成:(1)農地非農化是土地增值收益的最大源泉,為保障城鄉發展一體化,兼顧效率與公平為原則,國家和集體按各自要素貢獻進行分配;(2)集體內部分配是農村土地產權關系及土地保障職能的具體表現,不僅涉及“集體產權”或“社區產權”這一類復雜概念,還延續了傳統鄉土社區中樸素的“公平分配”原則①一個最典型的例證,即在頭兩輪承包經營權發包時,即使會使可耕田地總量下降并零散細碎化,農民往往也會通過遠近搭配、肥瘦搭配等方式來保證集體內部分配的“絕對公平”。在當前的土地實踐中,受制于集體土地價格評估體系的缺失,農民也愿意且只能通過橫向對比來判斷土地非農化的收益。,在當前集體所有權主體缺位的實踐中表現出公平高于效率、集體讓利于農戶的特征。集體內部收益分配的探討必須建立在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的制度基礎之上,在此不做探討;本文著力于國家與集體分配關系的研究,力圖探索出一個實踐可行的分析視角,以土地發展權作為量化不同主體貢獻的理論工具,通過構建一個集體和政府共贏的利益聯盟合作博弈模型來兼顧公平和效率問題。
在傳統征地制度框架中,法律對集體土地發展權限制之大,形成了農民集體土地發展權被“管制性征收”②“管制性征收”是相對“有形征收”而言的,后者指永久性的物理上有形地侵入財產,即使是微小的,也要補償;而前者則是土地所有者的經濟利益被政府管制完全剝奪,從結果來看可以分為完全征收和部分征收。的事實,長期以來依據原有用途制定補償標準的結果,而在毗鄰城市中心城區的農用地收益遠低于建設用地收益,這使得農地非農化過程中集體和農民被排斥在增值收益分配之外,國家攫取了幾乎全部的土地發展權價值,形成了“土地財政”的根源,并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大量征地補償相關研究文獻對此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與積極的探討。受篇幅限制,本文僅在此闡明農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基本觀點:無論是土地征收還是入市交易,無論土地是用于公益性建設還是經營性建設,無論分配形式是征地補償還是土地增值稅制,土地原有產權主體集體及農民,應獲得與失去的土地產權最高經濟收益用途(符合分區規劃)價值相匹配的貨幣收入。本文根據博弈論分析范式從各種模式中提煉出“參與主體”、“邊際貢獻”、“投入與收益”等內容,展開關于農村土地增值收益量化分配比例的探討。
2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合作博弈模型的理論分析
2.1 合作博弈——制度均衡后的集體理性
本文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縮小征地范圍”、“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是當前中國土地制度改革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制度約束→制度均衡”的階段,利益集團已經進行了長時間、反復的非合作博弈,最終所產生的一個制度均衡安排。在接下來的“制度均衡→利潤均衡”——即本文研究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階段,重點在“支付”如何表現,并最終形成了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合作協議——農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政策中國家與集體之間的量化比例,由國家權力強制保證實施。此時,直接觀察得益空間是否符合合作博弈的根本目的,即該博弈是否能夠滿足集體理性、公平和效率、聯盟總效益最大化的要求,提供一個在現實中改進效率的可能性。
必須強調的是,本文在考察“利潤均衡”過程中相關得益空間時,是從“集體—國家”視角對利益相關者的投入、策略與支付進行合作博弈分析;但在具體實踐中,土地征收、增減掛鉤、地票交易、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交易等所對應的制度環境、實施邊界和運行規則有著極大的區別:土地征收,即私人財產權對征收權的容忍及合理補償的正當訴求,屬于國家公權力范疇中的土地行政管理,其邊界受制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及土地公有制中對城市土地所有權人的設置;增減掛鉤并未脫離土地征收制度框架,其經濟激勵受制于年度計劃指標的總量控制及增—減兩地間的土地價值差異,屬于多用途的政策工具范疇,如優化城鄉土地空間布局、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及農村土地要素規模化利用,及當前的災后重建、精準扶貧;地票交易屬于重慶市在增減掛鉤制度基礎上的獨有創新,其價格與耕地開墾費、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掛鉤①《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暫行辦法(渝府發[2008]127號)》第25、27條。,相關交易極度依賴于重慶市的房地產市場;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交易才是真正的市場行為,根據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地方實踐,主要包括城市規劃區外的存量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交易、集體內建設用地指標覆蓋、集體間建設用地指標交易三種,但由于相關法律法規并未制定,真正的邊界和規則尚待明確。這些存在于不同途徑之間和途徑內部的差異和不確定性,一方面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內容提出了差異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導致了“制度均衡→利潤均衡”中存在不同的實踐情景,在探討農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量化比例時,必須根據不同的情景進行差異化建模分析。
2.2 模型建立
本文旨在討論土地增值收益在國家和集體之間的分配,因此假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農民和農民集體的目標函數一致,分別以“國家”和“集體”參與合作博弈(圖1)中土地開發商與農民集體A是市場合約關系,不屬于利益聯盟),分為不涉及集體間土地發展權轉移的兩方聯盟(如土地征收和集體建設用地權屬交易)和三方聯盟(如增減掛鉤和集體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兩種情況。考慮到初次分配對“效率”和“公平”的同樣重視,本文選擇sharpley值法②Sharpley提出根據聯盟成員的貢獻來衡量收益在聯盟成員之中的分配思路:如果聯盟“失去”該成員,那么對聯盟收益所帶來的邊際損失可以視為該成員的貢獻。這種思想從功利主義公平的視角體現了聯盟內部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有助于聯盟長期穩定的促進。求合作博弈的解,其大聯盟收益將按下式的Sharpley值進行分配。

圖1 傳統土地市場(上,以傳統征地及增減掛鉤為代表)及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下)中土地發展權及價值轉移示意圖①筆者認為農地發展權應是一種歸屬于集體的物權,但被國家的土地規劃權及用途管制所約束;由于土地的位置固定性,其所承載的物權是不能空間轉移的,因此交易的指標本身并不是土地發展權,而是一種“物權取得(轉移)權”,是農民集體被約束的“土地發展權”能夠釋放的權利表達。本文正文所述集體間發展權轉移是沿用美國的學術用語“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Fig.1 The diagram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 and value transfer in traditional land market and an integrated urban-rural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式(1)中,s表示聯盟S中參與者的個數。可以看出,局中人i參與到聯盟S中貢獻的匹配期望收益就是Sharpley值φi(V)。表1為變量及參量的約定。①
情景1:農民集體A的存量集體建設用地滿足交易,國家通過征收土地發展稅(增值收益調節金),使其進入城鄉建設用地市場進行交易。在這一博弈中,局中人集合為N = (1,2),局中人1農民集體A的策略向量為(0,IA1),局中人2政府的策略向量為(0,IG),定義其特征函數如下:
(1)V(1) = γIA1,在不向國家繳納土地發展稅的前提下,農民集體A受制于土地用途管制,只能將集體建設用地用于政策許可下的常規用途開發(下同),當前主要有農家樂、民宿、作坊等不涉及住宅地產開發的利用方式;
(2)V(2) = r1IG,即以稅收為主要渠道的政府財政收入增長情況;
(3)V(1,2)=At(IA1+ IG) - IA1,即繳納發展稅并在國家監管下,農民集體A將存量土地投于土地市場交易(或直接按規劃最高收益用途開發)獲得的增值收益,可以得到:

表1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合作博弈中對變量及參量的約定Tab.1 The variables and parameters of the cooperative game on land incremental revenue distribution

情景2:農民集體A的存量土地不足,通過自身建設用地整理滿足需求。在這一博弈中,局中人集合為N =(1,2),局中人1農民集體A的策略向量為(0,IA1+ IA2),局中人2國家的策略向量為(0,IG),定義其特征函數如下:
(1)V(1) = γIA1+ rIA2,即不通過政府規劃許可,農民集體A無法通過建設用地整理獲取新增集體建設用地,只能將存量建設用地用于常規用途開發,農用地維持原狀;
(2)V(2) = r1IG,即政府財政用于非土地項目時收支的增長情況;
(3)V(1,2) = At(IA1+ IA2+ IG) - xA2CR- xA1CA- xA2RA,即在政府監管下,農民集體A通過宅基地整理后將足量經營性土地投于土地市場交易(或直接按規劃最高收益用途開發),可以得到:

情景3:農民集體A的存量土地不足,需要在指標市場上向農民集體B購買指標將部分農用地轉為集體建設用地才能發生情景1。在這一博弈中,局中人集合為N = (1,2,3),局中人1農民集體A的策略向量為(0,IA1+ IA2),局中人2國家的策略向量為(0,IG+ IR),局中人3農民集體B的策略向量為(0,IB),其特征函數如下:
(1)V(1) = γIA1+ rIA2;
(2)V(2) = r1(IG+ IR);
(3)V(3) =rIB2,西南地區遠郊集體農用地和建設用地收益率有相同的收益率在當前中國是個合理的近似;
(4)V(1,2) =μAt(IA1+IG) -IA1+rIA2+r1IR,即包括次高收益用途下集體建設用地開發收益、農用地的正常收益及未投入的準備金正常增長部分;
(5)V(1,3) =γIA1+rIA2+rIB2,沒有國家參與,集體土地只能維持原用途;
(6)V(2,3) = -xBCR-IB,沒有農民集體A這一價值泉源,國家以財政兜底了整理成本并保護價庫指標,農民集體B的建設用地資產下降;
(7)V(1,2,3) =At(IA1+IA2+IG) +r1IR-xBCR-IB-xA1CA-xA2RA,通過購買指標,農民集體A將xA1+xA2的建設用地入市交易。
由以上研究可以發現,V(1,2)和V(1,2,3)均可能成為最優結果。但考慮到土地利用的規模效應,當μ遠小于1時,V(1,2,3)是博弈最理想的結果(部分項目中μ甚至為0)。由于地價可視為地租的資本化,因此可以得到:

式(4)滿足φ1(V) +φ2(V) +φ2(V) =V(1,2,3),各主體的增值收益分配率為:

3 模型數據來源、計算結果及分析
3.1 調研項目概述及數據說明
本文選擇筆者所在課題組于2011—2016年在成都、自貢、重慶三市調研的不同區位的增減掛鉤、地票交易、集體建設用地流轉項目①根據《土地管理法》對土地征收補償的規定,農民并未參與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中,因此本文沒有選擇土地征收案例的相關數據。的相關數據來探討農村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量化比例問題。成都市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從“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農村產權改革和用統籌城鄉的思路推進災后重建”進行了探索:邛崍高何鎮、新津興義鎮以跨縣和本縣的增減掛鉤為平臺進行災后重建建設;郫縣古城鎮、彭州丹景山鎮是普通的增減掛鉤項目,以實現農民集中安置和農村土地空間優化;邛崍羊安鎮、青白江福洪鎮、郫縣花園鎮是地區新增建設用地年度計劃指標的限制,只能通過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和增減掛鉤方式獲得產業發展所需的建設用地。自貢市于2013年成為全國唯一深化改革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市,打破了“縣內捆綁”的項目區設置,中心4城區、榮縣、富順縣可分別在區域內跨行政區域設置掛鉤試點區,按“預先安排、到期歸還、動態使用”的原則分配掛鉤指標。重慶市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直轄市,地票可在全市范圍內使用,以農民市民化過程中所減少的農村建設用地為主要來源。從土地發展權實踐出發,三市案例具有鮮明的代表性,因此以“異地掛鉤”、“縣內掛鉤”、“本地開發”進行分類并展開討論。
模型所需參數取值在表1基礎上進行設置:集體建設用發展權價值潛力按所在鎮(鄉)2011—2015年國有建設用地出讓樣本均價②本文通過成都市國土局及中國房地產信息網公布內容對成都(除中心5城區及高新區)、自貢(自流井、貢井、沿灘、大安)、重慶三地2011—2015年間住宅、商服用建設用地出讓情況進行了采樣,其中成都797宗、自貢109宗、重慶314宗,盡可能保證每個鎮級行政區一宗地的覆蓋度。算;西南農村地區尚未執行區片綜合地價,因此假設一個農村集體土地基準地價變量CA;銀行利率按2013年1年定期利率3.25%算,國債利率取2013年5年利率5.41%,所有項目周期均設1年;準備金率按2012年5月12日調整后大型金融機構20%算,基數取各地指標整理成本即IR=xBCR。本次分析中忽略了通貨膨脹、利率浮動、供需變化等環境因素,組織成本和交易成本等費用全部納入資本投入之中,因此不對誤差項進行討論。樣本區位及模型所用數值如表2,模型計算結果見表3。①②③由于樣本統計中郫縣花園鎮、青白江福洪鎮無出讓數據,根據實地調研,分別選擇經濟水平和區位條件近似、地價基本吻合的溫江區壽安鎮、新都區石板灘鎮的數據為參照。

表2 土地收益分配項目樣本數值一覽表 單位:畝,104元/畝Tab.2 The sample values of land revenue distribution unit: mu,104yuan/mu

表3 不同μ值時各主體分配比例范圍Tab.3 The range of distribution proportion of various subjects at differents μ values
3.2 模型分析及結果討論
3.2.1 模型分析 該模型中假設了4個主要影響變量:(1)IG:與項目區相關公共產品及服務的政府支出,是農地非農化中土地價值增值的主要影響因素;(2)γ和CA:近郊集體建設用地的土地收益率和基準地價,共同描述了集體建設用地的土地資產屬性,可近似認為CA~γRA/r2①產權還原法中集體建設用地基準地價估值公式為CA≈RC/r,集體建設用地地租RC = γRA/r,因此CA≈γRA/r2,RA可視為常量。;(3)μ:描述土地不同用途的收益差異,主要受制于土地規劃、土地市場的所有權差異及土地開發的規模效應。根據模型計算結果中變量的多少和分配主體的多少,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分為以下4類(由于本文調查的川渝地區沒有完全通過存量建設用地滿足用地需求的情況,因此未將情境1納入計算)。
第一類,項目8和9,滿足情境2,農民集體A投入新增建設用地進行經營性建設開發即xA1= 0,xB= 0,此時分配比例僅與國家的公共投入有關。考慮投資的乘數效應,單位面積投資如果超過土地價值增值可視為低效投資,近似認為IG的有效閾值是兩者分別為3474×104元、25758×104元。隨著國家公共投入的增加,農民資本A的分配比例線性下降,國家的分配比例線性上升。
第二類,項目7,滿足情境2,農民集體A同時投入了存量建設用地和新增建設用地用于經營性建設開發,此時分配比例同時受制于國家的公共投入、集體建設用地資產屬性及不同用途的收益差異。IG的有效閾值為,此時收益比例變化如圖2。
第三類,項目2、3、4,滿足情境3,農民集體A并無任何存量建設用地,必須向農民集體B購買建設用地指標以滿足最高經濟收益用途的建設開發需求,收益分配只與國家的公共投入有關,三者IG的有效閾值分別為358637×104元、11426×104元、153122×104元。
第四類,項目1、5、6,滿足情境3,農民集體A投入了存量建設用地并通過向農民集體B購買建設用地指標來滿足建設開發用地需求,很明顯,μ越大,收益分配越向農民集體A和國家傾斜。三者IG的有效閾值設為185651×104元、81989×104元、23540×104元,集體建設用地收益率取值范圍分別為(0,0.908]、(0,0.459]、(0,0.67]。此時三者收益分配變化如圖3(僅以μ取0.5時項目1為例)。
3.2.2 結果討論

圖2 項目7中農民集體A和國家收益分配比例變化Fig.2 Revenue distribution ratio between the collective A and the state in project No.7
(1)在只涉及單一農民集體和國家的收益分配項目中,農民集體收益率均約在40%—55%之間;而在現行征地制度框架中,農民集體只能獲取基于農地價值IA2的征地補償,即收益率僅為5% —10%。由此可以看出,通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集體土地財產權益得到更大的保障;另一個方面也反映了現行征地補償標準不符合市場配置精神,收益分配機制極大的扭向高談判勢力一方,這是未來征地制度改革的關鍵之一。

圖3 項目1中農民集體A、國家、農民集體B收益分配比例變化μ = 0.5Fig.3 Revenue distribution ratio among the collective A, the state and the collective B in project No.1
(2)模型分析中,項目3中農民集體A收益始終超過100%,國家和農民集體B的分配比例始終小于零;項目6中國家分配比例存在負的最小值,農民集體A的最大收益超過100%。分析結果顯示,這種農民集體A獲取超過100%增值收益率和國家負的收益率主要原因是A、B兩地地價差距不大,土地發展權轉移的內生價值不足以抵消項目的搬遷安置成本和工程成本,導致國家及農民集體B要承擔更多的成本①當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部分為負的實踐表現有二:一是農民需要承擔一定的建房安置成本(往往在參與項目時便需要繳納相當的保證金),在成都、自貢兩市的常規增減掛鉤項目(即縣內捆綁)中普遍存在;二是由政府財政兜底項目成本,筆者在成都近郊的部分集體建設用地流轉(農民集中建房)項目調研中了解到這種情況。。在此基礎上,農民集體A存量建設用地的地價和收益率越高,國家和農民集體B的收益率越低;若國家有準備金制度,則指標整理成本越高,農民集體B的收益率越有保障,但為國家帶來更低的收益率。應注意,農民集體B土地發展權損益大小在指標交易中對收益率的貢獻并不高,在本分配方法中難以體現。
(3)在除去項目3、6的涉及土地發展權轉移的項目中,農民集體A依靠高貢獻率保持了大于40%的分配率,其最大值逼近了60%;國家通過財政投入顯化城市化對項目區域的正面影響,為政府在土地增值收益中占據份額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使其收益分配率從10%左右的極小值上漲到了30%—35%;農民集體B的土地發展權轉移則是農民集體A土地開發的必備條件,由此享有較為穩定的20%—30%的收益分配率。在此基礎上,隨著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中集體經營性土地和國有土地同權同價,μ趨近于1,農民集體A和國家的收益分配還有小幅度(5%左右)提高,這使得農民集體B的收益率維持在20%左右。可以預見,若中國建立類似于美國的土地發展權轉移市場,其指標整理項目必然先從地價低廉的邊遠區縣市開始,逐漸向地價遞增的近郊地區發展。
(4)對分析結論取中間值,可以認為,不涉及土地發展權轉移的集體—國家分配率大致在50∶50(%),視集體存量建設用地資產投入和國家的區域公共財政支出多少發生幅度在10%之內的波動;當涉及土地發展權轉移,農民集體A、國家、農民集體B之間的一個較為合理的收益分配比例在45∶30∶25(%)左右,綜合考察農民集體A的存量建設用地資產、國家在兩地的公共財政支出、農民集體B的土地發展權損益量,這一比例發生幅度在5%之內的波動。結合當前西南地區(以成都市為主)對集體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增減掛鉤周轉指標的價格設定和接受程度,本文采用合作博弈的收益分配模型在當前的地方實踐中是可行的。在該模型下,各利益集團的分配依據是邊際貢獻率而非實際貢獻率,由此保證了政府不會因大量的公共財政開支對城市化的影響而占據極大的份額,農民集體B通過發展權轉移的指標交易獲取了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的資金而未加重自身負擔,從而基本維護了社會公平的實現。
4 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結果,若不存在集體間土地發展權轉移,“農民集體—國家”兩方聯盟的收益分配比例在[40∶60,60∶40]之間;若存在集體間土地發展權轉移,則轉移的集體所在兩地土地增值空間應具有較大差距,否則會給國家和轉出方造成較大負擔;農民集體A—國家—農民集體B三方聯盟的收益分配比例在40—50∶25—35∶20—30區間內是一個較合理的范圍。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就是,由于農民集體B的土地發展權潛力損益是一個預期值,很難在追求效率的本分配方案中得以體現,因此在執行土地發展權轉移時不應單純以指標整理成本作為發展權價值的評估標準而需要從社會角度綜合考察。本文提出的收益分配比例不僅僅能夠幫助制定新的征地補償標準及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還具有以下政策含義:
第一,在18億畝耕地紅線及集體建設用地零碎的現實下,通過土地權屬調整及集體間土地發展權轉移的形式滿足城鎮建設用地需求已成為一種趨勢,然而若項目拆舊區和建新區地價差異不大(這往往是由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縣內綁定”反而會加重地方政府和農民的負擔,為了提供足夠的經濟激勵,集體間土地發展權轉移的范圍擴大是一種必然,如災后重建、扶貧搬遷等項目中周轉范圍擴大到了市域和省域。
第二,本文通過實地調研及統計數據收集來確保案例數據的準確性,但由于調研區域的增減掛鉤指標、地票指標大部分由土地儲備中心回購并統籌使用,在估測近郊土地開發的增值收益及遠郊集體建設用地整理造成的發展權損益只得使用一個較大范圍的平均地價作為衡量標準,必然導致最終結果存在一定誤差。因此,構建科學的農村土地要素價格評估機制和信息平臺顯得極為緊迫。
第三,從維護農民土地權益出發,征地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環節在于清晰界定公共利益以及構建市場化的補償標準,并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作為補充。但在現行征地制度下,為了維護失地農民的權益,采取40%—60%土地最優利用途徑市場價格作為最終補償是一個可選的科學方案。
(
):
[1] 朱一中,曹裕. 農地非農化過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基于土地發展權的視角[J] . 經濟地理,2012,3(210):133 -138.
[2] 劉英博. 集體土地增值收益權歸屬的分析與重構[J] . 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6(43):43 - 46.
[3] 楊紅朝. 論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制度保障[J] . 農村經濟,2015,3(34):30 - 34.
[4] 徐美銀. 共享發展理念下農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研究[J] . 中州學刊,2016,3(89):33 - 38.
[5] 武立永. 農民公平分享農村土地增值收益的效率和正義[J] . 農村經濟,2014,3(24):35 - 40.
[6] 鄭雄飛. 地租的時空解構與權利再生產——農村土地“非農化”增值收益分配機制探索[J] . 社會學研究,2017,32(4):70 -93,243 - 244.
[7] 林瑞瑞,朱道林,劉晶,等. 土地增值產生環節及收益分配關系研究[J] . 中國土地科學,2013,2(72):3 - 8.
[8] 何芳,王小川,張皓. 基于Bootstrap與神經網絡模型的浦東新區土地收儲增值收益分配研究[J] . 管理評論,2015,2(712):57 -64.
[9] 張傳偉,石常英. 增減掛鉤中增值收益分配研究——以遼寧省大洼縣為例[J] . 中國土地,2014,3(311):13 - 15.
[10] 李志明. 空間、權力與反抗——城中村違法建筑的空間政治解析[M] . 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55,97.
[11] 皮特. 誰是中國土地的擁有者?:制度變遷、產權和社會沖突[M] . 林韻然,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52.
[12] 高潔,廖長林. 英、美、法土地發展權制度對我國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啟示[J] .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27(4):206 - 213.
[13] Leonie B. J. Space for space, a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initiative for changing the dutch landscape[J] .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8,87(6):192 - 200.
[14] Shapley L S. A value for n-person games[A] . Kuhn, Tucker.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Games[M]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307 - 317.
[15] Srinagesh Gavirneni, Benefits of co-operation in a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nvironment[J] .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1,(13):612 - 622.
[16] Andrew J. Plantinga, Douglas J. Miller. Agricultural Land Values and the Value of Rights to Future Land Development[J] . Land Economics,2001,77(1):56 - 67.
[17] Oliver E. Williamso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How It Works; Where It Is Headed[J] . DEEconomist,1998,146(1):23 -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