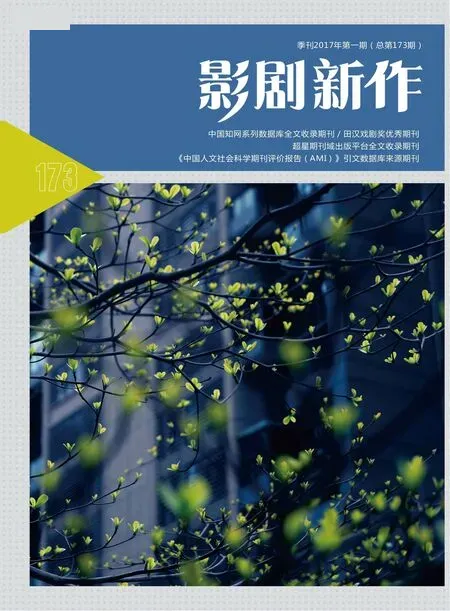《牡丹亭還魂記》與《西廂記》之比較研究
蘇子裕
《牡丹亭還魂記》與《西廂記》之比較研究
蘇子裕
元代王實甫的《西廂記》和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是中國戲曲史上兩座聳立的豐碑,在戲曲舞臺上一直盛演不衰。兩相比較:同是愛情的頌歌,但主題思想開掘的深度不同;主要人物配置基本相同,但性格特征有所不同;都是悲歡離合的故事,但戲劇結構和舞臺表現大不相同。二者各有千秋,但從總體上來說,《牡丹亭》略勝一籌。
牡丹亭 西廂記 比較研究
元明時期,作家迭起,劇作如林。表現青年男女追求愛情、婚姻自主一類題材的劇本,占有很大比重。其中,元代王實甫的雜劇《西廂記》和晚明湯顯祖的傳奇《牡丹亭還魂記》(以下簡稱《牡丹亭》)是冠絕一代的代表作,而且一直在舞臺上盛演不衰。對這兩部代表時代水準、充滿藝術魅力、永葆藝術青春的古典愛情戲曲作品進行比較研究,應當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這兩部劇作,明清曲家多有比較。明沈德符《顧曲雜言·填詞名手》記載:“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1]明張琦《衡曲麈談·作家偶評》云:“臨川學士旗鼓詞壇,今玉茗堂諸曲爭膾人口。其最者《杜麗娘》一劇,上薄風騷,下奪屈宋,可與實甫《西廂》交勝。”[2]湯顯祖的好友、戲曲家鄒迪光《湯義仍先生傳》認為:“公又以其余緒為傳奇,若《紫簫》、《二夢》、《還魂》諸劇,實駕元人而上”。這“元人”之中,當然也包括王實甫《西廂記》。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浙江錢塘人林以寧為《吳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還魂記》所作《還魂記題序》一文,則貶《西廂》,而高度贊揚《還魂記》:
君子為政,誠欲移風易俗,則必自刪正傳奇始矣。若《西廂》者,所當首禁者也。予持此說已久。……今玉茗《還魂記》,其禪理文訣,遠駕《西廂》之上,而奇文雋味,真足益人神智,風雅之儔所當耽玩,此可以毀元稹、董、王之作者也。書初出時,文人學士案頭無不置一冊,惟庸下伶人,或嫌其難歌。究之善謳者,愈增韻折也。
林以寧對《西廂》的評價雖然有失公允,但對《牡丹亭》的評價卻不無道理。
從上述明清兩代《牡丹亭》與《西廂記》的評價看來,筆者以為,說《還魂記》“可與實甫《西廂》交勝”、“幾令《西廂》減價”,這是毫無疑義的。說“遠駕《西廂》之上”,或許有點偏激,但從總體上來比較,湯顯祖《牡丹亭》的“禪理文訣”(即思想意義和藝術成就)確實是高于王實甫《西廂記》的。畢竟戲曲倚時而運,處于戲曲成熟期的明傳奇與處于戲曲成長期的元雜劇相比,當然會更完美一些。更何況《牡丹亭》是出自湯顯祖這樣的曠世奇才之手,即使在明傳奇之中,《牡丹亭》也堪稱標幟。
一、同是愛情的頌歌但主題思想開掘的深度不同
《牡丹亭》與《西廂記》都是謳歌男女青年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追求婚姻自主的斗爭精神。這兩部劇作以其強烈的戰斗性、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藝術性,對后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對封建社會起了很大的沖擊作用。把它們比作元明時期戲劇創作領域中兩座并歭的高峰,也不為過分。明末毛晉《六十種曲》所輯刻劇本皆為傳奇,收入的元雜劇劇本唯獨只有王實甫《西廂記》。該劇被收入“演劇二套”。有意思的是“演劇二套”所輯十種劇本中,頭一種為《南西廂》,最后五種即為湯顯祖“四夢”和《北西廂》。中華書局排印本就把這五個劇本編為第四冊。當然,我們不能僅僅以此認定,毛晉把《北西廂》與“四夢”等量齊觀,但在讀者方面,難免會產生諸如此類的印象。
《西廂記》的主題思想,在其最后一折【清江引】的唱詞表達得很清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牡丹亭》也是這一類的主題思想,但開掘的更深,這便是湯顯祖在《牡丹亭·題詞》中所表達的“情至說”: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杜如麗娘者乎?夢其人則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3]
這段文字說明湯顯祖的藝術哲學就是以“情至”為核心的,也就是前引林以寧《還魂記題序》所說的,湯顯祖“遠駕《西廂》之上”的 “禪理文訣”。湯顯祖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戲劇,萬歷四十二年(1614),久病體衰的湯顯祖,在《續棲賢蓮社求友文》中說:“吾猶在此為情作使,劬于伎劇”。他寫戲,是“為情作使”。而“情不知所起”,貴在“一往而深”。真愛深情是是可以超越時空、不可阻擋的,因而“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這在晚明社會的思想界、文化界,無疑是石破天驚之響,驚世駭俗之論。這是對封建禮教的戰斗檄文,必然會受到封建衛道士的激烈反撲。對這一點,湯顯祖是有足夠的思想準備的。所以,在其《題詞》最后部分寫下了如下一段話: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4]
顯而易見,湯顯祖的“情至論”是針對封建社會的“理學”而言的。
必須指出的是,湯顯祖的“情至論”,并不是“唯情說”。“情不知所起”,是因為“人生而有情”(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人之“情”既是與生俱來的,也是人生經歷中不斷萌動、激發和培育而成的。湯顯祖的“情至論”是以其藝術創作的“情境論”相表里的。他在《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就說過人世間 “緣境起情,因情作境”。這些在《牡丹亭》一劇中都得到了充分、完美的展現。湯顯祖的“情至”論,是對我國傳統美學的革新,它不把戲曲當作宣泄個人情感的工具,十分注重戲曲的社會功能:“以人情之大竇,為名教之至樂” (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因此湯顯祖的 “情至” 論,在我國戲曲發展史、文學發展史、美學發展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西廂記》、《牡丹亭》的主題都是“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兩者都是以情格理,但《牡丹亭》則在此基礎上著重表現出“情至”的思想光輝,當然比《西廂記》更加燦爛、深刻。
二、主要人物配置基本相同但個性特征有所不同
《西廂記》的女主角崔鶯鶯和《牡丹亭》的女主角杜麗娘都是官宦后裔,年輕貌美,知書達理。
《西廂記》的男主角張珙和《牡丹亭》的男主角柳夢梅都是名門后裔、滿腹經綸的才子,因家道中落,功名未遂,懷才不遇。張則書劍漂零,漂流四方,杜則“寄食園公”。
兩劇男女主角追求婚姻自主,受到女方長輩的極力反對。作為主要對立面的人物,《西廂記》中是崔母老夫人,《牡丹亭》中是杜寶。
兩劇中都有一個“串戲”的丫環,即紅娘和春香。她們都站在女主角一邊,同情和支持女主角。
兩劇中身份相同的人物性格有較多相似之處,但又各具個性特征。
(一)崔鶯鶯與杜麗娘
崔鶯鶯與杜麗娘都是我國古代官宦之家的窈窕淑女,追求純真的愛情,她們都渴望能找到一個至誠君子、如意郎君作為終身伴侶。她們在封建禮教的束縛下,身心不得自由,深閨之中,愁緒萬端。一旦在外界環境的影響下,立即會產生春情的萌動和追求愛情的沖動,最后走上與傳統觀念決裂、離經叛道的抗爭道路。但同樣是抗爭,崔鶯鶯與杜麗娘的行動,卻有所不同,體現了各自的個性特征。
崔鶯鶯是北方女子,開朗、大膽、敢作敢為,表達感情更為直率、熾烈。在第一本第三折,聽見張生吟詩,便立即依韻酬和:“蘭閨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當孫飛虎兵圍白馬寺要擄掠鶯鶯為壓寨夫人,鶯鶯挺身而出,建言與殺退賊兵者結為秦晉,以救母親及寺內眾人。當張生說有退兵之策時,鶯鶯暗喜:“則愿得筆尖兒橫掃了五千人”(第二本第一折)。張生請杜確退兵之后,老夫人賴婚,張生相思得病,崔鶯鶯為其深情所感動,亦為本人情思所熬煎,加上對母親食言賴婚的強烈不滿,幾度躊躇,終于邁出了關鍵的一步,與張生私會,得就枕席之歡。斯時斯境的崔鶯鶯能走出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這是真愛摯情的圣火燭照下的強力抗爭。但她的性格中另有相矛盾的另一面:由于受封建禮教的束縛,她在追求婚姻自主的抗爭中也是步履蹣跚,在私會之前便有“鬧簡”、“賴簡”的舉動,使張生對其捉摸不定,內心備受煎熬。她更具有賢淑女子的善良秉性,溫存體貼、柔情萬種,這在第三本第三折長亭送別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她對張生能否做官并不感興趣,反而怨恨“蝸角虛名。蠅頭微利,拆鴛鴦在兩下里”,“但得一個并蒂蓮,煞強如狀元及第”。當張生得中探花郎之后,修書回家,鶯鶯既惦念張生,又恐其不念舊,便修書一封,又要琴童捎去物品,件件物品寄托著她的思念。這種擔心和思念竟使她“到如今悔教夫婿覓封侯”(第五本第一折)。這些都從不同的側面塑造出崔鶯鶯“這一個”真實鮮活、光彩照人的美好形象。
西蜀女子杜麗娘則性格更為內向,她在言情作品的熏陶下,在嫵媚春光的撫觸下,產生了浩蕩的春情,但她無法向人訴說,也無法排遣,只有將深情掩藏在心中,默默地淘挖著自己的五臟六腑,用生命譜寫了一首郁悶、凄婉、哀傷的癡情之歌。她的性格和所處環境決定了她悲劇的人生,就這一點來說,崔鶯鶯比杜麗娘要幸運得多。
但杜麗娘骨子里卻具有強烈的叛逆性,這是她追求人間至情所鑄就的。湯顯祖神筆生花地為杜麗娘編織了一幅色彩絢麗、氣勢恢宏的尋愛抗爭圖。
她的抗爭是在夢中,她“一生兒愛好是天然”,因游園,見“裊晴絲吹來閑庭院”, “姹紫嫣紅開遍”,便感嘆“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她對自己未能早成佳配,感到虛度青春,覺得“春色惱人”,“沒亂里春情難遣”,于是便因情入夢,因夢癡情,傷情而亡,因情復生。
她的抗爭是在內心:“這般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愿,便酸酸楚楚無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的個梅根相見”。
她的抗爭是在陰間,她敢于在判官面前慷慨陳詞,理直氣壯地敘說自己傷情而亡的經歷。她魂游牡丹亭,為自己“只為癡情慕色,一夢而亡”的身世,十分感傷:“昔日千金小姐,今日水流花謝,……生生死死為情多,奈情何”。她與柳夢梅“幽媾”、“冥誓”:“生同室,死同穴。口不心齊,壽隨香滅”。
她的抗爭更表現在還陽后。她竟敢在皇帝面前照實陳述傷春而亡復又還陽、自媒自婚的經過。當杜寶斥責她說:“鬼也邪,怕沒門當戶對,看上柳夢梅什么來?”她反唇相譏:“人家白日里高結彩樓,招不出個官婿。你女兒睡夢里,鬼窟里,選著各狀元郎,還說門當戶對!”杜寶不認麗娘,說“離異了柳夢梅,回去認你時”,她堅決而又滿懷憤懣地哭訴:“叫俺回杜家,赸了柳衙。便作你杜鵑花也叫不轉子歸紅淚灑”。在全劇結尾處,湯顯祖翻造了《西廂記》“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唱詞,變為杜麗娘唱的“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誰似咱?”這就再一次點題:“生生死死為情多,奈情何”,真正的愛情是千古不朽的。
崔鶯鶯與杜麗娘對愛情都是堅貞不渝的。但杜麗娘有還魂的經歷,湯顯祖為其安排的場次較多,人物的行動和內心活動的刻畫較多,所以顯得尤其感人。
(二)張君瑞與柳夢梅
兩人都是名門之后,才華過人。他們的戀愛過程都是由慕色而癡情,勇敢地追求愛情。但這兩個人物形象,在性格上有差異,在塑造手法上有不同。
張君瑞漂游四方,在功名上并不順心,這當然與元代社會漢族讀書人的狀況與心態有關:“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兒愿”。他遇見鶯鶯,一見鐘情,便不想赴京應試。他忠于愛情,如癡如狂;白馬解圍,急人所難;被逼應試,仍然有“都只為一官半職,阻隔得千山萬水”的悵恨,高中狀元之后,連忙修書告知鶯鶯,免其憂憶。《西廂記》成功地塑造了這樣一個至誠男子的形象。
湯顯祖筆下的柳夢梅,實際是一個理想化的藝術形象。但歷來的評論對柳夢梅這一人物評價還不到位,多數把他當作杜麗娘的陪襯。有的論文對杜寶、陳最良、胡判官等人物形象都有分析,唯獨對柳夢梅只字不提,這就很不公平了。其實,柳夢梅在劇中的作用非同小可。他與張生一樣是個懷才不遇的窮秀才,他靠園公養活,得友人資助才能赴京趕考。染病借住南安府梅花觀,在太湖石下拾得杜麗娘自畫像,“早晚玩之、拜之、叫之、贊之”:“小娘子畫似崔徽,詩如蘇蕙,行書逼真魏夫人,小子雖則通雅,怎到得這小娘子”,由慕色、慕才而癡情,所以他對杜麗娘的愛情,不是一般的“慕色”,而是在仰慕之中含有敬重。正因為如此,他才會與杜麗娘的鬼魂“幽媾”“冥誓”,甚至不顧觸犯律條,開棺讓杜麗娘還魂,二人結為夫妻。天下男子若此癡情者鮮矣!杜麗娘傷春而亡,柳夢梅與“鬼”成親,這都是“情至”所致。實際上“還魂”及以后的重場戲,以柳夢梅為主,《鬧宴》《硬拷》《園駕》等出,“是斯文倒吃盡斯文苦,無情棒打多情種”,都是表現柳夢梅不屈服于權貴杜寶的淫威和世俗的偏見,矢志不移地捍衛自己的愛情和自由。
有的批評家對柳夢梅追求功名頗有微詞,認為這是封建知識分子的可悲之處,使其藝術形象有所減損。我覺得,這個問題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來看待。封建社會的讀書人,十年寒窗,懸梁刺股,無不不盼望金榜題名,得中高官。正像如今的莘莘學子,那個不想考個重點名校,讀碩、讀博,而后找個或權高位重、或收入頗豐的工作崗位。有何可悲之處?我覺得,湯顯祖恰恰在柳夢梅身上寄寓了自己未曾實現的政治抱負。在第四十一出中《耽試》中,柳夢梅赴考,對考官苗舜賓面陳對付金兵的“和戰守”之策。苗考官連聲贊道:“高見!高見!”并說:“似你阿,三分話點破帝王憂,萬言策撿盡乾坤漏。”這就不免使人聯想到湯顯祖本人中舉之后,滿懷濟世經邦之志,自謂“歷落在世事,慷慨趨王術。神州雖大局,數著亦可畢”(湯詩《三十七》)。自然也使人聯想到明萬歷十九年(1591)湯顯祖上奏《論輔臣科臣疏》的激昂慷慨之狀。柳夢梅關心國事,以天下為己任,是國家的棟梁之材。這樣的精英不參加科考,怎么能脫穎而出、為世所用呢?
張珙的摯誠使其矢志不渝、相思成病、不離不棄;而柳夢梅的摯愛使其超越陰陽、與鬼魂廝守、并掘墳使杜麗娘重返人間,需要極大的勇氣。可以說,柳夢梅在追求愛情的過程中付出了常人所難以做到的努力與抗爭。這是“至情”帶來的動力。
(三)紅娘與春香
紅娘與春香都是官宦家中的貼身丫環,機敏、活潑的天性,愛憎分明的個性,是其共有的特征。她們都是劇中穿針引線的重要配角。但春香在杜麗娘死后就沒有多少戲了。而紅娘則貫穿始終,并在戲劇沖突的高潮中起了關鍵作用,尤其是在《拷紅》一折中,把一個是非分明、俠肝義膽的青年女子形象塑造得有聲有色、栩栩如生。如果說崔鶯鶯的純情感動人心,而紅娘的機智、聰慧和敢作敢為卻更充滿活力,充分體現了戲曲愉悅人心的功能。我以為,紅娘是《西廂記》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戲劇性的人物形象。后來的京劇及許多地方劇種演出的是根據《西廂記》改編而成的《紅娘》,把紅娘當作主角。紅娘是戲曲史上最富于人民性的藝術形象之一。金圣嘆在《第六才子書批語》中說:
《西廂記》只為要寫此一個人(筆者按:即崔鶯鶯,亦即下文所說的“雙文”),便不得不又寫一個人。一個人者,紅娘是也。若使不寫紅娘,卻如何寫雙文?然則從《西廂記》寫紅娘,當知正是出力寫雙文。
金氏的批語,別具慧眼。紅娘是崔鶯鶯的貼身丫鬟,也是知音。實際上紅娘在劇中的重要言行都有鶯鶯的投影。尤其是在《拷紅》一折中面對老夫人的問罪,她振振有詞,針鋒相對:“非是張生小姐紅娘之罪,乃夫人之過也”,直言不諱地批評老夫人背信棄義的行為,陳說悔婚的弊端,致使老夫人啞口無言,覺得“這小賤人也道得是”,只得答應了這門親事,允許張生取得功名后成親。其實,紅娘的這一番話,也是鶯鶯所想說而又不便說的,借紅娘之口說出,更覺合情合理。紅娘這一人物的塑造,與崔鶯鶯的形象合璧生輝。
(四) 老夫人與杜寶
這兩個人物都是封建禮教的衛道者。是劇中男女主人公的對立面。
老夫人有濃厚的門閥觀念,兒女婚嫁講究的是門當戶對,瞧不起家道中落的窮秀才張生,所以在白馬解圍之后,食言悔婚,企圖拆散崔、張二人婚事,只是因為崔、張私會,木已成舟,在紅娘曉以利害的情況下才不得已同意二人婚事,逼張生赴京應試:“俺三輩兒不招白衣女婿,……得官呵,來見我,駁落呵,休來見我”。但她畢竟是母親,對不聽話的女兒,嚴厲的拘管之中飽含愛憐,遠沒有杜寶那么嚴酷。
杜寶是個清正廉明、為國盡忠的好官,也重視骨肉之情,甚至還說過:“功名富貴草頭露,骨肉團圓錦上花”。他對自己未有兒子感到 “可憐”,他對杜麗娘的要求只是“知書知禮,父母光輝”,要學“后妃之德”。但他生性固執,在女兒婚姻問題上聽不進別人(哪怕是夫人、同僚)半點意見。請來陳最良這一腐儒做官教書,拘束杜麗娘的身心。他又非常迷信,聞知杜麗娘游園得病,不問情由斷定是妖邪纏身,請來道姑診祟捉鬼,活活斷送了女兒性命。當柳夢梅冒著生命危險來到前線謁見他這位岳丈大人時,他認為是冒充女婿,不問青紅皂白令手下將柳夢梅抓了,送到臨安府監候。他在監中審訊柳夢梅時,不聽分辨,認定其為劫墳賊,嚴刑拷打。甚至當主考官帶著狀元冠帶來接柳夢梅時,向杜寶說明柳夢梅中了狀元,他還是不信:“異哉,異哉。還是賊?還是鬼?”當誤報消息的陳最良探得真情后,前來恭賀杜寶“三喜臨門”:“一喜官居宰輔,二喜小姐活在人間,三喜女婿中了狀元”,杜寶還是不信,還說麗娘還魂是“成精作怪”,“此乃妖孽之事。為大臣的,必須奏聞滅除為是”。此事鬧到皇帝面前,杜寶仍然固執己見,仍然說杜麗娘是“花妖狐媚,假托而成”,弄得狀元郎柳夢梅在金殿上放聲大哭:“好狠心的父親。他做五雷般嚴父的規模,則待要一下里把聲名煞抹。便閻羅包老難彈破,除取旨前來撒和”。幾經質證,皇帝下旨,方才作罷。杜寶是 “滅人欲”的兇神。當然也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個性解放道路上的絆腳石。這一封建衛道士的典型形象所蘊含的意義,遠比《西廂記》中的老夫人要深刻。
三、都是悲歡離合的故事但戲劇結構和舞臺表現大不相同
(一)戲劇結構
《西廂記》共五本,每本四折,共二十折。加上每本還都有一個楔子,也算得上是連臺本戲。
《牡丹亭》長達五十五出,其篇幅是《西廂記》的一倍。
《西廂記》以崔、張戀愛成婚的故事為中心線索,漸次展開情節,是我國戲曲傳統的“金線串葫蘆”式的結構方式,重點是表現他們相思之苦、婚姻之旅的艱難。
《牡丹亭》緊緊抓住“還魂”這一特別具有傳奇色彩的中心環節,“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最后合一,成為并蒂蓮。戲劇結構為雙線結構:《幽媾》以前,杜麗娘一條線,柳夢梅一條線,平行展開。《幽媾》至《急難》,杜、柳相會、結合,二線合一。《急難》之后,柳夢梅赴淮揚探望杜寶,仍分叉為二線,至最后一出《圓駕》,二線合一,大團圓結束。這種結構方式,增強了戲劇懸念,杜、柳相思之苦、婚姻之旅的艱難,比崔鶯鶯、張生更有甚焉。湯顯祖殫精竭慮,謀篇布局,正如近代著名曲家吳梅《還魂記跋》所說的那樣:
此劇肯綮在生死之際。記中《驚夢》《尋夢》《診祟》《寫真》《悼殤》五折,自生而至死;《魂游》《幽媾》《歡撓》《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至生。其中搜抉靈根,掀翻情窟,為從來填詞家屐齒所未及,遂能雄踞詞壇,歷千古不朽也。
吳先生的這段話,自是不刊之論。我還以為,《魂魂記》的精彩之處并不只以上所列十出。許多曲家對杜麗娘還魂以后的戲似乎不太感興趣,如著名劇作家石凌鶴改編的弋陽腔《還魂記》就只演到還魂為止。實則還魂以后有好戲,如第四十一出《耽試》柳夢梅考場慷慨陳述御敵之策,第五十三出《硬拷》杜寶嚴刑拷打狀元郎,就很有點黑色幽默的意味。第五十五出《圓駕》,頗有喜劇色彩,雖然上場人物較多,但安排得井然有序,逐步把劇情推向最后的高潮。從全劇的舞臺氣氛看來,還魂以前悲情場次較多;還魂以后,杜寶、柳夢梅的戲較多,除征戰殺伐的戰爭場面外。還有些歡樂、甚至帶有喜劇氣氛的場面。這些場面是不可或缺的,正好起到了調劑冷熱的作用,要不然,一味悲情到底,使觀眾壓抑得喘不過氣來,難以取得良好的戲劇效果,不符合我國戲曲觀眾傳統的審美意趣。前些年,江西省贛劇院黃文錫先生將還魂后的戲,改編為《還魂后記》,演出效果是不錯的。
總之,《牡丹亭》的情節比《西廂記》曲折,事件繁復,場面大,結構嚴謹,一些細節的鋪墊、交待、回應,針線綿密。
(二)舞臺表現
兩劇都寫了一些舞臺提示,唱詞中也有場景描寫,融情于景,情景交融,是兩劇共同的特點:《西廂記》的“云斂晴空,冰輪乍涌,風掃殘紅香階亂擁,離恨千端”,“碧云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等名句;《牡丹亭》的“裊晴絲吹來閑庭院”、“原來姹紫嫣紅開遍”、“遍青山題紅了杜鵑”等名段都是戲曲舞臺上千古絕唱。雖然沒有舞臺氣氛圖和導演提綱,我們還是不難看出兩劇舞臺表現方面的一些特點。
《西廂記》的故事,時間跨度不到一年光景,劇情基本上是在普救寺展開,僅第四本“草橋驚夢”和第五本【楔子】、第二折等三折戲是在外地。而《牡丹亭》故事的時間跨度有三年之久,故事始發于江西南安府,但劇中人物的足跡到了廣州、臨安、淮安、揚州等地,都是湯顯祖到過的地方。對這些地方的景物和風土人情,作者是有親身體驗的,其《勸農》一出,大概與其在浙江遂昌當縣令的生活有關,所以劇本對這些多有出色的描寫和表現。不同季節、不同地點有不同的場景,與《西廂記》相比,顯然更為豐富多彩。
《西廂記》的舞臺表現,事件單純,故事發展脈絡清晰,節奏明快。而《還魂記》的舞臺表現,圍繞還魂這個中心環節,設置了較多的事件,容量較大,情節起伏跌宕,張弛得當,錯落有致。這一方面可以比較的地方很多,本文僅就腳色行當體制方面作一比較。因為,戲曲藝術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程式化,而行當體制是最基本的程式,它涉及到戲曲的文本創作、音樂創作、導演構思、演員表演、化妝造型乃至戲班的人員結構。《西廂記》的人物約有 14 個。行當體制同元雜劇一樣,主要行當有正末(張珙)、正旦(崔鶯鶯)、外(老夫人)凈(法本、鄭恒)等四行。而紅娘標為“旦俫”、琴童標為“俫人”(俫字似可作“小”字解),但其它人物(法聰、杜確、孫飛虎、惠明、小二哥、卒子、太醫)未標明行當。
湯顯祖《牡丹亭》是用海鹽腔的支派——宜黃腔來編劇的。與崔時佩所編的《南西廂記》一樣,行當都是八個,即生、旦、凈、末、丑、外、貼、老旦,扮演89個人物。
需要指出的是,自清代梆子、皮黃等劇種興盛以來,一個行當可以有幾個演員,同一行當的不同的人物可以由該行當的演員來分擔。但在明清時期的海鹽腔、昆腔家庭戲班常常是一個行當一個演員。《牡丹亭》《南西廂記》都只有八個行當,只要八個演員就可演出。清初南昌名士李明睿的家庭昆腔女樂演出《牡丹亭》時,就只有八個女演員。前明進士、曾任浙江提學道僉事的黎元寬寫的觀劇后寫有就有這樣的詩句:“縈懷底事聊憑修褉,作語生香僅八奩”[5]。按,“奩”原意為梳妝盒,此處代指女伶。“作語生香僅八奩”,就是說僅有八個女伶在演出。《牡丹亭》八個演員要扮演89個人物,湯顯祖在編劇時必然要按照行當的特點安排角色,同時還要照顧到演員的精力和上下場“趕妝”的時間,確非易事。這表明湯顯祖是十分熟悉舞臺表演規律和劇種特點的。所以,從行當體制的角度來看,《牡丹亭》比《西廂記》更為進化、完備。
綜上,從戲劇結構和舞臺表現諸方面來看,《牡丹亭》也是有勝過《西廂記》的地方。
[1]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4冊[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206.
[2]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4冊[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270.
[3][4]徐朔方箋校.湯顯祖全集第二冊:詩文卷二十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153.
[5]裘弘君.西江詩話(清康熙刊本).見劉廷璣康熙四十三年序.
本文首發于《學術問題研究(綜合版)》(仰恩大學內刊)2010年第1期,經作者及原出版單位授權同意,本刊原文轉載。
蘇子裕:江西省藝術研究院
江西省撫州湯顯祖國際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