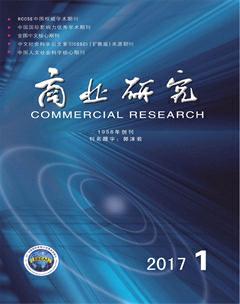戰略導向、商業模式創新與經營績效
內容提要:基于產業生態系統視角,本文區分效率型與新穎型兩類商業模式創新,進而探討戰略導向、商業模式創新與經營績效的內在聯系。通過分析192家制造型中小企業數據,發現商業模式創新在戰略導向與經營績效邏輯關系中發揮完全中介作用;市場導向驅動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而技術導向對效率型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均有正向影響;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積極影響市場和財務績效,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只對財務績效有正向效應。
關鍵詞:商業模式創新;市場導向;技術導向;經營績效
中圖分類號:F27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17)01-0034-08
一、引言
當前激烈市場競爭不僅是產品或單個企業之間的比拼,更是不同商業模式之下企業種群之間的較量,創新型商業模式成為企業應對市場競爭,實現持續成長的重要戰略手段[1]。“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強商業模式創新”已上升為國家意志,并被各級政府視為“調整產業結構、化解產能過剩的根本出路之一”。
商業模式創新是繼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后,企業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又一關鍵路徑;它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實現持續成長的重要驅動力[2]。然而,目前商業模式創新研究還有很大的拓展和深化空間:首先,現有商業模式創新研究絕大多數運用概念性或描述性分析方法,或者是案例研究方法,相關研究結論缺乏實證數據的檢驗[3]。其次,多數研究議題聚焦于商業模式創新的理論基礎、概念內涵或作用機理等方面[4],而對商業模式創新驅動因素的探討還有待加強。最后,高管團隊異質性、知識管理等組織因素已被證實為商業模式創新的重要驅動因素[5-6],而且商業模式創新作為企業戰略層面關鍵創造性活動必然受到組織戰略因素影響。戰略導向是引導企業資源配置與戰略行動的重要理念,對企業市場和技術層面的創新活動具有積極效用[7],戰略導向對產品創新與新產品開發管理的驅動效應已得到證實[8-9]。商業模式創新是企業創新活動的重要類型,必然也會受到戰略導向影響,但缺乏二者內在關系的探究。因此,本研究試圖從產業生態系統視角,在區分效率型與新穎型兩類商業模式創新的基礎上,探討戰略導向、商業模式創新與經營績效的內在聯系;將商業模式創新視為組織重要戰略行為,并探討其關鍵前置因素,豐富商業模式創新影響因素研究,同時深化商業模式創新與經營績效關系探討,為企業革新商業模式提供管理借鑒。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商業模式創新內涵分析
由于理論基礎與分析視角的不同,商業模式既被等同于企業盈利模式[10],又被認為是企業與利益相關方構成的交易模式或交易結構[11],還被認為是企業構建的綜合性價值創造系統[12]。雖然當前研究就商業模式的內涵理解存在分歧,但都將其視為企業的獨特競爭手段與市場優勢來源[2]。
當前科技進步與產業生態演化為企業創新商業模式提供了新機遇[13]。對商業模式內涵理解的不同,使商業模式創新成為“眾口一詞、莫衷一是”的術語[14]。現有研究從不同角度對商業模式創新進行內涵界定:(1)技術視角,指出商業模式是企業基于技術革新,對商業范式和市場規則進行重新設定;關注商業模式創新在技術創新活動中的重要價值,強調技術創新只有與商業模式創新有機結合,才能實現技術商業價值最大化[15]。(2)戰略視角,認為商業模式創新的本質是企業對發展戰略的革新,即企業革新現有游戲規則或改變競爭性質,實現對當前經營模式與管理過程的重組,從而提升顧客價值并實現企業成長[16]。(3)營銷視角,強調商業模式創新是企業基于既有市場結構、并面向顧客潛在需求,通過對銷售系統和營銷渠道的重新設計,或改變競爭方式與競爭規則,最終實現以提升顧客價值為目的的業務創新[17]。
商業模式本質上是企業與利益相關方(如顧客、供應商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形成的交易網絡,涵蓋交易內容、結構和治理方式。因而,從產業生態系統視角理解商業模式創新,更能夠反映商業模式的本質內涵[18]。產業生態系統是圍繞產品開發、設計與制造,并最終傳遞給顧客,從而實現價值創造的企業生態網絡,它由企業與供應商、經銷商、顧客,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如外部研發機構等)共同構成[19]。本研究借鑒Zott和Amit(2008)的觀點[18],基于產業生態系統視角,將商業模式創新分為效率型和新穎型兩類: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是指企業在產業生態系統中創造性實施能夠獲取交易效率的各項活動;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是指企業在產業生態系統中開發全新價值主張、構建新型交易方式的創造性活動。
(二)戰略導向與商業模式創新
戰略導向是引導企業運營活動的管理哲學,它規定企業對資源與能力的配置方向與使用方式,是企業創新活動的重要因素[8]。市場導向與技術導向是企業戰略導向的核心內容,它們具有不同的組織焦點:市場導向屬于外向型焦點,強調“市場引領技術”;技術導向屬于內向型焦點,強調“技術驅動市場”[9]。
市場導向既被視為組織文化,也被看著是組織行為。作為文化的市場導向,強調識別與滿足市場需求是指導企業營銷管理實踐的基本觀念與行動準則[20];它是由顧客導向、競爭者導向與跨職能部門協調三方面內容構成[21]。市場導向驅動商業模式創新的研究還比較缺乏,但有關市場導向影響企業商業網絡構建的研究發現,具備高水平市場導向的企業更能夠設計和管理高效分配資源,實現資源交換與累積,推動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商業網絡[22]。同時,堅持高效傳遞與維護顧客價值是市場導向的核心,為此企業必須在市場環境感知、市場知識積累與擴散,以及關鍵市場知識跨部門運用等方面進行積極投入[7];而那些描述市場環境現狀與潛在需求的關鍵知識,是企業設計卓越商業模式的重要資源[1]。因此,企業堅持市場導向,聚焦于顧客價值、競爭者行為與跨部門職能協調,既有助于針對當前市場環境現狀,開發和設計以提升效率為核心的商業模式,又有助于針對潛在市場需求,依托產業生態系統開發新的價值主張,構建新的交易方式。據此,假設如下:
H1a:市場導向對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有積極影響;
H1b:市場導向對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有積極影響。
技術導向反映技術驅動的企業經營哲學,它認為市場青睞技術出眾的產品或服務[7]。堅持技術導向的企業傾向于在研發資產方面給予更大投入,積極并購新技術,并快速實現技術的產品化與商業化[8]。一方面,在產業生態系統中,持續性技術投入推動產業技術創新,并構建有效的產業交易平臺,能夠顯著地降低產業內交易成本,并提升產業中資源流動的效率[23]。因此,從效率提升與成本降低角度上講,企業堅持技術導向有助于推動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另一方面,從技術管理角度看,企業在研發領域的持續投入,使企業更有效開發新技術產品;而新技術產品的商業化,必然伴隨新的價值主張,以及新的顧客與合作伙伴出現,因而對企業現有產業生態系統進行擴充和更新,納入新的利益相關方,從而推動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4]。總而言之,技術導向推動企業在技術資產方面進行持續投入,不僅可以通過革新產業技術,構建高效率交易網絡,還可以通過在產品開發等方面不斷進步,優化與拓展產業生態系統,從而推動商業模式創新。研究提出假設:
H2a:技術導向對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有正向作用;
H2b:技術導向對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有正向作用。
(三)商業模式創新與經營績效
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并不強調效率本身,而是關注產業生態系統中交易成本的降低,進而使系統內部交易參與各方獲利。在以提升效率為核心的商業模式創新中,交易成本的降低既可能來自對產業生態環境不確定性和復雜性的弱化,還可能來自降低交易參與各方協調成本與交易風險[18]。通過降低系統內交易成本,效率型商業模式能夠帶來更高水平交易量,同時吸引和鼓勵新顧客進入產業生態系統,而現有顧客則將增加交易頻率以獲得更低水平交易成本[24]。因此,以增強產業生態系統中利益相關方交易效率為中心的商業模式創新,通過降低企業生態網絡交易成本,提升各方交易效率,有助于改善企業市場和財務方面績效水平。基于此,提出假設:
H3a: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對市場績效有正向作用;
H3b: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對財務績效有正向作用。
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聚焦于產業生態系統中交易參與方的類型,以及交易方式的革命性變化,如開發新的價值主張,在產業生態系統中選擇新合作伙伴,或為系統內各參與方構建新的交易方式、設計新的交易機制[18]。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強調在交易各方中創造并實施新的經濟交換方式,其首要目標是創造新型交易,例如增加交易類型數量;同時也強調企業在與其他合作伙伴交易過程中通過開發新的價值主張、設計新的交易模式,從而增強在產業生態系統中的議價能力。商業模式的高新穎性能夠使顧客、供應商、經銷商,以及其他合作伙伴缺乏有效的交易替代者,進而帶來更高轉換成本[25]。可見,增強商業模式設計的新穎性,企業不僅可以在交易過程中獲得更高價格水平,同時還能夠憑借持續增加的議價能力,在多方交易中持續降低交易成本,有效提升企業經營績效水平。因此,假設如下:
三、研究方法
(一)數據收集
研究選擇制造型中小企業為調研對象,原因有二:一是在新經濟、技術與政策環境下,制造業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經營方式與業務模式的轉型升級成為企業必然選擇。二是相較于大型企業在技術等領域進行的高水平專有性創新資源投入,相對缺乏資源與能力的中小企業進行商業模式創新更具靈活性與必要性。樣本企業選擇的具體標準為:(1)依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02),選擇制造業(C類)中的各行業企業;(2)根據《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選擇從業人員1 000人以下的企業。
數據收集方式有兩種:一是,在北京市某大學的EMBA和MBA班,發放調查問卷100份;經研究人員甄別被調查者身份,并指導符合調查標準的被調查者填寫問卷后,回收95份有效問卷。二是,對重慶市三個工業園區進行抽樣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400份;在市場研究公司協助下,經電話聯系征詢參與意向,并向同意參加調查的企業管理者發放問卷,回收問卷153份,其中97份有效問卷。研究數據收集歷時兩個月,發放500份調查問卷,累計回收有效問卷192份(表1),有效回收率達3840%。
為檢測樣本企業代表性,以及避免非回應偏差問題,研究對不同方式收集的問卷進行差異化檢驗,并對有效及無效問卷進行T檢驗。檢驗結果顯示研究數據具有較好代表性,且非回應偏差問題不會對后續分析結果產生顯著影響。
(二)變量測量
商業模式創新的測量借鑒Zott和Amit(2008)的研究工具[18],包括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兩方面。戰略導向包含市場導向與技術導向兩方面:研究借鑒Narver和Slater(1990)經典測量工具[21],從顧客導向、競爭者導向和跨部門協調三個方面對市場導向進行測量。技術導向的測量,則借鑒Zhou等(2005)[7],以及李巍(2015)的研究工具[9],從技術先進性與產品柔性兩方面進行考察。由于經營數據屬于比較敏感的信息,企業并不愿意透露經營績效狀況;同時大多數中小企業并非上市公司,無法從公開數據庫獲取財務信息。因此,研究遵循一般慣例,改編李巍(2014)的研究工具[26],運用主觀評價的方式,從市場績效和財務績效兩方面對經營績效進行衡量。以上題項均使用李克特7點量表測評。
此外,研究遵循一般慣例引入兩類控制變量:企業年齡與規模。企業年齡是以企業成立時間為標準進行測算,企業規模則用企業正式員工的數量為計算標準。
四、實證分析
(一)信效度檢驗
變量測量信度的檢驗運用Cronbachs α值和組合信度(CR)兩項指標。數據表明(表2):變量的α值介于0836-0924之間,組合信度介于0751-0903之間,均大于07水平。可以認為變量測量的信度水平已達到要求。
研究所用測量工具均改編或借鑒已有成熟量表,因而測量的內容效度能夠得到保證。同時,運用驗證性因子分析來檢驗測量的結構效度。分析結論表明(表3),所有變量的測量模型卡方值與自由度的比值(χ2/df)介于10-20區間,RMSEA小于008水平,絕對擬合度指標GFI和AGFI均超過09水平,增值擬合度指標CFI和NFI也達到09水平,簡約擬合度指標PGFI和PNFI均超過05水平,表明變量測量的結構效度達到較高水平。
對測量判別效度的檢驗,運用Pearson相關系數及平均提煉方差(AVE)值的平方根兩項衡量指標。數據結論顯示(表2),部分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相關性,但均未超過07水平,且變量AVE值均大于05水平,變量AVE值平方根均大于其所在行與列相關系數絕對值,表明測量的判別效度也比較理想。
(二)中介效應檢驗
理論推導結論表明,商業模式創新在戰略導向與經營績效之間扮演中介角色。但在進行研究假設檢驗之前,確定商業模式創新發揮部分中介,還是完全中介效應,以為后續結構方程路徑分析提供準確的預設模型。研究運用中介效應“三步檢驗方法”對商業模式創新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27]。
具體檢驗步驟為(表4):第一步,將中介變量商業模式創新與自變量戰略導向進行回歸,回歸系數β=0267(p<0001),呈顯著性;第二步,將因變量經營績效與自變量戰略導向進行回歸,回歸系數β=0219(p<001),同樣顯著;第三步,將因變量與自變量、中介變量同時進行回歸:中介變量回歸系數β=0203(p<001),達到顯著水平,自變量回歸系數明顯減少且不顯著(β=0126,p>005)。結論表明:商業模式創新在戰略導向與經營績效關系中發揮完全中介效應。
(三)研究假設檢驗
運用結構方程模型的路徑分析方法來檢驗理論假設。依據理論推導和中介效應分析結論建立路徑關系模型。運用Amos 70軟件輸出模型結果,χ2/df為1682,RMSEA為0071,GFI和AGFI分別為0923和0912,CFI、NFI和TFI依次為0921、0915和0907,均大于09水平,表明模型擬合度達到相關要求,可用于檢驗研究假設。
路徑分析結論顯示(圖2):市場導向對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γ=0287,p<0001)有積極作用,而對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γ=0103,p>005)的正向效應不顯著,即H1a得到證實,H1b未通過驗證。技術導向對效率型(γ=0183,p<005)與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γ=0205,p<001)均有積極作用,即H2a和H2b均得到支持。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對市場績效(γ=0248,p<001)和財務績效(γ=0195,p<005)都有顯著正向作用,即H3a和H3b通過驗證;同時,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只對財務績效(γ=0293,p<0001)有積極效應,對市場績效(γ=0097,p>005)的影響作用并不顯著,即H4b通過驗證,H4a未被證實。
五、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文運用192家制造型中小企業數據,探究戰略導向、商業模式創新與經營績效之間邏輯關系,主要結論包括:
第一,市場導向對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有積極影響,而對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的作用并不顯著。市場導向作為一種組織文化,強調顧客導向、競爭者導向與跨部門協調,使企業聚焦于發掘、理解并預測市場需求;通過強化在市場知識累積、關鍵知識跨部門運用等方面持續資源投入,使企業對產業環境理解與反應水平更高,這有利于企業設計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商業模式革新措施。與此相對,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更聚焦于對新交易對象、新價值主張,以及新交易模式的建立,但市場導向更多是對現有產業環境的理解與響應,因而對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作用并不顯著。
第二,技術導向顯著影響效率型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水平。一方面,技術導向使企業進行更多技術資產領域的資源基礎投入,推動新產品開發管理達到更高效率水平;通過對新興技術的產品化和商品化,形成革命性產品,有助于企業開發新價值主張,鏈接新的交易伙伴,建立新的交易模式,從而實現對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的推動。另一方面,對技術資產累積的持續投入,有助于企業建立產業生態系統內的技術平臺,形成具有較強影響力的技術輻射。技術平臺的構建與運用能夠顯著地降低產業生態系統內各參與方的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從而推動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
第三,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對企業市場及財務績效水平提升都有正向作用,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只對企業財務績效改善的積極作用較為明顯。商業模式創新對財務績效的積極影響進一步印證國內學者先期研究成果[28]。但從企業績效整體來講,以效率改進為核心的商業模式創新活動關注產業內交易成本的降低;企業通過與上下游交易成本的控制,提升交易效率,能夠顯著地提升在市場和財務方面績效水平。然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立足于新價值主張開發、新交易伙伴鏈接、新交易模式構建,即創造新市場或創造新交易方式,這樣的“藍海競爭”有助于企業改善財務水平;但是,可能由于缺乏足夠市場規模,以及產業生態系統內各方對新事物漸進式的接受和采納,因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對市場績效的驅動并不顯著。
(二)研究價值與啟示
商業模式創新的關鍵價值已經得到廣泛認可,但對商業模式創新前置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仍然比較缺乏。本研究基于制造型中小企業實證數據,探討戰略導向、商業模式創新與經營績效內在聯系,具有以下價值:首先,基于產業生態系統視角,從效率型和新穎型兩方面解構商業模式創新,不僅拓展對商業模式創新內涵與分析維度的研究,更為科學測量商業模式創新,繼而進行量化研究奠定基礎。其次,與以往從高管團隊、知識管理分析視角不同,本研究從戰略導向視角探討商業模式創新的前置因素,豐富商業模式創新影響因素的研究。最后,在區分兩類商業模式創新的基礎上,探討其與市場及財務績效的關系,從而深化商業模式創新與經營績效的關系研究。
同時,研究結論為企業推動商業模式創新提供若干指引:一方面,堅持市場導向的企業,實施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是最佳選擇。通過提升產業生態系統內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可以有效地改善市場和財務兩方面績效。另一方面,推崇技術導向的企業,選擇效率型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都能夠對經營績效帶來積極效應。但從企業績效結果來看,企業應率先開展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進而過渡到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即先降低產業生態系統內交易效率,再開發新的價值主張、拓展新的交易類型,更有利于保證市場與財務兩方面績效的穩定。
參考文獻:
[1]Christensen M. The past and futur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01, 42(2): 105-109.
[2]Casadesus-Masanell R. & Ricart J. How to design a winning business model[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1(1/2): 1-9.
[3]Chesbrough H.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and barriers[J].Long Range Planning, 2010, 43(2/3): 354-363.
[4]Zott C., Amit R. & Massa L. The business model: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1): 1019-1042.
[5]肖挺,劉華,葉芃. 高管團隊異質性與商業模式創新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以服務行業上市公司為例[J].中國軟科學,2013(8):125-135.
[6]易加斌,謝冬梅,高金微. 高新技術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影響因素實證研究:基于知識視角[J].科研管理,2015(2):50-59.
[7]Zhou K., Yim C. & Tse D.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orientations on technology-and market-based breakthrough innova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 2005, 69(2): 42-60.
[8]Gatignon H. & Xuereb Jean-Marc.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the Firm and New Product Performance[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7, 34(1): 79-90.
[9]李巍. 戰略導向均衡對產品創新與經營績效影響研究[J].科研管理,2015(1):143-151.
[10]Downing 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Narrative and dramatic processes in the coproduction of organizations and identitie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005, 29(2):185-204.
[11]Amit R. & Zott C. Value creation in e-busines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6/7): 493-520.
[12]Osterwalder A., Pigneur Y. & Tucci L. Clarifying business models: Origins,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ncept[J].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2005, 16(1): 1-25.
[13]Mendelson H. Organizational architecture and success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J].Management Science, 2000, 46(4): 513-529.
[14]王雪冬,董大海. 商業模式創新概念研究述評與展望[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3(11):29-36.
[15]Chesbrough W. Open business models[M].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6.
[16]Schlegelmilch B., Diamantopoulos A. & Kreuz P. Strategic innovation: The construct, its drivers and its strategic outcomes[J].Journal of Strategic Marketing, 2003, 11(2): 117-132.
[17]Aspara J., Hietanen J. & Tikkanen H.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vs replicati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strategic emphases[J].Journal of Strategic Marketing, 2010, 18(1): 39-56.
[18]Zott C. & Amit R. The fit between product market strategy and business model: Implications for firm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29(1): 1-26.
[19李曉華. 產業生態系統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J].中國工業經濟,2013(3):20-32.
[20]Kohli A. & Jaworski B. Market orientation: The construct, research propositions,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 1990, 54(1): 1-18.
[21]Narver J. & Slater S. The effect of a market orientation on business profitability[J].Journal of Marketing, 1990, 54(3): 20-37.
[22]Ritter T., Wilkinson F. & Johnston W. Managing in complex business network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4, 33(3): 175-183.
[23]Gawer A. & Cusumano M. Industry platforms and ecosystem innovation[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4, 31(3): 417-433.
[24]Doz Y. & Kosonen M. Embedding strategic agility: A leadership agenda for accelerating business model renewal[J].Long Range Planning, 2010, 43(2/3): 370-382.
[25]Zott C. & Amit R.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J].Organization Science, 2007, 18(2): 181-199.
[26]李巍. 制度因素、顧客響應能力與經營績效:國有與民營企業的對比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4(4):119-124.
[27]Baron R. & Kenny D.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 1173-1182.
[28]蔡俊亞,黨興華. 商業模式創新對財務績效的影響研究:基于新興技術企業的實證[J].運籌與管理,2015(2):272-280.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ecosystem, distinguishes efficiency-centered and novelty-centered BMI, and then explor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 among strategic orientation, BMI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By analyzing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192 manufacturing SMEs in China, the paper finds that BMI plays the complete intermediary role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market orientation positively impacts efficiency-centered BMI, but technology orientation positively affects efficiency-centered and novelty-centered BMI; efficiency-centered BMI exerts positive effects on market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while novelty-centered BMI just has positive impact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Key words: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market orientation; technology orientation; business performance
(責任編輯: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