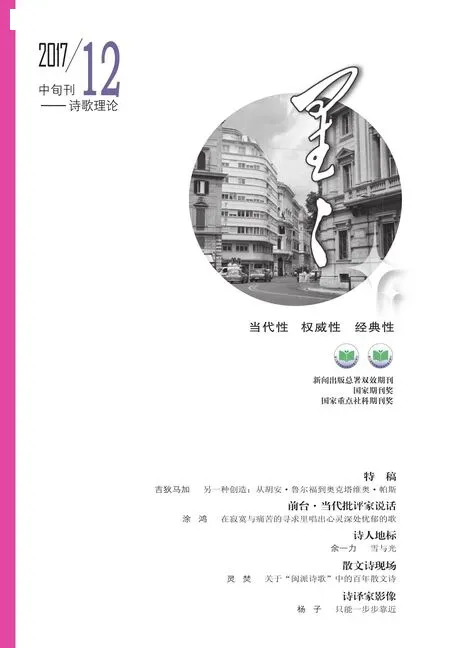“小”其實都不小
徐 鑫
《小黃馬》充滿著悲涼與無奈之感。當“小黃馬的媽媽死在草原上”后,小黃馬即將被人“安上雕花的馬鞍”,隨后將要經歷媽媽曾經歷的一切,而結局也會如同媽媽一樣,“死在草原上”。即使知道自身的結局,小黃馬也無力反抗,只能繼續“在草原上悲傷地慢慢跑”,默默承受著。此時,悠揚的琴聲并不能帶給人喜悅的心情,更多的是“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海子《九月》)。同時“悲傷”、“慢慢跑”、“說不出話”這些詩性語詞給全詩營造了哀傷的氛圍,小黃馬的悲劇結局更是讓滿滿的悲涼之情溢出全詩。詩歌每行均以“小黃馬”開頭,既有強調的作用,又形成了回環反復的詩歌音韻效果,加強了詩歌的韻律。重復的兩句“小黃馬在草原上悲傷地慢慢跑”,情感層次不斷加強,如果說第一句是平靜的敘述,那么到詩歌結尾就變成了深深的無奈。縱然知道我的一生,但是我只能按照這種悲傷的規劃前行。小黃馬的遭遇實際上代表了主體對命運和生活的無力反抗,小黃馬某種程度上是萬千個你我。雖然我們的人生不一定與小黃馬一樣無力反抗與更改,但生活中卻時有無力之感產生,我們拼盡全力試圖掌握自己的生活,最終卻發現主體的渺小,焦慮與痛苦正是在這種矛盾中產生。
胡弦的詩歌讓人驚喜。曾經有人說當代詩歌因為語言的破碎所以無法表達詩人復雜的情感,而胡弦的詩歌駁斥了這種說法。詩人以“流水濟世”起筆,以“孤獨于世”收筆,巨大的張力蘊含在詩歌之中。從流水到亂石,詩人的思緒突然轉到了“南方之慢”。南方的天空很藍,夜晚有“風卷北斗”和“丹砂如沸”。一天之間,時間老人似乎在慢騰騰地走動著,然而時光卻在“南方之慢”中飛快地流動、逝去。又到深春了,幽暗的峽谷在詩人眼中卻如 “萬花筒”一般絢爛與精彩,老槭樹如同偷心賊一般,時不時涌上心頭,記憶中的你“手指纖長,愛笑”,然而花團錦簇的小碎花卻只能孤獨地存在于世。詩中詩人的思緒不斷跳躍,從“流水”到“亂石”,到“南方之慢”,再到“飲酒的夜晚”,最后落腳到“愛笑的你”,看似無邏輯可言,然而正是這種跳躍呈現出了一幅萬花筒般的現世生活景象。流水與亂石的一動一靜,南方之慢與光陰下沉的一慢一快,手指纖長愛笑的你卻只有衣服上的小碎花存在于世,詩人從意象間的悖反性出發,通過碎片化的記憶,將偶然與必然、有限與無限、瞬間與永恒等思考呈現給讀者。詩思的哲理化探索并沒有通過拗口的語言堆砌來完成,而是從最日常平凡的事物出發,以小見大,從而建構了一個復雜的詩思空間。正是通過這種駁雜性和矛盾性,通過“流水濟世”與“碎花孤獨于世”的張力空間呈現,讀者在閱讀后容易產生一種熱鬧與孤獨并存的既駁雜又荒涼的感受。正如評論家羅振亞先生所說:“跳躍而別致的語句組接、詩性敘述,賦予了詩歌一種敘述長度,一種蒼涼的歷史感,使之對現實歷史更具包蘊性和吞吐力。”“小謠曲”包蘊萬千,吞吐萬千。
尤克利的詩歌深情。《小風歌》充滿著對故鄉的濃濃情誼,詩人“順風漂移”,在“風與風耳鬢廝磨中”,回到了魂牽夢繞的故鄉。“身陷故土”后,更是懇請當年送我還鄉的風兒不要“帶著我去遠行”,詩人只愿意長留故土。詩人生前渴望回到故土而不得,只能寄希望于生后,一股哀傷之感油然而生,然而詩人在這種沉重的敘述中,卻借助日常的輕盈的風來建構詩歌,又充滿著一股浪漫氣息,輕盈化解了沉重,使得全詩哀而不傷,只留下滿滿的情誼,讓讀者為之感動。詩歌淳樸而厚重,小風歌,其實不小。
詩歌能將生活織成一襲華麗的旗袍,這三首詩歌都從平凡的事物中發現了蘊含其間的巨大能量:樓蘭女子從小黃馬身上看到了命運的無奈;胡弦在普通的世事中體會到了孤獨于世的蒼涼;尤克利從輕盈的風身上找到了還鄉的希望。無論是《小黃馬》《小謠曲》,還是《小風歌》,都從最真實的個人體驗出發,最終創造了一個巨大的隱喻空間,寥寥數語卻意蘊無窮,讓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