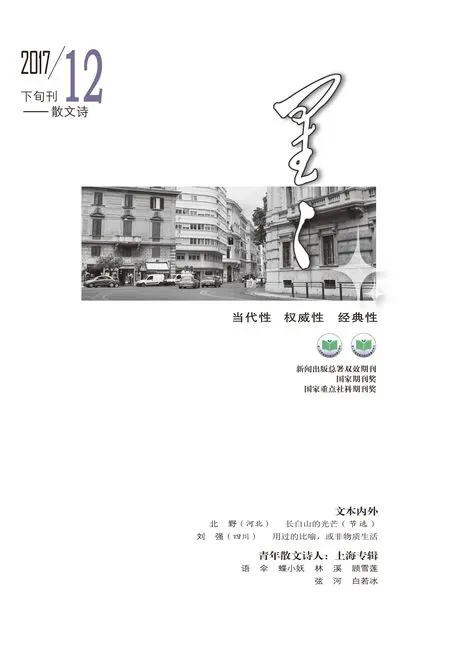樹 影(四章)
弦 河
樹 影
很遠。但我感覺到了近。依稀的,彌散的光點,灑在我赤裸裸的身體上。
此時,我像一只狗。一只可憐的狗。花斑散落,以此乞求茍活的命。沒有光走在黑夜,擦肩而過的陌生的人很低;
起初來到時,我與所有皆熟。自從腳步向前移動,就聽見腳底下有骨子斷裂,身體糜爛發出的低吟。
我一無所有地坐著,讓陽光消失在樹枝間。樹下,剛好看見一個細長的影子在時間的刻度上搖擺。它像家鄉的棕樹。獨立在我的窗前,卻沒有筆直的姿勢。也許它想讓我看的是,干枯的樹皮上割開的年輪,演化了山的背影。
那一道殘影,仿佛就要彎成斜陽的姿勢。俯身拾起的歲月,抖一抖就給了遠方一道狠狠的鞭子。
給 你
不應該有多余的裝飾,單獨的顏色。進行光合作用的葉子從未想過,穿過身體的光會把自己分解成另一種產物。在你沒說出口之前,我極力避免“疼痛”這個詞。疼,就對了,證明你活著,證明你尚未抵達終點。
黑夜的眼眸躲避光的映射,低于辯駁。像中毒的惡瘤躲避內心的刀,陳述事實并不代表苦難的偉大。
撕下頭顱上的面具吧!不應該有多余的理由和借口,也不必說它帶來了多少冬天的寒。我們相對而坐,我們對飲,忠實于彼此的相遇。佇立的木頭人遇見風化的葉。
城市借給你一件隱形的外衣。做一張面具,你去過的地方,很多人還在繼續閑逛。
有的人早早離開,有的人住下來訊問曾經走過的人,三言兩語就把一座城市描述了。看,那個美麗的城市,它將如同出生的故土一樣消失在記憶里。
而最后,要把自己撰寫在白凈的信箋紙上,把自己寄回故鄉,像最初出走一樣。
返璞歸真
要返璞歸真,雙手合十,吸山寺云煙。
鐘聲滲入溪水。
我在人間,以無根之水數落身上污漬,并承受它帶來的痛苦。
閉上眼,誰也不見。
誰也未曾離去,一直在。所以痛苦,并活著。從之前的昂首挺胸瞻望遠空,至頭顱藏于心間,青山綠水才能看見本性。
聽鳥鳴,然后匆匆離去。把一雙腳印留在山澗,被雨水打濕過的泥土上,讓風撫平。然后開出自然的笑容。
此刻我在山頂,仿佛靈魂的松懈撞響了久遠的鐘。
夜色詩
說不出喜歡黑夜的理由,也找不出渴望黎明的借口。這一切仿佛都在我活著的世界之外,我以為這是迷惑的根源。
我來到熟悉后又陌生的城市,試圖叫醒一些沉睡的老朋友。他們有的根莖深深扎入泥土,有的枝椏散得很開,宛如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我從空氣中打聽到:他們不再聆聽別人的故事,也不再向別人傾述衷腸。
風吹去,吹落一地梨花白。這個城市在一夜之間蒼老了許多。我想,是因為昨晚的黑夜吧。它在傍晚時分露出咄咄逼人的殺氣,讓真實的我從破曉的夜色中獲取了最初的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