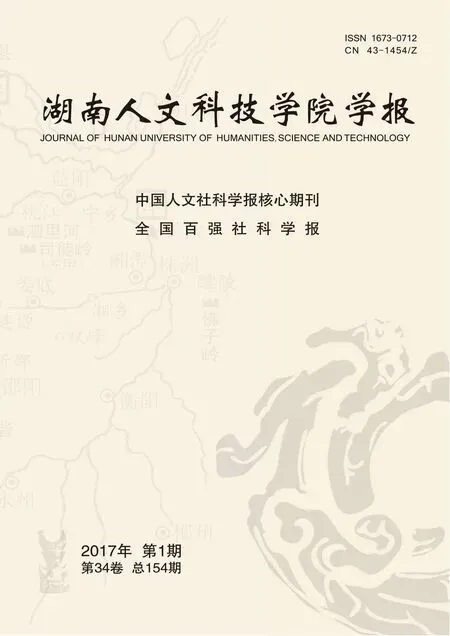當代媒介轉型與文學閱讀方式的多元化
周興杰
(貴州財經大學 文化法律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0)
?
當代媒介轉型與文學閱讀方式的多元化
周興杰
(貴州財經大學 文化法律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0)
20世紀80年代其實是深度閱讀與通俗閱讀并行的年代。這表明,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閱讀史,并不是一個從深度閱讀滑向“淺閱讀”的線性歷程。對于新媒介中的文學閱讀行為,形成了樂觀派與悲觀派兩種認識,它們在論證上都夸大了媒介這一技術邏輯的力量。網絡小說閱讀在新媒介文學閱讀中具有代表性,它體現為與經典文學閱讀不同的閱讀方式。因此,當代媒介轉型實際上使文學閱讀迎來了一個更為多元化的時代。
媒介轉型;閱讀方式;網絡小說;多元化
媒介是文學文本的物質載體,是文學閱讀得以實現的物質基礎,它對文學閱讀行為必然存在影響。因此,媒介與閱讀的關系,本是文學閱讀研究的必有向度。不過,在漫長的文學研究史中,只是到了接受美學的興起,文學閱讀的研究才得以系統化。而在文學閱讀研究中,更只是到了最近幾年,由于以網絡媒介為代表的新媒體對傳統印刷媒體的沖擊,媒介與文學閱讀的關系才受到真正關注。由于這種關注是隨著當代媒介轉型而發生的,許多研究自然貫穿了這樣一種比較意識,即將20世紀80年代印刷媒介語境中的文學閱讀與今天新媒介語境中的文學閱讀進行比較,結果卻形成了文學閱讀式微或者閱讀危機的論調。情況果真如此嗎?我們又應該如何來認識20世紀80年代和新媒介中的文學閱讀?本文試圖對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閱讀進行語境化后的再認識,對新媒介中的閱讀行為進行更為具體的考察,以求豐富我們對這一議題的認識。
一
20世紀80年代人們究竟是怎樣閱讀的?20世紀80年代經常被描繪成一個文學閱讀、乃至深度閱讀的黃金歲月。有學者列舉了大量數據來印證:《十月》的發行量在1981年已達到60萬份;《收獲》和《人民文學》的最高發行量分別達到100萬和150萬份;20世紀80年代初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北京大學的大學生幾乎人手一冊;薩特的《存在與虛無》1987年第1次印刷達37 000冊;卡西爾《人論》一年內就印了24萬本;等等[1]。也有人熱情回顧當年的閱讀經歷:
當時,看“硬書”成為一種時尚,在北大圖書館,學子們著迷地吸取著西方哲學家黑格爾、薩特、榮格的精神營養,每天在宿舍和課堂中進行著嚴肅而誠摯的討論:關于“人的解放”、理想、感情和人生……[2]
許多人在20世紀80年代的閱讀熱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人們真的都是這樣如饑似渴地讀“硬書”、讀名著嗎?這似乎只是歷史的一面,至少忽略了當年通俗文學閱讀的再度興盛。
解放前,通俗文學原有廣大的市場。到1954年,專營通俗小說的寶文堂在華北農村還有4000多處發行網[3],與當時的新華書店相比也不遑多讓。后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通俗文學在中國內地逐漸銷聲匿跡。但隨著改革開放,通俗文學又迅速回暖。這方面只要回顧一下當年的“金庸熱”就足夠了。20世紀80年代初,武俠小說就以盜版的形式悄然在內地廣泛流傳。20世紀80年代中期,嚴家炎等學者已開始了對金庸武俠小說的研究。據《遠東經濟評論》“文藝和社會”欄目的資深編輯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國內地、香港和臺灣的金庸小說的實際讀者,很可能就超過1億。如此看來,20世紀80年代讀武俠之類的通俗文學的閱讀群體,其數量恐怕遠超深度閱讀的群體。
以“金庸熱”為代表的通俗文學閱讀熱的出現其實不難理解。正如梅羅維茨所說的:“即使對有文化的人來說,閱讀也是一項辛苦的工作,例如,頁面上的墨字必須一個詞一個詞,一行一行,一段一段地掃過。為了獲取訊息你必須認真閱讀。為了閱讀這些詞,你的眼睛必須經過訓練,就像打字機的滾筒移動紙一樣沿著印刷的行移動。”[4]不難想見,所謂深度閱讀的難度遠超一般閱讀,它是需要長期的訓練和相當大的專業知識儲備的。那么,剛剛經歷了文革,被嚴格要求按“最高指示”來思考的國人中又有多少人具備這樣的閱讀能力呢?因此,大眾轉向通俗文學閱讀只是一個與自身的閱讀能力相適應的自然選擇罷了。
通俗文學閱讀與深度閱讀的時尚平行不悖于20世紀80年代,這表明,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閱讀史,并不是一個從深度閱讀滑向“淺閱讀”的線性歷程。20世紀80年代固然是深度閱讀的黃金期,但通俗文學閱讀同樣方興未艾。二者的交織并行,才更符合當年的歷史事實。一旦明了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閱讀實為深淺并置的狀況,那么,有如此之多的學者或文化名人選擇歌頌20世紀80年代的深度閱讀,進而宣示當下的閱讀危機就頗為耐人尋味了。筆者以為,他們的認識固然包含強烈的社會或人文關懷,但也流露出一定的懷舊情結。由于這種懷舊心理的作用,人們才對20世紀80年代的閱讀狀況作出了選擇性的“見”與“不見”,得出了理想化或審美化的結論,而掩映其下的則是若隱若現的精英式的價值觀。閱讀危機意識的出現無疑就是受這種精英價值觀的影響所致。
深度閱讀與通俗閱讀兩種閱讀方式的存在同樣折射了當代公共領域的分化形態。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的社會結構特點是政治公共領域獨大的話,那么20世紀80 年代的閱讀狀況則諭示了其它類型的公共領域的出現。深度閱讀的盛況自然印證了批判性的知識分子公共領域的再現,那么,通俗文學閱讀呢?通俗文學閱讀必須依賴通俗文學讀物的存在。20世紀80年代的通俗讀物實則多為盜版讀物,當年的中小城市有許多租書店出售或租賃這些盜版讀物,形成了一條有別于新華書店的營銷渠道。因而,通俗文學閱讀的興起,其實也隱隱透露出現代市民社會擴展的消息,表明了具有亞文化色彩的民間公共領域的出現。二者一道消解著政治公共領域獨大的社會結構。歷史地看,二者之間的關系并非是必然對立的。但是今天人們往往將批判性公共領域萎縮的原因主要歸結為受到了新的媒介文化的沖擊,而忘了在許多國家,通俗的、商業的文化領域更為發達,批判性的公共領域卻依然存在。因此,在重視新媒介文化沖擊的同時,我們是否應該也檢討一下所謂批判性公共領域自身的不足?
二
在新媒介情境中,人們又是如何閱讀的呢?對于新媒介語境中的文學閱讀的關注,必須從網絡文學閱讀說起。就像在傳統文學理論研究中,文學接受的研究晚于文學創作、文學文本等領域的研究而出現一樣,網絡文學閱讀的研究同樣要晚于其它領域的研究而出現。據筆者的初步考察,最早研究中文網絡文學閱讀的學理成果,應該要算是在2008年歐陽友權先生主編出版的《網絡文學概論》中藍愛國教授撰寫的《網絡文學欣賞》一節。藍教授在與傳統文學欣賞的比較中見出了網絡文學欣賞(閱讀)的不同之處,他認為網絡文學欣賞是一種“實時欣賞、‘拉’欣賞和解構式欣賞”:“實時欣賞使得網絡文學欣賞成為一種無障礙欣賞,‘拉’欣賞使它成為一種能動和互動的主體選擇性欣賞,而解構式欣賞則形成了網絡欣賞所特有的意義模式。”[5]“拉”欣賞強調的是網絡文學閱讀主體的能動性,以及網絡媒體與閱讀主體的互動性,將網絡閱讀視為文學閱讀權力的提升。因此,可以稱這種認識為網絡文學閱讀研究的樂觀派。
但對新媒介引發的閱讀方式嬗變,更多的學者表現出或多或少的憂慮。像有的學者在談到另一種新興媒介文學——微博文學的閱讀體驗時,就指認這種閱讀是“碎片化閱讀”:“在微博臨屏閱讀的過程中,人們的注意力被拉扯到數不清的信息碎片上,讀者很難心無旁騖地靜心品味這種飛馳而來又瞬間消失的文本而不受其他評論、視窗、鏈接信息的干擾,身不由己的思想主體迅即沉湎消逝于這種‘歧路花園’中的信息之流中。”[6]如果說學者的言說有些偏于客觀和理性的話,那么微博讀者的話則更鮮活而直白地傳達了這種閱讀體驗。如著名的網絡博客“和菜頭”在體驗了一段時間的微博閱讀之后,竟然哀嘆“我已經沒有辦法讀書了”[7]。與“拉”閱讀的認識不同,“碎片化閱讀”的提法凸顯了新媒介中信息量的龐大,以及它對閱讀主體的沖擊力。值得注意的是,閱讀主體的能動性、選擇權也相應地被主體的被操控感、乃至主體意識的渙散感所取代了。其實,不只是對手機短信、微博這樣的新媒介文學閱讀,許多人對以網絡媒介為基礎的新媒介閱讀方式均持批評性的、乃至輕視的態度。總體而言,他們認為這樣的閱讀只能是一種所謂“淺閱讀”。
“淺閱讀”一詞使用頻率很高,卻未獲得準確界定。與此對立的是基于經典文學閱讀的“深度閱讀”模式。比較二者,將有助于我們認識人們在如何使用“淺閱讀”概念。首先,從閱讀對象上看,深度閱讀面對的是經典文本,它有思想深度、審美價值。淺閱讀的對象則沒有或缺乏官方或權威認可的思想深度,以及相應的審美和倫理價值。所以淺閱讀首先是閱讀內容的“粗淺”。其次,深度閱讀要求有距離的靜穆觀照,或者全神貫注地對文本的反復沉潛和把玩。淺閱讀則是在時斷時續的閱讀時間中完成從閱讀到日常生活的不停切換,對文本多是一目數行的瀏覽和一次性的“消費”。所以淺閱讀還指閱讀狀態的“浮淺”。再次,從閱讀目的或效果來看,深度閱讀追求某種高遠的思想效益或巔峰性的審美體驗,淺閱讀則滿足于即見即得的快感體驗,甚至沉溺于所謂“YY(意淫)”滿足。所以淺閱讀還指閱讀目的的“膚淺”。由此可見,人們用“淺閱讀”來指稱新媒介文學閱讀行為,實質上包含了對此類文學閱讀方式的否定性的價值判斷。
面對上述認識分歧,我們應如何來認識新媒介中的文學閱讀行為呢?必須承認,上述認識為我們認識新媒介中的文學閱讀方式及相關問題提供了必要參照,但簡單地在上述兩種立場中進行選擇是不可取的。某種程度上說,上述兩種觀點雖然在價值判斷上存在對立,但在論證上都夸大了媒介這一技術邏輯的力量,即樂觀派的認識放大了新媒介技術的解放力量,而悲觀派則放大了新媒介技術的操控力量,因而形成了對立性的價值判斷。因此,我們有必要尋找其它的分析途徑。
三
其實對媒介技術力量效用的認識分歧早已存在。如本雅明思想中就有了對媒介技術解放力量的認識萌芽。而與之同時代的阿多諾則用“文化工業”來指稱這些媒介生產機構是統治階級操控大眾的意識形態工具。后來的伯明翰學派受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的啟發,將媒介空間場域化,進而辨析從領導到從屬不同階層的文化力量博弈,構建了更為辯證的理論框架。筆者以為,就本文議題而言,其創見性在于,他們不是抽象地思辨媒介技術力量的作用,而是從大眾具體的文化實踐入手探討各種力量的發揮。這就啟發我們思考,在新的媒體情境中,人們究竟是怎么閱讀的?
由于在各種新媒介中,網絡可視為某種“元媒介”,即波斯曼所言的“一種不僅決定我們對世界的認識,而且決定我們怎樣認識世界”的媒介工具[8]。而網絡小說擁有最為龐大的閱讀群體,故而,網絡小說閱讀是一個合適的考察對象。在網絡小說閱讀考察中我們注意到,這一過程自然生成了一個范疇——“更”,它能將新媒介中的讀者、作者和文本有機聯系起來,而所有的文學閱讀都必然是讀者、作者、文本和媒介等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因而“更”為我們的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切入點。
“更”,本指更新,即網絡寫手利用網絡媒介空間不斷發布自己最新的寫作成果,寫手每天更新幾次,就叫幾更。隨之,它也被用來指稱更新的文本篇幅,所以“更”也就成為一個類似于小說“章”“節”一樣的文本結構的計量單位。網絡小說閱讀就圍繞這些“更”展開,或者說網絡小說閱讀就是讀“更”。這就滋生了“追更”“等更”“養肥”等等獨特的網絡文學閱讀行為,也賦予了“更”一定的時間節奏和實踐意蘊。
從閱讀行為與寫作行為的關系來看,讀“更”就是面對一次次未完成的寫作行為。這有些類似于閱讀報刊連載小說,但不同的是,網絡文學寫作是即產即銷,閱讀則是即“消(費)”即感,乃至即感即評。而且,這些閱讀痕跡(點擊率、感想、評價)對于寫手而言也是可見可感的,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后續寫作。這樣,網絡文學實踐中閱讀行為與寫作行為具有明顯的相互伴生性,因而網絡文學閱讀不僅實現了所謂的“實時閱讀”,更是直接對接寫作的介入式閱讀,“作者中心”在此自然解體,就此而言,網絡的確擴大了閱讀權力。但其權力效應卻可能以悖論性的方式存在:一方面它會成為網絡寫作的興奮劑,書迷的好評、打賞會激勵作者不斷“加更”,即寫手自謂的“爆發”,像著名網絡小說家天蠶土豆就以超強的加更能力而著稱;另一方面欲罷不能的讀者會不斷催“更”,催而不得或讀后不滿又會謾罵,這樣的讀者不在少數,它形成巨大的壓力,迫使作者透支自己的寫作能力,乃至生命,使得像十年雪落、青鋆和風天嘯等網絡作家因長年累月的持續寫作相繼過勞而死。強大的閱讀權力變成了閱讀暴力。這是值得我們警示和反思的。或許,只有經過了長期實踐之后,才能形成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協商式倫理,促進二者平等的交互主體關系的形成。而這種協商式的倫理,無疑是我們整個公共領域生活都需要的。
從閱讀行為與網絡小說文本的關系來看,讀“更”意味著經常面對未完成的文本。這樣的文本一般沒有多少科技含量,不會形成所謂的“超文本”,也不見得有伊瑟爾所津津樂道的“空白”“罅隙”,但它因為未完成而自然處于向閱讀行為開放的狀態。為召喚持續的閱讀行為,網絡小說文本一面要盡力迎合讀者的期待視野,一面又要設置足夠大的懸念。讀者因此確實往往欲罷不能,卻無法像傳統閱讀那樣馬上進入下一章,只有焦急等“更”。如此在一“更”與一“更”之間必然出現比較長的閱讀時間空歇,出現閱讀狀態與日常生活狀態的反復切換。但讀者由閱讀引發的精神活動并未停止,許多人會回味故事,推測情節發展,借助新媒體交流平臺,他們會將這些想法訴諸比特符號,發表在網絡空間與書友共享,形成所謂“劇討黨”和“劇透黨”。更有甚者,有的讀者干脆親自操刀,續寫故事,推出所謂“山寨更”,自娛娛人。因此在網絡空間,我們慣見的不是作者獨立編寫的文本,而是小說文本敘事與各式讀者反饋話語彼此雜糅的綿延對話。可以說,網絡文本的未完成性,成為激發網絡閱讀創造性的一大誘因。但是,正如薩特曾說過的:“對于讀者來說,……作品只在與他的能力相應的程度上存在。”[9]在網絡文學語境中,情況更是變成了作品只能為相應的閱讀能力而存在。太多的網絡文學文本閱讀因此淪為一次性格式塔建構過程,這不能不說是網絡文學的阿喀琉斯之踵了。
此外,我們還不應忽略網絡閱讀行為的相互作用。簡言之,網上讀“更”促進了讀者“想象的共同體”的形成。借助網絡媒介提供的交流便利,網文閱讀突破了傳統文學閱讀的孤獨狀態,網絡書迷們自建虛擬社區(如QQ群、貼吧等),形成了一個個閱讀圈。網絡社區讀者群的成員有共同的閱讀興趣,成員間也沒有實質意義的約束,政治學家凱瑟琳·弗羅斯特就指出,沒有證據表明網絡社會已經建立固定的或有凝聚力的社會和政治的關系模式[10]。約束激發了讀者的游牧式行為。因為等“更”,他們無所事事又必須做點什么事,所以發出各式各樣的帖子與書友交流。許多帖子內容與書已經毫無關系,只是“樓主”(發帖者)自己感興趣,或者為了吸引其他人注意。從而,書迷的活動逐漸由“追文”變成了自我表演與展示。說這種游牧式的交往方式是在“抵抗”主流文化霸權顯然言過其實,但其中的確包含了某種“不跟你玩”的疏離態度。
可見,新媒介文學閱讀的確提供了與經典文學閱讀不同的閱讀方式。“拉”閱讀和“碎片化閱讀”都只描述了新媒介閱讀方式的某種極致形態,其實新媒介閱讀本身充滿了悖論性和矛盾感,是人們在新媒介中自發探索建構新的認知圖式的實驗行為的構成部分。新媒介文學閱讀不僅是以快感為目的的輕松閱讀,而且也有意無意地反映了大眾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需求。它或許游離于主流文化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知識分子的文化領導權地位,但是它卻沒有愿望、也沒有能力去消滅紙媒閱讀和經典文學閱讀,因此,當代媒介轉型使文學閱讀實際上迎來了一個更為多元化的時代。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學閱讀時代,我們要說,新媒介閱讀的局限與不足的確毋庸置疑,但是它們已形成了當代文化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試圖切實地推動我們的文化建設與發展,認識新媒介文學實踐、乃至投入其中就應是一個現實的選擇。
[1]趙勇.媒介文化語境中的文學閱讀[J].中國社會科學,2008(5):132.
[2]趙琬微.文化學者張頤武談國民閱讀:數字化帶來閱讀的復興[J/OL].[2015-11-07].http://news.163.com/12/0423/12/7VPCPFG400014JB5_all.html.
[3]李庚.正確地指導青年閱讀古典文學的作品[N].人民日報,1954-11-13.
[4]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2:78.
[5]歐陽友權.網絡文學概論[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72.
[6]季水河,蔡朝輝.輕逸與期許:微博文學的寫作特征探析及發展前景展望[J].湖南社會科學,2011(3):159.
[7]和菜頭.碎片化生存[EB/OL].[2015-11-07].http://news.cnblogs.com/n/160805/.
[8]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06.
[9]薩特.薩特文學論文集[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100.
[10]FROST C.Internet galaxy meets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solidarity after the Internet[J].Information Society,2006,22:45-49 .
(責任編校:鐘巧靈)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and Diversity of Literature Reading Modes in Modern Times
ZHOUXing-jie
(School of Culture and Law,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
In 1980s in-depth reading and reading with ease and fun paralleled with each other, showing that the history of read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was not a lineal decline from in-depth reading to shallow reading. There are optimistic and pessimistic views about literature reading behaviors in the age of new media, and both of them have exaggerated the power of the new media′s technical logic. Reading online-only novels is a typical example, as it represents a reading mode different from that for classical literatures. Therefore, in modern times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has actually led literature reading into a time of diversity.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reading mode; online-only novels; diversity
2016-10-1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網絡小說讀者群體研究”(16XZW006)。
周興杰(1973—),男,湖南懷化人,貴州財經大學文化法律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美學、文化。
I01
A
1673-0712(2017)01-004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