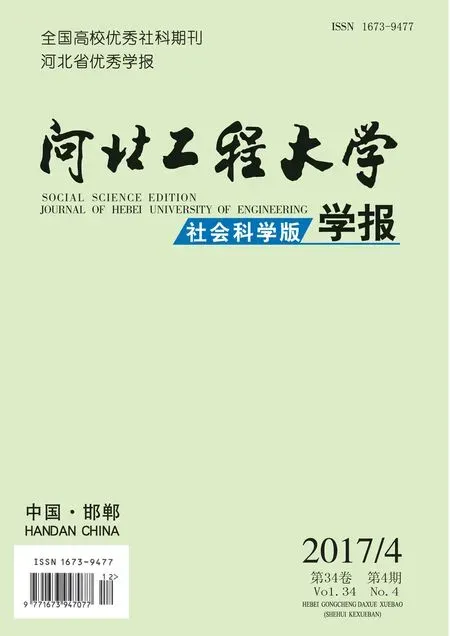村落文化與民間歌謠的傳承——以《更樂民間軼事》為個案
何石妹,常玉榮
?
村落文化與民間歌謠的傳承——以《更樂民間軼事》為個案
何石妹,常玉榮
(河北工程大學 文法學院,河北 邯鄲 056038)
村落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文化,是孕育民間文學的豐厚土壤,民間文學又是村落文化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是傳承村落文化重要載體。而這兩者在當代文化語境下都受到了沖擊,呈現出走向沒落的趨勢。村落文化的全面研究和村落生活空間的深入發掘成為必要,民間文學的現實存在狀態也成為值得關注的問題。《更樂民間軼事》是一個極具特色的個案,它體現出村落文化與民間歌謠創作的密切關系,又呈現了當代民間歌謠創作在文化傳承中的獨特作用。本文以此為個案,為當下的村落文化傳承與民間歌謠創作提供合理的評價立場。
村落文化;民間歌謠;傳承
村落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也是地域文化中最具本源性和傳承性的部分。中國村落從十九世紀開始進入西方人類學、社會學的研究視野,隨著研究理論的深入,對中國鄉村的研究范圍從早期的村落經濟逐漸擴大更為廣闊和復雜的村落文化,包括物質建筑、鄉村經濟、人際關系、文化教育、宗法禮制、民俗信仰等多方面的內容[1]。由于目前研究成果更多集中于物質形態和經濟形態,對于村落中民眾的生活空間和精神世界的調查研究在近年來呼聲很大,而能夠體現這一點的村落非物質文化遺產成了熱門的研究資源,如各種民間技藝、節日民俗和民間文學等。作為民間文學的一部分,民間歌謠也逐漸被人類學和社會史研究所重視,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
近些年的口述史研究工作,為地域性民間歌謠采集和研究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方法和大量資源,但當我們試圖以口述史研究的模式去分析民間歌謠能夠提供的社會學、地方學價值時,遭遇了兩個主要的問題,一是時至今日,除少數邊遠民族的史詩性歌謠之外,大部分的鄉村歌謠已經極為散落,即使是80年代以來的“三套集成”工程,能夠提供的特定區域的歌謠也大多是零散和簡短的,很難系統地呈現出村落文化的面貌;二是作為口承文學,民間歌謠的當代傳承走向衰落,村落經濟的轉型、多元文化的沖擊、書面傳統的主導,均使得民間歌謠的傳唱逐漸減少乃至消亡,這和傳統村落文化的失落是同一個過程。
在這樣的困境中,當代民間歌謠的創作更加被認為是難以承續的行為,村落文化也開始從民間話語的表達中逐漸消失。但這種千百年來傳承至今,用歌謠來講述民族歷史、描繪生存世界、傳授生存經驗的表達沖動卻沒有完全失落,筆者在田野調查中就發現,在一些偏僻的鄉村中, 依然有一些散見的民間歌謠傳唱和創作行為。而河北涉縣更樂村張某[2]的民間歌謠創作,可以說是當代民間歌謠創作中一個罕見的特例——他進行了系統的民間歌謠文字創作,以歌謠的形式再現了更樂古村的歷史文化全貌。他把作品結集為《更樂民間軼事》,于2013年1月出版。《更樂民間軼事》的面世并沒有在文學界引起很大的反響,卻足以成為我們研究村落文化與民間文學當代傳承的一個典型個案:在大的創作語境已不復存在的前提下,一個中原地區的村民如何以歌謠的方式完成對正在消失的村落文化的系統描述,這種描述對村落文化的延續和民間歌謠的傳承有什么樣的意義,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一、村落文化孕育出的個體民間歌謠創作
《民間歌謠軼事》是以文字出版的形式面世的,但時至今日,我們已經不能單純地以是否為純粹的口頭創作、群體流傳來界定民間文學,而應當把考量的重點放在民間文學的本源意義“民間”上,從生存土壤、精神內涵、話語立場和價值功能等層面去判斷它是否屬于民間范疇。在這個層面上,張某的歌謠創作是屬于民間范疇的,而這個“民間”更具體一點,就是其所生長的更樂村傳統文化。
張某于1949年出生,家中祖輩生活于更樂村一帶。更樂村古稱上黨,始建于春秋戰國時期,唐開元時發展為“戶三百”大型自然村。在改革開放之前,更樂村基本延續著農耕社會形成的農業文明形態,在居住環境、生活方式、倫理關系、風俗習慣等方面都保留了傳統村落文化的特征。在這樣的背景下,從小沒有上過太多學、一直生活在更樂的張某,無形中把更樂傳統文化作為他主要的文化食糧,在遍布古村的民居、古跡中,在節日慶典的儀式里,在長輩的故事、歌謠里完成了生存知識的汲取與道德教化的熏陶。在《更樂民間軼事》中,張某描述了大量的更樂村民俗習慣節慶儀式,他在采訪時表示,這些都是他親身參與見證過的,如今他還能詳細說出如祭香、求雨等儀式上的種種過程與細節。作為從未遠離過的一名村民,張某也同更樂村一起參與和感受著時代的變化,并以最真實的方式傳達出對時代變遷的體會。而生長于更樂,從長輩、鄉鄰那里聽到的故事、傳說和歌謠,更是孕育了他豐富的精神世界,并轉化為他原生的表達方式。在采訪中筆者問他既然要寫書,為什么還要以口頭歌謠的形式進行創作,他回答歌謠是他最拿手的表達方式,從小讀書不多,而母親、長輩擅唱歌謠,他耳濡目染,張口即能唱出一二句,仿佛是與生俱來的本領。這種“本領”的形成,不排除張某語言能力的出眾,但若非多年的鄉村生活、民間語言環境的熏陶是無法實現的。
二、“歌謠能手”對村落文化傳承責任的承擔
可以說在深厚的村落文化與民間傳統的土壤中,幾乎每一位村落成員都會生長出民間話語表述的因子,事實上今天我們還可以采訪到在更樂村能夠傳唱歌謠、講述故事的老人,但他們大部分只是能夠將過去的歌謠、故事片段復述一二,并表示這些“老掉牙”的東西已經極少被關注。而張某卻花費了多年的時間搜集、整理更樂民俗典故、奇聞軼事,并耗費六年的時間進行反復寫作,才完成了《更樂民間軼事》的創作。我們可以認為他最基本的出發點是出于對更樂這片土地的熱愛,但能夠把熱愛轉化為描述的沖動,并堅持完成一場系統的描述與表達,并不是每一個村民都能夠完成的。
我們在研究傳統民間歌謠時會發現,在一個較小的地域范圍內(村落、鄉鎮),總會存在著一個或幾個著名“能人”,他們往往成為歌謠創作和流傳的主體。張某在更樂就是這種“能人”的代表。他曾經獲得過“農村十面紅旗支部書記”,“勞動模范”、“為民致富”等稱號,退休后被當地的工廠返聘做管理者,除此之外,還經常擔任鎮上的婚禮“執事”。他思維活絡、擅于組織,對各種儀式習俗了如指掌,而且嘴皮利索,在各種典禮中能夠隨機應變,出口成章地說唱儀式歌謠和吉利話。這個“執事”的部分功能其實已經接近于民間藝人。
張某這樣的“能人”,不只是民眾文化生活的活躍分子,也是村落文化的傳承者。而由于語言才華的出眾,他們能夠把自己民族的歷史、生存的經驗講述得更為生動和完整。在這樣的期待下,歌謠“能人”無形中承擔了一種“言說代表”的責任,很容易滋生出一種對于描述民間生活、傳承民間文化和表達民眾心聲的責任感。對于時代變遷導致的村落文化的沒落,處于言說前沿的張某感受更為鮮明,而從文化土壤中滋養出來的使命感,使他依然愿意日益在失去受眾的語境下發聲。如果說,傳統藝人是在順向的文化傳統中,不自覺地承擔文化傳承的責任,進行文學創作,張某這樣的當代歌謠創作者,則是在逆向的語境中,自覺地承擔著挽救民間文學傳統和傳承村落文化的責任。
三、個體民間歌謠創作在村落文化傳承中的特點與價值
關于傳統民間歌謠在民間文化傳承中的作用,已經被諸多學者論證過,在特定的村落文化中,民間歌謠同樣是記錄歷史、展示風貌的載體。但是在某個村落范疇內,歌謠往往是散落的,呈現的都是片段的一人一事,很難在有序的時間和空間中全面呈現村落文化。尤其在更樂這樣的中原村落,傳統民間歌謠的收集已成難事,而從這些零散的只言片語中恢復真實的村落文化生活原貌,是許多人類學、社會學者面臨的共同難題。
張某的《更樂民間軼事》則是一部完整的歌謠集,分為“古村概況”、“古跡廟堂”、“民俗風情”、“年節習俗”、“婚喪嫁娶”、“古今人物”、“農家婦女”、“農業農事”、“奇聞軼事”和“農村經歷”等十二章,雖不絕對嚴謹、但相對有序地進行了更樂村落文化的整體描述。張某做了至少四年的調查和采風活動,從更樂古街道、布局的確認、各種建筑遺跡的考察、民風民俗、軼聞傳說的搜集,這個過程與地方文化研究者的田野調查極為相似,也正是這些寶貴的資料,使得《更樂村軼事》成為蘊含著更樂村豐富文化的寶庫。這其中有詳細的村落布局、古跡遺址,有祭香、求雨等完整的儀式習俗展演過程,有豐富的歷史人物故事,在這個古村歷史在當代人的視野中逐漸遠去的時候,張某以他的作品完成了村落文化的完整記錄。
但與學者客觀記錄的結果不同,張某最終呈現出的既不是原汁原味的原始口述資料,也不是像作家一樣經過精心加工過的文學文本,而是以民間歌謠形態為載體的二次創作。這個創作過程十分有趣,在采集、記錄資料的第一步就已經開始:當張某聽到一個關于更樂古跡或者名人的傳說時,他常常直接以即興創作的歌謠將之記錄下來,回去之后再進行加工整理。而初稿完成之后,他會再次回到村民之中,將歌謠念給村民,聽取他們反映和意見。這樣的創作方式,首先保證了張某歌謠創作的純粹民間立場。張某之所以能夠在現場就能夠將散落的村民口述轉化為歌謠,并獲得民眾的認可,除了他出色的語言能力之外,根本的原因是張某和村民處于同一個話語系統之中,他們所關注和想要表達的東西是一致的。例如《北洞》一節,描述村民請碧霞元君:“說撲空、沒撲空,碧霞元君顯神靈。用手一指起狂風,招來葷山昭懿君。”這種“神神道道”又栩栩如生的形態,是最普遍的民間認知和表達方式,可以說張某是以一名普通民眾的立場,對自己村落的歷史文化進行關照的。
不可避免地,張某以一己之力對村落文化的“拯救”行為遭遇了尷尬的境遇:一方面,即使在更樂村這樣的傳統村落中,口頭傳統業已中斷,雖然他以“能人”的身份召集村民聽他講唱歌謠,但這些歌謠極少再被口頭傳播。如今在更樂村中,像他一樣能夠講唱歌謠的老人已經越來越少,而生長于多元文化環境中的年輕一代則對這種形式失去了熱情。而當他以文字出版的方式讓作品面試,卻面臨書面傳統標準對其文學性的批判。就連張某自己,也存在對書面權威的敬畏。這使得他在文字出版的過程中,開始有意識地向書面傳統的評價體系靠攏。
到目前為止,《更樂民間軼事》并沒有在學術界和文學界引起較大的反響,這不得不說是一件憾事:從村落文化保護的角度來看,如此完整和系統地描述一個村落歷史文化的當代資料極為少見,正如張某所說,如果他不言說,恐怕再沒有人去如此詳細生動地言說這個古老的村鎮了。而張某的歌謠創作本身,又是村落文化的一部分,它一方面說明了豐厚的民間文化土壤孕育了民眾言說歷史、表達自身生活圖景的熱情,另一方面,它為民間文學的延續和發展提供了一條思路:傳統歌謠那種即興創作、現場表演并口口相傳的創作和傳承模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民眾以歌謠“發聲”的內在需求并沒有磨滅,這種發聲在當代依然擁有熱情而忠實的“代言者”,即民間歌謠個體創作者,他們的作品應當得到符合民間文學價值體系的判斷和評價。
當代的學術關注、文學評價對張某這樣的個體創作者來說,同樣是一種“土壤”,倘若這種土壤對其創作給予了合理的定位和充分的肯定,無疑會成為一種催生更多創作熱情的動力,這樣的個體創作成為民間文學延續的主體力量,進而成為村落文化、乃至地域文化、民間文化傳承的載體,也并非不可能的結果。
[1]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J].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0-21.
[2]應作者要求,隱去其真實姓名,以“張某”代替。
[責任編輯 王云江]
Village culture and the inheritance of folk songs——A case study of " Folk anecdotes in Gengle"
HE Shi-mei, CHANG Yu-rong
(School of Arts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56038, China)
The village culture is the roo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rich soil of folk literature. Folk literature is par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village culture. it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inheriting the village culture. Village culture and folk literature are influenced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text, showing a trend of declin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village culture and give a thorough exploration of the village living space. The contemporary heritage and the creation of folk songs can not be ignored. "Folk anecdotes in Gengle " is a very special case. It reflects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culture and folk songs, and the contemporary folk songs creation play a unique role in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as a case study, hopes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evaluation for the current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village and folk songs.
village culture, folk songs, inheritance
10.3969/j.issn.1673-9477.2017.04.025
I207.7
A
1673-9477(2017)04-075-03
2017-07-10
河北省社科基金2017年度項目(編號:HB17SH016)
何石妹(1981-)女,河北邯鄲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民間文學與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