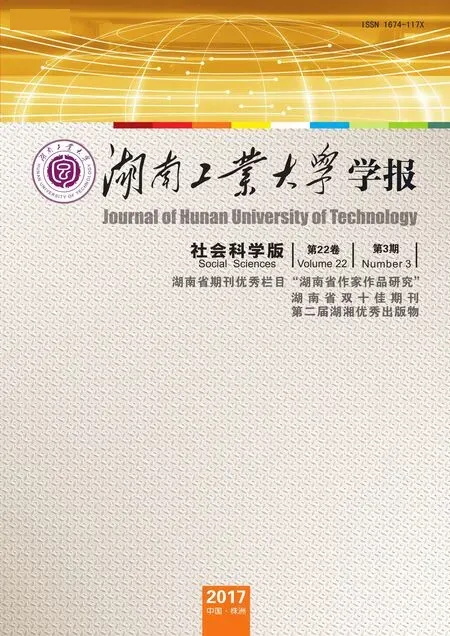中國文學外譯模式考
劉紅華
(湖南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株洲 412007)
中國文學外譯模式考
劉紅華
(湖南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文學外譯是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重要環節。海外部分中國文學外譯本因過分忠實于原作而不能完全為目的語讀者理解與接受,部分因迎合目的語讀者的閱讀習慣而無法充分地傳達原文中所承載的中國文化。中國文學外譯模式有助于避免出現有問題的譯作,為中國文化準確而有效地“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啟示:以中國政府主導的中外合作模式為文學外譯之翻譯活動發起者模式;以具有純熟的雙語雙文化能力、濃厚的中國情懷以及堅定的翻譯立場的譯者為文學外譯之譯者模式;以兼顧譯文忠實與流暢的策略為文學外譯之翻譯策略模式。
中國文學外譯;翻譯活動發起者;譯者模式;翻譯策略
在中國文化“走出去”已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今天,國內多位譯界學者們紛紛為中國文化如何通過翻譯“走出去”出謀劃策,從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者模式、翻譯策略與方法、譯介途徑、譯介受眾、譯介效果等多方面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并建構了具體的中國文化外譯模式。譯界目前建構的文化外譯模式綜合考慮了翻譯及翻譯之后的傳播與接受環節,不可謂不高屋建瓴,為中國文學與文化更有效地“走出”國門提供了真知灼見。
中國文學在國外的傳播和接受效果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各種出版與銷售策略的改善等息息相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業,需要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翻譯足夠的文學作品并將其“送出去”是目前比較現實的一種策略。[1]翻譯足夠數量的中國文學作品的確可為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做足準備工作,但是把握譯作傳播效果這一關也不可或缺。目前海外部分中國文學外譯本存在兩個問題:其一,譯文過分忠實于原作;其二,譯文過分迎合目的語讀者的閱讀興趣。第一個問題可能導致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效果不佳。第二個質量問題可能導致中國形象與中國的文化內涵在翻譯中受損。為解決上述問題,須產出既忠實于原作又符合目的語讀者期待的譯作。
究竟怎樣的外譯模式有助于產出既忠實又流暢的譯作呢?對于這個問題,譯界學者見仁見智,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基于學者們對中國文化外譯的現有研究成果,并結合目前部分海外中國文學的外譯本質量堪憂的問題,本文從翻譯活動發起者、譯者模式以及翻譯策略這三個方面來探究中國文學的外譯模式,以確保產出更適合“送出去”的中國文學的外譯本。
一 中國文學外譯活動發起者
翻譯活動發起者,主要指發起翻譯活動的出版機構、文學代理人、譯者或作者等。中國歷史上出現的中國文學外譯發起者主要包括17世紀的西方傳教士、20世紀初的中國留學生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中國政府機構。在這三種發起人中,中國政府機構是較受譯界學者詬病的,其發起的翻譯活動被作為不成功案例的代表加以抨擊,理由是:由其組織翻譯出版的譯作在國外的傳播與接受效果并不理想、收效甚微。比如《中國文學》(英文版)雜志“譯介效果并不顯著”。[2]《熊貓叢書》同樣“未獲得預期的效果。除個別譯本獲得英美讀者的歡迎外,大部分譯本并未在他們中間產生任何反響”。[3]《大中華文庫》系列叢書“除個別幾個選題被國外相關出版機構購買版權外,其余絕大多數已經出版的選題都局限在國內的發行圈內,似尚未真正‘傳出去’”。[4]
為傳播與接受效果起見,中國文學外譯的發起者似乎離不開國外出版社,因為他們更能把握并傾向于迎合目的語讀者的閱讀興趣與閱讀習慣,能讓中國文學在國外的傳播與接受效果更佳。但是,由于所有文化從本質上講,對外來事物都是抵制的,一個文化在需要吸收外來“他者”補充的同時,也會抵制外來的“異質”,以確保本族文化的“純粹性”與“完整性”。[5]國外出版機構因此對外語文本和文化實施“民族中心主義的暴力”“透明的”(transparent)、“流暢的”(fluent)歸化翻譯就是這一“暴力”實施的具體表現。國外出版社或編輯大都喜歡根據自己和英美讀者的標準對譯文進行大幅度刪減和隨意改寫。[6]由此可見,國外翻譯活動發起者在保留中國文化的“純粹性”與“完整性”上并無太大保障,更甚者,他們對譯文的隨意改寫行為還極有可能使中國文化在譯文中遭到扭曲。
因此,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活動發起者應該是以中國特別是中國政府機構為主導。“各國文學的外譯離不開政府的支持”,[7]而且“主動‘送出去’,特別是政府牽頭‘送出去’,已成為除英語國家之外多數國家(地區)文學外譯的常態,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以中國政府牽頭的翻譯活動在翻譯的質量把關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對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責任心也相對較大。但在譯材選擇、翻譯策略與方法、譯作銷售與傳播方法等方面,中國政府機構可以借鑒西方出版社的經驗,選擇性地聽取他們的意見與建議,爭取綜合考慮中國文化的“完整性”與目的語國家讀者的閱讀習慣,做到讓“異域”的中國文化毫無理解障礙地被西方讀者接受。這便涉及到中國政府機構與西方出版社、漢學家、代理人等的合作,只是中方要掌握這種合作模式的主動權,后者只能作為前者的協助者。
中國政府機構應怎樣把握與西方出版社、漢學家、代理人等合作的度才能夠達到中國文化真實而有效在國外傳播的目的呢?首先,中國政府機構應宏觀調控翻譯的生產與傳播過程,從整體上把關中國文學外譯的選材、翻譯、定稿、出版的全過程,杜絕西方出版機構為迎合目的語讀者而隨意篡改中國文學的行為,確保最終出版的譯作的“完整性”與“純粹性”;其次,中國政府機構應借助外力,彌補自己在把握西方讀者閱讀興趣、接受能力等方面的缺陷,確保“不引起海外受眾對我國文學和文化的反感”[1],甚至能增強其“吸引力與感染力”。[8]如在譯材選擇與定稿階段聽從西方漢學家、編輯等的建議;在翻譯階段尋求漢學家的幫助;在譯作出版階段可以將版權轉讓給西方出版社,一則可以消除外國讀者對中國官方出版社的抵制而帶來的銷售障礙,[9]二則畢竟世界著名出版機構是擴大中國小說在國外傳播的有效途徑。[10]
二 中國文學外譯之譯者素養
國內多位譯界學者曾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出謀劃策。在對譯者模式的探尋中,有的認為為了中國文化少受損害,“中國譯者模式”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11]有的考慮譯作在國外的傳播與接受效果,建議“不妨請外援”,[12]或認為“漢學家模式”為較佳譯者模式,[13]10有的則綜合考慮前兩個問題,認為“中西合譯模式”[14-15]最為理想。同時考慮中國文化通過翻譯傳播的真實性與有效性,“中西合譯模式”的確最為理想。因為有些漢學家可能會因學藝不精而對中國文化無意誤譯,也有一些可能會為了自己或自己國家的某些利益而故意誤譯中國文化。而大部分中國本土譯者因對目的語語言規范的掌握還不夠純熟,對目的語讀者興趣的把握還不夠到位,產出的譯作無法滿足目的語讀者的閱讀期待。但“中西合譯模式”也并非無懈可擊,雖然這種譯者模式能讓中外譯者各取所長,跨越差異,卻也需要在翻譯的各個環節不斷地磨合,比較費時費力,最后還不一定能達成共識。胡安江曾提及,像葛浩文一樣具有中國經歷、中文天賦、中學底蘊以及中國情誼的漢學家是最理想的譯者模式。[13]14漢學家本就不多,符合這四個條件的漢學家更是有限了。
筆者認為有一類譯者可同時解決漢學家數量有限問題與中西譯者合作耗時耗力的問題,可以考慮作為中華文化外譯的較佳譯者模式。這一類譯者就是居住于海外的華人譯者與居住在中國的外裔譯者,即“離散譯者”。[16]他們集漢學家與中國本土譯者兩者的優勢于一身,既具有漢學家對目的語的純熟運用能力以及對目的語讀者閱讀興趣的精準掌控能力,也具有中國譯者對中國的濃厚情懷,對中國文化的充分理解的能力。啟用離散譯者暫且可以解決中國文化外譯優秀譯者缺失的問題。畢竟目前移居海外的華人數量較為可觀,居住在國內的外國人也日漸增多。
除了能力與漢學家不相上下之外,離散譯者對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貢獻也并不亞于漢學家。不管是居住在中國的外國譯者沙博理、戴乃迭等,還是居住在國外的中國譯者聶華岺、王際真等,都對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沙博理翻譯了200部中國文學作品,譯作題材豐富、質量上乘,被譽為“洲際文化的艄公”,其《水滸傳》英譯本在譯界被奉為“信、達、雅”佳作典范;戴乃迭與其丈夫楊憲益合作翻譯了“整個中國”,共翻譯了220多部中國文學作品,其中獨譯作品80余部,與楊憲益合譯作品140 余部,作品涵蓋各種題材,夫妻二人合譯的RedMansions(《紅樓夢》)享譽海內外;聶華苓是第一個在臺灣翻譯《毛澤東詩詞》的人,其開辦的國際寫作坊成為世界了解中國文學的窗口;王際真翻譯了《紅樓夢》《戰國策》《呂氏春秋》《儒林外史》《鏡花緣》等古代典籍與名著,還介紹了魯迅、老舍、張天翼、葉紹鈞、凌叔華、巴金和沈從文等中國現當代作家,被夏志清稱為“中國文學翻譯的先驅”。
具有純熟的雙語雙文化能力以及對中國有特殊感情的譯者,的確具備在譯文中準確地保留原作中文化內涵的能力與情懷,但由于各種利益的驅使,他們在實際的翻譯中不一定會做到這一點。上文提到部分漢學家可能會因各種利益而扭曲中國文化,部分離散譯者亦是如此。如離散譯者張愛玲就曾寫作并翻譯了丑化共產黨與新中國的作品《秧歌》與《赤地之戀》。這兩部作品是張愛玲在復學無門,投奔美國駐港新聞處之后,出賣靈魂,胡編亂造,寫出的“反共反華”的壞小說,后來她還將這兩部小說譯成英文出版。可見,除個人能力與情感因素之外,譯者還必須具有堅定的翻譯立場,這種立場不能因個人利益而有絲毫改變。
綜上,符合以下三個條件的譯者可以考慮作為中國文學外譯的較佳譯者模式:1.具有純熟的雙語雙文化能力,包括對中國文學的透徹理解能力以及清晰的目的語讀者意識;2.具有濃厚的中國情懷,即熱愛中國及中國文化;3.具有堅定的翻譯立場。
三 中國文學外譯之翻譯策略與方法
翻譯策略包括歸化與異化。歸化追求譯文的流暢易懂,符合譯入語語言及文化規范,而異化追求原文語言及文化的特色的傳真,以豐富譯入語語言及文化。[17]譯界在翻譯中同時存在歸化與異化策略上已基本達成共識,贊成歸化與異化應相得益彰。[18-21]但是在中國文學的外譯策略的選擇上,學者們對于以哪種策略為主的問題仍然各執一詞。有的贊成應以異化為主、歸化為輔,以便更好地保留中國的異域文化,[22-23]有的則贊同歸化為主、異化為輔,以便增加譯本的可讀性。[24-25]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加以爭論已無太大意義,畢竟要保證中國文化在海外的有效傳播,譯者應盡可能地保留文學作品中的“異質文化”,同時考慮譯文的可接受性。因此,我們目前要探究的是究竟在翻譯中如何具體實施歸化與異化策略才能達到以上兩個目的。在這一點上,筆者認為孫致禮的觀點值得借鑒。他認為,在文化層面上,譯者要力求最大限度的異化以保存原作的風味,而在語言層面上,譯者則要進行歸化以利于通俗易懂。[20]這種適度調和,既忠實于原作,又照顧了讀者的閱讀習慣,的確不失為歸化與異化兩種策略相得益彰、圓滿調和之舉。此處語言層面上的歸化是指符合目的語的語言規范,包括篇章布局規范、遣詞造句規范等。
文化層面最大程度的異化與語言層面的歸化(下文稱“圓滿調和策略”)可解決“異化為主,歸化為輔”以及“歸化為主,異化為輔”模棱兩可的問題,也為這兩種觀點的殊途同歸找到了緣由。“異化為主,歸化為輔”的觀點傾向于保留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實際就是號召文化層面的異化;“歸化為主,異化為輔”的觀點傾向于照顧讀者的閱讀興趣與理解能力,也即語言層面的歸化。這兩種觀點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異曲同工。在文化層面的異化策略可減少中國文化外譯中文化的損失,在語言層面的歸化策略則可迎合目的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可見,這種翻譯策略的采用的確可以避免在翻譯中出現本文開篇提及的兩個質量問題。
“圓滿調和策略”之于中國文化外譯的較佳之處還體現在幾位著名翻譯家對這種策略的青睞上。著名漢學家、翻譯家葛浩文認為譯者既要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盡可能保留原文文化的“異質性”,又要保持譯文的流暢性。[6]沙博理認為要把真實的中國介紹給全世界,但是必須要“用我們的英語把我們的中文意思傳達出來”。[26]
“圓滿調和策略”指導譯者在忠實于原作的同時關照讀者的閱讀習慣與接受能力。在這一策略指導下的翻譯方法可以為中國文學外譯譯者提供一定的參考:
1.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國文化詞的音、形、義。如在命名文化詞方面,對于無特殊含義的人名、地名等,譯者應直接采用音譯法,保留中國語言的拼音文化;對于特殊含義的人名、地名等,譯者應采用直譯法保留其形與義;對于一部分有特殊含義而另一部分又無特殊含義的人名、地名等,譯者應采用音譯+直譯法,同時保留其音、形、義。
在習語方面,譯者應盡量采用直譯法保留其所承載的文化意象與準確含義。對于部分歇后語,在直譯令人晦澀難懂時,譯者則可適當文內釋義,以便讀者清楚理解其準確含義。
譯者最大限度地保留文化詞的音、形、義,這其中的“最大限度”體現在譯者可視情況對部分文化詞進行意譯處理。這些文化詞包括:文化內涵厚重,大段注釋都無法解釋清楚的典故;形象性或邏輯性不強,直譯之后令目的語讀者費解的成語或歇后語;雖有形象性而格調不高或比較粗俗的,直譯之后影響中國形象的成語或歇后語。
2.合理遵循目的語的篇章布局規范。如在段落劃分上,譯者應遵循一個段落有且僅有一個主題以及人物引述獨立成段的標準。如將原作中包含幾個主題的一個段落按主題切分成幾個小段;將原作中講述一個主題的幾個段落融合成一個段落;將人物的引述都獨立成段。
在情節的處理上,譯者通過調整句子甚至是段落的順序來實現譯文篇章的銜接與連貫,如在缺乏主題句段落的段首添加主題句,或將段落中已存在的主題句移至段首;在每章節開頭添加主題段落,或將散落在章節內的主題段落移至章首。
在句法結構上,應巧妙使用英漢語共有的句法結構。游離句是英漢語中共有的一種句法結構。譯者可在翻譯中使用游離句來達到忠實于原作句式以及迎合目的語讀者閱讀習慣雙重效果。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中華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導意見》中倡導“向世界闡釋推介更多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精神、蘊藏中國智慧的優秀文化……增強中華文化親和力、感染力、吸引力”,[8]強調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數量與質量。為中國文化“送出去”積累足夠多的、高質量的中國文學的外譯本,是中國文學外譯艱巨而長久的使命。而符合習總書記《意見》中所倡導的高質量的中國文學的外譯本應具有兩個特點:其一,忠實傳達原作中所承載的中國精神與文化;其二,照顧目的語讀者的閱讀興趣與接受能力。本文的努力方向正是探尋合適的外譯模式以便產出具有以上兩個特點的譯作。經探究發現,中國文化外譯模式可為產出上述高質量譯作提供一定的借鑒:(1)翻譯活動發起者:以中國政府為主導,西方出版機構、漢學家等從旁協助;(2)譯者模式:具有純熟的雙語雙文化能力、濃厚的中國情懷、堅定的翻譯立場的譯者。(3)翻譯策略:異化與歸化圓滿調和,即在文化層面以異化為主,在語言層面以歸化為主,以便在目的語讀者充分理解原作的前提下忠實傳達中國的文化內涵。
[1] 韓子滿.中國文學的“走出去”與“送出去”[J].外國語文,2016(3):65-73.
[2] 鄭 曄.國家機構贊助下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以英文版《中國文學》(1951—2000)為個案[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2012.
[3] 耿 強.文學譯介與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熊貓叢書”英譯中國文學研究[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2010.
[4] 謝天振.中國文學走出去:問題與實質[J].中國比較文學,2014(1):2.
[5] BERMAN Antoine.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M].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149.
[6] 李文靜.中國文學英譯的合作、協商與文化傳播:漢英翻譯家葛浩文與林麗君訪談錄[J].中國翻譯,2012(1):57-60.
[7] 馬士奎.英語地位與當今國際文學翻譯生態:《譯出與否:PEN/IRL國際文學翻譯形勢報告》解讀[J].民族翻譯,2013(3):36.
[8] 習近平.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中華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導意見[EB/OL].[2016-11-04].http://www.ihchina.cn/11/33213.html.
[9] 鮑曉英.中國文化“走出去”之譯介模式探索[J].中國翻譯,2013(5):62-65.
[10] 李清柳,劉國芝.外文社版英譯中國當代小說在美國的傳播[J].中國翻譯,2016(6):37.
[11] 潘文國.譯入與譯出:談中國譯者從事漢籍英譯的意義[J].中國翻譯,2004(2):40-43.
[12] 謝天振.譯介文學作品不妨請外援[N].中國文化報,2013-01-10(2).
[13] 胡安江.中國文學“走出去”之譯者模式及翻譯策略研究:以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為例[J]. 中國翻譯,2010(6):10-14.
[14] 黃友義.漢學家和中國文學的翻譯:中外文化溝通的橋梁[J].中國翻譯,2010(6):16-17.
[15] 胡安江,胡晨飛.再論中國文學“走出去”之譯者模式及翻譯策略:以寒山詩在英語世界的傳播為例[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2(4):54-61.
[16] 劉紅華,黃 勤.譯者聶華苓研究綜述[J].翻譯論壇,2015(2):64.
[17] 劉艷麗,楊自儉.也談“歸化”與“異化”[J].中國翻譯,2002(6):22.
[18] 郭建中.翻譯中的文化因素:異化與歸化[J].外國語,1998(2):12-19.
[19] 陳麗莉.翻譯的異化和歸化[J].中國科技翻譯,1999(2):43-45.
[20] 孫致禮.翻譯中的異化與歸化[J].山東外語教學,2001:32-35.
[21] 羅選民.論文化/語言層面的異化/歸化翻譯[J].外語學刊,2004(1):102-106.
[22] 孫致禮.中國的文學翻譯:從歸化趨向異化[J].中國翻譯,2002(1):40-44.
[23] 張智中.兼容并蓄 雙層操作:異化歸化之我見[J].語言與翻譯,2005(2):44-48.
[24] 王志勤,謝天振.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問題與反思[J].學術月刊,2013(2):21-27.
[25] 汪慶華.傳播學視域下中國文化走出去與翻譯策略選擇:以《紅樓夢》英譯為例[J].外語教學,2015(3):100-104.
[26] 沙博理.中國文學的英文翻譯[J].中國翻譯,1991(2):4.
責任編輯:李 珂
Exploration on the Translation Model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U Hong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s “going out” strategy. The quality of some overseas translated tex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yet to be improved. Some of the translated texts are too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o be completely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the target readers, while others cater for the target readers’ reading habit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Chinese culture reflected in the original texts couldn’t be fully transmitted.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model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uld avoid the production of the translations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hence providing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hinese culture’s “going out” in an accurate and effective way. Firstly, its initiator should be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model l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condly, its translator model should be the translators with skillful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competence, bearing a deep love for China and taking a firm translation stand. Thirdly, it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those which could realize both faithfulness and fluency of th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itiator; translator mode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3.002
2017-04-09
劉紅華(1983-),女,湖南永州人,湖南工業大學講師,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社會翻譯學、文學翻譯。
H059
A
1674-117X(2017)03-0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