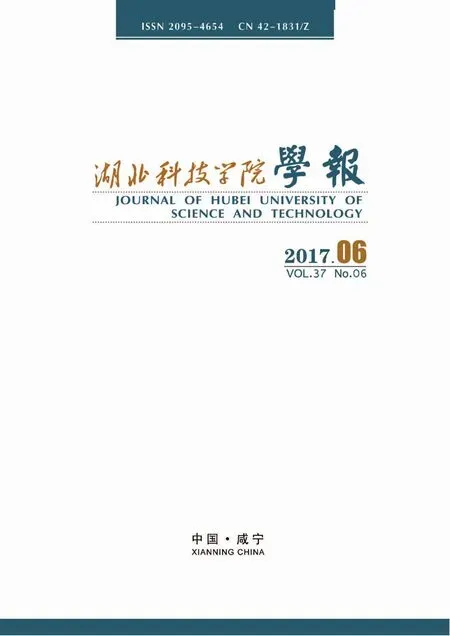曉蘇小說中的瘋傻書寫
吳平安
(武漢市洪山高級中學,湖北 武漢 430074)
曉蘇小說中的瘋傻書寫
吳平安
(武漢市洪山高級中學,湖北 武漢 430074)
曉蘇將瘋癲書寫與憨傻書寫別開來,納入到民間化敘事中,尋找到一個關注底層生理和心理苦難獨特視角,使小說中同一類型人物呈現出不同的樣態,從而豐富了文學的多樣性,拓展了小說的審美空間。
瘋癲;憨傻;悲劇性;喜劇性
撇開世界文學中的瘋癲書寫不論,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經典亮相,自然當屬《狂人日記》了,魯迅筆下的瘋癲,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瘋癲,是政治狂人的做派,其直接指向是對兩千年“吃人”封建禮教的顛覆與清算,它只能是五四時期思想啟蒙的文學表達。秉持民間敘事立場,以寫“有意思的小說”為美學追求的曉蘇,顯然無意去賡續如此高大上的文學傳統,不過這并不妨礙他將瘋癲書寫接過來,納入到民間敘事中去。對于這種獨特的、非常態的敘事策略,曉蘇其實有著清醒的理論自覺,他甚至在博士論文中,將瘋癲視角做了更細化地切分:“有些研究者把瘋癲視角與傻瓜視角并為一類,筆者認為這種合并似乎不太恰當。因為傻瓜主要是智力問題,瘋癲則主要是精神問題,而智力低弱者的敘事和精神失常者的敘事顯然會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樣態。因此,我們不能把瘋癲視角與傻瓜視角混為一談。”[1]
有別于書齋學者的純理論研究,曉蘇的思考有在豐富的創作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經驗做依托,凝結著自身在小說創作中探索的感悟、發現和提升。在我看來,這一切分的意義在于,它放大了中外作家都十分鐘情的瘋癲書寫范圍,往大里說,是一個作家對小說審美空間的拓展。只要分析一下相關作品,就很容易領略到在曉蘇筆下,瘋癲書寫和傻瓜書寫,的確是“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樣態”。
在我讀到的曉蘇小說中,《酒瘋子》大概是唯一一篇可以歸入瘋癲書寫的作品,之所以使用“瘋癲書寫”(或者“瘋癲敘事”),而不用論文中提及的“瘋癲視角”,是因為主人公酒瘋子袁作義,其實并非“視點”人物,小說的視點是開雜貨鋪的“我”,通篇是透過這個精明的鄉村小老板的眼睛,觀察袁作義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的;從題目即可看出,這是一個正常人在酒精作用下暫時性的“瘋癲”,與病理學意義上的瘋癲不是一回事,完全可以視為“常態”瘋癲書寫的一個變種。
“見了酒比見了自己的親媽還親”的袁作義,是一個可憐可悲的小人物,橫行鄉里的村長霸占了他的妻子,自己被打發出去借酒澆愁。酒瘋子喝酒的第一個階段,是借酒壯膽,平常“膽子比老鼠還小”的人,在酒精作用下,用鄉野民間最惡毒的語言詛咒村長,宣泄心頭的奪妻之恨。佛家視酒為昏狂之藥,能使眾生思亂神昏,心生顛倒,故原始佛教經典《阿含經》中,即將飲酒列為五戒之一,大乘小乘、出家在家,皆須恪守,“遮止”不犯。袁作義自然不信那一套,他的飲酒哲學是,“度數越高越過癮,喝了像當神仙似的”。酒瘋子喝酒的第二個階段,是幻覺妄想,酩酊大醉的袁作義果然就當上了“神仙”,在他有限的想象力中,一村之長就是神仙,他被“任命”為“代理村長”了。在明眼人雜貨鋪老板看來,他這是思亂神昏了,是心生顛倒了,他“顛倒”的是官與民的身份。當了村長的袁作義就有了大展宏圖的機會,民間俗語說“酒后吐真言”,酒話常能將壓抑到潛意識層面的意識,用醉話釋放出來,這種狀態可以得到弗洛伊德現代心理學的合理解釋。將酒瘋子的醉話歸納一下,中心內容只有兩項,一是弄錢,二是找“相好”,這其實正是現任村長所干的勾當,弄錢與找相好的技術手段,或許就是直接從村長克隆來的,這又令我們想起躺在土谷祠里構想“革命”美好愿景的阿Q,也無非“東西(元寶、洋錢、洋紗衫、寧式床等等)”和“女人”兩樣,不會再有第三樣了,因為阿Q“沒有想得十分停當,已經發了鼾聲,四兩燭還只點了小半寸”[2]。可以說,阿Q是革命尚未成功時的村長,村長是革命成功后的阿Q,袁作義則是村長的意淫,在相當程度上返祖了土谷祠里的阿Q。這一解讀不難看出,曉蘇一旦強化了介入現實的批判功能,也即提高了“意義”在小說中的含量,民間敘事與政治敘事、精英敘事的界限其實不會是涇渭分明的。
誠如曉蘇所言,“傻瓜主要是智力問題,瘋癲則主要是精神問題”,而在現代科學看來,“智力”是可以量化的,智商(IQ)概念的提出及其相應的測試手段,已經逐漸為社會認可并接受,這一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是英國華威大學的科學團隊,利用核磁共振成像(MRI)掃描人類大腦,將智力的計量化又朝前大大推進了一步。
如果把曉蘇涉及傻瓜敘事的小說作一排序,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人住牛欄》《打飛機》《麥子黃了》《村口商店》《麥芽糖》,五篇小說中出現的傻瓜人物,其智商是以從低到高的梯級排列的,如果換作心理學、病理學的專業人士,完全可以根據作品提供的信息,分別估算出一個相應的IQ數值,顯而易見,這一數字化之于小說的意義,在于使同一類型的人物彼此區別開來,從而呈現并豐富了文學的多樣性。
《人住牛欄》《打飛機》和《麥子黃了》都寫到了傻瓜,寫到了傻瓜光棍漢的性苦悶,但傻瓜與傻瓜不一樣,割麥季節的金盆和打飛機的哥哥的智商,顯然高于住在牛欄中的苕,曉蘇在給人物賦名時顯然是費了一番心思的,“苕”這個字在湖北方言中作名詞有“傻子”的意思,作形容詞則為“傻的”;“哥哥”未提姓名,僅提及綽號“打飛機的”,“打飛機”是“一個傻子的標志性節目”(小說中另有雙關意義),“哥哥”的倫理身份限定了人物有限的活動范圍;金盆則有名有姓,以此便獲得了一個參與社會活動的身份符號。三人智商的梯級在命名上亦可見一斑,正是以智商差別奠定的生理與心理基礎,使同一類型人物的命運,在三篇文本中分別呈現出悲劇(荒誕)、正劇、喜劇的不同樣態。
先看苕,《人住牛欄》中的苕,屬于醫學上有嚴重智力缺陷的精神病患者亦即白癡。小說在完全被生理本能控制的苕、急于給苕弟弟找對象的姐姐、小心眼的姐夫、以充當“媒婆”為手段一心打姐姐主意的謝甲幾人之間展開,故事核是姐夫發現姐姐出軌,暴怒的姐夫毆打了來家里為苕介紹對象的謝甲,無辜的謝甲以冤枉挨打為要挾,終于達到奸占姐姐的目的,那么究竟是誰同姐姐發生了性關系呢?小說暗示,是屢次為苕弟弟介紹對象屢次未果而萬般無奈的姐姐亂倫性質的獻身。
孤立地解讀這篇小說,很容易誤解曉蘇的良苦用心,甚至會將其歸入炫奇獵異之類的不經之談,然而學者樊星先生以史家眼光,將其擺放到新時期以來熱鬧一時的“性文學”的廣闊背景下,歷數諸名家名作的性描寫作參照系,在這篇“主題不那么明晰,好像也不那么具有時代感”的小說中,便獨具慧眼地發現了“作家在短篇小說創作上的新探索”,樊星寫到:“將《人住牛欄》放在這樣的‘譜系’中揣摩,還是頗有意思的話題:曉蘇撇開了一切與政治、心理、文化、浪漫情調的考慮,寫出了偏遠山村底層生活的單調,以及在這單調的氛圍中性心理的扭曲,這樣就還原了一種生命的狀態:只為肉欲而燃燒。雖然,《小城之戀》《伏羲伏羲》和《罌粟之家》中已經蘊涵了這樣的主題,但曉蘇還是寫出了那份簡單和樸拙。在這樣的簡單和樸拙中,欲望的陰暗、可憐與荒唐得到了耐人尋味的呈現。”[3];學者李遇春先生則一針見血地稱之為“嚴重的亂倫性苦難”,進而歸納出曉蘇在底層敘事中,“喜歡通過寫性來寫苦難”的敘事策略,直言“通過性視角觀照底層農民的生理和心理的苦難,有時候比宏大的社會政治視角確實看得更清楚、更直接一些”[4],肯定了曉蘇于政治化敘事、精英化敘事之外,致力于民間化敘事的美學方向,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打飛機的哥哥與“只為肉欲而燃燒”的苕最大的不同在于,除了這種純動物性的存在之外,人的社會性一面還并未泯滅,他與弟弟間的手足深情,讓人想起賣炊餅的武大郎和打虎武松之間的兄弟情分。自弟弟外出打工,“駕牛耕田的活都甩給我哥了。我哥任勞任怨,也不要任何報酬”,他不但對留守家鄉的嫂嫂從不曾動過邪念,而且充當了嫂嫂的保護神,時刻警惕和回擊著地痞楊梆的騷擾;為了尊奉鄉間習俗,弟弟特地從南方打工返鄉,給哥哥過48歲生日,其間邂逅同在一地打工回鄉治病的按摩女黑耳,為了緩解哥哥的性焦慮而花錢讓其接受黑耳的性服務;已染艾滋病的黑耳不忍心傷害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哥哥,遂以“打飛機”形式搪塞了事;地痞楊梆卻不依不饒對黑耳糾纏不已,最終咎由自取。不難看出,“通過寫性來寫苦難”不再是這篇小說的著力點,儒家的孝悌倫理在油菜坡的殘存,使我們記起“禮失而求諸野”的古訓,身體淪落而良知善念不泯的風塵女子,更讓我們在這個紅塵滾滾人欲橫流的時代,對人性不至于徹底失望,善惡有報的結局最終完成了小說的正劇審美。
《麥子黃了》則從頭至尾洋溢著喜劇性,我曾推想,倘若機緣巧合,被哪位導演青眼相看搬上銀幕,一定是一部不錯的鄉村喜劇片,因為小說豐富的喜劇元素,生活場景的畫面感,主次人物的動作性,為影視改編提供了堅實的文學基礎。
麥收大忙季節,懶惰成性的姬得寶心生一妙計:罹患癌癥眼看不久人世了。消息傳出,引來十幾個光棍漢一片雀躍(“都高興得像過年呢”),人人奔走前來探視(探望病人卻“一個個笑得連嘴都合不攏”),還競相效力磨鐮割麥,內心不過是覬覦其漂亮的老婆徐瓜,以圖取而代之,只有勤勞善良的傻瓜金盆不明就里,他對徐瓜的幫助完全出于同情而不夾帶任何私心,姬得寶的如意算盤被徐瓜識破,其貪婪、吝嗇、寡情的不斷暴露,與恪守“做人要憑良心”的徐瓜日益疏遠,與“雖說傻頭傻腦的,但心腸不壞,遇到人有困難總想幫一把”的金盆卻日漸靠攏,兩人終于走到了一起。金盆不僅避免了苕亂倫的悲劇,超越了哥哥“打飛機”的短暫的性滿足,還更進一步贏得了在傻瓜光棍漢世界里難以企及的奢侈——愛情,從而獲取了人之為人的尊嚴。
一爿鄉村小店是曉蘇喜歡為小說選擇的場景,在這個窄狹封閉的空間內,一個精明的小老板搭配上三兩個各色人物,便能像萬花筒般,旋轉出斑斕的風景來。
《村口商店》寫的是開商店的精明的紅鼻子老金,與不太精明的買豆腐的老龔和賣香菇木耳的老陳之間的生意競爭,相比于地產巨子的勾心斗角,金融大鱷的翻云覆雨,股市莊家的做多做空,三個鄉村小老板的“商戰”不過是杯水風波,然而杯水風波也能寫得跌宕起伏妙趣橫生,小說又一次彰顯了曉蘇的喜劇才能。喜劇不好寫,難在戲謔與油滑,幽默與搞笑常只有一步之遙,尤其是曉蘇秉持的民間敘事的“俗(通俗)”,雖然與喜劇性有天然的親和力,但與政治敘事的“正”和精英敘事的“雅”相比,墮入“三俗(庸俗、低俗、惡俗)”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或許正因為如此,西方古典美學干脆把喜劇擺放到比悲劇低一個檔次的位置上。曉蘇在喜劇精神和喜劇手法兩個維度上發力,避開了一不小心就會跌入的陷阱。喜劇品位的高低,在于笑聲背后有無喜劇精神的支撐,而所謂喜劇精神,說到底是一個價值立場問題,《酒瘋子》對袁作義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鞭撻,《麥子黃了》對姬得寶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嘲諷,其笑聲所指,與今日滿世界招搖的“小品王”“段子手”并列,便高下立判了。在技術手段上,曉蘇努力避開“夸張+誤會+巧合+噱頭”的慣常喜劇伎倆,引入一個視角人物左二,以類似于戲曲丑角的形象,勾連人物,活躍場面,把一段尋常故事,撩撥得風生水起。
為了在小說中完成通常在戲曲中賦予丑角的串場功能,曉蘇把左二的智商又明顯提高了一個級別,他已經不全乎是一個傻瓜,而只是“腦袋沒老金靈光”的二流子笨蛋了。他糊里糊涂地充當老金霉變食品的實驗品而不自知,充當老金手中的提線木偶,游走于三個小老板之間,促成了奸商老金將老龔老陳玩于股掌之中,同樣糊里糊涂而不自知。可以說,沒有笨蛋左二這一丑角的串場,小說的喜劇效果就幾乎蕩然無存了,這正應和了戲曲界的一句行話:無丑不成戲。
從嚴格意義上說,把《麥芽糖》的主人公務農歸入傻瓜行列是不恰當的,使用民間語言“憨”或許更準確一些。《酒瘋子》中的次要人物,小店老板的媳婦娃子即屬此類,這個“一聽說新鮮玩意就大驚小怪……只有芝麻大點兒出息”的“死腦筋”,讓人想起英國電視劇中那個智商號稱只有“007”的憨豆先生,“a little clumsy, a little naive, a little way thinking (brain does not turn), a little shy, but also a little short guy”(有一點笨拙、有一點幼稚、有一點單向思維(腦筋不轉彎)、有一點靦腆、又有一點短路的家伙”)[5],靠了她與老板一暗一明地插科打諢,以及同酒瘋子袁作義構成相聲捧哏逗哏關系的對話,讓這篇小說笑料百出。這種憨態,更多的是囿于見識的短淺,如井蛙之不可言海,夏蟲之不可語冰,但也正因為閉塞一隅,沒有受到高度物化的外部世界的誘惑與污染,相當程度上維護了心底的純潔,《酒瘋子》中偶爾現身的“憨”人,在《麥芽糖》中有了充分地完形。
務農的三個中學同窗,“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大學畢業后又去了美國,還在美國找了一個洋老婆”的楊致遠,“考上了武漢的一所大學,讀完大學就留在了省城;做了省報的大記者”的肖子文,“雖然只上了一個中專,但畢業后還是想方設法留在了縣城……后來就開了一個公司;當上了財大氣粗的老板”的余乾坤,是“油菜坡家喻戶曉的三個人物”,曉蘇概括的這三種類型,是當今社會認可的“成功人士”樣板,是而今家長嘴里念叨的“別人家的孩子”,與作為“高考時考砸了鍋,連中專都上不了,沒辦法就只好回油菜坡種田來了”的務農,構成了強烈的對比性存在。然而在農歷新年的節日氣氛中,“沒有出息的男人”與“成功人士”的對比發生了逆轉。按當地習俗,要為去世三周年的父親立碑抱靈牌的楊致遠,因“買不到回國的飛機票”而無法盡人子之孝;因“老婆不讓他回來”過年否則以離婚相要挾的肖子文,只能捎來年貨以物代人;身患糖尿病的余老爹老媽,為了能見“公司業務忙,不能回家過年”的兒子一面,竟然大吃麥芽糖以求犯病。無論是立碑時的抱靈牌救場,還是幫助肖大叔扛年貨,背發病的余老爹到醫務所打吊瓶,關鍵時刻都是“沒有出息”的務農伸出援手。小說刻意渲染的年關務農家共享天倫其樂融融的溫馨祥和,與三個成功人士爹娘獨守空巢的凄涼孤獨,讓人對成功和幸福的世俗理解產生了懷疑。
這是一篇獲獎作品,一經發表,即引來好評如潮,我也能體察作者的良苦用心:在舉世汲汲于“勵志”和“成功(有出息)”,甚至將這種渴求以“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咒語,理直氣壯地剝奪孩子童年的時代氛圍中,曉蘇卻給我們展示出還有另一種生活方式值得一過,那是清寒簡樸卻彌漫著麥芽糖甜味的平淡而又平常的日子,曉蘇以此對紅塵滾滾人欲橫流的世界背過臉去,對世風的批判盡在不言中。毋庸諱言,當代小說(這里指與當下生活同步的小說)創作與評論的一個重要參照系,是當代(當下)的生活,這既是從事這一工作的誘人之處,也是其困難所在。面對比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要復雜的當代(當下)生活,我們有理由就這幅農家樂圖畫提出一點詰難,換言之,是哪些因素阻礙了《麥芽糖》從“高原”到“高峰”的登攀呢?在我看來,三人無法回家過年的種種理由,并非都有必然性(比如國際國內的航班都有提前售票的慣例),而“成功”與“孝親”兩者是否存在必然的矛盾,也是大可質疑的,設想假如父母大病,只能給父親抓背的親情便會立顯其脆弱性,因為熬麥芽糖的收入顯然抵不過三個“成功人士”的財力,更重要的還不在此,在我看來,小說透露的價值觀,并非如有些論者所言,是“一簞食,一壺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6],“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7]的儒家道德,而是對絕圣棄智,小國寡民理想的脈脈溫情,小說告訴我們,生活中倘若不再有任何功利性追求,“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8],過上莊子所言那種“含哺而熙,鼓腹而游”[9]的日子,便可享受自然生命本身的快樂,而這,才是幸福的所在。然而,現代文明的腳步是誰也阻擋不住的,伴隨智能手機長大的低頭族,不會留戀鴻雁傳書的詩意,更難想象將其廝守父母身邊盡孝,而不去承擔那份應盡的社會責任,倒是養老的逐步社會化,無疑更是現代社會努力的方向。如此看來,我們一方面大聲疾呼“人的現代化”,一方面痛心疾首“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究竟該如何取舍呢?哈姆雷特的糾結:to be or not to be ,曉蘇顯然也意識到了“這是個問題”,他在博士論文中,言及“作家如何深化和拓展小說的民間化敘事”時,就深有體會地將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列為“研究的難點”之一,顯然是他的甘苦之言(可惜論文中未及展開)。由此也可以看出,優秀小說的一個標志,不在于或不全在于贏得掌聲的熱烈,能夠揭示出社會人生中的諸多困惑和悖論,引發人們深層次的探究和思考,或許更是小說生命力的所在。
當我們將上述小說的瘋傻書寫略加梳理歸類之后,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在曉蘇數量目前已經相當可觀的小說創作中,瘋傻書寫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這至少說明這種非常態的敘事仍然還有很大的書寫空間,如同他通過許多小說,把反轉式結局藝術推向極致那樣,對他在這塊地盤的進一步拓展,我們完全有理由懷抱樂觀的期許,實際上正如以上分析的那樣,他在某些方面已經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這讓我們不由得想起歌德的那句老話:“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一個作家的創作實踐,常常能超越理論宣示,無論這種理論是如何正確與宏偉,人類的文學史已經證明,凡是卓越的作家,絕不會在意文壇上飄揚的形形色色的旗幡,更不會墨守理論教條去按圖索驥,他們唯一聽從的,是鮮活的生命(生活)與大地的召喚。
[1] 曉蘇.當代小說與民間敘事[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92.
[2] 魯迅.魯迅小說精選·阿Q正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13.
[3] 樊星.耐人尋味的敘事——讀曉蘇的新作《人住牛欄》[J].歲月,2009,(4):12.
[4] 李遇春.麥芽糖·序[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
[5] 百度文庫·憨豆先生[DB/OL].https://wenku.baidu.com/view/20171116.
[6]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58.58.
[7]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M].北京:中華書局,2016.334.
[8] 道德經·八十章[M].長沙:岳麓書社,2011.250.
[9] 莊子·馬蹄[M].北京:中華書局,2014.96.
2095-4654(2017)06-0051-04
2017-09-17
I247
A
熊 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