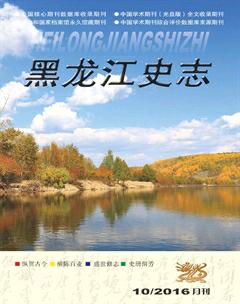鄭玄注《三禮》方法略探
[摘 要]自鄭玄注解《三禮》之后,始有《三禮》之名。鄭玄注經,先是總體上綱舉目張,兼采今、古,既注重名物訓詁,又注重章句之釋,然后再具體而微,深入到經文的具體字詞,兼用直訓和義界的方法注解之。
[關鍵詞]鄭玄;三禮;今文經;古文經;注經方法
所謂《三禮》,是指《周禮》《儀禮》和《禮記》。這三部傳世文獻,奠定了中國傳統禮制的基礎,研究者代不乏人,注疏者亦難以計數。但影響最大者,非東漢學者鄭玄莫屬。
雖然《后漢書·馬融傳》言馬融所注之書中有《三禮》,(1)同書《盧植傳》亦言盧植作有《三禮解詁》,(2)但此《三禮》,有學者認為是《后漢書》作者范曄自起之名,“蓋范蔚宗自后記而名之歟?”(3)因為同書《儒林列傳下·董鈞傳》有言“(鄭)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4)近人黃侃《禮學略說》亦云:“……鄭氏以前,未有兼注《三禮》者(以《周禮》、《儀禮》、小戴《禮記》為《三禮》,亦自鄭始。《隋書·經籍志》《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5)可見,《三禮》之名,始自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東漢經學世家子弟,順帝永建二年(127)生,獻帝建安五年(200)卒。據《漢書·鄭玄傳》,其先從京兆第五元習今文經,又從東郡張恭祖通古文經,后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靈帝末,黨禁解”,雖被征辟,但仍隱居不仕,專心經業。“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萬余言。”(6)其著述宏富,除本傳所載之外,另有《周禮注》、《喪服經傳注》、《喪服變除注》等。(7)
筆者在讀鄭注《三禮》之時,結合時彥前賢的研究成果,細致思考,發現鄭玄注經是先總體再具體,采用層層深入的方式,既高屋建瓴,又具體而微,總體感覺是循序漸行,逐層深入,有章可循。現試探之。
一、綱舉目張,兼采今古
《后漢書·章帝紀》載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章帝下詔白虎觀:“(光武)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欲議減省。”(8)《后漢書·桓郁傳》:“初,(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9)《后漢書·張霸傳》:“初,霸以樊■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詞,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10)《后漢書·張奐傳》:“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余言,奐減為九萬言。”(11)在《后漢書》中,多可見關于漢代經注“浮辭繁多”之弊,為此,統治者多次下令刪減,但結果卻不理想。至鄭玄時,“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余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12)在這種情況下,鄭玄提出了“綱舉目張”的注經方法。在《詩譜序》里,他對自己的注經方法作的概括:“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于是與?”“綱舉目張”之法,可謂有的放矢。
在“綱舉目張”之法的指導下,鄭玄注經往往簡明扼要。據統計,其經注之文字,往往少于經。如《儀禮》之《有司》篇經4790字,注3356字。《禮記》之《學記》、《樂記》兩篇,經6459字,注5533字;《祭法》、《祭義》、《祭統》三篇,經7182字,注5409字。凡此種種,皆注少于經。另據鄭氏門徒仿照《論語》所整理關于其言論的著作——《鄭志》,鄭玄答張逸語,“……文義自解,故不言之。”(13)為了簡潔明了,對于“文義自解”之處,常常“不言之”。比如《周禮·地官·司稽》有“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鄭注:“不物,衣服視占不與眾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14)對于此句經文的注解,確實唯“不物”一詞令人犯難,余者皆可“文義自解”,鄭注抓此關鍵,全句之意即明。
如前所述,鄭玄所生活的時代,不惟立于官學的今文經“異端紛紜”,家法林立,浮辭繁多,學者之間“互相詭激”,彼此詰難,令“后生疑而莫正”,尚有今、古文經學之對壘。那么,鄭玄作為貫通今古文的大家,注經時就能夠高瞻遠矚,沖破家法之藩籬,打破今、古之壁壘,網羅眾家,兼采眾長。對此,皮錫瑞有一段議論可明:
案鄭注諸經,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費氏古文,爻辰出費氏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丘《易》又亡,無以考其異同。注《尚書》用古文,而多異馬融;或馬從今而鄭從古,或馬從古而鄭從今。是鄭注《書》兼采今古文也。箋《詩》以毛為主,而間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謂“己意”,實本三家。是鄭箋《詩》兼采今古文也。注《儀禮》并存今古文;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是鄭注《儀禮》兼采今古文也。《周禮》古文無今文,《禮記》亦無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論。注《論語》,就《魯論》篇章,參之《齊》、《古》為之注,云:“《魯》讀某為某,今從《古》。”是鄭注《論語》兼采今古文也。注《孝經》多今文說,嚴可均有輯本。(15)
同時,也正是因為鄭玄注經,兼采今、古兩家的特點,既看重“訓詁名物”,又重視章句之義,“……有時不得不繁。豈秦近君說《堯典》篇目二字,至十余萬言之比哉?”(16)故而遭到諸如黃侃這樣的古文經學家的“譏其繁”。
二、名物訓詁與章句釋義兼重
一般而言,今文經學注重章句釋義,擅于汪洋恣肆發揮經文的“微言大義”,但其弊端也如前所述,常常“浮辭繁長,多過其實”,(17)故為楊終指責:“……章句之徒,破壞大體”。(18)而古文經學家,重在訓詁,舉其大義,不為章句。《后漢書·桓譚傳》謂其“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19)《后漢書·班固傳》謂班固“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20)《后漢書·王充傳》也說王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21)《盧植傳》同樣也說盧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22)等等,皆謂古文經學家好訓詁,不守章句之實。但鄭玄注《三禮》,兼采今、古,前已述及,正是由于兼顧名物訓詁和章句之釋,“有時不得不繁”。
鄭注《三禮》中,關于名物訓詁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鄭注:“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23)《禮記·玉藻》:“王后■衣,夫人揄狄”,鄭注:“■讀如■,揄讀如搖。■、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于衣以為飾,因以為名也。后世作字異耳”;(24)《儀禮·士昏禮》:“設洗于阼階東南”,鄭注:“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25)
當然,既然兼采今、古,兼重訓詁與章句,鄭玄并非毫無目的的“繁”,而是為更全面明晰地解釋經文服務的。比如《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26)此句經文,若無對“殤”字的訓詁,就難以理解經文的全意,章句之釋亦不會如此易懂。
三、長于直訓和義界
傳統訓詁學中訓釋的方式有多種,章太炎先生曾經進行了歸納,他認為:“訓詁之術,略有三涂,一曰直訓,二曰語根,三曰界說。”(27)章學后人黃侃亦云:“訓詁之方式,以語言解釋語言,其方式有三:一曰互訓,二曰義界,三曰推因,三者為構成訓詁學之原因,常人日用而不知者也。”(28)盡管學者們的分法有異,但總體而言,在鄭注《三禮》的訓詁方式中,據筆者所見,至少有直訓和義界兩種。
在名物訓詁和章句之釋兼用的情況下,為了便于注經的簡潔扼要和利于閱讀,鄭玄在注釋詞義時,常常采用直訓的方式。所謂直訓,即“直接用單詞訓釋單詞的一種釋義方式”,(29)就是在注釋時選用常人容易理解的字詞,以解釋經文中較難理解的部分,從而掃除閱讀經文的障礙。而常人容易理解的字詞,一般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意義相同的詞,即同義詞,具體操作就是選用與經文中意義相同的字詞來解經。此例不勝枚舉。如《周禮·天官·大宰》篇:“以八柄詔王馭群臣。”鄭注:“詔,告也,助也。”(30)即此句經文中“詔”的意思與“告”相同,將“詔”理解成“告”,有助于理解經文。《儀禮·覲禮》:“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深謂高也。”(31)就是“深”、“高”同義。《禮記·曲禮》:“疑事毋質,直而勿有。”鄭注:“直,正也。”(32)同樣是用同義詞注經。此外,在找不到合適的同義詞的情況下,鄭玄就退而求其次,選用意義相近的詞加以解釋。如《禮記·哀公問》:“其順之,然后言其喪算,備其鼎俎。”鄭注:“言,語也。”(33)《說文·言部》:“直言曰言,論難曰語。”(34)“言”和“語”本來是有一定區別的,但在此處,都可指“表達”或“說”之意,算是運用二者詞義相近的現象來解經。另如《周禮·天官·大宰》:“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鄭注:“典,常也,經也,法也。”(35)此句中的“典”本意是指“五帝之書”,但結合上下文,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中,則可理解為一般原則和規律,所以在解釋的時候,鄭玄選用了幾個意義相近的詞對其進行注解和補充,以期更加充分地表達“典”字所傳達的內容。
在同義詞或近義詞無法注經,或一時找不到恰當的同義詞或近義詞的時候,鄭玄就采用義界,即下定義的方法,使經文的注解更易于人們理解。如《周禮·夏官·大司馬》云:“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36)就是歸納出相關字詞的外延和內涵,以下定義的方式,將其說明之。但此種注經方式,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有其弊端。那就是詞義的改變,致使人們不僅對經文原字的理解不知所以,且對其所下的定義亦不知如何解讀。所以,在鄭注中,這種下定義的方式,相對于直訓的方式,不甚普遍。當然,鄭玄對經文中具體字詞的注解,所采用的方法,肯定也不止直訓和義界這兩種,而筆者只是就自己所熟悉、所察覺的這兩種方法分析之罷了。
四、余論
經書難讀,更難懂。不僅唐代大文豪韓愈為之苦惱不堪,(37)清代碩儒阮元亦深有同感。但鄭玄卻能貫通今古文,遍注經文,而《三禮》經文,也因此舉,嘉惠后學。但由于鄭玄所生活的時代,不論今文經學,還是古文經學,研究與注解都碩果累累。這就決定了鄭氏在注經時不得不獨具慧眼,在兼采今、古的同時,采用綱舉目張、簡明扼要的方法。并打破今、古經學家法的藩籬,兼重名物訓詁和章句之釋,在具體的字詞解釋方面,采用直訓和義界的方式,做到注經的簡明易懂。
統而觀之,鄭玄所采用的注經方式,可謂層層深入,循序漸進。先是高屋建瓴,從總體上統觀全局,提綱挈領,“舉一綱而萬目張”,做到以點帶面,從而“解一卷而眾篇明”。然后,再根據今、古文已有的研究成果,為了兼采并蓄,取長補短,而兼用名物訓詁和章句釋義這兩種在此之前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互不兼容的注經方式。在此基礎上,再深入到具體經文字詞的解讀,采用直訓和義界的方式訓釋經文。如此,從面到點,從全局到具體,鄭玄注經猶如層層剝筍,既兼顧得當,有條不紊,又透徹深入,巨細無遺。
注釋:
(1)[宋]范曄:《后漢書》卷六十上《馬融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972頁。
(2)[宋]范曄:《后漢書》卷六十四《盧植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116頁。
(3)楊天宇:《鄭玄三禮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156頁。
(4)[宋]范曄:《后漢書》卷七十九下《儒林列傳下·董鈞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577頁。
(5)黃侃:《禮學略說》,見氏著《黃侃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448頁。
(6)[宋]范曄:《后漢書》卷三十五《鄭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07-1213頁。
(7)楊天宇:《鄭玄三禮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15頁。
(8)[宋]范曄:《后漢書》卷七十九下《章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8頁。
(9)[宋]范曄:《后漢書》卷三十七《桓郁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56頁。
(10)[宋]范曄:《后漢書》卷三十六《張霸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42頁。
(11)[宋]范曄:《后漢書》卷六十五《張奐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138頁。
(12)[宋]范曄:《后漢書》卷三十五《鄭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12-1213頁。
(13)《鄭志》答張逸云,見李學勤主編:《毛詩正義》卷第一《國風·周南·螽斯·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4頁。
(14)李學勤:《周禮注疏》卷第十五《地官·司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79頁。
(15)[清]皮錫瑞:《經學歷史》五《經學中衰時代》,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2頁。
(16)黃侃:《禮學略說》,見氏著《黃侃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449頁。
(17)[宋]范曄:《后漢書》卷三十七《桓郁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56頁。
(18)[宋]范曄:《后漢書》卷四十八《楊終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599頁。
(19)[宋]范曄:《后漢書》卷二十八上《桓譚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955頁。
(20)[宋]范曄:《后漢書》卷四十上《班固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30頁。
(21)[宋]范曄:《后漢書》卷四十九《王充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629頁。
(22)[宋]范曄:《后漢書》卷六十四《盧植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113頁。
(23)李學勤:《周禮注疏》卷第五《天官·籩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33頁。
(24)李學勤:《禮記正義》卷第三十《玉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909頁。
(25)李學勤:《儀禮注疏》卷第四《士昏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71頁。
(26)李學勤:《周禮注疏》卷第十四《地官·媒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66頁。
(27)章太炎:《與章士釗》,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87頁。
(28)黃季剛著,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6頁。
(29)徐啟庭:《訓詁學概要》,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95頁。
(30)李學勤:《周禮注疏》卷第二《天官·大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9-30頁。
(31)李學勤:《儀禮注疏》卷第二十七《覲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25頁。
(32)李學勤:《禮記正義》卷第一《曲禮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9頁。
(33)李學勤:《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哀公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374頁。
(34)[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9頁。
(35)李學勤:《周禮注疏》卷第二《天官·大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4頁。
(36)李學勤:《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九《夏官·大司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779頁。
(37)見韓愈《進學解》:“《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及《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參見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6、39頁。
基金項目:貴州省教育廳2016年度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項目“《儀禮·士昏禮》相關文獻與注疏研究”(項目編號:2016QN29)
作者簡介:雷銘(1982-),男,漢族,河南信陽人,安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史專業2016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秦漢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