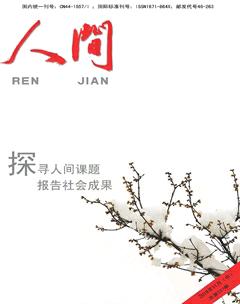究竟怎么評價優秀和幸福?
(北京語言大學,北京 100193)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11-0025-01
在上大學之前,我在一所市重點高中讀書。那里藏龍臥虎,強手如林,教學理念先進,然而在應試教育的大潮下,評價一個學生的標準也主要只以成績為主,輔以為人是否能夠左右逢源。于是每天談話中稱贊自己同學的話往往是這樣的:喲,他真厲害,物理考了滿分;啊,他好強,數學拿了全國高中聯賽決賽獎;哇塞,她真有才華,寫下了讓語文老師交口稱贊的59分作文;天哪,她簡直不是人,托福考了116,賽達一考了接近滿分。誠然,我們學校高一有原創詩歌大合誦,英語電影配音以及一二九短劇比賽,高二有英語短劇比賽。從高一到高三都有電影節和運動會以及合唱比賽。但是提起原創詩歌合誦和一二九短劇比賽,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請語文老師做指導,順便找個語文成績好文章寫得漂亮的寫詩,寫短劇。而與英語有關的比賽時,想到的同樣是請英語老師做指導,然后英語強人跟進。至于合唱比賽和運動會那只不過是在學習之余的鹽巴或者辣醬,調調味兒,讓自己放輕松,然后好更好地投入到學習當中。另外高二的合唱比賽與其說比拼藝術,不如說是把寫給高三學生的勵志歌曲由我們唱出,比拼我們奮進的決心。電影節拍的電影多半以激勵學生把無限青春加以激情投入到準備成為中國崛起棟梁的努力中,怎么努力?好好學習,考個好大學。而對于成績差學生來說假如他其他方面有特長,那叫做不務正業:而對于成績優秀的學生,其他方面厲害(會做漂亮視頻,會歌舞),那叫做全面發展,錦上添花。相比十個指頭就能數出來的文藝比賽,我校舉辦的數理化以及語文英語學科競賽雙手雙腳也數不過來。無論班主任科任老師還是學校領導都在三令五申地告訴我們一件事情: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帥如安)。這個邏輯就是好好學習,考一北大清華,努力再努力,一畢業年薪就十多萬,不到三十年薪破五十萬。四十歲成功上位上流社會。總之就是通過在年少時期的努力成為中年時候的人上人,可以在窮人騎著摩托時開著法拉利駛過積攢的雨水然后濺人家一身再揚長而去,可以做一個對別人頤指氣使的人,可以因為自己的優秀心安理得占有更多的資源。總之舍棄現在的努力,換回未來的高傲,但自始至終不是一個真性情的人。
高考時我頂風冒雪考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學。上了大學以后發現對學生的評價多元化了:學習,科研,社工,文體,實踐。但主要以學習和社工為主,基本還是兩件事,學生腦子是否聰明,做事做人是否八面玲瓏。于是我看到某些人成為了學生會主席,讓麾下諸多干事部長畢恭畢敬,儼然已經提前在學生時代體驗了那種官大一級壓死你的感覺;我看見某些人終日不上騰訊,人人,不從事娛樂活動,乃至一個月才逛一次街,終日趴在自習室里,一問干什么,考托考G,等著哈佛耶魯橄欖枝。于是你要再問他去哪里干什么,他會告訴你畢業以后那兒的學生年薪超過二十萬美元,二十年后平均薪資五十萬美元。再問為何,我要做地球上最發達國家的上層 ,為黃種人爭氣。搞科研的不過二十歲出版了專業學術著作,暢銷叫好又叫座,一問我是為了科學,于是心懷佩服;搞文藝的輕松跟文化公司簽約,唱的歌兒優美猶如天籟,只是別人說起她的厲害,會告訴你她呀,一年能賺幾十萬呢;搞實踐的,多半是做兼職,當時我覺得我算其中一個優秀一點兒的,大一上學期給雜志寫稿子,做家教賺不到兩千,大一下學期賺兩千五六,大二上學期賺三千五六。那個時候我評價我兼職做得怎樣,不是稿子獲得了多少雜志讀者認可,給讀者帶來了多少快樂,也不是家教讓小孩子成績提高了多少,而是一個又一個充滿權威性的數字,冷冰冰但高高在上的數字,這決定著你的價值。可是這樣比有意思嗎?我在想。最近有個南京林業大學的學生做家教公司年賺三十萬,可我看完報道后覺得為什么媒體不把目光放在他給小孩子帶來了什么。作為一名貧困的大學生,他享受過社會帶來的幫助也經歷過社會中殘酷的風霜,可為什么不說說他怎樣回饋了社會呢?做社工的人為什么不說說自己組織了什么活動,給大家帶來了什么呢?上了大學之后,我知道評價一個人的角度是多元的,于是我努力學習,績點3.5,我認真做兼職,掙的錢可以支撐自己的日常吃穿,我寫一些科研論文,發表在校內刊物上,我參加書畫比賽,給校刊寫文章,我參與社會工作,自己組織社團。可是我忘記了人來到這個世界不僅僅要通過自己得到了什么來獲取對自我價值的認可,而是更要告訴自己奉獻了什么。人的價值必然是體現在貢獻上的,這也就是為什么敬佩作家科學家的人不比敬佩富豪的人少。而評價貢獻更不能僅僅通過數字,而是要以更靈活也更人性化的標準。
于是這個學期我開始選擇了志愿者工作。我開始去打工子弟小學支教,用自己十余年對英語的學習和一顆愛心換來他們對這門學科的興趣;我在街頭巷尾勸募,喚醒更多人的愛心,點燃貧苦孩子的希望;我去臨終醫院為老人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帶來快樂與美好。這些事情誠然微小,也許我一天勸募不了1000元,這1000元沒有一元進我的口袋;我去支教,農民工的小孩不愛學習可能也不聰明,小學只給我提供一頓簡單的午飯;我去臨終醫院也許會常常被生命的脆弱與人的逝去而落淚。但是我知道我所收獲的遠遠大于用一個周末八個小時家教拿到那六百四十塊錢。錢買不來那種被社會需要,被弱勢群體依賴的感覺,而這樣的感覺也不可能被錢所替代。周六周日我現在只帶一個初中小孩兒,一小時八十塊。而我也不再關注拿多少錢。有時候當你的經濟地位已經達到社會中上層時,幸福不幸福優秀不優秀就不再取決于你掌控了多少金錢多少權利,而是你奉獻了什么你與家人朋友和諧與否。自從進入大一開始到這學期之前我一直迷茫而淺薄,我不知道怎樣評價優秀和幸福。我以為幾個冷冰冰的數字就是評價優秀與幸福最簡單最便捷也是最正常的方式,但真的不是這樣。任何數額的財富取代不了你心底對美好的觸碰,更取代不了你的幸福;多高的分數取代不了你真正的高貴與優秀,你內心的潔凈與柔軟。所以當每一個天之驕子匆匆奔走于校園中自習室圖書館和食堂間的時候,當每一個懷揣自己的夢的大學生修飾自己簡歷找最厲害的企業進行專業實習的時候,當你們在實驗室里,在大禮堂舞臺上,在學生會團委縱橫捭闔的時候,不要忘了不管你績點怎樣逼近,不管你一個月可以拿到怎樣豐厚的上萬美元的薪水,不管你寫出的科研專著怎樣吸引眾多人的眼球,請別忘了這些可以成為衡量你價值的一把尺子,但絕不是唯一的尺子,而且記得為這個世界奉獻些什么。
作者簡介:榮蕾(1992-),女,漢族,河北唐山人,北京語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2014級現當代文學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