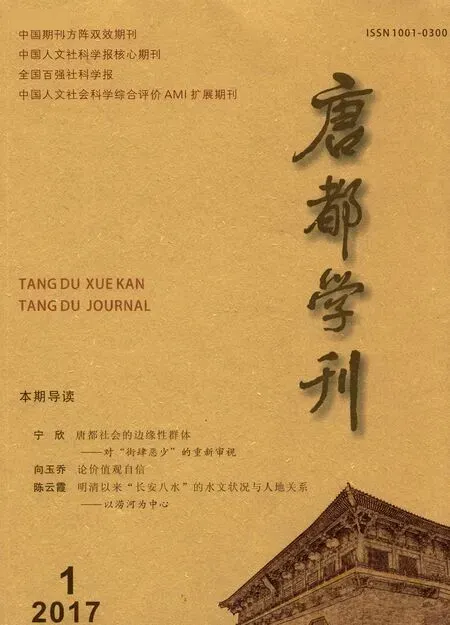“師法”向“門閥”的演進
——“偃武修文”與東漢文人的士族化
馬天祥
(西藏民族大學 文學院,陜西 咸陽 712082)
【漢唐研究】
“師法”向“門閥”的演進
——“偃武修文”與東漢文人的士族化
馬天祥
(西藏民族大學 文學院,陜西 咸陽 712082)
東漢初年,政府推行“偃武修文”的國策,私學蓬勃發(fā)展。擁有眾多弟子的經師們不僅聲名遠播,而且具備舉薦人才、推薦弟子入仕為官的權力。經師及其推薦入仕的弟子們,父子相傳,師徒相依,代代為官,逐漸擁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豐富的人脈,于是“士族化”進程迅速開啟,形成了一種具有“開放性”的“門閥制度”的雛形。在這一進程中,西漢以來的“師法”體制走向沒落而“門閥”制度最終得以形成。
“師法”;“門閥”;“偃武修文”;東漢文人;士族化
一
自清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將“師法”獨立條目專章論述以來,關于“師法”與“家法”的討論至今不絕*關于“師法”和“家法”的討論已有臺灣學者姜龍翔《兩漢博士師法、家法探析》,《華梵人文學報》第13期2010年1月,第123~155頁。丁進《漢代經學中的家法和師法辨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9月第5期,第33~41頁。兩文都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立足史料做了細致的研究工作,并且都認為“師法”和“家法”在意義上并不存在太過明顯的差別。而“師法”與“門閥”又有何關聯(lián)呢?從《漢書·儒林傳》和《后漢書·儒林傳》的比較中就會發(fā)現(xiàn)許多細微的差別。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后漢書·儒林傳》中所載諸多儒者弟子門生的數(shù)量遠遠超過《漢書·儒林傳》中的儒者。《漢書·儒林傳》中所載師徒間的傳授方式多為一人傳授于一人或幾人。像眭孟那樣“弟子百余人”的情況[1]3616實屬特例。可以推想,西漢師徒相傳亦應存在一定的規(guī)模,然而在班固看來這種規(guī)模與師承譜系相比或不值得多廢筆墨。不過,相比之下《后漢書·儒林傳》中師徒傳授的規(guī)模則要顯得宏大許多。“教授數(shù)百人”的情況實屬普遍,“教授常千人”也絕非個案,且將這些記載與《東觀漢記》和《八家后漢書》進行比對,亦非范曄獨門夸大之詞。如牟長,《后漢書·儒林列傳》載其“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余人,著錄前后萬人。”[1]2557《東觀漢記》亦載其“牟長,字君高,少篤學,治《歐陽尚書》,諸生著錄前后萬人。”[2]799又如薛漢,《后漢書·儒林傳》載其“漢少傳父業(yè),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shù)百人。”[1]2573《東觀漢記》亦載其“薛漢,字子公,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昭覽,推道術尤精,教授常數(shù)百弟子,自遠方至者著為錄。”[2]803
《后漢書·儒林傳》中獨自為傳者共32人,其中進行教授且弟子眾多者(依范曄語“教授百人”以上者)有23人。從這一比例可以看出東漢私人教授的風氣之盛。相關文章研究“私學之盛”多就其本身的特征及其對當時乃至以后的社會的影響而論,似乎并沒有對東漢一朝的“私學”緣何而盛作太深的探究*張鶴泉《東漢時代的私學》,《史學集刊》1993年第1期,對東漢時“私學”的辦學者階層、辦學類型、生源特點等問題做了詳細的論述,且已經注意到了“私學興盛”是為獲得利益。。
這種師門之盛,實是因其為“利祿之門”。其一,東漢開國以來經生名士得到任用,所以這是經學興盛的一個直接原因。
永元中(霸)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后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并有名稱。其余有業(yè)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jié),習經者以千數(shù)計,道路但聞誦聲。[1]1241
也許,這便是鄰郡程曾身為經師且無官無爵,但依然門徒眾多的直接原因。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yè)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余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shù)百人常居門下。[1]2581
然而,問題并不僅僅止步于此。我們不妨再回到原典做進一步的分析,考諸《后漢書·儒林傳》中所載弟子眾多的23人中,所歷官職祿秩曾達到“二千石”*因漢代祿秩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的差別,一一羅列失之瑣碎不便歸納統(tǒng)計,故將此三種祿秩皆劃為“二千石”級別。級別的有16人,祿秩達到“千石”級別的有1人,祿秩“六百石”以下(含六百石)的有5人,終身不曾為官者唯有1人。而“兩千石”這一級別在東漢一朝可以說是位高權重的級別了,在京為公卿、在郡為牧守,手中都掌握著向朝廷舉薦人才的權力。東漢一朝,京師的三公九卿乃至大將軍和驃騎將軍都擁有“辟舉”的權力,地方的州郡太守擁有舉薦人才的權力當然更不容置疑了。有關東漢人才“辟舉”的問題,張鶴泉《東漢辟舉問題探討》[3]已經做出詳細探討,茲不贅述。在此,我們不必偏執(zhí)于到底是弟子門徒日盛導致其聲名遠播,還是聲名遠播導致其弟子門徒日盛。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些弟子門生眾多的經師手中握有實實在在的舉薦人才的權力。
他們因弟子眾多而逐漸在地方上擁有名望,進而手中掌握了舉薦人才的權力,而后可以讓越來越多的弟子入仕為官。與之相伴的自然是自己學說抑或名氣逐漸進入社會上層,有機會得到帝室貴胄、名士碩儒的耳聞和認可,而后這種高貴的“認可”再反作用于自身,使自己聲名遠揚。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初期講學時的“弟子眾多”為經師們光明正大地贏得了人才的“舉薦權”,而經師們?yōu)楣僦蟮摹伴T徒眾多”實是一種表象,根本在于已經牢牢握在經師手中更加廣泛的“舉薦”和“征辟”的權力,即“經師”與“官僚”雙重身份的整合。如《后漢書·楊仁傳》所載:
(仁)勸課掾吏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1]2574
因此,有些身居高位的經師弟子門徒眾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后漢書·張興傳》所載:
永平初,(興)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shù)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1]2553
相較之下,范曄在《后漢書·儒林傳》中描述那些近乎“終生不仕”的經師時,可謂拿捏得當、筆觸細膩,只言教授,不言門徒多寡,其中意蘊值得玩味。如《后漢書·任安傳》所載:
任安字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后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征,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涂隔塞,詔命竟不至。[1]2551
又如《后漢書·孫期傳》所載: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勤習典籍。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yǎng)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zhí)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郡舉方正,遣吏赍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于家。[1]2554
從范曄書傳的筆法中不難看出,經師是否具有官員背景與門徒的多寡確實存在著緊密的聯(lián)系。范曄《后漢書·儒林傳》中“著錄”達到萬人級別僅有的三位經師:牟長、張興和蔡玄,其祿秩皆為“二千石”。

綜上,已經對東漢私學興盛的原因做了兩方面的分析,然而更為根本的原因遠遠不止于此。東漢經師教授弟子動輒百人以上。從求學經生的角度來看,吸引他們的除經師教授經典的專精獨到之外,更重要的是經師的名望和地位為他們開辟出一條入仕的捷徑。然而,這一切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為何東漢開國經生入仕之路能夠相對順暢?為何東漢開國對經生的吸收能夠帶動如此龐大而普遍的私學興盛?這一切的答案還要從東漢光武帝開國時的一項政策說起。
二
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東漢功臣多盡儒”條已經注意到了東西兩漢開國功臣家世的差別。楊聯(lián)陞在《東漢的豪族》中更注意到開國功臣的“豪族”出身,并將功臣開國受封概括為“豪族用經濟勢力取得政治地位的大成功”[4]。因此,才有余英時的光武能夠得天下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和士族大姓之間取得了更大的協(xié)調”的結論[5]242。
東漢開國面臨的局面較之西漢要艱難得多,從京師到地方功臣外戚、豪族大姓遍布天下。光武自號理天下“以柔道”,不僅在打天下時與士族大姓取得了協(xié)調,而且在坐天下時也在與士族大姓謀求著協(xié)調。
光武開國之后實行“偃武修文”政策。對外,一面削弱了軍功貴族,一面大力裁撤地方武裝。對軍功貴族的削弱主要體現(xiàn)在利用懷柔政策,使軍功貴族主動放棄兵權,封侯、厚賞雙管齊下,而對執(zhí)迷不悟者則絲毫不留情面。對一味好戰(zhàn)喜功的馬援,光武甚至“追收援新息侯印綬”[1]844,以致王夫之發(fā)出“抑援自取之乎”的慨嘆[6]。對地方武裝的裁撤,光武亦從一表一里兩方面入手。所謂表,即對不歸順者剿滅之;*參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頁,《光武集團與士族大姓的一般關系》一章中言及此問題,并輔之以光武對蜀中地區(qū)少數(shù)不歸附的大姓豪族采取強硬手段史料作為支撐。所謂里,即“強干弱枝”之法從根本的兵制上削弱地方軍事力量[7]。
對內,鑒于西漢滅亡的教訓,一方面“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加強集權;一方面極力安撫、抑制外戚勢力。對待外戚郭氏、陰氏雖極盡恩寵,但亦不失震懾。中元元年(前149)以“賊害三趙”之名“遷呂太后廟主于園”[1]83,這一舉動足以讓外戚明白光武的“良苦用心”。因此,大體上來看東漢中期之前的歷朝外戚雖有豪橫之事,但女主仍能保持比較克制的態(tài)度。
但最重要的是,光武無論對于功臣還是外戚的主要手段大體都是封侯而不任事,賜爵而不賜官。
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并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1]667
光武的這一理念在明帝一朝也得到了很好的貫徹: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后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1]124
在此種情況下,功臣和外戚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于是一定數(shù)量的經生便補充進了東漢王朝的各級機構之中了。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士人入仕之途的暢通也只是相對而言。畢竟較之西漢開國之時,東漢士人的基數(shù)已經相當龐大,因此,士人入仕的真實情況多是從職位較為低微的功曹、掾吏開始。恰如《東漢會要》卷27“州郡辟除”條后徐氏所云:
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亦艱。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并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有如此者初不以為屈也。[8]
雖然現(xiàn)實的情況并不太過樂觀,但范曄已經注意到了兩漢開國用人策略的不同,故于《后漢書》卷22篇末附以精辟獨到的“論曰”之詞:
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醫(yī)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勛,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shù)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夫崇恩偏授,賜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1]787
所以,在東漢中期之前,特別是光、明、章三朝,一定數(shù)量的士人被委以重任。考諸《后漢書·儒林傳》不難發(fā)現(xiàn),獨立成傳的32人中所歷官職祿秩達到“二千石”級別的有25人,在這25人中有20人分別受任于光、明、章三朝;有3人分別受任于安、順兩朝;有兩人受任于桓、靈二朝。由此,可以推知東漢開國初年光武推行的“偃武修文”政策切實地使一定數(shù)量的士人得到了重用。
三
然而,不論經生以“舉薦”“辟舉”或者其他途徑入仕,一旦累遷至“二千石”這一高級官階,他便有了成為“世家”的可能。首先,在物質基礎上得到了保證。*參見許倬云著,程農、張鳴譯《漢代農業(yè)》,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頁。許氏參看宇都宮清吉、藪內清《續(xù)漢志百官受奉例考》中的表一、表二具體羅列各級官吏每月俸祿糧食斛數(shù)、錢數(shù)外,更指出漢代高級官僚還會享有到國家提供的一套宅邸和來自帝王的各種賞賜等一系列的優(yōu)厚待遇,憑借這些便可累積起大量的財富。其次,出身經生的高級官僚既可能出自經學世家,也可能受業(yè)于他人門下。但無論是哪種情況,都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經學修養(yǎng),為世代通經入仕打下了基礎。最后,受當時世風影響,從京師到州郡豪族云集。所以,一旦一人入仕為官,便自覺地努力使子孫也能夠相繼為官。余氏已經敏銳地察覺到了西漢中期前后士人心中“士族”意識的差別,指出武帝朝之前的士人多為“游士”意識,而武帝推行儒術之后,士人們的“士族”意識開始產生。因此,東漢許多經學傳家的“士族”都是發(fā)端于西漢中后期。但余氏似乎仍未將士人心中的這種“士族”意識的產生,乃至東漢時成為士人頭腦中的普遍信條,這一切背后的玄機一語道破。余氏認為“那時的士尚未能普遍地確定政治地位”[5]196。要之,使得這種意識從萌生進而上升為士人普遍信條背后的根本原因,即從西漢末的動亂至東漢初年的安定,就個體之人而言,“士族”的優(yōu)勢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證。經濟上,憑借收容大量破產農民建立了自己的“莊園經濟”,并依靠對奴仆盤剝和國家低稅率之間形成的巨大“差額”囤積大量財富[9]。政治上,左右人才舉薦權使自家宗族子弟可以世代為官。軍事上,遭逢亂世可以組織自己的獨立武裝,退可以閉門自保靜觀其變,進可以舉族從征手中握有“投機”的資本。因此,在“士族”優(yōu)勢得到充分印證的大背景下,士人們一旦位列高官,多會努力向“士族”邁進。驗之《后漢書·儒林傳》,此種情勢已經較為普遍,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清楚地看到,東漢開國以來經生入仕為官并向“士族”發(fā)展的傾向頗為明顯。雖然,這些傾向與伏恭家族、崔骃家族等興自西漢且至東漢綿延不絕的經學世家不可等量齊觀。但父子經學相承、皆入仕為官的現(xiàn)象已經比較普遍。并且,需要注意的問題是,范曄著《后漢書》時對原始史料是存在刪減問題的。諸家后漢史料的撰寫起自東漢末,皆對漢代的官修史書——《東觀漢記》存在不同程度的刪減。范曄的《后漢書》也不例外,其篇制規(guī)模當在《東觀漢記》之下。再則,史書固然是歷朝歷代的史料匯編,但并不等同于著錄人物的家族譜系合集。就《東觀漢記》本身而言也存在前后時期史料簡繁不同的問題。因此,即便范曄未作刪削,《東觀漢記》等原初史料也不大可能將每位有傳之人的家世譜系一一載錄。所以,這里以《后漢書·儒林傳》為例,發(fā)現(xiàn)了以上十位經生出現(xiàn)“士族化”傾向的案例,且這一數(shù)量也足以印證了這種傾向的確鑿存在。但如果回到歷史本真,只能肯定有明確記載者確有這種動向,而不能否定那些沒有明確記載者確無這種動向。簡而言之,這種動向要比史料直接傳達給我們的要強。另外,考諸《后漢書·黨錮列傳》以及其他后漢黨人傳記,不難發(fā)現(xiàn)“清流的領導人物大多數(shù)都是以經學傳家的世宦豪族”[10]。盡管有些名著于世的“士族”究竟起自何人、興自何世無從得知。如王龔家族“世為豪族”、尹勛家族“家世衣冠”、羊陟家族“家世冠族”等。

表1 父子入仕表
但多數(shù)人物家族的興起,還是可以從他們傳記中的記載來推知的。金發(fā)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中“黨人的家世”[10]一則,已經將《后漢書·黨錮列傳》及其他各列傳中的黨人家世進行了詳盡的羅列,由于篇幅原因茲不贅述。從金氏整理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得出結論:東漢末年黨人中經學傳家的“士族”已經占有很高的比例,并且這類“士族”的興起幾乎都不晚于東漢中期,翻檢范曄《后漢書》中有關黨人的傳記,此類例證頗多。這種情況與前文中提及的《后漢書·儒林傳》中位列“二千石”級別的25位官員中有20人分別受任于光、明、章三朝的情況實有同樣的社會原因。即東漢開國初年懾于帝王“偃武修文”一系列政策的壓力,軍功貴族和外戚勢力在攫取政治權力時尚能保持一定的克制,且東漢末年為害尤甚的宦豎集團尚未形成,所以經生便有了進入權力高層的可能。然而,進入東漢晚期,一方面軍功貴族、外戚勢力、宦豎集團這三股力量幾乎將權力瓜分殆盡;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東漢中期之前得以列于高位的經生迅速“士族化”成為一股新的力量。所以,東漢末年的黨人名士凡通經入仕者幾乎都是“士族”后裔而少有“寒門”子弟。金氏羅列的材料也確實證明了這一點,所列57人中僅有4人是出身低微的。*參見金發(fā)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金氏所列實為58人,但因“張奐”被重復列舉一次,故實為57人。
因此,可以推知東漢末年存在一定數(shù)量的經學傳家的“士族”,實是緣于東漢初年的通經入仕。當然,從史料中來看多數(shù)“士族”仍屬于父子兩代或祖孫三代通經入仕的簡單類型,與典型“士族”存在一定距離。如李固、黃瓊、王暢、趙典、范滂、張儉、岑晊、劉炬(叔父光,順帝時為太尉)、馮緄、張奐、何休、周舉、陳球、種暠、史弼、劉茂等家族皆興自父代。劉淑、李膺、陳翔、橋玄、趙岐等家族皆興自祖父代。造成這些“士族”力量相對薄弱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只任官而未封侯,權力沒有得到世代承襲的制度保證。根本上看則是經濟上無法與地方豪族相抗衡,政治上由于外戚和宦官的阻隔而無法真正意義上地接近皇權。
但這類人群的存在,已經昭示著在東漢晚期經學傳家的“士族”已經在權力的夾縫中成長起來,進而用他們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來左右那個時代了。
四
在這一潮流之中經師的地位得到了穩(wěn)固,世代經師的表象下更是世代為官的實質。隨之而來的是這些經師手中越發(fā)膨脹的“選舉”和“征辟”的權力。與此同時,更是經生隊伍的愈加龐大與入仕之途的更加艱辛。因此,經師與弟子門生的關系便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經師和弟子門生不再簡單地等同于既往單純學問的傳授,而是趨向于一種具有某些“依附”性質的關系。“著錄”制度的普遍存在便是這情況的直觀反映。“著錄”不是弟子門生人數(shù)的簡單記錄,弟子門生人數(shù)的記錄在范曄《后漢書》中另有書法:“教授門徒前后三千余人”[1]1125弟子和門生已然有別,而“著錄”更是另外一重關系了。弟子是側重師徒授業(yè),門生和“著錄”制度更側重的是一種“依附”關系。“(門生)并不一定受業(yè),只是假借名義,與有力者造成隸屬關系,希圖任用”[4],而“著錄”則全然是一種“依附”了*關于“著錄”問題的說明有楊聯(lián)陞《東漢的豪族》,《清華學報》1936年第4期,第1036頁。引述了顧炎武和趙翼的論述,意在說明門生皆為依附名勢。張鶴泉《東漢時代的私學》,《史學集刊》1993年第1期,第58頁。張氏亦承襲這一觀點,但張氏指出“在東漢私學中,著錄名籍,不只是直接入學受業(yè)者,還有其他的士人”,即弟子、門生等姓名皆錄在一起。。
因此,東漢時代的經師(尤其是為官入仕者)與弟子門生間的關系較西漢要更為緊密,為老師請命者、代罪受罰者皆不乏其人: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系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1]2552
歙在郡,教授數(shù)百人,視事九歲,征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藏罪千余萬發(fā)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系,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乞殺臣身以代歙命。”[1]2556
此外,在東漢為宗師操辦葬禮、服喪也成為一種通例。更有因師喪而去官者,如延篤“以師喪棄官奔赴”,孔昱“因師喪棄官”等。可見,東漢經師與弟子門生關系的“依附”特征已經頗為明顯。因此,一個長久以來關于“師法”與“家法”區(qū)別的探討,可以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去審視。探討兩漢“師法”“家法”關系的文章頗多,大多還是走從史料出發(fā)逐條分析語義進而歸納總結得出結論的路數(shù)。東漢之所以出現(xiàn)“家法”的概念,從經學的傳承上講,實是因為東漢自開國以來經學出現(xiàn)了不同于西漢的“新氣象”。西漢解經章句日趨繁復,而東漢初年已出現(xiàn)了“刪繁”之風,例如:
(伏恭)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1]2571
鯈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1]1125
(鐘興)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向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1]2579
(桓榮)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1]1256
霸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1]1242
張奐……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余言,奐減為九萬言。[1]2138
以上諸人,伏恭、桓榮、鐘興、樊鯈,皆主要活動于光武朝;張霸主要活動于章、和朝;張奐主要活動于桓帝朝。可以看出,經學的“刪繁”之風自東漢初年便已興起,并且從東漢前期一直綿延至漢末。所以,至東漢末年張奐將《牟氏章句》由“四十五萬余言”驟刪至“九萬言”,才不會顯得過分的突兀。
東漢開國以來更將西漢末年的“兼通”之風發(fā)揚光大。西漢經師雖通他經,但其通熟程度較之東漢經師則稍遜一籌。
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1]2554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shù)家法。建武初,舉明經,……及有難者,輒為張數(shù)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余人。[1]2581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圣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jù)理體,于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1]2582
戴憑、張玄主要活動于光武朝,李育主要活動于章帝朝,三人皆為東漢前期時人。戴憑與他人的辯難應當不專限于一經的范圍;張玄更是為辯難者陳盡各家之言;李育雖習《公羊》,但卻能從其《難左氏義》四十一事看出他對《左傳》研究的精深,藉此也便成為東漢末羊弼、何休師徒追述的典范。東漢自開國以來“刪繁”和“兼通”之風便已悄然盛行。
并且,在范曄《后漢書》中雖然“家法”一詞得到一定程度的使用,但這個產生于東漢中期之后的詞語有“一家之學的意涵”*參見姜龍翔:《兩漢博士師法、家法探析》,《華梵人文學報》2010年第13期,第136頁。姜氏列舉了家法指經內之各流派;家法指各經之分別;家法等于師法;家法涵蓋師法;非官學之《傳》亦以家法稱之。。另據(jù),袁宏《后漢紀》卷15:
(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寵父躬復以律令為廷尉監(jiān)。寵少習家法,辟太尉鮑昱府。[11]
更進一步證明了“家法”確有一家獨有之學而不同于別家之學的意思。而范曄《后漢書·陳寵傳》在敘述幾乎相同的內容時卻采用了“家業(yè)”而非“家法”:
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躬生寵,明習家業(yè),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1]1548
驗之范曄《后漢書》,且單就《后漢書》而言,通過對《后漢書》中該類詞語出現(xiàn)語境的總結分析,發(fā)現(xiàn)“家法”“家業(yè)”和“家學”還是存在一定差別的。“家業(yè)”和“家學”多指個人身處經學世家,經學從家族內部習得;“家法”多指個人身處非經學世家,經學從外人習得,或將經學傳授與外人。可以看出,如此“隱微”的筆法至東晉時的袁宏尚未能曲盡其妙。也許,范曄著史時之所以將“家法”這一概念弄得模糊不堪,就是為了將“家業(yè)”和“家學”的特征展現(xiàn)得清晰可見。“家法”概念的模糊亦是無奈之舉。此外,對同樣修習經學的士人的家族出身,能夠做到如此細致的“關照”,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已然成為一個注重等級和出身的社會即將到來的重要信號。
現(xiàn)在回過頭來,基于以上的分析來重新審視經師與經生的關系。經師在授業(yè)的過程中皆或有損益,更有以能提供入仕為官機會的私人講學形式與之互為表里。所以,這種依托經學傳家“士族”興起的師生關系模式更適合被冠以“家法”的名號。如果簡單地認為“‘家法’即‘章句’”[12]的話,那么東漢“家法”一詞豐富的社會內涵將被全部抹殺。
但必須注意到兩漢“師法”和“家法”一個宏觀上的區(qū)別,即西漢的“師法”多學在官學博士,經生的入仕權力多掌握在國家手中;東漢的“家法”多學在私人經師,經生的入仕權力多掌握在經師手中。在這種情況下,不僅經師家族世代通經、世代為官成為“士族”,而且依附這些“士族”的士人也較其他沒有“依附關系”的士人,能夠獲得相對多的仕進機會。這種情況下,這些經學傳家的“士族”已然形成了一種具有“開放性”的“門閥制度”的雛形。舉薦或征辟弟子門生中的士人一方面是緣于儒家思想的熏陶和身處人師特殊位置;另一方面,面對各勢力集團紛爭的局面,提拔士人既有利于在士人階層中贏得良好的聲望,又可擴大自己的勢力和影響,并為其家族世代發(fā)展做長遠鋪墊。因為,“門生不只止是一個人的門生,并且是一家人的門生。”[4]因此,漢末黨錮之禍時力量相對薄弱的清流士族才能得到廣大士人群體的響應和支持。然而,一旦隨著社會外部環(huán)境趨于緩和,“士族”必然會通過自身更進一步的發(fā)展普遍晉升為豪族乃至貴族。進而憑借這種普遍而穩(wěn)固的地位便可以與國家政權謀求一種“默契”——使自身家族利益能夠得到世代保證的制度。這種制度確立之日,便是“門閥”形成之時。
[1] 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 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3] 張鶴泉.東漢辟舉問題探討[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0(4):82-88.
[4] 楊聯(lián)陞.東漢的豪族[J].清華學報,1936(4):1007-1063.
[5]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 王夫之.讀通鑒論[M].北京:中華書局,1975:154.
[7] 勞干.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J].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10冊,1987:48.
[8] 徐天麟.東漢會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05.
[9]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1:6-8.
[10]金發(fā)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J].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1963(34):第2分冊.
[11]周天游.后漢紀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22.
[12]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223.
[責任編輯 賈馬燕 朱偉東]
Evolution from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mparted by Teachers (Shi Fa) to Hereditary Aristocracy (Men Fa)——The Policy of “Stopping the War and Revitalizing Education” and Scholars’ Gentrificatio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MA Tian-xiang
(SchoolofLiterature,XizangMinzuUniversity,Xianyang712082,China)
In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Eastern Han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national policy of stopping the war and revitalizing education so much so that private schools were thriving greatly. Confucian classics masters, together with their disciples, not only became widely known but also were empowered to recommend talents and their disciples to become government officials, which passed from fathers to sons and from masters to disciples for generations, having gradually accumulated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and a rich interpersonal network. Therefore, the process of the gentrification started and the hereditary aristocracy (Men Fa) system took shape, which eventually brought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former since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the latter.
“Stopping the War and Revitalizing Education”; gentrification; hereditary aristocracy (Men Fa)
K234.2
A
1001-0300(2017)01-0019-08
2016-08-27
馬天祥,男,遼寧鐵嶺人,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講師,北京師范大學古典文獻博士,主要從事文學文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