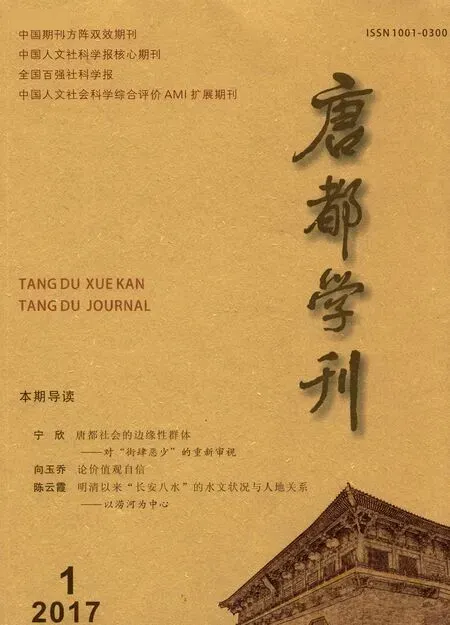從人倫維度探究揚雄思想的體系架構與內在關聯
桑東輝
(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 科研處,哈爾濱 150010)
【倫理學研究】
從人倫維度探究揚雄思想的體系架構與內在關聯
桑東輝
(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 科研處,哈爾濱 150010)
作為擅長思辨的哲學家和工于辭賦的文學巨匠,揚雄的思想大廈體大思精,不僅體系龐大,而且內在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性。從人倫的維度看,揚雄人倫思想的本體論基礎主要是太玄宇宙圖式,其人倫思想的歷史哲學淵源主要是循環更迭、變革損益觀,其人倫思想的人性論基礎主要是善惡相混觀,其人倫思想的道德取向主要是以仁義為核心的五常觀,其人倫思想的美學意蘊主要在于中和之美,其人倫思想的文學價值主要表現在辭賦諷諫,其人倫思想的修養論主要體現在“強學力行”上。
揚雄;人倫思想;體系構建
作為一位研精覃思的大儒和辭賦巨擘,揚雄不僅在思辨哲學、歷史哲學、辭賦文學等方面取得了開創性的成果,而且構建起龐大的思想體系。目前,學界對揚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研究、著作研究、思想研究、影響研究四個大的方面。其中,在思想研究方面,則主要集中在對他的哲學思想、文學思想和美學思想的研究上[1]。也有人將揚雄研究歸為全面研究、生平研究、著作研究、思想研究、語言學研究、影響研究六個方面[2]。相對而言,對揚雄思想體系內在關聯進行研究的尚不多見。本文主要以其人倫思想為視角,對其思想體系的架構,特別是其思辨哲學、歷史哲學、道德哲學、文學、美學之間的內在關聯進行研究,以此來透視揚雄思想體系的內在結構特點。
一、太玄圖式:揚雄人倫思想的本體基礎
揚雄繼承《周易》法象天地和天、地、人“三才之道”思想,吸納老子“玄牝之門”道家理念,提出了以玄為特質的太玄哲學,建立了“夫玄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3]212的本體論哲學。《太玄》雖效法《周易》,但在結構上卻不完全照搬《周易》架構。揚雄自己概括為“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群家。”[3]211桓譚《新論》稱贊其為“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遍,不可損易。”“在揚雄看來,宇宙是依據玄道推演出來的,玄圖即是宇宙的圖式,天地萬物不過是這一圖式所呈現的具體樣態。……太玄即是宇宙的縮影,它順應天道,像天一樣,渾淪周行,永無止境。”[4]
揚雄作為兩漢之際的思想家,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盛行于漢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影響。其“太玄”天道本體思想也必然要反映到人道倫常上,這也是“天人合一”的邏輯指向。揚雄的所謂天道是他的太玄宇宙本體論,也即“玄生神象二,神象二生規,規生三摹,三摹生九據。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天地人是相對應的,天的“始、中、終”對應的是地的“下、中、上”和人的“思、福、禍”。從揚雄的本體論與人倫思想的關系看,天道自然規律是人類道德立法的準則,天道的陰陽決定人倫的尊卑,“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歷陳,故君臣理。”[3]187“晝夜相丞,夫婦系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孟季有序,長幼際也;兩兩相闔,朋友會也。”[3]213可見,夫婦、父子、君臣、長幼、朋友等人倫秩序都是取法于天地設位和四時更替的天道規律。揚雄一再指明他的“玄”乃“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從而,將天、地、人三道統一起來,其落腳點在于人世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
二、損益變革:揚雄人倫思想的歷史哲學
揚雄的歷史哲學也是來源于太玄本體論,核心是“罔直消長,盈虛消息”的新故更迭、循環遞嬗觀點和“道非自然,應時而造”的與時俱進、因時損益觀點。
按照《太玄》的宇宙圖式,八十一首對應天地四時,“極為九營”。這一圖式既體現了四時遞嬗、九天消長的過程,也體現了天地變化、陰陽盈虛的過程。從時間遞嬗看,按《太玄·玄圖》,九天具體為“中羨從、更眸廓、減沈從”。“故思心乎一,反復乎二,成意乎三,條暢乎四,著明乎五,極大乎六,敗損乎七,剝落乎八,殄絕乎九。”從“一天”到“九天”,就是陰陽消長、萬物盛衰的過程。從空間盈虛看,《玄文》云:“罔、直、蒙、酋、冥: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戴也;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則復于無形,故曰冥。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酋乎西,冥乎北。……罔蒙相極,直酋相敕,出冥入冥,新故更代。陰陽迭循,清濁相廢。”這個“罔直蒙酋冥”也是描繪事物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盛轉衰、循環往復的變化過程。
基于天道相因變化、循環往復的道理,揚雄認為人類社會也是因循消長、漸進遞嬗的。在他看來,人類社會文明的歷程就是因革損益的結果。“《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于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5]13一切事物都是發展變化、損益傳承的,“可則因,否則革”[5]11。就禮法而言,“堯、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5]21時代不同,禮法各異,要“因往以推來”。政治制度也要“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5]11,從而做到“為政日新”[5]25。基于“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6]120-121的道理,他告誡為上者要居安思危,不要暴虐于民。鑒于“自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為政者還要因革損益。“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之効也”。[3]190-191在他看來,不論是天道、地道還是人道,其規律都是一樣的,即都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不斷發展變化的。對于人類社會發展而言,要有所因循,有所變革,該因循的時候就要因循,該變革的時候就要變革。沒有繼承就沒有發展,沒有變革也就沒有進步。如果只知道繼承而不加以必要的批判分析,就會“物失其則”;反之,如果只知道變革,而完全否定過去,就會導致走向另一個極端——“物失其均”。要“革而化之,與時宜之”。因此,因革是國家政治倫理的基本法則,是政治成敗的關鍵。
受時代局限,揚雄的歷史哲學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環論。在《劇秦美新論》中,揚雄認為:宇宙初起時,“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或萌,或黃或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有了人類社會,逐漸有了帝王,并有了法度禮儀和政治制度。“太上無法而治……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儀哨哨。”[5]10按照揚雄《劇秦美新論》的觀點,從伏羲開始,人類社會經歷了從蒙昧到文明的依次遞嬗,但逐漸盛極而衰,循環往復。固然,揚雄的《劇秦美新論》有阿附王莽之嫌,但其中亦可見揚雄的政治倫理思想。
三、善惡相混:揚雄人倫思想的人性論
揚雄的人性論也是建立在其太玄本體天道觀基礎上的。他認為:“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縱與橫,表人之行曰晦與明。”[3]191“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3]186很明顯,在揚雄思想里,人性的晦明、善惡也是受到天道的影響,是天道陰陽特質在人類身上的體現。蔡元培在論及揚雄倫理思想時曾敏銳地指出:“揚雄之倫理學說,與其哲學有密切之關系。”就人性而言,“宇宙間發生人類,人類之性,必同于宇宙之性。”[7]揚雄雖然沒有說明其“人之性也善惡混”[5]6-7的理論依據和來源,但他主張天道影響人道,既然立天之經是陰與陽,表人之行是晦與明,那么,由天有陰陽、地有縱橫,推致出人有晦明、人性有善惡的善惡相混的人性論則是揚雄思想邏輯之必然結論。
古往今來,對揚雄善惡混的折中人性論一直存在著不同看法,有的認為本質上揚雄是堅持性惡論的[8]。也有人認為“由于玄既是人道先天的根據,又是經過后天努力,可以達到的最高境界,是天道與人道渾然一體的狀態,氣與心性合一。……揚子事實上有性善論的傾向。”[9]深入研究揚雄的太玄宇宙論與人性論的關聯,不難發現,揚雄的人性論雖然綜合繼承了先秦儒家的性善說和性惡說,并一定程度地吸納融會了西漢以來的天人思想和易學思潮,但他的人性論具有獨創性。“揚雄人性論中能夠別樹一幟的地方,一是他以玄論性,玄不僅具有本體論的色彩,而且是純善的;二是他提出人性善惡混的觀點,對此后的人性論產生重大的影響。”[10]揚雄善惡相混思想為其人倫思想提供了人性論基礎。按照揚雄的觀點,一個人要修成圣賢,首先要用善念來保持自己的心。“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仁。能常操而存者,其惟圣人乎?”[5]13并且強調凸顯人作為道德主體的自覺選擇。面對禽、人、圣三途,人的道德選擇是最根本的,是成就人倫的內因。“由于情欲,入自禽門;由于禮義,入自人門;由于獨智,入自圣門。”[5]9
四、仁宅義路:揚雄人倫思想的道德取向
盡管揚雄的思辨哲學是會通儒道的,但其人倫思想歸根結底是儒家的,他把儒家的仁義道德作為其道德觀的根本。《法言·問道》:“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在董仲舒仁、誼(義)、禮、知(智)、信五常之道的基礎上,揚雄進一步將五常對應具體事物。“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5]7揚雄對五常之中的仁義尤為重視,宣揚所謂的“仁宅義路”,并將仁義與道德并舉。“夫進也者,進于道,慕于德,殷之以仁義。”[5]38有時他也將仁、義、禮與道、德聯系起來,“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5]9-10同時,對于不仁不義的行為多有批判。他指出:“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5]36將毀譽與仁義聯系起來,反對妄毀妄譽之行,提倡仁義之舉。如前所述,揚雄作《太玄》不僅僅是為了建構他的宇宙哲學體系,更在于為人世立法,而其所立之法就是仁義。在《法言·問道》中,揚雄自說自話地道出了作玄的主旨。“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在《太玄·玄掜》中也再次指出“尊尊為君,卑卑為臣,君臣之制,上下以際”,這里反復強調的是上下尊卑的秩序。揚雄的人倫思想由仁宅、義路、禮服、智燭、信符的五常觀擴展到強調上下尊卑秩序的政治倫理。
受仁義為核心的人倫思想影響,揚雄的政治倫理突出的是仁政取向。他曾用“思政”和“斁政”來分疏他的仁政思想取向。按照揚雄的“審其思斁”思想,何謂“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轅濤涂,其斁矣夫!於戲!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污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斁。”[5]25如此看來,揚雄的思斁思想實際上是繼承了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1]的仁政思想,體現了揚雄為政治國的德治仁政主張。
五、中和之美:揚雄人倫思想的美學意蘊
在揚雄本體論宇宙圖式中,“中”占據重要位置。他將《中》列為《太玄》八十一首之首,并將中的宇宙論引申到道德領域,提出中和的道德美學觀念。“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甈,柔則壞。龍之潛亢,不獲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于中乎!圣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5]27在揚雄的思想里,中與玄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同一關系,“太玄”就是模仿《易》的“太極”或“太和”,是陰陽二氣未分混一的元氣,而這一陰陽未分的混一之“太玄”也是“中”。[12]

六、寓諷于賦:揚雄人倫思想的文學諷諫
作為辭賦大家,揚雄的辭賦不僅僅在于文字的鋪排,更具有道德意蘊。他通過辭賦作品,寓諷于賦,寓諫于頌,委婉地表達自己對君主的勸誡,將其人倫觀落實在忠諫中。
揚雄辭賦不僅頌美,而且諷諫,是披著頌美外衣的諷諫,其作賦主旨顯然不在于頌美,而在于諷諫。在揚雄自己作的賦序中,已經說明甘泉、羽獵、長楊、河東四賦都是因諷而作。《甘泉賦》自序云:“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河東賦》自序云:“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跡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知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羽獵賦》自序云:“孝成帝時羽獵,雄從。……尚泰奢麗夸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后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長楊賦》自序云:“明年,上將大夸胡人以多禽獸。……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抑以風。”以上不難看出,揚雄的辭賦其根本點在于諷諫,在于勸上。不僅在賦序中點明諷諫意圖,而且在華麗的字里行間可以看出其美刺微諷的良苦用心。如《甘泉賦》的“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妙遠,肅乎臨淵。”李善注引服虔曰:“襲,繼也。桀作璇室,紂作傾宮,微諫也。”很明顯,揚雄以璇室和傾宮來提醒君主吸取桀紂暴政亡國的教訓,目的在于忠諫。但在君尊臣卑的專制社會里,冒死強諫尚不能打動昏君,揚雄的諷諫所起到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他后期在《法言》中悔其年少作賦,稱其“壯夫不為”,并“輟不復為”,其原因也在于他看到辭賦諷諫起不到作用。
綜觀揚雄的辭賦,其諷諫的具體指向都在于勸告君主行仁政,即多行思政,少行甚至不行斁政。在揚雄看來,政治喪亂主要歸咎于統治者的窮奢極欲,“游觀侈靡,窮妙極麗”,“苑囿之麗,游獵之靡”。[6]117他主張君主應“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6]114“不奪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6]113“烝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遍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立君臣之節,崇賢圣之業”。[6]117這樣才能保證漢家江山“于胥德兮麗萬世”,“子子孫孫,長無極矣”。[6]98而要做到上述的關鍵,就是要“朝廷純仁,遵道顯義”。[6]120“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凱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6]121只有這樣,才能“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6]117
七、強學力行:揚雄人倫思想的修養路徑
揚雄構建起龐大的思想體系,其落腳點在于對社會現實的關注,特別是指導人提升自我修養,提高道德水準。作為漢代大儒,揚雄所倡揚的人倫追求核心在引導人們向圣人看齊,做一個有良好道德情操的君子。基于其“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者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5]6-7的人性論,揚雄指出一個人要想學習圣人,成就君子,主要靠后天的“修”。這個“修”既包括學,也包括行,這也就是他將在《學行》放在《法言》之首的用心所在。
首先,揚雄肯定學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他看來,學習是人禽之分的一個重要條件。“鳥獸觸其情者也,眾人則異乎。賢人則異眾人矣,圣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5]2而學習的目的就在于激發潛藏在人性中的善質。揚雄用刀與礱、玉與錯的關系,生動地說明通過學習來激發人性善本質的必要和可能。“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礱諸,有玉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5]1在他看來,上天讓人有耳目也都是用來學習禮樂的,“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5]11
其次,揚雄強調踐履的重要性和現實性,他主張將學與行結合起來。“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眾人。”[5]1并提出“強學力行”的道德修養論。所謂“圣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是以君子強學而力行。”[5]7他認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5]2無疑是將人的日常行為作為學習修性的內容,從而將道德知識的學習與道德實踐的踐履緊密結合起來。
再次,揚雄提出“強學力行”要堅持正道。在揚雄看來,道德學習和踐履的內容就是儒家倫理,只有儒家倫理才是“正而不它”之道。《法言·問道》載:“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它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而要歸于正道,禮樂教化至關重要。“圣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5]11在揚雄看來,一個人如果不知禮,則失去做人的依托,更談不上德。“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5]10即使一個人智勇雙全,但如果沒有禮樂修養,也難稱社稷之臣。譬如,“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悟,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5]35
此外,揚雄突出修性成人的目的性,提出“不鑄金但鑄人”的理念。他認為道德教化的目的主要在于引導人們尊奉儒家倫理正道,自覺地希圣希賢,學做圣人,修成君子。揚雄反對人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亂象,主張“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圣”[5]6。在他看來,如果一個人立志正道,“強學力行”,最終就是要成為孔子、顏回那樣的圣賢。“有教立道無止,仲尼;有學術業無止,顏淵。”“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5]4揚雄將人倫修養的重點最終落在了強學力行、學為君子、學為圣人的層面上。
綜上所述,揚雄的思想大廈雖然體系龐大,但其內在的結構性和關聯性非常強。從人倫視角不僅透視出其本體哲學、歷史哲學、道德哲學、美學、文學等體系的完整性和嚴密性,而且不難發現這些內在系統之間的關聯性和和諧性。正如桓譚《新論》所指出的,其“言圣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在揚雄的思想體系中,“太玄”無疑是構成其思想大廈的最基礎砫石和本根,同時又是連接各系統的最基本線索和骨架。
[1] 張曉明.二十年來揚雄研究綜述[J].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2(4):94-97.
[2] 趙為學,王棟.揚雄研究的源流與不足[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6):7-9.
[3] 揚雄撰,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8.
[4] 周立升.《太玄》對“易”“老”的會通與重構[J].孔子研究,2001(2):83-92.
[5] 揚雄.揚子法言[M]∥諸子集成: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54.
[6] 蕭統.文選[M].上海:上海書店,1988.
[7] 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9.
[8] 鄭文.揚雄的性“善惡棍”論實際是荀況的性惡論[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4):9-12.
[9] 問永寧.從《太玄》看揚雄的人性論思想[J].周易研究,2002(4):25-33.
[10]李沈陽.漢代人性論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8.
[11]焦循.孟子正義[M]∥諸子集成: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4:51-52.
[12]董根洪.“動化天下,莫尚于中和”——論揚雄的中和哲學[J].社會科學研究,1999(6):76-79.
[13]萬志全.揚雄美學思想的發展歷程[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3):123-126.
[責任編輯 王銀娥]
Study of Yang Xiong’s System Establishment andInternal Relevance from Ethical dimension
SANG Dong-hui
(CenterforScientificResrarch,HarbinAcademyofSocialSciences,Harbin150010,China)
As an intellectual philosopher and literary master, Yang Xiong’s thought was broad in conception and meticulous in details with an all-encompassing system and a close relevance. From the ethical dimension, Yang Xiong’s thought on human relations was built upon Tai Xuan universal diagram; his historic philosophical origin of thought on human relations was focused upon the cycling changes and changes in profits and losses; h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was based upon the mixed good and evil conceptions; his moral orientation was centered upon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with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s its core; his aesthetic implication was represented by the beauty of the golden mean; his literary value found its expression in the satire of his Ci and Fu; his theory of cultivation is embodied by morality-cherishing and truth-seeking.
Yang Xiong; thought on human relations; system establishment
B82
A
1001-0300(2017)01-0035-06
2016-10-26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傳統人倫觀的價值合理性及其現代審視研究”(13BZX071)
桑東輝,男,黑龍江哈爾濱人,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科研處特邀研究員,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倫理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