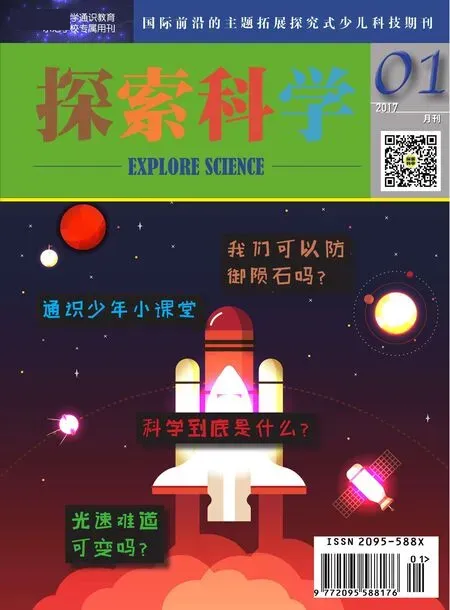科學到底是什么?
科學到底是什么?
不需要定義的科學
“從小愛科學”是一個喊了幾代人的口號,現在大家都知道,科學是好的,應該愛科學,這已經成了一個常識。不過,我們愛科學,總該知道科學是什么吧。但偏偏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真正的科學家并不執著于“什么是科學”這樣的問題,他們在經過長期而綜合的思想訓練之后,對一些事情有了明確而堅定的信念,在具體研究的過程中,反而不受定義的限制,可以因地制宜。所以哲學家庫恩對科學有個奇妙的定義:科學就是科學家們在 做的事情。
其實,科學確實不需要一個明確的定義。因為科學是面向未來的,而誰也不知道未來會怎么樣,所以科學家們需要自由的思想和創造的勇氣,任何畫地為牢的定義,本質上都不利于科學的發展。不過,科學雖然沒有明確的定義,但是有規范和功能,另外也有一個包含的范圍。
所謂規范,就是不能因為科學定義不明確,就可以把任何事情都說成是科學。科學有其研究方法,就是重視實驗,用事實說話,用數據說話。很多民間的理論沒有實驗支持,也沒有數據支持,就是看大家相信不相信,那就不是科學。科學非常講究懷疑和批判,如果沒有證據,我為什么非要相信別人說的呢?
科學的功能是很明確的,那就是預測和解釋。科學是面向未來的,它可以做出其他任何理論都無法做出的精確預測。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的時候,首先就是預測了1919年日全食的時候可以觀察到一個前所未知的天文現象,從此聲名鵲起。另外,科學必須對觀測到的結果有一個完整而合理的解釋,如果無法自圓其說,也不是科學。好比說20世紀,有學者提出大陸漂移學說,但是解釋不出大陸為什么會漂移,怎么能漂移,于是并不被認為是科學,直到后來發現海底火山,能解釋大陸漂移的成因和動力了,這才成為科學的理論。
廣義的科學
現代科學主要是數理實驗科學,就是用實驗和數字來說話。它的起源是古希臘的理性科學,后來受了基督教的一些影響,成了今天的樣子。廣義的科學里還包括了應用技術和對大自然的客觀記錄。
有一種說法,認為一切人類文明都有自己的科學,這個話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邏輯太模糊了。應該說,一切文明都有應用技術和對自然的客觀記錄。
所有的人類古代文明,包括埃及文明、希臘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乃至美洲的瑪雅和印加文明等,都有很高的智力水平和先進的技術。以中國為例,漢代的玉雕,唐代的鑲嵌,水平之高,工藝之巧,令人嘆為觀止,以今天科技之昌明,也無法完全復制出來。其他的古代文明也是各有擅長,好比說印加文明的羊駝毛紡織技術就是獨步世界,技術失傳之后,到現在也做不出來。
但是,這些“技術”不能等同于科學。中國人總喜歡說科技這個詞,原因之一是我們分不太清科學和技術的區別。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科學的一部分,但技術畢竟只是技術,并非意識形態上的“科學”。
另一個人類文明共有的現象,是喜歡做博物性的歸納總結,就是對自然界各個物種,甚至天文地理現象,進行歸類和記錄。古書上經常會記載各種天文地理知識,還有農產品的分類甚至礦物的分類。這種學科以前叫作博物學,意思是博覽世上萬物,這個學科確實也是科學的一部分,但和技術一樣,博物學和科學最本質的概念還是有距離的。

要了解科學的核心本質,最直接的方法是了解科學的前因后果,了解了人類為什么會發展出科學,你也就明白科學究竟是什么了。

科學并非中國的傳統文化
關于科學的本質,我們必須從文化的角度去看,才能真正地理解。
從根本上說,科學的思想來自歐洲,它并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中國古代沒有和“科學”相對應的詞,古時候的“科
學”指的是“科舉之學”,就是考試的學問,是一個基本上沒人用的詞匯。把英文的Science翻譯成科學,
是日本人的發明,在19世紀中后期,自然科學高度分化,變成了物理、化學、天文、生物等諸多學科,所以日本人以“科學”作為統稱,可以突出其“學科眾多”的含義。
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理念,只有“格物致知”的觀念,意思就是研究事物,從而獲得知識,但是在傳統教育體系里,這個觀念不太重要。中國古代教育的目標是讓人有良好的道德品格,從而可以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所以長期以來,中國都以人品道德作為知識和教育的核心。雖說鼓勵人們“德才兼備”,但德總是比才更重要。

中國近代對于科學的理解,一開始就是技術。在19世紀中期,魏源等有識之士,看到中國和歐洲的工業科技相差甚遠,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概念,就是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從而避免國家衰亡的悲劇發生。從1861年開始,中國興起了洋務運動,用西方的技術來修建工廠,制造武器。但當時人們并不理解什么是科學,不知道隨著科學的發展,技術會不斷提高,他們的觀點還停留在古代,認為技術學到就可以了,并不追求更新和發展。
到了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中國的知識分子意識到,光有技術不行,開始正視更深層的科學問題。1897年,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里提到了《科學入門》和《科學之原理》兩本書,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接觸科學的概念,之后科學的傳播在中國步步深入,成了人們普遍最認可的觀念。但是由于科學并非中國傳統思想,大家理解起來有困難,所以長期以來,中國人都會把科學和技術混為一談。
古代中國和古代希臘的差異
真正的科學思想,發源于古代歐洲,具體而言是古代希臘。為什么科學的發源地是希臘而不是中國呢?是因為雙方完全不同的地理環境導致了文化上的巨大差異。
古代希臘文明和古代中國文明,都發源于距今三四千年前。從考古上看,希臘古老的克里特—邁錫尼文明和中國最早的二里頭—殷墟文明時間差的不多。真正相差巨大的,是雙方的地理環境。
中國文明起于河南,二里頭文明(也就是傳說中的夏文明)興起的地點,在今天河南偃師。在最古老的夏商西周三朝,文明全在內陸,對大海只有個模糊的認識。古中國的經濟基礎是農業,吃飽飯最重要,所以土地是最重要的財富,商業反而并不重要。中國人以前覺得商人不會種地,等于沒有生產力,是社會的負擔,于是在政策上重農抑商,這個傳統沿襲了三千多年。
但是希臘不同,它的文明誕生于愛琴海上,有一個半島和眾多小島,海運四通八達。希臘土地貧瘠,糧食產量不高,多的只有橄欖油和葡萄酒,為了獲得糧食,他們只好和外部開展貿易,方法就是到處航海經商。所以希臘文明一開始就是海洋商業文明。

農業文明不喜歡遠行,古人說“父母在,不遠游”,而且風險也大,出去一趟能不能活著回來都不一定。由于長期定居,不遠游,周圍打交道的都是熟人,所以中國人的文化是“熟人文化”,七大姑八大姨的都認識,干什么事喜歡講人情,而不是法理。但希臘不同,希臘人做生意,經常出海去很遠的地方,和完全不認識的人打交道,是徹底的“生人文化”,沒有什么人情可言。在這種情況下,法理就很重要了,只有雙發都遵守教義的契約準則,生意才能做得下去。所以希臘人和后來的歐洲文化,特別重視契約精神。

為了自由而誕生的科學
在歐洲的文化里,契約是人們交往的準則和基礎,那契約最需要的是什么呢?答案是自由。因為每個人都必須是獨立自主的人,這樣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西方人在幾千年中,形成了“自由至上”的觀念。美國有自由女神像,法國最出名的畫作是“自由引導人民”,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更有一首名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
者皆可拋。可見“自由”二字在西方的地位是無上尊崇的。
與此相對,中國古代幾乎沒有“自由”這個概念,這個詞和科學一樣,都是日本人翻譯的。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人是社會的一部分,集體遠遠比個體重要,太重視自己是自私,而自私是個不好的事情。這就是文化上的巨大差異。
古希臘人認為自由是最重要的,所以最具侮辱性的詞匯是“奴隸”,因為奴隸沒有自由。那人該如何獲得自由呢?古希臘人認為,除了法律上的人身自由,還需要在精神上獲得自由。
古希臘人盡皆知的一個名言是“認識你自己”,這句話是“神諭”。為什么是神諭呢?因為它太重要了,所以只能說是神的指令,無可置疑。所謂“認識你自己”,就是必須要對自己進行反思,獲得屬于自己的知識,這樣才能獲得精神上的自由。
古希臘人認為,知識是屬于自己的,堅持追求知識,是自由的象征。而且這個知識和我們理解的不同,我們現在認為“知識就是力量”,中國古人認為“書中自有黃金屋”,都講究學以致用,知識必須要運用才行,但是古希臘的哲學家反復強調,純粹的科學唯一的目的就是求知本身,不能為了其他任何目的存在。曾經有一個人,找古希臘大數學家歐幾里得學習幾何,上來就問學幾何有什么用,結果被趕了出去。歐幾里得憤怒地說:誰不知道我的學問是完全無用的!
科學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塑造自由的人格
古希臘和古中國有一點是一樣的,就是強調教育對人性的塑造。中國的三字經里說:人之初,性本善,茍不教,性乃遷。希臘人也是這樣認為的。
古希臘學者認為,只有自由的知識,才能塑造自由的人格。所以知識必須是非實用性的,因為如果知識成了工具和手段,那知識本身就不自由了,不是純粹為了自己而存在了。所以希臘人樹立的科學傳統,是為了知識而知識,為了學術而學術,不是為了實用,甚至不是為了發展技術,這一點和中國學以致用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古希臘人對于科學實用性的排斥,是有些過度了,但其精神依然值得學習。中國長期以來缺乏“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骨子里就是因為學以致用的思維傳統太過強大,所有的教育都在強調知識有什么用,這在長遠來看是有害的,因為科學的發展需要那種“為了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歷史上那些重要科學理論的發現,并不是為了獲得財富或者有什么實用價值,就是因為學者喜歡思考而已,但之后改變了世界。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牛頓創立牛頓力學,不是為了制造機械,卻讓世界進入工業時代。愛因斯坦創立相對論,也不是為了讓GPS衛星定位,但是今天的一切航天工業都要依賴于相對論。如果用一句話形容,那就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古希臘的科學,不講究實驗,純粹就是思考,但是取得了相當出色的成果。好比說原子論、進化論、日心說等理論,都來自于古希臘的哲學家,因為這些理論是可以由純粹的思考來發現的。像進化論,古希臘人怎么知道人是進化而來的呢?因為人的嬰兒太弱小了,無法保護自己,甚至無法覓食,總之就是無法靠自己生存下去。那么無限倒推上去,世界上的第一個嬰兒也無法靠自己生存,所以人類的祖先必須是一種能自己生存的動物,我們是從那種動物演化而來的。

大學的誕生
從古希臘到古羅馬,哲學家們用自己的智慧盡可能地演繹了科學,尤其在數學和天文等學科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到了兩千年前的羅馬時代,希臘哲學演變成了“自由七藝”,就是自由之人應該學習的七門基礎課程,其中包括語文三藝:語法、修辭、邏輯,還有數學四藝:算數、幾何、天文、音樂。
公元四世紀,羅馬帝國接受了基督教,不久之后羅馬帝國分裂并崩潰,但基督教作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在歐洲一直延續了下來。
基督教信奉一個全能的上帝,和希臘科學是完全不同的思想派系。但是基督教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羅馬政府長達數百年的壓迫,所以它很了解如何跟不同的信仰體系打交道,甚至把其他派系的思想吸納到自己里面來。而且基督教的領導者也是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后裔,所以他們理所當然地把古希臘哲學和基督教融合在了一起。
基督教統治下的歐洲,是現代科學得以孵化的地方。在13世紀的法國和意大利,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學。當時的本科學院只有一個,就是“藝學院”,學習的對象是“自由七藝”。在本科畢業之后,可以去法學、神學、醫學等專科學院深造。大學的觀點,是學生必須塑造好自由而有知識的人格,才能學習專業知識。
直到今天,歐美名校的本科依然是沿襲了中世紀的優良傳統,好比說世界最好的哈佛大學的法學院、醫學院、管理學院等是沒有本科生的,他們的生源都來自文理學院的畢業生,而這個文理學院就是中世紀大學教授自由七藝的地方。教學的方式主要是答辯,就是通過提問和辯論,讓學生獲得知識。
當歐洲的大學概念傳入中國的時候,著名學者蔡元培,也就是北大的第一任校長,力圖將北大建設成一個本科學校,希望學生完成了對知識系統的學習之后,再去專科進行深造。但可惜的是,后來沒有人繼承蔡先生的工作,中國大學的本科里逐漸出現了法學、醫學、管理學等專科學生,甚至連教學方式也由提問答辯轉成了課本教學。相信通過理順科學教育的發展史,將來中國的大學也會不斷改進。
走向現代科學
古希臘的科學和現代科學是有區別的。古希臘的科學,是純粹為了追求知識,他們認為有了自己的知識,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古希臘人也希望能認識大自然的本質,但大自然本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為自然是諸神的領域,好比說海里有海神,山上有雷神,太陽上有太陽神,諸如此類。這是遠古時代薩滿文化的遺留,在文化上叫“多神論”。由于有這種觀念的存在,古希臘人認為,對大自然可以觀察,可以模仿,但是人造的東西永遠比不上大自然的東西。大自然是神圣的,不能隨意探索,至于拷問和改造大自然,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但我們看今天的科學概念,會發現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想要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需要很多相關的知識,你要用水利來發電,就要知道水的運行方式,那這些知識從哪里來呢?答案就是拷問自然,科學家們會把自然界里的東西,好比說一塊石頭,放進實驗室,像對待犯人一樣,把不同的溫度、濕度、壓力......等等,一一施加在石頭上面,看看石頭遇到高溫會怎么樣,遇到強酸會怎么樣,施加各種刺激,看看石頭的反應。這其實就是用無數的方法,逼著大自然吐露自己的秘密。
為什么會有如此巨大的思想轉變呢?原因就在于基督教的影響。希臘人對大自然奉若神明,因為大自然就是神域,但是基督教極大地改變了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基督教雖然主張有一個萬能的神創造了一切,但在所有的創造物中,人的地位是最高的。人類始祖命名了萬物,人是神在世上的代理人,而大自然反而沒有了神性,或者說,大自然是被神創造出來為人類服務的。在這個觀念的影響下,無論對大自然做些什么,似乎都成了合理的。現代科學雖然不相信有這么一個神的存在,但是也不能否認基督教在歷史上的影響。
培根和唯名論對科學觀念的改造
在基督教的思想影響下,大自然喪失了神性,但這并不等于人們就會對大自然開刀。真正完成這個思想轉變的,是英國的大哲學家佛朗西斯·培根(1561-1626)和基督教的思想派系“唯名論”。
培根有一句名言,叫“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針對的,就是古希臘的科學。
在培根看來,希臘人的科學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卻完全不拿來為人類造福,簡直就是暴殄天物。希臘人認識自然,目的就是認識本身,而培根認為,只有改造自然才是目的,認識只是手段。所以,現代科學和古希臘的科學一開始就有區別,現代科學為了給人某福利,可以隨意改造自然。改造自然需要技術,所以現代科學和技術一直就是聯系在一起的。科學家研究出科學理論,然后會有無數發明家和技術人員拿著科學理論去實踐,制造出先進精密的儀器。這就是為什么中國人了解科學,首先是從技術入手的。
另一個塑造了現代科學的理念,是基督教的唯名論。在古希臘人的眼里,大自然是穩定的,天地的運行有著穩定而完美的邏輯,你只要認真思考,用理性就可以了解世上萬物萬事的真諦。基督教一開始也接受了這個觀點,但后來有一派哲學家發現了希臘人和基督教的矛盾之處。基督教相信世界上有一個萬能的神,就是上帝,這個神既然是萬能的,那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只要上帝愿意,他可以讓太陽從西邊升起來,也可以讓人返老還童。換言之,人類無法憑理性了解上帝會對世界做些什么。唯名論對古希臘科學的抨擊,催生了著名的經驗學派。他們認為,要了解世界上的一切,不能單靠想象,而必須從經驗入手,那怎么獲得經驗呢,就是靠實驗,在實驗室里做各種實驗,看看世界究竟是什么樣子。用一句老話說,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一切標準。
改變世界的科學
總之,培根的知識實用主義,還有經驗主義主張的“通過實踐來了解世界的真相”,極大地改變了古希臘科學傳統的面貌。傳承兩千多年的思辨求知傳統,還有深厚的數學積淀,和大量的物理實驗互相促進,讓人類對世界的認知一下子上了好幾個臺階。從17世紀之后,以牛頓為首的一大批科學家噴涌而出,還有卡特等一批發明家拿著最先進的科學理論去制作精密機器,于是世界的面貌從此被改變了。一些本來沒有現代科學的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被迫要進入新的科學時代,而這個過程可能是很痛苦的,就像中國悲慘的近代史那樣,很多古老的帝國,像印度,甚至徹底成了殖民地。
世界的近代史,外表看來是歐洲的擴張史,究其根本而言,其實也是一部科技普及史。這個過程給世界帶來了不少災難和悲劇,但是從長遠看來,科學給這個世界帶來的東西還是正面的。如果歐洲沒有出現科學,也許我們還過著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生活,晚上沒有電燈電視,出門沒有汽車飛機,冬天沒有暖氣,夏天沒有空調,人均壽命只有三十多歲,一輩子聽不到幾次音樂,能吃飽飯就是上上大吉了,至于手機就更不用想了,一般人恐怕連字都不識。
科學是面向未來的學問。了解了它的過去,就可以明白科學的本質,但我們也要記住,就像唯名論認為的那樣,人類其實無法真正預知未來,就連明天太陽從哪里升起來,在太陽實際升起來之前,我們也無法絕對斷言。所以唯一科學的方法,就是認真總結經驗,然后抱著懷疑的態度,仔細觀察這個世界。
科學家根據經驗總結科學規律,再根據科學規律預測未來,然而一旦現實不符合預測,那就要對科學規律進行修改。科學規律歸根結底是人總結出來的,只能向真正的自然規律靠攏,但其本身并非真理。所以科學是不斷更新和進展的,科學家們的重要工作,就是發現科學中的錯誤,不斷地糾正,然后讓人類能更加完善地改進自己的生活。與科學相反,那些號稱自己是真理,從不修正的理論,反而不能給人類帶來美好的生活,因為人類的思想,根本就沒有一個是真理,但只有科學在努力地向真正的真理靠攏。
現在,科學對自然的改進,有時候反而會不利于人類自身。好比說大規模的工業生產會造成霧霾,威脅了人們的身體健康。但這些事情的解決,最終還是依靠科技的進步。歐美日本等國,在現代化的路上,都曾經遇到過嚴重的工業污染,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這些問題一一得到了解決,昔年著名的污染城市,英國的霧都倫敦,現在已經重現藍天白云了。我們相信,給一些時間,中國的科學家也可以讓中國的天空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