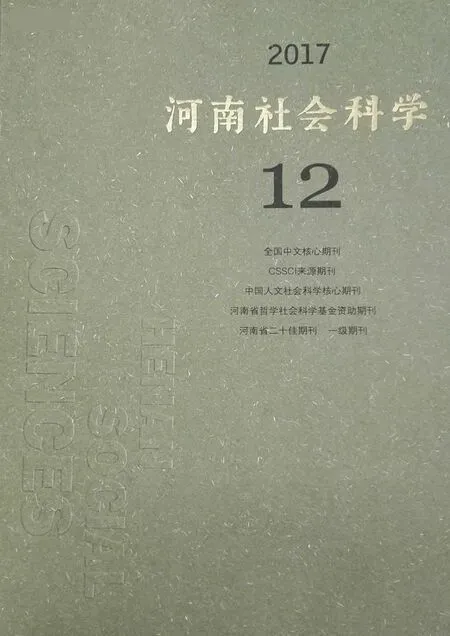明清浚縣古廟會:權力主體與場域構建
——基于浚縣浮丘山明清碑刻的研究
邢 涵
(東南大學,江蘇 南京 211100)
浚縣正月廟會,是全國著名古廟會。因廟會的主要活動在大伾山、浮丘山上進行,所以浚縣正月廟會又稱浚縣山會。浚縣正月古廟會與山東省的泰山廟會、山西省的白云山廟會、北京市的妙峰山廟會,被公認為華北地區四大廟會。由于浚縣正月廟會起會早、時間長、規模盛大、民俗味濃,又被公認為“華北第一古廟會”。廟會的主體是廟宇本身,廟宇和人的行為共同構成了廟會,人們在廟會活動中會產生選擇性的行為,這種選擇性是由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角色地位和時代性所決定的。法國社會學大師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是社會學的主要理論之一,是關于人類行為的一種概念模式,主要指每一個行動均被行動所產生的場域所影響,而場域并非指單一的物理環境,也包括他人的行為以及與他人行為相關聯的許多因素。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進一步說,場域是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空間,相對獨立性既是不同場域相互區別的標志,也是不同場域得以存在的依據。皮埃爾·布迪厄在《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一書中提出了資本、場域、習性這三個概念,“場域”(field)是皮埃爾·布迪厄從事社會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也是皮埃爾·布迪厄藝術場理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場域的定義是“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網絡,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正是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強加于占據特殊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上的決定因素之中,這些位置得到客觀的界定,其根據是這些位置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占有這些權力就意味著把持了在這一場域中利害相關的專門利潤(profit)的受益權——的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處境(situs),以及它們與其他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支配關系、屈從關系、結構上的對應關系,等等)”①。場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而非單純的地理空間,在一個社會空間中,由于資本和權力的運作,會有無休止的斗爭,因此這個空間是一個動態的空間。基于這一理論,可以清晰地分析明清時期古廟會的發展方式和過程,為當今古廟會的保護和發展提供新的思路。
一、廟觀修筑:政府與官僚政治資本的攫取
在廟會活動中,我們可以將一切與廟會有關的活動看作一個獨立的場域,在這個場域中占有資本和權力的顯然是政府和當地官員,以明代為例,明代中后期皇帝崇尚道教,尤其是嘉靖年間,嘉靖皇帝對于道教的尊崇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有了這樣的信仰基礎,自然會產生出與之相匹配的空間主體,即廟宇和道觀。官員們也是上行下效,在全國各地建起了道觀。浚縣也不例外,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浚縣知縣蔣虹泉主持修建碧霞宮,歷時21年才建成,建成之后又歷經數次翻修擴建,終成現在的規模,而蔣虹泉也馬上就得到了提拔,由知縣升為河南布政使,緊接著又當上了云南都御史。碧霞宮的建成對于浚縣當地來說意義深遠,時至今日,每年正月前來上香朝拜的人依然絡繹不絕。有趣的是,華北地區的四大古廟會所祭祀的主神都是碧霞元君,可見在政府和官員的引導之下碧霞元君信仰的興盛程度。
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重修碧霞元君行宮記》②“明興敬神恤民,神道設教,世加崇奉,歆動靈貺,赫赫奕奕。歷圣天子封神為‘天仙玉女廣靈慈惠恭順普濟護國庇民碧霞元君’,敕賜廟額,歲命中貴捧香以進,上祝圣壽,下祈國泰。而天下民士無不敬禮,應顯尤多,山東西,河南北,歲時道路不絕于行。如不及走登,則建為行宮,遍郡邑閭里矣!……嘉靖庚子,普安進士蔣虹泉來尹于浚……蔣始神之,復具衣冠往謝。因其祠卑隘,大捐俸資,遷之浮丘山椒。浚人淳厚者歡然助之……工訖,蔣方為河南布政使,已而升云南都御史,萬里馳書屬記于思……”這段碑文明確記載了明代對于碧霞元君信仰的推崇和浚縣碧霞宮的建成過程,并且說明了碧霞元君祠是有官方背景的,碧霞元君也是被“官方認證”的神祇。這塊碑記是由“鄉進士龍川孟思撰文,邑庠生它山陳瑤書篆”的,也說明在碧霞元君信仰的宣傳上來說,文人、知識分子及神祇的官方身份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二、道釋儒化:鄉紳、文士與地方文化的重構
之后清朝的宗教政策基本延續了明朝的政策,但清朝的皇帝并不像明朝皇帝那么崇尚道教,因此對于民間信仰的道教神祇進行了一部分的改造,模糊了碧霞元君的身份,淡化了民間佛教和道教的界限,碧霞元君作為道教的神祇,在清代的碑刻之中則被稱為觀音的化身,如清順治年間的《浮頂進駕萬善碑記》③云:“嘗聞釋教以無我為宗,儒道以同人稱大……考諸傳記,圣母元君乃觀音大士之化身也。大士駕慈航而渡苦海……”而參與立碑的人也并非普通香眾,其中包括“林文郎知浚縣事江東王譽命縣丞張有孚,典史陶爾錦,儒學教諭冷然善,訓導王珹,四川道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馬大士,欽差陜西榆林道今轉江南淮海道布政司參政兼按察司副使佟國楨,原任河南按察司驛傳道兵備僉事李子和,欽差河南清軍驛傳、鹽法兵備道按察司僉事程淓,大同山陰縣知縣張施大,工部觀政進士侯夢卜,禮部觀政進士黎煥然,舉人劉芳譽,舉人鄒镕,原任宣大督標旗鼓游擊趙景云”等。如此多的官員和知識分子在立碑之時,犯下佛道不分的錯誤,顯然是有意為之,而碧霞元君與觀音大士這兩個神祇對于普通香眾來說在功能上并沒有太大分別,都是用來求子和祈求平安的,模糊道家和佛家的界限會使碧霞元君的地位進一步提高,信眾更多。時至今日,當地一些群眾還認為浮丘山是佛家圣地。除了這塊《浮頂進駕萬善碑記》之外,還有很多進香的碑記中也會用到很多佛經教義中的詞語。清代對于神祇的改造不僅僅限于模糊佛教與道教的界限,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創建純陽呂帝君洞閣碑記》④云:“堪輿形勝之論,儒者每諱引之。雖然,勿過執……客曰:‘邑夾伾浮兩山間,東伾西浮,東西文武所分署位也。按天文志,東方木星曰“歲”,歲主文章;西方金星,曰“太白”太白主甲兵。伾浮既劃然列東西,地與天應,則文武之各有攸司,不甚明耶?今浮之巔有岱之玉女離宮在焉,雕甍畫棟,金碧燦然,而香火傾大河南北。乃伾,則青壇故跡,已翳荊榛,雖有佛閣龍洞,名在實亡,幾于寂寂空山矣。龍精為虎氣所奪,縫掖之劣于韜鈐也,或職是故?’予曰:‘是說有似,然則補救之道何出?’客曰:‘是宜增勝于左,以與右敵,俾龍虎各得其所而已。’予因思增勝之說,非仍以神道設教不可,而求其神之英靈盻蚃,可埒于岱之玉女者,一則于佛,取觀音大士焉,一則于仙,取純陽呂祖焉。即而思之,大士以浮屠之道道天下,釋與儒不相為謀。而純陽,唐之進士,終歸于道,始則為儒,且好為篇章……此文章神仙也。此祠于伾而擬于浮,庶幾純陽太陰之兩不相絀乎?……”此碑為文林郎知浚縣事開原劉德新所書。從這塊碑能夠看出,作者看到浮丘山香火過于旺盛,而大伾山人跡寥寥,覺得陰陽不能協調,因此要在大伾山建造呂祖祠,吸引香眾,來遏制浮丘山的碧霞元君信仰的發展。而作者本身是儒生出身,對于鬼神之說并不篤信,在選擇供奉的神仙上就能看出,選擇了和儒家有密切關系的呂洞賓,并指出呂洞賓是唐代的進士,在成仙之前也是儒生,較為隱晦地宣傳和抬高了儒家的地位,而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吸引香客到大伾山祭祀,而這一行為被動地使得浚縣廟會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從呂祖祠內的很多香客朝山的碑刻就能看出,這座道觀落成之后,確實香火旺盛,甚至延續至今,縣令劉德新也是不遺余力地宣傳大伾山,大伾山上現存的劉德新的題字遍布各個角落。時至今日,浚縣廟會的朝山活動還是正月初九上大伾山,正月十六上浮丘山。而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仁育萬物碑》⑤則是通過另一種方式對廟會活動加以改造和解釋:“……德思以善鼓一方之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幾幾乎聚居而成邑矣。思先王以神道設教,約鄉人虔奉三仙圣母,會朝浚邑浮丘山進香焉……會始于康熙肆拾肆年,唱者數人,和者百余人。善男信女不介自孚,如候鳥之依于長,如葛藟之依于木。于今三年矣……眾歸功于會首,曰:‘眾善始于一人也。’而玉侯王君愕然曰:‘人性皆善,啟眾者予,啟予者誰耶?非神耶?是不可不有以志神之功、彰神之靈以明人之誠焉。’因乞吉于予,予曰:‘人耶,神耶?知之者人也,不知者神也,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人之至,神之至也。’是誠不可不志之以為后來者勸。”這塊《仁育萬物碑》更多地贊揚了香會中會首的教化作用,認為人宣揚教化、組織香會的過程本身也是功德無量的,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會社會首的分量,并賦予了會首更多的義務,使得香會中會員關于會首的競爭更加激烈,會首的當選條件也更為苛刻。從朝山進香的碑刻中可以看出,自順治年間之后,幾乎沒有女性會首,會首多為當地德高望重的鄉紳或官員家屬。
三、經濟促動:寺觀與鄉民的利益訴求
在廟會這一場域中,擁有資本和權力的一方不僅會引導和把控,也需要對既得利益進行保護。《清康熙五十二年告示》⑥中明確說如果有人前來搗亂,允許到官府說明,官府將“立拿重處,決不寬宥”,用行政手段保證寺廟和香眾利益。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的嚴禁作踐廟宇告示牌也明確說,在廟會活動期間,禁止商販在廟宇內強搭鋪面,如有違反,嚴懲不貸。在廟會活動中不僅有罰還會有賞,用一定的獎勵制度來鼓勵這種民間的廟會活動。在浚縣,民間的香會會以自然村或家族為單位參加廟會活動,并自發排演祭祀時用來娛神的歌舞活動。清朝當地政府為鼓勵這樣的民間文藝活動,還會制作并頒發銀牌給表現優秀的會社,使得各個會社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競爭的關系,從而使民間參與廟會活動的熱情更加高漲。如現在浚縣衛溪社區順河街道張和平一家就珍藏有清代縣令陶珙賞賜給順河街道花船圣會的葫蘆形銀質獎牌三面,獎牌上“正堂陶”和“賞”字可清晰看到。在廟會這一場域中,存在著多方資本的斗爭,宗教之間的斗爭、儒生與宗教的斗爭、商人與政府的斗爭等。各方都希望能夠把控廟會這一資本,這種資本斗爭被動地促進了廟會的繁榮與發展。而對于普通鄉民來說,則是希望在廟會活動中,通過向神祇祈禱,獲得諸如平安、求子等心愿的滿足。這種行為本身是符合普通群眾的需要的,因此廟會香火的繁盛程度對于普通香眾來說更容易獲得認同感和滿足感,同時也會讓大家覺得寺廟中的神仙確實很靈驗。
對于寺廟本身來說,廟會活動也會擴大寺廟的影響力,香火的多寡直接影響到的是寺廟的利益,因此寺廟本身也會維持一定的秩序,比如禁止一些影響到進香安全的活動出現,禁止一些商業活動影響到進香的秩序,更不允許搗亂的人前來破壞。其中有些并不是寺廟本身可以執行的,需要通過官方的渠道進行,因此康熙和嘉慶年間的告示通知碑刻就出現了這樣的官府行為,這一行為本身也是在宣示政府的管理和引導作用,對場域中的既得利益方進行維護。同時廟會行為也需要對事物或活動進行選擇,即優勝劣汰,這是一個殘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摒棄一些不符合社會主流思想或者資本需求的活動,廟會行為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進化,最終形成如今我們能夠看到的廟會活動。
四、習俗傳衍:香會與會首的信仰傳達
浚縣古廟會在浚縣當地傳承了數百年乃至上千年(具體出現時間尚無定論),若僅僅將其歸類為信仰的強大體現則未免過于牽強。在廟會的傳承中,習性和習俗的傳衍起到了關鍵作用。如果將場域這一概念看作一個游戲的話,資本無疑是這個游戲規則的制定一方,而習性則是這個游戲能夠進行下去的重要保障。人們會在得到游戲體驗后獲得參與的能力,其對于游戲的理解和對規則的遵守就形成了習性。習性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使其更加符合自身行為邏輯,而民間廟會活動繁榮興盛并活躍至今,習性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早在先秦時期,中國就已經出現了類似于廟會形式的活動。《禮記·雜記下》就有記載:“子貢觀于蠟,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其中的“臘”就是指臘祭,是古代的一種祭祀活動,從對話中就能看出,這種祭祀活動具有很強的全民娛樂屬性,而子貢本身就是衛國(今河南省鶴壁市浚縣)人。時至西漢,《鹽鐵論》中就有了關于“朝山”的記載:“古者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岳,忘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而《通俗編》中,直接指出“俗于遠處進香謂之朝山,據文,則此俗之興,由于西漢”。之后的數千年中,這種活動都不曾消失,只是在不斷地變化。
明清時期的民間香社空前壯大,是民間參與廟會活動的主要力量,浚縣眾多廟宇中的碑刻也記載了當時的盛況,并從側面反映了當時民眾參與廟會活動已經成為一種習性,這種習性是以線性方式存在的,更多的是通過時間線來反映習性的產生。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常香會善信題名碑記》⑦云:“浚縣南關內韓應龍母姓林氏者,性秉懿微,樂蠲好善,約閨閫淑媛二百余眾,于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神廟點常香會,繼十余年而未有已也……”由碑文內容就可以看出,有能力的廟會參與者會帶動更多的人參與到廟會活動中來,如“韓應龍母林氏”這樣一個德行兼備的信眾就能夠帶領自己的朋友閨蜜二百余人參與到廟會活動中。這種“榜樣”的力量會產生一種巨大的慣性。時至今日,筆者在浚縣的采訪過程中,依然看到有很多周邊縣市的群眾和香會參與廟會活動,最遠的甚至是從北京專程趕來上香的,更多的則是游客來參觀這一民間盛會。當地很多參與廟會活動的人認為這樣的活動已經在當地延續了上百年,到現在不應該丟棄,并且參與廟會活動已經和當地的過年風俗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成為年內必須做的一項活動,這種習慣深入當地人的骨髓。在浚縣當地,不僅是廟會活動被相對完整地保留下來,各個大大小小的香會組織也都延續了下來,其內部的組織構成及文藝表演內容也都延續了明清時期的樣式。這一慣性“來源于社會結構,通過社會化,即通過個體生成過程(ontogenesis),在身體上體現,而社會結構本身,又來源于一代代人的歷史努力,即系統生成(phylogenesis)”⑧。清代乾隆二年(1737年)的《十王圣會四年完滿碑記》⑨更是體現了這一理論觀點:“……而邑東張耀祖一會,父子相承,祖孫相繼,已歷七十余載,其間苾芬歆香以饗以祠,其誠敬可謂至矣。前已立碑者二,今至周士儒、至張耀祖又四年完滿。會眾議立碑刻名以垂不朽,屬余作文以紀其事……”這說明這個香會是以宗族家族為單位的會社。在家族的傳承中,廟會活動也作為其重要一環傳承了下來,經過數代人的努力,形成了這樣的習性。
習性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使其更加符合行為主體自身的邏輯性或自身的利益。法國社會學家菲利普·柯爾庫夫認為:“稟性,也就是說以某種方式進行感知、感覺、行動和思考的傾向,這種傾向是每個個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觀條件和社會經歷而通常以無意識的方式內在化并納入自身的。持久的,這是因為即使這些享性在我們的經歷中可以改變,那它們也深深扎根在我們身上,并傾向于抗拒變化,這樣就在人的生命中顯示某種連續性。可轉移的,這是因為在某種經驗的過程中獲得的享性(例如家庭的經驗)在經驗的其他領域(例如職業)也會產生效果;這是人作為統一體的首要因素。最后,系統,這是因為這些享性傾向于在它們之間形成一致性。”⑩一個群體的習性的產生一定是和當時的社會情況、群體受教育程度、歷史文化的傳承密不可分,習性代表著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我們將考察某一習性的時間線拉長就不難看出,習性在浚縣的廟會活動中一直在發生著細微的變化,并最終由量變的積累引發質變。引起這些變化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社會原因,另一方面是資本對抗。廟會活動起源于早期祭祀活動,自漢代佛教傳入中國后形成了很多宗教祭祀的活動。在中國,宗教祭祀與民間祭祀是并存和共生的關系,到了唐代商業活動加入到祭祀活動中;而宋代則形成了相對發達和固定的廟市體系,祭祀活動與商業活動的聯系更加緊密。因此,廟會這一場域并非突然出現的,其本身就是習性的延續。依照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來分析,廟會是由于資本的介入而形成的場域,而資本之所以會介入也是習性作用的結果。而在民間祭祀活動中一直不斷地有新的資本介入,資本與資本之間形成了一種對抗的關系,這種對抗也使得習性在其中不斷發生變化。例如,明清時期香客朝山進香還有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立碑,浚縣浮丘、大伾兩山留存朝山進香的碑刻就有80余塊。最早記錄朝山進香的碑刻是明代嘉靖年間的《浮丘山岳神靈應記》,立碑人為“浚司訓謝載”。到明代天啟年間的《重修子孫祠碑記》,捐資和立碑人都是平民。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泰山圣母碧霞行宮供會四年圓滿記言碑》,立碑人為“會首王思艾妻李氏”。順治十三年《善信進香題名碑記》立碑人為“總領會首申養德母郭氏、會首鄧守信母楊氏、會首劉天就母王氏、會首李一成妻盧氏、會首李三秋母屠氏、會首李從云母毛氏”。從這些立碑人就可以看出,順治十三年以前的會首和立碑的人基本都是女性;時至順治十六年《碧霞元君行宮碑記》,立碑人為“駕主李尚春,妻張氏;男李蘭芳,妻李氏;次男李桂芳,妻孫氏;孫李進國,李進賢,李進忠”,此外還有部分捐資的官員名單,這塊碑的立碑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但基本是以男性為主;清順治十七年《浮頂進駕萬善碑記》則是幾家共同立碑,立碑人除一些官員外,還有上文提到的“駕主李尚春”,但這塊碑記中已經沒有女性出現了;之后的碧霞宮朝山進香的碑刻中僅4塊中出現了女性。從這些立碑人的身份及性別變化就可以看出習性的變化,浚縣早期的廟會活動很可能是由官員主導的,隨后參與的人員以女性為主,畢竟從神祇的職能上來說,碧霞元君主要是負責送子和保平安的。康熙年間之后則是以男性為主導,神的功能也愈加強大,上文中提到的清康熙四十七年《仁育萬物碑》也為男性知識分子參與廟會活動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撐,使得能夠參與廟會活動的人群范圍更為廣泛。時至今日,廟會活動已經不僅僅是一種信仰或觀念的傳達,甚至脫離了信仰傳承的范疇,更多的是在慣性的作用下在當地形成了一種風俗習慣,這種風俗習慣將進一步與市場和新的觀念相融合并不斷延續下去。
五、結語
在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中,資本、習性和場的概念是要聯系起來分析的,在分析廟會這一獨立場域的時候也是一樣的。廟會活動中的場,不僅僅指的是空間和地理的場所,更多的是指民間信仰和傳統文化,所謂習性正是由民間信仰和文化創造出來的,包含了深刻的歷史印記,外部的資本介入才使得這一習性形成相對獨立的一個場域,而資本在介入的過程中本身也會經過習性的改造。可以說,資本本身就是習性的產物,資本的介入使得場域中充滿斗爭性,讓這一場域本身充滿力量,并在斗爭中不斷優化和改良,使這個場域更加符合一定的內在邏輯性,這樣才能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被破壞并延續至今。用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來分析廟會這一場域,我們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浚縣古廟會是如何在歷史發展中一直得以延續的,在了解之后我們也更加容易得知現在應該如何去保護古廟會這一優秀的民間文化內容。
注釋:
①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論》,李康、李猛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171頁。
②《重修碧霞元君行宮記》,此碑位于浚縣浮丘山碧霞宮前院東側,雕龍碑首,赑屃碑座,高380厘米,厚21厘米,楷書。
③《浮頂進駕萬善碑記》,此碑位于浚縣浮丘山碧霞宮前院西側,高266厘米,寬88厘米,厚84厘米,楷書。
④《創建純陽呂帝君洞閣碑記》,此碑位于浚縣大伾山呂祖祠乾元殿前,雕龍首,赑屃碑座,高207厘米,寬79厘米,厚22厘米,楷書。
⑤《仁育萬物碑》,此碑位于浚縣浮丘山碧霞宮中院東廊前,高235厘米,寬86.5厘米,厚23.5厘米,楷書。
⑥《清康熙五十二年告示》,此碑位于浚縣浮丘山寢宮樓前西配樓內,高122厘米,寬73厘米,楷書。
⑦《常香會善信題名碑記》,此碑位于浚縣浮丘山碧霞宮中院東廊前,高214厘米,寬71.5厘米,厚24厘米,楷書。
⑧皮埃爾·布迪厄,漢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裕芳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84頁。
⑨《十王圣會四年完滿碑記》,此碑位于浚縣浮丘山碧霞宮中院東廊前,高97厘米,寬127厘米,厚19厘米,楷書。
⑩菲利普·柯爾庫夫:《新社會學》,錢翰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