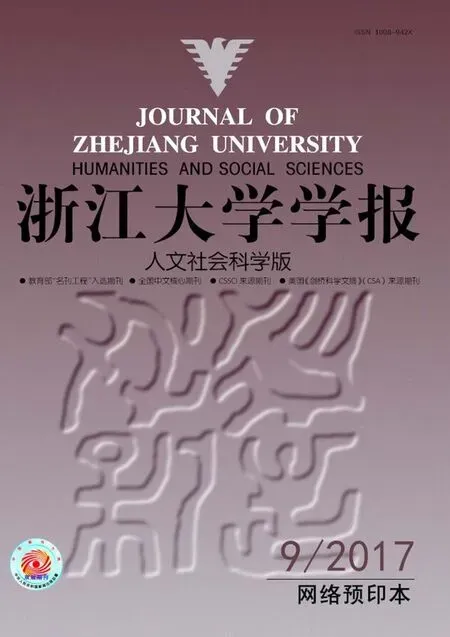基于組織間學習的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機理
——來自企業的實證研究
陳艾華 鄒曉東
(1.嘉興學院 商學院, 浙江 嘉興 314001; 2.浙江大學 科教發展戰略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58; 3.浙江大學 中國科教戰略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一、 問題的提出
合作網絡的日益拓展與團隊優勢的愈益突顯,表明合作對創新思想的形成和工作績效的提升具有關鍵作用[1]。作為合作的一種創新形式,產學研合作因其深遠影響而受到廣泛關注[2-3]。國內外學者從宏觀的創新系統理論、中觀的三重螺旋理論和微觀的開放式創新理論等不同視角,闡述了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對創新績效提升的重要性。盡管已有學者基于知識流動構建了產學研協同創新過程的理論框架[4],然而,產學研異質性組織間的知識共享對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機理尚不明確。
從資源觀視角而言,企業進行產學研協同創新可以整合外部公共知識以彌補內部的知識落差[5],獲得較稀缺的研究人員或高水準的研究設備,有效實現各類創新資源的突破和融合[6]。然而,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只是為企業提供了利用和整合外部知識資源的機會,組織間知識壁壘的存在容易導致沖突和不協調[7],可能會限制互補效應的發揮[8]。
從交易成本視角而言,企業參與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獲得知識溢出效益,降低研發成本[9]。但是,產學研歷來缺乏溝通[10],一些企業的吸收能力有待提高,且高校和研究機構的諸多科研成果聚焦于知識生產與知識積聚,市場導向性不強,從而導致技術需求與技術供給錯位,反而提高了企業知識交易成本[11]。此外,知識與信息由于具有公共產品特性,易出現“搭便車”現象,難以規避機會主義行為[12],從而影響企業創新績效。
如何推進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是學界探究的熱點問題,也是政府亟待破解的現實難題。學者們主要從資源觀視角和交易成本視角對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進行了詮釋,但一些研究結論還存在不確定性,甚至相互矛盾。同時,絕大多數的研究解釋皆基于理論演繹,實證研究相對匱乏[13],使其結論難以令人信服。不同的協同度,其知識鴻溝和知識粘性也存在差異,對產學研知識聯盟中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也各不相同[14]。目前,學界對基于組織間學習的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的廣度與深度鮮有研究。這些研究空白啟示著本文從組織間學習視角入手,基于企業實證分析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的內在機理。
二、 理論與假設
(一) 知識共享模式與創新績效
Hedlund提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在個人、團隊、組織及組織間進行互動與轉移[15]。Crossan等進一步對學習系統內各層次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指出戰略學習評價圖涵括個體層學習、群體層學習和組織層學習三個學習存量[16]。Albino等也指出參與知識轉移過程的轉移主體既可以是組織,也可以是個人[17]。根據不同的知識主體,知識可由個體傳遞給個體、組織傳遞給個體、組織傳遞給組織,以實現知識共享,達成企業提高效率和知識創新的目標[18]。知識尤其是隱性知識通過正式網絡很難進行有效傳遞,只有通過信賴而緊密的非正式網絡才能實現有效轉移,而聯盟各方在非正式網絡中緊密的個人接觸能促成組織中的知識轉移,特別是隱性知識的轉移[19]。原長弘等通過單案例研究發現,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使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得到提升[12]。Subramanian等認為,企業與高校在知識轉移上開展合作,在獲取各種創新資源的同時還能獲得新的科學知識和新發現[6]。曹霞、于娟指出,穩定的產學研聯盟通過協同互動,共同實現產學研協同創新的任務[20]。因此,企業通過產學研知識聯盟實現知識共享,從外部獲取滿足創新活動所需的知識以提升企業創新績效。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對知識共享模式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知識共享中的個體—個體模式對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2:知識共享中的組織—個體模式對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3:知識共享中的組織—組織模式對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二) 組織間學習與創新績效
組織間學習是組織學習的延伸,由于其通過知識共享而產生強大的協同效應,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受到學界的關注。但對組織間學習的內涵,目前學界還未達成共識。對組織間學習過程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兩大類:解決問題導向和處理信息導向。將組織間學習視為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程,即為解決問題導向[21];將組織間學習視為不斷地獲得知識或信息并加以應用而再創造的過程,即為處理信息導向[22-23]。基于處理信息導向視角,學者們對組織間學習過程進行了詮釋。Gomes-Casseres等指出,組織間學習的過程包括共享、轉移、吸收、整合、應用和創造知識,結成聯盟后有利于促進知識轉移,實現知識創造,達成知識創新[24]。Dyer和Singh認為組織間學習是在特定聯盟合作環境中獲取知識,并運用聯盟合作環境中的知識搜尋機制創造知識的行為[25]。鄭素麗等發現,知識的動態能力由知識獲取、知識創造和知識整合等要素構成[26]。朱學彥通過理論與實證研究發現,知識獲取與知識創造并列構成了組織間學習過程*參見朱學彥《基于嵌入性關系和組織間學習的產學知識聯盟研究》,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這與Nielsen等的觀點相吻合,即知識經由組織間學習進入聯盟企業后,會出現兩種可能性,即原封不動地成為累加的新知識或與已有知識互補融合后變異成創新性的新知識[27],不論何種情況,均能拓展聯盟企業的知識深度與寬度,使聯盟企業越有可能對環境變化做出迅速反應并獲取回報[28]。這一點也獲得了Teece的認同,即對企業的成功而言,從聯盟伙伴中學習和獲取知識的能力尤為關鍵[29]。本文綜合以上研究成果,并順承Dyer、Singh、朱學彥和Nielsen等的研究,認為知識的共享、轉移、吸收可以統稱為知識獲取,而知識整合與應用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創造知識,因此以知識獲取、知識創造并列表征組織間學習內涵。組織間學習強調合作主體間學習行為的聯結互動所產生的知識流動與知識創造,通過組織間學習,企業在產學研知識聯盟內可以獲取合作伙伴的知識資源,有助于建立新的知識體系以強化企業的競爭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對組織間學習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獲取對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5: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創造對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三) 知識共享模式與組織間學習
作為產學研知識聯盟中的個體,可以向組織搜索自己所需要的知識,即知識由組織向個體擴散,經內化后成為個體的專屬知識。專屬于產學研知識聯盟中個體的隱性知識通過個體之間的交流,盡管還未上升為組織知識,但為組織間學習即知識的獲取與創造提供了條件。林莉等指出,營造自由開放的氛圍可以促使聯盟各方的個體進行緊密接觸,進而使組織間信息和技能成功實現交換和轉移[19]。作為產學研知識聯盟,知識源的團隊與接受知識的團隊彼此共享知識,以實現優勢互補,提升各自的工作績效[30-31]。王飛絨等發現,知識從個體層流向群體層然后上升至組織層,在知識創造的螺旋過程中,個體與個體以及個體與組織間的交互作用能夠使企業內原有知識與聯盟知識碰撞,從而構建新知識[32]。Levin等指出,聯盟企業內部員工將獲取的外部知識與已有知識整合,從而使自身行為發生改變,便稱為有效的知識轉移,其最終目的是有效利用組織知識[33]。Krogh等進一步指出,有效的知識轉移不僅注重員工個體知識和行為的改變,更為重要的是注重聯盟企業組織知識和行為的改變[34]。通過知識共享,聯盟中的企業將所獲取的知識資源與已有的知識資源進行重新整合,以創造新知識,實現知識的溢出效應,形成企業特有的知識優勢[35]。寧燁等認為,組織知識應用與創新的效率取決于知識共享能力[36]。由此可見,知識共享模式有利于促進組織間學習。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對知識共享模式與組織間學習之間的關系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6:知識共享中的個體—個體模式對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獲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7:知識共享中的組織—個體模式對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獲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8:知識共享中的組織—組織模式對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獲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9:知識共享中的個體—個體模式對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創造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10:知識共享中的組織—個體模式對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創造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11:知識共享中的組織—組織模式對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創造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通過文獻梳理與理論分析,本文逐一剖析了知識共享模式、組織間學習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提出了11個假設,構建了如下初始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基于組織間學習的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機理初始概念模型
三、 研究過程
(一) 變量測量與樣本收集
基于文獻研究、專家意見和實地調研,本文分別對各變量包括知識共享模式(解釋變量)、組織間學習(中介變量)、創新績效(被解釋變量)采用多個題項進行度量。為了保證測量工具中指標設置和表述的合理性,隨機抽取6家企業對調查問卷在小范圍內進行了前測,基于反饋和建議對調查問卷進行了修改與完善,形成了最終的調查問卷。
2.解釋變量:知識共享模式(KS)。借鑒Horwitz等[39]以及Fritsch[40]和Bock等[41]學者的觀點,結合深度訪談和實地調研,本文采用以下9個題項度量知識共享模式:(1)本人可以與合作中的他人共享工作經驗;(2)本人可以與合作中的他人共享技術訣竅;(3)本人可以與合作中的他人共享業務報告和建議書、工作手冊、流程和模型;(4)本企業可以與合作中的他人共享工作經驗;(5)本企業可以與合作中的他人共享技術訣竅;(6)本企業可以與合作中的他人共享業務報告和建議書、工作手冊、流程和模型;(7)本企業可以與合作中的組織共享工作經驗;(8)本企業可以與合作中的組織共享技術訣竅;(9)本企業可以與合作中的組織共享業務報告和建議書、工作手冊、流程和模型。
3.中介變量:組織間學習(IOL)。借鑒Lane等[42]、張方華[43]、Woodman等[44]學者的觀點,結合實地調研,本文采用以下6個題項度量組織間學習情況:(1)獲得更多關于新技術的知識;(2)獲得更多關于新原材料的知識;(3)獲得更多關于新市場機會的知識;(4)創造更多有關工藝創新的知識;(5)創造更多有關產品創新的知識;(6)創造更多有關研發流程優化的知識。
盡管企業年齡(Age)、企業所屬行業(Ind)等不是本文研究的焦點,但鑒于其可能會對企業的創新績效產生顯著影響,因此本文選擇企業年齡、企業所屬行業等作為控制變量。發放問卷共計489份,在回收的363份反饋問卷中剔除因各種原因產生的不合格問卷37份后,獲得有效問卷326份,問卷總有效率為66.67%。
(二) 數據分析和處理
本文對理論模型的構建和測量工具的選擇建立在大量文獻研究基礎之上,并基于專家意見、實地調研和預測試情況修正測量工具,這使本文的總體研究結構、變量測度及數據獲取的信度與效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證。為進一步檢驗研究結果的可信度與說服力,本文還對研究變量的測度是否達到信度與效度的要求進行了具體分析。
如表1所示,各變量Cronbach’s Alpha系數值均大于0.7,因此信度符合要求。如表2和表3所示,由KMO檢驗和巴特利球體檢驗可知,樣本數據的KMO均大于0.7,因子值的顯著性水平均為0.000,小于0.001,各因子各自的測度題項的負載系數均大于0.5,且累積解釋率均大于50%,表明各變量所選取的因子效度符合要求。

表1 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數

表2 樣本數據的KMO和Bartlett’s檢驗
本文采用經過了最大方差正交旋轉(Varimax)的因子分析結果值進行相關分析,因此各自變量之間、各中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不顯著,主要變量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見表4。知識共享模式與創新績效之間存在非常顯著或極顯著的正向關系;組織間學習與創新績效之間存在極顯著的正向關系;個體—個體模式與知識創造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與知識獲取之間存在極顯著的正向關系,組織—組織模式與知識創造之間存在不顯著的負向關系,與知識獲取之間存在非常顯著的正向關系;組織—個體模式與知識創造和知識獲取之間均存在極顯著的正向關系。后文將建立回歸模型,對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更為精確的驗證。
以低年級為例,繪本閱讀要講究圖畫和文字的相得益彰,光看圖畫或者光看文字都是片面的,還要學會汲取其他信息,如看封面、扉頁、作者、出版社、圖畫中隱藏的標志以及書中作者要表達的情感。中年級,為了提高閱讀速度,可以用手指著讀,但手指的速度要比眼的速度快;對于書中人物眾多的書籍,可以利用圖表或者思維導圖進行梳理,并摘錄關鍵詞,幫助理解;“我手畫我心”,將書中最愛的畫面通過想象畫出來展示。高年級的讀書交流會每月兩次,展示批注與心得,并募集學生主持讀書交流會,大家暢所欲言,品評人物……
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本文對所有回歸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序列相關和異方差等問題進行了檢驗。本文所有回歸模型的容許度值和方差膨脹因子值都近似等于1,說明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所有模型中DW值均接近于2,表明不存在不同編號樣本值之間的序列相關問題;所有的標準化殘差的散點圖均呈現無序狀態,表明本文中的回歸模型均不存在異方差問題。

表3 因子載荷及因子分析方差解釋

續表3

表4 主要變量相關系數
注:*、**、***分別表示在5%、1%和0.1%的水平上顯著,下同。
(三) 直接效應與中介效應檢驗
本文以組織間學習為被解釋變量,采用強制回歸法對知識共享模式進行回歸,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進行模型估計。回歸結果見表5和表6。

表5 知識共享模式對知識獲取的回歸分析結果
注: Constant表示常數,下同。
由表5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企業年齡、企業所屬行業等統計特征變量之后,知識共享模式對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獲取有極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結果支持假設6、假設7與假設8。對R2(0.316)和調整后的R2(0.306)的考察表明,該模型的解釋力較好,模型的統計結果(F=29.616,p<0.001)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表6 知識共享模式對知識創造的回歸分析結果
由表6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企業年齡、企業所屬行業等統計特征變量之后,知識共享模式中個體—個體模式、組織—個體模式對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創造有顯著或極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結果支持假設9與假設10;組織—組織模式對知識創造有不顯著的負向影響,研究結果拒絕假設11。對R2(0.107)和調整后的R2(0.093)的考察表明,該模型的解釋力尚可,模型的統計結果(F=7.632,p<0.001)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本文以企業創新績效為被解釋變量,采用強制回歸法對知識共享模式、組織間學習進行回歸,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進行模型估計(結果見表7)。由表7可以看出,模型2中,在控制了企業年齡、企業所屬行業等統計特征變量之后,知識共享模式對企業創新績效的正向影響極顯著或非常顯著,研究結果支持假設1、假設2與假設3。在模型3中,組織間學習對企業創新績效有極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結果支持假設4、假設5;個體—個體模式對創新績效的影響非常顯著(模型3中個體—個體模式對創新績效的標準化回歸系數為0.111,小于模型2中個體—個體模式對創新績效的標準化回歸系數0.432),組織—個體模式、組織—組織模式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不顯著,說明知識共享模式中個體—個體模式通過組織間學習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中介效應部分成立,組織—個體模式通過組織間學習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中介效應完全成立,而組織—組織模式通過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獲取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中介效應完全成立。對R2(0.652)和調整后的R2(0.644)的考察表明,該模型的解釋力較好,模型的統計結果(F=85.172,p<0.001)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表7 知識共享模式、組織間學習對創新績效的回歸分析結果

續表7
綜上,知識共享模式對產學研知識聯盟企業創新績效的直接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圖2所示。

圖2 知識共享模式對企業創新績效的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四、 討論與結論
(一)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文從企業層面出發,對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機理進行了探索,研究結果僅部分驗證了知識共享模式對組織間學習的促進作用以及兩者共同對創新績效產生影響的過程。
1.知識共享模式包括個體—個體模式、組織—個體模式、組織—組織模式。其中,個體—個體模式及組織—個體模式對企業創新績效有極顯著的正向影響,而組織—組織模式對企業創新績效有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產學研知識聯盟企業通過知識共享可以提升創新績效,雖然知識管理領域的學者對此已達成共識,但鮮有相應的實證研究文獻對知識共享模式進行分類,并實證驗證知識共享的不同模式對聯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本文通過對326份有效問卷的分析發現,在知識共享模式中,個體—個體模式對聯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力路徑系數為0.432(t=9.239),組織—個體模式對聯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力路徑系數為0.303(t=6.468),而組織—組織模式對聯盟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力路徑系數為0.144(t=3.049),由此實證檢驗了知識共享的不同模式對創新績效顯著的正向促進程度,補充完善了現有研究。
2.組織間學習包括知識獲取與知識創造,對企業創新績效有極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也是組織間學習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受到學界關注的原因,同時,這一研究結論也為日益發展的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實踐提供了理論支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知識共享模式中的個體—個體模式及組織—個體模式對組織間學習分別有顯著和極顯著的正向影響,但知識共享中的組織—組織模式對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創造有負向影響,雖然這種負向影響并不顯著,但其原因值得深究。基于資源觀與交易成本視角,形成產學研知識聯盟只是為組織間提供了獲取外部知識的機會,能否利用這些機會進行知識創造還取決于參與各方的文化認同[30]、溝通機制、利益機制、吸收能力[35]以及合作生態環境[5]等的協同作用,而個體—個體模式及組織—個體模式由于其具有較強的靈活性,可能受上述因素的影響較小,因此更易獲取與創造知識。這一研究結果不僅探明了以往關于產學研協同創新研究結論產生分歧的根源,而且也豐富和深化了知識共享、組織間學習理論的相關研究。
3.知識共享模式中個體—個體模式通過組織間學習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中介效應部分成立,組織—個體模式通過組織間學習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中介效應完全成立,組織—組織模式通過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獲取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中介效應完全成立。產學研知識聯盟中各知識轉移主體之間的知識勢差及利益互補構成了知識轉移的自然推動力和社會基礎,有利于參與各方獲取有助于自身發展的知識,形成驅動演化發展的知識創造機制,實現提升創新績效的目標。然而,該研究結論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目前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缺乏廣度與深度,未能從知識共享中的組織—組織模式這一廣度上通過知識創造這一相對較深層次的方式提升企業的創新績效水平。
(二) 理論貢獻與實踐啟示
本文的理論貢獻在于:第一,已有研究大多理論闡釋知識共享對創新績效的作用,鮮有研究從知識共享的不同模式實證驗證其對創新績效的影響,而本文基于理論探討,實證檢驗了知識共享的不同模式對創新績效的促進程度,彌補了現有研究的不足。第二,借鑒組織間學習直接作用于創新績效的研究思路,驗證了組織間學習在知識共享模式與創新績效之間的中介作用。研究結論既揭示了以往關于產學研協同創新研究結論產生爭論的本質,也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知識共享、組織間學習的理論發展。第三,構建和驗證了“知識共享模式—組織間學習—創新績效”的概念框架,揭示了提升創新績效的路徑,也反映出目前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的深度與廣度,有助于指導實踐。
本文為產學研知識聯盟企業協同創新實踐提供了以下重要啟示:首先,研究表明,知識共享有利于促進創新績效。因此,產學研知識聯盟企業應營造一種分享、交流、拓展知識的氛圍,有效利用產學研知識聯盟伙伴互補性的優勢知識資源,實現企業內部知識與“知識源”知識的有機融合。其次,研究顯示,組織間學習對創新績效存在正向影響。因此,組織間學習應成為產學研知識聯盟企業的戰略重點,企業應根據自身的能力和知識庫主動建立跨組織的學習團隊,積極設定學習目標與策略,在企業中構建起組織間學習的長效機制。最后,知識共享模式中的組織—組織模式對組織間學習中的知識創造的負效應表明,產學研知識聯盟企業應避免因過度強調資源柔性所導致的組織惰性和知識資源剛性化,從而削弱產學研知識聯盟企業學習外部新知識的意愿,阻礙其創造知識;同時,產學研知識聯盟企業應擴展知識寬度與深度,強化能力柔性,縮減對機會識別及環境變化反應的時間與成本,從而有效實現創造知識的目標。
(三) 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文借鑒已有相關研究對基于組織間學習的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機理進行了嘗試性的分析,但由于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機理現象較復雜,要全面對其進行把握并非易事。雖然通過此次研究獲得了一些較為重要的結論,但尚存諸多不足,這些局限性或可成為后續研究的深入之處。首先,本文采用7點量表,運用主觀評分的方法對知識共享模式、組織間學習、創新績效等變量進行度量,盡管變量的測度通過了信度與效度檢驗,但難以避免主觀性所帶來的測量偏差,從而影響研究結果。如有客觀數據支撐,可以進一步提高研究效度和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其次,本文僅從企業視角對基于組織間學習的產學研知識聯盟協同創新機理進行了研究,研究樣本較為單一,難以對企業、高校、研究機構等進行比較分析,未來的研究可以在這一方面深入挖掘。另外,由于本文重點關注知識共享模式、組織間學習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對企業的其他因素如企業文化、社會資本等未充分考慮,后續研究可以考慮在現有研究模型中加入上述因素,以使研究結論更具普適性。
[1] S.Wuchty, B.F.Jones & B.Uzzi,″The Increasing Dominance of Teams in Production of Knowledge,″Science, Vol.5827, No.316(2007), pp.1036-1039.
[2] H.Etzkowitz & L.Leydesdorff,″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ResearchPolicy, Vol.29, No.2(2000), pp.109-123.
[3] 陳鈺芬、陳勁: 《開放式創新促進創新績效的機理研究》,《科研管理》2009年第4期,第1-9, 28頁。[Chen Yufen & Chen Jin,″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Open Innovation Promoting Innovative Performance,″ScienceResearchManagement, No.4(2009), pp.1-9, 28.]
[4] 涂振洲、顧新: 《基于知識流動的產學研協同創新過程研究》,《科學學研究》2013年第9期,第1381-1390頁。[Tu Zhenzhou & Gu Xin,″Study on Process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ased on Knowledge Flow,″StudiesinScienceofScience, No.9(2013), pp.1381-1390.]
[5] 何郁冰: 《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理論模式》,《科學學研究》2012年第2期,第165-174頁。[He Yubing,″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I-U-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StudiesinScienceofScience, No.2(2012), pp.165-174.]
[6] A.M.Subramanian, K.Lim & P.H.Soh,″When Birds of a Feather Don’t Flock Together: Different Scientists and the Roles They Play in Biotech R&D Alliances,″ResearchPolicy, Vol.42, No.3(2013), pp.595-612.
[7] Y.Aharoni & D.M.Brock,″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Loc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JournalofInternationalManagement, Vol.16, No.1(2010), pp.5-15.
[8] 許春: 《中國大學專利、技術轉移與企業創新——基于累積創新視角》,《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3年第12期,第78-86頁。[Xu Chun,″Universities’ Patent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Firms’ Innov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Accumulation Innovation,″ScienceofScienceandManagementofS.&T., No.12(2013), pp.78-86.]
[9] B.Y.Eom & K.Lee,″Determinants of Industry-Academy Linkages and, Their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Korea as a Latecomer in Knowledge Industrialization,″ResearchPolicy, Vol.39, No.5(2010), pp.625-639.
[10] W.Wu & Y.Zhou,″The Third Mission Stalled? Universities in Chin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TheJournalofTechnologyTransfer, Vol.37, No.6(2012), pp.812-827.
[11] 朱桂龍、張藝、陳凱華: 《產學研合作國際研究的演化》,《科學學研究》2015年第11期,第1669-1686頁。[Zhu Guilong, Zhang Yi & Chen Kaihua,″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StudiesinScienceofScience, No.11(2015), pp.1669-1686.]
[12] 原長弘、章芬、姚建軍等: 《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與企業競爭力提升》,《科研管理》2015年第12期,第1-8頁。[Yuan Changhong, Zhang Fen & Yao Jianjun et al.,″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GIURU and Firm Competitiveness Improvement,″ScienceResearchManagement, No.12(2015), pp.1-8.]
[13] 程芬、郭瑾、梁喜: 《產學研聯盟知識轉移研究述評與展望》,《科技進步與對策》2016年第11期,第157-160頁。[Cheng Fen, Guo Jin & Liang Xi,″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University-Industry Alliance Knowledge Transfer,″Science&TechnologyProgressandPolicy, No.11(2016), pp.157-160.]
[14] Y.Wang & L.Lu,″Knowledge Transfer through Effective University-Industry Interactions: Empirical Experiences from China,″JournalofTechnologyManagementinChina, Vol.2, No.2(2007), pp.119-133.
[15] G.Hedlund,″A Mode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he N-form Corporation,″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 Vol.15, No.S2(1994), pp.73-90.
[16] M.M.Crossan, H.W.Lane & R.E.White,″A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ramework: From Intuition to Institution,″The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Vol.24, No.3(1999), pp.522-537.
[17] V.Albino, A.C.Garavelli & G.Schiuma,″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ter-firm Relationships in Industrial District: The Role of the Leader Firm,″Technovation, Vol.1, No.19(1998), pp.53-63.
[18] 魏江、王艷: 《企業內部知識共享模式研究》,《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04年第1期,第68-69頁。[Wei Jiang & Wang Yan,″Study on the Modes of Knowledge Sharing in Enterprises,″Technoeconomics&ManagementResearch, No.1(2004), pp.68-69.]
[19] 林莉、鄭旭、葛繼平: 《產學研聯盟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及促進機制研究》2009年第5期,第39-43頁。[Lin Li, Zheng Xu & Ge Jiping,″Study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Knowledge Transfer in Industry-University-Institute Alliance and Its Promotion Mechanism,″Forum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 No.5(2009), pp.39-43.]
[20] 曹霞、于娟: 《聯盟伙伴視角下產學研聯盟穩定性提升路徑——理論框架與實證分析》,《科學學研究》2016年第10期,第1522-1531頁。[Cao Xia & Yu Juan,″The Upgrading Paths of Stability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Alliance from the View of Alliance Partner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Analysis,″StudiesinScienceofScience, No.10(2016), pp.1522-1531.]
[21] S.H.Haeckel & R.A.Nolan,″Managing by Wire,″HarvardBusinessReview, Vol.71, No.5(1993), pp.122-132.
[22] J.M.Sinkula,″Marke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ournalofMarketing, Vol.58, No.1(1994), pp.35-45.
[23] S.F.Slater & J.C.Narver,″Market Orientation and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JournalofMarketing, Vol.59, No.3(1995), pp.63-74.
[24] B.Gomes-Casseres, J.Hagedoorn & A.B.Jaffe,″Do Alliances Promote Knowledge Flow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 Vol.80, No.1(2006), pp.5-33.
[25] J.H.Dyer & H.Singh,″The Relational View: Cooperative Strategy and Sourc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The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Vol.23, No.4(1998), pp.660-679.
[26] 鄭素麗、章威、吳曉波: 《基于知識的動態能力:理論與實證》,《科學學研究》2010年第3期,第405-411, 466頁。[Zheng Suli, Zhang Wei & Wu Xiaobo,″Knowledge-based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 and Empirical Study,″StudiesinScienceofScience, No.3(2010), pp.405-411, 466.]
[27] B.B.Nielsen & S.Nielsen,″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ole of Trust and Tacitness,″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 Vol.46, No.6(2009), pp.1031-1056.[28] 張紅兵: 《技術聯盟知識轉移有效性的差異來源研究——組織間學習和戰略柔性的視角》,《科學學研究》2013年第11期,第1687-1696,1707頁。[Zhang Hongbing,″What Makes the Knowledge Transfer Effectiveness Different in Technology Alliance: A Perspective from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StudiesinScienceofScience, No.11(2013), pp.1687-1696, 1707.]
[29] D.J.Teece,″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 Nature and Micro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 Vol.28, No.13(2007), pp.1319-1350.
[30] 張紹麗、于金龍: 《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文化協同過程及策略研究》,《科學學研究》2016年第4期,第624-629頁。[Zhang Shaoli & Yu Jinlong,″The Process and Strategy of Cultural Synergy i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Cooperative Innovation,″StudiesinScienceofScience, No.4(2016), pp.624-629.]
[31] E.G.Carayannis, J.Alexander & A.Ioannidis,″Leveraging Knowledge,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 Forming Strategic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GUI) R&D Partnerships in the US, Germany, and France,″Technovation, Vol.20, No.9(2000), pp.477-488.
[32] 王飛絨、池仁勇: 《基于組織間學習的技術聯盟與企業創新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以生物產業為例》,《研究與發展管理》2011年第3期,第1-9頁。[Wang Feirong & Chi Renyong,″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lliance and Enterprise’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aking Biotechnology Industry as An Example,″R&DManagement, No.3(2011), pp.1-9.]
[33] D.Z.Levin & R.Cross,″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You Can Tru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Trust in Effective Knowledge Transfer,″ManagementScience, Vol.50, No.11(2004), pp.1477-1490.
[34] G.von Krogh, I.Nonaka & M.Aben,″Making the Most of Your Company’s Knowledge: A Strategic Framework,″LongRangePlanning, Vol.34, No.4(2001), pp.421-439.
[35] 魏奇鋒、顧新: 《產學研知識聯盟的知識共享研究》,《科學管理研究》2011年第3期,第89-93頁。[Wei Qifeng & Gu Xin,″A Study on Knowledge Sharing i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Knowledge Alliance,″ScientificManagementResearch, No.3(2011), pp.89-93.]
[36] 寧燁、樊治平: 《知識能力的構成要素:一個實證研究》,《管理評論》2010年第12期,第96-103頁。[Ning Ye & Fan Zhiping,″An Empirical Study: Genes of Knowledge Capability,″ManagementReview, No.12(2010), pp.96-103.]
[37] R.G.Cooper,″New Products: The Factors that Drive Success,″InternationalMarketingReview, Vol.11, No.1(1994), pp.60-76.
[38] E.Brouwer & A.Kleinknecht,″Innovative Output, and a Firm’s Propensity to Patent: An Exploration of CIS Micro Data,″ResearchPolicy, Vol.28, No.6(1999), pp.615-624.
[39] S.K.Horwitz & I.B.Horwitz,″The Effects of Team Diversity on Team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eam Demography,″JournalofManagement, Vol.33, No.6(2007), pp.987-1015.
[40] M.Fritsch & G.Franke,″Innovation, Reg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R&D Cooperation,″ResearchPolicy, Vol.33, No.2(2004), pp.245-255.
[41] G.W.Bock, R.W.Zmud & Y.G.Kim et al.,″Behavioral Intention Formation in Knowledge Sharing: Examining the Roles of Extrinsic Motivators, Social-Psychological Forces,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MISQuarterly, Vol.29, No.1(2005), pp.87-111.
[42] P.J.Lane, J.E.Salk & M.A.Lyles,″Absorptive Capacity,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 Vol.22, No.12(2001), pp.1139-1161.
[43] 張方華: 《知識型企業的社會資本與知識獲取關系研究——基于BP神經網絡模型的實證分析》,《科學學研究》2006年第1期,第106-111頁。[Zhang Fanghua,″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Based Firm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StudiesinScienceofScience, No.1(2006), pp.106-111.]
[44] R.W.Woodman, J.E.Sawyer & R.W.Griffin,″Toward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The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Vol.18, No.2(1993), pp.293-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