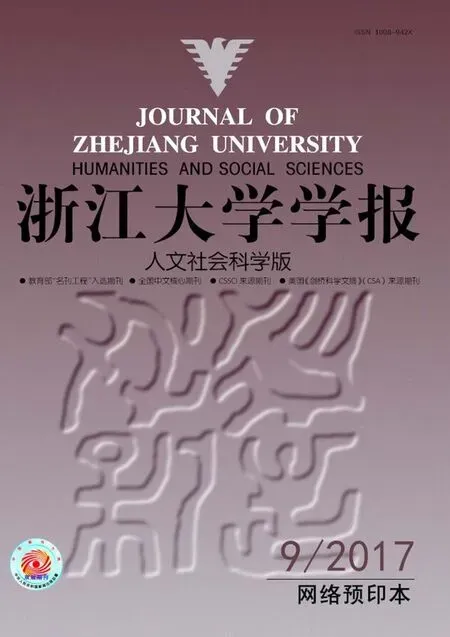基于食物安全層次性的耕地保護: 政府與市場的合理邊界
郭 珍 吳宇哲
(浙江大學(xué) 公共管理學(xué)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一、 引 言
為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中國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由中央政府分配耕地保護指標(biāo),在耕地保護上絕對集權(quán),地方政府與市場均沒有數(shù)量配置權(quán)。中央政府的絕對權(quán)威有利于對耕地數(shù)量進行有效保護,但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在執(zhí)行過程中卻出現(xiàn)了偏差,某些地方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fā),以耕地數(shù)量保護替代耕地質(zhì)量與生態(tài)保護,導(dǎo)致耕地質(zhì)量等級不高、污染嚴重,嚴重制約了糧食安全與食物安全的可持續(xù)性[1]。而且,隨著城鎮(zhèn)化、工業(yè)化的持續(xù)推進,現(xiàn)有耕地保護制度的執(zhí)行成本越來越高,耕地占補平衡的質(zhì)量以及生態(tài)平衡越來越難以實現(xiàn)。在新形勢下,選擇低經(jīng)濟社會代價的食物安全戰(zhàn)略與耕地保護制度安排有助于土地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實現(xiàn)糧食安全與食物安全的可持續(xù)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指出,經(jīng)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ān)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在耕地保護中,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對提高耕地保護制度的實施績效具有重要意義,有利于以低經(jīng)濟社會代價實現(xiàn)食物安全與新型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那么,耕地保護究竟是應(yīng)該將市場交易完全納入組織(政府),對耕地保護進行內(nèi)在化,即完全通過政府進行保護;還是應(yīng)該通過市場進行資源配置,抑或?qū)⒔M織(政府)的部分職能通過市場外在化,即政府利用市場進行資源配置?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哪里?何種制度安排組合會產(chǎn)生較高的績效?
在中國耕地保護制度實施績效不高的情況下,學(xué)者對政府與市場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中的邊界[2-3]以及集權(quán)與分權(quán)兩種治理模式在管理上的適用性進行了研究[4],但現(xiàn)有研究忽視了糧食安全與食物安全的生產(chǎn)和消費特性,較少考慮食物安全的層次性,在能夠確定何種制度安排組合會激勵較高而不是較低的績效之前,需要研究特定公益物品的生產(chǎn)和消費特性。對于任何公共服務(wù),都不存在唯一最優(yōu)的組織模式,其制度安排取決于物品的性質(zhì)[5]。食物安全可以劃分為不同的層次,而與此對應(yīng)的耕地保護的制度安排組合應(yīng)根據(jù)各層次食物安全的生產(chǎn)和消費特性來決定,并不存在唯一高績效的制度安排。市場和組織(政府)之間并非孰優(yōu)孰劣的問題,它們的優(yōu)勢和弱點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zhuǎn)化。不同層次的食物安全都有一個適當(dāng)規(guī)模的公共組織,在決定何種制度安排時,應(yīng)根據(jù)食物安全的生產(chǎn)和消費特性來考慮控制的標(biāo)準(zhǔn)和效率的標(biāo)準(zhǔn),為食物安全的生產(chǎn)和提供設(shè)計適當(dāng)?shù)摹鞍?組織規(guī)模)。換言之,應(yīng)根據(jù)不同層次的食物安全的生產(chǎn)和消費特性來決定其由政府提供還是市場提供,或由政府和市場合作提供,以及由哪一級政府提供。鑒于此,本文在對食物安全的層次及其生產(chǎn)、消費特性進行分析的基礎(chǔ)上,根據(jù)其各層次的物品性質(zhì),在控制與效率標(biāo)準(zhǔn)下界定耕地保護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研究集權(quán)與分權(quán)治理模式在耕地保護中的適用性,并從具體操作層面提出耕地保護的管理體制,以期為食物安全提供高績效的制度安排,從而實現(xiàn)耕地數(shù)量、質(zhì)量、生態(tài)“三位一體”保護,降低食物安全與耕地保護制度的實施成本。
二、 食物安全層次及其生產(chǎn)、消費特性
耕地保護最重要的目標(biāo)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與食物安全,在設(shè)計低經(jīng)濟社會代價的耕地保護制度安排時,應(yīng)先了解食物安全的層次性及其生產(chǎn)、消費特性。食物安全的第一層次是口糧安全,口糧包括稻谷和小麥;第二層次是谷物安全,谷物包括口糧、玉米及其他雜糧;第三層次是糧食安全,糧食包括谷物、豆類、薯類;第四層次是食物安全,即保證農(nóng)產(chǎn)品有效供給,除糧食外,食物還包括蔬菜、水果、動物產(chǎn)品等*本文食物安全的層次是狹義的,如第二層次谷物安全,在下文分析中所包含的意義是在口糧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保證玉米及其他雜糧的供給安全,以此類推。。下面具體分析食物安全各個層次的生產(chǎn)、消費特性及物品性質(zhì)。
(一) 口糧安全: 純公共物品
口糧產(chǎn)量由口糧播種面積與口糧單產(chǎn)決定,相對于1997年(口糧產(chǎn)量的一個歷史高點)而言,1997—2015年稻谷產(chǎn)量年均增長率為0.2%,小麥產(chǎn)量年均增長率為0.3%。口糧產(chǎn)量的提高主要來源于單產(chǎn)的提高,而單產(chǎn)提高的主因是技術(shù)進步,即對單位面積耕地投入大量的化肥、農(nóng)藥、農(nóng)膜,促使口糧供需達到緊張平衡[6]。由于種植口糧的耕地常年無休、過度利用,耕地質(zhì)量退化,耕地污染嚴重以及化肥、農(nóng)藥等過度施用所導(dǎo)致的邊際增產(chǎn)效應(yīng)不斷遞減,口糧單產(chǎn)的進一步提高受到明顯限制。口糧的國內(nèi)生產(chǎn)彈性小,且由于耕地污染,高質(zhì)量口糧的生產(chǎn)彈性更小*國內(nèi)市場上口糧供給量由當(dāng)年產(chǎn)量和庫存構(gòu)成,但如果生產(chǎn)量持續(xù)減少,庫存將難以持續(xù)提供人們所需的口糧,因此,本文分析國內(nèi)口糧的生產(chǎn)彈性,而不是供給彈性,下同。。而口糧作為人們生存的必需品,難以用其他產(chǎn)品替代,其需求彈性非常小,且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高質(zhì)量、無污染的口糧需求將進一步增加。同時,通過國際貿(mào)易保障口糧供給的風(fēng)險較大,口糧難以通過國際市場得到有效供給[7]。隨著中國人口高峰期的到來,為人們提供充足的、高質(zhì)量、無污染的口糧對國家的穩(wěn)定至關(guān)重要,口糧安全關(guān)系到人們的生存安全和國家穩(wěn)定,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因此,口糧安全必須通過國內(nèi)生產(chǎn)實現(xiàn)。口糧的國內(nèi)生產(chǎn)和消費特性決定了其純公共物品屬性,為了保證水稻、小麥兩大口糧100%自給,政府應(yīng)對生產(chǎn)口糧的耕地數(shù)量進行嚴格控制,保護好生產(chǎn)口糧的耕地的質(zhì)量與生態(tài)。
(二) 谷物安全: 公共物品
谷物除了口糧外,還包括玉米和其他雜糧,其中,其他雜糧的生產(chǎn)和消費量都較小,因此,這里主要分析玉米的生產(chǎn)、消費特性。1991年玉米產(chǎn)量為9 877.3萬噸,2015年達到22 458萬噸,玉米產(chǎn)量年均增長率達到3.48%,玉米占谷物的比重從1991年的22.69%上升到2015年的36.14%,中國谷物產(chǎn)量的增長主要來自玉米產(chǎn)量的增長[8]。但玉米單產(chǎn)增長不穩(wěn)定,起伏較大,受自然災(zāi)害等因素的影響較大。1991—2015年玉米產(chǎn)量的提高主要是因為播種面積的增加,1991年玉米播種面積為21 574千公頃,到2015年上升到38 116.6千公頃,年均增長率為2.40%。而在玉米播種面積提升的同時,稻谷、小麥的播種面積呈減少趨勢,因此,雖然國內(nèi)玉米的生產(chǎn)彈性較大,但更多的是通過占用播種稻谷、小麥的耕地來增加產(chǎn)量。玉米在我國主要是作為飼料用糧,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肉類等的需求將進一步增長,對玉米的消費需求也將進一步增長。南北半球在玉米收獲與供給上恰好互補,中國能從國際市場上以較低風(fēng)險購買玉米以彌補國內(nèi)玉米生產(chǎn)的不足,但玉米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國家的貧困人口中是作為主要口糧的,如果中國大規(guī)模進口玉米作為飼料用糧,那么可能對非洲、拉丁美洲貧困人口的口糧購買產(chǎn)生影響,使他們難以以較低價格購買到生存所需的食糧。為了避免這一問題,除了口糧外,中國對包括玉米在內(nèi)的谷物也應(yīng)基本自給,中國谷物基本自給能為其他國家的貧困人口帶來正外部性,具有公共物品性質(zhì)。由于中國玉米產(chǎn)量的提升主要依靠播種面積的增長,因此,保證一定數(shù)量的高質(zhì)量、無污染的耕地對谷物的基本自給具有重要意義。
(三) 糧食安全: 準(zhǔn)公共物品
糧食除了谷物外,還包括豆類、薯類,下面分析豆類與薯類的生產(chǎn)和消費特性。中國豆類產(chǎn)量從1991年的1 247.1萬噸上升到2015年的1 588萬噸,豆類產(chǎn)量年均增長率為1.01%。1991—2015年豆類單產(chǎn)平均值為110.14公斤/畝,年均增長率為1.16%;豆類播種面積從1991年的9 163千公頃下降到2015年的8 851.6千公頃。中國薯類產(chǎn)量從1991年的2 715.9萬噸上升到2015年的3 330.1萬噸,薯類產(chǎn)量年均增長率為0.85%,其中,1991—2015年薯類單產(chǎn)平均值為234.81公斤/畝,薯類播種面積從1991年的9 078千公頃下降到2015年的8 840千公頃。豆類與薯類的單產(chǎn)(特別是豆類)相對于谷物來說很低,從成本收益角度出發(fā),農(nóng)戶減少了豆類與薯類的種植,其國內(nèi)生產(chǎn)彈性較小。而從國際市場來看,豆類與薯類在南北半球的收獲與供給上恰好互補,國際市場供給彈性較大,從國際市場進口豆類、薯類的風(fēng)險較小。豆類主要作為油料及飼料用糧,有很多其他的替代品。薯類在市場上也有很多替代品。谷物以外的糧食,其國內(nèi)生產(chǎn)彈性小,國內(nèi)需求彈性大,而國際市場供給彈性較大,為了低成本地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谷物以外的糧食供給可以更加積極地利用國際市場。在保障谷物基本自給后,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耕地可以適當(dāng)?shù)赝ㄟ^市場進行配置。通過進口耕地密集型糧食如大豆等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減輕國內(nèi)資源環(huán)境壓力,通過國內(nèi)生產(chǎn)和國際市場供給來保障糧食安全。
(四) 食物安全: 私人物品
糧食的耕地約束性強,鑒于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總的來說,國內(nèi)生產(chǎn)彈性較小,需求彈性也較小,公共物品屬性較強。而食物除了糧食外,還包括蔬菜、水果、動物產(chǎn)品等。水果、動物產(chǎn)品以及部分蔬菜可以通過草地、林地、河海、湖泊、海洋等國土資源獲取,耕地約束性小,且中國的水面面積、草地、林地等資源較為豐富,其國內(nèi)生產(chǎn)彈性較大,可以根據(jù)市場需求較靈活地調(diào)整產(chǎn)量。由于食物種類多,能通過不同類型的土地進行生產(chǎn),國際市場上供給充足,國際市場供給彈性也較大。在滿足對糧食的需求后,人們對食物的需求彈性較大,當(dāng)某種食物短缺或價高時,可以用其他食物替代;或者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愿意為綠色、有機的農(nóng)產(chǎn)品付出較高的價格。由于國內(nèi)、國外生產(chǎn)彈性大,以及國內(nèi)需求彈性大,糧食之外的食物供給完全可以通過國內(nèi)市場和國際市場的調(diào)節(jié),不需要對其加以過多限制。因此,食物安全具有明顯的私人物品性質(zhì),可以通過市場的自發(fā)資源配置,形成與市場需求相適應(yīng)、與資源稟賦相匹配的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和區(qū)域布局,穩(wěn)步增強食物供給能力以保障食物安全[9]。
三、 控制與效率標(biāo)準(zhǔn)下的耕地保護: 政府與市場的合理邊界
根據(jù)食物安全的層次性及其生產(chǎn)、消費特性,在控制與效率標(biāo)準(zhǔn)下界定政府與市場的合理邊界,選擇最合適的耕地保護制度安排,以最小的經(jīng)濟社會代價實現(xiàn)耕地數(shù)量、質(zhì)量、生態(tài)“三位一體”保護,切實保障食物安全。耕地保護中政府與市場的合理邊界如圖1所示。

圖1 耕地保護中政府與市場的合理邊界* 本文耕地保護后一層次的分析是在前一層次得到有效保護的前提下通過適當(dāng)?shù)闹贫劝才艑崿F(xiàn)的,如糧食安全是在中央政府切實保護好永久基本農(nóng)田的情況下,在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制度下地方政府利用市場進行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轉(zhuǎn)移交易,確保耕地數(shù)量與質(zhì)量平衡以實現(xiàn)糧食安全。
(一) 保障口糧絕對安全、谷物基本自給的耕地: 嚴格控制下提高效率
口糧與谷物特別是口糧的需求彈性非常小,國內(nèi)與國外市場的供給彈性也非常小,確保口糧絕對安全與谷物基本自給具有明顯的公共物品性質(zhì),因此,需要對保障口糧與谷物安全的耕地進行嚴格控制。在原有的耕地保護制度安排中,中央政府實行基本農(nóng)田保護制度以保護一定數(shù)量的優(yōu)質(zhì)耕地。在基本農(nóng)田保護制度下,占用被劃入基本農(nóng)田保護區(qū)的耕地需通過中央政府的批準(zhǔn),中央政府批準(zhǔn)占用后,地方政府需補充劃入數(shù)量及質(zhì)量相當(dāng)?shù)幕巨r(nóng)田。在韋伯的理性組織理論下,中央政府是終極的權(quán)威,中央政府指揮下級政府來執(zhí)行基本農(nóng)田保護任務(wù),通過一體化的命令結(jié)構(gòu)對地方政府實施控制。在科層制組織中,中央政府在組織內(nèi)部進行層層控制,能有效解決委托—代理問題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實現(xiàn)基本農(nóng)田保護制度保護優(yōu)質(zhì)耕地的目標(biāo)。但在基本農(nóng)田保護制度的執(zhí)行過程中,中央政府的正式目標(biāo)在組織演化過程中被地方政府的目標(biāo)所替代。執(zhí)行過程是決策過程的繼續(xù),這意味著制度執(zhí)行者雖然被排斥在決策過程之外,但他們可以在執(zhí)行過程中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其上[10]。地方政府作為有限理性的經(jīng)濟人,在發(fā)展經(jīng)濟與保護耕地的雙重任務(wù)下,從自身利益出發(fā),更傾向于占用優(yōu)質(zhì)耕地以拉動經(jīng)濟快速增長。在基本農(nóng)田保護制度下,只要能得到中央政府占用基本農(nóng)田的許可,地方政府就取得了占用基本農(nóng)田的合法性[11]。在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時期,中央政府對耕地資源分配的最佳方案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中央政府采用“親密型”的干群關(guān)系管理模式以了解更多的信息,使決策更有針對性。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利用自身信息優(yōu)勢來促成對自己有利的決策,從而取得占用優(yōu)質(zhì)基本農(nóng)田的許可,獲得有利于自己的資源分配方案。雖然中央政府規(guī)定在占用基本農(nóng)田后,地方政府需補充劃入數(shù)量和質(zhì)量相當(dāng)?shù)幕巨r(nóng)田,但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及中央政府注意力分配的有限性,中央政府難以對占用與補充的基本農(nóng)田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進行有效監(jiān)督與控制。在補充基本農(nóng)田時,某些地方政府以次充好,基本農(nóng)田甚至上山入海。基本農(nóng)田質(zhì)量下降,可能會威脅口糧絕對安全與谷物基本自給。
口糧絕對安全與谷物基本自給需要對一定數(shù)量的優(yōu)質(zhì)耕地進行嚴格控制,保護好優(yōu)質(zhì)耕地的生態(tài),并減少中央政府協(xié)調(diào)、監(jiān)督成本以提高控制效率,因此,應(yīng)對現(xiàn)有基本農(nóng)田保護制度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改進。由于口糧絕對安全與谷物基本自給的公共物品屬性,與此相對應(yīng)的耕地保護應(yīng)由政府提供,而地方政府是集團中的個體,有自己的利益考慮,可能傾向于搭便車[12],在確保口糧絕對安全中難以形成一致的集體行動,在分權(quán)的、自發(fā)的過程中難以達到優(yōu)等水平,因此,與口糧安全和谷物基本自給相對應(yīng)的耕地應(yīng)由中央政府進行嚴格控制。但在原有的基本農(nóng)田保護制度下,地方政府通過“游說”使制度執(zhí)行偏離制度原有目標(biāo),在中國經(jīng)濟進入新常態(tài)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對資源分配的不確定性較低,因此,在耕地資源分配中,應(yīng)改原有的“親密型”干群關(guān)系管理模式為“疏遠型”干群關(guān)系管理模式,將優(yōu)質(zhì)、無污染的耕地劃入永久基本農(nóng)田保護區(qū)。永久基本農(nóng)田保護區(qū)內(nèi)的耕地嚴禁轉(zhuǎn)換,既不能轉(zhuǎn)換為建設(shè)用地,也不能轉(zhuǎn)換為其他農(nóng)用地,從而嚴格控制優(yōu)質(zhì)、無污染耕地。由于地方政府難以占用永久基本農(nóng)田,中央政府不需要對占用的基本農(nóng)田與補充的基本農(nóng)田的數(shù)量與質(zhì)量進行監(jiān)督,大大減少了協(xié)調(diào)、監(jiān)督成本,提高了控制效率。
(二) 保障糧食安全的耕地: 提高效率,有效控制
在保證口糧絕對安全與谷物基本自給后,糧食安全具有準(zhǔn)公共物品性質(zhì),因此在保護與糧食安全相對應(yīng)的耕地時,可以適當(dāng)利用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在原有制度安排中,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制度被用來保障糧食安全。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制度的執(zhí)行者同樣是地方政府,而監(jiān)督者是上級政府。與基本農(nóng)田保護制度相比,中央政府主要對省級政府的耕地保有量進行控制,對下級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度相對較弱。地方政府作為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制度的執(zhí)行者,面對兩種不同的環(huán)境:技術(shù)環(huán)境和制度環(huán)境。這兩種環(huán)境對地方政府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技術(shù)環(huán)境要求地方政府有效率,即按最大化原則組織生產(chǎn);而制度環(huán)境要求地方政府服從“合法性”機制[9]。在發(fā)展經(jīng)濟與保護耕地中,耕地是重要的資源,地方政府在效率機制下需要占用優(yōu)質(zhì)耕地,而合法性機制則要求地方政府保護耕地的數(shù)量與質(zhì)量,那么,地方政府的應(yīng)對策略是什么呢?在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制度中,雖然制度規(guī)定占用耕地與補充耕地的數(shù)量與質(zhì)量必須相等,但地方政府利用自有信息優(yōu)勢,補充的耕地往往質(zhì)量較差,甚至是邊際耕地,只是在數(shù)量上實現(xiàn)占補平衡。
地方政府的這一行為不利于對耕地質(zhì)量和生態(tài)的保護,中央政府也了解地方政府在制度執(zhí)行過程中的問題,對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制度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化,如規(guī)定“占用水田必須補充水田”等具體操作細則。由于不同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程度與耕地資源稟賦的不同,一些地方政府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上具有很大優(yōu)勢,但耕地資源稟賦較差,占用水田補充水田的成本高昂,且補充的水田產(chǎn)量很低;而另一些地方政府在發(fā)展工業(yè)及第三產(chǎn)業(yè)上的優(yōu)勢并不明顯,但耕地稟賦較好,在此基礎(chǔ)上,一些地方政府自發(fā)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如通過在省內(nèi)轉(zhuǎn)移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的方式或省內(nèi)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增減掛鉤的形式,實現(xiàn)效率機制與合法性機制的協(xié)同。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市場機制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現(xiàn)階段的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轉(zhuǎn)移或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增減掛鉤模式,更大程度上是在省級政府的協(xié)調(diào)下,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體制實現(xiàn)的,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可能只是地方政府在執(zhí)行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制度時為了取得合法性的又一應(yīng)對策略,并不能真正實現(xiàn)耕地質(zhì)量平衡與提高配置效率。保障谷物安全后,糧食安全只具有準(zhǔn)公共物品屬性,因此,筆者認為在中央政府對永久基本農(nóng)田進行嚴格控制后,對永久基本農(nóng)田之外的耕地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利用市場以提高效率,激勵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轉(zhuǎn)移市場,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市場購買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以取得合法性,同時,由于市場上買者、賣者眾多,通過充分競爭,提高市場效率,使效率機制與合法性機制從沖突走向互補。地方政府通過全國統(tǒng)一市場購買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通過充分競爭,既提高了土地配置效率,又保證了耕地數(shù)量與質(zhì)量的動態(tài)平衡,從而實現(xiàn)對耕地的有效控制。
(三) 保障食物安全的耕地: 效率為主,適當(dāng)控制
保障糧食安全后的食物安全是私人物品,根據(jù)其生產(chǎn)、消費特性,市場可以在其中發(fā)揮基礎(chǔ)性作用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草地、林地、河流、湖泊、海洋等國土資源都能提供食物,而在現(xiàn)有的耕地保護制度下,為了實現(xiàn)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地方政府將一些草地、林地、湖泊、海洋等資源通過土地開發(fā)轉(zhuǎn)變?yōu)楦匾詰?yīng)對上級政府的檢查。但耕地數(shù)量上的平衡可能對總體食物供給能力造成不利影響,一方面,草地、林地等轉(zhuǎn)變?yōu)楦睾蟛⒉贿m用于種植糧食作物,其糧食產(chǎn)量很低,是邊際耕地,農(nóng)戶并不愿意耕種,導(dǎo)致其最后被拋荒,無法提供糧食,無法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生產(chǎn)力;另一方面,草地、林地等土地資源被開發(fā)為耕地,其原有的提供水果、禽畜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力遭到破壞。因此,將草地、林地等土地資源轉(zhuǎn)變?yōu)楦睾螅赡芗炔荒芴峁┘Z食,又損失了其生產(chǎn)其他食物的能力,總體上降低了國家提供食物的能力,且對生態(tài)環(huán)境造成破壞[13]。在現(xiàn)有制度安排中,耕地轉(zhuǎn)變?yōu)槠渌r(nóng)用地也受到限制,因為需要保證耕地總量的動態(tài)平衡。但筆者認為,農(nóng)戶的風(fēng)險規(guī)避性較強,作為理性的決策主體,在需要較大的投資、較高的技術(shù)及面臨更大的市場風(fēng)險時,農(nóng)戶不會輕易改變耕地用途,如將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轉(zhuǎn)變?yōu)榉N植經(jīng)濟作物的耕地或?qū)?yōu)質(zhì)耕地轉(zhuǎn)變?yōu)閳@地、林地等,農(nóng)戶在轉(zhuǎn)變農(nóng)用地用途時是謹慎的,更有可能是將邊際耕地轉(zhuǎn)變?yōu)榱值亍⒉莸氐纫垣@得更多利潤。因此,在市場機制下,將邊際耕地轉(zhuǎn)變?yōu)槠渌r(nóng)用地并不會影響食物安全,反而能提高效率,既能促進農(nóng)戶增收,又能更好地保障食物安全。
在糧食安全得到保障后,從食物安全角度出發(fā),應(yīng)對現(xiàn)有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制度進行改進。高質(zhì)量、無污染的耕地通過中央政府的嚴格控制和有效保護以確保口糧絕對安全與谷物基本自給;在耕地轉(zhuǎn)變?yōu)榻ㄔO(shè)用地時,應(yīng)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轉(zhuǎn)移市場以保證耕地占補數(shù)量與質(zhì)量平衡,在有效控制下提高效率,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而在糧食安全得到保障后,對農(nóng)用地之間的轉(zhuǎn)換應(yīng)以市場配置為主。農(nóng)用地之間的轉(zhuǎn)換以市場配置為主,并不會導(dǎo)致大規(guī)模開荒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行為,中國已經(jīng)由大規(guī)模開荒的年代變成農(nóng)村青年勞動力短缺的時代,開墾所得利潤不能與城市打工收入相比,因此,從經(jīng)濟角度考慮不會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將林地、草地等開墾為耕地的行為,也不會出現(xiàn)將高質(zhì)量耕地轉(zhuǎn)變?yōu)閳@地、林地的行為,而只是將糧食作物生產(chǎn)率低的邊際耕地轉(zhuǎn)變?yōu)樗绒r(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率更高的園地、林地等農(nóng)用地。在保障糧食安全后,農(nóng)用地之間的轉(zhuǎn)換通過市場配置能更好地提供食物、促進農(nóng)戶增收。因此,農(nóng)用地之間的轉(zhuǎn)換應(yīng)以市場為導(dǎo)向,對質(zhì)量等級較差的耕地和邊際耕地轉(zhuǎn)換為其他農(nóng)用地不加限制,但必須是農(nóng)用地之間的轉(zhuǎn)換,而不能將耕地轉(zhuǎn)換為建設(shè)用地,耕地轉(zhuǎn)換為建設(shè)用地應(yīng)按相關(guān)制度執(zhí)行。在農(nóng)用地轉(zhuǎn)換中,政府應(yīng)當(dāng)進行適當(dāng)控制,以確保轉(zhuǎn)變?yōu)槠渌r(nóng)用地的是邊際耕地。
四、 耕地保護管理體制: 激勵機制與監(jiān)督機制配合
改進現(xiàn)有耕地保護制度之后,關(guān)鍵是如何以低成本實施制度變遷[14]。新的制度安排也不可避免地會遭遇信息不對稱下的委托-代理問題,因此,關(guān)鍵是采取怎樣的管理體制才能使代理人(地方政府)與委托人(中央政府)的目標(biāo)一致。要解決委托—代理關(guān)系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目標(biāo)不一致的問題,監(jiān)督與激勵是可以采用的兩種機制,它們之間有著互補關(guān)系。激勵就是使用物質(zhì)的或精神上的報酬促使地方政府采取與中央政府目標(biāo)一致的行為,監(jiān)督就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耕地保護的環(huán)節(jié)、過程、結(jié)果等進行監(jiān)視、督促和管理,使地方政府嚴格遵循耕地保護制度。監(jiān)督對激勵有直接影響,監(jiān)督可以使中央政府更準(zhǔn)確地對地方政府進行激勵,而明確的激勵機制有助于中央政府減少監(jiān)督強度與成本。下面具體分析如何運用激勵與監(jiān)督機制使地方政府耕地保護的目標(biāo)與中央政府真正保持一致,從而使永久基本農(nóng)田的數(shù)量、質(zhì)量、生態(tài)得到有效保護,實現(xiàn)占補耕地質(zhì)量、生態(tài)平衡。
(一) Ⅰ象限: 永久基本農(nóng)田
中央政府通過嚴格控制永久基本農(nóng)田對優(yōu)質(zhì)、無污染的耕地進行保護以確保口糧絕對安全與谷物基本自給,但永久基本農(nóng)田的劃定工作還是由地方政府進行。面對地方政府可能出現(xiàn)的應(yīng)對策略,在永久基本農(nóng)田劃定時,中央政府需加大監(jiān)督力度,如果發(fā)現(xiàn)地方政府的工作存在問題,應(yīng)加大懲罰力度,以確保劃入永久基本農(nóng)田保護區(qū)的耕地優(yōu)質(zhì)、無污染或只有輕度污染且農(nóng)業(yè)基礎(chǔ)設(shè)施配套完善。耕地劃為永久基本農(nóng)田后,實行嚴格保護,確保其面積不減少、土壤環(huán)境質(zhì)量不下降,除法律規(guī)定的重點建設(shè)項目選址確實無法避讓外,其他任何建設(shè)均不得占用。
在劃定永久基本農(nóng)田后,中央政府應(yīng)改變過去“撒胡椒面”的補貼方式,各類農(nóng)業(yè)補貼應(yīng)向永久基本農(nóng)田多的地區(qū)傾斜,將農(nóng)業(yè)綜合開發(fā)、高標(biāo)準(zhǔn)農(nóng)田建設(shè)、農(nóng)田水利建設(shè)、耕地保護與質(zhì)量提升、測土配方施肥等涉農(nóng)資金向永久基本農(nóng)田集中的縣(市、區(qū))傾斜,將土地占用費更多地用于永久基本農(nóng)田保護區(qū)的建設(shè)。同時,在職務(wù)晉升、榮譽等激勵機制上,提高永久基本農(nóng)田管護在政績評價中的比重,激勵地方政府做好永久基本農(nóng)田保護工作。農(nóng)戶直接占有永久基本農(nóng)田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其耕地利用行為直接影響永久基本農(nóng)田的質(zhì)量與生態(tài),因此,也需激發(fā)農(nóng)戶管護永久基本農(nóng)田的積極性,創(chuàng)新農(nóng)村土地制度,做好農(nóng)地確權(quán)工作,確保農(nóng)戶土地承包權(quán)穩(wěn)定,使農(nóng)戶對永久基本農(nóng)田的投入有合理預(yù)期,從而實現(xiàn)永久基本農(nóng)田的地力提升與可持續(xù)利用。同時,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三權(quán)分置”辦法,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和服務(wù)主體,促進農(nóng)地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
中央政府應(yīng)提高監(jiān)督強度以確保劃入永久基本農(nóng)田的耕地的質(zhì)量與生態(tài),在劃定后利用激勵機制激發(fā)地方政府與農(nóng)戶管理和維護永久基本農(nóng)田的積極性,進一步提升永久基本農(nóng)田的質(zhì)量,建成更大面積的高標(biāo)準(zhǔn)農(nóng)田。通過監(jiān)督機制與激勵機制的配合,使永久基本農(nóng)田地力和生產(chǎn)力不斷提升,有效保障國家口糧絕對安全與谷物基本自給。
(二) Ⅱ象限: 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制度下耕地轉(zhuǎn)變?yōu)榻ㄔO(shè)用地
原有的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轉(zhuǎn)移市場是在省級政府的協(xié)調(diào)下,省內(nèi)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的地方政府購買欠發(fā)達地區(qū)地方政府的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或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交易主體有限,可供交易的耕地數(shù)量也有限,競爭不充分,市場效率不高,賣方政府的積極性也不高。為了提高市場競爭程度,激勵買賣雙方提高土地資源配置的效率,應(yīng)打破原有的行政邊界,擴大市場容量,建成全國性統(tǒng)一的市場以增加市場競爭主體。市場上買方、賣方增多,形成充分競爭,類似于市場交易,使參與交易的耕地質(zhì)量與價格成正比,這對交易雙方來說都是一種經(jīng)濟激勵。但這需要在政績評價體系上進行相應(yīng)的改革,當(dāng)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政績評價以經(jīng)濟發(fā)展為主要衡量標(biāo)準(zhǔn)時,耕地用于建設(shè)用地的利益相對來說遠高于用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利益,地方政府不愿意出讓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或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可能造成市場上賣方非常少,而買方非常多,則市場難以構(gòu)建,土地難以按照比較優(yōu)勢進行配置。
改革政績評價體系,對不同的主體功能區(qū)實行不同的政績考核體制和官員晉升機制。對城市化地區(qū)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主要標(biāo)準(zhǔn)是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而對農(nóng)產(chǎn)品主產(chǎn)區(qū)的地方政府則主要考核其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能力。在主體功能區(qū)績效考核標(biāo)準(zhǔn)下,農(nóng)產(chǎn)品主產(chǎn)區(qū)的地方政府出賣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或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能獲得較高收益,而這些收益可用于投資耕地,其供給農(nóng)產(chǎn)品的能力將不斷增強。在經(jīng)濟激勵與政治晉升激勵的雙重激勵下,農(nóng)產(chǎn)品主產(chǎn)區(qū)的地方政府有動力出賣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市場上的賣方數(shù)量將會增加。而城市化地區(qū)地方政府發(fā)展經(jīng)濟的比較優(yōu)勢較為明顯,發(fā)展經(jīng)濟需要占用耕地,需要在市場上購買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以實現(xiàn)其合法性,因此,城市化地區(qū)的地方政府有強烈的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的購買欲望,市場上的買方數(shù)量也會增加。在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轉(zhuǎn)移、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增減掛鉤市場上,城市化地區(qū)地方政府可以購買農(nóng)產(chǎn)品主產(chǎn)區(qū)地方政府的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從而高效率地發(fā)展工業(yè)及第三產(chǎn)業(yè);農(nóng)產(chǎn)品主產(chǎn)區(qū)地方政府加大對農(nóng)地的投入以發(fā)展農(nóng)業(yè),提高土地生產(chǎn)率。通過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轉(zhuǎn)移市場來提高市場競爭程度,實現(xiàn)土地資源的最優(yōu)配置,提高土地的總體使用效率。
地方政府通過市場進行交易能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但可能出現(xiàn)占補的耕地質(zhì)量、生態(tài)不平衡的問題,買方政府可能更想低價獲得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或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因此,在利用市場提高效率的同時,中央政府也應(yīng)加強監(jiān)督。市場上占補耕地的位置、質(zhì)量、生態(tài)等信息應(yīng)完全公開、透明,以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便于中央政府(國土資源部)利用第二次土地調(diào)查信息低成本地進行判別。在信息較充分的前提下,中央政府監(jiān)督買方地方政府,買方地方政府監(jiān)督賣方地方政府,賣方地方政府在聲譽機制下進行自我監(jiān)督,在“三重監(jiān)督”下,通過市場實現(xiàn)耕地占補的數(shù)量、質(zhì)量和生態(tài)平衡,使效率機制與合法性機制互補,最終實現(xiàn)提高效率、有效控制的制度目標(biāo)。通過經(jīng)濟激勵、政治晉升激勵與“三重監(jiān)督”,通過分權(quán)與市場降低中央政府的監(jiān)督成本和制度實施成本,真正實現(xiàn)耕地質(zhì)量、生態(tài)的占補平衡。地方政府通過市場進行交易是對人口高峰期而言的,而從長期來看,在人口高峰期后,可以考慮以市場為主、政府為輔的制度安排,更多地引入市場力量以降低糧食安全保障成本。
(三) Ⅲ象限: 農(nóng)用地、建設(shè)用地
農(nóng)用地之間的轉(zhuǎn)換應(yīng)以市場為資源配置的基礎(chǔ),政府只對農(nóng)用地之間的轉(zhuǎn)換進行適當(dāng)控制和監(jiān)督,而對于建設(shè)用地,在符合土地利用規(guī)劃后,也應(yīng)以市場配置為基礎(chǔ)。在土地產(chǎn)權(quán)主體不明晰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可以強勢地決定城鄉(xiāng)土地的利用與開發(fā)。以低價土地引入高污染企業(yè)快速拉動經(jīng)濟增長是一種粗放型的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xù)的,應(yīng)改變過去地方政府強制征收農(nóng)村土地用于商業(yè)及工業(yè)發(fā)展等非公眾利益用途的土地配置方式,建立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土地市場。在符合規(guī)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許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營性建設(shè)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quán)同價。農(nóng)村集體建設(shè)用地轉(zhuǎn)化為城市建設(shè)用地時,應(yīng)通過土地市場進行,而不能強制征收,充分體現(xiàn)土地價值,改變過去地方政府“以地生財”的模式,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農(nóng)村集體土地所有者不僅擁有農(nóng)業(yè)用地價值,還應(yīng)分享城市建設(shè)用地價值。改革完善農(nóng)村宅基地制度,在試點基礎(chǔ)上慎重穩(wěn)妥地推進農(nóng)民住房財產(chǎn)權(quán)抵押、擔(dān)保、轉(zhuǎn)讓,嚴格執(zhí)行宅基地使用標(biāo)準(zhǔn),嚴格禁止一戶多宅,探索農(nóng)村宅基地退出機制。
建立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土地市場后,城市化地區(qū)的地方政府難以通過強制手段低價占用耕地,為了發(fā)展經(jīng)濟,只能通過對存量建設(shè)用地進行整理、再開發(fā)或從市場上購買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對存量建設(shè)用地進行再開發(fā)可以減少對耕地的占用,降低耕地保護壓力,地方政府可以減少購買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的支出,對還有調(diào)節(jié)潛力的處于快速發(fā)展、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的城市化地區(qū)的地方政府而言具有內(nèi)在激勵,對于高度發(fā)達的城市化地區(qū),由于從本地區(qū)進行調(diào)節(jié)的潛力有限,可以選擇從市場上購買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而農(nóng)產(chǎn)品主產(chǎn)區(qū)的地方政府通過低效建設(shè)用地再開發(fā)、農(nóng)村宅基地退出機制能節(jié)約更多的耕地,將此轉(zhuǎn)換為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在市場上進行銷售,從而獲得較高的收入;同時,通過減少耕地占用及整理復(fù)墾土地能提高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能力,對農(nóng)產(chǎn)品主產(chǎn)區(qū)地方政府而言也是一種正向激勵。建設(shè)用地市場化配置能提高土地集約利用率,降低耕地保護壓力,是對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轉(zhuǎn)移市場的有益補充,有利于低成本地實現(xiàn)食物安全與經(jīng)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Ⅳ象限未利用地不是本文分析的重點,對于未利用地最合理的配置方式可能是使其保持自然狀態(tài)。
五、 討 論
本文在分析食物安全的層次性及其生產(chǎn)、消費特性后,根據(jù)食物安全各個層次的物品性質(zhì)界定耕地保護中政府與市場的合理邊界,進一步提出運用監(jiān)督與激勵機制使制度變遷能夠低成本地實施。本文提出的是漸進式制度變遷模式,不是一個全新的制度安排,現(xiàn)有耕地保護制度不變,只是對制度進行改進與完善,在治理結(jié)構(gòu)與管理體制上對耕地保護制度進行優(yōu)化與細化能降低制度變遷的阻力與成本。永久基本農(nóng)田是對基本農(nóng)田制度的進一步優(yōu)化,中央政府改原有的“親密型”干群關(guān)系管理模式為“疏遠型”干群關(guān)系管理模式,通過將優(yōu)質(zhì)、無污染的耕地劃入永久基本農(nóng)田保護區(qū)進行保護,對地方政府的游說一概拒絕,嚴格控制優(yōu)質(zhì)、無污染耕地,通過監(jiān)督與激勵機制的配合使地方政府與農(nóng)戶的目標(biāo)與中央政府一致,以保護優(yōu)質(zhì)未污染耕地,切實保障口糧絕對安全與谷物基本自給。通過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轉(zhuǎn)移市場,提高土地配置效率,使地方政府的效率機制與合法性機制互補,地方政府在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轉(zhuǎn)移市場上能購買到中央政府要求的耕地保有量,同時通過經(jīng)濟激勵、政治晉升激勵與“三重監(jiān)督”,真正實現(xiàn)耕地質(zhì)量、生態(tài)占補平衡,這既維持了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又提高了土地資源配置效率,是對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制度的改進。邊際耕地與其他農(nóng)用地的轉(zhuǎn)換通過市場進行,能增加食物(農(nóng)產(chǎn)品)的有效供給能力,又不會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是對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制度的優(yōu)化。另外,建設(shè)用地更多的通過市場進行配置,能提高建設(shè)用地的效率,降低建設(shè)占用耕地的壓力,有利于耕地保護。中央政府應(yīng)嚴格控制永久基本農(nóng)田,保護好一定數(shù)量的高質(zhì)量無污染耕地,地方政府利用市場進行農(nóng)地發(fā)展權(quán)交易以實現(xiàn)耕地數(shù)量、質(zhì)量、生態(tài)的動態(tài)平衡,邊際耕地與建設(shè)用地通過市場進行配置以提高效率,各級政府、市場相互配合,以低經(jīng)濟社會代價保障口糧絕對安全、谷物基本自給、糧食安全及農(nóng)產(chǎn)品的有效供給。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側(cè)重于研究基于食物安全層次性的耕地保護制度的改進,而沒有涉及具體需劃定多少永久基本農(nóng)田以保障口糧絕對安全與谷物基本自給、需保有多少耕地以保障糧食安全以及多少邊際耕地可以轉(zhuǎn)換為其他農(nóng)用地。對此,已有部分學(xué)者進行了初步研究,而在接下來的研究中可以根據(jù)人口規(guī)模、食物需求變化等對上述議題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1]郭珍: 《石油農(nóng)業(yè)、污水灌溉與耕地污染防治》,《南通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6年第5期,第111-116頁。[Guo Zhen,″Petroleum Agriculture, Sewage Irrigation and Farmland Pollution Control,″JournalofNantong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No.5(2016), pp.111-116.]
[2]譚榮、曲福田: 《中國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與農(nóng)地資源保護:從兩難到雙贏》,《管理世界》2006年第12期,第50-59, 66頁。[Tan Rong & Qu Futian,″Convers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Farmland: From the Dilemma to a Win-Win Situation,″ManagementWorld, No.12(2006), pp.50-59, 66.]
[3]譚榮、曲福田: 《市場與政府的邊界:土地非農(nóng)化治理結(jié)構(gòu)的選擇》,《管理世界》2009年第12期,第39-47頁。[Tan Rong & Qu Futian,″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Function of the Market and That of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Non-agricultural Use of Farmland,″ManagementWorld, No.12(2009), pp.39-47.]
[4]靳相木、姚先國: 《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管理的分權(quán)取向改革及其情景模擬》,《公共管理學(xué)報》2010年第3期,第10-20頁。[Jin Xiangmu & Yao Xianguo,″The Options between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in Farmland Conversion,″JournalofPublicManagement, No.3(2010), pp.10-20.]
[5]M.D.McGinnis(ed.),PolycentricGovernanceandDevelop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6]倪國華、鄭風(fēng)田: 《糧食安全背景下的生態(tài)安全與食品安全》,《中國農(nóng)村觀察》2012年第4期,第52-58頁。[Ni Guohua & Zheng Fengtian,″The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Food Safety in the Context of Food Security,″ChinaRuralSurvey, No.4(2012), pp.52-58.]
[7]毛學(xué)峰、劉靖、朱信凱: 《中國糧食結(jié)構(gòu)與糧食安全: 基于糧食流通貿(mào)易的視角》,《管理世界》2015年第3期,第76-85頁。[Mao Xuefeng, Liu Jing & Zhu Xinkai,″China’s Grain Structure and Food Safety: Grain Circulation and Trade,″ManagementWorld, No.3(2015), pp.76-85.]
[8]李國祥: 《2020年中國糧食生產(chǎn)能力及其國家糧食安全保障程度分析》,《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2014年第5期,第4-12頁。[Li Guoxiang,″An Analysis of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in 2020 and Its Indemnification to Food Security of China,″ChineseRuralEconomy, No.5(2014) ,pp.4-12.]
[9]鄧大才: 《糧食安全的模型、類型與選擇》,《華中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2年第1期,第1-7頁。[Deng Dacai,″Food Security: Model, Type and Choice,″Journalof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No.1(2012), pp.1-7.]
[10]周雪光: 《組織社會學(xué)十講》,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3年。[Zhou Xueguang,TenLecturesontheSociologyofOrganizatio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3.]
[11]郭珍、吳宇哲: 《耕地保護制度執(zhí)行過程中的“目標(biāo)替代”——基于多任務(wù)代理模型的研究》,《經(jīng)濟學(xué)家》2016年第6期,第58-65頁。[Guo Zhen & Wu Yuzhe,″′Object Substitu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 Protection System: A Study Based on Multitask Proxy Model,″Economist, No.6(2016), pp.58-65.]
[12]張蔚文、李學(xué)文: 《外部性作用下的耕地非農(nóng)化權(quán)配置——“浙江模式”的可轉(zhuǎn)讓土地發(fā)展權(quán)真的有效率嗎?》,《管理世界》2011年第6期,第47-62頁.[Zhang Weiwen & Li Xuewen,″The Allocation of the Right of the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Farmland under the Function of Externality,″ManagementWorld, No.6(2011), pp.47-62.]
[13]郭珍、吳宇哲: 《基本農(nóng)田保護制度應(yīng)優(yōu)先于耕地總量動態(tài)平衡制度》,《湖南財政經(jīng)濟學(xué)院學(xué)報》2016年第2期,第54-62頁。[Guo Zhen & Wu Yuzhe,″Basic Farmland Protection System Should Be Priority in Dynamic Balance System of Total Arable Land,″JournalofHunanFinanceandEconomicsUniversity, No.2(2016), pp.54-62.]
[14]D.C.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