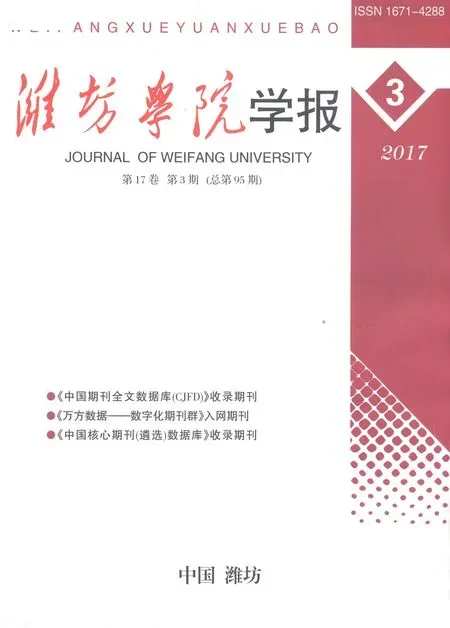在歷史和現實之間輾轉騰挪
——論莫言的長篇小說創作
王恒升
(濰坊學院,山東 濰坊 261061)
在歷史和現實之間輾轉騰挪
——論莫言的長篇小說創作
王恒升
(濰坊學院,山東 濰坊 261061)
迄今為止,莫言共創作了十一部長篇小說,雖然形式上各種各樣,藝術表現方法多姿多彩,但寫作內容無外乎兩個,一個是歷史,一個是現實,莫言總是在歷史和現實之間輾轉騰挪。這一點,不僅與中國傳統文學高度一致,而且表現出了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就崇尚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高尚追求。
長篇小說;歷史;現實;輾轉騰挪
自古以來,中國文人就崇尚“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寫出了眾多彪炳史冊的宏大巨著。考察這些恢弘著作的寫作內容,無外乎兩個,一個是歷史,一個是現實。歷史與現實構成了傳統文學的主要內涵。它們共同為中國新文學的發生、發展奠定了基礎。雖然自新文學以降,文學的表現內容有了極大的豐富,出現了遠如武俠、言情,近如玄幻、穿越的創作,但占據文學主流的,依然是以歷史和現實為寫作對象的作品。絕大多數作家仍然在歷史和現實兩大傳統領域精耕細作,辛勤耕耘。莫言即是其中之一。迄今為止,莫言共創作十一部長篇小說。雖然從創作理念和文本形式上說,莫言的作品和傳統文學有較大的出入,它吸收借鑒了一些西方現代派的東西,繼承學習了一些傳統的東西,更融合創新了一些具有鮮明的個人特征的新形式、新方法、新手法,但就內容而言,仍舊沒有脫離歷史和現實兩大題材。他的創作看起來令人眼花繚亂,但仔細品味,就不難發現,他只不過善于在歷史和現實之間輾轉騰挪,就自己感興趣的某個歷史話題或某種社會現象,要么做出富有深度的歷史探究,要么做出富有卓見的現實評判,或者,將歷史與現實聯系起來,從歷史的深處追尋現實的場景,從現實的存在探掘歷史的根由。
一
莫言純粹將歷史作為小說內容的,有三部作品,它們是《紅高粱家族》《食草家族》和《檀香刑》。
《紅高粱家族》是莫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但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嚴格意義上的長篇小說,應該從構思到結構都渾然一體,是作者才華、能力、經驗、思想、精神、技術、身體、耐力的一次完整的體現。而《紅高粱家族》不是。它是由5部中篇小說聯袂拼接而成的一部長篇小說。雖然說小說的人物、故事、情節、主題、風格、氛圍一脈相承,有明顯的連續性,但它確實是在各自獨立成篇后又連綴而成的,缺少內在肌理的一致性。《紅高粱》是第一部,發表后引起了巨大反響,于是莫言乘勝追擊,又連續寫了《高粱酒》《高梁殯》《狗道》《奇死》,將一個原本已經講得很透徹很圓滿很凝練也很震撼的故事,稀釋成了一部注了水的歷史大片。然而,盡管《紅高粱家族》結構上讓人感到不嚴謹,風格上讓人感到重復,但它透露出來的對于歷史本相的還原與揭示,還是讓人感到震驚不已。它的出現,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抗戰歷史的傳統而簡單的認知,拓展了長期以來抗戰文學過于狹窄的寫作路徑,深化了人們對于變化莫測的復雜的人性的認識,開闊了人們的藝術審美視野。不無夸張地說,它與周梅森的《國殤》《大捷》、喬良的《靈旗》等一起,改變了當代戰爭文學在題材、主題與藝術表現等方面的固有走向。
在人們的傳統認知中,抗戰文學應如《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烈火金剛》《野火春風斗古城》《小兵張嘎》《鐵道游擊隊》《苦菜花》等,高舉著民族大旗,張揚著民族大義,彰顯著正義主張,鳴響著勝利號角。尤其是在歌頌勝利者的光輝形象中,人民軍隊及其它的領導者,是當仁不讓的主角。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和規律,是被歷史所深刻證明了的。但是,這不是全部。在14年的抗戰史中,既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游擊戰爭,也有國民黨擔負的正面戰場,還有民間自發的各式各樣的抗戰。總之,是一場全民族的抗戰。在這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每一個不愿當亡國奴的中國人,無論什么背景,出于什么考量,都義無反顧地投入到了其中。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多姿多彩的民族抗戰卻被詮釋成了一種單一政黨領導的抗戰,沒有得到全面地藝術展示。久而久之,抗戰歷史也就成了一種殘缺不全的歷史,或者說,成了一種被過濾了的凈化了的歷史。顯然,這樣的歷史不是歷史的全貌,不利于全面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團結全國各階層人民輕裝前進。任何時候,對歷史的正確態度都應該是不虛美,不隱惡,實事求是。經過思想解放運動的莫言,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于是有了表現土匪抗戰的《紅高粱》及其家族。莫言曾說:“寫土匪抗戰,事實上也是有一點歷史根據的。在抗日戰爭初期,我們的膠東地區冒出了幾十支游擊隊,一幫土匪搖身一變,樹立一個旗號,我不是土匪了,我是抗日游擊隊,實際上還是按照過去的生活方式在生存。”[1]還說,土匪“本來也沒有這么高的覺悟,在沒有外敵入侵的情況下,他們也是破壞社會安定的力量。”“只有到了要么是餓死要么是被敵人殺死的時候,才會奮起反抗。”[2]《紅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鰲,就是在日本鬼子侵占了家鄉,原本自由自在的生活空間被逼仄到無法生存的狀況下,才憤然舉起了抗日大旗。雖然這種自發的抗日行為多半會因為沒有正確理論和正確政黨的指導,不會長久,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抗日形勢。余占鰲的所作所為,也不會因為有了抗日行動就會消弭半點匪性,他后來的經歷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但它畢竟是一種可歌可泣的抗日行為,是一種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的爆發,是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的原始生命追求,應該值得肯定。莫言通過對家鄉抗戰歷史的挖掘,揭開了歷史的厚重帷幕,發現了土匪抗戰的歷史史實,認識到了它們蘊藏的巨大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價值,將它們真實地再現了出來。不但豐富了抗戰文學的題材,繁榮了抗戰文學的英雄人物譜系,打破了讀者原有的閱讀期待心理,升華了讀者的審美情趣,而且更重要的是,將歷史追索推向了縱深,引領了新時期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的隆隆前行。難怪王彪編選《新歷史小說選》和張清華寫作《十年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回顧》時,都把《紅高粱家族》看作是“新歷史小說”或“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的直接出發點之一。
《食草家族》是一部秉承著《紅高粱家族》寫下來的小說。從風格到內容再到形式,幾乎如出一轍。就風格而言,《紅高粱家族》就有溢丑現象。其中對羅漢大爺被日寇殘忍剝皮的描寫,對余占鰲往酒里撒尿偶得佳釀的描寫,對麻風病人的骯臟描寫,對井底的癩蛤蟆和毒蛇的可怕描寫,對狗吞人尸、人食狗肉的無奈描寫,對高密東北鄉人的幾個高度鮮明的對比概括,尤其是描寫到這些細節時,莫言表現出來的細致從容,津津樂道,無不讓人觸目驚心,毛骨悚然。到了《食草家族》,這種溢丑現象有過之而無不及。它不但詳細描寫了亂倫、偷情,而且濃墨重彩地描畫了大便,超出了人們心理所能承受的極限。就內容而言,《紅高粱家族》除了反映民間抗戰,還有一個很突出的內容,就是謳歌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蓬勃生命。甚至相對于抗戰,謳歌生命強力、張揚生命本質,是一個更加光彩奪目的內容。這一內容到了《食草家族》中,又有了新的表現。如果說《紅高粱家族》主要是從“我爺爺”“我奶奶”不受羈絆、為所欲為的浪蕩行為,歌頌他們天不怕地不怕的大無畏精神,把種的退化作為隱線處理的話,那么,《食草家族》則是通過四老爺、九老爺年輕時生命力旺盛,八九十歲了依然精神矍鑠,來映照食草家族的后代們因為長期脫離土地,而導致的生命力孱弱、腳上普遍長蹼、出現逆生長的現象,把種的退化作為主要內容來描寫。通過對種的退化的神奇描寫,反襯了自然偉力的強大。就形式而言,《紅高粱家族》是一部虛構的家族史小說,是以“我”的視角講述的“我爺爺”“我奶奶”的傳奇人生。《食草家族》也是一部虛構的家族史小說,也是以后輩的眼光來評述前輩人的故事和后人的生活。在結構上,《食草家族》如同《紅高粱家族》一樣,也是一部狗尾續貂式的小說。《紅高粱家族》是先有中篇《紅高粱》,然后才有其他。《食草家族》是先有中篇《紅蝗》,然后才有其他。而且都在第一部中,把想說的都已經說得差不多了。對讀者而言,讀了第一部,不讀其他幾部,都幾乎不會留有什么遺憾。
如果說,在《紅高粱家族》中,莫言把藝術視角伸向了曾經被遮蔽的歷史,在《食草家族》中,又將藝術視角伸向了荒誕不經的民間野史,那么在《檀香刑》中,他把歷史事實和藝術想象巧妙地架構在一起,展現了一部慘烈的酷刑文化史。孫丙抗德事件,在歷史上是實有其事的。1900年,高密人孫文率領鄉民以德國人修筑膠濟鐵路給當地民眾造成巨大的財產損失為由,同德國人及其清政府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最后不幸壯烈犧牲。孫文的抗德行為雖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膠濟鐵路的既成事實,但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鄉民的利益,迫使德國膠澳總督和清政府改變了原先的設計線路,更多地預留了鐵路橋梁和涵洞,不致高密西部低洼區壅水成患。更重要的是,在當時那種列強環伺、覬覦我邦的情況下,孫文領導的高密人民的抗德斗爭,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偉大反抗精神。雖然這一歷史事件到了小說中,孫文被改稱孫丙,并且為了增加小說的藝術趣味和閱讀噱頭,將孫丙寫成了一個失落的戲子,頭腦中不乏愚昧的想法,行為中不乏滑稽的舉動,甚至有些懵懂傻逼,分不清戲里戲外,但抗德初衷和抗德行為還是基本符合歷史真實的。當然,莫言寫《檀香刑》,絕不是為了再現這一歷史事件,而是借助這一歷史事件,展現中國歷史上的酷刑文化。酷刑,是指對一個人故意施加的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任何使他在肉體上或精神上極度痛苦的懲罰。酷刑自古就有。愈往人類歷史的深處追溯,酷刑的程度愈烈。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施行過酷刑,中國也不例外。也許是因為歷史更悠久、更動蕩、更反復無常,中國較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和民族在使用酷刑方面更慘烈,更駭人聽聞。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酷刑很多,諸如凌遲、梳洗、剝皮、烹煮、車裂、刖刑、宮刑、幽閉、腰斬、縊首、灌鉛、抽腸、活埋、杖殺、騎木驢、俱五刑、剜鼻、株連等,每一種聽起來都令人毛骨悚然。中國歷史上也有許多著名的酷刑案例,如秦始皇坑儒、李斯遭腰斬、商鞅被五馬分尸、孫臏遭刖刑、司馬遷受宮刑等,每一種想起來也都令人不寒而栗。面對不堪回首的歷史,魯迅先生曾感嘆:“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或異族屠戮,奴隸,敲詐,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3]雖然越到后世,文明程度越高,對肉體實施的酷刑越來越少,但幾千年的歷史積淀,已在人們的心目中形成了一部厚重的酷刑文化,況且這種酷刑文化有越來越演變成精神枷鎖的趨勢,只不過換了一種方式來繼續摧殘中國民眾而已。酷刑文化在國家、民族和個人的心靈史上,產生了嚴重的心理暗影。《檀香刑》總共寫了六次行刑過程,可謂是對酷刑文化的高度凝練。其中,“閻王閂”和“檀香刑”是莫言通過藝術想象虛構出來的,雖然藝術象征的意味大于實際操練,但殘酷的本質卻與歷史上的實有酷刑一脈相承。更重要的是,《檀香刑》所闡發的意義絕不僅僅在于講述幾次酷刑刑術的執行過程,而在于通過劊子手趙甲的口吻,來講述酷刑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行刑人的心路歷程,從一個更獨特的層面上,展現了酷刑文化的豐富內涵。在趙甲看來,他研究、發明、實施任何一種酷刑,都不只是用來結束一個人的自然生命,而是用來宣示皇家政權的至高無上和不容冒犯的威儀,以及自己這一職業在維護皇權統治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此一來,他精心創造的“檀香刑”,就不是一項單純的酷刑刑術了,而成了一個酷刑文化的象征性、標志性、隱喻性符號。
歷史是什么?是教科書中明確記載的文字,還是民間口口相誦的傳說?是一種既定的反映了事物發展的規律與本質的所謂的真實印跡,還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站在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認識。同樣,文學對于歷史的藝術反映,也會有不同的回聲。可以說,莫言關于歷史題材內容的寫作,回應了這些認知。
二
莫言關注現實內容的長篇小說,有四部,它們是《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國》《紅樹林》。白居易曾說:“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莫言創作上述四部小說,無不是感時撫事。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完整構思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雖然在這之前,《紅高粱家族》已經出版,但它是由五部中篇聯袂而成的,缺乏前后一致的貫通。《天堂蒜薹之歌》的寫作時間極短,在不到40天的時間里,莫言一氣呵成。莫言之所以寫得快,與兩件事情對他的強烈刺激有關。一件事情是1987年夏天發生的震驚全國的“蒼山蒜薹事件”。當時,由于一些領導干部不作為,又加上地方利益保護主義思想作祟,致使農民豐收的蒜薹賣不出去,大面積爛在地里。農民一氣之下,用蒜薹堵了縣政府大門。農民想見縣長,希望政府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解決農民負擔。但政府官員避而不見,導致農民采取了更激烈的行動。農民沖進縣政府,砸毀了縣長辦公室,焚燒了政府辦公大樓,一時間輿論大嘩。后來,事件雖然得到妥善處理,政府干部要么被撤職,要么被降職或調走,領頭鬧事的農民受到法辦,但事情的前因后果產生的沖擊波對莫言影響很大。說到底,莫言那時雖已遠離鄉村,身棲京華,但他骨子里仍然是一個農民,他對一切漠視農民利益的行為都深惡痛絕。所以,當他看到這個新聞報道后,馬上就萌發了強烈的創作沖動。他曾說:“我看了這個報道以后,內心馬上就很沖動,當時感覺到是想替農民說話,實際上我是替自己說話。直到現在我一直認為自己和農民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在1987年我更感覺我就是一個農民,家里都是農民,農村的任何一個事情都會影響到我的生活。我寫《天堂蒜薹之歌》,實際上是把我積壓多年的、一個農民的憤怒和痛苦發泄出來。”[4]另一件事情發生在1984年10月,莫言的四叔被鄉鎮書記的汽車撞死。當年,莫言的四叔和親家一起往縣城送甜菜。返回的路上,被給書記拉蓋房材料的汽車撞死,連同已經懷孕的拉車的母牛也一起撞死。雖然那個書記和莫言一家還沾親帶故,但最后處理事故的方式和態度卻讓莫言很不滿意。3500元錢就將一個活生生的人和兩頭牛打發了,而且揚言,即便是打官司讓交通隊處理,交通隊也向著他們。莫言聽說這事后,氣憤不過,想把事情鬧大,希望死者和死者的家屬得到起碼的尊重。但是,由于死者的孩子們不爭氣,根本不看重死去的父親,看重的是到手的錢財,再加上父母等人的反復勸阻,莫言最后才放棄了抗爭。然而,盡管不再爭執,但農民生命賤如草芥這件事,仍然像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莫言的心頭,讓他久久不能釋懷。這次,“蒼山蒜薹事件”再次勾起了他對往事的回憶,使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便想用筆來表達對農民的憐憫和同情。在小說中,莫言將以上兩件事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反映了農民的生活現狀,揭示了農民的悲哀、愚昧、讓人可憐可嘆的思想狀況,又揭露了領導干部的不作為,抨擊了愈演愈烈的官僚腐敗作風,表現出了強烈的干預現實的創作態度。莫言寫這部小說時,正值新歷史小說創作風生水起,而他作為領頭人之一,毅然從歷史的深處折回身來,寫出這樣一部充滿人生苦難和現實窘況的小說,不能不說表現出了巨大的敢于擔當的勇氣。小說的藝術也很高明,它不僅具有鮮明的寫實風格,透露著嚴苛的批判精神,而且在敘述方式、藝術結構、語言表述等各方面,做了迥然不同于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形式的探索,形成了一種整體時空統一而局部時空錯亂、于嚴謹中又透露著活潑的別具一格的小說形式。
緊接著《天堂蒜薹之歌》,莫言又寫了《十三步》。應該說,《十三步》的內容很有現實意義,它寫的是教育問題,觸及了社會弊端,反映了社會矛盾,尤其是把教師放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背景下進行藝術關照,其凸顯的社會意義就更加顯著。教育問題,一直是全社會高度關注的大問題。教師的待遇問題,或曰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一直是諸多社會問題中的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諶容的《人到中年》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就是因為她寫了知識分子問題,反映了剛從“文革”中跋涉過來、仍處在撥亂反正中的中年知識分子艱窘的生存狀況,引發了全社會的廣泛共鳴。莫言寫作《十三步》時,雖然陸文婷、傅家杰遭遇的不受社會重視的尷尬現象有了很大改觀,但社會地位低下、生活壓力大、經濟困難的現狀,依然嚴重地存在著,它們依然是教師從教道路上的攔路虎。《十三步》講的主要就是這一內容。中年物理教師方富貴活活地累死在講臺上,另一教師張赤球為了擺脫貧困,讓殯儀館整容師給他改頭換臉、一門心思掙大錢。但現實是殘酷的,一個稱職的老師未必是一個稱職的生意人。張赤球空有發財夢想,卻無實際經營之道,因此,他在生意場上摸爬滾打了一番之后,不得不灰溜溜地以失敗告終。當年,經濟雙軌制改革啟動以后,有多少人懷揣發財夢想,毅然下海經商,又有多少人被無情的經濟大潮拍死在了沙灘上,落了個人財兩空。張赤球可以說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的心理和行為,是當時一批一心想逃離傳統體制約束、實現發財之夢的人的形象寫照。如果塑造好了,張赤球也許會成為又一個陸文婷式的藝術典型。但遺憾的是,莫言根本沒有把精力放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而是本末倒置,放在了如何講述故事上,將藝術表現手段當成了小說寫作的終極目的,浪費了一個絕好的描繪社會巨變的現實題材。在《十三步》中,莫言沉溺于多個人稱的敘述實驗,在“你”“我”“他”、方富貴、張赤球、李玉蟬、“蠟美人”等敘述主體的頻繁轉換中不能自拔,不僅沒有矗立起任何一個人物形象,而且連最基本的人物賴以存在的故事情節都沒有交代清楚。也許,莫言把希望寄托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希望通過讀者的二度創作把作者故意打碎的生活片段連接起來,實現人物形象的再塑。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讀者的二度創作是建立在作者的一度創作的堅實基礎之上的,而且是建立在一度創作開啟了讀者的思維空間,讓讀者擁有了更高、更闊大的思考平臺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一個毫無頭緒的非理性的語言迷宮里,讓讀者找不著北。莫言之所以如此寫,顯然受到了當時風靡文壇的先鋒文學思潮的影響,滑入了“怎么看不懂就怎么寫”的泥淖。莫言自己后來都感嘆:“《十三步》這部小說我想真正看懂的人并不太多,確實寫得太前衛了,把漢語里面所有的人稱都實驗了一遍。”[5]
同是先鋒小說,《酒國》的實驗比《十三步》要理性很多,也成功很多。《酒國》聚焦社會腐敗問題,比同樣是反腐題材的如張平的《抉擇》《十面埋伏》等直面現實的官場小說,其諷喻性、穿透力也更強烈一些。《酒國》寫的是一個叫酒國市的地方,已經腐敗到了烹食嬰孩的地步。高級檢察院的特別偵察員丁鉤兒奉命去偵破此案,沒想到卻深陷其中,被腐敗分子同化。最后,丁鉤兒掉入一個巨大的茅坑被淹死,實際上象征的就是曾經對腐敗深惡痛絕的他,再也回不到清白之身了。90年代初,隨著市場經濟的突飛猛進,社會腐敗之風愈演愈烈,不僅請客、送禮司空見慣,就是社會道德也每況愈下,全社會出現了久入鮑魚之肆不聞其臭、笑貧不笑娼的奇怪現象。莫言敏銳地發現了這一現象,并將它以變形、夸張、荒誕等形式,形象地表現了出來。如果說,賈平凹的《廢都》是通過一個城市的文人們的集體陷落,來形容全社會道德淪喪的話,那么,莫言的《酒國》就是通過一個城市的肆無忌憚的吃喝,來象征全社會無孔不入的腐敗。它們有異曲同工之妙。
《紅樹林》是莫言從部隊轉業到中國檢察日報以后寫的一篇作品,而且是一部先有電視劇后有小說文本的作品。它同樣是一部反映腐敗的小說,寫一個城市的女市長林嵐如何從一個漁村少女成長為一座沿海城市的市長,又如何經受不住貪欲、情欲的腐蝕,一步步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雖然其中夾雜著情愛、母愛、錯愛和社會遺留問題,但貪腐的主題還是很明顯的。可以說,這樣的貪腐故事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不足為奇,相信每一個受審的貪官都能講出一大串比林嵐的故事還要精彩得多的故事。那么,莫言為什么寫這樣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主要原因是作為檢察日報的工作人員,他要完成這方面的任務。由于他當時還不了解國家工作人員是如何瀆職犯罪的,尤其不了解貪官們的心理動因和貪腐軌跡,所以描寫起來有模式化、概念化、拼湊化傾向,不像寫其他作品那樣駕輕就熟,水到渠成。又由于是由電視劇改編而來,情節設置上有明顯的橋段化現象,所以又顯得不夠自然、人性。后來,莫言曾經深有感觸地說:“我認為寫這樣的題材應該把貪官污吏當成人來寫,從人的角度考慮,從自我的內心考慮,或者說,要把貪官污吏當成‘我’自己來寫。在當前的社會機制和法律狀況下,假如我變成了某一個部門或者某一個級別的官員時,能不能保持清廉?會不會也跟那些貪官一樣變成了人民的罪人?并由此對我們的社會制度進行反思……這里邊應該包含著對社會的批判和對于自我的批判,涉及人的根本弱點,和一個存在諸多問題的社會對人的弱點的縱容……”[6]如果莫言真從這些方面來寫貪官污吏,也許會塑造出一個令人難忘的貪官形象。
純粹現實題材的長篇小說創作,不是莫言的強項。這從以上四部小說發表或出版以后的社會反響中就可以看出來。莫言的文學特質是想象力豐富,虛構力強大,如果讓莫言寫一個莫須有的故事,他便會充分發揮自己的文學特質,天上地下,云里霧里,渲染出一個多姿多彩的文學世界。但是如果讓他感時就事,他便會像老虎關在籠子里,有本事施展不出來。況且,現實生活中正在發生的故事,有的遠比人們想象的精彩。
三
莫言還有四部長篇小說,是將歷史和現實聯系起來,要么從歷史的深處追尋現實的存在,要么從現實的場景探掘歷史的根由,歷史和現實互為表里,互相依存,在一個廣闊的時空背景上,探索、展現民族和國家的一段艱難的心路歷程。它們是:《豐乳肥臀》《四十一炮》《生死疲勞》《蛙》。
《豐乳肥臀》是莫言極其看重的一部小說,不止一次地表達過《豐乳肥臀》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書、是他的代表作的意思。《豐乳肥臀》也是一部極具爭議的小說,譽者稱贊它是一部“通向偉大的漢語小說”、“一部真正具備了‘詩’和‘史’的品格,一部富有思想和美學含量的磅礴和宏偉的作品,”[7]毀者批評它是一部“不顧歷史事實”,用“障眼法,用色情、性變態掩蓋他的投槍所指”[8]的作品。那么,《豐乳肥臀》究竟是一部怎樣的作品?這還要從它的基本品質說起。在新時期文學史上,有一個階段是新歷史小說的天下。所謂新歷史小說,是一種不同于傳統歷史小說的小說。傳統歷史小說把歷史當作一種既定的客觀存在,小說所做的一切,既是對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或出現過的人進行還原式講述,讓人們通過小說來了解歷史。雖然其中也有虛構,但虛構多發生在細節描寫上,對故事的進展和人物的性格無傷大雅。它追求的是所謂的歷史的“真實性”。而新歷史小說則把歷史看作是一種話語形式或文本存在,里面充滿了想象與虛構。因為在歷史的生成過程中,它深受“講述話語的年代”的影響,是話語講述主體在一定的時空場域或意識形態的控制中選擇、構造、再塑的結果。所謂的歷史的“真實性”,是永遠也無法真正還原的。因此,新歷史小說家認為,利用小說揭示歷史的真相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通過與歷史的對話,傳達出個人的某些歷史認知、歷史情緒或歷史感慨。基于此,新歷史小說普遍呈現出了敘事立場的民間化、歷史視角的個人化、歷史進程的偶然化、還原歷史的欲望化、主題表達的隱喻化、人物塑造的人性化等眾多不同于傳統歷史小說的新特征。《豐乳肥臀》是一部典型的新歷史小說。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解讀它,也許有些歧義就不會產生。《豐乳肥臀》以上官家的母親上官魯氏和兒女們的命運變遷為脈絡,勾勒起了云譎波詭的近百年中國歷史。如果說,上官魯氏和幾個大女兒的命運主要展現的是中國現代史,那么兒子上官金童的遭遇主要映照的就是中國當代史。百年中國歷史,在上官一家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中,演繹得蕩氣回腸,令人不勝唏噓。上官魯氏的悲慘命運,源于“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傳統人生觀。為了生一個兒子,她忍辱負重,一連生了八個女兒,才始得上官金童。她把所有的愛都給了上官金童,從而使得幾個女兒如野高梁般蓬勃生長。適逢戰爭年代,幾個女兒為了愛情,各有所靠,又使得她們被各種政治力量所綁架,開始了跌宕起伏的苦難人生。她們一會兒蕩上人生的巔峰,一會兒滑入人生的低谷,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政治的力量無所不在。上官金童在母親的百般疼愛下,喪失了自食其力的能力,終其一生只能吊在女人的奶頭上慘淡度日。最后,當母親去世,又遭遇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的開放年代,他無以為繼,只好皈依宗教,繼續過著吃白食的生活。顯然,上官金童的隱喻意義更為突出,一個本沒有多少傳統基因的“雜種”,欲想在傳統濃郁的氛圍中生存下來,是何等的艱難!歷史的“丑花”終究沒有結出現實的“甜果”。
《四十一炮》是莫言對新時期農村改革開放歷史的反思與追問。通過親歷者羅小通懺悔式的敘述,把當代中國社會步入市場經濟以來農村變革的成與敗、罪與罰、光榮與夢想、貪婪與無恥,形象地展示了出來,表現出了深刻的歷史反思意識和強烈的現實批判力度。毫無疑問,改革開放給中國農村帶來了巨大的利好變化,這從農村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可以看到。但也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也給農村帶來了一些讓人憂慮的副產品。比如,人情的冷漠,人際關系的緊張,欲望的膨脹,以及不擇手段地謀求利益最大化帶來的道德淪喪和雙面人的大量出現。小說中,羅小通通過自己的親身感受和親眼觀察,反映了這一切。如果說,羅小通在五通神廟里向大和尚訴說的關于父母親、妹妹、老蘭、野騾子等的一切話語,是對農村改革開放歷史的追憶,那么,他在五通神廟里觀察到的一切,就是對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現實的總結。原本善良、樸實、厚道甚至有點不開竅的羅通和楊玉珍在被老蘭拖入欲望追求的快車道后,一發不可收拾,朝著欲望的深淵急速滑落下去。雖然羅通最后有所醒悟,雖然羅小通在家破人亡后毅然走上了反叛之路,但是他們都是以付出巨大的代價為前提的。況且,羅小通的反叛并沒有起任何作用。他想斬斷老蘭這棵欲望之根,朝他發射了四十一發炮彈,卻發現根本無濟于事,老蘭照樣活得生龍活虎,戾氣逼人。十年前,老蘭是欲望的始作俑者,十年后,老蘭是欲望的收獲者。十年前,老蘭僅僅是一個屠宰村的村長,充其量兼著村辦華昌肉食品公司的董事長,十年后,老蘭成了著名的鄉村經濟發展的帶頭人,市政協常委。老蘭的不凡經歷和前后變化,說明了欲望在改革開放年代展現出的強大的生命力。欲望本無罪,甚至在人類歷史上起過進步催化劑的作用,但是如果任由欲望泛濫,它也會成為人類精神的一劑毒藥,對生產力產生破壞作用。只不過,徜徉在改革紅利中的人們,尚未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莫言用一部《四十一炮》,向人們敲響了警鐘。
莫言多次說過,自己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農民。當然,這不是說身份,而是說情懷。既然莫言一直把自己當作一個農民,那么他就經常把鄉土當作自己的關注對象,把農村、農民當作藝術反映的焦點。繼《天堂蒜薹之歌》《四十一炮》后,他又寫了《生死疲勞》。《生死疲勞》的時空含量遠比《天堂蒜薹之歌》《四十一炮》遼闊,它從1950年1月1日寫起,一直寫到新千禧年的到來,在長達50年的時間跨度上,全面展現了幾代農民的命運變遷,為當代中國農村、農民書寫了一部歷史與現實交相輝映的傳奇大書。同時,從純粹的農民的情感出發,對當代中國農村的政治生態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與評判。中國農民最在意什么?粗覽一下三皇五帝以來的歷史,就不難發現,中國農民最在意土地!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無論古代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還是近代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即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革命戰爭,農民和土地都是首先考慮并解決的問題。誰解決了土地問題,誰就贏得了掌控歷史變遷的主動權。一部中國歷史,實際上是一部中國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史。就中國當代歷史而言,同樣存在這個規律。哪個階段農村和農業政策把農民和土地的關系理順了,農民就會心情舒暢,社會就會發展,哪個階段出現了偏差,農民就會怨聲載道,社會就會停滯不前,甚至倒退。莫言發現了這個規律,并通過《生死疲勞》活畫出了一部當代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史。他曾說:“幾千年以來中國改朝換代,農民起義,圍繞的核心問題就是土地。土地兼并再均分,反反復復。1949年之后,農村的變遷實際上還是土地的問題……根本問題就是農民與土地的關系。”[9]
《生死疲勞》中的人物,無不為土地生,為土地死,為土地而“生死疲勞”。其中,“單干戶”藍臉給人印象最深。他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土改運動,歷經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直到改革開放,都堅持單干,以不變應萬變,與時局賭博,迎來了一個土地政策的輪回。《生死疲勞》中的洪泰岳,也是一位極具典型化意義的農民形象。如果說,藍臉傳達出的是傳統農民和土地的關系,那么洪泰岳傳達出的就是新型農民和土地的關系。這種新型農民,是在黨領導的農村革命道路上萌芽的,在黨指引的互助合作的集體化道路上成熟的,同時又是在黨的農村土地政策改弦更張之后變得冥頑不化的,某種程度上,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化身、堅定的執行者和后來的陌路人。他與堅持單干的藍臉一樣固執,不過他執著的是集體化道路。現在看來,如何評價堅持單干的藍臉和積極入社的鄉親們在那個時代的選擇孰是孰非,已變得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們都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形象地詮釋出了農民對建國后土地政策的鮮明態度,成了后人認識那段歷史的最好的見證人。
在莫言自己的歷史記憶中,給他留下最深刻最慘痛印象的莫過于計劃生育政策了。同時,這也是共和國歷史上怎么也繞不過去的一段印記。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處于當時的社會現實狀況和對未來的發展考慮,國家開始實施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要求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并作為一項基本國策。雖然獨生子女政策在一定時間內緩解了人口爆炸帶來的各方面的巨大壓力,但從長遠看,也存留了許多隱患。造成勞動力缺乏固然嚴重,而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如養老問題、教育問題、承擔災難問題乃至民族素質問題等等,則更加讓人憂心忡忡。否則,國家也不會一再修改計劃生育政策,不斷增加人口生育數量。但即便如此,計劃生育仍然在幾代人身上留下了終生難以抹去的隱痛。莫言是其中的一個。莫言本來可以和老一輩人一樣,享受兒孫滿堂帶來的歡樂,但嚴厲的獨生子女政策卻使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個人的慘痛記憶和民族、國家的歷史融合在一起,不時地揉搓著他的心,促使他最終寫出了全面反映計劃生育政策的《蛙》,將計劃生育政策的來龍去脈以及給個人、家庭、社會、國家造成的方方面面的問題,形象地描述了出來。其實,莫言對計劃生育的思考,早就開始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還在計劃生育開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他就寫了短篇小說《爆炸》《棄嬰》《地道》,從不同側面對計劃生育進行了藝術反映,顯示出了一個有良心的作家對事關國家、民族大業的大事小情的拳拳之心。
在《蛙》中,莫言并沒有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樣一味地抨擊計劃生育政策,而是比較理性的闡釋了計劃生育政策的誕生與實施過程,讓不明事理的人了解了國家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這從小說中的“我”寫給日本友人杉谷義人的三封信中完全可以看出來。當然,如果莫言僅僅是站在國家的層面上,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解釋計劃生育政策,那《蛙》是完全沒有可能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它的可貴之處在于寫出了計劃生育政策實施過程中,不同身份的人迥然不同的心路歷程,以及后來人們對它的深刻反思。其中,“我”和姑姑的形象比較有代表性。“我”是一個計劃生育的受難者,原配妻子死在引產的手術臺上,續弦妻子又不能生育,“我”只好通過非法的手段來獲取子嗣。雖然一開始“我”不知道實情,但當知道了陳眉代孕的孩子是自己的骨肉時,“我”便不擇手段地同陳眉爭奪了起來。葫蘆僧判斷葫蘆案,高知縣謬斷嬰兒案。孰是孰非,歷史留下了一個解不開的疙瘩。姑姑是計劃生育的堅定執行者,在長達三十多年的從醫經歷中,經她之手做掉的嬰兒達二千八百多個。然而,到了晚年,她卻違背倫理,慫恿“我”占有非法出生的嬰兒。同時違背初衷,在自己的家里捏了二千八百多個泥娃娃,祭奠那些被她親手做掉的嬰兒。如何理解姑姑前后心理和行為的巨大反轉,也只有從她年輕時愛情的不幸遭遇、執拗的性格、嚴酷無情的政治壓力和人性本質的軟弱入手,才能看得清楚,而這些,又包含了怎樣豐富多彩的歷史和現實內涵。
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在歷史和現實之間,總有一根剪不斷、理還亂的紐帶。莫言順著這根紐帶,游走在歷史和現實之間,盡可能地對國家、民族走過的一段路程,以及結出的現實果實,進行形象地評說。其目的,無非是認清過去,立足當下,展望未來。
以上,我們對莫言的長篇小說創作進行了一次回眸式巡禮,足見莫言秉承了中國文人的道義意識和擔當精神。當然,這只是從內容上而言。在藝術上,莫言并沒有拘囿于傳統文學的窠臼,而是廣采博取,為我所用,創造了一個斑斕多彩的藝術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有為道義意識和擔當精神增光添彩的,也有達意未盡的。個中緣由,上文已做過簡單交代,在此不再深入分析。
[1][2][4][5]莫言.在文學種種現象的背后——2002年12月與王堯長談[M]//莫言對話新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75,74-75,79,81.
[3]魯迅.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M]//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180-181.
[6]莫言.作為老百姓寫作——2002年與大江健三郎、張藝謀對話[M]//莫言對話新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496.
[7]張清華.敘述的極限[J].當代作家評論,2003,(2).
[8]彭荊風.視角的癱瘓——評《豐乳肥臀》[J].文藝理論與批評,1996,(5).
[9]莫言.重建宏大敘事——與李敬澤對話[M]//莫言對話新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305.
I206.7
A
1671-4288(2017)03-0014-07
2017-03-16
王恒升(1964-),男,山東濰坊人,濰坊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