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維尼斯特的陳述理論看小說中的對話結構
張怡
秉承索緒爾“語言作為話語進入行動”的主張,埃米爾·本維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在其兩卷本《普通語言學問題》(1966年,1974年)中提出話語是“行動中的語言”這一重要論斷,并在研究中更進一步將話語研究與陳述行為緊密結合,指出話語即“陳述的外現”,而陳述意味著從“語言”到“話語”的個體轉化這一重要的事實。本氏認為,陳述是個體語言的實現過程,它使得說話者將語言的形式配置占為己有成為了可能,也使得語言和世界有了能產生關聯的中介。換言之,即在陳述行為發生以前,語言只代表一種語言的可能性,只有憑借陳述行為,語言才可能在話語時位中成為現實。說話者一旦進入了陳述之中,便會建立起一種對話關系,使受話者也進入陳述,最終構建起一種本維尼斯特稱之為以“我:你”極性(lerapport je-tu)為基礎的主體間交流,而由這種主體間的交流關系,又自然而然地引出一個關于“陳述的形象框架”(cadrefiguratif)的問題。①Benveniste,Emile.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II.Paris:Gallimard,1974,pp.79-81. 后文凡出自本維尼斯特《普通語言學問題》的引文,將隨文標明出處頁碼,不再另行作注。通過論文《陳述的形式配置》(L'appareil formel del'énonciation),本維尼斯特針對陳述行為的定義、實現情境、形式特征及其得以實現的框架結構,進行了明晰的闡述。他強調陳述是以語言為工具的說話者的行為,是說話者依據自身需求發動語言的事實,簡言之即“通過個體使用行為得以實現的語言的實際運用”。(Benveniste:80)
縱觀本維尼斯特的陳述理論,首先不同于其他語言學家,他將說話者這一陳述的必要條件的參數引入研究視野。本氏特別指出,對陳述行為的考量必須置于標志說話者與語言關系的語言特征之下,這一在日常使用中司空見慣的語言現象,恰恰在語言學理論研究領域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通過陳述行為,“說話者將語言的形式配置占為己有,通過某些特定標志并借助某些輔助手段,來陳述自己作為說話者的立場。”(Benveniste:82)陳述行為一旦發起,說話者同時在其對面又樹立起一個他者——不論后者是否在場,任何陳述行為都必定預設一個受話者。而在說話者動用和占用語言的過程中,語言一旦被用來表達與世界的某種關系,又勢必引入“指涉參照”(la référencedel'énonciation)這一個體語言實現的必要條件。一方面,陳述將說話者引入其語言,通過話語進行指涉,使每一個話語時位都構成一個內在的參照中心;另一方面,說話者和受話者雙方為實現會話的語用協調,又存在著進行共同指涉的必要。因此,指涉參照與說話者、受話者三者同為陳述行為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支配陳述行為的這一整套參照機制則主要由人稱標記(我-你)、指示標記(這個、這里等)以及關于時間形式的表述聚合三類特定形式構成。不同于有完整恒定位置的語言實體,這部分語言的特定形式只源于陳述行為本身,并且只涉及說話者的此時此刻。由于它們的存在,說話者與其陳述之間才建立起某種恒定且必然的關系。
在陳述行為中,無論受話者是真實的抑或想象的,無論是以個體的形象出現還是以集體的形象出現,陳述行為的特征都強調了說話者和受話者之間的話語關系,即一種被稱之為以“我:你”極性為基礎的主體間交流。這種主體間的交流關系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又引出關于陳述的形象框架(lecadreformel dela réalisation del'énonciation)的問題。本氏指出,“作為話語形式,陳述設立了兩個同樣必不可免的‘形象’,一個是陳述的來源,另一個是陳述的目標。這就是對話結構(structuredu dialogue)。兩個形象處在交談者的位置上,輪流充當陳述的主角。這個形象框架是隨著陳述的定義而必然產生的。”(Benveniste:85)簡言之,本氏認為陳述的形象框架即為對話結構;陳述外的對話抑或無對話的陳述都不可能存在。
至此在這一篇《陳述的形式配置》中,本維尼斯特試圖在語言內部從陳述所實現的個體外現出發,去勾勒陳述的形式特征的目的已基本達成。然而在《陳述的形式配置》的文末,本氏又提出關于陳述理論的一個新問題,即區分口頭陳述(l'énonciation parlée)和書面陳述(l'énonciationécrite)的必要。因為“后者是在兩個層面上運行的:作家通過寫作來自我陳述,而在其作品內部,他又讓一些個體進行自我陳述。”(Benveniste:88)他認為如果從其所勾勒的陳述形式框架出發,對復雜的話語形式的分析還大有可為。
因此,本論文將嘗試從本維尼斯特在此處留下的開放式提問入手,運用其陳述理論與對話結構,嘗試按照書面陳述中的陳述層面、陳述對象、對話結構的實現形式來重新梳理小說中的對話結構,同時并對小說寫作敘事策略的變革進行思考。①本文分析所用材料,主要以法語小說為主。
一、小說中不同對話結構下的陳述層面和陳述對象
正如本維尼斯特所指出,書面陳述存在兩個層面,一是作家陳述的層面,另一是作品內部某些個體的陳述層面。在小說作品中,第一陳述層面即為作家寫作陳述的過程,而第二層面則涵蓋小說敘事者和人物的陳述過程。顯然這兩個層面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出現重合:許多帶有自傳色彩或是回憶錄性質的小說,其內部作者、敘事者與人物三者的合一即體現了作者陳述與作品內部某些個體陳述層面的合二為一,例如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的自傳體系列小說《位置》(La Place)與《一個女人》(Une Femme)中,作者即敘事者即主人公分別講述了其父母一生的故事;而在克里斯蒂安·博班(Christian Bobin)的小說《生命之上》(La Plusquevive)中作者(同時也是敘事者和主人公)則回憶了他女友吉斯蓮(Ghislaine)的一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一般的自傳或回憶性質的小說,這部小說不是以讀者作為“你”,而是以作者已故的女友為對話目標“你”的。
由此,便引出了小說中書面陳述的另一個特點,即陳述對象的多變。不同于口頭陳述,擁有兩個陳述層面的書面陳述,其陳述對象也存在某種多變性。在作者寫作的陳述層面上,陳述一般以讀者為陳述目標,即讀者處于對話結構的另一端。而在書面陳述的另一層面——作品內部一些個體的自我陳述中,陳述對象的問題更為復雜。
首先,需要將這一問題,按陳述的來源進行區分,再按陳述對象的不同進行劃分,如此可以得到敘事者向讀者陳述、敘事者向人物陳述和人物向人物陳述、人物向敘事者陳述四大類陳述模式。其中敘事者向讀者陳述可算是小說寫作最經典的對話模式之一,同樣人物向人物陳述也是小說組成的基礎部分,只要人物間有言語的交流,那么小說中就必定會有人物向人物的陳述出現。至于敘事者向人物陳述和人物向敘事者陳述這兩種陳述模式,其出現必須以一個條件為前提:即敘事者在小說中必須也是人物,否則兩者會因不處于同一對話層面而無法對話。在以上四大類陳述中,無疑敘事者向讀者陳述這一陳述模式在傳統小說中占據了敘述的主導地位,而其它三類陳述皆可被嵌套包涵于其中。喬治·杜阿梅爾(Georges Duhamel)的《子夜的懺悔》(La Confession deminuit)以及普雷沃神父(L’abbéPrévost)的《瑪儂·列斯戈》(Histoiredu chevalier Des Grieux et de Manon Lescaut)便是同時包含這四類陳述的典型例子。《子夜的懺悔》中的主人公即敘事者薩拉萬(Salavin),不斷地以讀者為陳述對象講述自己的經歷并進行自我的心理剖析,同時在他的陳述中又充滿了他與其他人物的雙向對話交流以及其他人物間的對話。《瑪儂·列斯戈》的敘事者在旅途中遇到騎士德?格里厄(Des Grieux),后者向他講述自己和瑪儂·列斯戈(Manon Lescaut)的故事,在敘事者向讀者陳述的過程中又包含人物德?格里厄騎士向敘事者做的陳述。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自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包括福樓拜、于斯曼、左拉等在內的一眾頗具現代意識的小說家,他們在寫作過程中有意顯現出對使用自由間接引語(discoursindirect libre)的某種偏愛。而這一由自由間接引語在文本中產生的特殊美學效果,正源于陳述層面的某種曖昧不明。由于標志陳述行為的動詞缺失,本應歸于人物陳述層面的內容經轉寫后被直接置于敘事者或是作者陳述的層面。陳述邊界的不確定與模糊,致使多層敘事聲音在話語時位上產生交錯。巴赫金在《小說話語》中提出“混合陳述”(énoncéhybride)的概念,認為混合陳述的話語“按照語法(句法)標志和組成標志,只屬于一個說話者,但事實上卻混雜著兩種陳述、兩種說話方式、兩種風格、兩種‘言語’”。①Bakhtine,Mikha?l.Esthétiqueet Théoriedu Roman.Paris:Gallimard,1978,pp.125-129.混合陳述在不同聲音、不同陳述之間并不存在任何句法形式或是結構形式上的界限,兩者的分界甚至是有意識地被處理成撲朔迷離、搖擺不定的。杜克洛(O.Ducrot)在此基礎上借用巴赫金的研究,針對陳述研究提出“復調”概念,②Ducrot,Oswald.Le Dire et le Dit.Paris:Minuit,1984,pp.203-204.即在敘事者-說話者的話語內可能存在囊括兩位陳述者(作為敘事者的陳述者和替人物發聲的陳述者)的特殊現象,因此在小說陳述中,“簡單過去時敘事與自由間接引語共存的復調現象并非不可能出現”。③Ducrot,Oswald.?Analysespragmatiques.?Communications32(1980),p.11.顯然兩者談論的問題關鍵最終都回歸到陳述層面的問題上。正是小說書面的陳述層面間發生異常的混淆情況,才使得自由間接引語能夠在小說陳述話語中制造出特殊的文體效果。
二、小說中對話結構的不同實現形式
上文利用陳述理論梳理了小說中不同對話結構的陳述層面和陳述對象,需要注意的是,關于小說中對話這一陳述的形象框架,其實現形式卻不只是我們日常所見的會話形式那么簡單。誠然,常見的會話形式是小說中對話結構最常見的實現形式。但在這里,我們想將這種最普遍的形式放在一邊,先來考察一下小說中那些不那么常見的對話實現形式,更準確地說,即小說中普通會話形式的某種變體——即日記體或書信體。
與普通的日常會話一樣,日記和書信都屬于陳述理論下的對話結構。書信體是對話結構的物質化形式,拉克洛(Laclos)的《危險關系》(Les Liaisonsdangereuses)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至于日記,不論寫日記者的陳述對象是真實的存在,還是想象的產物,都不會改變日記體之下對話結構的實質。在安德烈·紀德 (AndréGide)的《田園交響曲》(La Symphonie pastorale)中,牧師的日記看似沒有明顯的陳述對象,在寫作時既沒有日后公開的打算,也不以讀者為陳述對象。但這并不能說明牧師的日記沒有陳述對象,在這種情況下毫無疑問牧師是以自己為陳述對象的。他自己既是說話人,又是受話人。在陳述的過程中,牧師本人一分為二,既是陳述的來源,又是陳述的對象。書信和日記這兩種對話結構的變體形式在莫里亞克(Mauriac)的小說《蝮蛇結》(Le N?ud devipères)中得到完美的結合。小說的前半部由主人公寫給妻子的信組成,主人公出于怨毒,要她在自己死之后看到這封正在寫的信;但出乎主人公意料之外的是,妻子居然死在自己的前面,因此小說接下去的后半部轉由主人公的日記構成。書信和日記這兩種對話結構的變體形式在這里合理且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堪稱小說形式探索過程中的經典之筆。
在分析完小說中對話結構的兩種邊緣實現形式后,再讓我們回到小說文本中對話結構最普通最常見的會話形式上。這一形式幾乎在所有小說中都有出現,其實現形式一般不外乎以下模式:
A說:“……”
B說:“……”
A說:“……”
B說:“……”
……
……
依此類推,直至對話結構結束。如果出現多人會話的情況,那依此類推加入C說、D說、E說……即可。這種對話模式的使用是廣泛的,甚至可以說直至19世紀這一模式在小說創作中一直都幾乎是無處不在的。這里僅分別選取司湯達的《紅與黑》和巴爾扎克的《玄妙的杰作》(Le Chef-d’?uvreinconnu)中的一個對話片段為例:

①Stendhal.Le Rouge et le noir:chronique de 1830.Paris:Editions Garnier Frères,1950,pp.26-27.
在正文中為保持對話結構原有的形式,故引用法語原文,而將譯文附于附錄中,以下的法語引文處理同此處,不再另行說明。
在德·雷納爾夫人和于連首次相遇的這一對話場景中,雖然只有兩人參與對話,但從用下劃線作出標識的部分來看,可以發現作者幾乎是不厭其煩、一板一眼地遵照這一模式進行寫作的(司湯達在這個簡單的對話場景中居然沒有省略任何一個“XX說”!)。至于巴爾扎克的小說《玄妙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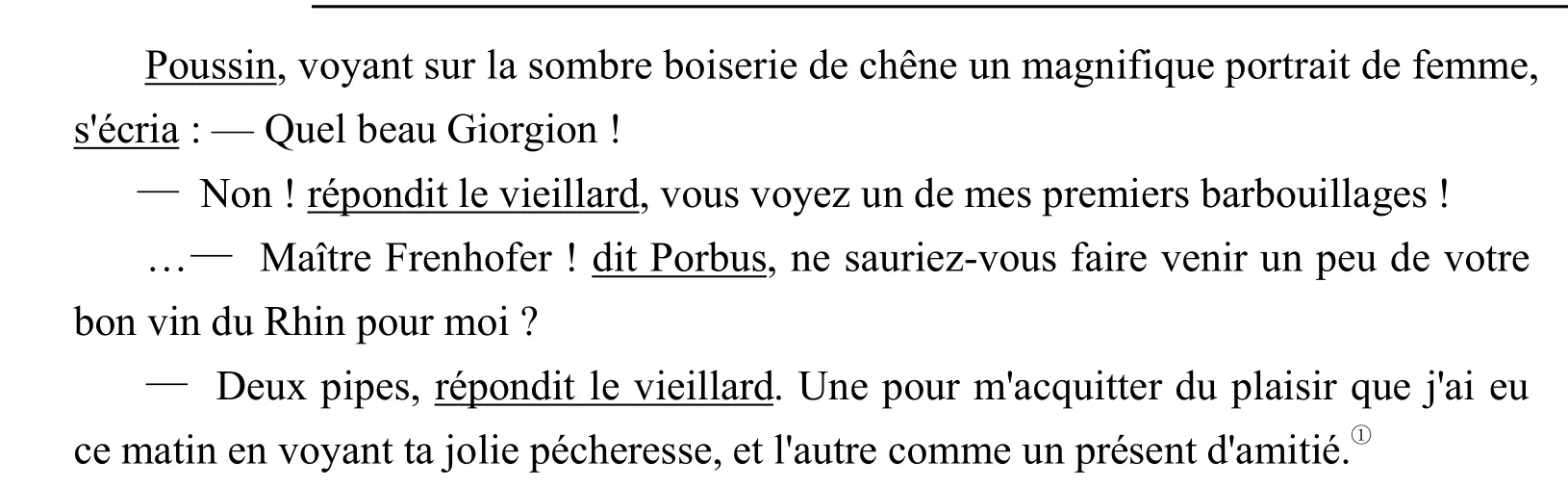
雖然此處出現的是存在兩個對話者以上的多人對話場景,但巴爾扎克使用的對話模式并沒有大的改變,完全可以被視為兩人對話模式的簡單升級類推。②但同時也由于在該對話場景中,出現了三個參與對話的人,所以巴爾扎克每次不厭其煩地在言說的內容前標明說話人究竟是誰,還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對于這種在對話結構中不厭其煩地指明是“誰在說”的書寫模式,錢鐘書亦曾有觀察,他指出“西文有引語符號,記言卻未克擯‘曰’、‘云’、‘問’、‘答’等字而不用”,③錢鐘書:《管錐編?補訂重排本(一)》。北京:三聯書店,2001,472頁。“小說里報道角色對話,少不得‘甲說’、‘乙回答說’、‘丙于是說’那些引冒語”,于是“外國小說家常常花樣翻新,以免比肩接踵的‘我說’、‘他說’、‘她說’,讀來單調”。④錢鐘書:《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2002,98頁。如上文所舉《玄妙的杰作》一段對話中,巴爾扎克便前后共使用了s'écrire/répondre/dire/reprendre四種同樣表現陳述行為的不同動詞。
不過,依照法文對話的書寫習慣,除了上文所提及的一板一眼“A說:‘……’B說:‘……’A說:‘……’……”的對話模式外,在許多小說中尤其是現代小說中的對話,還可能采用一種更簡單更靈活的寫作模式,即將人物對話單獨分行排版,用破折號(tiret)引導直接引語,以達到使對話部分與純粹的敘事部分分開的目的;相較之下,上文提及的“A說”“B說”輪替出現的對話寫作模式,似乎則更多是出于希望突出在敘事行文中插入人物對話的考慮,因此特意使用引號并配合以“他說”(dit-il)之類提示語來標明直接引語的插入。
在此,隨意抽取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的小說《地鐵姑娘扎姬》(Zazie dans lemétro)中一段對話為例。⑤Queneau,Raymond.Zaziedanslemétro.Paris:Gallimard,1996,p.132.扎姬和莫阿克寡婦的對話來回有十數次之多,但作者只在三處標明了說話者(這三處標志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應把作者添寫人物說話神情的意圖考慮在內)。不難發現,這樣的省略處理并不影響讀者理解。因為對話結構一旦被發動,在兩個對話者交替進行陳述的過程中,兩者便依次在自己的周圍形成一個“場域”。讀者只要通過兩者所使用的對對方的稱謂(在上文中,扎姬用您vous來稱呼莫阿克寡婦,而莫阿克寡婦用你tu來稱呼扎姬)、對自己的稱呼、指示詞甚至是說話者的口頭禪(如上文中扎姬的口頭禪seulemon cul)或是說話時所用語言的語級(如扎姬所用的俚語語級),就可以很容易地進入該對話結構。盡管對話結構的實現形式中缺省了標識陳述行為的“A說”“B說”,但讀者仍可以毫不費力地識別出說話者和受話者在對話結構中的轉化過程,弄明白兩人究竟是如何交流的。
對話書寫形式中,這一特殊的、將指示詞“XX說”進行省略的現象,正可以用本維尼斯特在《陳述的形式配置》中所指出的陳述概念來解釋。陳述在實現的時候需要滿足三個初始條件:即說話者標明自己為說話者,并承擔起語言;說話者為陳述預設一個受話者;說話者通過話語進行指涉,并使受話者一方能夠參與共同指涉。在上文所述的情況中,在讀者的閱讀過程里幫助理解、起到作用的,正是陳述的那第三個初始條件:“指涉參照”。作為人稱的“我”(je)、作為空間的“這里”(ici)和作為時間的“現在”(maintenant),三者一體,共同構成說話者和受話者“指涉參照”的出發點。“我-這里-現在”三個因素產生于個體性并且只發生一次的陳述行為,因此這三個因素在每一個話語時位之下都是獨一無二的,每有新的陳述產生,隨即被重新生成,且每次都具有新的意義。而對話中的人稱代詞、指示詞和時態又分別構成了這三個因素在陳述中的體現。①對話中的人稱代詞、指示詞和時態因此有別于語言中有完整而恒定位置的實體,一般只存在于陳述所建立的“個體”網絡中,不能在語言的認知使用中產生并發揮作用。所以,通過對話中的人稱代詞、指示詞以及時態,讀者便可反推出對話中每一次陳述行為的發起人究竟是誰。簡言之,盡管上文對話結構內部并沒有出現“A說”“B說”的標識物,但其實每句對話內都已包含“A說”或是“B說”的標識,只不過呈現的方式有時較為明顯有時較為隱形罷了。也因此,“A說”“B說”這樣的標識物在小說對話結構的實現形式內的缺省,才不會影響讀者的理解,因為在事實上標識陳述行為的“XX說”從未離開過這一對話體系。
當然,如果在同一個對話場景中,出現多人參與對話的情況,那么又可能是另一種情形。例如在讓·吉奧諾(Jean Giono)的小說《山岡》(La Colline)中有這么一段對話。②Giono,Jean.Colline.Paris:Bernard Grasset,1929,pp.82-84.在對話場景的前半部分,作者采用的對話模式與上文提及《地鐵姑娘扎姬》的選段沒有什么大的不同。參與對話的若姆(Jaume)和雅內(Janet)僅僅分別通過他們在對話中對對方的稱呼(黑體部分),就很容易地讓讀者識別出他們兩人在這一對話結構中的各自位置。但是在該場景快結束的時候,最后卻出現“若姆(Jaume)低聲問道”(下劃線部分)這樣的指示詞。乍一看下似乎是有些奇怪,但如果將上下文聯系來考慮,便不難理解了:這是因為此處有第三者瑪格麗特(Marguerite)的加入,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她打破了若姆和雅內間原有的對話結構,而之后由她和若姆兩人開始了另一個對話結構。如果在這里沒有出現“若姆問”這樣的標記,那么讀者將既無法確定這句問話是由誰發出的,也無法確定它是指向誰的。所以,由此看來,如果在這種簡約化的對話模式下,突然出現“XX說”的指示詞,那么很可能是作者發現此處如不向讀者交代清楚說話者的身份,將會影響讀者的閱讀。
當然如果更仔細地觀察這一段落,不難發現瑪格麗特在第一個對話場景中的插入其實要更早些,即當雅內說“格麗特,水”(Gritte,de l’eau)的時候,這句話已經將她拉入對話,并改變了原有的對話框架。那么為什么此處沒有出現必要的提示詞“XX說”呢?筆者以為,這是由于雅內在說話時,多加入一個呼語“格麗特”造成的。瑪格麗特是雅內的女兒,所以雅內會用昵稱來稱呼她。就由于這個呼語背后隱藏著兩人的身份關系信息,所以反倒沒有必要再使用“XX說”的標記來特意點明受話者是誰。對于讀者而言,只要看到這個隱含著對話雙方關系的稱呼,即使此時沒有“XX說”的標記出現,他們的閱讀也不會受到絲毫影響。
本維尼斯特陳述理論內的“參照指涉”系統概念,后來在巴赫金那里又被進一步擴大邊界。巴赫金提出陳述行為“語言環境”的概念,用來標識陳述的暗指部分。他認為陳述行為的語言環境意味著對話者之間的共同視野,通常由時空、語義和價值成分構成①[法]托多羅夫:《巴赫金、對話理論及其他》,蔣子華等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232-233頁。。這一“語言環境”的提法,等于將本氏“我-這里-現在”三位一體的指涉概念進一步擴大,把對話結構內部所有包含著的說話者的信息都囊括在內。上文示例中提到說話者扎姬所使用的俚語語級以及口頭禪,雅內所使用的“格麗特”的昵稱,這些隱含說話者和受話者身份信息的因素,不能被本維尼斯特的“參照指涉”概念所解釋涵蓋,但是正好落在經過巴赫金擴展補充之后的“語言環境”的概念區域內。
至于為何這種省略“XX說”的對話書寫形式會在現代小說中更廣泛地出現?也許,這與近現代以來眾多小說家在小說中盡力減少敘事者的介入,并力圖拋棄全知敘事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這樣的對話模式在客觀上將敘事者的介入影響降到最低,為讀者們留下一個沒有敘事者,似乎就是人物們在那里直接陳述的閱讀印象。
綜上所述,本文從本維尼斯特在《陳述的形式配置》一文中最后留下的開放式結尾出發,根據語言學家對口頭陳述和書面陳述的區分,并利用該文所勾勒的形式框架,嘗試對小說所包含的書面陳述的復雜話語形式進行分析。文章以一眾法語小說為分析對象,運用本維尼斯特關于陳述和對話結構的理論,最終按照書面陳述中的陳述層面、陳述對象以及對話結構的實現形式的不同,來重新梳理和歸類小說中的對話結構。而在分析小說中對話結構的實現形式時,我們發現由于交流中主體間性的存在,因此小說對話結構的實現形式中,有時存在著說話人標志“XX說”缺失的特殊現象。陳述行為標志物“XX說”的存在并非是必需,這種更簡潔的對話書寫形式背后,更隱含著敘事者在書面陳述中暫時隱身現象的小說敘事革新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