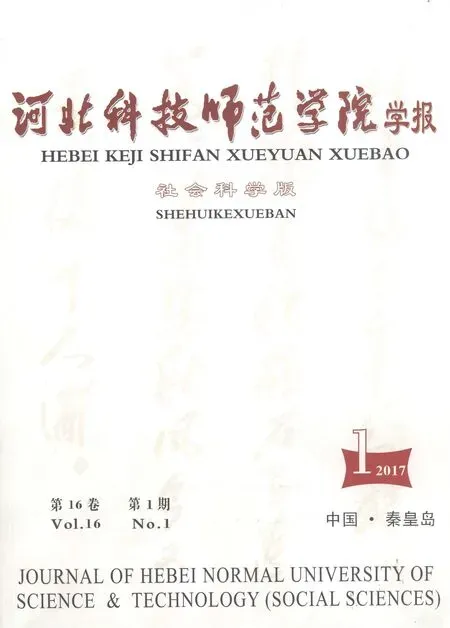論杜夫海納的語言觀
董惠芳
論杜夫海納的語言觀
董惠芳
(渤海大學文學院,遼寧錦州121013)
杜夫海納的語言觀是對20世紀語言學轉向的回應。他主張從本體論的角度看待語言,不再把語言僅僅看作客體和工具,而是強調人與世界的平等,語言是人與世界的基礎,世界向我們說。他還認為人與世界的根源在于造化自然,詩喚醒了造化自然的詩性狀態,詩是人類的初始語言,詩使人類與世界回復到了最自然的狀態,這正是藝術的意義。杜夫海納的語言觀依然關注人與世界的關系,并貫穿著超越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
杜夫海納;語言學轉向;索緒爾;藝術;人與世界
作為現象學美學的集大成者,杜夫海納的國際聲譽主要來自他在美學領域的貢獻。因此,無論國內外,研究者們都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他的美學理論上。事實上,杜夫海納的語言觀也是他整個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杜夫海納對語言問題的關注,持續體現在《語言與哲學》一書、論文集《美學與哲學》(三卷本)和專著《詩學》中。《語言與哲學》是杜夫海納1959年秋在印第安納大學的公開演講,在此書中,他主要研究的是語言哲學。在《美學與哲學》(三卷本)、《詩學》中,有關藝術與語言的思考占據了一定的比例。這樣,哲學語言觀和藝術語言觀共同構成了杜夫海納的語言觀。
杜夫海納的語言觀是在20世紀語言學轉向的大潮中誕生的,不僅與結構主義、符號學具有密切關聯,而且也與現象學的語言觀一脈相承。因此,全面、系統地研究杜夫海納的語言觀,一方面,可以厘清杜夫海納語言觀與其整個美學理論體系的關系;另一方面,有助于認識現象學語言觀的演變,同時深化語言學大潮中現象學與結構主義、符號學之間的關系的認識,從而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揭示20世紀的語言學大潮。
一、杜夫海納的哲學語言觀
自從柏拉圖的《克拉底魯篇》以來,語言已經成為一個哲學話題,19世紀末20世紀初,邏輯學和語言學的深入發展,為語言哲學的產生奠定了直接的理論基礎。杜夫海納對語言的哲學思考,是對20世紀語言學轉向的回應。他注意到語言學的進步、符號邏輯的發展,以及哲學反思都推動了這一轉向。杜夫海納將所有有關語言的哲學反思總結為兩種趨向:一是朝向語言的本體論,一是朝向言語的現象學。在他看來,前一種趨向強調的是語言的力量,即通過語言揭示存在,顯示意義,如海德格爾、謝林、黑格爾、赫拉克利特等人的研究。杜夫海納本人選擇的是后一條道路。在《語言與哲學》一書中,他以“語言與語言學”“語言與邏輯”和“語言與形而上學”三個部分完成了他的言語現象學研究。杜夫海納認為,言語的現象學將使我們返回到語言的形而上學領域。而且,現象學與本體論能完美地相符合。他還相信這一條道路會帶領我們到達語言自身的源泉,最終循言語之跡返回詩,這也使他最終轉向了藝術與語言關系的思考。
杜夫海納首先審視的是語言學領域的語言研究,他最為關注的是索緒爾的語言學。他雖然承認索緒爾為現代語言學制定的基礎規則具有開創性意義,但他更意在指出索緒爾語言學的不足。索緒爾區分了語言與言語,并把言語從屬于語言,于是,語法學在地位上便優越于語義學。因為語義常常帶有偶然性,而一種給定的語言卻可以是一個確定的客體,它相對穩定,并獨立于特定的環境,有字典和語法可依據。但在杜夫海納看來,語言作為客體,關注的就不是它的內容與意義,而是它的物質基礎,也不再關注它的獨特之處與發音,或者它的語法順序,而是僅僅尋求它們的共同之處。而且,把語言視作一個客體就是把它視作一個系統,也就是說,它的各要素被法則支配構成了一個整體。
對上述問題杜夫海納都很不滿,他認為索緒爾的語言思想中存在某些模糊之處:其一,支配各要素的法則模糊不明。其二,系統思想本身也存在模糊之處。而事實上,區別規則系統和要素系統的不是規則和要素,因為每一個系統都包括這兩者。杜夫海納又進一步質疑規則系統和要素系統:“規則是任意的,其總體性既不連續,也不徹底、飽滿。相比較而言,一種給定的語言的各要素構成的領域卻真是一個系統,它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典型的結構。”[1]24即對于語言學來說,規則系統其實是不存在的,而“結構”這個概念也是模糊的。根據杜夫海納的理解,結構的概念一方面有生物學的內涵,另一方面,又有數學的內涵。這樣,結構實際上包括了兩種不能同構的模型。
更重要的是,“結構”這個概念逐漸被構想成了一個封閉的系統,這一點的影響尤為巨大。格雷馬斯曾對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模式所引發的影響進行了概括,他稱之為“兩輪光輝”:第一輪主要發生在社會學和精神分析學領域,特點是根據某一學科的需要以通俗化的名義對語言學中具有方法論意義的結構進行扭曲和變形,甚至不惜抹去語言學中某些基本概念之間的根本對立。另一輪光輝是方法論上的,不過,并不是標準意義上的方法借用,而是一種從認識論角度所取的態度:若干模式、若干發現程序的移植,極大地豐富了梅洛-龐蒂、列維-斯特勞斯、拉康、巴爾特等人的思想[2]。無疑,索緒爾語言學的大肆擴張都是以某種抽象的結構和模式的應用為前提的,因此語言學中的二元對立結構在各種社會文化領域中被應用起來,杜夫海納譴責“結構主義與控制論結盟。語言學加入了實證主義的時代”。杜夫海納的批評揭示出索緒爾語言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忽略生動的言語活動而奔向言語背后恒定不變的語言規則與結構。這一點既使語言學到處攻城略地,也導致它常常受到人們的指責。
運用結構理論,結構主義總是企圖發現“科學的”“客觀的”人文科學事實,在杜夫海納看來,這是異常危險的:“結構分析處于危險之中,即屈服于用本體論的觀點看待純形式的誘惑。那么,這個理論掉進了它自己的陷阱。……一個人必須注意不要在現實之上設計形式結構,也不要忘記物質結構的特異性和多樣性。……一旦一個人將此定義為一種無意識的邏各斯,而這種邏各斯形成了整個文化的特定的、邏輯的形式,那么,一個人不是正在創造一個只是人類學家自己的邏輯操作計劃的客體嗎?這正是一個人自稱發現了他已經放在那里的物體。”[1]38這無疑是說,結構主義按照自身的邏輯提前預設了自己想要的結論。德里達的批評意見與杜夫海納有相似之處,他說:“結構首先說的是一種有機的或人造的工程,一種裝配、一種建構的內在統一性;是由統一性原理支配的工程,是在特定地點建立起來的、可見的建筑。”[3]這就表明,結構主義試圖達到的客觀、科學的結果實則都是精心設計的結果。
杜夫海納還非常嚴肅地批評了語言學領域中忽略語義的情況。他指出,受索緒爾的影響,結構語言學從一開始就忽略了語言的現世維度。語義學通常是被結構語言學忽略的,因為結構主義處理的是符號,而非意義。意義被減少到了對聲音的清晰理解,好像僅有的問題就是正確傳送或登記信息,而不必說明或解碼。而實際上,語言具有突出的多樣性,這一點不僅影響語言,還有文化、宗教、科學、技術、意識形態,甚至家庭關系和社會制度。語言與社會制度總體性的聯系在人類學的研究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但這二者之間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杜夫海納重點分析了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他認為列維-斯特勞斯所開創的道路無論如何都是值得贊許的,但這種方法必然帶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當運用語言學精確分析語言的時候,文化必須服從于僅有的觀測技巧,這一點尤其在考慮其總體性時表現得分外突出。因而,結構人類學的結論只能是總體文化的部分表達,它被迫遺失了部分更好的意義。
與索緒爾的語言學和結構主義的見解相反,杜夫海納特別強調意義對于語言的重要性。索緒爾批判語詞中心論,主張代之以整體論的意義理論。而杜夫海納認為語詞中心論與意義的整體性并不沖突,甚或意義整體性以語詞中心論為前提:“人們能從無中引出意義嗎?不能。要給詞以意義,單靠句子是不夠的(神話對神話素、旋律對音符、影片對一組鏡頭、繪畫對色彩也都是不夠的)。句子要有意義,詞必須先要有意義。”[4]149詞與句子的意義某種程度上是互相依賴的,詞語不僅與整個語言體系,而且還與它指向的事物本身是姻親關系。語言之所以能使人與世界、人與他人的交流得以實現,因為意義啟用的是人與世界之間的聯系。
杜夫海納的言語現象學對于語言與邏輯的關系也予以重新闡釋。邏輯實證主義者主張哲學問題歸根結蒂是語言問題,因此,他們把對語言進行有效的邏輯分析以澄清誤解當作哲學研究的中心任務。杜夫海納發現“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論文》(Tractatus)中曾經遇到過這個問題。因為邏輯創造邏輯語言,他曾一度認為邏輯的語言就是語言的邏輯,以后他才明白話語表現的是另一種邏輯,這種邏輯隨語言的運用而千變萬化,同時也是令人困惑的。”[4]78他聲稱:“現象學將重新發現內在于語言的邏輯。但它將在人與世界的聯系的更普遍的哲學中為此尋求辯護。正是在那樣的聯系中,語言找到它的根源;正是在同樣的語境中,語言可以被自然地說出。”[1]39由此可知,語言的邏輯應該從人與世界的聯系中去探尋,他的研究方向完全不同于邏輯實證主義。
關于邏輯的闡釋,杜夫海納主張回到亞里士多德的源頭,他說:“我們真的遠離了邏輯的傳統概念。……亞里士多德主義的邏輯制定的規則不是主觀任意的選擇的結果,而是反映了存在的本質。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是那樣的邏輯預設了語言與存在之間的不言而喻的協議:語言是真實的并且是真實的條件,因為它是存在的語言并且它的規范從存在出發。”[1]44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傳統的邏輯概念認為語言與存在之間具有不言而喻的關系,但形式邏輯在后來逐漸成為亞里士多德邏輯的核心,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種邏輯在認識和強調言辭本身的客觀邏輯結構上具有強有力的作用,杜夫海納不能認同的正是這種以追求真理為目的的語言分析邏輯。
杜夫海納把語言看作人與世界關系的紐結,與語言相比,他更為關注活生生的言語現象,他說:“我們將注意力集中于意義的語言所有權,集中于人類制造的語言的使用——那就是說,集中于說話的人,集中于說的語言本身。”[1]70那么,為什么要重視“說的語言”呢?他這樣解釋:“經驗是我們與世界第一重要的聯系,這正如在感知中生活和用言語來命名。因為言語是與世界的最初始的結,這個世界與感知同在,并且不能脫離它。第一意識(承擔邏輯的意識)是一種‘說’的意識。這就是為什么邏輯語言植根于自然語言,正像是形式思想植根于直覺。現象學,被視為先驗邏輯,邀請我們從被說的語言回到說的語言,正在說的語言,因為人們說,而且因為這個世界向人們說,這一點,反過來,因為人與世界真正的聯盟甚至從誕生以來已經形成。”[1]67-68這說明杜夫海納關注的是活生生的現實生活中的正在被使用的言語,這樣的言語中包含著我們對世界的經驗與感知,“說”的意識本身承擔著說清楚的目的,內在地承擔著邏輯的意識,這種極為平常的現象中恰恰蘊藏著邏輯的根源。像英美分析哲學家那樣冷靜客觀地解釋語言中的邏輯,杜夫海納是完全不能贊同的。
杜夫海納還從形而上學的高度對語言展開了思考。與傳統的把語言看作工具的觀點不同,他認為語言與說話者是一體的,二者不可割裂。在《語言與哲學》一書中他反復表示如下意思:“當我說的時候,我就是我說的話;我與我的話變成一體。當然,正如我已經說的,說話把我放到了與我所說的一定距離處。但在我的意識與我的言語之間根本沒有距離:我與我用的語言是一個整體。”[1]84語言不可證明同一于任何一種工具,語言是人與世界之間的中介,通過語言,人與他人、自己和世界得以交流,但人不是通過語言而存在,人與他的語言就是一個整體。海德格爾認為,人之說是無意義的,遮蔽了語言之說,與之不同,杜夫海納卻充分肯定了人之說。
不僅人之說是有意義的,我們使用語言的方式揭示的是我們思考的方式,因此,意識到這個世界其實也是對自身的意識,“從一種生存狀況到一種思維方式的轉換怎么可能?依靠語言是可能的。正是語言引進了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必不可少的距離。正是利用語言的調解,間隔(interval)被創造出來,在那里思想開始起作用。然而,我們將很快看到,調解是一個——同時分離與統一。假如語言在世界與我之間挖了一條溝,它也在上面架了一座橋。詞語插入了事物與我之間。但仍然,詞語沒有恢復事物的實際呈現,它現在已經變成了意義。”[1]73這就是說言語表達與思維具有同一性,這為杜夫海納提出的“前意象”(preimage)奠定了必要的前提。
關于語言與世界的基本關系,杜夫海納并不承認世界變成了語言的對象,他強調的是世界在說,這是最為根本的。“自然語言既不是由智力組織也不是由情感推動。它表達的不是人的本質,而是造化自然本身。說,首要的是讓世界為自己而說,就好像它通過詩為自己而說。”[1]97-98世界之說是通過“前意象”展開的。“在這種我們稱作前意象的水平上,人類感知而不是看到。但在情感上已經總是有一種意向性:情感不是無可救藥地疏遠于它的主體性。人類感到的是打動他的東西,是向他說的東西。”[1]94-95“世界利用來宣稱自己的語言已經呈現,同時還有情感。情感在話語(words)中表達自己的同時,它使自己在意象中更明確。我說前意象,因為世界的這些粗糙的意象沒有描繪明顯的可識別的對象。”[1]95由此可知,“前意象”是人類因被打動而模糊地感知到的那些關于世界的初步意象。“前意象”實則揭示了人與世界的原初聯系,這種聯系證明,在根源上人與世界的關系不是對立的。作為人與世界原始交流的裝置,詩是語言的第一形式,因此,藝術與語言的關系必然上升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二、杜夫海納的藝術語言觀
在索緒爾語言學的巨大影響下,當巴爾特的符號學將藝術視為語言時,杜夫海納對于藝術與語言的問題進行了專門的研究。根據索緒爾的語言學,人們總是按照語言的特殊模型去給意義整體下定義。在符號學領域,“這特殊模型就是用來交流信息、也就是說交換意義的代碼(code)。‘代碼’和‘信息’,就是語言和話語(parolc)。”[4]74運用此種方法,符號學可以把各種意義整體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巴爾特把研究對象甚至擴大到了服裝、食品、汽車和家具。在這種背景下,藝術也被同一于語言。如果非要用代碼與信息的系統來給藝術找一個位置的話,杜夫海納認為在符號學的中央應該是語言學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信息與代碼互相依存,二者是平等的,人們能利用代碼傳遞信息。在這個中心的兩端分別存在著次語言學領域和超語言學領域。次語言學領域包括所有尚未具有意義的系統,有代碼,但沒有信息,意義被還原為消息。杜夫海納認為藝術屬于超語言學領域,并且是超語言學領域的最佳代表。在超語言學這個領域里,系統是超意義的,它們能傳遞信息卻沒有代碼,或者說是這種情況:代碼越不嚴格,信息越含糊不清,意義就主要是為了表現。根據這種劃分,可以體會到,杜夫海納并不認為藝術是語言學的正統對象,藝術可能也受語言學規則的支配,但卻是超越語言的。所以,他的藝術語言觀集中強調的是藝術對于語言的超越性。
杜夫海納認為藝術與語言雖然具有某些相似性,但更為重要的是,藝術不能等同于語言,藝術也并不適合符號學的研究。如果按照符號學的研究思路來看藝術,首要的是找到各種藝術中存在的“系統”,可是,各種藝術千差萬別,到哪里才可以找到一個藝術的系統呢?如何把藝術當作整體給它下定義呢?“人們只有兩種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一是尋找哪些詞匯和語法是創造者所使用的,二是首先在被創造的作品中,也許也在作品的整體中去尋找能滿足一個系統的東西來。”[4]81但是,藝術畢竟不可能像語言那樣被劃定范圍。“語言是在言語的整體中表現的,它給每種言語規定出某種共同的東西,從而使這些言語構成一個同質的總體。而一定的藝術的作品整體卻沒有顯示出一個系統所表現的性質。藝術是各單獨創造者的結果,創造性的實踐總是無政府狀態的。”[4]82如果非要把藝術視為語言,這一思想應該要從以下兩點去解釋。其一,作品是設定某種代碼的一種言語;其二,藝術家是通過作品說話的。這兩點顯然是回到了語言和話語的區分,或者代碼與信息的區分。杜夫海納沒有停留在泛泛而言上,他細致、深入地考察了音樂、繪畫和電影的情況,逐一證實了自己的看法:藝術不能像其他社會人文現象那樣,如人類學、敘事學等,被當作語言來進行代碼與信息的二元對立的研究。
那么,在杜夫海納看來,藝術與語言到底是什么關系呢?他認為只有對于那些二流藝術家,藝術才僅僅是語言:“關于二流藝術家,關于一切沒有天才的藝術家,應該說他們也遵循一種代碼,這種代碼不是他們的種族的代碼,而是他們的時代的代碼。對他們說來,藝術是一種語言,符號論說得有道理。這也就是為了什么符號論選擇工業品或手工藝品作為研究對象而不選擇真正藝術作品的原因。”[4]105而對于真正的藝術家來說:“審美創造似乎沒有語言。更正確地說,藝術確實含有代碼,但這種代碼既不是確定的也不是嚴格的,尤其是它只在審美實在的周圍、在觀眾的經驗和創作者的行為之內起作用。”[4]101因此,杜夫海納著重從觀眾的經驗和創作者的行為這兩方面研究了藝術與語言的關系。
對于藝術家的創作來說,“語言的地位完全是奇特的:它是工具,又是非工具;它在我之中,又在我之外。”[4]104這正是藝術創造的特殊之處。因為藝術家的作品最需要的是獨創性,他并非是在從事一種單純的編碼工作,雖然不同門類的藝術各有自己的一套程序與規則,但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并非是完全受制于這些程序與規則,杜夫海納指出:“藝術不同于語言,更加普遍地說,藝術不同于真正的意義系統。總而言之,目的是為了表明語言學范疇是如何只能有保留地加以使用:它們與創造行為所不了解的或所忽視的代碼有關。如果想要把它們運用于創造行為,那就必須指出這行為是如何超出這些范疇的。”[4]108顯然,藝術創造更加愿意突破常規,發明句法,產生自己的語言,這也是藝術成為自身的重要手段。
對于觀眾的經驗來說,藝術家想表達自己這一觀念甚為流行,人們經常提出這個觀念來證明“藝術是語言”的說法。作品確實會發出一種信息,那這種信息是什么性質?該如何來界定呢?針對這一問題,杜夫海納認為:“不是藝術家在說話,而是他的作品在說話。甚至在說雙重的話:它在揭示屬于作者的某個世界的同時代表作者。藝術家的真實在他的作品之中。需要追尋的就是這種作品的真實。”[4]113我們知道,作品客觀上會流露出藝術家本人的情感,他思考的東西會不可避免地滲透和表現在他的作品中,但首先要承認,藝術家通過作品傳達的不是他個人的信息,不是自說自話,或者說,展現他自己不是他創作的目的。作品風格也不是作家刻意營造的。就好比說,某些程度地展現藝術家自己,是創作的副產品。
作品確實在說話,但它不是述說它的作者,杜夫海納提出,是自然在借助藝術家說話:“自然為了說出自我求助于人,為了能被理解求助于文化。因而,藝術確實是言語,不過,在藝術領域是自然在說話,就像有時自然通過某些自然物說話一樣。”[4]116這顯然又回到了創作問題,但凡偉大的作品總是使人產生如有神助的感覺,詩中萌動著自然的請求。在《詩學》中,杜夫海納進一步說,是自然喚起了詩性的狀態和詩性的語言,“自然需要人,因為自然需要人來點亮她。而且應該說自然需要言語的人,而人類最初的話語就是詩。”[5]226
與海德格爾一樣,在各種藝術中,杜夫海納特別偏愛詩歌,他賦予了詩歌語言以特殊的使命,詩歌不是語言哲學,而是初始語言,“詩就是第一語言,一種人類回應自然的語言的語言,或者說一種使自然作為語言顯現的一種語言。”[5]229詩歌語言不僅在人與世界中起著原始交流的作用,它的表現性使讀者在閱讀中能夠直接感知到人與世界的本然關聯,這種關聯證明人與世界的關系是平等的。“語言是聯系人與世界的滋養性的結,它也是人解放自己和確證自己愿望的手段。人能認識和掌握事物僅僅因為他能命名;他能命名僅僅因為事物向人揭示自己,因為‘創造的自然’(Natura naturans)發明了語言并召喚人來說。這就是詩人知道的、他的詩歌說出的東西:詩提出了語言的問題并以它自己的方式提供了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1]101這又體現了杜夫海納不同于海德格爾語言觀的地方,海德格爾把語言視為存在之家,把語言和存在結合在一起,從本體論的高度研究語言,杜夫海納則把人與世界的根源歸于造化自然,而語言是人與世界的聯結點。
整體上看,對于藝術與語言的關系,杜夫海納反對通過語言去理解藝術,而主張通過藝術去理解語言。他特別強調的是藝術的獨特性、創造性與心靈的自由,雖然藝術與語言一樣是一種表達活動,但藝術的表達在本質上絕對不同于語言,藝術的表現力喚醒的是人與世界的和諧感,喚醒的是造化自然的詩性的狀態和詩性的語言,這是藝術與語言最大的不同。
綜上所述,杜夫海納主張從本體論的角度看待語言,不再把語言僅僅看作客體和工具,而是強調人與世界的平等,語言是人與世界的基礎,世界向我們說。世界之說通過“前意象”而展開,“前意象”暗示了人與世界的本源和諧。人與世界的根源在于造化自然,詩喚醒了造化自然的詩性狀態,詩是人類的初始語言,詩使人類與世界回復到了最自然的狀態,這正是藝術的意義。與分析哲學重視語言與形式邏輯、語言與本體論等問題不同,杜夫海納的語言觀基本符合存在論現象學關注語言與思想、詩歌語言的傳統。而杜夫海納對結構主義等流派的批判,根源正在于杜夫海納思維方式與索緒爾語言學思維方式的對立。那么,在語言問題上,杜夫海納延續了他在《審美經驗現象學》中確立的超越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總體上服務于他長久以來對人與世界的關系的探索。
[1]MIKEL DUFRENNE.Language and Philosophy[M].Translated by Henry B.Veatch.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3.
[2]格雷馬斯.結構語義學:方法研究[M].吳泓緲,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3]楊大春.語言·身體·他者:當代法國哲學的三大主題[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84.
[4]杜夫海納.美學與哲學[M].孫非,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5]MIKEL DUFRENNE.Le Poétique[M].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73.
(責任編輯:劉燕)
本刊加入《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的聲明
為了適應我國信息化建設的需要,繼續擴大學術交流的渠道,《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于2004年1月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部《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其作者著作權使用費與本刊稿酬一次性給付,免費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統計分析資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編入該光盤版和數據庫,請在來稿時聲明,本刊將做適當處理。
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學報編輯部
On Dufrenne’s View of Language
Dong Huif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Bohai University,Jinzhou Liaoning 121013,China)
Dufrenne’s language view is a response to the 20th century linguistic turn.He advocats the study of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no longer regards language as the object and tool,but emphasizes the equality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He also believes that the root of man and the world lies in Nature,poetry has awakened the poetic state of Nature;Poetry is the original language of human beings,and it brings the human and the world back to the most natural state,which is the meaning of art.Dufrenne’s linguistic view is still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and run through beyond subject-object duality of thinking.
Dufrenne;the linguistic turn;Saussure;arts;man and the world
B83-069
A
1672-7991(2017)01-0016-06
10.3969/j.issn.1672-7991.2017.01.003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杜夫海納美學思維方式研究”(13YJC720009);遼寧省社科聯2015年度遼寧經濟社會發展立項課題“杜夫海納的語言觀研究”(2015lslktziwx-05);2015年遼寧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現象學‘詩之思’的嬗變研究”(W2015013)。
2016-12-20
董惠芳(1977-),女,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人,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學理論與美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