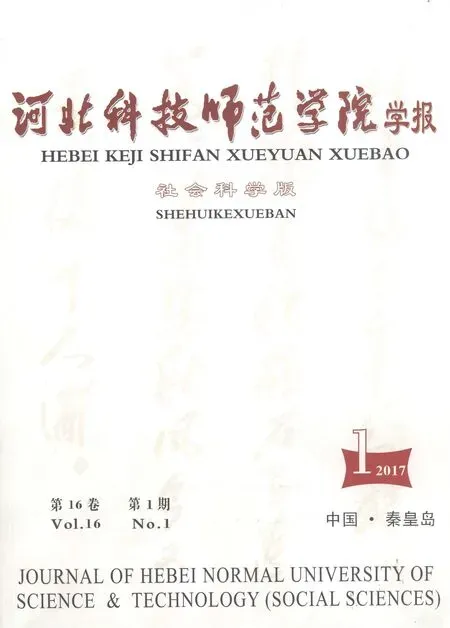食品安全社會共治背景下村民參與機制研究*
——以鄉(xiāng)規(guī)民約為核心
辛宇鶴,王雪梅,丁義娟
食品安全社會共治背景下村民參與機制研究*
——以鄉(xiāng)規(guī)民約為核心
辛宇鶴,王雪梅,丁義娟
(河北科技師范學院文法學院,河北秦皇島066000)
“社會共治”是農村食品安全監(jiān)管改革的必由之路,而廣大村民對于食品安全監(jiān)管參與度一直走低,這成為農村“社會共治”的“瓶頸”。指出實現農村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的關鍵在于構建和完善鄉(xiāng)規(guī)民約。因此借鑒古代“鄉(xiāng)治”的經驗,對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宗旨、制定程序、內容和實施方式提出了完善建議。
社會共治;食品安全;村民參與;鄉(xiāng)規(guī)民約
農村食品安全不僅關乎農民的生命健康,更關乎農村穩(wěn)定和新農村建設。然而由于農村食品生產經營主體分布零散且流動性強,加之基層行政監(jiān)管力量嚴重不足,使得農村成為食品安全的“重災區(qū)”。對此,很多學者都指出農村食品安全不能單純依靠行政監(jiān)管,應該充分調動社會各方力量,建立公眾參與機制。如倪楠在《農村食品安全監(jiān)管主體研究》中指出:“要使社會團體和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廣泛參與到農民維權中來。……村民委員會、各專業(yè)合作社、行業(yè)協會以及農民自愿組成的公益性非正式組織應該在農村社會監(jiān)管中發(fā)揮主體作用。”[1]霍有光等指出:“農村地區(qū)充分發(fā)揮第三方監(jiān)管的作用,即媒體監(jiān)管、行業(yè)組織監(jiān)管和公民監(jiān)管。”[2]齊萌提出食品安全合作治理理論,通過建立政府與企業(yè)、政府與公眾、政府與媒體、企業(yè)與公眾以及各個主體之間多維度的合作關系,克服政府監(jiān)管失靈現象[3]。在理論界的呼吁下,2015年《食品安全法》修訂,增加了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的內容。它的提出是我國食品安全監(jiān)管理念的一大創(chuàng)新,也給農村公眾參與食品安全綜合治理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據。2015年10月27日出臺的《國務院、食品安全辦等五部門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食品安全治理的工作意見》中亦把“構建社會共治格局”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因此,無論是從農村食品市場的特殊性出發(fā)還是考慮國家政策法規(guī)的導向,踐行社會共治的路線,調動村民力量,構建農村本土防線,已經成為農村食品安全監(jiān)管的必然選擇。
一、食品安全“社會共治”與村民參與機制
(一)“社會共治”的內涵
“社會共治”字面意思即社會共同治理,“治理”不同于“統治”,“統治”有非常明顯的公權力色彩,而“治理”一詞則更傾向于社會合作。古今中外學者關于“治理”有很多論述①卞輝博士在《農村社會治理中的現代鄉(xiāng)規(guī)民約研究》中列舉:《孔子家語·賢君》中有:“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荀子·君道》中有:“明分職,序事業(yè),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英國學者羅伯特·羅茨對于治理下的的六種定義,其中談到作為社會控制體系的治理,體現為政府與民間、公關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合作與互動;在信任與合作基礎上形成的社會協調網絡。格里·斯托克研究治理的含義時,歸納出五種觀點,指出治理主體不僅限于政府。政府并不是國家唯一的權力中心,各種公共的和私人的機構,只要得到了公眾的認可,就都可能成為在各個不同層面上的權力中心。在手段上并不僅限于政府的發(fā)號施令或運用權威。俞可平認為治理是官方的或者民間的公共管理組織,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共需要的過程。全球治理委員會在1995年給治理下了一個較權威的定義,即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xù)過程。,盡管表述不同,但是對于“治理”的內涵卻有著共同的認知:
第一,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政府承擔重要角色,但不是唯一角色,還應該有眾多的非官方機構和個人的參與。這些非官方機構和個人與政府是平等合作的關系,不是政府的附屬。如格里·斯托克指出政府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各種公共的和私人的機構也可以成為不同層面上的權力中心;羅伯特·羅茨列強調在社會管理體系中政府與民間的合作與互動[4]30-31;這些都說明“治理”是多元主體合作共贏的模式。第二,治理手段的多樣化。行政管理是國家重要的社會控制手段,不過除了行政管理以外還應當有更多的管理技術和方法,而且這些措施應當盡可能地減少行政色彩,凸顯社會公信力和公斷力,如媒體監(jiān)督、公眾監(jiān)督、行業(yè)自律等。第三,治理維度的雙向性。“治理”不同于“統治”,“統治”是運用公權力,通過行政法規(guī)、行政命令對社會公共事務實施自上而下的管理,管理維度是單一的。而“治理”則不同,全球治理委員會將“治理”描述為多方主體為了調和利益而采取的“聯合行動的持續(xù)的過程”。多個主體通過協商,達成管理機制上的默契與共識。每個主體都能獨立發(fā)揮作用,但彼此之間又能相互配合,協調一致,其管理維度是縱橫交織、聯合互動的。比起單一的縱向管理模式,這種雙向性的模式更完善、更靈活。
綜上,“社會共治”是政府公權力與社會力量有機結合的綜合治理模式。長期以來,我國各個領域普遍以公權力為主導,隨著社會問題的日益復雜化,公權力部門無論是從專業(yè)上還是精力上都無法做到有效解決。因此簡政放權、充分利用社會力量解決矛盾,成為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方針就是政府在食品安全監(jiān)管領域簡政放權的新探索,其核心是利用全社會的力量共同促成食品安全的全面提升,彌補單一行政監(jiān)管的不足。具體表現為包括政府在內的最廣泛的食品利益相關者,在平等合作的基礎上,充分利用信息優(yōu)勢和資源優(yōu)勢,通過多元化的治理模式形成群管群控的食品安全保障機制。
(二)村民參與是農村踐行社會共治的關鍵
“社會共治”責任主體包括政府監(jiān)管部門、食品生產經營者、行業(yè)協會、消費者協會和社會公民②《食品安全法》只在第三條規(guī)定了社會共治原則,但沒有界定其責任主體,也沒有明確的司法解釋,所有學界的觀點并不統一,筆者采用全國人大法工委《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解讀》中的解釋。。各方主體良性互動、有序參與,形成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的格局。但對于農村食品監(jiān)管而言,最現實最穩(wěn)定的共治主體是村民。因為行政監(jiān)管在農村本身就存在失靈的狀況,農村的食品生產經營主體多以小作坊、小賣店為主,資金薄弱,加之小農的趨利性,這些主體缺乏社會責任感,難以實現嚴格的自律;行業(yè)協會和消費者協會多設立在地級市,很難做到對分散的農村小作坊、小攤點的有效監(jiān)管;新聞媒體確實是食品安全社會監(jiān)督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由于農村向新聞媒體舉報的途徑不暢,使得媒體對農村食品安全關注度也不高。所以,構建村民參與機制才是農村踐行社會共治理念的核心要義。只有調動村民的積極性,才能實現農村社會共治的常態(tài)化發(fā)展。
二、建立村民參與機制遭遇的困境
(一)農民缺乏參與食品安全監(jiān)管的積極性
村民參與是農村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的關鍵,然而很多學者在農村實地調查后,發(fā)現如今農民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高了,但是真正參與到食品安全監(jiān)管中來的積極性并不高。劉文萃在天津農村地區(qū)進行調查發(fā)現,超過七成的受訪農民對食品安全問題表示“非常關注”或者“比較關注”,然而能夠對本地區(qū)食品安全監(jiān)管積極參與和表達訴求的人僅占3.3%[5]。趙謙從我國中東部16個省選取了61個縣進行抽樣調研,當問及“發(fā)現有人制假造假,會怎么做”時,回答親自制止只占13%,近35%的人選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6]116。沒有廣大村民的參與,農村的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會因為沒有社會基礎而流于形式。
(二)農村缺少公眾參與的制度平臺
面對村民對本土食品安全監(jiān)管的“淡漠”,很多學者都發(fā)表了自己的觀點:劉文萃指出:“以教育推動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社會公眾梳理現代食品安全意識和參與意識,提升食品安全專業(yè)知識和依法維權能力,是構建農村食品安全多元協同治理的基本途徑。”[7]耿雪娟、韓宏燈認為:“農村居民對食品標識及具體區(qū)別的認知缺乏,應當加強對食品安全的宣傳力度,提高居民食品安全認知水平。”[8]許亞寶,周幫揚指出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知識還處于被動接受的狀態(tài),在維權領域還處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始狀態(tài),因此主張?zhí)岣咿r村食品消費者的安全意識,積極維護自身合法權益[9]。張俊瑤也提到農民文化素質不高是農村食品安全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10]。這些觀點總體認為村民參與度低關鍵在于農民對于食品安全認識不充分,因此主張加大對農村公眾的食品安全法制教育,提升農村公眾的防范意識和參與意識。農村食品安全教育固然重要,但是關鍵問題不在于此。社會共治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管理模式,需要有相應的制度做依托。而現代農村則普遍缺乏一種農村公眾與行政機關平等合作的制度平臺,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國家在農村食品安全治理方面不斷推出新舉措,如2014年國務院食品安全辦公室、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總局、工商總局三部門聯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四打擊四規(guī)范”專項治理行動,河北省食品藥品監(jiān)管局自2016年5月上旬至2016年12月下旬在全省開展為期7個多月的農村食品安全“掃雷”專項行動。所有這些舉措都是在國家法的體系下,依靠行政權力自上而下實施的。即便在已經開展食品安全村民自治的試點地區(qū),如被媒體廣泛報道的湖北新寧縣,試點村掛牌成立“農村食品安全村民自治委員會”,通過自治委員會制定《食品安全村民自治章程》,賦予村民相應的自治職責,旨在實現農村群防群管的治理格局[11]。但從其構建的“政府主導、部門協作、村民參與”的食品安全社會共治工作機制來看,“自治”過程中實際上反映的是政府對農村食品安全秩序的改革與重構,村民依然處于附屬地位,與社會共治理念的要求還是有一定差距。在單一的國家法的體系下,農民很難以主人翁的姿態(tài)與行政機關平等合作。
首先,國家法的制定是公權力行使的過程,農民沒有參與制定的權力。國家法代表人民的意志,但是其制定卻是上層決策,農民只能是被動地接受。這種制定過程本身就凸顯了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隸屬關系,很難提供一個農民和國家行政機關合作共治的平臺,
其次,國家法的內容具有宏觀性,往往和農村的實際情況相距甚遠,致使很多法規(guī)在農村成為具文。比如《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質量安全控制基本要求》僅對設施和設備的要求就有十六個單項,再加上人工成本,農村的食品作坊很難達標[12]。如果強行推行,會使很多農村食品作坊轉入地下,增加監(jiān)管難度。
最后,國家法與農村傳統文化產生的沖突,導致農民在情感上對法律是疏離而冷漠的。比如近幾年農村集體宴會的食品安全引發(fā)了社會關注,很多地方都出臺了監(jiān)管制度,要求農村集體聚餐要向有關部門提前申報,由食品監(jiān)管部門進行現場指導和審查。從國家法的角度來說,這是加強執(zhí)法監(jiān)督,無可厚非。但是趙謙在實地調查過程中發(fā)現,有68%以上的村民不希望政府插足[6]116。原因是很多農村宴飲都是幾百年來的延續(xù)下來的習俗,它承載著地方的傳統文化,也是村民尋求地方認同感的主要形式。如果在濃濃的鄉(xiāng)情中介入冰冷的執(zhí)法行為,的確是一個“不和諧的音符”。
梁治平曾經說過:“在整個歷史上,國家權力,尤其是國家法律對于鄉(xiāng)民社會的滲透始終極為有限。”[13]即使在當代,國家法在農村也依然不能“一統天下”。“國家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后盾’的象征的意義而存在的,農民更多地是生活在鄉(xiāng)村內生秩序的民間法中,由民間法調控和解決一切。”[14]作為民間法的重要組成部分——鄉(xiāng)規(guī)民約,在農村社會治理中發(fā)揮著國家法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農村公眾得以參與“社會共治”真正平臺。
三、“鄉(xiāng)規(guī)民約”在實現農村社會共治中的價值
(一)何為“鄉(xiāng)規(guī)民約”
董建輝稱“鄉(xiāng)規(guī)民約”是鄉(xiāng)里百姓從實際生活的需要出發(fā),通過合意的方式訂立的大家共同遵守的規(guī)則[15]。楊開道指出鄉(xiāng)約制度是由士人階級的提倡,鄉(xiāng)村人民的合作,在道德、教化方面去制裁社會的行為,謀求大眾利益[16]。《中國大百科全書》將其解釋為中國基層社會組織中社會成員共同制定的一種社會行為規(guī)范[4]23。從中可以歸納出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一些基本特征:一是地域性,鄉(xiāng)規(guī)民約不具有國家法的普遍性,只在其形成的地域,即鄉(xiāng)里中發(fā)生效力。二是民間性,鄉(xiāng)規(guī)民約是村民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達成的契約,是村民意思自治的產物,不代表國家意志;盡管到了明清時期,部分鄉(xiāng)約帶有了半官方的色彩,但是就其主流而言,民間性始終是其最突出的特征。三是自律性,鄉(xiāng)規(guī)民約在執(zhí)行過程中,更多的是靠村民自覺遵守與維護,而不是靠國家公權力推行。綜上,鄉(xiāng)規(guī)民約可以界定為一種產生于農村本土,獨立于國家法之外的民間法。它融合了本地域的風俗習慣、鄉(xiāng)土人情,代表著本地域的社會道德觀和價值標準,比國家法更容易得到村民情感上的認同。因此在中國歷史上鄉(xiāng)規(guī)民約一直是鄉(xiāng)村社會治理的主要手段,即使在強調依法治國的當代社會,很多鄉(xiāng)規(guī)民約已經“內化”為村民潛意識中的約束機制,這些民間法在解決鄉(xiāng)村人際沖突、摩擦,維護地方秩序和諧方面通常比國家法更有效[17]。
(二)鄉(xiāng)規(guī)民約能夠最大限度的調動村民參與積極性
首先,鄉(xiāng)規(guī)民約與農村生活的高度契合。農村社會人情關系豐富而復雜,國家法由于其宏觀性,很難與農村實際貼合。但是鄉(xiāng)規(guī)民約不同,它是大量農村內生規(guī)則的一種,是千百年來鄉(xiāng)民文化生活的積淀,比國家法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基礎。其次,鄉(xiāng)規(guī)民約是鄉(xiāng)民自己的事業(yè)。楊開道提到:“鄉(xiāng)村是人民的鄉(xiāng)村,社會是人民的社會,大家有了了解,大家有了契約,才能辦理鄉(xiāng)村的事業(yè),維持社會的禮教。”[16]所以鄉(xiāng)規(guī)民約是鄉(xiāng)民自治的產物,盡管存在核心人物的“首唱”,但是其最終形成取決全體鄉(xiāng)民合意[15]116。“鄉(xiāng)規(guī)民約”制定主體是村民,制定基礎是深厚的地域文化傳統,制定的過程需要村民合意,其內容又反映了村民的共同利益。農民也只有在這樣的體系中才能真正的以“主人翁”的姿態(tài)置身其中,做鄉(xiāng)規(guī)民約忠實的守護者和執(zhí)行者。
(三)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實施能夠實現監(jiān)管方式的多元化
“社會共治”理念在強調治理主體多元化同時,也強調治理方式的多元化,擺脫對行政權的過度依賴。根據上文分析,當前在農村實施的各種食品安全監(jiān)管制度,包括部分地區(qū)實施的食品安全村民自治,都沒有擺脫行政為主的模式。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執(zhí)行則不同,它不屬于國家法,自然不會以行政權去推行。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約束力源自鄉(xiāng)民對規(guī)則的認可以及社會輿論等情感道德的力量,所以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實施方式集中體現了社會公信力和公斷力。在農村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社會公信力和公斷力要比法律的制裁更具有威懾力。當一個人被國家法制裁了,或許能獲得鄉(xiāng)民們在情感上的憐憫,但是一旦違反了鄉(xiāng)規(guī)民約,則會從人格上被徹底否定,甚至在該地域無法立足。
(四)鄉(xiāng)規(guī)民約是構建“鄉(xiāng)治”的基礎
社會共治本身就是一種雙向的治理模式,而鄉(xiāng)村治理也從來不是單一的自上而下的統治模式,它既包括源于國家主權的自上而下的“統治”,又包括立足于鄉(xiāng)土社會的自下而上的“鄉(xiāng)治”。在中國歷史上,鄉(xiāng)治是貫穿始終的。秦漢以降至明清,封建國家除了賦役的征發(fā)、社會治安的維護外,很少干涉鄉(xiāng)民的生活秩序,在基層管理上一直是以鄉(xiāng)民自治為主。在自治的背景下,各種民間組織、鄉(xiāng)規(guī)民約迅速發(fā)展起來,成為鄉(xiāng)村社會秩序的主要的維護者。從南宋的《呂氏鄉(xiāng)約》到明代的《南贛鄉(xiāng)約》,再到明清時期全國農村普遍推行的保甲、社倉和社學制度,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一套以“鄉(xiāng)規(guī)民約”為載體的“鄉(xiāng)治”體系。新中國建立后,鄉(xiāng)規(guī)民約淡出。但是很快就出現了問題,國家公權力在農村總會出現“鞭長莫及”的尷尬。因此1983年中央文件再次提出重視“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作用,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第十六條正式提出了鄉(xiāng)規(guī)民約這一法律形式①1983年[中發(fā)(1983)1號]《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規(guī)定:“要通過制訂鄉(xiāng)規(guī)民約,開展建立文明村、文明家庭的活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第十六條村規(guī)民約由村民會議討論制定,報鄉(xiāng)、民族鄉(xiāng)、鎮(zhèn)的人民政府備案,由村民委員會監(jiān)督、執(zhí)行。村規(guī)民約不得與憲法、法律和法規(guī)相抵觸。。這說明鄉(xiāng)規(guī)民約在當代鄉(xiāng)村社會治理過程中具有劃時代的價值。
鄉(xiāng)規(guī)民約承載了村民共同的利益需求和價值觀念,有著高度的權威性和穩(wěn)定性;其形成過程也體現了村民對地方規(guī)則制定、實施和維護的能力[17]44。在農村食品安全社會共治中,沒有一種規(guī)則可以比鄉(xiāng)規(guī)民約在村民中更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忽視鄉(xiāng)規(guī)民約,村民就會是一盤散沙,除了牽扯到自身利益,更多的是以“看客”的身份對待食品安全,踐行社會共治也就流于形式了。
四、農村食品安全監(jiān)管中“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建構
(一)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建構宗旨
鄉(xiāng)規(guī)民約雖然屬于獨立于國家法之外的民間法,但是“獨立”并不意味著“對立”,在當前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構建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都不能與國家法相抵觸。因此,鄉(xiāng)規(guī)民約在構建過程中應當以與國家法相互融合、實現二者良性互動為宗旨。一方面其內容應當貼近農村實際,利用習慣、傳統、道德的力量對農村社會秩序進行有效調控;另一方面,鄉(xiāng)規(guī)民約也要跟上政策法規(guī)的發(fā)展,將國家法中有益于新農村建設的內容貫穿到鄉(xiāng)規(guī)民約中,推動國家法的實施。最終形成以國家法為基礎的“國治”和以鄉(xiāng)規(guī)民約為基礎的“鄉(xiāng)治”合作共贏的治理格局。
(二)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制定程序
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制定程序應當科學性和民主性并重。首先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制度要充分體現鄉(xiāng)民的意志。鄉(xiāng)規(guī)民約草案擬定之前,應當征詢每一位鄉(xiāng)民意見。草案形成后,應當向全體鄉(xiāng)民公布,同時設立意見箱,向廣大村民征詢修改意見,反復修改。內容確定以后,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二條規(guī)定的程序召開村民會議,經到會人員的過半數通過,并報鄉(xiāng)政府備案。其次,食品安全監(jiān)管帶有較強的專業(yè)技術性,為了保障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內容能夠行之有效,在制定鄉(xiāng)規(guī)民約之前應當對村民進行必要的食品安全專業(yè)知識和法律法規(guī)的培訓。建議建立分級培訓制,先由縣級食品藥品監(jiān)督局組織各鄉(xiāng)監(jiān)管人員和分管干部進行培訓,再由鄉(xiāng)鎮(zhèn)主管部門組織村干部和村民骨干進行培訓,最后由村干部組織本村全體村民進行培訓。這樣既保障了內容的科學性,還有利于鄉(xiāng)規(guī)民約與國家法的融通。為了使培訓有穩(wěn)定的資金支持,培訓經費應當由縣級財政統一撥付。
(三)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內容
首先,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制定不能與國家法相抵觸。國家法是國家主權行為,任何一個公民與組織都應當無條件遵守,這是基本前提。鄉(xiāng)規(guī)民約應當將國家法律中規(guī)定的索票制度、建立購銷臺帳制度、村民投訴舉報制度、食品生產經營用工信用檔案制度、農村小作坊的資質許可制度或者資質備案制度,食品小作坊生產加工食品目錄等加以強化,這些制度是農村食品安全監(jiān)管中的關鍵,但往往又是比較薄弱的環(huán)節(jié),將這些國家法的內容“鄉(xiāng)規(guī)民約化”,更有利于其貫徹實施。其次,鄉(xiāng)規(guī)民約應當尊重農村的傳統習俗,與當地的風土人情高度契合,這是鄉(xiāng)規(guī)民約本質特征決定,也是鄉(xiāng)規(guī)民約比國家法在農村更深入人心的主要原因。比如農村傳統宴會,其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隱患不容忽視,但是現場檢查的制度會破壞鄉(xiāng)民和諧的氣氛,使村民產生抵觸心理。所以鄉(xiāng)規(guī)民約對此應當根據農村現實情況規(guī)定明確的食品標準,引導村民自覺遵守,采取事后追責的方式對違法行為進行查處,而不是現場檢查。第三,對農村普遍存在的食品小作坊,應本著監(jiān)管與保護并重的方針來制定鄉(xiāng)規(guī)民約。農村食品小作坊的食品安全標準不應簡單照搬城市食品企業(yè)的標準,應當結合當地的經濟水平、農民收入水平、食品生產的風險因素制定。禁止農村小作坊生產嬰幼兒、老年人、病人等特殊人群的專供食品,但是對于食品生產風險率低、口碑好的食品作坊可以做出一些豁免性規(guī)定。《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條規(guī)定:“國家對食品生產經營實行許可制度。從事食品生產、食品銷售、餐飲服務,應當依法取得許可。但是,銷售食用農產品,不需要取得許可。”通過該規(guī)定可以看出國家法對農村食品生產經營者也是有豁免性規(guī)定的。鄉(xiāng)規(guī)民約可以在此基礎上將豁免主體、豁免食品、豁免食品銷售區(qū)域和銷售方式進一步細化,既要保障食品安全又要給農村的“草根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創(chuàng)造相對寬松的空間。
(四)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執(zhí)行
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執(zhí)行應當本著“剛柔并濟”的原則。所謂“剛”指的是作為民間法,鄉(xiāng)規(guī)民約也應當和國家法一樣,有常設的執(zhí)行機構和嚴格的執(zhí)行程序,不能僅僅口頭宣講或張貼在公告欄里流于形式。在歷史上,鄉(xiāng)規(guī)民約都有一整套組織機構。朱熹修訂后的《呂氏鄉(xiāng)約》中規(guī)定“領導班子”由四人組成:約正一人,副正兩人,直月一人。明代《南贛相約》“領導班子”擴展到十七人,包括約正、約副、約史、知約、約贊等,這些人都是鄉(xiāng)里德高望重且通曉文理者。他們各司其職,約正為鄉(xiāng)約首領,負責裁處約內重大事項,主持鄉(xiāng)約聚會。約正以下為具體辦事人員,分別負責讀鄉(xiāng)約、彰善惡、造簿錄等[15]27。鄉(xiāng)約執(zhí)行的主要形式是集會,堪稱鄉(xiāng)間的大典。鄉(xiāng)約集會的地點多在當地神圣的公共建筑中,如寺廟、道觀、社學、祠堂等,足見鄉(xiāng)規(guī)民約在鄉(xiāng)民心目中的地位。集會時秩序井然,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位次。其具體程序包括:禮拜尊者、誦讀鄉(xiāng)約、推糾善惡、造冊登記。善者的善行記錄在善簿上,由直月朗誦;惡者的惡行記錄在惡簿上,眾人傳閱。之后聚餐,餐畢,自由活動,可以談論文學亦可切磋武藝[16]140。這種形式既蘊含著濃濃的鄉(xiāng)情又有著不可小覷的震懾力。因為在農村這樣一個封閉社會,“父兄在旁,子孫在下,眾口共舉,眾目共斥”[16]144,這種輿論的壓力比刑罰加身還要厲害。現代鄉(xiāng)約的執(zhí)行不需要有繁瑣的形式,但是必須有明確的執(zhí)行機構和嚴明的程序,否則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權威無法樹立。鄉(xiāng)約的領導機構應當充分體現“去行政化”,普通村民的比例應當占到一半以上,以品德為核心,綜合考慮年齡、閱歷、文化程度等因素選舉產生,實行任期制。該組織負責本村中食品安全的日常監(jiān)管,仿效古代集會形式,并定期召集全體村民舉行食品安全情況通報會。表彰遵紀守法的商戶,批評違法違規(guī)的不良商戶,建立商戶誠信檔案,每次通報的情況進行歸檔。久而久之,奉公守法的商戶會形成良好的口碑,生意興隆,不良商戶則會在當地舉步維艱、無法立足。
此外,鄉(xiāng)規(guī)民約作為一種民間法,在執(zhí)行過程中還應當體現柔的一面。《食品安全法》對于違法行為的處罰主要有兩種措施:一是罰款,二是拘留。鄉(xiāng)規(guī)民約則不宜采取上述措施。首先,從歷史上看,鄉(xiāng)約源自周禮的“讀法之典”,“讀法”就是基層官員宣講法律,教導人民。可見鄉(xiāng)規(guī)民約從產生就是一種以教化為主的社會規(guī)范[16]38。朱熹在增損《呂氏鄉(xiāng)約》時就果斷地將原有的“罰金”廢除,“要大家各自省家,互相規(guī)誡”“小則密規(guī)之,大則眾戒之”,屢教不改才登記在“惡簿”中。王陽明在《南贛鄉(xiāng)約》中對彰善糾惡主張忠厚之道:彰善之詞可以顯而決,糾過之詞應當隱而婉。當代鄉(xiāng)約的內容和性質和古代大有不同,但是以教化為主的方針應當是一脈相承。鄉(xiāng)約本身就是人情的產物,如果動輒罰錢甚至拘留,人情臉面被撕破,鄉(xiāng)規(guī)民約也就失去了社會基礎。其次,社會共治本身要求治理手段的多樣化、“去行政化”,如果鄉(xiāng)規(guī)民約依然采取行政處罰的方式,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所以當代鄉(xiāng)規(guī)民約也應當遵循“小則密規(guī)之,大則眾戒之”的古訓,輕微的違法行為經規(guī)勸及時改正,不用當眾通報,更不用向當地工商部門舉報。只有屢教不改或者行為達到了《食品安全法》中規(guī)定的比較嚴重的情況下,那就必須向工商部門舉報,同時通過村民大會向全體村民通報,還要登記在誠信檔案中,讓不法分子背負法律與道德的雙重制裁。
習近平說過:“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18],保障農村食品安全是農村群眾共同的事業(yè),也需要村民共同完成。在農村踐行“社會共治”理念離不開鄉(xiāng)規(guī)民約,只有在這個體系中,農民才能以主人翁的姿態(tài)置身其中,盡心地去遵守它、維護它。同時,鄉(xiāng)規(guī)民約還能對違法分子形成國家法都難以實現的道德震懾。其實食品安全社會共治,不僅彰顯法制的力量,而且通過某種規(guī)則的構建形成一種價值觀、一種文化的力量,提升道德的約束力。鄉(xiāng)規(guī)民約就是這樣一種規(guī)則,它將千百年的地域文化和當代食品安全規(guī)則融為一體,在村民中形成了食品安全共同的價值觀,使得農村食品監(jiān)管能夠長治久安。所以,在完善食品安全國家立法、加強基層行政監(jiān)管力量同時,必須進一步加強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規(guī)范化和系統化建設,使其和國家法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凝聚農村本土力量,打通食品安全“最后一公里”。
參考文獻:
[1]倪楠.農村食品安全監(jiān)管主體研究[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134-136.
[2]霍有光,于慧麗.農村食品安全的現狀與對策——基于農民權益保護的思考[J].廈門社會科學,2014(5):154-157.
[3]齊萌.從威權管制到合作治理:我國食品安全監(jiān)管模式之轉型[J].河北法學,2013(3):50-56.
[4]卞輝.農村社會治理中的現代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研究[D].楊陵: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3.
[5]劉文萃.農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眾參與:問題識別與路徑選擇——基于天津調研的實證分析[J].云南行政學院學學報,2015(3):161-166.
[6]趙謙.農村消費者參與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的實證分析[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版),2015(8):110-120.
[7]劉文萃.協同治理視域下農村食品安全教育問題探討[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5):140-145.
[8]耿雪娟,韓宏燈.農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識的實證研究—基于東川區(qū)農村的調查分析[J].云南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6):28-32.
[9]許亞寶,周幫揚.城鄉(xiāng)食品安全監(jiān)管的差異化研究[J].安徽農業(yè)科學,2014(4):3391-3392.
[10]張俊瑤,毛麗平,張聯社.我國農村食品安全問題的原因分析和對策研究[J].安徽農業(yè)大學學報,2014(4):70-74.
[11]湖南省試點推行農村食品安全村民自治制度著力構建農村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機制[EO/OL].[2017-03-12].http://www.sda.gov.cn/WS01/CL1683/110585.html.
[12]鐘剛.農村家庭食品銷售的特殊法律規(guī)則思考——以《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條為起點[J]社會科學,2013(3):88-97.
[13]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163.
[14]田成有.傳統與現代:鄉(xiāng)土社會中的民間法[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5:15
[15]董建輝.明清鄉(xiāng)約:理論演進與實踐發(fā)展[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16]楊開道.中國鄉(xiāng)約制度[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17]范忠信.民主法治視野下的村規(guī)民約建設研究[J].公安學刊,2013(3):44-51.
[18]兩會之外,習近平如何關心政協工作?[EB/OL].[2017-03-04].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3/ 04/c_1118233637.htm.
(責任編輯:楊燕萍)
本刊加入《萬方數據—數字化期刊群》的聲明
為了實現期刊編輯、出版工作的網絡化,《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現已入網“萬方數據—數字化期刊群”,所以,向本刊投稿并錄用的稿件,將一律由編輯部納入“萬方數據—數字化期刊群”,進入因特網提供信息服務。凡有不同意者,請另投他刊或特別聲明,需另作處理。本刊所付稿酬包含刊物內容上網服務報酬,不再另付。
“萬方數據—數字化期刊群”是國家“九五”計劃重點科技攻關項目。本刊全文內容按照統一格式制作,讀者可上網查詢?yōu)g覽本刊內容,并訂閱本刊。
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學報編輯部
Stay on the Mechanism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ext of Food Safety Social Cohabitation——Based on the Village Rules
Xin Yuhe,Wang Xuemei,Ding Yij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Law,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Qinhuangdao Hebei 066000,China)
Social co-governance is the crux of reformation of the rural food safety regulatory system.However it has become such a bottleneck problem in caring out social co-governance that the degree of the majority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ng in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has been low.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ke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build and improve the rural rules.This paper aims to offer a proposal on the purpose,procedures.
social co-governance concept;food safety;villagers’participation;village rules
D621.5
A
1672-7991(2017)01-0040-07
10.3969/j.issn.1672-7991.2017.01.007
2016年河北省科技廳軟科學課題“社會共治理念下農村食品安全政府監(jiān)管制度創(chuàng)新性研究”(16456204D)。
2017-2-21;
2017-03-10
辛宇鶴(1981-),女,河北省無極縣人,副教授,主要從事食品安全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