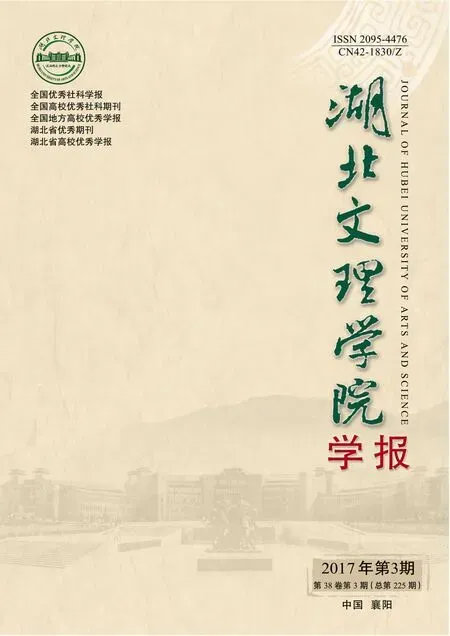論香港邵氏電影《貂蟬》對《三國演義》中貂蟬的形象重塑
王 凡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論香港邵氏電影《貂蟬》對《三國演義》中貂蟬的形象重塑
王 凡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投資拍攝、集中展現《三國演義》中王允通過貂蟬巧施連環美人計誅除董卓這一情節的影片《貂蟬》,一方面著意彰顯了貂蟬“公義為先”的獨特形象、重繪了貂蟬命運軌跡,在主流意識形態及傳統歷史思維的影像書寫中折射出李翰祥電影一以貫之的家國情懷;另一方面,影片又出色發揮了黃梅調戲曲唱段對于片中主人公貂蟬的影像重塑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從而既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的香港電影對于《三國演義》人物精神內涵的特殊理解與詮釋,亦體現出傳統戲曲元素對于古典名著改編的重要意義。
《貂蟬》;《三國演義》;人物重塑;戲曲唱段;文學改編
一代電影巨匠李翰祥曾對自己拍攝的歷史宮闈片《貂蟬》(1958年)評道:“這個戲雖然使我得到1958年第五屆亞洲影展的最佳導演獎,我卻覺得它是我作品中較糟的一部。既荒唐,又幼稚,電影不電影,戲曲片又非戲曲片,不倫不類,非驢非馬。”[1]460盡管李氏對于《貂蟬》并不滿意,然而這卻不能抹殺該片本身的藝術成就。作為20世紀50年代香港邵氏“三國”題材電影的重要作品,這部依據小說《三國演義》改編拍攝的影片再現了原著中王允通過貂蟬巧施連環美人計誅滅董卓的情節。該片不僅在尊重原著、尋求創新的名著改編理念下對原著人物尤其是主人公貂蟬的藝術形象進行了影像重塑,并且還出色地發揮了戲曲片展示人物心理、刻畫人物性格的特點,這在貂蟬的形象重塑中也有著鮮明的體現。
一、貂蟬“公義為先”形象的影像彰顯
作為中國古代歷史演義小說的代表作,《三國演義》一方面在政治歷史的變遷更迭和殺伐征討的戰爭書寫中塑造了眾多具有典型意義的君主、武將、謀士形象,在抒發深沉歷史感慨、寄寓明君賢臣共興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之際,又凸顯出獨特的男性陽剛美與力度美;另一方面,這部小說也展現了豐富多彩的女性形象譜系,并投射出復雜的女性觀念。“女性禍水”是在中國古代社會流傳甚廣的一種認識,帝王天子因美色而致喪國亡身之例可謂不絕于史,然而歷史的罪責卻往往被歸咎于女性。商紂王時期的妲己、周幽王時期的褒姒、唐玄宗時期的楊玉環皆為“紅顏禍水”的歷史典型,“她們共同的特點是都有無與倫比的美貌,因此好色的君王一見到她們就無法克制自己的欲望,為討好美人就做出許多荒唐事,以致亡國喪身。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潛規則是為尊者、賢者諱,因此在總結歷史教訓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地把罪責全部推給了女性,而真正應該承擔歷史責任的帝王則可以輕易地得到寬恕。”[2]這一特殊的女性歷史觀在明清小說中也多有反映,《三國演義》亦不例外,該作品一方面如其它古典小說一樣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傳統文化心理積淀的潛在影響,折射出“女性禍水”觀。劉表之妻蔡氏與其兄蔡瑁陰謀篡權,不僅疏離了劉表、劉琦父子的親情關系,對劉表亡故秘不發喪,更將荊州之地盡獻于曹操。在與之相關的劉琦問計諸葛亮以求自保的情節中,孔明言“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更是直白無飾地語涉驪姬亂晉之事,可以說蔡氏與《東周列國志》中“生得貌比息媯,妖同妲己,智計千條,詭詐百出,在獻公前,小忠小信,貢媚取憐。又時常參與政事,十言九中。”[3]163終致晉國離亂叢生,申生被殺、重耳出亡的驪姬在形象設定上無疑是異曲同工。黃奎因其妾李春香和妻弟苗澤將自己密謀除曹之事告之曹操而被殺,而事后苗澤反與李春香一并被斬。可以說,身為人妻、卻又與他人安通款曲的李春香呈現出與潘金蓮等人相似的通奸“殺”夫之行為特質,其不僅假他人之手殺夫,更成為其情夫身亡的肇始之因;而與蔡氏、李春香等包藏“禍”心之女相比,在曹操奪占張繡之嬸鄒氏,以致張繡受辱復反、曹之愛將典韋及子侄殞亡的情節中,作為無辜女性的鄒氏卻身不由己地卷入到政治斗爭漩渦中,從而如《水滸傳》與《西游記》中同樣溫良賢淑的林娘子和殷溫嬌一樣在無形之間扮演了女性禍水的可悲角色。
另一方面,作為歷史演義小說代表作的《三國演義》在敘寫政治歷史進程、展現軍國爭戰場景的同時,也展現了女性之美,如對甄氏、貂蟬等女子美貌的描刻,常常在只言片語之間便已窮形盡相、入木三分。更為重要的是,“作品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上,描述了眾多女性個體作為文化載體與文化行為者的七情六欲”[4]185,從而對這些女性人物的真實性情給予了相對客觀而鮮活的展現,如吳國太看到劉備儀貌時的欣喜之情,孫權之妹怒斥奉命追趕劉備的丁鳳、潘璋等人,伏皇后被杖殺前的哀切之情,都可謂情真意切。由此可見,《三國演義》在塑造豐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之際,也表現出彰顯女性之美、揭示女性內心與貶斥、矮化女性的復雜矛盾與內在沖突。而就貂蟬這一人物而言,其與《三國演義》中的其他女性相比,又更具特殊性,同時也更能體現出作品本身在女性觀方面的復雜與多面。“貂蟬是作品熱情禮贊的女性,但作者的心理仍然是矛盾的。且不說她與嚴氏的阻止使呂布喪失了戰機,就是在她作為政治斗爭的特殊工具周旋于董卓、呂布之間時,作者似乎仍沒有擺脫女色誤人的陳腐觀念。”[4]189董卓雖為《三國演義》批判的竊國亂臣,但其本身的覆滅也折射出這一典型觀念,他正是因“納貂蟬后,為色所迷”而不納李儒之諫才招致亡身。然而不可忽視的是,由于董卓的篡權亂政、禍國殃民,使得貂蟬獻身美人計具有為國除奸的積極意義,可以說,在《三國演義》中,雖然貂蟬與李春香、蔡氏等皆具有“女性禍水”的意味,但貂蟬對于董、呂關系的離間分化無疑與李春香、蔡氏為一己之私而獻媚挑撥或枕邊吹風截然不同;同樣,孫權之妹因其兄孫權為奪荊州所施之計而嫁與劉備亦和貂蟬這種關系朝局安危和生民疾苦的獻身之舉不可等量齊觀。
在貂蟬這一形象身上,除了折射出“女性禍水”的曖昧多面性外,其獻身美人計的行為動機亦是聚訟紛紜、人言人殊。對于貂蟬,毛宗崗曾評價道:
十八路諸侯不能殺董卓,而一貂蟬足以殺之;劉、關、張三人不能勝呂布,而貂蟬一女子能勝之。以衽席為戰場,以脂粉為甲胄,以盼睞為戈矛,以顰笑為弓矢,以甘言卑詞為運奇設伏,女將軍真可畏哉!當為之語曰:“司徒妙計高天下,只用美人不用兵。為西施易,為貂蟬難。西施只要哄得一個吳王;貂蟬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呂布,使用兩副心腸,妝出兩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謂貂蟬之功,可書竹帛。若使董卓伏誅后,王允不激成李、郭之亂,則漢室自此復安。而貂蟬一女子豈不與麟閣、云臺并垂不朽哉?[5]52
在毛宗崗看來,《三國演義》中的貂蟬不僅不是王允計謀里的一個工具,更非男性政治斗爭的犧牲品,而是利用自身條件來實現殺賊平逆、復興漢室之崇高目標的巾幗英雄,她并非是完全被動的聽命于王允,而是表現出極強的主動性與頗具膽識、臨勢機變的一面。而劉再復先生則認為: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不把女人當作人,即當作尤物、器物、動物等。骨子都對女人有種極度的蔑視。但是,《水滸傳》更對此表現出對婦女的殺戮。而《三國演義》則更多得表現出對婦女的利用。《三國演義》中的女子簡直像政治馬戲團的動物,一個個被推到政治前臺作表演。如果說潘金蓮、潘巧云屬于可憐,貂蟬、孫尚香則屬于可悲。[6]119
同時,劉再復還認為與孫權之妹不同的是,貂蟬“完全是自覺的工具,知道整個陰謀計劃,并成為陰謀主體,在整個陰謀的實施與實現中積極主動,起了決定性作用。”“貂蟬的權術游戲,是《三國演義》這部權術大全的另一個重要側面,它恰恰說明,心機權術已成為華夏民族的一種集體性格。”[6]123可以說,與毛宗崗將貂蟬獻身視為不朽之功來加以頌揚的態度大相徑庭的是,劉再復認為貂蟬雖在計誅董卓的過程中表現出相當的主動性,但其歸根結底仍不免淪為軍國政治斗爭和男性權力爭奪過程中的附屬性工具,毫無女性自身主體意識可言。
實際上,無論對《三國演義》中的貂蟬形象及其獻身“美人計”作何種向面的文化解讀,其行為動機中確實不乏為報恩養之情而愿以己身來為心系國運的王允去憂除患,繼而實現誅奸除佞的目的,這由出場伊始的貂蟬向王允表明心志:“妾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優禮相待,妾雖粉身碎骨,莫報萬一,近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又不敢問。今夜又見行坐不安,因此長嘆。不想為大人窺見。倘有用妾之處,往死不辭”[5]53便可見出。貂蟬這種特殊的報恩行為體現了“一種小生產者的觀念,即‘士為知己者死’。這是封建私有制下小農經濟的產物,如濟困扶危、患難相助、禍福與共。”“貂蟬的報恩思想的本身并不閃光,閃光的是她在連環計中扮演滅奸的角色,客觀效果是正義的;閃光的是他在這場斗爭中展現出了超人的智慧和驚人的膽略。她不是依人眼色歡歌賣笑的俗女,而是有自己思想情感、有自己的個性的俠女。”[7]334可以說,在《三國演義》中,知恩圖報、勇于擔當的貂蟬為王允分憂解難是其孤身赴險的直接動機和內在初衷,而除奸滅佞、安邦定國則是上述動機生發的外在行為結果。
與《三國演義》中貂蟬報恩獻身、為國除奸相映成趣的是,在依據該書改編拍攝的影片《貂蟬》中,導演李翰祥一方面生動再現了貂蟬獻身美人計的原著情節,另一方面又別具意味地重構了一心除賊、卻又苦無良法的王允于后園中巧遇貂蟬,繼而醞釀美人計的過程:當身為歌姬的貂蟬目睹王允因董卓柄權、社稷將傾而愁眉緊鎖、不思宴飲時,她先是以“莫不是大勢難回轉,莫不是奸臣又弄權,可惜貂蟬空有愿,殺奸報國恨無緣”的戲曲唱段吐露自己欲為王允分憂,卻又不得機會的心跡。之后,她又夤夜于后園中焚香祈愿道:“對明月,叩蒼天,保佑司徒壽命延,保佑他壽命延,為國為民除大患,重新扶起漢江山。”王允恰聞其聲,感其忠義,欣喜萬分,遂定下美人計以除董卓。可以說,影片《貂蟬》一方面將原著小說中王允深夜偶聞貂蟬涕淚,繼而明曉貂蟬心志的情節易變為貂蟬焚香祈愿、抒發內在心志而為王允巧遇的劇情。更為重要的是,片中貂蟬上述內心獨白式的唱詞既生動地揭示了其作為女性豐富的真實心緒和敏銳練達的洞察力,更展現了她面對奸臣弄權、國運衰微的政治危局而渴望投身報國的巾幗氣概。這從“可惜貂蟬空有愿,殺奸報國恨無緣”的唱詞即可得到印證。而原著中貂蟬所言之“妾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優禮相待,妾雖粉身碎骨,莫報萬一”即以身報恩的動機卻在影片中已難覓其蹤。雖然影片著重表現了貂蟬焚香祈盼王允福壽安康之行,但這一舉動在此更多地是她出于對位列三卿而又憂心社稷的王允其忠正品格發自內心的感佩之情,她期慕處于政治漩渦中的王允能夠平安無事實際上亦折射出其本人已將王允這樣的社稷肱股視為了國家政治安定的一種象征,她對王允的祈福保佑實際上更潛隱著她對整個國家社稷、民生安危的關切與牽掛,寄寓著面對衰亂政局的她對國朝安泰、百姓安居這一美好愿望的真實期許。由此可以說,在將《三國演義》中的貂蟬故事加以影像化的過程中,李翰祥淡化了原著中貂蟬出于私恩而投身誅董行為所富于的個人情感色彩,《三國演義》“貂蟬獻身美人計”故事中的“私恩圖報”已完全讓位于“公義為先”的歷史宏大敘事,從而彰顯了感佩王允政治品格的貂蟬在肩負起誅奸除惡、撫國安民等社稷重任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為天下公義而任事的獨特女性形象。
二、貂蟬命運軌跡的影像重繪
小說《三國演義》在貂蟬出場之時,僅言其為王允府中歌姬,而對其入府之前身世際遇卻未加追溯,這無疑為導演李翰祥在《貂蟬》中的改編創作提供了某種客觀契機。正是以此作為創作基點,李翰祥在影片中對貂蟬入王允府宅之前的命運際遇給予了合理的鋪衍生發。影片開場伊始“漢朝末年亂紛紛,董卓欺君又壓臣,關東諸侯興兵馬,遍地黃巾,遍地黃巾起戰塵。奸董卓心膽驚,遷都限日到西京,百姓不愿長安去,放火燒盡了洛陽城,老百姓,淚零零,拖兒帶女往西行”的女聲合唱曲段配之以百姓被驅、妻離子散、背井離鄉的畫面交代了漢末動蕩、董卓作亂的時代背景。接著影片表現了貂蟬的父母在奸臣為亂、兵戈擾攘導致的百姓西遷中病歿。面對家破人亡、命運無著的悲凄境遇,貂蟬唱道:“心頭只把奸臣恨,害得我家破又人亡。”正是因為貂蟬歷經這樣一場由國家政治變亂而直接導致的家庭慘變,才使得她對國家敗亡、政局動蕩給百姓帶來的災禍有著較于常人更為刻骨銘心之痛。因而她對安定的生活環境及平穩的社稷政局更為渴求與向往,這一改編虛構既直觀地呈現了貂蟬獻身、誅除董卓的廣闊社會時代背景,更在片中貂蟬“公義為先”、勇于擔當的基礎上,為其獻身義舉提供了更富說服力、更為具體的內在因由,藝術性地稀疏了原著“連環計”情節所潛隱的“為了維護男性的權益,男性可以而且應該善于利用女性的美貌與肉體”[8]這一男性文化視域。如果說,影片《貂蟬》將《三國演義》中貂蟬感懷王允知遇恩養之情而獻身報恩的形象變為貂蟬因贊許、感佩王允為國憂勞而毅然獻身的影像改編是以李翰祥為代表的該片主創者依據原著鋪衍生發的藝術創作,那么該片對于主人公貂蟬其命運際遇的重新架構則可以說是李翰祥改編主體意識的鮮明寫照。
除了對《三國演義》中貂蟬的人生際遇進行補綴式虛構外,影片《貂蟬》亦有意通過貂蟬命運軌跡的藝術重繪來淡化其原著形象所附著的“女性禍水”意味。在“黃梅調及歷史宮闈片中,李翰祥追溯中國悠久的歷史,以華美的布景和流暢的鏡頭構建了一個以‘江山’‘美人’為中心的世界,或刻畫湮沒在歷史中的宮廷權力爭奪,或描摹借由稗官野史流傳至今的愛情傳奇,或感嘆政權更迭中的世事變遷和人心無常。”[9]241《貂蟬》也不例外。在《三國演義》中,呂布本欲采納陳宮所獻的斷曹糧道之計,但卻被其妻嚴氏和貂蟬所阻,終至兵敗下邳、命喪白門樓,而嚴氏和貂蟬在此成為勇武難當的呂布走向窮途末路、最終兵敗身亡的無形之因,這一情節也折射出較強的“女性禍水”意味。影片《貂蟬》在虛構貂蟬因戰禍背井離鄉、親人亡故這一“命運前奏”的同時,并沒有以原著中呂布被擒而亡、貂蟬不知所蹤來結束全片,而是節取呂布誅殺董卓為情節終點,更于連環美人計的宮廷斗爭情節主線中細密穿插了貂蟬和呂布之間“英雄美人”式的人物情感關系,虛構了兩情相悅的二人在董卓之亂平定后終成眷屬、相攜而去的大團圓結局。蔣勛曾在《李翰祥塑造中國人的造形》一文中說:“早期李翰祥的電影傾向于傳奇故事的敘述,因此他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是概念性的人物。《江山美人》中的正德皇帝和李鳳姐,《梁山伯與祝英臺》,《貂蟬》中的呂布、董卓、貂蟬莫不是在戲劇發展中建立起相對的情節關系。”[10]179可以說,《貂蟬》中的這一英雄佳麗歷經磨難而成就神仙眷侶的傳統戲劇化情節模式一方面雖難免陷入陳規格套式的審美窠臼之中,但對貂蟬這一人物形象而言,這卻從客觀上有助于規避原著情節中貂蟬所可能附著的“女性禍水”色彩,因而不僅未使貂蟬的形象被矮化,反而進一步豐富了其藝術形象;另一方面,二人曲折的情感發展歷程與誅除董卓、撫國安民的計策實施相互穿插纏繞,形成了爾虞我詐、驚心動魄與細膩溫婉、圓融流轉這種兩極化敘事節奏的有機交融,使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更顯張弛有度。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貂蟬》在對貂蟬的命運軌跡加以影像虛構的過程中,戲曲表現手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著名導演張徹曾說:“胡金銓、李翰祥和我,全都愛好傳統戲曲且多少有點研究,受到的影響也都很大。”[11]16受傳統戲曲的藝術熏陶,當胡金銓與張徹將中國傳統戲曲元素融于武俠影像之際,同為香港電影巨擘的李翰祥則通過傳統戲曲和古典影像的有機結合,創作了大量的古裝黃梅調戲曲片,“這些作品因為黃梅調插曲的運用,透過音樂渲染出的鄉愁情緒,并由歌詞發出對君權時代的政治國勢、社會經濟提出或淺或深的批判,幾可視之為所謂‘南國影人’對中國當代時事的反省與哀嘆。”①陳煒智.絲竹中國古典印象——邵氏黃梅調電影初探.黃愛玲.邵氏電影初探.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3:43-61.作為一部改編自《三國演義》的邵氏古裝片,《貂蟬》從情節內容上來看是以古典小說為情節基礎的古代宮闈片,其從類型風格方面來看則又屬典型的黃梅調戲曲片。該片不僅充溢著大量黃梅調戲曲唱段,而且還突破了“獨唱能推動劇情與矛盾的發展,塑造人物性格;而群唱旁唱則可以渲染和強化氣氛;間奏曲主要是承擔了電影音樂的功能。”[12]這一戲曲演唱在電影中的固定功能設置,而是或由片中人物唱出的曲段、或是女聲合唱的畫外音旁白式唱段,這些戲曲唱段不僅以傳統黃梅調藝術為觀眾提供了別樣的視聽審美愉悅,而且也在影片中承載著各種特殊的藝術功能。譬如以“群臣敢怒不敢言,王允歸來更惘然,啊,啊;美酒當前添憤恨,笙歌入耳助憂煩,啊,啊”的旁白式女聲合唱與相應的影像畫面表現了目睹董卓倒行逆施的王允回府后因除賊乏術而無心宴飲、“坐不安席”的原著情節,從而運用旁白式的戲曲女聲唱段來推進敘事情節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影片亦多次通過貂蟬自己的戲曲唱段來揭示其復雜的內心世界,展現其豐富的人性情感。如在“大鬧鳳儀亭”之后的一個情節段落中,貂蟬唱道:“要算那恩仇賬,投進了是非場,我是殘花敗柳無奢望,他是密愛輕憐情意長。到如今百樣溫存成夢想,鳳儀亭上最難忘。”這一唱段看似簡短,實則意涵豐富,其曲詞不僅通過貂蟬的獨唱為影片渲染了風花雪月、細雨柔情的浪漫舒緩意趣,更以“恩仇賬”、“是非場”、“殘花敗柳”等語匯含蓄地映射出因家國破敗及感佩王允政治品格而自愿獻身的貂蟬身處這場政治漩渦中時所表現出的復雜心緒。她一方面渴望通過一己之身來誅奸除惡、解民倒懸,從而能使和自己一樣因政治變亂而流離失所、飽受荼毒的黎民百姓恢復平靜生活;然而另一方面,面對董卓義子呂布這樣一個與己方處于對立面的勇武俊才及其表露出的真情,本來義無反顧為國除奸的貂蟬亦真情萌發,愛上呂布。這一藝術虛構看似難脫“才子佳人”、“英雄美女”式的敘事程式,然而,就貂蟬這一女性形象本身而言,這種女性真實人性情感的本能反應與自然流露,卻在突出該人物主要性格的基礎上,呈現出其復雜性格的層次和豐富的人性側面。貂蟬的性格系統中不再是堅定純然的除奸心志,而是多了一份因愛上敵方將領而生發的悵惘迷茫中的不知所措,更雜糅了一絲女性自身因命運無著及情感迷失而萌生的飄零感與孤寂感,從而令《三國演義》中的貂蟬在巾幗女杰、報國女俠等多重形象解讀之外呈現出些許莎翁筆下哈姆雷特式的延宕和猶疑,進而使貂蟬這一藝術形象不僅更顯搖曳多姿、立體多維,更富于真實生命個體的審美質感,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圓形人物”[13]63的審美特質,同時由于這類段落所占影像篇幅比例的較好控制,而未出現謹毛失貌,甚或本末倒置之弊。
作為一部早期拍攝的邵氏“三國”題材電影,《貂蟬》雖不乏人物形象整體較為扁平、性格多顯單一,影片仍未擺脫戲劇化大團圓的敘事程式化束縛等藝術缺憾,然而誠如著名電影理論學家貝拉·巴拉茲所言:“沒有一部藝術作品不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藝術家的個性,他的階級意識、他的民族傳統以及他的時代的愛好。”[14]286作為香港影壇的杰出電影作者,李翰祥在根據《三國演義》的貂蟬故事拍攝影片《貂蟬》的過程中,依舊通過貂蟬命運軌跡的影像重繪與“公義為先”的獻身精神的獨特彰顯體現出其對忠實原著精神與現代改編創新的有機融合,由此不僅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的香港電影對于《三國演義》人物精神內涵的特殊理解與詮釋,更呈現出“江山”、“美人”共融于宏大歷史背景這一李翰祥古裝歷史片特有的敘事模式,進而在主流意識形態及傳統歷史思維的影像書寫中折射出李翰祥電影所獨具的“娥眉抖擻,家園頹唐”①黃愛玲.娥眉抖擻,家園頹唐——李翰祥的文藝片.黃愛玲.風花雪月李翰祥.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7:26-35.[16]26的女性主義色彩和一以貫之的家國情懷。與此同時,作為邵氏電影發展史乃至整個香港電影史上將傳統戲曲元素融入“三國”題材的少數電影作品,該片又無疑在以戲曲手段來影像詮釋“三國”人物這一方面具有篳路藍縷的探索意義,從而有效拓展了香港電影“三國”改編的影像表現手段,為其后此類藝術實踐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創作審美經驗。
[1] 李翰祥.影海生涯[M].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7.
[2] 蔡美云.《隋唐演義》的女性觀[J].明清小說研究,2007(3):290-299.
[3] 馮夢龍,蔡元放.東周列國志[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4] 胡世厚,衛紹生.二難選擇——《三國演義》的女性觀評析[C]//陳其欣.名家解讀《三國演義》.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184-195.
[5] 羅貫中.三國演義[M].毛宗崗,評點.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6] 劉再復.雙典批判: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7] 鄭鐵生.《三國演義》敘事藝術[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
[8] 周曉琳.男權話語的產物——《三國演義》女性形象論[J].四川師范學院學報,2002(6):71-74.
[9] 蘇 濤.浮城北望:重繪戰后香港電影[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10] 蔣 勛.藝術手記[M].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
[11] 張 徹.回顧香港電影三十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
[12] 藍 凡.邵氏黃梅調電影藝術論[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37-43.
[13] 福斯特.小說面面觀[M].馮 濤,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14] 貝拉·巴拉茲.電影美學[M].何 力,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3.
Adaption of the Image of Diao Chan in the Movie Diao Chan Produced by“Shaw Brothers(Hong Kong)Limited”
WANG Fan
(College of Literature,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
The movie Diao Chan,produced by“Shaw Brothers(Hong Kong)Limited”focused on the plot that Wang Yun killed Dong Zhuo through honey trap appeared in the novel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on the one hand,manifests Diao Chan’s first choice of righteousness;on the other hand,the movie specially give play to Yellow Plum Opera in remodeling the leading character,Diao Chan,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unique explanation on the novel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from Hong Kong films in 1950s,but also discloses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singing’s significance for adaption on classical literature.
Diao Chan;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remodeling of character;traditional opera singing;literary adaptation
J905
:A
:2095-4476(2017)03-0015-05
(責任編輯:陳道斌)
2016-12-05;
2017-03-03
王 凡(1984—),男,陜西西安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