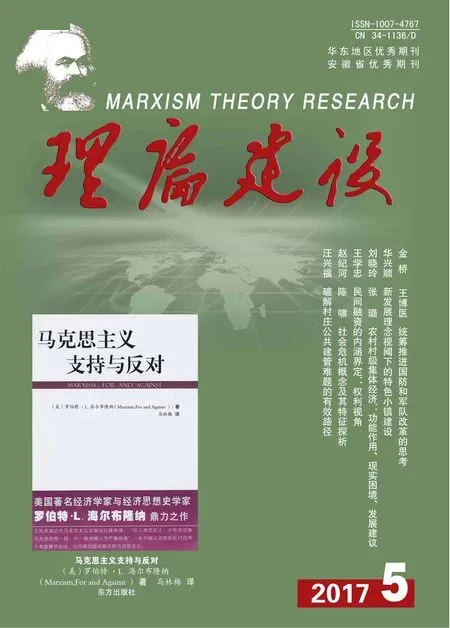中外文摘
中外文摘
司法體制改革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當前,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場廣度和深度都前所未有的改革,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和軍隊的方方面面,牽涉到上至黨和國家、下至人民群眾的錯綜復雜的利益格局,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如何選好改革突破的方向、確定改革的方案,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直接影響到改革的進展與成效。
改革現實展現出蘊含規律的歷史一致性,無論習近平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還是正在向縱深發展的改革實踐,都將司法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習近平在對司法體制改革作重要指示時強調,司法體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中居于重要地位,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意義重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通過了兩份文件,一份文件是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另一份文件則是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據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依法治國對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且,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下簡稱“中央深改組”)2014年1月舉行第一次會議以來,司法體制改革一直是議事的重要內容。據統計,僅2015年中央深改組就審議了22份司法改革文件,占全年審議文件的1/3;截至2016年10月,中央深改組總共召開了27次會議,其中21次涉及法治建設議題,18次涉及司法體制改革;到2017年7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確定的129項司法體制改革任務中,118項已經出臺改革意見,11項正在深入研究制定改革方案。由此可見,司法體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將司法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是一項意義深遠的重大戰略決策。從司法權的性質來看,司法權是一種判斷權,即對案件事實和法律適用的判斷權和裁判權。這是一種被動性的權力,其對社會生活的介入以當事人提起糾紛為前提。“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的力量與財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動的行動”,是各項國家權力中最弱的權力。孟德斯鳩認為,“司法權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不存在的”。換言之,司法權是最不危險的權力,在國家權力結構調整過程中所涉及的利益較小。因此,將司法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改革風險相對較小,最容易達成廣泛共識,最能避免社會動蕩,實踐操作起來也比較容易。而且,司法制度本身是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體制改革本身便具有政治改革的試點意義,可以作為其他領域改革的試金石,為其他領域的改革積累經驗。在某種意義上,司法體制改革是我國能否推行法治、能否全面推行國家治理體系法治化的試金石,也是一根非常重要的 “操作杠桿”。
從司法的功能來看,司法作為一種規范有效的糾紛解決機制,在現代社會發揮著社會穩定器和政治穩定器的作用。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各種社會矛盾突出,需要司法化解糾紛,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精神文明不斷發展,人民的物質、精神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但隨之而來的民事法律關系也愈發復雜,民事糾紛數量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態勢。而且,當今社會處于矛盾高發期,刑事案件的發案量居高不下,尤其是新型犯罪、金融犯罪、網絡犯罪頻發,這些對于社會治理都是巨大的考驗,司法機關承擔著刑事案件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的法律義務,如何提高司法能力以應對大量、復雜的刑事案件,以維護社會治安、保障人民安全,亦為司法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司法作為一項終局性權力,需要為社會主體提供有效的權利救濟渠道,尤其對于行政權之不當侵害,更需要司法來提供救濟,以保障公民合法的財產權利與人身權利。習近平指出,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權利一定會得到保護和救濟,而違法犯罪活動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懲罰。一旦司法的運轉出現問題,大量的社會矛盾將無法得到化解,社會治安將無法得到保障,公民權利將無法得到救濟,這些將對社會秩序構成重大威脅,容易引起社會混亂。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特別是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正在不斷推進。關乎這些改革成效的,不僅是這些改革舉措自身科學與否,也與改革的環境密切相關。也就是說,改革、發展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沒有穩定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一切改革都無法有序推進。而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需要司法予以保障。司法作為一種定分止爭的常規性解決機制,其所具有的公開性、平等性、參與性、終局性等特質,決定了其具有最高的權威和最終的糾紛解決功能,對于改革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可以提供制度化的緩釋機制。可以說,司法是社會、政治的穩定力量,它能夠促進社會的秩序化和規范化。作為一種消除社會矛盾的常規性機制,司法常被稱作政治穩定的“安全閥”。從這個角度來講,司法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和基礎。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需要從法治上提供可靠的保障。
司法體制改革也是針對我國司法實踐提出的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司法實踐中,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司法人員作風不正、辦案不廉等問題十分突出,這不僅影響到司法應有功能的發揮,也影響到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而公正則是司法的靈魂和生命。“一次不公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如果司法這道防線缺乏公信力,社會公正就會受到普遍質疑,社會和諧穩定就難以保障。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靠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決不能讓不公正的審判傷害人民群眾感情、損害人民群眾權益。
總之,司法在國家治理和改革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目前司法能力、司法公正亟待提高的現狀,使得司法層面的改革、尤其是體制性改革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和重要突破口。將司法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對于理清改革步驟、有序推進改革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將司法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是習近平司法體制改革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寶貴經驗。
作者:陳衛東,原文《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經驗——習近平司法體制改革思想研究》刊發于《法學研究》2017年第5期。(王子晨 摘)
習近平總書記法治理論的重要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法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無論是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建設,還是執政黨依規治黨、依法執政建設,抑或是法治社會建設,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法治建設之所以能取得這些重大進步和成就,是與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創新的法治理論的指導分不開的。習近平總書記法治理論的創新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法治宏觀理論的創新,也包括法治制度理論的創新,還包括法治運行環境和法治運作方式理論的創新。
一、習近平總書記對法治宏觀理論的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對法治宏觀理論的創新主要體現于他關于法治的性質、功能、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體系、內容和基本特征的一系列論述。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傳統法治理論認為,法治的基本功能是控制政府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法治的諸多創新論述將傳統法治理論大為向前推進了一步。他指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2017年5月3日,他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進一步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法治建設將承載更多使命、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專制時代的法治理論認為,法主要是用于治民的。韓非說,“治民無常,唯治為法”。現代法治理論認為,法是國家制定和認可的,法治主要是指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控制國家公權力。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論斷全然區別于專制時代的法治理論,也超越了一般現代法治理論。他將法治的范圍從國家和政府擴大到社會和執政黨,將法的范圍從國家法律擴大到社會規范和黨內法規。這是對現代法治,特別是對中國現代法治特色的一個全新描述,也是對現代法治,特別是對中國現代法治發展道路的一個全新設計。
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習近平總書記這一論述是關于社會主義國家語境下黨的領導與法治關系的重大理論創新。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理論輕視法治。列寧說,“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提出這一論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有其道理的。但是,當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共產黨掌握了國家政權,由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以后,再 “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就必然導致權力濫用和腐敗,最終動搖其執政根基。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即開始加強法制和法治建設,1999年法治入憲,黨的十六大更是提出執政黨依法執政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 “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的論斷,清晰明確地為兩者的關系定位,既避免歷史上輕視法治、踐踏法治的錯誤重演,又防止只講法治而否定黨的領導的新的錯誤傾向。
二、習近平總書記對法治制度理論的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對法治制度的理論創新主要體現于他關于改進立法,保障良法善法的供給、推進執法,促進法律的實施、改革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一系列論述。
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質量的根本途徑。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法治建設在立法方面的主要任務是解決“有法可依”的問題。但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以后,法治建設在立法方面的更重要的任務乃是提高立法質量的問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注重依法治國過程中的良法、善法的供給問題,他引用北宋王安石的名言:“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他認為,我國目前雖然總體上有法可依,但立法質量尚有較大不足:“有的法律法規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愿不夠,解決實際問題有效性不足,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還有就是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爭權諉責現象較為突出,有的立法實際上成了一種利益博弈”;另外,“一些地方利用法規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對全國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造成障礙,損害國家法治統一”。怎么解決良法、善法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根本途徑是“要完善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機制,創新公眾參與立法方式,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和建議”,使立法尊重和體現客觀規律,保障立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2014年,他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又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他指出,“‘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實施,束之高閣,或者實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無濟于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點應該是保證法律嚴格實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針對怎么保障法律的嚴格實施,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提出五點要求,一要推進權責法定;二要建立合法性審查機制;三要理順執法體制和完善執法程序;四要加強政府內部權力制約;五要推進政務公開。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司法在一個國家法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基于我國司法領域一個時期以來存在的司法不公問題,“辦金錢案、關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習近平總書記引用英國哲學家培根的話指出其嚴重危害,“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他進而指出,“如果司法這道防線缺乏公信力,社會公正就會受到普遍質疑,社會和諧穩定就難以保障”,“司法不公的深層次原因在于司法體制不完善,司法職權配置和權力運行機制不科學,人權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正是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對司法不公現象和原因的深刻分析,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對司法體制和司法運行機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如推動省以下司法機關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法院、檢察院、推進司法去行政化,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等。
三、習近平總書記對法治運行環境和法治運作方式理論的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對法治運行環境和法治運作方式的理論創新主要體現于他關于全民守法、全社會信仰法律,建設法治社會,反腐敗標本兼治、從嚴治黨,建設嚴格依規治黨、依法執政的執政黨和提高各級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治國理政能力等一系列論述。
法律要發揮作用,需要全社會信仰法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不僅需要政府依法行政,整個公權力依法運作,還需要有政府依法行政、公權力依法運作的法治環境,即需要建立法治社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律要發揮作用,需要全社會信仰法律”。他引用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話,“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但是,“我國是個人情社會,人們的社會聯系廣泛,上下級、親戚朋友、老戰友、老同事、老同學關系比較融洽,逢事喜歡講個熟門熟道,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權力領域,就會帶來問題,甚至帶來嚴重問題”。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引導群眾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逐步改變社會上那種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現象”;“要引導全體人民遵守法律,有問題依靠法律來解決,決不能讓那種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現象蔓延開來,……誰違法就要付出比守法更大的代價,甚至是幾倍、十幾倍、幾十倍的代價”。只有這樣,才能逐步在廣大干部群眾中樹立法律的權威,逐步使廣大干部群眾樹立對法律的信仰,建立法治社會。
管黨治黨不僅關系黨的前途命運,而且關系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習近平總書記基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將管黨治黨提高到關系黨和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高度:“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為了解決從嚴管黨治黨的問題,保證從嚴管黨治黨的實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創造性地提出了四個 “著力”和四個“統一”的要求。四個“著力”是:著力從嚴從細抓管黨治黨,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著力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嚴抓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落實;著力從作風建設這個環節突破,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著力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四個“統一”是:堅持高標準和守底線相統一;堅持抓懲治和抓責任相統一;堅持查找問題和深化改革相統一;堅持選人用人和嚴格管理相統一。只有通過這四個“著力”和四個“統一”,才能把執政黨自身建設好,從而實現依法執政、依法治國的法治總體目標。
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 “關鍵少數”。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領導干部對法治的信念、決心、行動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特別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在治國理政過程中 “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要“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謀劃工作要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問題要運用法治方式”,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領導干部要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帶頭遵守法律、執行法律,帶頭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領導干部要把對法治的尊崇、對法律的敬畏轉化成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只有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真正信法、尊法、守法、用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體目標才有可能實現。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法治的上述論述和他關于法治的其他許多論述,均閃耀著法治思想創新、法治理念創新、法治理論創新的光芒。特別是在法治理論創新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帶頭實現了他對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所提出的要求:理論一定要體現原創性、時代性,要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創新是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永恒主題,也是社會發展、實踐深化、歷史前進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的法治理論創新正是對他自己關于哲學社會科學這一論述的最好詮釋和實踐。
作者:姜明安,原文《習近平總書記法治理論的重要創新》刊發于《人民論壇》2017年第26期。(王子晨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