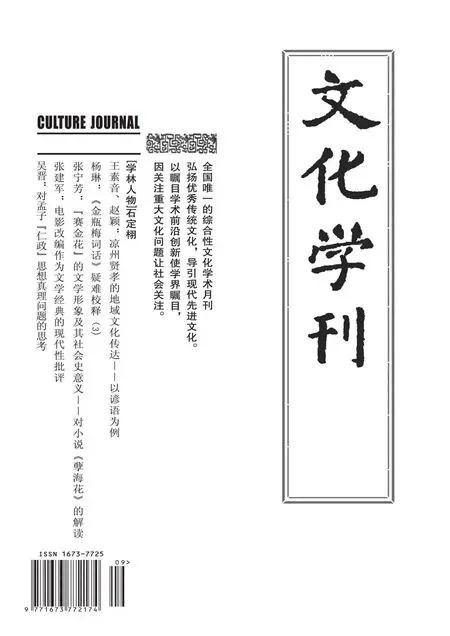陜西關中地區喪葬習俗探析
常經宇 孫永剛
(赤峰學院,內蒙古 赤峰 024000)
【辨風正俗】
陜西關中地區喪葬習俗探析
常經宇 孫永剛
(赤峰學院,內蒙古 赤峰 024000)
關中地區的葬俗較多地繼承了傳統的喪葬文化,雖然隨著時間的發展,葬俗的內容發生了很多變化,但在這種歷史的變化中,人們形成了一整套嚴密而繁復的禮儀。看似簡單的喪葬習俗,其實體現了生者對于死亡的認識和追求、串聯了生者間的人際互動和社群關系的整合。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傳統的喪葬習俗遭到了外來文化的強烈沖擊,這種沖擊使關中地區的喪葬習俗呈現出明顯的量變態勢,這種文化因素的變與不變,正是生產方式多元化和定居式農業瓦解的最直觀的體現,也讓人們對死后世界的態度由向往變為對現實的追求。
喪葬;關中地區;葬俗
喪葬,包括兩方面內容,即喪與葬。喪,亡也,從哭從亡;葬,藏也,從死在茻中[1]。喪葬體現了生者對死者的態度、儀式和處理方式,包括物質和行為等多方面內容。喪葬習俗不同于字義解釋,它不是兩條獨立的發展路徑,而是交織在一起的儀式組合。
對于喪葬的研究,學術界有著不同的視角。徐吉軍先生[2]和張捷夫先生[3]從歷史學角度分析了不同時期、不同地方的喪葬禮儀過程制度,馬惠娟先生[4]和李彬先生[5]從社會學的視角探討了喪葬儀式的社會功能,巫鴻先生[6]從美術學的角度解析了人對墓葬和死亡的精神認識。除開考古發掘的遺跡和遺物,人們對于喪葬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學的調查,并且調查的對象主要針對少數民族地區,忽視了對關中地區尤其是漢族的觀察。雖然關中地區的傳統文化在不同時期都遭受過各種文化的沖擊,文化面貌的改變相對較大,但是作為傳統文化核心的喪葬習俗,卻在歷史的動蕩中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形成了一整套嚴密而繁復的禮儀。喪葬習俗在關中各地雖有差異,但總體面貌略同,本文便以關中地區的渭南市作為分析對象。
一、關中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
關中并非是一個行政地理區劃,而是一個自然人文地理概念。從自然地理的視角來看,關中地區指秦嶺山脈以北,子午嶺和黃龍山以南,隴山以東,潼關以西的廣大地區[7]。南北寬約 10-80 公里,東西長約360公里,將近800里,故人們形象地將關中地區稱為“八百里秦川”。關中地區在氣候條件上屬于溫帶大陸性氣候,從地貌單元上來講,其主體為涇渭流域的河流谷地、黃土臺地,因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而適宜農耕生產。
從人文地理的視角來看,最早提及并大量使用關中這個概念的,是司馬遷編著的《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貨殖列傳》記載: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8]。由于不同時期軍事戰略目的的不同,關中的范圍時有伸縮。
二、喪葬習俗的內涵分析
作為多種儀式復合體的喪葬習俗,其內容包括物質載體、禮儀程序和喪葬觀念三個層面。這些內容層面在人們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了嚴格的明文規定,而這些規定便一直以儀式流程的形式傳承下來。
喪葬習俗的程序主要包括:初喪、發喪、吊喪、暖喪、成服、請靈、走村、迎飯、入殮、下葬和宴飲等內容。由于對于喪葬流程的描述,以往文章多有分析,本文在此不再贅述。
(一)喪葬習俗的矛盾性
作為靈魂的居所,陰間一直為人所恐懼。它是包含著苦難與輪回的幻想地,是人們不愿意去觸碰而又不得不去面對的問題。
在喪葬習俗的諸多儀式中,矛盾是一直貫穿于生者始終的態度。親人的去世,對人們來說是悲痛而又不舍的情境。人們祭奠、吊喪、祈福,他們不愿意一個鮮活的生命就這么離人而去。人們用數天的時間等待,等待生命重新回到陽間。可當人們真正意識到親人已經去世的時候,對陰間的恐懼、靈魂的驚擾,又讓他們對死者敬而遠之。人們期望死者的靈魂能找到回來的路,但又不希望他找到家的位置;人們希望陪伴在他的身旁,卻又擔心他對人們造成侵擾。靈魂在這里似乎成了人們寄托的產物、自身利益的追求。
龍形的靈轎、仙境的靈堂、虔誠的祝語,人們以此希望死者能夠成仙入圣,擺脫生前的貧苦,擁有渴望的生活。但當死者真正下葬以后,人們對他的祝語,便成了對自身利益的渴求,渴望在天上的死者能夠讓生者福祥、讓罪者恕免。
這種生與死的利益矛盾,在各類人群中都廣泛存在。在東南亞和臺灣的許多土著民族中,直到上個世紀還存在著居室葬的風習。陳國鈞先生曾經對臺灣地區的少數民族居室葬進行過詳細的民族學的調查[9]。在十個土著民族中,除了阿美族和雅美族實行公墓葬以外,其他各族居民死后皆葬在屋內的地下。墓葬大多以石板覆蓋或以石塊圍繞四壁并且多隨葬日常生活用品。關于葬于室內原因,泰雅族認為可以得到亡靈的保護,邵族人則認為能防止被野獸撕咬,布農人不愿死者遠離家門,希望在身邊能趨于照顧,但又怕他變鬼害人。可以看到,這些土著民族既因為親情舍不得死者離開,又害怕死亡的危險而與他們多有隔離,在表層上,他們是情感的;在深層上,他們又是功利的。
成仙與求仙的愿景,無不是一種逃避死亡、追求利益的手段,而這種手段僅僅需要簡單的幻想、輕微的付出便可期許達成。成仙與求仙、祝愿與回報、悲傷與害怕,這種矛盾的反差或許就是自私與自利的一種途徑,人們通過構建生與死的窗口,達到自己生的目標和死的延續。
(二)喪葬習俗的男尊女卑
以男女為本的獨立家庭的出現,是與生殖崇拜觀念的轉變有直接的聯系。當處于女性生殖崇拜時期,由于先民不懂得男女結合的作用,單身男女的家庭構成便毫無必要,性也僅僅是作為一種本能的需要,毫無推崇的意義可言。當獨立家庭大量出現,意味著男性生殖崇拜的概念在先民的思維中已經占據主導,只有男女結合,才能產生后代,并且由于男性在生產活動中的主導因素,男性在家庭的地位中逐漸顯現。
《韓非子·忠孝》有云: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10]。可以看出,法家關于夫妻關系的論述,是被上升為與君臣關系一樣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邏輯關系中,而這種男尊女卑的秩序態度得到了秦、漢統治者的高度認同,并被后來的各個朝代所強化,在明清達到了頂峰。男尊女卑的秩序態度在過去的生活中有無數的表現形式:經濟不獨立、政治不參與、教育不允許、婚嫁不自由,這些無形的枷鎖讓附庸成為了她們唯一的生活方式。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各種男尊女卑的習俗受到了社會猛烈的抨擊,女性的權利似乎得到了徹底的解放,但在傳統的喪葬習俗中,男尊女卑的現象還是難以動搖。祭奠不允許參與、靈堂不允許上香、請靈不允許加入,這種不公正的禮儀對待在這個女權主義號角唱響的年代還是根深蒂固。
(三)喪葬習俗的互助性
在喪葬習俗的諸多儀式中,村民的互助貫穿于所有流程的始終。約定成俗的喪葬規矩,毫無怨言的義務幫助,是血緣關系紐帶和農業生產方式的發展。
通常情況下,每個村的村民多為同姓,其間的關系為直系或五服外的親屬。隨著后代的持續繁衍,關系較疏遠的五服外的親屬,便不會再履行孝子的職責,更多情況下只參與幫助,而后來新遷入的村民,也會履行相應的規矩,以便為自家喪事做準備,這是一種息息相關的互惠模式。但這種互助性僅局限于喪葬儀式中,隨著葬禮的結束,人們便會遠遠地避開這件事情,作為一種忌諱,孝男和孝女在特定時間內也不允許到他人家做客。
農業生產在機械化尚未普及之前,群體性是農業生產的基本特征。在農業生產中,一份簡單的田野勞作往往需要數人的協作才能完成,而這樣生產方式的集體性形成了一種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集體性,而喪葬習俗和農業協作便是這種集體性和互助性的具體表現,村落間人群關系的互動和社群關系的凝聚都在此刻得到了有效的串聯。
三、喪葬習俗的變與不變
(一)喪葬用品的變化
在喪葬習俗的諸多儀式中,隨葬品、葬具等喪葬用品是喪葬文化的物質表現和和地域傳統的文化繼承,是考古學判定文化歸屬的關鍵性因素。
一直以來,喪葬用品受文化面貌影響較大,地域之間有較為明顯的文化差異,在喪葬品的物質表現上也便有明顯的不同。但隨著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城鄉一體化高速發展,地域之間的文化差異越來越窄,體現在喪葬用品的物質表現上也越來越共性,外來文化因素快速地融入到本地文化當中,出現了很多變與不變的因素。
紙質品的大量涌現是喪葬用品最明顯的變化。大量過去的隨葬品名目都被紙制品所替代,成為一種簡單的紀念性質的物品,這是迷信的心態在科學的影響下逐漸淡化的物質體現。
外來文化快速地融入到傳統的喪葬用品當中,這在當地人看來是一種財富與身份的象征,但這種物品僅限于生活器。禮儀性強的物品在喪葬文化中的地位難以撼動,仍較多地繼承傳統。
在考古發掘中,一個遺址能經常發現多種文化面貌的器物,甚至以器物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在某個時間段會發生大幅度的變化。分析這種文化因素變化的時候,便不能僅僅依靠生活器的變化就判定考古學文化的變化,而應該更多地參考禮儀性物品的變化。
(二)人群生計的變化
“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這是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對中國村落特點的描述[11]。作為以農業為本的關中地區,定居是人們生計方式最重要的生活載體,因此互助性在喪葬和農業活動中表現最為明顯。隨著人口的增多、教育的普及和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定居的這種常態開始發生了變化,生計方式由逐漸由單一走向了多元,年輕人開始大量走出農村,步入各行各業。喪葬活動的互助性本是由生計方式和血緣關系所發展而來,但隨著生計方式的變化、血緣關系的淡化,這種互助性在城市的喪葬活動中已經取消,在農村的喪葬活動中開始淡化。喪葬活動的大部分儀式也會隨著互助性的消失而走向沒落。
(三)“上禮”的變化
喪葬文化的“上禮”風俗,是血緣關系紐帶下的互惠發展。舉辦一件喪葬活動,對以農業為生計的人群來說是一件花費巨大的事情,為了讓喪葬事宜舉辦順利,親朋便會為主辦喪事的孝子提供應有的幫助。這種為祖先崇拜式而進行的互惠更可以說是一種匯集,是一種社會交往中的內部關系、村落部族的利益關系,而不僅僅是一種兩者間的互惠關系。通過資料的匯集,建立了村民間的合作化關系,規訓了一種相當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組織的集體化。
由史前社會統一的祖先崇拜到以家為中心的祖先崇拜,這種“上禮”的行為,由不計較的不約而同變為以禮單契約為中心的互惠模式,它不僅僅是一種物質互惠,更是一種以農業為本的、祖先崇拜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的互惠。
隨著生計方式的多元化和定居式農業的轉變,這種以祖先崇拜為基礎的匯集變為了以自私自利為基礎的匯集。這種匯集與祖先崇拜一樣,也擁有共同的目標,也擁有不約而同的不計較,互惠的模式沒有發生變化,以禮單為中心的契約仍然發揮著約定成俗的作用。
四、結語
通過對關中地區喪葬習俗的程序和內涵分析可以看出:作為多種特質文化復合體的喪葬習俗,其傳承一直是傳統的關節點。受到家庭本位的社會結構以及以孝道為中心的倫理道德的支持,為死者提供一個理想世界的期望,讓生者激發了無窮無盡的創造力。看似簡單的喪葬習俗,其實體現了生者對于死亡的認識和追求、生者間的人際互動、社群關系的整合和凝聚。
隨著科學的普及和生計方式的多元化發展,喪葬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死后成仙的愿景也變為了現實利益的追求。從喪葬用品到葬俗的變化、從協作方式到匯集目的的變化,這種從表層到深處的文化改變,正是社會變革最直觀的反映,也是社群關系和文化觀念最重要的體現。
[1]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3.
[2]徐吉軍.中國喪葬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3]張捷夫.喪葬史話[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4]馬惠娟.膠東農村喪葬儀式的象征與功能分析[J].文化學刊,2010,(5):131-135.
[5]李彬.金嶺鎮回族的喪葬習俗及其社會功能[J].回族研究,1994,(1):52-56.
[6]巫鴻.黃泉下的美術[M].北京:三聯書店,2009.
[7]史念海,李之勤.陜西軍事歷史地理概述[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
[8]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3.
[9]陳國鈞.臺灣土著社會婚喪制度[M].臺灣幼獅書局,1971.
[10]王先慎.韓非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6.
[11]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責任編輯:董麗娟】
K87
A
1673-7725(2017)09-0073-04
2017-06-16
常經宇(1991-),男,陜西渭南人,主要從事植物考古、史前考史研究;孫永剛(1978-),男,內蒙古赤峰人,教授,主要從事植物考古、史前考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