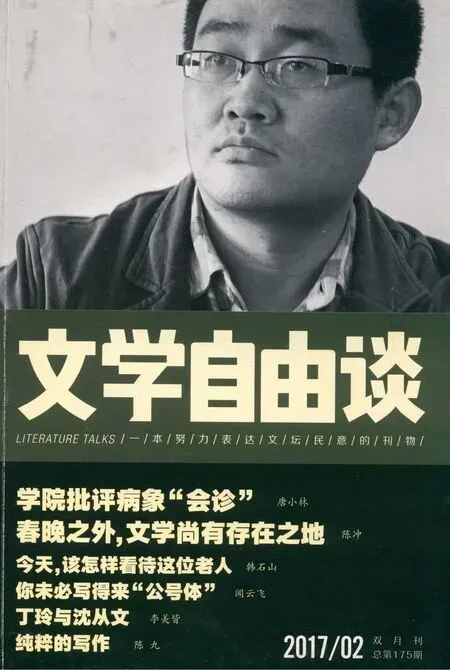學院批評病象“會診”
唐小林
學院批評病象“會診”
唐小林
在當代文壇,學院批評長期廣遭詬病。一些大學已經變相成為學術垃圾的生產基地,某些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早已蛻變成為學術垃圾的“生產能手”。有的學者雖然大紅大紫,著作等身,但其學術“成果”,大都是一些貌似“高大上”,實際上卻缺乏學術含量,甚至在“忽悠”讀者的“學術磚著”。多如牛毛的作家作品研討會,往往成為學院批評家們傾情表演、集體歌唱的人生大舞臺。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文學批評已被某些學院批評家當成了跑馬圈地、為我所用、翻云覆雨的文字雜耍和屠龍術。在這些批評家看來,文學批評是沒有是非標準和審美判斷的,最多只有個人喜好。對于作家的同一部作品,他們今天可以憤怒猛批,明天可以拼命狂捧。總而言之,收鬼和放鬼的,都是這些批評家。他們采取有失批評家尊嚴的方式,跪在地下,一叩三拜,大唱贊歌,將文學批評當成了向當紅作家大拋“媚眼”、求得青睞的文學諛評。在他們看來,所謂文學批評,其實就是向當紅作家溜須拍馬的諂媚書:于是,在眾多的學術期刊中,我們看到了古今中外罕見的肉麻文字。
本文“請出”的幾位批評家,雖只是當代學院批評家中極少數的幾位,但卻有著非同尋常的標本意義。從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癥狀”,集中反映出當今學院批評典型的病灶,反映出我們這個時代學院批評深陷泥淖的典型特征。如何將學院批評的各種頑癥匯總起來,進行科學的研判和醫治,可說是當代文壇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必須時刻面對的一個巨大的難題。
孟繁華:出爾反爾為那般
1993年,賈平凹以“□□□□”“作者刪去XX字”為噱頭的性描寫泛濫成災的小說《廢都》甫一出版,便立即遭到了文壇眾多有識之士的猛烈批判。孟繁華在《賈平凹借了誰的光》一文中,對《廢都》的嚴重病象,進行了一針見血的批判:“作家在描述這些性行為的時候,完全是以欣賞和投入的筆調進行的,它突出表現的是淫蕩的生理快樂,它的敘述語調同《金瓶梅》、《肉蒲團》等所謂奇書已沒有什么差別。不同的是西門慶和未央生毫無歉疚愧悔之感,這倒表現了二位惡人心理上的真實。”孟繁華進一步指出:“《廢都》赤裸裸的‘性描寫’,在現當代文學史上大概是空前的。‘性’的隱秘性和其它涵義在這里已蕩然無存,只剩下人生理需求上的放縱和刺激,從這個層面上說,它僅僅具備了商業的品格。”在孟繁華看來,《廢都》無疑是一部 “淫穢小說”:“我確實無法想象,小說還會淫穢到什么地步呢?”由此,孟繁華將《廢都》比作《花花公子》的“中國兄弟”,稱其與那些不堪入目的黃色淫亂作品相比,不同的只是,它是經過了“嚴肅文學”包裝的“嫖妓”小說。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多年之后,孟繁華卻出爾反爾,像許多影視劇里的窩囊男人一樣,狠狠打自己的臉,公開向《廢都》舉起了投降的白旗。孟繁華當眾檢討說:“我當年也參加過對《廢都》的‘討伐’,后來我在各種場合表達過當年的批評是有問題的,那種道德化的激憤與文學并沒有多少關系。”“經過十年之后,這部作品的全部豐富性才有可能重新認識。”這個重新認識包括:“一、作為長篇小說,它在結構上的成就,至今可能也鮮有出其右者。(筆者按:古今中外浩如煙海的長篇小說經典,其結構難道都不如《廢都》?這究竟是孟繁華孤陋寡聞,還是其故意掩蓋事實?)長篇小說是結構的藝術,很多長篇小說寫不好,不是作家沒有才華,沒有技巧和生活,主要是對長篇小說文體的理解有問題,也就是對長篇的理解有問題。(筆者按:既然對長篇小說的結構理解都有問題,怎么又稱得上是有才華的作家?我真不知道孟繁華發明的是什么太空邏輯)但《廢都》在結構上無論作家是否有意識,都解決得很好;二、小說在思想內容上得風氣之先:賈平凹最早感受到了市場經濟對人文知識分子意味著什么。可以說,這個階層自現代中國以來,雖然經歷了各種變故,包括他們的信念、立場、心態以及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但從來沒有經歷過市場經濟的大潮的沖擊。這個沖擊對當代中國人文知識分子來說,實在是太重大了。”緊接著,孟繁華將對《廢都》的贊美,進一步推向了高潮,激情澎湃地宣稱:《廢都》“提供了知識階層當代性的一個范本”。
有誰能想到,世界上居然會有如此既唱紅臉又唱黑臉的“雙料”文學批評家?當年被孟繁華批得狗屎不如的《廢都》,搖身一變,又被他說成是世界上美麗無比的鮮花。但誠如學者周澤雄先生所說:“《廢都》的庸常性質,在我心里早已牢牢固定,就我個人而言,只要我的文學鑒賞力一息尚存,它就不會重見天光。”“對曖昧情色抱有好奇,原是人心之常;作為一種偷襲讀者下三路激情的手段,它也始終存在,只是真正的作家不屑為之罷了,故即使偷襲成功,也只是商業性成功,與文學成就貌合神離。”周先生還提到一些人搬出據稱是季羨林說的“《廢都》二十年后將大放光彩”來“作證”的做法:“季先生已駕鶴西去,我們無從核實那句話的真偽。不過我可以確認,季羨林雖在佛教文化和中亞語言的研究上成果斐然,但沒有證據表明,他還具有值得刮目相看的文學鑒賞力……喋喋于所謂季老的預言,只能說明,他們下定了忽悠到底的決心,同時堅信讀者都是不明真相之輩,只會唯名人之言是從。”
其實,孟繁華對同一部作品做出前后矛盾、判若兩人的評價,并非孤例。在《在不確定性中的堅持與尋找》中,孟繁華盛贊張煒的《你在高原》:在當下這個浮躁、焦慮和沒有方向感的時代,能夠潛心20年去完成它,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和奇跡。這個選擇原本也是一種拒絕,它與艷俗的世界劃開了一條界限。450萬字這個長度非常重要:與其說這是張煒的耐心,毋寧說這是張煒堅韌的文學精神。因此這個長度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高度。但轉眼之間,孟繁華又奚落張煒:“寫這么長,真是考驗我們的耐力和閱讀能力。”在這樣的文學批評中,孟繁華就像是“百變天后”,誰能告訴我,哪一個才是真實的孟繁華?
張清華:“神話”的制造者
在眾多的學院批評家中,張清華最大的“特長”,就是在文壇制造神話。他只要開動起贊美機器,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 “醉駕”,一路狂奔,根本就剎不住車。無論是詩人,還是作家,只要張清華喜歡,一律都會被他吹捧得通體完美,光芒四射。
我們知道,詩人海子可說是當代文壇的一個“神話”,對于這樣一個“神話”,人們已經有所警覺;而學院批評家張清華恰恰就是“海子神話”的制造者。張清華對海子大而無當的飆捧,簡直令人咋舌,就像面對明星偶像時粉絲們在舞臺下發出的一聲聲尖叫,除了刺耳,還是刺耳:“在人們回首和追尋當代詩歌發展的歷史脈絡時,越來越無法忽視一個人的作用,他不但是一個逝去時代的象征和符號,也是一盞不滅的燈標,引領、影響甚至規定著后來者的行程。他是一個謎,他的方向朝著靈光燦爛的澄明高邁之境,同時也朝向幽晦黑暗的深淵。這個人就是海子。”“這位集詩人和文化英雄、神啟先知和精神分裂癥患者于一身的人,已用他最后的創作——自殺,完成了他的生命和作品,使它們染上了奇異的神性光彩與不朽的自然精神。由于這一切,海子對于當代詩歌的發展產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他在詩歌和世界幽暗的地平線上,為后來者亮起了一盞閃耀著存在之光的充滿魔力又不可企及的燈,使詩歌的空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廣闊和遼遠。”
僅僅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出,張清華的確是把做文學批評當成了寫詩。但文學批評并非是站在高山之巔,血脈僨張地抒發豪情。張清華的文章,缺乏的是客觀冷靜的學術分析,而是大量采用詩歌創作中常見的抒情、比喻、想象和夸張,將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混為一談,以致讓人在閱讀時,就像看到了一個激情澎湃的抒情男高音,總是情不自禁地在引吭高歌。
在當代的學院批評家中,拿海子的死亡來說事的,并非只有張清華一人,但將海子的死亡吹捧得如此出神入化的,卻非張清華莫屬。事實上,海子的死亡,只不過是一個精神分裂者在人生失意之后發生的不幸悲劇。但為了吸引眼球,追求“學術成果”,張清華不惜人為地拔高海子死亡的意義:“尼采或許通過對上帝的否定而泯滅了自己內心的神性理想,海子則因保持了對世界的神性體驗而顯得更加充滿激情和幻想,大地的神性歸屬使他心迷神醉并充滿體驗的力量,由此生發出主動迎向死亡的勇氣。”在張清華的眼里,海子簡直比屈原還要屈原,比古今中外任何一位詩人都偉大,是海子以他領悟神啟的超凡悟性和神話語義的寫作,提升了這個時代的詩歌境界。張清華甚至妄下斷語說:“對海子來說,死亡意味著他走向他所敘述的神話世界的必由之路與終極形式,是他內心英雄氣質的需要和表現形式。”在我看來,任何對海子死亡的妄加猜測和任意拔高,都是對死去的海子極大的不尊重。倘若海子地下有知,他也會為張清華的顢頇和這樣不著邊際的浮夸感到不安的。
為了在文壇制造神話,張清華常常都是在一種心潮起伏的跪拜式的狀態下進行寫作的。他如此飆捧莫言說:“尤其是在《豐乳肥臀》和《檀香刑》之后,莫言已不再是一個僅用某些文化或者美學的新詞概念就能概括和描述的作家了,而形成了一個異常多面和豐厚的、包含了復雜的人文、歷史、道德和藝術的廣大領域中幾乎所有命題的作家。”“莫言是在藝術的范疇里做出了最驚險、最具有觀賞性和‘難度系數’的動作,這使他成為了最富含藝術的‘元命題’的、最值得談論的作家。”(筆者按:在筆者的記憶中,“最最最紅”“最最最偉大”這樣的極限用法,早已被視為敝屣,成為笑談。 )
張清華等學院批評家“巨大的學術成就”就是,開創了一種新型實用、專門用于諂媚作家的文體——“最字體”。在張清華的眼中,莫言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歡樂》中長達八萬字不分段的極盡擁擠和憋悶,堪稱是形式上的極限;《酒國》中通篇漫不經心地將寫真與假托混為一談的敘述,堪稱是荒誕與諧謔的極限;《檀香刑》中劊子手趙甲以五百刀對錢雄飛施以凌遲酷刑的場面描寫,堪稱極限……”總而言之,當代其他的作家,沒有哪一個能夠像莫言這樣對人類學的豐富要素有如此的敏感和貼近的理解。莫言的小說,不是被張清華飆捧為天籟之作、極致和奇跡,就是被夸耀為首屈一指,無人可比的“偉大的小說”。
的確,張清華就像是當代文學批評家中的夜鶯,只要一張開歌喉,就要放聲歌唱。他恨不得為那些當紅作家拼盡全力,唱出世界上最美麗的贊歌。在張清華的文章里,不需要邏輯支撐,更不需要令人信服的學術分析,一切都是根據個人的喜好為評價標準。這里我們不妨來看一看他運用排比手法,書寫的一段充滿激情的贊美詩:
顯然,母親這一形象是使《豐乳肥臀》能夠成為一部偉大小說、一部感人詩篇、一首壯美的悲歌和交響樂章的最重要的因素,她貫穿了一個世紀的一生,統合起了這部作品“宏偉歷史敘述”的復雜的放射性的線索,不僅以民間的角度見證和修復了歷史的本源,同時也確立起了歷史的真正主體——處在最底層的苦難的人民。
作為一部虛構的文學作品,我不知道,莫言憑什么能夠——像張清華所說的那樣——見證和修復歷史的本源。倘若歷史的本源能夠被一部小說隨便修復,這樣的歷史豈不成為了泥塑木雕的人造工藝品?文學批評絕不是寫詩,隨時都可以“燕山雪花大如席”“黃河之水天上來”的。
張學昕:在文壇“大煉鋼鐵”
1958年,在中國的大地上,曾掀起過一場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的轟轟烈烈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以及糧食畝產超萬斤的浮夸風。在浮夸風之下,連教授也要按其所種的農作物產量來評級,畝產1000斤只能當五級教授,2000斤的當四級,3000斤的當三級,4000斤的當二級,5000斤的當一級。
讀張學昕的“學術文章”,我的腦子里總是情不自禁地浮現出一幅當年糧食“高產”的美好圖景:社員們樂不可支地坐在高入云天的稻堆上,贊美著他們連肚子都吃不飽的“幸福生活”……
如今,我們雖然再也看不到當年那些隨處可見的“小高爐”,但意識形態里的“小高爐”,卻依然牢牢地矗立在張學昕這樣的學院批評家們的腦海中。張學昕撰寫學術論文,采用的就是“大煉鋼鐵”和浮夸風似的模式,其學術論文,簡直就像是當年的水稻高產報告。張學昕似乎堅信,只要把中國作家寫作的水平確定為世界一流,向世人大聲宣告他們寫出的都是經典,中國的文學就完全可以用大干快上的方式,趕英超美了。基于這樣的認識,在張學昕的文章中,到處都是對當紅作家令人渾身起雞皮疙瘩似的肉麻浮夸:
多年來,賈平凹的寫作特別注重對文學表達的古典性追求,他的大量作品都表現出“崇尚漢唐”文化的雅致和氣度,并由此開拓出自己的敘述文體,他小說、散文兼工,常常在敘述中漲溢出各自不同文體規范的限制,創造出令人驚嘆的文體。
最令人驚異的是,賈平凹從容地選擇了如此綿密的甚至瑣碎的敘述形態,大膽地將必須表現的人的命運融化在結構中,對于像賈平凹這樣一位有成就的重要作家來說,這無疑是一種近于冒險的寫法,但他憑借執著而獨特的文學結構、敘事方式追求文體的簡潔,而恰恰是這種簡潔而有力的話語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往長篇小說的寫作慣性,重新擴張了許多小說文體的新元素,改變了傳統小說的敘事心態……
我堅信,沒有人會懷疑,相對于同時代的作家,蘇童,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穩健、最富才華和靈氣、最杰出的短篇小說家。
我們在蘇童的短篇小說中看到了一個作家,如何憑借智慧運用最精煉、最集中、最恰當的材料或者元素,表現復雜、豐富、開闊而深遠的內容。
就短篇小說這種文體的凝練、精致和唯美品質而論,蘇童的作品在中國當代短篇小說中是首屈一指的……對一位同樣也擅長寫長篇和中篇的作家來說,我還是忍不住將其稱之為“短篇小說大師”……因為蘇童對短篇小說寫作的酷愛,孜孜不倦的精心耕耘,不僅給他的寫作帶來激情、興奮和快樂,而且給它的閱讀者帶來了無比的幸福。
音樂商要炒作和包裝一個五音不全的人,就夸獎她天生麗質、采用的是原生態唱法。賈平凹絮絮叨叨、缺乏藝術構思、猶如一盤散沙的《秦腔》,曾令許多著名的作家和批評家讀來頭痛。這種忽悠讀者的寫作,居然被張學昕狂捧成了綿密的敘述,是成功的創造和藝術的探險。批評家并非媒婆做媒——麻子也要吹捧成天仙。照張學昕這樣的邏輯,那些不從大門進入而是翻墻入室的人,也可以被稱之為人生的另一種選擇和別樣的追求,是人生的冒險。
我始終覺得,作為一個學人,張學昕似乎從來都缺乏一種理性的思考和客觀的分析。其文章不是以理服人,而常常是以夸張的手法和“演講大師”似的煽情來誘惑人。在張學昕的文章里,動輒就是“假大空”的“最XX”“極致”“驚異”“首屈一指”“無比”“最高成就”……漢語中所有最高級的形容詞,都被張學昕一網打盡。單說“幸福”,倘若蘇童的小說真的能夠給讀者帶來無比幸福的話,那些正在為找工作而煩惱,為買房而憂慮,或被婚姻困擾的人們,從此就再也不用發愁,他們只需人手一冊蘇童的小說,就可以過上幸福的生活,擁有快樂的人生了。
難道文學批評就等于轎夫抬轎子?張學昕寫作的病象,凸顯出學院批評長年的沉疴。其對小說藝術的理解,其實就像一個不得其門而入的門外漢。如:“賈平凹敘事的信心、耐心、功力,直逼漢語寫作的極致。”如果真是這樣,那么賈平凹的寫作水平就遠遠超過了曹雪芹;但稍有一點文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便是《紅樓夢》,也并非完美無缺,而是存在著無可否認的瑕疵。張學昕對賈平凹不顧事實的吹捧,要么是不懂文學,要么是有違學術品格的瞎忽悠。又如:“一般地說,短篇小說對作家的寫作來講,較之長篇、中篇文體有著更高的精神要求和技術衡定指標。這不僅需要作家思考世界的功力,而且需要作家非凡的藝術能力。”小說作為一門藝術,從來就沒有什么技術衡定指標,只有藝術評判的標準。說短篇小說比長篇和中篇小說的精神要求更高,就像說短跑比中長跑對身體的要求更高一樣,完全是只有體育盲才會說出的外行話。而所謂的“精神要求”,可說是張學昕為了顯示其學術“創造力”憑空發明的一個“學術名詞”。
在這里,筆者還想就以下這段“太空語”,請教張學昕先生。我不知道,這段文字,讀者諸君是否已經讀懂,反正我要實事求是地講,盡管文中的每一個字我都認得,但卻無論如何也讀不懂,并且越看腦袋越大:
確切地說,賈平凹《秦腔》的敘述,在努力回到最基本的敘述形式——細部,如同被堅硬的物質外殼包裹的內核,可摸可觸,人物的行為、動作在特定的時空中充滿質感。也許,賈平凹在敘述觀念上,想解決虛構敘事與歷史的敘述,或者說,寫實性話語與想象性話語之間的緊張關系。但是,他更加傾向將具有經驗性、事實性內容的歷史話語與敘述形式融會起來,在文字中再現世界的渾然難辨的存在形態。
與其說這樣的文字是學術論文,倒不如說是張學昕在用繞口令和讀者玩起了腦筋急轉彎。并且我們看到,這種游戲一旦玩上癮,張學昕就會樂此不疲:
這(《秦腔》)是一部真正回到生活原點的小說,它是作家內在化了的激情對破碎生活的一次藝術整合,是智慧與睿智對看似有完整結構的生活表象的真正顛覆和瓦解,我們就在這幅文學圖像中強烈地感覺到了生活、存在的“破碎之美”。
以上這段文字,讓我們真正領略到了什么叫做“不明覺厲”,什么叫做把人當猴耍,更使我們真正知道,夢囈似的文字,也可以故作高深地組合成討好當紅作家的“諂媚書”。
欒梅健:頭腦發熱的學界“粉絲”
眾所周知,那些大牌明星的粉絲,是絕不需要什么音樂知識、懂得什么表演藝術的。他們只需要高舉著“XX,XX我愛你,就像老鼠愛大米”之類的牌子或者熒光棒,發出一聲聲刺耳的尖叫,就可以成為某些明星的“鐵粉”了。
在當代文壇,批評家心甘情愿地為當紅作家喝彩“站臺”,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但像欒梅健這樣經年累月、不遺余力地為當紅作家欣喜若狂、拍手叫好的批評家,的確是當代文壇一道“別樣的風景”。從欒梅健的“學術”文章中,筆者基本上看不出其究竟有多少文學的感悟能力,雖然同為名牌大學的學者,欒梅健的文學鑒賞能力和學術水平與孟繁華、張清華都不在一個檔次。欒梅健崇拜某些當紅作家,這本身并沒有什么不妥,也純屬是私人的事;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誰要是批評欒梅健追捧的作家,欒梅健就會怒不可遏,對批評者進行頭腦發熱的大潑臟水。
魯迅先生早就主張:“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但欒梅健卻只允許說好話,絕不允許別人說半個“不”字。欒梅健將批評某些當紅作家寫作病象的學術文章,強行宣判為別有用心地揮舞著大棒的邏輯混亂的“酷評”。經過欒梅健臟水一潑,正常的文學批評,就被可怕地妖化成為了斷章取義、嘩眾取寵的罵派文章。
欒梅健的文學鑒賞能力很低,因此只能常常撰寫一些飆捧當紅作家的諛評文章。在《論〈帶燈〉的文學創新與貢獻》中,欒梅健說:“《帶燈》甫一問世,便受到了讀者的廣泛歡迎。‘《帶燈》的電子書版,單本定價十五元,借助騰訊閱讀平臺大量的用戶群基礎及強勢的推廣傳播,獲得了單月過萬冊的銷售成績’,而‘結合全國各地的新華書店及各民營書店等實體渠道,今年年內 《帶燈》銷量有望突破五十萬冊。’在文學日趨邊緣化的今天,五十萬冊的銷售量,在當下的閱讀市場,無論如何都算得上是一個奇跡。”恕我直言,我寧可相信這樣的文字是一份賺得盆滿缽滿的商業報告,也絕不相信這是一篇合格的學術論文。如果僅僅是以銷售量,以及賺錢的多少來評定作品的好壞和貢獻的話,我敢說,《帶燈》和《鬼吹燈》就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
欒梅健對《帶燈》里的文字大雜燴,不但視而不見,反而大談其文學創新,又根本談不到點子上。因此,他只能像路邊的測字先生,故弄玄虛地說:“《帶燈》的突破,主要在于賈平凹采取了他以往小說中從未有過的‘俯視眼光’。這種視角,既不同于他過去駕輕就熟的、從農村底層觀察與描寫的民間視角,也不同于當下文壇流行的、站在歷史和道德高度對社會丑態與官場黑暗加以揭露的反腐小說。”欒梅健飆捧說,《帶燈》最典型地調動了賈平凹四十余年之久的城市生活經驗,及其作為文化名人和級別不低的公職人員的親身感受。
小說畢竟是小說,如果真要說賈平凹這部憑空虛構的小說調動了其什么城市經驗和親身感受的話,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賈平凹換湯不換藥和大炒冷飯的本領。而欒梅健的許多“學術文章”,幾乎都是尋章摘句的“文字串燒”。如其論多位作家文學觀的文章,只不過是將該作家的作品內容進行簡單的復述,然后再引用一些作家本人談文學和小說創作的文字,以及別的學者的評論文章,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就算制作完成了。如:
看賈平凹的文字,既有現代意識,又有傳統氣息,還有民間味道。重整體,重混沌,重沉靜,憨拙里的通靈,樸素里的華麗,簡單里的豐富,達到了語言大師的境界。
這段評論《秦腔》的文字,只不過是移花接木地挪用了謝有順撰寫的《秦腔》授獎詞。至于將賈平凹稱之為是“語言大師”,則清楚地說明,欒梅健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語言大師。在賈平凹的作品中,各種文字差錯和硬傷可說比比皆是。一個連基本語法都不懂,寫了一輩子小說卻老是分不清結構助詞“的、地、得”和時態助詞“著、了、過”的作家,居然被欒梅健稱為“語言大師”,這本身就說明也許才疏學淺的欒梅健自己就不懂語法。
作為一個中文系教授,欒梅健的中文水平,不禁令人擔憂,其捉襟見肘的漢語知識,常常讓人啼笑皆非。如:
在新時期文學之初,他又如饑似渴地關注歐美現代派作品、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和日本的翻譯小說。
“如饑似渴”,出自曹植的詩歌《責躬》:“遲奉圣顏,如渴如饑。”嵇康《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中也有這樣的詩句:“思我良朋,如饑如渴,愿言不獲,愴矣其悲。”在《古今小說·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中,則出現了“如饑似渴”的用法:“吾兒一去,音信不聞,令我懸望,如饑似渴。”形容要求或愿望非常迫切。欒梅健將“如饑似渴”和“關注”相搭配,顯然屬于用詞不當,難免給人一種頭重腳輕的感覺。
在《廢都》、《秦腔》、《古爐》諸佳作已然奠定當代文壇的重鎮地位以后,賈平凹在最近發表的長篇小說《帶燈》中,絲毫沒有顯露出馬虎。
在漢語中,所謂“重鎮”,通常指的是在軍事上占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城鎮,后來也泛指在其他某些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城鎮。說賈平凹的幾部小說奠定了“重鎮”地位,這顯然是一種詞不達意的表述和不顧事實的瞎吹捧。此外,誰能說“絲毫沒有顯露出馬虎”也值得大書特書?
后人常用樸拙而靈秀來形容賈平凹的藝術風格,其實這特性蘊含于他家鄉的石頭中,蘊含于他對家鄉自然、風物的體悟與品賞中。
所謂“后人”,是指后代的人,或者子孫。連常用詞都弄不明白,我真為欒梅健教授感到害羞。生在當代的欒梅健,怎么會知道后代的人對賈平凹的評價?
看到以上這些似通非通、語病扎堆的句子,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欒梅健的漢語水平其實就像洗臉盆里扎猛子,實在是太淺。
在《與天為徒——論賈平凹的文學觀》中,欒梅健不顧事實地說:“多達六十余萬字的長篇小說《古爐》,又被眾多研究者認為是一部精準描寫‘文革’十年浩劫的民族史詩。”據筆者所知,所謂“十年浩劫”“民族史詩”,只不過是出版商為了推銷賈平凹的小說,印在該書封面上的一句廣告語。將書商的廣告語蓄意偷換成學者研究得出的結論,這本身就是對讀者的欺騙。而關于《古爐》中漏洞百出的描寫,已有多位學者撰文指摘。一部人物顛倒、時空錯亂、細節失真,多處穿幫的小說,在欒梅健的眼里,居然成了“精準描寫”的曠世佳作。如此不負責任的海侃神吹,本身就說明,欒梅健的學術態度非常不嚴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