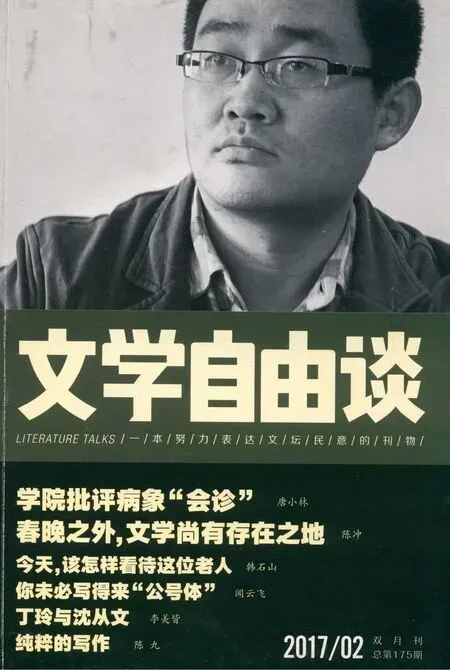春晚之外,文學尚有存在之地
陳沖
春晚之外,文學尚有存在之地
陳沖
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搖滾歌手鮑勃·迪倫。對中國文學界來說,這種事應該不是太突然,因為就在不太久以前,我們也認真討論過崔健可不可以參評魯迅文學獎的問題。這個討論公眾知道的內(nèi)容并不多,人們比較有所了解的內(nèi)容之一,是有個叫謝冕的北大教授,乃力挺派的主力。后來傳出一個消息,說這位北大教授退休后住進了敬老院,于是廣大人民群眾不答應了。這個“不答應了”的“廣大人民群眾”,是個很含糊的群體,有時候在,有時候不在。那里面不一定有聽過謝冕授課的學子,也不一定有對崔健應否參評“魯獎”持有任何看法的人,但他們表示的“不答應”是有力量的。他們這么做也沒有什么特別的道理,或者是因為他們覺得像謝冕這樣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人,“我們”不應該虧待他們,也或者還有別的原因。后來弄明白了,謝教授進的敬老院很高檔,他住進去是想體驗一下那里的高檔服務,不是因為老無所依,廣大人民群眾也就放心了。這個“放心了”的“廣大人民群眾”,也是個很含糊的群體,里面不一定有智商極高的聰明人,也不一定有知識淵博的精英人士,但是他們肯定不會被任何人忽悠,比如那種偽搖滾的自戀自慰。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老無所依了,把你留在哪兒都夠嗆。
正因為我們的生活就是在這樣混混雜雜纏纏繞繞地進行著,所以近幾年來,每年的第二期《文學自由談》,我都會把春晚扯上,一是借借它的話題性的光,同時也是給文學一個不同的角度,比如其中第一篇的標題就叫《文學眼看春晚》。到去年,這事兒有點難以為繼了,因為似乎春晚里不怎么能找到文學了。你怎么能假裝用文學眼,去看找不到文學的春晚?但我也不認為這就說明“文學已死”。我不喜歡動不動就說什么“已死”,況且這事兒真沒那么嚴重。一臺晚會里要不要有文學,完全是主辦者的事,別人盡可不必操心。之所以還想議論幾句,是因為忽然有了一個猜想:沒有文學,不一定是主辦者不想要,說不定是找不到能往里裝進一點文學的寫手了。
這么說真的有點不厚道,姑妄言之,就從比較容易說的地方講。就不說文學性不文學性的了,只說文學里最基本的那個東西:文字。如果把一臺晚會的文字整個兒翻一遍,工程量明顯太大了,還是得隨機抽樣。說是隨機,也還是有點代表性的好,這兒抽的樣就是晚會后據(jù)說頗受點贊的歌:毛阿敏和張杰唱的那首 《滿城煙花》,說是讓人又想起了當年的風采和盛況。當年的風采和盛況我是記得的,就去找來看。很慚愧,毛阿敏的風采一時間沒有抓到,她在舞臺上的形狀,已經(jīng)被據(jù)說要花費上億元的燈光切成了碎片,不過她的歌聲還是讓我記起了當年那上佳的漢語歌詞:你從哪里來,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飛進我的窗口。這是誰的手筆,人們應該還記得,不用再在這里提醒了。可也就在這時,現(xiàn)場傳出的一句歌詞,已經(jīng)像射釘槍里射出的鋼釘,釘在了我的現(xiàn)實感覺上:“每當煙花推動世界年輪”!這是漢語嗎?任何一個能通過小學畢業(yè)考試的學童,應該都能知道,“年輪”不是一種能轉(zhuǎn)動的“輪”,也推不動,不僅虛張聲勢的煙花推不動,就是實打?qū)嵉摹伴L征5號”火箭也推不動。如果這個“世界”指的是地球,那么它一旦長出年輪來,就不可能是一個“球”了,只能是一個圓柱體;而一旦這個年輪轉(zhuǎn)動起來,最可能出現(xiàn)的景觀就是一層層往下掉皮,相當于天崩地裂,“世界”解體。中國人使用漢語已經(jīng)幾千年了,早已形成了嚴格的漢語詩學的規(guī)律和規(guī)則,意象怎樣形成,聯(lián)想怎樣建立,意境怎樣營造,都有特定的途徑,不是字面上有一點重合或近似,就可以硬往一塊去捏——看見一個“輪”字,立刻就有了車轱轆;也不是中紀委下令“老虎蒼蠅一起打”,動物園里的老虎就嚇得躲進老虎洞里不敢出來了。
這其實是一個過程。如果我們用邏輯倒推的方法往以前“捯”,這個過程是可以捯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廣大人民群眾”有時候在,有時候不在;有時候好像不在,其實在。比如想到那些年時,我們都還能想起一些名字——閻肅、喬羽、劉熾、谷建芬等等,我們會說他們是深受廣大人民群眾喜愛的詞作家、作曲家。后來這些名字漸漸從“音樂界”淡出了。你或許還記得,谷建芬“金盆洗手”的時候,說過一句很傷感、但絕對是很清醒的話:我已經(jīng)看得很清楚,現(xiàn)在的音樂界已經(jīng)不需要我這樣的作曲家了。這句話在當時相當?shù)夭缓枚魳方缭趺磿恍枰軇?chuàng)作出優(yōu)美旋律的作曲家了呢?要到那個過程結(jié)束以后,人們才明白為什么不需要閻肅、喬羽、劉熾、谷建芬那樣的詞作家、作曲家了。在那個過程中,為了完成這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很多人付出各自的努力,相當?shù)夭蝗菀住2徽f別的,單說要建立那樣一支規(guī)模宏大、組織嚴密的“職業(yè)觀眾”隊伍,最后達到每年上十億元的產(chǎn)業(yè)規(guī)模,容易嗎?但是,這個任務最終還是完成了。這個過程相當長,做得也不是那么公開透明,再加上種種的遮遮掩掩,很多人都以為它早已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里了。這是可能的,但并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中國歷史的好玩之處,就在于它的不可終結(jié)性。總有人認為存在某種永不結(jié)束的東西,這個主要是讓皇上們鬧的。皇上們當然是萬壽無疆,從理論上到制度上都可以千秋萬代地把皇上一直當下去。但是也會出現(xiàn)一些其他情況,比如皇上身患重病,大臣們不得不跟他討論其身后之事了。看來這是個根本無法討論的問題,皇上怎么會有“身后”之事呢?但中國的大臣們是有足夠的智慧解決這種事的。他們匍伏在地,磕三個響頭,然后開口奏曰:啟奏萬歲,皇上千秋萬代之后……對了,就這么簡單,既然有千秋萬代,就會有千秋萬代之后。
其實,這個“千秋萬代”之后,并不一定真要等很長時間。比如,在某一個“千秋萬代”之后,廣大人民群眾不答應了。他們可能會問,在“千秋萬代”之前的某一個時期,有一段不短的時間20年、30年,偌大一個中國,那么廣袤的土地,那么眾多的人口,為什么竟然沒有出現(xiàn)哪怕一首稍微像回事兒的器樂曲,能夠在音樂會上反復演出并受到聽眾的喜愛?就算是一句單抽出來的旋律,能夠用某種樂器正常地演奏出來,讓人聽了以后能回味上一段時間,有嗎?事實形成之后,真相自然就顯現(xiàn)出來:這是一段幾乎沒有情懷、沒有旋律的音樂史。這種情況的制造者,有可能含糊過去,也有可能被翻出來,誰個說過什么,誰個做過什么,誰個投過哪筆缺德資,誰個賺過哪筆昧心錢,張三李四劉五趙六王二麻子,一個個都被五寸長釘釘在中國音樂史的恥辱柱上。這就是不相信存在一個“廣大人民群眾”的結(jié)果。當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說到“人民”這個詞的時候,并不是所有人都看懂了他臉上那種敬畏的神態(tài)和情懷;而當他和閻肅侃侃而談,對這位優(yōu)秀的詞作家給予極高的評價和期許時,有的人可能正在暗自慶幸,得意于已經(jīng)先行一步,早把那個不需要這樣的詞作家、作曲家的局做好了。
想到這些,我也得為我們的文學界暗自慶幸了。文學界真的還遠遠到不了這一步。春晚里沒有文學了,自然還會有人去看;而春晚之外,文學還有廣闊的天地。就在不久之前,我就讀到過兩部出自年輕女作家的佳作,一部是張悅?cè)坏摹独O》,一部是付秀瑩的《陌上》。這兩部截然不同的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特別令人高興之處,就是都展現(xiàn)出了扎實的、上乘的“描寫”現(xiàn)實的基本功。文學中的“描寫”,相當于音樂中旋律;沒有描寫的文學,跟沒有旋律的音樂是一樣的。我一度有過擔心,覺得文學的這種最基本的能力正在弱化,搞得不好甚至有可能失傳,不想?yún)s在兩位這樣年輕的女作家身上再次閃出光芒!正像曹文軒在為《陌上》所寫的序言里所說:“在一個失去風景的時代,閱讀她的作品,我們隨時可以與風景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