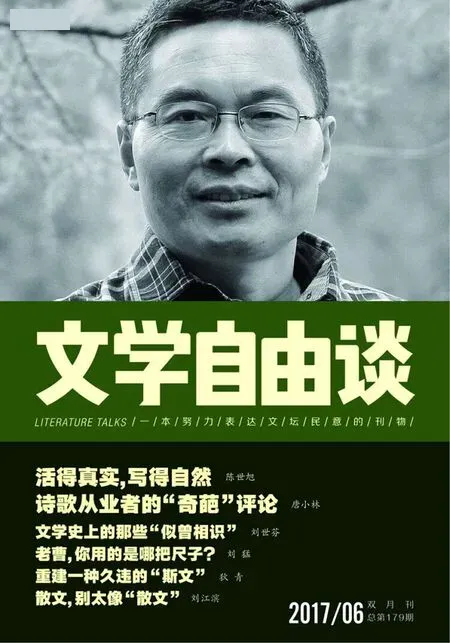寫作是一種專業嗎?
曾念長
寫作是一種專業嗎?
曾念長
寫作是一種專業嗎?這個問題或許不算新鮮,但近些年時常被拿來討論。一方面,我們這個時代的專業化傾向已是大勢所趨,一切事物均以專業化為標準被重新組織起來,每個人身處復雜交織的專業體系之中,以至于社會學家吉登斯大膽斷言:一旦專業失靈,將引發颶風式的社會風險。根據這個邏輯,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寫作是一種專業;即便原來不是一種專業,如今也必須朝著專業化方向發展。否則,在一個連走路和微笑都有專業可言的時代,寫作又要如何立足呢?
今人所理解的專業,是一種現代產物,是知識分類不斷進化的結果。倘若寫作是一種專業,它就必須形成一種專門的知識體系,可以在同行內部進行標準化評估,可以向未來同行傳授。按照這種要求,這個時代出現了一門“寫作學”,并且建立了一整套面向寫作同行的知識傳播體系。這其中最具參考價值的,或許當屬美國高等院校的創意寫作碩士和創意寫作工坊。如今,這一整套技術標準和教學系統也被引介到中國,在國內形成了寫作研修熱潮。不少名校開設了創意寫作專業碩士點,許多年輕作家魚貫而入,脫穎而出,似乎未來文壇的中堅力量正誕生在這條知識生產的流水線上。我們討論寫作是否構成一種專業,其實和當下一撥接一撥的寫作研修熱有關,也是一個頗為應景的話題。
以上只是略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始終有人懷疑是否存在寫作這樣一種專業。懷疑者通常會列出一長串名單,用來說明許多杰出作家未曾接受過任何專業訓練。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魯迅棄醫從文,似乎從一個醫生轉變為一個作家,如平常人切換電視頻道這般簡單。還有余華,從一名牙醫華麗轉身為一名作家,在外人看來似乎也是不費吹灰之力。可惜這些盡人皆知的案例雖然頗有看點,有時也讓那些欲步其后塵者熱血沸騰,但在邏輯上卻是破綻百出:我們何以證明,他們不是通過自學成才步入寫作這個專業的呢?
有力量的懷疑,不是來自那種模棱兩可的外部猜測,而是來自眾多杰出作家的自我否定和現身說法。他們聲明,這個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種可以標準化操作且可普及推廣的寫作知識。當福克納被問及是否存在寫作的秘訣時,他果斷回答說沒有,倘若有,那就是不停地寫。
還有更極端的例子,比如普魯斯特,公然否認智力在個人寫作中的有益作用,甚至全然推翻前輩作家對后世天才作家的必然影響。在他看來,一切天才從零開始。這個零,意味著一切累積性知識的消失,即便一個作家在寫作上貢獻出了獨特智慧,也不可能被復制到其他作家身上。僅憑這一點,寫作是一種專業的假設就站不住腳了。因為可復制性和可累積性正是人類經驗被塑造成一種專業的重要前提。一切科學知識都是可復制的,不因接受個體的差異而發生傳播變形;一切科學知識也是可累積的,呈現出線性增長的趨勢。但寫作不是科學,充其量只是一種可能會涉及一點點科學知識的手藝活兒。寫作的發生因人而異,且如西緒弗斯的寓言所揭示的,時時顯示出從頭再來的悲劇意識。
一些作家否認寫作是一種專業,是因為他們看到了知識和手藝這兩種寫作要素的不同。知識依賴于人的智力,而手藝卻存乎于人的心靈。一個人有很好的智力,掌握了大量有關寫作的知識,但他能否將這些知識轉化為手藝,一直是存疑的。《莊子》講到了一則“輪扁斫輪”的典故:制造車輪的手工藝人輪扁,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狂傲,連齊桓公捧讀的圣人之書,也被他視為糟粕了。這是對知識的不信任,后人自然可以嘲笑輪扁的眼界之小,卻也不得不承認,作為一個手藝人,他有看待事物的獨特視角。在輪扁看來,斫輪這種手藝活兒“得之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倘若訴諸有形之法,精華早已不存了。“輪扁斫輪”的典故被陸機、黃庭堅等詩詞文章大家反復引用,以此延續了一種古老的態度:在寫作這個行當里,知識與手藝是不能對等轉換的。
杜甫晚年作《偶題》,以詩代論總結自己一生的創作,開頭兩句著實驚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按照杜甫的說法,寫作實乃寸心之術,精微奧妙,充滿了不確定性,得失無法為外人道也,自然也就無法轉化為某種通用的知識,以之指導別人的寫作。但這并不意味著寫作是一種怎么都可以的活兒。在同一首詩里,杜甫又說道:“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從中可以看出,杜甫早年學詩,其實是有法可依的,自弱歲之年就已熟練于心了。這個法,就是以知識形態存在的寫作,它可以講授,又未嘗不是一種專業要素呢。
從“有法”到“無法”,正是多數有成就的作家必須走過的寫作進階路線。但也不是每個作家都入得“無法”之堂奧,因此難免被“有法”所困,終其一生也走不出一個有形的天地。這是兩種寫作類型,也是兩種寫作境界。
清代吳修齡有一觀點:“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為飯,詩則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吳氏所說的文與詩,并非實指文體,而是泛指實用性寫作與精神性寫作的區別。這可從他的后續論述中見出其真實含義:“啖飯則飽,飲酒則醉。”對于生產者來說,做飯是可以后天教練的,而釀酒得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領悟力。關于這一點,我有切身體會。我的父親,不善處理生活實務,這方面往往是一塌糊涂,但每逢家中釀酒,就得依賴他的自然天成的手藝。而我的母親,懂得生活的世故,理得俗世的規矩,卻是怎么也釀不出一壇好酒來的。
寫作大抵如此。實用性寫作可以依賴于某種有形之法,而精神性寫作,光有智力和體力,未必就能奏效。關于后者,古人早有不同程度的領悟。曹丕在《論文》中說道:“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這個“氣”,其實正是古典時期的精神性存在。曹丕論述了精神性寫作的特殊意義,開辟了一個時代,遠非孔子時代的詩教觀能夠涵蓋得了的。孔子的詩教意在化俗,因而是可傳授的,所以誕生了《詩三百》這樣發行量巨大的選本性教材。但是曹丕從寫作的角度看問題,發現了個體精神的差異性,不僅“不可力強而致”,而且“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寫作是不是一種專業?我們依然無法簡單做出一個判斷。倘若較真,我們就得深究,哪一種寫作可以授業傳道,哪一種寫作只能寸心感知。我們都知道,應用文寫作有具體規范,盡管乏味,卻可以在課堂上講授,現學現用。各種知識性寫作和思想性寫作,比如學術論文和評論文章,更多依賴邏輯、術語和觀點,也是可以做到訓練有素的。而文學寫作呢,涉及人類復雜的情感體驗和精神認知,則要復雜得多。在這個時代,文學雖然不再像古時的文章一樣無所不包,但依然還是一種寬泛的存在。它的一個極限是潛入人類的精神深淵,如暗夜里的潛行,一切來自白晝的理性法則都有可能是失效的;另外一個極限則與我們的俗世生活相聯,與人民同呼吸,與市場共命運,自然也就能在人類智力所及的范圍內,通過概念、理論和套路,與各種現實法則相勾嵌。若是前者,作家需要走出技術窄門,完成對狹隘的專業主義的超越;若是后者,作家需要重視各種已經獲得世俗成功的寫作之法,深耕各種技術套路。
不過,對于多數作家來說,精神性和現實性并無清晰的界限,而是相互糾纏在一起。因此,討論寫作是不是一種專業,也就沒有什么意義了。倘若真有意義,就在于我們借助這種討論,明晰了對寫作本身的某種看法,同時也增加了辨識真假寫作的一點能力。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不管在知識和手藝上是否構成一種專業,至少在職業上已經是一個龐大的行業圈子,一個利益可觀的社會空間。于是,有些人混跡在這個行當里,識得些字,懂得些遣詞造句的方法,就以作家自居了。他們深諳兩邊倒的辯證法:當有人說寫作是一種專業時,他們就削尖了腦袋去上幾堂寫作課,加入幾個協會,獲得幾本證書,以此加持自己的專業身份;當有人說寫作不是一種專業時,他們更是增加了無知者無畏的勇氣,以“功夫在詩外”為借口,充當起行業權威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