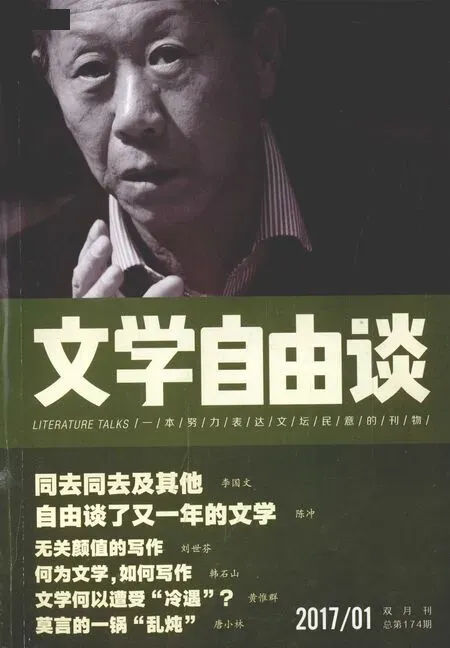妄分軒輊的“危險”
陳歆耕
妄分軒輊的“危險”
陳歆耕
2016 年,中國學界的壓軸之作問世,這是一部向莎士比亞與湯顯祖致敬的最為厚重的理論建構(gòu)。
四百年前 (公元 1616 年), 人類星空有兩顆璀璨的巨星隕落。他們分屬東西方,然而都是文學史上不朽的巨子。穿越數(shù)個世紀,人們?nèi)匀辉趧≡汉蜁邢硎芩麄兊木駝?chuàng)造。 在此刻,想起他們紀念他們品味他們,是出自我們內(nèi)心的自然生發(fā),而非某個外力需要來擦拭遮蔽著他們的塵埃。對他們的記憶,不需要人為地喚醒。 他們穿過歲月和種種“偏見”,仍活在當下。
就在此刻,評論家李建軍先生用一部 30 多萬字的專著——《并世雙星: 莎士比亞與湯顯祖》(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2016年 10 月版)——來品評他們的藝術成就和內(nèi)蘊, 無疑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事。我有幸成為這部書的首批讀者。當然,我也毫不諱言初獲新書的擔心,擔心這部出版社“命題”的書,它進入我們視野的理由僅僅是“紀念”。 讀畢全書,我的“擔心”被驚喜所取代。 建軍先生在這部書中傾注全部心力,揮灑才情,使得這部理論專著成為他多年閱讀思考、文學批評積累的一次爆發(fā)和飛躍。這部書是理論的,但表達卻又是充滿激情和詩意的,新見迭出,文采斐然,文氣貫通——猶如瀑布,飛流直瀉。 即便是望理論而生畏的閱讀者,也可以如同進劇院欣賞《羅密歐與朱麗葉》和《牡丹亭》一樣,輕松地跟隨他一起,進入兩位巨星的精神世界。
讀此著,最讓我受到啟發(fā)的是,作者提出了一個學界未強烈意識到的重大問題;這是不同語言在轉(zhuǎn)譯過程中無可避免的一個問題,即不同語種之間轉(zhuǎn)譯的困境。 因為不同地域、民族創(chuàng)造的不同語言,其中都會蘊含著該民族獨有的遺傳密碼、人文信息、表述方式。 有些語言表達在本民族人民中,是只可意會無法言傳的,更何況用另一種語言來傳遞。因此,無論英譯漢,還是漢譯英,在轉(zhuǎn)譯過程中都必然會產(chǎn)生信息損耗的狀況。作者特別強調(diào)了漢語言文學作品轉(zhuǎn)譯成其他文字的難度。 他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語言,都表現(xiàn)出對翻譯的反抗和不服從的姿態(tài)……深蘊在文學語言深處的美感和詩性意味,很難被翻譯和轉(zhuǎn)化到另一種語言中去。作為一種‘深度語言’,漢語對翻譯的抵抗性似乎更強。”由此帶來的狀況是,我們在讀他國翻譯過來的著作,以及他國讀者讀漢語文學作品,之間有無法消解的“隔”。莎士比亞與湯顯祖都是偉大的劇作家,但在世界范圍的影響或有強弱,其中就有翻譯帶來的障礙。 無法想象,湯顯祖那些典雅、細膩、深刻,充滿馥郁詩性的文字,翻譯成英文該如何表述。 “若如玉茗四夢’,其文字之佳,直是趙璧隨珠,一語一字,皆耐人尋味。 ”吳梅《顧曲塵談》)如此充滿“微意象”的文字,如何譯成其他語種而不失其味?
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會坦然地面對包括湯顯祖這樣的中國最為經(jīng)典的作家的作品,為何很難產(chǎn)生世界性的影響?建軍先生提醒學界:“我們無須為如何幫他‘走出去’而煞費心思和焦慮不安。”我想接著說的是,一個中國作家的文學成就,恐怕也不能用能否“走出去”來衡量。他的文學成就所抵達的高度,完全取決于他在本國人民心中的認同度。經(jīng)過翻譯的文本,往往與它的原貌大相徑庭;它們是經(jīng)過不同語言再創(chuàng)造的文本。 因而,一個好的翻譯,可以把三流作家翻譯成一流作家;同樣,一個差的翻譯,也可能把一流作家翻譯成三流作家。莎士比亞在漢語世界的影響力,得益于朱生豪先生精彩的譯文;那么,誰能擔當英語世界的湯顯祖的“朱生豪”呢? 由此想到,我們的文化自信,似乎也無須建構(gòu)在漢語言文學作品在世界范圍的接受度上。賽珍珠曾經(jīng)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臺上,高度贊譽中國四大古典名著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說。她的評價之所以有說服力,是因為她曾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年,能夠深刻領會漢語言文字的魅力;同時,她又是諳熟英語的美國作家。
這樣一個基本認知,成為建軍先生構(gòu)建《并世雙星: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理論框架的基石。在品評這兩位巨星的文學成就時,他時分時合,對他們各自所處時代的特征及與創(chuàng)作、命運、生活的關聯(lián),對他們的戲劇文本蘊含的深刻的思想內(nèi)容、精神向度、美學理念,對他們塑造人物的不同技藝,對他們偉大的人格形象,都進行了精到的評析。他不斷地尋找,不斷地開掘,不斷地發(fā)現(xiàn),然后對他們的共同點和異質(zhì)點,進行客觀的鑒賞和論說,卻絕少如某些學者那樣,在他們之間妄分軒輊。 論異同,卻不論高下。 “蘭有秀兮菊有芳”,他們都是人世間絕佳的風景。 對兩座聳立在不同地域的山峰,褒貶失當,則陷虛妄。難能可貴的是,建軍先生在品評他們的文學成就時,既對他們的藝術高度給予充分闡釋,同時也客觀地綜述了他們在不同疆域引發(fā)的巨大爭議。面對爭議,作者用現(xiàn)代學者的眼光,對其爭議的核心焦點進行了深度剖析并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引我深思的是,兩位大師級的作家、學者,曾對莎士比亞和湯顯祖有過極為尖刻乃至否定性的批評——在托爾斯泰眼中,“不僅不能把莎士比亞看作偉大的、天才的作家,甚至不能看作最平常的文人。”“莎士比亞享有的無可爭辯的天才的偉大作家的聲望,以及他迫使當代作家向他效顰,迫使讀者和觀眾歪曲了自己的審美的和倫理的見解,在他的作品中尋找不存在的優(yōu)點,像所有的謊言一樣,是巨大的禍害。”寫過《宋元戲曲史》的王國維先生,對湯顯祖也作出類似的批評,他認為,戲曲在“明以后無足取”:“元曲為活文學,明清之曲,死文學也。”“湯氏才思,誠一時之雋;然較之元人,顯有人工與自然之別。故余謂北劇南戲限于元代,非過為苛論也。”面對類似對兩位偉大戲劇家的尖刻批評,同樣也曾尖刻批評過許多當代名家的建軍先生,則顯得雍容大度和理智客觀。 他不是簡單地為莎、湯回護,而是深入分析批評者的美學思想和趣味,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偏見”。對“偏見”,他有態(tài)度,卻也不過多辯駁,而是綜述各家觀點,讓讀者去做延伸思考。
托爾斯泰和王國維對兩位同樣是大師級戲劇家的嚴苛批評,讓我想到了另一個問題:作家有三六九等,批評家也有三六九等。 當一位頂級的批評家批評一位作家時,作家應會想到,相比較那些三流批評家的廉價表揚,能夠享受他的批評,其實應該感到榮幸;因為進入他的視野也是需要“門檻”的。
在品讀本著時,我的思維也不斷地被撞出火花。我不斷地在書的頁邊寫下自己的感受,有些感受是可以另行撰文,獨立成篇的。 建軍先生的評析,有時也有我并不認同的“偏見”,但我愿意享受一部充滿卓見但也不乏“偏見”的讓人提神的好書,而不會讓時光耗費在那些通篇皆正確“廢話”的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