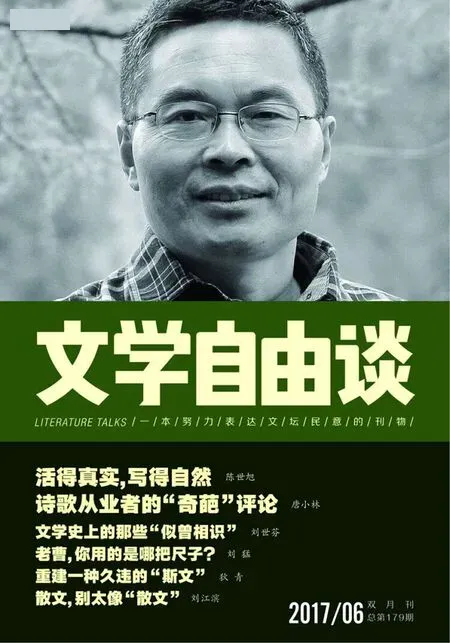朝霞初暈的“早晨”
周嬰戈
朝霞初暈的“早晨”
周嬰戈
2017年是恢復高考40周年。1977年,國家意識到恢復高考、培養人才的緊迫感,遂在當年12月打開了進入高等院校的考場之門,冬日的陽光,在那個月溫暖了大江南北。幾十年過去了,對1978年2月入校、但仍屬于“七七級”的“文革”后首批大學生們來說,那曾經的校園生活,恍如昨日。于是,各種記寫當年校園青春的紀念文集接踵而出,如南開大學中文系七七級的《青春回響》等。這其中,我想提一下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這本書,不必說70萬字、上百幅老照片的厚重,不必說北京大學文學七七級四十余位學子的深情文字,也不必說十余位學者教授、文學宿將的厚愛,僅書中收錄的四期班刊《早晨》油印雜志,已經讓我們回味起曙光初現的那份紅暈和誘惑了。
文學,變革前的曙光。就像《新青年》雜志和小說《狂人日記》,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北大學生走向街頭時懷揣的星火,文學在1978年的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的“前言”說,那個春天坐進北大文學課堂的青年,“多是煤礦、油田、田野、毛皮廠的底層青年”,他們唯一共同的精神特質就是“殺不滅的文學細胞”。“歷史的轉折使‘文學’再次承擔起‘新的國民之精神’的使命”,“遂有油印刊物《早晨》的問世,遂有卷入當年文學論爭的種種活動,遂有推動文學新潮的眾多作品發表”。文學,對北大文學七七級的48同學來說,“不再是一種專業,而成了他們終身的志業”。
還是從厚達574頁的書中去領受那《早晨》的光芒吧。全書分同學、老師、記錄三大部分,歸入“記錄”部分的四期的《早晨》,呈現出最初的原始面貌,此書“后記”自稱是“為了留住我們過往的記憶”。這記憶,就是全身心地“弄文學”!雖然有“中文系是培養學者的地方”“進階要看英語和文學史的考分”等告誡,但是,文學七七級與學弟學妹們顯著的不同在于,他們“充分呈現了一個特殊歷史時期一代有些特殊的學子的歷史特征:道義感、承擔勇氣、對社會的關懷、創造歷史的豪邁以及刻苦的思索與執著的探索”。這是對他們極準確的評價,也是他們自身無法掙脫的品格。他們就是要把文學“弄”起來,在課堂筆記之外,用他們曾經所處的“底層社會”的浸染,來把文學“弄”活。他們太熟悉社會生活那個課堂了,他們在那里浸潤了十年,而以后的大學生,已無法有那種群體經歷。歷史使然,《早晨》不可阻擋地在東方露出霞光,文學創作的勢頭無可遏制地在七七級中涌現,陳建功、黃蓓佳、王小平、梁左、查建英……就這樣進入甚至影響著文壇。
北大1980級文學專業的吳曉東是一位學者,他準確地評價了《早晨》的歷史位置:“《早晨》不僅是純粹的校園文學雜志,它既留有一個大時代的歷史烙印,也深深介入了中國的社會政治與行進中的歷史。”今天,我們通過《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來讀《早晨》的作品,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種對過往歷史的“介入”,僅從那些作品的名稱——《流水彎彎》《夏天最后的玫瑰》《夕陽下的江水》《小罪犯》等,你就體味到作者們心緒的蒼茫和“底層浸染”的蒼勁;詩歌《鋼的音樂》《沙棗》《夯歌》,彌漫著粉塵與泥漿,毫無半點兒未名湖的月影垂柳;已逝去的吳北玲還有一部長篇小說構想,打算寫盡“陜北苦人們的那個苦”,那幅著名的油畫《父親》恐怕就是這部長篇最好的詮釋,最終她為《早晨》遞上了一篇短篇小說……
1956年,北大文學專業出過《紅樓》學生刊物,從它的成員——激情的謝冕、單純的溫小鈺、直率的林昭、坎坷的江楓……你就知道《紅樓》在一年后的風暴中會有什么遭遇。《早晨》依然續寫著《紅樓》的單純與直率。謝冕把激情又融進了《早晨》,成為《早晨》唯一的教師成員。后來,當謝冕從助教晉升為碩士生導師時,《早晨》的主編黃子平成了謝冕的碩士生。
《早晨》是《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一書中最鮮亮的部分,換句話說,《早晨》顯現出了北大文學七七級的性格本相和歷史坐標。后來,黃子平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查資料時,驚奇地發現,該館竟然收藏有一套完整的《早晨》!他“當場傻在那里沒動”。
《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為我們保存的那份蒼勁的文學,正可以窺見到當年熱血的流動和有血色朝霞的早晨。每個新的一天,都是從早晨開始……
《我帶著遼闊的悲喜》
林馥娜著 陽光出版社
林馥娜的詩歌囊括著多姿的面孔、多元的觸角和豐沛的情感,在物我轉換之間尋找到優雅得體的姿態和精神的微光。在展示生活的熱情和渴望之際,她的有所思內化為感性又細密的語言觀照,在不緊不慢之處獲得生命的喜悅和自我的覺醒。她的詩歌因為對生活范疇的把握、人物命運的深悟,從而在蒼茫人世里獲得了生命的律動和精神層面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