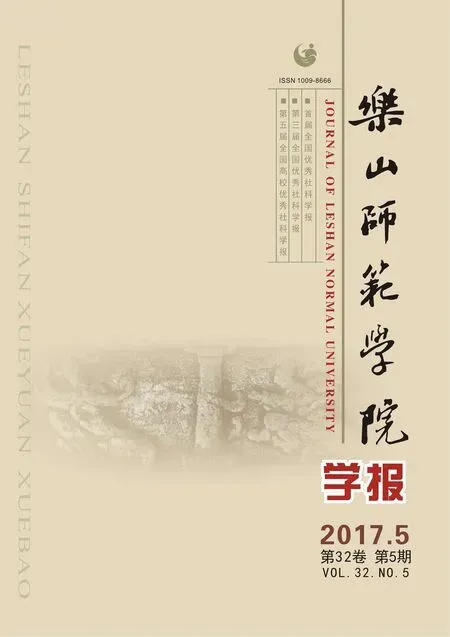田漢佚文兩篇
金傳勝
(南京大學 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0023)
田漢佚文兩篇
金傳勝
(南京大學 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0023)
新近發現田漢20世紀20年代在長沙、上海兩次講演的記錄稿,按學界慣例皆系田漢的佚文。兩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與研究田漢早年的文學觀與戲劇觀,更是研究田漢戲劇教育活動的重要史料。
田漢;佚文;講演稿
田漢是公認的中國現代戲劇奠基人之一,在戲劇、電影、詩歌、散文、文藝批評等領域皆卓有建樹。花山文藝出版社早在2000年已出版《田漢全集》,共20卷830余萬字,保存了大量文學史料,成為研究田漢思想與創作的較為權威的引文來源,具有彌足珍貴的文獻價值。據筆者掌握的資料,《田漢全集》出版后,僅有學者胡靜對其有所補遺,披露了《南國來矣》《時代與藝術》兩篇集外佚文[1],其他輯佚文章并不多見。筆者新近看到田漢20世紀20年代在長沙、上海兩次學術講演的記錄稿,分別為《研究文學的出發點》《戲劇的本質及其新趨勢》,失收于《田漢全集》,《田漢年譜》《田漢評傳》等研究資料都未見提及,按學界慣例當系田漢佚文。今將兩文輯錄整理于此,并略作說明與探究,以供學術界參考。
一、佚文一:《研究文學的出發點》
今晚承攖寧學會招待,要我講點關于文學的事情,在我是很僭越的;雖常研究文學,但是回國以來,為事物所累,沒有許多時候看書,恐怕沒有好意見貢獻各位。
本來約定的題目是《兩種寫群眾的戲劇》,原意是講德國的Hauptmann’s“Die Wieber”and Galsworth’s“Strife”。戲劇本不止這兩種,因為近日忙于編黃花崗腳本,無暇找參考的書籍,沒有充分的預備,只好候有機會再來研究;或做成文章發表。
因為貴會組織不久,所以我今晚把研究文學的出發點講講。文學的本質是什么?若詳細講來,短時間斷難做到,今晚我只能說個大概。
本來文學Literature有三種反應 :1)作者個性。2)時代風潮。3)國民性即文學之屬性。無論什么事物都有二體:即屬性與本體。來描寫一物象時,其材料不過兩種:即自然與人生;凡描寫事件,總離不了這二種。譬如這里有把椅子,是自然;今晚這個演說會,把它描寫出來,就是人生。處置材料的手段如何呢?現在舉例來說明:
一個藝術家畫孫文的相,一點不移的畫出來,這是印象派(Impressionisme)的畫法;法國印象派是點彩主義,拿顏色來表光線,與網膜相終始;譬如畫一張三種顏色的圖,把一色一色點上,這是科學的;不是文學的真體。
印象派又分三種:1)印象派(Impressionisme),2)新印象派(New Impressionisme),3)后期印象派(Post Impressionisme)。到后來就不同,覺得對于藝術的態度不可全是再現(Representation),想像依原形畫出極詳;因再現僅有相對的價值;如所畫之像,若使不識者觀之,便不明白,因為物象加進個性去了。真正的藝術家所畫孫文的像,我們可以由我看出孫文的個性與作者的個性。因作者對于孫文,有很深的了解,懂得他的個性;作者的人格與孫文的人格相接近,由作者的個性把它傳達出來。凡藝術家畫圖,須擇其重要部分畫出,方有個性,譬如畫一中校舍斷不能全部描寫,如飛機在空中所攝之全影,那是沒有個性;總要拿出好的一部分,來表示它的個性。所以藝術家不會千篇一律,因作者有個性,孫文也有個性,他倆的個性,起一種共鳴,產出來的藝術名 ,使人看了不僅明了作者的個性,且能明了孫文的個性;且這種藝術品,不獨此時有價值,即垂之永久,仍有價值,此所謂絕對的價值:藝術家非求其再現,并非徒與網膜相終始,是求其表現,這是第一要緊的。
現在試舉例來說明另一問題——自然與人生。
藝術家對于自然與人生的觀察,須知觀察法。如作詩與愛情都是重要,我們對此方法,一是知,一是愛。我們要描寫自然,不能不懂自然,描寫電燈,不能不研究電學,所謂知(To understand)是很重要的。且藝術家對于人生的材料,越懂越愛。如朋友然,不相識者必不相愛,須平日研究期性格,使兩者人格漸漸接近;比如我好文學,他也好文學,我好運動,他也好運動,我愛花,月,他也愛花,月……兩者相知,始發生愛;到了這種地步,幾乎成為一個人,感情便會分外的密切了。文學家亦然,如他想描寫花,月,愛……等,便須埋身于自然界中,才能表現花,月,愛……與自己的個性出來。今舉英國浪漫主義 Romanticism的文學家丁尼生(Lord Alfred Tennyson)(1809—1892)的“Flower In The Crannied Wall”一詩如下:
Flower in the crannied Wall,
I pluck you out of the crannies;
Hold you here,root and all in my hand,
Little flower……but if I could understand what you are,root and all,and all in all,
I should know what God and man is.
我們看了這首詩,可明白詩人對于自然的態度應該怎樣了。Tennyson看見斷壁中一朵小花,就摘下來觀察,即中國古人之所謂格物;惟其知然后才了解它。但知有二種:一是內在的(inward),一是外表的(outward)。如觀察一花,只視其花瓣,花冠,花萼……等,不過是外界的觀察,只能使人冷靜,而不能引起熱情。真的生命,是須用慧眼(Mind-eye)來觀察的。
詩人之宗教的觀察法有二:一是有神論(Theism),一是泛神論(Pantheism)。泛神論是一種說我們這世界上有超過自然的主宰,向后轉的說,神無所不至,此即所謂詩人觀察法。
藝術家描寫茶壺的時候,如果把它當作一件應用的東西看待,那就對于它不能生出愛。真正的藝術家,無論對于何種事物,都能看出神秘的純粹形式;宇宙萬物,都是有神秘和韌力的組織的,所以他對于茶壺,只注意直線,曲線,與光之跳舞等。英國有一個畫家有幾句話說:
How to see objects as pure forms is to see them as ends in themselves。
要看出物象的純式(Pure form)——如茶壺是有真生命的,超一切的實用的美的價值,是在其本身——我們應該不用肉眼(naked-eye)而用慧眼(mind-eye),因為肉眼是肉體的細胞組織的;慧眼才能看出物機 后面韌力的構成,才能看出真的好處來。其所以一般人不能見者,以其為習俗,小我主觀種種所蒙蔽,不能以慧眼去觀察;所看到的,僅是物體的表面。我們要用原始之眼與小兒之眼(child-eye)去觀察。如法國某畫家畫女人,以為巴黎女子是不純的,對于自然天天隔遠,他便跑到某島上與一女子結婚;以其不注意人工的文飾,故所畫她底像,絕不如巴黎女人,而更難顯出其兒童自由畫的狀態。近代自由畫運動,常利用天真爛漫的原始小兒之眼去觀察。因為這樣,比成人更能寫出真情。此外表現派的法國作家,甚至材料都寫原始人的生活。
我們須打破一切,而用慧眼去觀察物象,這是文學的運動;也就是講“知”。“愛”與“知”同來,如不知必不愛,我在前面已講過。比如愛一女子,愛其貌,則為網膜之愛,看出其人格之美,才是真愛;知是理性的。愛是情感的,知與愛極應調和,這是對于自然的態度,目的是內在的。可舉美國文學家Emerson,Ralph Waldo (1803—1882)的“The Rhodora”一詩于下:
In may,when sea-winds pierced our solitudes,
I found the fresh Rhodora in the woods,
Spreading itsleaflessbloomsin a damp nook,
To please the desert and the sluggish brook.
The purple petals,fallen in the pool,
Made the black water with their beauty gay;
Here might the red-bird come his plumes to cool,
And court the flower that cheapens his array.
Rhodora!if the sages ask thee why
This charm is wasted on the earth and sky,
Tell them,dear,that if eyes were made for seeing,
Then Beauty is its own excuse for being:
Why thou wert there,O rival of the rose!
I never thought to ask,I never knew:
But,in my simple ignorance,suppose,
The self-same Power that brought me there brought you.
這是說一種自然力來支配我們,同是宇宙的表現;他說我為何來塘邊?為來看花。為何來看花。為何來看花?因其美麗。為何因其美麗而來?那就連自己都不知道了。原來那是一種力(Power)所驅使。
真正藝術家之愛,無所不至,對于任何事物都愛,此為泛愛;如由親子,兄弟,夫婦之愛,推而至于朋友之愛,至泛人類之愛,至萬物之愛。因有強烈之愛,始有真文學出現,這種文學,是活的,不是死的。如一花是標本,一是畫,那末,畫是活的,因為可以看出它的生命來;標本是死的,因其僅有解剖之真,沒有綜合的美,而只是分類的罷了。如英國詩人Wordsworth,William(1770—1850)的“The Daffodils”一詩說:
The waves beside them danced,but they
Out-did the sparking waves in glee:——
A Poet could not but be gay
In such a jocund company!
I gazed,and gazed,but little thought
What wealth the show to me had brought:
For oft,when on my couch i lie
In vacant or in pensive mood,
They flash upon that inward eye
Which is the bliss of solitude;
And then my heart with pleasure fills,
And dances with the daffodils.
他是湖畔詩人,常見水仙花開得甚美,花在跳,波在舞。詩人有此良朋,故甚愛之。因詩人是藝術家,所以對于一花一物皆愛,因此,他雖注視花,但絕不想此物象于我之實生活——衣食住——有何好處。
中國人的墮落性就是實利性(Varied to me),凡事是要利己的;對于文學也是這樣,故常言“文以載道”,“詩三百篇輔王教之不足”,“……”;這樣衍成為風俗,凡文學總要求與人類發生關系;中國文學不發達,就是原于此。所以幾千年來,中國無純正的文學,哲學,及長篇作品,惟其研究是有因的,如讀者為求功名,所以獨立的研究,為創作的創作,便永遠沒有發達。故我們現在要想研究文學,就切不要先為實生活所蒙蔽了。
人生本來極自由的,赤裸裸的,把衣一穿便束縛了;要到真絕對的自由時,才有好的作品。如果是這樣的作品,讀之自己亦因而感動,他人讀之,精神亦因而提高;所以文學雖為內在的,但其結果,每生社會上之價值。然而作者是不過為表現自己不得已的沖動,絕不曾顧及在社會之價值是如何的。此為我們研究文學的人所首當明白。
今晚承各位在聽,因精神不足,只好候有機會,再來作長期的討論。
該講演稿《研究文學的出發點》刊載于1925年7月10日《嬰寧月刊》第4期,署“田漢先生在本會講孔慕農蔣參寥合記”。《嬰寧月刊》1925年2月在長沙創刊,有月刊和半月刊兩種出版形式,出版四期后休刊,不久復刊,也使用過《攖寧月刊》這一刊名。該刊由攖寧學會發行部發行,攖寧學會文學研究部編輯,屬于文學刊物。通訊處是湖南第一中學校蔣德恒。攖寧學會是一個研究各種學術的團體,會員主要來自湖南第一中學。草創之時僅成立了一個文學研究部,后又成立美術研究部、史地研究部、生物研究部、語言練習部。茅盾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中指出,中國新文學自1922年開始,進入了全國性的文學團體和小型文藝期刊蓬勃發展的時代。在列舉各地文學社團活動時,他便提到了湖南長沙的攖寧學會與《攖寧》。可見,當時攖寧學會與《攖寧月刊》名氣不小,其影響并不僅僅限于長沙,得到了茅盾等的關注。
從開場白可知,此次演講是田漢應攖寧學會之邀而作,地點應在第一中學校內。本來約定的講題是《兩種寫群眾的戲劇》,擬介紹霍普特曼的《織工》與高爾斯華綏的《爭斗》,由于田漢當時正忙于創作《黃花崗》,不便查閱文獻,便換成文學研究的話題。考慮到攖寧學會文學研究部是一個學術性組織,田漢的講演顯然具有實際指導意義。兩位記錄者都是攖寧學會會員,結尾尚有一段附識:“此稿記出后,因本刊急于付梓,未能待田先生修改,謬誤之處,在所不免,祈田先生和讀者原諒!記者附識。”這說明講稿并未經演講者本人審閱,嚴格意義上系田漢的一篇“準佚文”。由于文中存在大量外文,或許田漢事先曾將演講大綱散發給聽眾。同時,亦可據此推斷此次演講的大致時間是1925年6月。
1925年春,田漢在長沙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任國文教員,與趙景深、汪馥泉、王魯彥、葉鼎洛等共事,共同創辦了綠波社與《瀟湘綠波》刊物。根據趙景深的回憶,田漢在長沙任教時,“因為潛心于西洋文學,所以講‘國文’時也就專講文藝思潮和西洋文學史,尤其是戲劇,因此被學生們戲稱為外國國文教員。”[2]72《研究文學的出發點》這篇講稿即可反映出,當時的田漢對于西方文藝思潮確實興趣濃厚。作為一位飽含詩情的作家,田漢對于歐美浪漫主義、超驗主義詩歌甚為稔熟、傾心,推崇包含象征主義、表現主義等思潮在內的新浪漫主義文學。一方面,田漢表達了對將藝術功利化的“文以載道”觀的不滿,強調藝術創作要運用詩人觀察法,要用“原始之眼與小兒之眼(childeye)”或曰“慧眼(mind-eye)”去觀察事物背后的“神秘和韌力”、“物象的純式”,認為“藝術家非求其再現,并非徒與網膜相終始,是求其表現,這是第一要緊的”;只有達到絕對的自由,才有好作品的誕生。這與他在《新羅曼主義及其他》一文中將新羅曼主義歸納為“想要從眼睛看得到的物的世界,去窺破眼睛看不到的靈的世界,由感覺所能接觸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覺的世界的一種努力”[3]168的觀點相呼應。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他關于調和“知”與“愛”即理性與感性的思考,以及他雖倡言“為創作的創作”,但在文學藝術的內在價值之外,并不否認其“社會上之價值”。同時,田漢對于霍普特曼《織工》與高爾斯華綏《爭斗》的關注更是立足于戲劇的“寫群眾”傾向。這種關注一直持續,只是到了1937年,田漢轉而在《關于寫作態度——〈國民公敵〉與〈爭強〉》一文中批判《爭強》(即《爭斗》)中“近于超歷史的幻想的性格”[3]554了。
二、佚文二:《戲劇的本質及其新趨勢》
今天的講題,甚為廣泛,我又以事忙,不能有充分的預備,但將平日常常講的話,對諸君隨便說說。
戲劇我們所以研究他,因為他與生活極有關系,如果與我們的生活沒有關系,我固不必來講,諸君亦無須來聽了。
戲劇發達,東西各國都是一個樣子。例如中國的戲劇起于“巫”,希臘的戲劇起于“酒神祭”,都是拿來娛神的。希臘劇最初是一人做的,同時又有Chorus在他旁邊。后來漸漸由祭長一人的進步,分為二人,就是由“獨白”Monologue進為“對話”Dialogue,這是講希臘劇。至于中國戲劇,起源很早,有人說屈原的《離騷》就為最初的獨話劇。其所作的九歌,尤為原始戲劇的典型。湘人信鬼,往往打鼓敲鑼,且歌且舞,屈原見了,愛其歌舞之形,而恨言詞過于鄙俚。所以他就大加修飾,而成九歌,九歌原型,實在包含言詞,動作,音樂三者,實為一種Ballad Dance。不過后來動作音樂皆不可復識,單剩言詞了。
后來由神的戲劇,進而為人的戲劇;再由個人的娛樂,進而為群眾的娛樂,“獨樂樂不如與眾樂樂”。從前戲劇僅僅為某部分人看得見的,現在漸漸普及到一班了。例如俄國戲劇,不獨國家設有許多公共劇場,不獨學校里有戲劇團體,即是所謂立于“藝術”反對地位的“軍隊”里(例如我國在戰爭的時候一般軍人往往四散鉆進戲園不出分文叫吶看戲以致戲園關閉)也差不多每一個軍隊,都附有一個舞臺由軍人自己做戲,自己娛樂。像這樣無論古今,無論東西,無論普通市民,及學校軍隊,都對于戲劇有這樣熱烈的要求,可知他一定與我們人生有極深的關系,是無疑了。
“人生”Life,什么叫作“人生”?說來像似非常渺茫。其實這個“人生”,我們可以用“生”,“長”,“滅”,三字包括一切。這三個字是法國的名小說家Anatole France,在一篇小說中借一老教授的口中指示人類歷史的精義的。至于這篇小說內容,大致述一老教授有個學生,當其繼承皇位時候,年紀很輕,但是他想沒有學識,所以他就請老教授把世界的歷史教他。這老教授費了三十年的工夫,收集世界歷史材料,訂成了幾百本。皇帝見了,非常驚異,這許多的歷史,怎的看得了,請簡單一些。老教授又費了五年,刪成了幾十本,依然太多;又是五年,變成十多本了,可是皇帝年紀一天老似一天,即使十幾本的歷史,亦看不了。后來老教授再刪改成為一本,但皇帝已是氣息奄奄行將就木。不能看了,所以結果一本歷史,依舊沒有看完。在他瞑目以前,老教授就把“生”“長”“滅”三字告訴了他,什么“人生”,什么“歷史”,均不外這三字。其實這三個字還嫌多了,有“生”“死”二字就夠了。所謂“生”有二種,即孔子的所謂“食”“色”。食為保己,色為保種。這是人類極根本的要求。因為保己,就須勞動;因為保種,就須有愛。除此之外,其次支配人類的心靈的,便是死的問題。所以以前的戲劇,無不是為“愛”與“死”,換一句話,“愛”與“死”是前此戲劇最重要的題目,到了近代境遇悲劇發達以來,勞動與饑餓的問題,又為戲劇家興味的中心了。
悲劇的性質,分為三種:A運命悲劇。B性格悲劇。C境遇悲劇。以前的戲劇家把“運命”與“性格”看得極其重要,凡悲劇的責任在自己,如挨饑受餓由自己懶惰而起時,便是性格悲劇;自己的努力,敵不過運命的力量,如一個人雖日夜的勤勞,而仍無飽飯吃,終且至于犯罪,其悲劇的責任不在自己,是謂運命悲劇。例如我國古人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又謂人當“樂天知命”,這可以代表中國的運命觀念。后來卻發見了一個新天地了,人但凡“勤勉”,便應該得著食物,得著妻子。倘是雖然怎樣“勤勉”,依舊沒有飯吃,沒有妻子,那并不是運命性格不好的原故,乃是境遇,即社會組織不良故,所以近代戲劇多對于舊的社會,大下攻擊。在戲劇方面言,希臘劇是代表運命悲劇;沙士比亞Shakespeare劇是代表性格悲劇;易卜生Ibsen劇代表境遇悲劇。他們代表那種悲劇,都可以從戲劇里看出來。舉一個例沙士比亞的麥克比絲Macbeth的Ambition可以知道他是代表性格悲劇。再如德國的 Hauptman主張Generic的有一次他愛了一個女子,很想結婚。但因女子的祖父是有酒毒的,倘是娶了有酒毒的女子為妻子,那不是與他所主張的Generic沖突了嗎?結果寧愿犧牲可愛的女子,于是給一封信與女子,自己逃了。可是女子一見信后,極為驚駭,終于自殺。為什么呢?境遇使然。這可以代表境遇悲劇。但自從“表現主義”出,前此自然科學的人生觀又多少改變了。表現派的戲劇,主張人是獨立的。從前的戲劇家總覺得人是運命性格境遇的奴隸,非獨立的。表現派則謂人當有高尚的情操Moral,有強固的意志Will,支配一切,而不受別的運命性格境遇——支配的。表現派起于德國,我們知道德國在世界大戰爭以前,固然強盛。但在大戰以后,情形大不大不同了,可憐極了。奪取外國的食物女子的工具,——槍炮,海軍,陸軍,飛船,與潛水艇,——均被人破壞或限制。假使人為了境遇的奴隸,應順從境遇時,德人早應心灰意懶自殺了,但剛毅不拔的德國人,覺得物質方面,雖不可靠,而發起見Mind power的偉大了。他們要以意志力去征服境遇。現代人不甘為境遇的犧牲,必欲進而以崇高優美的情意,支配境遇以及其他一切,這大約便是戲劇界的新趨勢了!
十五,五,十二。
該講詞刊發于1926年5月24日《國大周刊》第26期,署“田漢先生講殷芝芳筆記”。《國大周刊》1925年10月創刊于上海,1927年10月第45期停刊,由上海國民大學國大周刊社編輯出版,屬于校刊。此前5月17日《國大周刊》第25期的“學術講演會消息”一欄,已對田漢的蒞校演講作了報道:“本校本周學術講演者,系戲劇研究會諸君特請當世文學專家田漢先生演講‘戲劇之本質及其新趨勢’一題。是日(五月十二日)午后,適值大雨,田先生仍不辭泥濘而來,聽者益為興奮,到會約百余人。該題記錄,已寄請田先生校定,大約在廿六期本刊,方與讀者晤面云。”由是可知,田漢此次演說作于5月12日午后,是應上海國民大學戲劇研究會(又稱“戲劇研究社”)之邀請,講稿發表前已由田漢本人審訂。
《戲劇的本質及其新趨勢》主要闡述了中西戲劇的起源與歷史,發表了對于戲劇與人生關系的思考,進而將悲劇分為運命悲劇、性格悲劇、境遇悲劇,分析了三種悲劇類型的代表與特征,最后介紹了以德國表現派戲劇為代表的歐洲戲劇的新趨勢。田漢的此次講演著力于戲劇理論的講授與傳播,以開闊的學術視野統攝中西戲劇的衍變與發展,同時不乏比較文學的眼光,讓聽眾較為清晰地了解到中西戲劇文化特別是悲劇觀念的異同之處。尤為精彩的地方,是結合社會背景與政治語境,闡釋了表現派戲劇起源于德國的緣由。這表明田漢當時的戲劇觀念并不是完全的蹈空凌虛,脫離于社會人生,與他開場即聲稱戲劇與生活的關聯性相呼應。
除國民大學外,當時任教于上海大學、大夏大學的田漢,還在其他學校作過學術講演,如《申報》1926年5月7日“教育信息”版有《遠東大學請田漢演講》簡訊,全文如下:“遠東大學于前日下午二時,請田漢君演講,題為‘近代戲劇底趨勢’,首由事務長陳景新君致介紹辭,嗣由田君演講,略謂戲劇的本質對于文學上之位置極為重要,可分二種,即詩式與戲式,前者主熱烈的后者主冷靜的,至戲劇的基礎,是在真實生活,不能作偽,所以表演戲劇僅悲劇最易感動,其種類有三:1)命運悲劇、2)性格悲劇、3)境遇悲劇云云,末由訓育主任蔣達文致謝辭畢,遂進茶點而散。”該報道說明田漢于1926年5月5日在上海遠東大學作過《近代戲劇底趨勢》講演,內容與一周后在國民大學的講演相近,遺憾的是完整的講稿迄今未見。
此外,1946年9月18日《今日東北》第2卷第5期刊登了一篇署名“田漢”的文章《殺人不眨眼的盛世才》,敘述了作者與盛世才的一次會面。文中透露了作者可能是《今日東北》的創辦者或編輯,由于現有材料中還沒有田漢參與該刊與今日東北社的記載,所以該文歸屬問題只能暫時存疑,有待于方家解惑。
三、結語
以上兩篇講稿佚文的發現,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與考察早期田漢的文學觀與戲劇觀,更是研究田漢戲劇教育活動及生平行藏的重要史料。包括田漢在內的許多現代戲劇家、文學家、學者,并不僅僅坐在書齋中進行創作或研究,同時也以教學、演講、編輯、出版等活動,推動了新文學新文化在社會大眾中的傳播,使新文學積極地介入、引導人們的精神生活,提升了讀者或聽眾的文學素質與文化修養,切實發揮了文藝的文化功效與社會價值。這些課題尚未得到學界的應有重視,相關史料的挖掘與研究工作還有進一步拓展的余地。
注釋:
①指德國劇作家霍普特曼的《織工》和英國劇作家高爾斯華綏的《爭斗》。德文Wieber應作Weber。
②“反應”應作“反映”。
③“名”應為“品”。
④“機”疑為“體”。
⑤此句中的兩個“他”應作“它”。
⑥“班”應為“般”。
⑦“他”應為“它”。
⑧“發見”現作“發現”。
⑨“原故”現作“緣故”。
⑩此處應有標點,Hauptman應寫作Hauptmann,Generic疑為德文Genetik(遺傳學)。
?“他”實際應指霍普特曼劇本《日出之前》中的男主人公洛特。
?“起”疑為衍字。
[1]胡靜.新發現的田漢佚文《南國來矣》《時代與藝術》[J].新文學史料,2004(4).
[2]張向華.田漢年譜[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
[3]田漢.田漢年譜:第14卷[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
Two Uncollected Works of Tian Han
JIN Chuɑnshenɡ
(Center for Research of Chinese New Citeratur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23,China)
Two newly-discovered records of speeches,which were delivered by Tian Han in Changsha and Shanghai during the 1920’s,are called Tian Han’s uncollected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academic convention.These two articles are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study Tian Han's early literary and drama concept,and 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ian Han’s drama education.
Tian Han;Uncollected Articles;Speech Records
I206.6
A
1009-8666(2017)05-0038-07
10.16069/j.cnki.51-1610/g4.2017.05.006
[責任編輯、校對:王興全]
2016-09-05
金傳勝(1988—),男,安徽蕪湖人。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