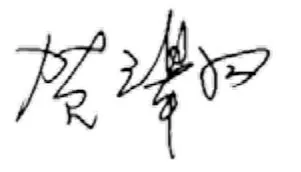考古學是文化遺產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代考古學有著文物學、社會歷史學、文化學、文化遺產學乃至科技學的不同取向,這是由考古學自身的學科內涵、特性及其自身的發展邏輯所決定的。
16世紀前后是考古學的早期階段,它主要以“古物”或“文物”為發掘和研究對象,直到1764年,溫克爾曼發表《古代藝術史》,主要還是以古物造型演變及其編年體系作為學術目標;19世紀中葉,湯姆森提出史前史“三個時代說”,還是依據文物的質地和形態而做出的時代特征認定。19世紀中下葉,考古學趨向成熟,但對文物的發現和編年研究、對社會歷史的復原與修補仍然是學科的主要任務。20世紀初,米勒在《歐洲史前史》一書中使用了“文化”這一概念指代考古遺物,此后,經過科辛納、柴爾德等的探索,考古學家最終選擇了“考古學文化”這樣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論作為新的學術目標,許多科技手段也逐漸為考古學所廣泛采用,“田野資料”擴充到“文物”之外的一切考古發現。
從“文物”到“文化”,從“古物學”、“社會歷史考古學”到“文化考古學”、“科技考古學”,這個過程是考古學史上的重要階段性特征和邏輯過程,也是考古學從文獻史學的附庸走向獨立學科的重要標志性成果。中國考古學同樣也有過這樣一個歷程。試想,如果不是“考古學文化”理論傳入,中國何以產生從“仰韶文化”的發現到目前數以百計的考古學文化的發現和建立?何以觀察到不同考古學文化的發生、發展及其背后不同空間、時間、人群對“文化”乃至“文明”的創造與推動?
我們感興趣的還有考古學的文化遺產學取向的發生。20世紀中葉以后,人類提出了“世界文化遺產”的事業方向,而此前考古學文化的研究,已經為之做了學術上的準備和鋪墊,由此,考古學自然就變成了文化遺產事業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世界遺產公約》中對“文化遺產”內容的界定包括三個方面:文物、建筑群、遺址,每一個方面都與考古學緊密相關。正是在這樣的內涵界定下,全球已經成功列入世遺名錄的項目中,有許多實際就是由考古學家們發現或發掘的考古項目轉化而成,如中國的殷墟、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秦始皇陵、元上都遺址等,其他國家也大概如此。近年來出現的世界文化遺產新類型如文化景觀、遺產線路、傳統運河、歷史城鎮和城鎮中心等,同樣也離不開考古學的參與。以“歷史城鎮和城鎮中心”為例,《世界遺產操作指南》中指出,符合申請條件的城區包括三種對象,其中第一種就是“無人居住但卻保留了令人信服的考古證據的城鎮”;“中國大運河”成功申報世界遺產的過程中,考古學為之作出了突出貢獻;“天山廊道”作為“遺產線路”列入世遺名錄,包含了多年來絲綢之路考古的諸多成果。國外亦有許多同樣案例。
考古學成為人類文化遺產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不僅是考古學學術功能上的拓展,同時還影響到考古學的學科定位和考古學家的行為模式。從人類現代文明發展需求而言,世界文化遺產一是對“可持續發展”及“生態文明”建設有著巨大的貢獻;二是能夠為人類“文化多樣性”事業發揮獨特作用。《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強調:“文化多樣性創造了一個多姿多彩的世界,它使人類有了更多的選擇,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價值觀,并因此成為各社區、各民族和各國可持續發展的一種主要推動力。”這些思想和目標促使當代考古學家不僅致力于不同時、空多樣性文化遺存的發現和研究,而且也按照“文化遺產”的理念,探索考古遺產涉及的“形式與設計、材料與物質、用途與功能、傳統與技術、地點與背景、精神與感情,以及它內在或外在因素”諸問題,同時還注重對發現對象的保護、保存、展示、利用,以確保能夠“代代相傳”。
今年是中國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誕生30年的日子,也是中國考古學成就作為“文化遺產”形態走向世界的重要紀念日,作為考古人,我們為自己能夠成為全球文化遺產事業的參與者而感到光榮,也更了解自己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在此我們必須說明,考古學發展進程中出現的階段性目標的變化并不是彼此否定的關系,而是互相包容、提升、深化的關系,今天,考古學多樣性的學科取向其實同時存在于不同考古學家的實踐之中,它們共同支撐著考古學的宏偉大廈,共同譜寫著考古學的輝煌篇章!